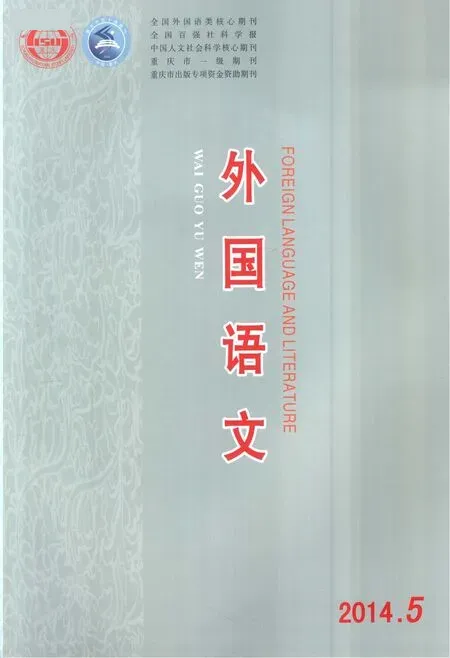迟到的帝国焦虑——论鸦片战争前“夷”字翻译中译者、文明话语与赞助人的互动
付 强
(四川外语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部,重庆 400031)
1.引言
近年来,刘禾(2008)有关跨语际实践的一系列论著不断在国内学界引发共鸣,质疑与争论。在2004年出版的The Clash of Empires一书中,刘禾教授将汉字“夷”的翻译过程放在“中国近代历史与整体世界秩序变化的关系这样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面来加以展开分析”(杨念群,2010)。她提出,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一直采用英文单字“foreigner”(外国人)来翻译汉字“夷”。(刘禾,2008:46)而从1832年开始,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slaff)等人推翻了以前的翻译惯例,改用barbarian(野蛮人)来译“夷”字。对于惯于将西方以外的社会视为野蛮的英国官员来说,“夷”这个在翻译中被人为加入暴力规训意味的字眼显然是荒谬的,极大地刺伤了帝国的自尊心。于是,衍指符号英夷/English barbarian成为了英国殖民地式伤害话语的一部分,也是英国人发动战争的法律依据。刘禾教授最后得出结论:我们不能把“夷”字看做是它自身可靠的词源依据,更不能将其简单视为中国人排斥外国人集体意识的证据。夷/i/barbarian的出现,“是大英帝国与大清国碰撞的结果”(刘禾,2008:131)。最终“夷”字的正确含义必须屈从于英文单词,而这一过程背后折射的是“国际关系在19世纪中的大转变,以及现代地缘政治的大转折”(刘禾,2008:131)。
刘禾(2008)的论述无疑给跨文化翻译研究带来了许多新鲜独特的启示。有研究者指出,借助她的话语分析,我们可以从文本、符号、语词的层面深入到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历史关系,从而看到殖民主义话语背后的暴力性。(赵京华,2010)当然,学界对刘禾教授的观点也不乏质疑的声音,如李昌银(2008)认为从“夷”字的历史沿革和清朝的历史语境来看,清朝官员所用的“夷”字表达了对西方人的蔑视和憎恨,因此译为英语的“barbarian”无误。方维规(2013)认为“夷”字在中国历史上的贬义特色是很浓重的。“‘夷’字不仅是地域概念,更是华夏中心主义之华夷对举、夷夏之辨中表示等级和低劣性的文化符号”笔者同意上述学者所做的分析,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争论多少又有些“隔墙打拳”的意味,因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并不相同:一方的质疑围绕历史语境下“夷”字是否与“barbarian”等义展开,而另一方立论的要旨在于围绕“夷”字翻译的嬗变而展开的国家主权话语交锋。
令笔者困惑的是,刘禾教授在将一个字的翻译与两个帝国的碰撞联系在一起时,似乎有意无意的模糊了一些关键细节。刘禾教授一再强调译者郭实腊等人的“特殊贡献”:把“barbarian”固定为汉字“夷”的英文翻译,变成新的衍指符号,将其上升为法律事件,影响了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和律劳卑(Lord Napier)等人的判断乃至英国国内舆论,从而对日后鸦片战争的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面又引汤姆斯等人的话暗示马礼逊可能是“受人指使”,而他改把“夷目”译为“barbarian eye”实为译者与大英帝国建立新型关系的开始。从此翻译官的个人判断不得背离大英帝国的官方政策。(刘禾,2008:72)围绕“夷/i/barbarian的争议,“明显是和当时欧洲人的文明话语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刘禾,2008:71)。当然,我们可以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整合上述两种角度的叙述:译者的主体性(subjectivity)不再意味着个性化的,独立自持的东西,同时也意味着对意识形态的屈从。翻译活动既受意识形态的控制又不断生产意识形态。然而,即使我们相信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它随时都在影响或左右着译者的思维或行文,甚至连译者呼吸的空气都可能被某种莫名的或无形的(意识形态)力量所操纵,我们依然难以解释翻译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 欧洲关于文明和野蛮的话语机制为何单单选择在“1832年的某一天”兴风作浪?要回答此疑问,则有必要回顾“夷“字的翻译史,将译者,欧洲文明话语与翻译的赞助人(东印度公司或是英国政府官员)的互动重新做一番认真的梳理。
2.1794,诏书翻译中缺失的殖民主义话语
让我们回到马戛尔尼使团访问清帝国的年代。这次中英相遇不仅是两个不同文化观念的帝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同时也催生出了让后世学者争论叹息不已的各种翻译话题。天朝话语机制对乔治三世致乾隆国书的检查、规训与改写固然是题目中应有之义。(王辉,2010)而乾隆致乔治三世的两份“勅谕”在英国使团那里同样历经了一番大胆的改写,改写后的译本对原文的扭曲与颠覆程度丝毫不逊于前者。当这两份文件首先被翻译成拉丁文时,负责翻译的两位神父贺清泰与罗广祥就对其做出了一些修改,使其中的“天朝”语气显得和缓。“除了加入一些对英王的敬语外,他们还删去了带有侮辱性的语词”①在之前贺清泰给马戛尔尼的信中,他还特意提到乾隆皇帝“对待欧洲的国王就像对待他们属国的小王一样,而这些小王不过是皇帝的奴才而已”。(见戴廷杰《兼听则明——马戛尔尼使华再探》,载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6年编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页137)。。而马戛尔尼和他的副手斯当东对于这封措辞缓和的信还是不满意,在将信译为英文时,又进一步作出修改,“把清廷一切天朝大国的痕迹都尽量磨掉,删除所有可能刺伤英国人自尊心的部分”(王宏志,2009)。
如果以马戛尔尼等人的译本和后世颇为流行的E.Backhouse和 J.O.P.Bland两人1914的译本做一番对比,不难发现:前者对可能引发“谁是野蛮人”之类争议的词句都做了淡化处理,如“倾心向化”被改译为“仰慕帝国光辉”(glory of our Empire);而广为后世学者征引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经过翻译后变成了“中华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依赖别国货物”(Morse,1926:247-292)。马戛尔尼等人的译文中通篇都没有出现“barbarian”这样的措辞。而 E.Backhouse等人则特意将原文中隐含的优越感在翻译中做了放大。“向化”被译成了“向往我们的文明”(yearned after the blessings of our civilization);而凡是出现“夷”或“外夷”字眼的地方,几乎都被译为了“barbarian”。(Backhouse& Bland,1914:322-334)
刘禾(2008)在其书中特意提到英国人眼中的乾隆皇帝是个高傲自大的君主,这在乾隆给乔治三世的信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不仅如此,马戛尔尼使华的传奇故事,还标志着“殖民地史学”的开端。其中心论点为:中国在19世纪没落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对待外部世界这个问题上,顽固地坚持华夏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刘禾,2008:150)然而根据何伟亚的研究,尽管这两封信在现当代的中西关系史研究中被频繁征引,但据目前所知的材料看,在19世纪外交官考虑对华关系时,这封信并不受重视。在马戛尔尼回国后,这封信还长期受到忽视。(何伟亚,2002:242-243)何伟亚忽略了目前流行的英文译本与马戛尔尼等人的改写本实在大相径庭,这恐怕也是其受冷落的重要原因。令人费解的是,恰恰是在面对最能凸显中国傲慢与自大的乾隆回信时,刘禾(2008)所说的殖民主义伤害话语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宁愿将“外夷”这样的字眼处理得中性化,默默忍受着它们对英国的主权意识造成精神创伤而无所作为。
实际上,早在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等人出使中国之前,负面的中国形象已在英国国内四处蔓延。英国中产阶级舆论制造出的中国形象包括:单一刻板,知识停滞,文字艺术都粗糙不堪,带着毫无理由的优越感等。中国人在当时英国人的集体观念中“顽固的拒斥欧洲人的渗透和公共领域所定义的‘理性’,并继续在欧洲中心所构想的世界之外运行”(何伟亚,2002:25)。从另一方面来说,英国人早已先入为主地构建了中国人的英国观。在马戛尔尼出使前,东印度公司在给他的训令中就谈到中国上层认为英国人野蛮(barbarous)(何伟亚,2002:79)在漫画家Gillray1793年的一幅漫画上,面对单膝下跪奉上国书的马戛尔尼使团,中国皇帝只是神情傲慢地倚在宝座上抽烟。漫画的题目“Tribute from the Red Barbarians”恰如其分地渲染了在英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的排外情绪。(Gilling ham,1993)中国人野蛮而傲慢,这在在英国国内俨然已成为了一种“常识”。
而决定马戛尔尼等人翻译措辞的显然既非欧洲的文明话语也非译者个人的中国观。由马戛尔尼的使华日志可知,在与清朝官员在讨论乾隆敕书时,他关注的焦点只在于清政府能否满足英政府提出的各项要求。对于乾隆皇帝书信中的所谓傲慢的措辞他反倒不甚重视,而清方陪同官员松筠老练圆滑,为了尽早将使团送走,私下表示乾隆皇帝心里也赞同英方主张,只是碍于祖宗成法无法明确写在敕书中。他还向马戛尔尼透漏清方即将派员整顿广州关税制度。这番虚与委蛇的表态无疑给失望的马戛尔尼产带来了极大希望。在随后给国王的报告中他甚至说中英的首次接触已经使“英国商人的问题在中国人思想里开花结果”(佩雷菲特,1993:430)。马戛尔尼在文书翻译中没有选择“barbarian”这样的字眼与他当时希望复萌的心态不无关系。既然个人荣誉都可以为了英王的使命而舍弃,翻译自然也要服从于这一宏大目标。从目的论角度看,以英国可以接受的话语方式翻译乾隆回信就保留了完成使命的希望。虽然这未免只是马戛尔尼的一厢情愿,但从中也不难看出赞助人在此次翻译实践中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力。
3.马礼逊:“barbarian”,欲说还休
刘禾(2008:86)认为,郭实腊释“夷”为“barbarian”造成了夷/barbarian指称功能本身成为了一个重叠、翻译的情景:中国人对英国人说“夷”字,而英国人听见或看见的是“barbarian”。而马礼逊在1815年编撰的《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将“夷”译为“foreign”,正是刘禾教授认定郭实腊修改翻译成例的关键证据。
然而细查史料,在当时英国人的记述中,“foreign”与“barbarian”无论是在语义上还是在感情色彩上却常常相互粘连。如1830年5月号的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Miscellany杂志上刊登了两广总督对英商禀帖答复的英译本,译者将“夷商”译为“foreign merchants”,但又特意加了脚注:(中国官方)到处用“foreigners or barbarians”这样的字眼替代代词“我们”。与之相呼应的还有马礼逊本人的回忆录。在1821年2月17日的一篇评论中,他指出行商对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来信的本意与文风都做了修改。不仅把行文语气改得低三下四,所有的代词“我们”也都用“夷”(E)字替换。马礼逊强调说“夷”字经常被翻译为“foreigner”,但除了表达“不属于中国”这层意思外,这个词还传达了低人一等的含义,就如同古希腊人称呼别人为“barbarian”一样(Morrison,1839)。
“律劳卑事件”发生后,英国报刊对“夷”字的译法也多有讨论。1835年在一篇题为“Dispute with China”的文章中,作者意识到汉语词与相对应的英文词之间会存在语意上的不对等,所以他主张翻译“夷”字时不能按字面意思译得太拘泥。他认为汉字“夷”(E)的意思(meaning)毫无疑问是“barbarian”,只不过在地道的英语中这个词的含义(sense)是“foreigner”。而英商报纸《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上的反驳文章赞同将“夷”字译为“foreigner”或“stranger”,但是又强调“夷”字在被中国官员用来称呼在广州的外国人时,明显是一种“侮辱性的,嘲弄的,不敬的措辞”。“中国官员们明明有“远客”(Yuenkih)这样无懈可击的措辞可以用来称呼外国人,但是他们清楚用“远客”会让外国人觉得很舒服,正像他们清楚用“夷”字会让外国人不舒服一样。”(The Review of“The Dispute with China”,1835)双方的分歧既不是“夷”字的译法,也不是这个词的本意,而是在中英交往的具体语境下这个字应该如何理解。刘禾(2008)反复警告我们“barbarian”这个英文单词对汉语不露声色的入侵,将汉语的“夷”字变成了它的能指,从而驱逐了这个汉语词的其他意义。而上述例子则提醒我们词义扩张和变异的复杂程度经常超过我们的想象。刘禾(2008)曾追问:如果英国官员沿用了马礼逊更早的翻译,把“夷”字理解为“外国人”而不是“野蛮人”的话,英国人的行为会有什么不同吗?马礼逊等人的例子恰好说明了刘禾教授将“夷/barbarian”的出现阐释为影响深远的“翻译事件”多少有夸大的成分。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词语翻译背后更加广阔的具体历史语境,既包括政治机制与文化心理,也包括具体的政策与利益关系。
果蔬运输系统是指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而进行的农产品物质实体及相关信息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物理性流动。该系统目前在农产品运输系统中实施较为困难、投资较大,效果却难以令人满意。我国地大物博,地处北温带和亚热带,南菜南果北运线路可长达2 000~3 000km,产地和销地温差最大可达30°,运输情况复杂。欲在运输途中保持果蔬品质、延长寿命,与水果蔬菜的采后处理、装卸水平、运输中的环境条件、运输时间、运输工具、路途状况和组织工作均有密切关系。
从译者的角度来看,马礼逊本人对于英国有关中国人“排外”、“野蛮”的一整套主流话语是认同的。比如他谈到中国人将所有外国人都视作魔鬼;(Morriosn,1839:240)又言“对所有外国人的厌恶是中国人的主要特征”(Morriosn,1839:240);马礼逊将广州大火视为上帝对富足的、堕落的、偶像崇拜的广州一次最严厉的惩罚。(Morriosn,1839:184)他还表示中国人对待外国人士的行为展示了他们“性格中最恶劣的特征和最低的文明程度”(the worst features of character and the lowest degree of civilization”)是“最为卑劣的自私自利的行为”(the most debasing selfishness)(Morriosn,1839:329)。尽管如此,马礼逊本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仍将“夷”译为“foreigner”,可见“夷”字翻译策略的选择与是否受欧洲有关野蛮与文明的话语机制影响无关。
需要注意的是,马礼逊翻译策略的选择又随着其翻译活动的具体赞助人不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律劳卑事件”发生之前,马礼逊就因受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主席马奇班克斯(Charles Majoribanks,旧译马治平)的影响而改变了自己的翻译惯例。马奇班克斯在围绕结束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垄断权展开的辩论中立场强硬。他致信印度监督局局长格兰特预言广州当局将会对即将到来的贸易制度变化反应冷漠。“广州的衙门可能会发布谕令,说‘夷(barbarian foreigners)性善变,改其旧制。今公班衙既散,自此英王领事将负对华全责。天朝亦将漠然视之。新任之番鬼(foreign devils)须谨遵天朝永世不易之法’。”(Urmston,1834:457)他强烈主张在派遣使节到中国时,必须伴以海军力量,并说:“英国的海军司令是最好的大使……因为海军司令在几小时内就可以收到外交官用几周、几个月才能得到的效果。”马奇班克斯已经事先为两广总督衙门尚未发布的谕令准备好了措辞,在对华动武论在东印度公司高层甚嚣尘上的背景下,马礼逊甚至将他早先译为“foreign”的地方都替换为“barbarian”。(Urmston,1834:458)赞助人对于译介活动的影响可见一斑。
4.夷妇入城事件与律劳卑事件:“barbarian”的使用策略
前文已述,在华英国人对“夷”字的抱怨与抗议早已有之。然而根据资料显示,直到1830年10月至11月间,“夷”字才在中国官方谕令的译文中频繁被译作“barbarian”。而这些谕令大多都是针对前文提到的“夷妇入城”事件而发布的。盼师在1930年10月12日致两广总督的申辩信中说中国官方的公告中包含了“许多针对外国人的毫无根据的可耻言论:比如‘行商与通事须常教导外夷,抑其骄纵,务使其倾心向化’但是除了两三位行商外,他们全都无知无识,而那些海关的通事更是愚蒙之辈。现在本地的大人们竟然让这些人摆出主人的派头向外国人教授文明,真是可笑之至……看来政府的高官们是希望让本地人把外国人都看成是蛮国野人。这可真是对外国人以示怀柔啊!”(Baynes,1832:34)我们可以把这封信归入刘禾教授所说的“殖民伤害话语”中,但盼师在复述中方谕令,表达对“文明”“野蛮”相互逆转的愤慨时,仍是用“foreigner”称呼外国人。就在这封信写成一周后,自由商人与委员会便向广东官宪提交了语气强硬的抗议书。值得玩味的是,10月23日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同时收到了两份对他们抗议书的咨复。在两广总督的咨复译文中,“夷人”依然译为“foreigner”,旁边专门加了注音:(E.jin)而粤海关监督的咨复译文中,“外夷”一词则被译成了“outside foreigners(or barbarians)”(Baynes,1834:38),直到中方派出军队包围商馆区之后,在10月28日的总督咨复译文中,此前一直被译为“foreign Factory”的“夷馆”一词才变成了“barbarian Factory”,译者自注说:“用‘foreign’一词翻译已经不可能传达此句主旨了”(Baynes,1834:41)。
可见,词语翻译的变化背后折射出的是事态的逐渐升级和盼师本人日益强硬的对华立场。盼师本人始终“对当地官宪的许多使人烦躁的压迫甚感愤怒”(Downing,1938:98),但只是在中英双方激烈对峙的这段时间内,清方的政府文告的“夷”字才被翻译成了“barbarian”以加强轻蔑的语气。“夷”字由“foreigner”改译为“barbarian”,绝不是刘禾教授所说的由译者的大胆修改导致“情势急转直下”,而恰恰是中英双方矛盾激化的表现。与其说有关野蛮与文明的欧洲话语是这一转变的幕后推手,倒不如说翻译赞助人的现实需要才是此时决定译者翻译策略的关键。
在刘禾(2008)的叙述中,1834年的“律劳卑事件”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一系列词语翻译的争执酿成的。两广总督卢坤谕令里“夷目”被译为“barbarian eye”,这大大激怒了律劳卑,这也成为后来发生的中英第一次军事冲突的催化剂。总之,“衍指符号‘夷/i/barbarian’,是现代外交史上十分惨痛和代价高昂的一场文字案”(刘禾,2008:67)。然而“夷”字果真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吗?
试将当日双方文书往来翻译的情况作一番分析。律劳卑自述7月25日凌晨到达广州,翌日正当马礼逊在翻译律劳卑致总督的信件时,行商吴秉鉴(Howqua,即浩官)等人带来了总督致行商谕令的抄件向他宣读。(Napier,1840:20)在卢坤这封7月21日的谕令里,多处都出现了“夷目”字样。蹊跷的是,律劳卑本人在8月9日致巴麦尊信的中对此却只字不提,只是表示行商代英商传话的制度已经不合时宜,他本人要遵照训令亲自与总督沟通。(Napier,1840:8)直到8月17日律劳卑再次致信巴麦尊,才随信附上了包括这份谕令在内的5份文件的英译本。律劳卑其人自尊而敏感,在9日的信中还专门谈到自己的名字被中方以侮辱性的“劳卑”(laboriously vile)两字称之,并要求行商解释为何无端对他加以侮辱。试想,如果马礼逊在当日口译中真的把“夷目”译为“barbarian eye”,律劳卑何以无一语提及?况且,马礼逊曾将“夷辈”译成“foreigners”(Napier,1840:61),而对于包含有“目”字的中国官吏名称他也是以拼音加解释的方法处理的。(如:典籍侍诏孔目:teen-tseǐh-she-chaou-keungmùh,all of which titles express different literary departments;吏目:Le-Mùh,attendants in courts)(Morrison,1817)即便他有可能“受人指使”把“夷”字译为“barbarian”,也不应该只把“目”笼统的释为“某种对人的称呼”,所以“barbarian eye”应该不是“夷目”最初的英译名。
在8月1日马礼逊去世后,由其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接替律劳卑随行翻译的任务。“barbarian eye”的译名很可能就出自马儒翰之手。除了修改其父老马礼逊的翻译成例外,马儒翰在翻译其它中方文件时也颇“煞费苦心”。如在8月11日行商致英商的信中有“贵国”(your honourable nation)一词,下面的译注强调此处“honourable”仅仅是“你们”的意思。行商们提到英国官员时说“your honourable officer”,只相当于看望病人时说“贵恙”(your honourable disease)一样,并不表示尊重。(Napier,1840:16)为什么要特意花费笔墨讨论一句无关痛痒的套话呢?其中原委便在于“your honourable nation”这样的用语和后面卢坤谕令英译中反复出现的“barbarian eye”反差实在太大,所以才有意加以淡化,不惜牵强地将其与疾病硬联系在一起。
马儒翰真的享有如此大的翻译“自由度”,可以随心所欲根据个人好恶操纵文件翻译吗?事情恐怕绝非如此简单。与老马礼逊相比,马儒翰“在对华交涉问题上,与英国商人和官员基本未发生异议。他更愿意将自己当作一个英国公民,为祖国贡献一切”(胡其柱、贾永梅,2010)。所以马儒翰的翻译活动理应与律劳卑等人的对华立场与策略联系起来考量。比如,1831年,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宾曾发布谕令,表示“如果公司散局,仍应酌派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胡其柱、贾永梅,2010)。而马儒翰在翻译此谕令时把“大班”(taepan)译为“chief”。这一改看似无关宏旨,却有深意存焉。因为律劳卑由此便可顺理成章为自己的在华身份找到法理依据。律劳卑后在1834年8月发布一份名为《中英关系现状》的文告,由马儒翰译为汉语后,在广州城广为散发。文告开篇即引用了李鸿宾的这个谕令,并借此谴责中方言而无信,朝令夕改。(Napier,1840:37)奇怪的是,马儒翰在翻译时并没有直接引用汉语原文,而是“画蛇添足”地把自己的英译稿再转译为汉语。因为唯有如此,律劳卑的满腔“义愤”方能自圆其说。
在中英矛盾尚未激化的8月初,律劳卑致国内的信中尽管提到英方受到了一些屈辱,但语气克制,也并未使用“文明”“野蛮”之类的字眼。而到了8月中旬,行商们停止了对英贸易。此时的律劳卑不得不面对国内商人们的批评,他更要为自己的强硬立场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向巴麦尊等人辩解。欧洲的文明话语此时才“恰如其分”地出现在了律劳卑致巴麦尊与首相格雷的信中。律劳卑在这些信中反复表示,中国当局傲慢无礼,竟要求国王陛下政府对其“恭顺”。中国法律禁止“交接外夷”(communicating with outside barbarian)(Napier,1840:31)。英政府不能用文明国家之间制定的行事常规对待中国。(Napier,1840:16)此时的律劳卑急于劝说英政府采取炮舰政策,无论是文明话语的使用还是“夷目”的改译都与这一政策的转变密不可分。之前无论是“夷”还是“夷目”都在翻译中波澜不兴,而此时偏就变成了一段难解的公案。与“番妇进城”事件如出一辙的是,“夷/barbarian”随翻译赞助人的“愤怒”产生,而它的杀伤力恰恰源自翻译赞助人自身。
5.结语
从鸦片战争前“夷”字的翻译史可以看出,翻译赞助人的种种现实目的对“夷”字翻译策略的选择影响最大。而欧洲的文明话语只不过被译者有选择地用来为翻译赞助人服务。无论“夷”字被译为“foreigner”还是“barbarian”,都无法成为深刻影响中英关系的“翻译事件”。
[1]Backhouse,E.& J.O.P.Bland.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CourtofPeking[M].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14.
[2]Baynes,Wil1iam.Papers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N]//Accounts and Papers Relating to Colonies(Vol.XXXI),1832:34.
[3]Downing,C.Toogoog.The Fan-Qui in China in1836-1837(Vol.3)[M].London:Henry Colburn Publisher,1938:198.
[4]Gillingham,Paul.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1792-94[J].History Today,1993(10):28.
[5]Governor Li’s Reply to the British Merchants’Petition[N].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and Foreign India,China,and Australasia(vol 2).London:Parbury,Allen,and CO,1830:42.
[6]Morrison,Eliza A.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vol 1)[N].London:Longman,Orme,Brown,And Longmans,1839a:Appendix 31.
[7] Morrison,Eliza A.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vol 2)[ M ].London:Longman,Orme,Brown,And Longmans,1839.
[8] Morrison,Robert.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M]Bengal:Serampore,1815:61.
[9]Morrison,Robert.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Containing a Sketch of Chinese Chronology,Geography,Government,Religion&Customs,Designed for the Use of Persons Who Study the Chinese Language[M].London:Black,Parbury,and Allen,1817:88,94.
[10] Morrison,Robert.Memoirs of Robert Morrison,D.D.[J].The Methodist Magazine and Quarterly Review.(Vol.XXII),1840:329
[11]Morse,H.B.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M].Oxford:Clarendon Press,1926.
[12]Napier,William John.Lord Napia to Viscount Palmerston(Aug,9,1834)[M]//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London:T.R.Harrison,1840.
[13]The Dispute with China[M]//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and Foreign India,China,and Australasia(Vol.XVI).London:Parbury,Allen,and CO,1835:148.
[14]The Review of“The Dispute with China”[N].The Canton Register,1835-09-29.
[15] Urmston,James Brabazon.Free Trade to China [J].Quarterly Review(Vol.L)1834(1):457.
[16]方维规.一个有悖史实的生造“衍指符号”—— 就《帝国的话语政治》中“夷/barbarian”的解读与刘禾商榷[J].文艺研究,2013(2):139.
[17]郭庭以.中英鸦片战争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3.
[18]胡其柱,贾永梅.翻译的政治:马儒翰与第一次鸦片战争[J].浙江社会科学,2010(4):87.
[19]李昌银.翻译与历史语境——“夷”字的语义沿革与英译问题[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7):144-146.
[20]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1]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 —两个帝国的碰撞[M].北京:三联书店,1993.
[22]王宏志.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J].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9,63(3):135.
[23]王辉.天朝话语与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书的清宫译文[J].中国翻译,2010(1):27-32.
[24]杨念群.作为话语的“夷”字与“大一统”历史观[J].读书,2010(1):33-37.
[25]赵京华.概念创新与话语分析的越境[J].读书,2010(1):40-42.
[26]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