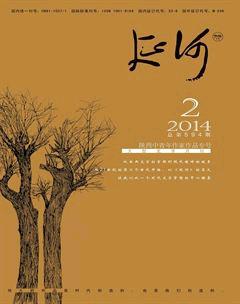赫拉克利特的灵魂
宋小云
干燥
“一个醉汉由一个孩子领着,他跌跌撞撞地跟在身后,并不知道要走向哪里,因为他的灵魂潮湿了。灵魂喜欢变成潮湿的。干燥的灵魂是最智慧最好的 。”这是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在他看来,干燥的灵魂是最优秀的灵魂。奥修曾说:“人类意识可以遵循两条道路。一条是水的路,向下流淌;另一条是火的路,向上运动。水和火,这虽是象征,但非常有意义 。”奥修所说的水,是人类精神“向下”的表征;奥修所说的火,是人类精神“向上”的姿态。在赫拉克利特的这句话里,酒鬼代表着人类灵魂中的麻痹、享乐以及畏缩的不良倾向,
因此,他的灵魂是没有方向的,是潮湿的。
即便是被人牵引,也找不到灵魂的方向:小孩便是他灵魂退缩的表征,小孩是潮湿的,因为他只有本能和欲望。而火则代表了与水完全相反的方向和力量。普罗米修斯盗火作为人类精神的原初迸发,在人类精神的懵懂黑暗中,点燃了一道智慧之光。在这则希腊神话中,我们读出最早的关于火的隐喻——干燥。干燥,这人类精神永远向上的属性,孕育了无数摆脱了欲望之水、时间之水的干燥智慧。赫拉克利特把人类精神停滞不前的状态,称为“意识的潮湿状态”。“潮湿的意识”具有水的属性——它永远向下漂流:沉迷幻觉,不需要努力,永远只在镜中花与水中月里黯然徘徊。那么灵魂降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西方有一个很好的英语单词形容这种状态:stoned(烂醉如石)。灵魂开始只是有些迷醉,继而又有些麻痹,麻痹到一定程度便会丧失意识,最终他便会退化成一块石头,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人存在的意义被完全架空,徒具其形,失去了对世界的任何一点敏感度,世界对他关上了大门,他也在世界中严重地缺席。然而,向上运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困难的。在希腊神话中,火并不是属于人间的事物,它只有被盗取,才能为人类带来永恒的福祉。神话隐晦地向我们表明:火的稀有与火的不易。因此,任何与火沾边的事物,都应该有“难”的属性,灵魂也不例外。灵魂每一次向上的飞跃,都必须经受火的煎熬,只有这样,“干燥”才能降临他的灵魂。有一则关于老子的传说,据说他一生下来就是干燥的:他在母亲的子宫里活了八十二年,一生下来就满头白发,而且非常非常的“干”,孩子时期他就变成了一个干瘪的老头。
当然,还不仅仅是他的肉体“干”,连灵魂也变得非常的“干”:他几乎是那种生而知之的人,他在一开始就是全觉全知的人。灵魂不干燥的人只依靠重力生活,像水一样,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永远只会向下流淌。水气过重的地方会产生沼泽,会生发瘴气。一个人的“水气”过重,他的灵魂就会很容易地粘上世俗的灰尘。就像一个人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穿过漫天都是灰尘的工地,他的衣服必然会脏。灵魂也一样,如果它本身是潮湿的,它必然会越来越脏,因为在世界中,欲望与享乐的灰尘始终在纠缠着他,稍不注意,灵魂就会丧失它本身对世界的敏感性。即便是希腊神话中伟大的赫拉克斯的灵魂也会偶尔地潮湿:他曾在吕狄亚女王翁法勒手下做奴隶。当她听说他就是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时,立即使他恢复了自由,并招他为夫。从此以后,赫拉克勒斯过着东方人的豪华生活,他逐渐忘掉了美德女神在他年轻时给她的教诲,沉湎在享受中,不思进取。女王给伟大的赫拉克勒斯穿上妇女的衣裙,让他和女仆们一起纺纱织布,连妻子翁法勒也开始瞧不起他了。
她自己披上他的狮皮,而把女人的衣服给他穿上, 用来羞辱他。赫拉克勒斯迷恋于她的爱情,竟甘愿坐在妻子的脚旁为她纺羊毛。他在原先几乎能够顶住天空的脖子上挂了一条金项链,两只健壮的胳膊上戴上玉石手镯,头上戴着女人的发饰,身上披上一件女人的华丽长袍。此时,赫拉克勒斯的灵魂是潮湿的,他被女王的“爱情”之水紧紧包围。他对女王的爱,是一种无意识的爱,丧失了自我,自然也就看不清自己,意识不到自己所拥有的可以和宙斯相媲美的力量。但伟大的赫拉克勒斯很快就从昏聩的状体中苏醒过来,他意识到,自己还是属于“火”的,要继续完成他的丰功伟绩。赫拉克勒斯没有忘记他的选择,当幸福女神为他指出一条“潮湿”的人生道路时,他断然地拒绝了她的诱惑:可以享尽生活乐趣,一生没有烦恼和不平;他不用参加任何战争,不用操心买卖的事,只是享用美酒和佳肴,他也可以睡在温暖柔软的床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用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可以尽情享用别人的劳动果实,享不尽荣华富贵,因为我给予我的朋友享用一切的权利。
赫拉克勒斯选择了“干燥”的人生道路,经历了许多艰辛和考验,将他的自我意志摆放在希腊精神显赫的顶端。在一个人的灵魂即将“上升”的时候,他对整个世界是直觉的、敏感的。即便一个人在夜里昏睡,他的灵魂依然是燃烧不止的。只需一道窄门,世界所有的层面都会向灵魂打开。在《神曲》中,但丁就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干燥”的尤利西斯。他探险回家后,儿子的孝顺、老父拉厄耳忒斯的挽留、妻子佩涅洛佩的美貌都无法打消他探知未知世界、了解人类缺点与美德的愿望。尤利西斯的灵魂毫无疑问是越老越干燥,它永无休止地渴望上升。于是,即使他垂垂老矣,仍然乘上他的最后一条船,带着仅有的几个忠实的水手,再次向迷茫的、未知的大海驶去。他们都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但他们想要探索无人的大陆和无人行驶过的海洋的渴望不可遏止,直到死亡为他们永无休止的探寻加章封印。尤利西斯内心的火焰仍然在燃烧,灵魂向上的精神永不止步。即便冥王哈得斯给他一万次重生的机会,我相信他依然会踏上那最后的船只,到苍苍茫茫的大海上,冒险并再次迎接他的死亡。但丁笔下的尤利西斯做着永不停息、永远向上的运动。尤利西斯的灵魂也就是但丁的灵魂,只不过但丁是作为一个书写者的尤利西斯,在灵魂的一步步上升之中,寻找着关于地狱及天堂的真理。难怪奥古斯特.吕埃格这样评价他:“但丁是个冒险家,他像尤利西斯一样,走上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游历了前人未曾见过的世界,他追求最艰难、最遥远的目标。”但丁用干燥的灵魂为我们写了一本干燥的书:《神曲》是一本被时间晾干了的书,它几乎没有任何水分。因为但丁用自己的灵魂烤干了它,让它在永恒的时间之河里获得了纯粹平静的目光。因此,人类文化历史中诞生的每一部经典,都应该是干燥的。
尼采曾对此有过精彩的表述:“每一部新出现的作品,只要它还处在它的时代的热烘烘的气息包围中,它就具有最小价值——因为在这个时候。它还没有同市场的东西、敌人的东西、舆论的东西以及一切从早到晚变个不停的东西分开。经过一段时间后,它的水分消失了,它的“时间性”不见了——这时它追求的是永恒的沉静的目光的话,开始获得永恒沉静的目光 。”因此,赫拉克里特说:“干燥的灵魂是最智慧最好的。”赫拉克利特鼓励那些灵魂向上的人,觉得一个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让自己逐步脱离水分,变得干燥。所有的人类的欲望他都一目了然,所有外面的世界他都已悉数游历,最后他便会到达自身——让世界整个地在他的灵魂深处洞开,并且一目了然。此时,他才会拥有真正干燥的灵魂,真正干燥的智慧。
知识与土
大量学习并不会教给人悟性。找金子的人挖了很多土,但是几乎没有找到什么。
——赫拉克利特《残篇》
赫拉克利特说:“大量的学习并不会教给人悟性。”同样地,大量的阅读也不会带给人悟性,有时还起到相反的效果。看看那些成天呆在大学里面的人文教授们,他们似乎学习了一切,但又好像什么也不“知道”。我所谓的“知道”,在于知晓存在的本身状态,存在向神性靠拢的最高阶段——不是知识,知识永远是外在于一个人的东西,即便它有时比功勋章还耀眼,可以用来炫耀和评定职称,但毫无疑问它是不属于存在本身的东西——真理未经体验便不是真理,至少它不是你的真理。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生命是有限度的,然而知识却是没有尽头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不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么?在这里庄子向我们指出了学习的虚妄,过于追逐知识将是一件“危险”(殆)的事情。那么追逐知识的危险之处在哪儿呢?在于一个人在过分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把他自己给忘了,他忽视了生命的本体,把自身活生生的存在一脚踢开,而让自身沦为某种意识形态或信仰的单纯承载工具。这样难道还不危险么?现代人大面积地处在危险之中,所有的知识都被处理成信息,自我则被完全地弃之荒野。
如果在古典的时代里,知识还多少有点“人性 ”气味的话, 那么到了现代社会,知识完全沦为了工具——科学的、技术的、职业的、应试的工具,而与生命无涉,与海德格尔所说的“在”无涉。所以现代人充满了知识,而头脑却是苍白的,生命也是苍白的。他们学习得太过匆忙,以至于对基本的生命没有觉知。就连孩子们的那点觉知,也在现代社会的步步紧逼下,几乎丧失殆尽。他们(她们)从一出生,父母、老师、社会就企图灌输给他们各种各样的知识。因此,童年不见了,对世界的基本感知被“排除”在了本体之外,个个呆头呆脑,毫无灵性,大脑里装满了与己无关的知识,对生命的体验从一开始就被无情地抽空。于是对大多数孩子来说,装饰在盆景中的塑料花与在田野中开放的鲜花没有区别,生命的体验消失了,只剩下单纯的物象。
奥修曾引用过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篇很意思的寓言:有一次,有个人来到一位牧师那儿,俄国最大的牧师那儿,他说:“我认识三个圣人。他们住在岛上,他们已经达成上帝了。”牧师说:“这怎么会发生呢?我是全国的主教。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知道这件事,这三个人怎么可能已经达成上帝了?我要去看看他们。”他坐船去了。他到了那个岛。那三个单纯的人正坐在树下做他们的祈祷。他听了祈祷后大笑起来,说:“你们这些笨蛋!你们从哪里学的这祈祷?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荒唐可笑的事情,而我是全国最大的牧师,这算什么祈祷?”三个人开始吓得抖起来了。他们说:“饶恕我们吧!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来没学过。这个祈祷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个祈祷很简单。他们说,“我们是三个人”——基督教相信三位一体,所以他们说——“我们创造了一个祈祷:‘我们是三个人,你也是三个人——仁慈我们吧!我们自己创造了它:我们是三个人,你也是三个人——仁慈我们吧!我们一直这么做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是对的还是错的。”牧师说:“这完全是错的。我会教给你们正确的、权威的方式。”它是教堂里很冗长的祈祷。那三个人听着,不停地发抖。牧师很高兴。他回去的时候想着他做了一件有德行的事,一件真正的好事,他把三个异教徒转变成基督徒了。“这些笨蛋!他们已经出名了。很多人为了接近他们而去,抚摸他们的脚,崇拜他们。”他回去的时候,他很高兴他做成了一件事。突然间,他看见一个像风暴一样的东西从湖面上过来了,他变得很害怕。然后他看清楚了;那三个圣人正从水面上跑着过来。他没法相信他的眼睛。
那三个圣人到了,他们说:“请再说一遍祈祷,因为我们已经忘了!它太长了,我们都是乡下人,没受过教育。就一遍……?”牧师跪在他们脚下说:“宽恕我吧!我犯下罪孽了。你们走你们的路吧。你们的祈祷是对的,因为它是从你们的心中来的,我的祈祷是没有用的,因为它是我学习得来的。不要听我的,原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如果我们能抛去托尔斯泰的道德训诫不谈,那么这将是篇很深刻的关于“知识”与“知”的寓言。牧师的祈祷之所以没用,那是因为它是通过“学习”得来的,是些知识(knowledge),而不是“知”(knowing)。因为“知”是从内心长出来的,是永远地与“生命”相关,与“在”相关。 因此,禅宗提出了一种极端的看法:知识除非是由我们自身体悟而来,否则便没有任何意义。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佛总是沉默的,因为佛在“悟”;而知识则可以用作谈资,炫耀才华,因而世间的“才子们”总是吵吵闹闹的。——这大概就是老子所谓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禅宗提出了一种极端的看法:知识除非是由我们自身体悟而来,否则便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现在学者却热衷于“挖土”,穷尽一生收集和整理各种各样的知识,将自己的大脑训练成承载信息的垃圾收容库,然后这个世界上才会多了那么多无聊的教授、喜欢自慰式尖叫的学者。赫拉克利特说:“找金子的人挖了很多土,但是几乎没有找到什么。”那些学究、博学者们挖了很多土,图书馆就是他们的土堆,看上去多么像他们为自己堆起的坟茔。——他们埋葬了自己,还不自知,并对自己的学生无耻地宣称:你们看,我挖出的土就是金子。他们摆出了权威的架势,迫使信任他们的学生闭上眼睛,在想象里将他们导师的土变成金子。现在有多少这样无聊的学府与流派,什么PKU的讲经学派,什么ZSU的古典学派,如果他们仅仅是挖土倒也罢了,还无耻地捧着土向世人宣称:“我手里拿的是金子。”以至于他们自己都欺骗了自己,甚至连土与黄金都分不清楚。尼采有一句名言说:“知识的力量不在于真实的程度,而在于知识的古老,被人接受的程度,以及它作为生存条件的特性。”看来,教授们很懂得知识的力量,怪不得会培养出那么多愚蠢的学生,就是为了让他们接受自己的事业,继续挖土,好让千秋万代“金”、“土”不分。传说,有一天,亚里士多德正在海边沙滩上走路。他看到有个人正在用勺子从海里舀水,然后把水倒在岸边他挖的一个小洞里。
亚里士多德正在为他自己的问题着急呢。他没有在意——一次,两次,他走近了那个人,但那个人那么专注,以至于亚里士多德也好奇了:“他在做什么?”他没法控制自己,而那个人绝对地专注。他走到海边,舀满一勺水,带着水过来,把它倒到洞里去,再去海边……最后,亚里士多德说:“等一下,我不想打扰你,但你在做什么?你搞得我莫明其妙。”那个人说:“我要用整个大海来填满这个洞。”亚里士多德,即使是亚里士多德,也大笑起来。他说:“你真笨!这是不可能的!你简直是疯了。你在浪费你的生命!只要看看海有这么大,你的洞这么小——而且就用一把勺子,你想把大海都勺到这个洞里去?你简直是发疯了!回家休息去吧。”那个人笑得比亚里士多德还响,他说:“是的,我会走的,因为我的工作做完了。”亚里士多德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你做的也一样——甚至更傻。看看你的头,它比我的洞还小。再看看神性、存在,它比这海洋还大。再看看你的思考——它们比我的勺子更大吗?”这人走了,大笑着走了。在奥修看来,即便是西方理性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也是挖土人之一,因为他是逻辑的、知识的;而嘲笑他的人则是存在的、神性的。这个嘲笑亚里士多德的人也一定会嘲笑我们的时代,愚蠢而又肤浅的时代:技术飞速发达——技术的发达是欲望的发达,因而是肉体的发达;图书馆越来越大,各种各样的知识铺天盖地,而作为“存在”的人却消失了——生命的整体感与深度在现代人身上已找不到丝毫影踪。希伯来有一句谚语:“我是自己存在的存在。”真正的知识也应该是关于自己存在的存在:生命是“在场”的,而不是被各种知识抽离。这句谚语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在隐约地表明,关于自我的真理就是上帝。只有生命真正地参与到世界,世界才有可能向一个人的自我显现神秘、揭示真理。自我与世界融合的过程也就是真理逐步显示的过程。
如果只是一味迷信“知识”,而忽略人性与觉知,那么自我与世界只会越来越远。——于是,现代人离回家的路也越来越远,以至于步入旷野,在迷茫与困顿中不知所措。
责任编辑:王彦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