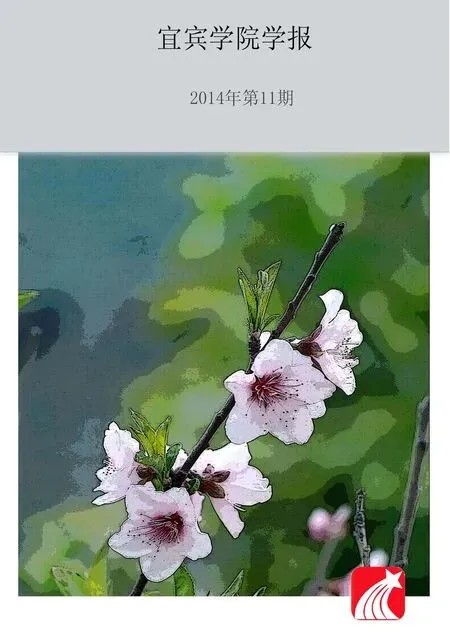《文心雕龙》视域中的《楚辞》
黄文彬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桂林541006)
《文心雕龙》视域中的《楚辞》
黄文彬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桂林541006)
《文心雕龙·通变》篇认为《楚辞》是文章“从质及讹”的转折点,希望通过“宗经诰”与“变乎骚”,达到文章“通”与“变”的平衡。在这一大背景下,刘勰将《楚辞》列入“文之枢纽”,并在《辨骚》篇中提出了“倚经驭骚,酌奇存真,玩华保实”的写作原则,把“文”之变纳入可以指导的范围内,《辨骚》篇的宗旨就是指导人们如何“驱辞力”和“穷文致”的。这一写作原则与“正言体要,恶乎异端”的思想密切相关。《风骨》篇与《定势》篇还从不同角度对《辨骚》篇的写作原则进行了补充和丰富。实际上,刘勰就是借《楚辞》来述其运辞之道,这是他解《楚辞》的独特之处。
《文心雕龙》;《楚辞》;《通变》;《辨骚》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写道:“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1]1924《辨骚》篇又云:“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1]134可见“骚”在刘勰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刘勰如此重视《楚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楚辞》是文章“从质及讹”的转折点
《楚辞》的“奇文郁起”使文章之发展起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文心雕龙·通变》篇认为,从纵向的历史看,《楚辞》是文章“从质及讹”的转折点,改变了自经典产生以来文章发展的历史轨迹。
《通变》篇云:
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於黄世;虞歌《卿云》,则文於唐时。夏歌“雕墙”,缛於虞代;商周篇什,丽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1]1084-1090
从中可以看出,刘勰认为《楚辞》是文章“从质及讹”的转折点,《楚辞》之前的文章作品“序志述时,其揆一也”,原则都是一致的。楚以后则“从质及讹,弥近弥澹”,变化的原因是“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
南朝时期的另一位批评家钟嵘在他的著作《诗品》中,亦批评了当时的文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荡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2]64-69“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2]74钟嵘与刘勰时代相近,都对当时的诗坛(文坛)不满,认为当时的诗坛(文坛)创作有弊病,不同的是钟嵘品评的是诗歌,刘勰谈的则是所有的文章。可见当时的文坛的确出现了问题,以至于理论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批评的意见,这些问题也是他们撰写批评著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质及讹,弥近弥澹”的文坛状况,实际上是文章发展中“变”与“通”的不平衡导致的结果;而“竞今疏古”的文坛风气,则是士人们过分求“变”,忽略了“通”的创作心理所致。刘勰提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1]1094,用经书的典雅、淳质之风来改变文坛“讹”“浅”的弊病,就是希望文坛再回到宗尚古人的作文之法上。但是,“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1]1079,经书有其常体,“文”之发展却“日新其业”,经书之体显然不能适应文章之变,且“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1]1106,刘勰显然意识到了这些,所以又指出为文不仅要“资於故实”,还须“酌於新声”,学会通变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1]1081。实际上,刘勰在处理文章发展“通”与“变”的问题上,非常注重“通”与“变”的平衡,他努力使“变”不能压过“通”,但是“变”之于文章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如何达到“通”与“变”的平衡就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而《楚辞》则是刘勰解决文章发展“通变”矛盾的突破口。
二 刘勰对《楚辞》的评价
刘勰并没有系统地注释或解说《楚辞》,但是他对《楚辞》的评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文心雕龙·辨骚》篇追述了汉代人对《离骚》(亦可视为对《楚辞》)的评价:
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翳,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1]136-144
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汉人对作品进行艺术分析和评价的三个突出特点:一是与政治伦理联系密切,汉代统治者对《离骚》(亦可视为对《楚辞》)的喜好和评价成为影响人们对《离骚》看法的重要因素,政治直接介入到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中;二是以经书为标准,无论是班固所谓的“非经义所载”,还是王逸的“依经立义”,汉宣帝的“皆合经术”以及扬雄的“体同《诗》雅”,都透露出汉人依经立义,以儒家诗论为标准来衡量一切作品价值的时代倾向,是儒家政教文学观的体现;三是受到“知人论世”说的影响,如班固在评论《离骚》时,注意联系屈原的品行谈论其作品。而这三个特点实际上都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可见汉人对《离骚》和《楚辞》的评价是在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依托这一大背景下作出的。
面对前人的评价,刘勰认为“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1]144,于是提出了自己对《楚辞》的评价。他认为《楚辞》有“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四事“同於《风》《雅》”,[1]146又有“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四事“异乎经典”,[1]148并总论《楚辞》:“固知《楚辞》者,体宪於三代,而风杂於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旨,亦自铸伟辞。”[1]152-155刘勰将其对《楚辞》的评价细化,但是他以“《风》《雅》”和“经典”为标准评价《楚辞》的内容并没有超出汉人评价的范围,而且刘勰以经评骚的方式恰恰是对汉儒以儒家经典作为衡量一切作品准的的治学观念的继承,与汉代人“依经立义”的观点实相契合。
三 “文之枢纽”与《辨骚》篇的写作原则
关于《辨骚》篇的归属问题,《文心雕龙》的研究者分歧很大。有人认为,《辨骚》篇虽属“文之枢纽”,但不是“总论”;而更多的人认为,虽属“文之枢纽”,但兼有文体论的性质。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未有定论。
要弄清楚这一问题,必须理清《辨骚》篇与“文之枢纽”其他各篇之间的内在联系。除了刘勰在《序志》篇中言明:“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他在《原道》篇中的阐述亦颇能说明“文之枢纽”各篇之间的关系:
爰自风姓,暨於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1]24-28
圣人根据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来进行著述,“创典”“述训”“敷章”,他们“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道、圣、经典各逞其义,然后才“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这段话即是《原道》《征圣》《宗经》三篇贯通之意旨。而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1]124,倚《雅》《颂》,驭《楚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1]164,可知《正纬》《辨骚》正是“彪炳辞义”之意。“《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文辞是“文之枢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道、圣、经、纬、骚就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又,刘勰在《序志》篇中写道:
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異,宜体於要。於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1]1909-1913
这段文字对我们理解《文心雕龙》的宗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解释了刘勰“乃始论文”的缘由。文章之用,五礼六典,君臣炳焕,军国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是为《宗经》篇之意旨;“去圣久远”,所以要《征圣》;“《周书》论辞”“尼父陈训”也是《宗经》《征圣》;“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则可以说是《辨骚》,因为《辨骚》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写作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段文字就是《征圣》《宗经》与《辨骚》三篇之间互相承接的理路。“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1]163-164则是《辨骚》篇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是《辨骚》篇作为“文之枢纽”地位树立的一条作文准则,是刘勰对《楚辞》作用的一种界定。
关于作文,刘勰主张征圣宗经,他在《征圣》篇中写道:“是以论文必征於圣,窥圣必宗於经。”[1]46在《宗经》篇又写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1]56并指出:“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1]83-84同时,他也认为“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1]50,“若稟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1]82,虽然是强调圣文之“雅丽” “衔华”,须以“佩实”为基础;作文要“禀经以制式”,“富言”须“酌《雅》”而为,但是却从另一面证明了圣人之文也须“衔华”和“富言”。所以他在《征圣》篇中说圣人(生知)“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1]53,指出圣人为文是“辞富山海”的,并不排斥文采,只是有一个前提,必须以雅、实为基础。刘勰从圣人的角度肯定了文采、辞藻,这就为《辨骚》篇和之后关于文辞的内容提供了依据。
因为《楚辞》有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可以作为辩证学习的典范,刘勰便以《楚辞》为载体把以上思考融合起来,于是就有了《辨骚》篇所谓的“倚经驭骚,酌奇存真,玩华保实”的“驱辞力、穷文致”之法。“倚《雅》《颂》”即是宗经,“驭楚篇”就是要“酌奇而不失其真”,存其“真实”,避免“楚艳汉侈,流弊不还”[1]85的文病,也就是要不诡、不诞、不淫,“玩华而不坠其实”就是“衔华而佩实”。因此,《辨骚》篇是《征圣》《宗经》篇“衔华佩实”“酌《雅》富言”思考的继续。
《通变》篇云:“名理有常,体必资於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於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1]1081“资於故实,酌於新声”是刘勰“望今制奇,参古定法”[1]1106的“制奇”之法。而这一方法实即是《辨骚》篇写作原则的另类表述,指导文章“通变”之法的就是《辨骚》篇树立的原则。实际上,刘勰作《辨骚》篇,就是要从文章写作原则上纠正《楚辞》以来不合于经典那一方面的文风,消除其不合理的影响。刘勰接受《楚辞》入“文之枢纽”即是接受了文章自《楚辞》以来之“变” “变乎骚”即是此意。“倚《雅》《颂》”“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与《通变》篇所谓的“矫讹翻浅,还宗经诰”一样都是通,都是为了合于经典的规范,使“变”有所依。既“宗经诰”,又“变乎骚”,以此达到“通”与“变”的平衡,以期明文章发展的“通变之数”。
综而述之,《辨骚》篇是对《征圣》《宗经》篇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所树立的指导人们如何“驱辞力” “穷文致”的写作原则,是文士作文通达经书“六义”的途径之一,亦是“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之需要,这也是《辨骚》篇“文之枢纽”地位的体现。它更多表现为一种指导如何“为文驱辞”的方法论的意义,而不是所谓的“文体论”的性质。这与《文心雕龙》全书的宗旨和性质也是相符的。[3]7-24在《通变》篇的结尾,刘勰希望后世作者为文驱辞要“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1]1102,“会通”与“适变”并举,这与“倚经驭骚”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刘勰就是要把“文”之变纳入可以指导的范围内,防止再次出现“楚艳汉侈”的流弊。一如《征圣》篇所说:“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1]45
四 《辨骚》篇写作原则与“正言体要,恶乎异端”的思想
《序志》篇在陈述了“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等“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背景后,郑重引用了《周书》和孔子在《论语》中说的话:“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於要。”此处的“《周书》论辞”,即《尚书·周书·毕命》所谓:“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4]245“尼父陈训”即《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5]2462异端指不合正道者。
在《征圣》篇中也有相似的征引:“《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不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美。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1]47-49“《易》称”来自《周易·系辞下》:“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開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6]89“《书》云”即与《序志》篇的“《周书》论辞”一样同为引用《尚书·毕命》的内容。《风骨》篇也引述了这句话:“《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1]1069
“体要”的要求接着也出现在了《诠赋》篇和《奏启》篇中。《诠赋》篇云:
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於雕虫,贻诮於雾縠者也。[1]307
《奏启》篇云:
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1]871
《诠赋》篇和《奏启》篇的这两段话共同透露出了刘勰“体要”观的一些精髓,即“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为文写作应表达要义,有一定的常规、法度,否则就会导致“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的弊病。《风骨》篇引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便直接言明“盖防文滥也”,亦是此意。此外,刘勰在《神思》篇中还提到了艺术构思和写作时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意翻空而易奇”[1]984“辞溺者伤乱”[1]1000,而“正言体要,恶乎异端”的要求恰恰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实际上,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引用《尚书》《周易》和孔子之言,就是想借用经书和圣人的地位,来表达他关于作文运辞必须符合“正言体要、恶乎异端”要求的思想。《楚辞》有四事“同于《风》《雅》”,是为正言;四事“异乎经典”,即是异端。因此,《辨骚》篇提出的“倚经驭骚,酌奇存真,玩华保实”的写作原则,即是倚正言、去异端、存体要要求的体现。而这些思想的反复出现,归结起来还是为了指导如何“驱辞力”。
五 “诗骚”传统的形成与《风骨》篇对《辨骚》篇写作原则的补充
“奇文郁起”的《楚辞》之所以被刘勰列为“文之枢纽”与《时序》篇所谓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1]1653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屈平联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1]1664,“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於是乎在”[1]1677,“且《诗》《骚》所标,并据要害,故后进锐笔,怯於争锋”[1]1751,《楚辞》之艳说“笼罩雅颂”,“衣被词人,非一代也”[1]162,其影响已大到与《诗经》“并据要害”,即与经典并驰,几乎取得经书的地位。
《楚辞》之所以有这么重大的影响和这样高的地位,原因就在于汉魏以来“诗骚”传统的逐渐形成,“诗骚”或“风骚”并举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多次这样运用,如《章句》篇云:“六言七言,杂出《诗》《骚》。”[1]1270《练字》篇云:“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1]1467《物色》篇云:“且《诗》《骚》所标,并据要害。”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亦是如此运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於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7]1778同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巨著的《诗品》也是“风骚”并举,如:“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2]43钟嵘更直接将《诗经》《楚辞》列为所品论诗人的源头。
“诗骚”传统的形成,再加上“爱奇之心,古今一也”[1]1475,受《楚辞》影响,当时人们为文写作出现“尚奇”“尚艳”的倾向有其必然之势。《楚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1]160,可谓风力遒劲,但自汉以来的文人“祖述《楚辞》”,多是学习《楚辞》之“奇辞”与“艳采”,刘勰自己也认为“屈宋以楚辞发采”[1]1770,于是便有了“楚艳汉侈”“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1]1777,纪昀就曾在评论《辨骚》时说道:“辞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辨’字极为分明。”[1]133因此,在文章的写作中,就难免会出现“瘠义肥辞,繁杂失统”等“无骨之征”[1]1055,面对这样的情况,刘勰便联系“风骨”谈到了如何驾驭“奇辞”的问题。
《风骨》篇说:
若夫镕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莩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1]1066-1069
刘勰以经典为本,要人们以经书为典范来学习写作,再杂以子书和史书的写作方法,并深入了解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情况,详悉各种文章的体势,然后便能“莩甲新意,雕画奇辞”,这是刘勰在洞悉《楚辞》对后代文章的影响后,对如何掌握运用其所代表的“奇辞新意”提出的指导原则。
此外,《风骨》篇一开始就提出:“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於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1]1048《楚辞》上接《诗经》,四事“同於《风》《雅》”“气往轹古”,忠怨之情溢于言表,但《辨骚》篇提出的“倚经驭骚,驱辞穷文”之法却没有谈到作文之前应先树文章之“骨”,《风骨》篇涉及到了这一问题,指出在“驱辞力”之前,首先还应练“骨”,“情与气偕,辞共体并”[1]1073,否则又会导致与“楚艳汉侈,流弊不还”相似的“习华随侈,流遁忘反”[1]1071的局面和弊病,这是刘勰关于如何“驱辞力”的又一条准则,亦可视为对《辨骚》篇写作原则的补充。
六 执正以驭奇
在《定势》篇中刘勰将其关于《楚辞》的思考进一步深化。《定势》篇说:“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1]1117“模经”与“效《骚》”的指归似乎相反,但是刘勰转而指出:“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1]1120-1124奇正虽反,却不对立,必须“兼解以俱通”;如果爱典恶华,爱经恶《骚》,就会导致“兼通之理偏”。重要的是“功在铨别”“随势各配”,要“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1]1125。
近代辞人和新学之锐们却没有“循体而成势”,他们“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1]1134,“逐奇而失正”[1]1140,最后导致“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1]1140。面对这样的情况,刘勰指出“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1]1140,“执正”即同于“倚《雅》《颂》”,“驭奇”则等于“驭楚篇”。模经“自入典雅之懿”,是为正与典雅,效《骚》“必归艳逸之华”,是为奇与华艳,因此“执正以驭奇”也即是“倚经驭骚,酌奇存真”,是对《辨骚》篇思想的概括。刘勰还指出“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反之,若执典雅之经,驭华艳之《骚》,爱典而不恶华,则能“兼解以俱通”“兼通之理”不偏,这是他在《序志》篇中提出的“擘肌分理,唯务折衷”[1]1933思想的体现,也是刘勰遵循儒家中庸思想的一种表现。《辨骚》篇所树立的“倚经驭骚,酌奇存真,玩华保实”的写作原则亦是这种“折衷”观的体现,“唯务折衷”才能经骚相济,正奇兼解,典雅与华艳兼通。“折衷”观实际上也贯穿于《文心雕龙》的整个体系中,说其是《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亦不为过。
结语
《文心雕龙》以《楚辞》为载体述文章写作之法与运辞之道,既是汉魏六朝时期业已形成的“诗骚”传统巨大影响的体现,也代表着《楚辞》本身对文章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它的“奇”与“华”,为“文”之发展提供了“宗经”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当然,刘勰认为“文”必须以“宗经”为本);而《辨骚》篇树立的写作原则和其他篇章对这一原则的补充与丰富,不仅有助于解决当时的文坛弊病,而且对南朝至唐初绮靡浮艳文风的改进亦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1]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增订本)[M].第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王运熙著.文心雕龙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阮元校刻.尚书正义[M]//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5]阮元校刻.论语注疏[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6]阮元校刻.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7]沈约撰.宋书:第六册:卷六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王 露〕
ChuCiintheViewSystemofTheLiteraryMindandtheCarvingDragon
HUANG Wenbin
(CollegeofArts,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 541006,Guangxi,China)
Accroding toTheLiteraryMindandtheCarvingDragon·Tongbian,ChuCiwas the turning point of literary writing from quality to novelty, with a desire to achieve the balance between “tong” and “change” in article writing through “Zong Jing and Gao” and “Change on Sao”.It was for this reason that Liu Xie elevatedChuCias the “Literary Pivot”, and put forward the writing principle inDiscriminationofLiSao, which placed emphasis on harnessingChuCi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Ya and Song, pondering over novelty without breaking its trueness, using flowery language without sacrificing the fact, putting the change of Wen into the scope of guidance for literary writing.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ofDiscriminationofLiSaois to guide people how to use rhetorics creatively and give full play to language.This principle had a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thought of “Using correct words to expound the point without pursuing heresy”.The article ofFengguandFixedTendencyalso complemented and enriched the writing principles proposed inDiscriminationofLiSaofrom different angles.In fact, Liu Xie usedChuCito state how to use rhetorics and give full play to language, which was the unique point of his interpretation ofChuCi.
TheLiteraryMindandtheCarvingDragon;ChuCi;Tongbian;DiscriminationofLiSao
2014-09-10
黄文彬(1990-),男,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与文论研究。
I207.22
:A
:1671-5365(2014)11-004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