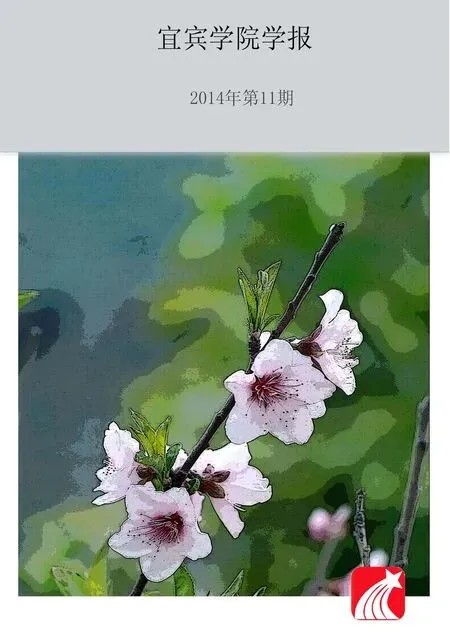接受美学视角下的直接翻译与逆向翻译——基于《金锁记》与《倾城之恋》英译本的比较
付迎雪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英语学院,北京 100024)
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和逆向翻译(inverse translation),又称服务型翻译(service translation),是与翻译的方向性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根据 Mark Shuttleworth 和 Moira Cowie[1]41所著《翻译研究词典》的定义,直接翻译是指译者译入自己的本族语或者常用语的翻译形式,反之则为逆向翻译。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内罗毕建议书》均要求译者应尽可能采取直接翻译的形式。随着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英语国家的翻译研究学者和从业人员处于较为优势的地位。提倡直接翻译,那么将外语译为英语就需要以英语为母语或者常用语的译者来进行,这当然更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样的大环境强化了国际组织对翻译方向性的规定性要求,即更倾向于直接翻译。
目前,翻译研究对逆向翻译总体上持消极态度。李美的《母语与翻译》一书可以算是从母语对翻译的干扰角度,比较直接翻译与逆向翻译的研究著作。[2]书中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对直接翻译的积极倾向。该书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认为母语对译者的干扰妨碍译者的表达,从而影响译文的接受。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对直接翻译与逆向翻译译本的个案对比中,研究者往往会挑选有利于该臆断的案例,证明此先入为主的观念,而非系统性和客观的对比。本文选取张爱玲的两部代表作《金锁记》与《倾城之恋》的英译本进行比较(《金锁记》由张爱玲翻译,为逆向翻译,《倾城之恋》由汉学家金凯筠(Karen S.Kingsbury)翻译,为直接翻译),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直接翻译与逆向翻译对译文接受的影响。
一 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起源于德国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在阐释学和现象学的基础上,以Jauss和Iser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创立了接受美学。1967年,Jauss于康斯坦茨大学发表就职演说,后以《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为题发表论文,标志着接受美学的诞生。这篇文章阐述了接受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Iser的就职演说《不定性与读者反应》(Indeterminacy and the Reader’s Response in Prose Fiction)在学术界也同样引起了轰动。80年代中期,接受美学传入我国,在文学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其影响后来远远超出文学理论界,渗透到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尽管Jauss与Iser都关注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但Jauss主要从宏观上考察文本的接受和文学史,而Iser则关注微观上的读者阅读过程研究。接受美学并无系统化的理论阐述,常被应用在翻译研究领域的概念主要为“期待视野”“文本的召唤结构”“隐含读者”。
(一)期待视野
期待视野这一概念源自哲学阐释学,特别是Heidegger与Gadamer的学说。
Gadamer[3]认同 Heidegger的“此在”概念,即“此在”是历史性的、有局限的,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主体与客体是内在地存在于历史中的。因此,真正的理解不能通过古典诠释学提出的方法实现(即通过克服主体的历史局限性,消解主体与客体间的历史距离,实现对文本的客观理解)。真正的理解应通过发挥这一历史性,获得新的视野来得以实现。主体对客体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而这样的“偏见”由于不可避免,因而是合理的,不应被设法排除,反而会积极促成真正的理解,引导主体进行创造性的阐释,而非对文本的意义进行复制。
Gadamer又提出“视野”这一概念,指从某一视点可以观察到的所有视野。理解既不能要求主体克服其历史局限性来迎合文本,又不应过度发挥“偏见”,消解文本,而是来自主体与文本间的互动,阐释者的任务在于将其现有的视野与客体内在的过去的视野相融合。因此,视野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处于不断的发展中的。基于视域融合这一概念的基础上,Gadamer提出了对话逻辑的概念。阐释者的中心任务是找出文本中内在提出的问题,理解文本就意味着理解这些问题。只有当文本向主体发问时,文本才会成为理解的客体。主体与客体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对话的状态,在此过程中,主体跨越客体的历史视野,与之进行融合,主体的视野反过来也被改变。[4]5
Jauss在吸收阐释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期待视野”这一概念,即“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对作品显现方式的定向性期待,这种期待有一个相对确定的界域,此界域圈定了理解之可能的限度。作家创作出文学作品,不是创造出一种把观赏者排除在外、作为事实独立存在的一系列事件。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独立自定、对每个时代每位读者都提供同样内容的客体。它不是一座文碑独白式地展示自身的超时代本质,而更像一本管弦乐谱,不断在它的读者中激起新的回响,并将作品从本文的词语材料中解放出来,赋予它以现实的存在。这就是说,离开了读者及其反应,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堆印刷符号组成的词语材料,不能算是现实的存在”。[5]10
期待视野这一概念对翻译研究有重要启示。但翻译研究往往关注原文的可译性和译文的可读性,读者被视为被动的接受者,如果超出其接受能力,与其期待视野不相符合,文本便失去了文化交流价值。按照这样的逻辑,接受美学就成了直接翻译的理论依据。潘文国在《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一文中,针对格雷厄姆只承认直接翻译的合理性的结论便称“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更是如此”[6]。但需要指出的是,接受美学不同于后来在美国兴起的较为偏激的读者批评理论,将读者视为文本价值的唯一评判者。接受美学将阐释视为一个文本和读者对话的过程,读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有创造力的主体。在这一点上,穆雷认为,“如果把读者看成具有期待视野的接受者,这种读者应该具有理解和接受异域文化的要求及心理准备,有一定的审美情趣和接受水平,他就是要通过阅读译文去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译文读者对译文不是被动地去接受,而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译文进行再创造”,“具有这种主观能动性的读者才是真正的接受者”。那么在翻译时,一方面就要考虑读者现有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能力,如果文本和读者的审美距离过大,译文不能被读者接受,文本便失去了文化交流的作用。另一方面,正如穆雷所说,“在接受理论看来,艺术作品的历史本质不仅在于它再现或表现的功能,而且在于它的影响之中。译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再现了原作这件事本身,而且还在于它对译文接受者所产生的影响……译文读者的阅读过程不但是一个接受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过程”[7-8]。译者不仅有传递原文信息的责任,更有通过翻译,提升读者期待视野的责任,这对长远的文化交流是十分必要的。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逐渐得到认可,并且被视为必要就是逆向翻译的产物。在拓宽读者期待视野的同时,逆向翻译还可以使进一步的逆向翻译更容易被接受,在传播中国文化和中文语言特征层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文本的召唤结构
文本的召唤结构是Iser根据Ingarden的现象学理论提出的概念。Iser认为,任何文学本文都具有未定性,都不是决定性的或自足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需要读者的具体化才能完成文本的生成。Iser据此将文学文本分为艺术级和审美极。艺术级指的是作者创造的文本,审美极则是由读者完成的文本意义潜势的具体化。读者的具体化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到文本文学性的制约。[9]
就翻译研究而言,董务刚认为,“译文也是一个文学本文,译文的存在本身并不能产生独立的意义,而要通过译文读者的阅读使其意义的实现具体化,最终达到译文的彻底完成。译文读者在解读译本时,会受到译文的内在特性的规定和制约。原作、译作中的语言文字通过语音、语调、语义建构、修辞格等层次逐层递进地为译者、读者指示着重构意向的途径,规划着译者、读者的审美价值取向。不光译者、读者不是被动地接受,原作、译作也不是消极地被解读,它们对译者、读者也在发生着作用和影响”[10]。这与人们臆想的接受美学的内涵是有所差别的。一般认为,接受美学,顾名思义,即研究读者的“接受”。但实际上,接受美学并非仅仅关注读者的接受,它还包括对文本的召唤结构和文本与读者的互动研究。
(三)隐含读者
傅修延将此概念概括为“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作为一种纲要性的图式化结构,有限的文本会对读者形成一种召唤性结构,期待读者在阅读中通过自己的意向性活动去填补其中的空白和不定点”[11]155。因此,Iser理解中的隐含读者是一种超验的、符合作者全部阅读期待的东西,它代表着文本中一切潜在的阅读可能。现实生活中真正的读者只能凭着自己在具体化过程中所作的选择,完成对隐含的读者的部分实现。如果直接翻译与逆向翻译译文文本确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那两者的隐含读者很可能是不同的。直接翻译因为在语言和文化层面更易为英语本族语读者所接受,其隐含读者可能为一般的、更为广泛的英语读者。而逆向翻译则更有可能被国外的汉学研究专家和有一定汉语基础的外国读者所接受。接受美学不仅可以作为直接翻译的理论依据,也同样可以作为逆向翻译的理论支撑。
二 《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的译本比较
(一)《金锁记》与《倾城之恋》英译本简介
《金锁记》是张爱玲最负盛名的代表作。1955年,张爱玲移居美国后一心想跻身美国小说界,成为职业的英文作家。为此,她将其最为成功的作品《金锁记》改写成英文小说,取名为《粉泪》(Pink Tears),但被美国出版社拒绝。在《粉泪》的基础上,张爱玲创作了英文小说《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由英国的Cassell出版社出版,但评论和读者反映都比较冷淡,这使张爱玲放弃了成为主流英语作家的努力。1971年,张爱玲受夏志清委托,将《金锁记》译为英文,收录在夏志清所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里。
海外汉学家金凯筠(Karen Kingsbury)曾多次在香港出版的《译丛》(Renditions)上发表张爱玲的散文和小说英译。2007年,由金凯筠翻译的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倾城之恋》被美国“发行量大、影响深远,撰稿人多是学界、知识界一时之选”的《纽约书评》出版发行,被刘绍铭赞为“张爱玲作品‘出口’一盛事”[12]90。《纽约书评》在欧美出版社中声誉极高,由该社出版发行张爱玲作品,对于张爱玲文学走向世界来说是个极具意义的里程碑。向来以选录标准极为严格而在英语文学圈影响巨大的英国企鹅经典文库于2007年12月收录了金凯筠英译的张爱玲作品集《倾城之恋》。可以看出,张爱玲的逆向翻译译本在当时的接受度远远低于金凯筠的直接翻译译本。但是否证明直接翻译比逆向翻译更具有合理性呢?
(二)《金锁记》与《倾城之恋》英译本对比
1.期待视野
(1)翻译策略
张爱玲自译的《金锁记》(The Golden Cangue)是一个十分忠实的译本,从语言到文化层面,均保留了原文的特点,这是一般认为逆向翻译常有的特点。《倾城之恋》的英译属于直接翻译,但仔细考察译本,金凯筠同样采取了异化的策略。
鉴于两篇小说篇幅并不长,为了较为客观和全面地对比两者的特点,笔者将《金锁记》与《倾城之恋》中的全部文化负载词进行了归纳,如表1、表2所示。

表1 《金锁记》文化负载词翻译

表2 《倾城之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由表1、表2可见,张爱玲对这些极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词语,采用了十分忠实的直译策略,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征。金凯筠的《倾城之恋》译本也采取了同样的翻译策略。金凯筠的直接翻译和张爱玲的逆向翻译译本在译文的语言特征上并无明显区别,这印证了Pokorn《挑战传统原则——译入非母语》一书的发现:“翻译的质量并不取决于译者的母语,主要取决于译者的个人能力、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对源语语言与文化及所涉及领域的了解程度”[13]。针对文化负载词,张爱玲和金凯筠均采取了非常忠实的直译翻译策略,仅从译文文本很难判断孰为直接翻译,孰为逆向翻译。
事实上,读者接受是张爱玲创造和翻译中重点考虑的问题。但是,张爱玲对读者并不是一味迎合。她对读者的“中心”地位有非常理性和辩证的认识[14]71。她在《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一文中提到“我从来不低估读者的理解力”,在散文《我看苏青》中,张爱玲说:“迎合大众,或者可以左右他们一时的爱憎,然而不能持久”。在《论写作》一文中,张爱玲的观点是“作者有什么可给,就拿出来,用不着扭捏地说:‘这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罢?’那不过是推诿。作者可以尽量给他所能给的,读者尽量拿他所能拿的”[15]59。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张爱玲的观点符合对期待视野概念的辩证认识。虽然可能会冒着不被当时的读者接受的风险,但是张爱玲坚持选择非常异化的翻译策略,这并不是张爱玲没有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而是恰恰相反。金凯筠的译本也并没有显示出对读者现有期待视野的妥协,而是非常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和文化特色。张爱玲的译本是对原文十分忠实的翻译,在当时接受度可能并不十分理想,但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加,英语读者的期待视野也在发生变化,《倾城之恋》英译本的成功就是一个例证。
译者与原文作者一样,也有心目中的理想读者,译文展现的图示化结构也是为了“隐含读者”而存在,并不是为了所有现实中的读者。张爱玲并没有因为实际读者的阅读偏好而作出过度调整,在文化层面的翻译上,张爱玲仍然坚持直译,造成了十分强烈的陌生化效应。这在后期张爱玲翻译《海上花》时更为明显,甚至冒着不被一般读者接受的危险。林以亮评价这种译法为“字眼扣得准,行文流畅,绝不采用英美俚语,以免造成化华为夷的印象”[16]75。金凯筠的译文一经出版便受到较高认可,但金译本并没有表现出对大众的英语读者的过分妥协,反而译文风格和张爱玲的英译本接近。金译本的成功,张爱玲作品读者接受度的提高,都说明了张爱玲当时的翻译策略和对读者接受的辩证认识是有前瞻性的。随着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增强,中国文学的英译本展现出对原文语言风格和文化上的忠实倒是迎合了作品的隐含读者的期待视野。
(2)社会文化环境
a.《金锁记》英译本出版时西方社会文化环境
讨论读者的期待视野离不开对社会文化环境的考察。从20世纪50年代《金锁记》英译本的出现到70年代收录进《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西方世界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
二战后,美国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人民对未来情绪乐观,但很快就被美苏的冷战所打破,麦肯锡主义盛行。虽然张爱玲并不喜欢过问政治,但《金锁记》中对破落、摧残人性的封建大家庭悲剧的书写会被人别有用心地认为是颂扬共产主义的证据[17]。蓝诗玲在其文章 Literary Leap Forward①中将中国文学与日本现代文学在西方的接受差异进行了总结,她指出冷战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20世纪50年代,美国为了扶植日本成为区域同盟来对付中国,通过精心选取日本现代小说,将日本塑造为一个安静且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国家,完全不同于日本战前的侵略和极端形象。而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蓬勃兴起的时期,将自己隔离在西方世界的外面,西方读者并不能接触到中国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此时,英国学校开始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翻译的质量参差不齐。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读者本来就不太愿意读翻译作品,出版社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英译本的选择上工作比较粗糙,更加深了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印象,即中国一味重宣传鼓吹共产主义,而日本作品则讲究美感和人文气息,因此,可以忽略中国文学作品。这导致了张爱玲出版《金锁记》英译本的困难。
b.《倾城之恋》英译本出版时西方社会文化环境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与外界的交流增多,西方读者对中国的了解逐渐增加。中国也积极走出去,向世界展示中国。张爱玲的作品走出去,李安的贡献不可否认。笔者在亚马逊书店上搜索“Love in a Fallen City”,在读者的评论中发现很多读者是因为受李安电影的影响去读《倾城之恋》的英译本的:
自从李安的电影《色·戒》上映,读者对这位与众不同、避世隐居的作家又产生了新的兴趣。②
2.文本的召唤结构与隐含读者
夏志清所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在当时的美国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权威的教材。刘绍铭在美国教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时,必少不了研究张爱玲的作品。在课堂上,美国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反应热烈,对鲁迅、巴金和茅盾的作品,他们都积极给出自己的看法,只有张爱玲是个例外。当他们被提问时,他们会说“搞不懂其中复杂的人物关系,不知道作者想表达什么”[12]4。但在考试的时候,一位平时很少发言的女生对《金锁记》中的女主人公七巧的评价是“这个女人令人毛骨悚然,太变态了,太邪恶了”。可见,外国读者也能对书中人物得出同样的印象,但在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世界里,《金锁记》这本有着浓厚中国封建社会色彩的小说还是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尤其是其中复杂的人物关系。《金锁记》的故事发生在封建大家庭内部,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封建文化的根基十分深厚。
《倾城之恋》相对于《金锁记》来说,故事情节较为简单。故事虽是以封建大家庭为背景开始,以封建大家庭为背景结束,但故事的主体主要是男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对话,与封建文化背景关联并不大。故事的主要情节发生在香港,其中的风土人情对外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
文本召唤结构上的差异无法一一从各个结构进行详细剖析,在本个案研究中,最主要的差别体现在主题层次。笔者在亚马逊书店上搜索“Love in a Fallen City”,发现读者对《倾城之恋》英译本评论更多,对小说的理解也较为深刻,而对《金锁记》的评论则十分有限,寥寥数语,甚至还有明显的文化误读:
在小说《金锁记》中,缺乏交流影响了家庭关系。二奶奶想和老太太交流时,云泽讽刺道:“她的话,老太太哪里听得进?”老太太那一代人并不听家庭中的年轻一代说话,她是象征性的“有点聋”。她忽略年轻人的愿望,只允许他们参加她允许他们参加的活动,发展她允许他们发展的关系,这最终导致了家庭成员关系的紧张③。
隐含读者概念决定了读者对文本的阐释不能是任意的,而是要遵循文本的召唤结构的安排,《金锁记》因其浓厚的封建色彩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其隐含读者与现实中的西方读者群体差距较大,而《倾城之恋》的译者金凯筠能较好地把握原文的召唤结构④,进而翻译该小说,后来其英译本在西方读者中接受度较高,可以归结为《倾城之恋》原文本身的隐含读者涵盖的范围较广。两个文本接受度不同,还与原文的隐含读者有关,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翻译的方向性。
结语
直接翻译与逆向翻译的对比研究对于中国译者从事汉译英的合理性论证有着重要的意义。接受美学不仅研究读者的接受,它还有更为深厚的内容,不能望文生义,认为接受美学只是对读者期待视野的研究,仅仅为直接翻译提供理论支撑。接受美学也不否认逆向翻译的合理性。接受美学不是一味提倡为顺应读者当前的期待视野采取归化策略的理论,除了对读者接受能力的考虑之外,接受美学还有更深刻和广阔的内容。
翻译的方向并不会导致译文在语言上的显著差异。直接翻译并非一定会采用归化的策略,逆向翻译也未必会呈现异化的特征,当然关于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理论论证和语料支撑。类似Pokorn的研究还没有在语言系统差别较大的英汉语之间展开,Pokorn的研究是否能在英汉翻译中得到验证还有待发现。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对直接翻译和逆向翻译的先入之见,在研究中就选择有利于该臆断的例证,这样只会加深成见,不利于得出科学的研究结果。影响译文接受的因素很多,除了语言的可读性外,宏观的社会环境因素对译本的接受度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不能仅仅把译本接受度的不同归因于翻译的方向问题。
注释:
① 参见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5 -06/23/content_453803.htm中的相关内容。
② 原文为:Since the release of Ang Lee’s Lust,Caution which was based on one of Zhang’s short stories,interest in this unusual and reclusive writer(Eileen Chang,added by the author)has been revived,该段文字为笔者译。
③ 原文为:In the novella The Golden Cangue,miscommunication interferes with family relationships.After it is inferred that Second Sister-in-law would like to speak to Old Mistress,Yün - tse cynically comments,“as if Old Mistress would listen to anything she had to say!”.The older generation,Old Mistress,does not listen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of her family.She is symbolically“a little deaf”.She ignores the desires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and only allows them to partake in relationships or activities she agrees with ultimately heightens tension between her family members,该段文字为笔者译。
④ 金凯筠翻译《倾城之恋》的具体细节参见覃江华《语言钢琴师——美国汉学家金凯筠的翻译观》一文,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Shuttleworth M,Cowie M.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李美.母语与翻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3]Gadamer H -G.Truth and Method[M].New York:Crossroad,1975.
[4]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5]Jauss H R.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J].Trans.Elizabeth Bengzinger.New Literary History,1970,2(1):7-371.
[6]潘文国.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J].中国翻译,2004(2):40-43.
[7]穆雷.从接受理论看习语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J].中国翻译,1990(4):8-14.
[8]穆雷.接受理论与习语翻译[J].外语研究,1990(1):61-65.
[9]Iser.The Act of Reading: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
[10]董务刚.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53-59.
[11]傅修延.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2]刘绍铭.到底是张爱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13]余静.《挑战传统原则——译入非母语》述评[J].中国翻译,2011(1):52-54.
[14]杨雪.多元调和:张爱玲翻译作品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
[15]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16]林以亮.更上一层楼[M].台北:九歌出版社,1986.
[17]游晟,朱健平.美国文学场中张爱玲《金锁记》的自我改写[J].中国翻译,2011(3):4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