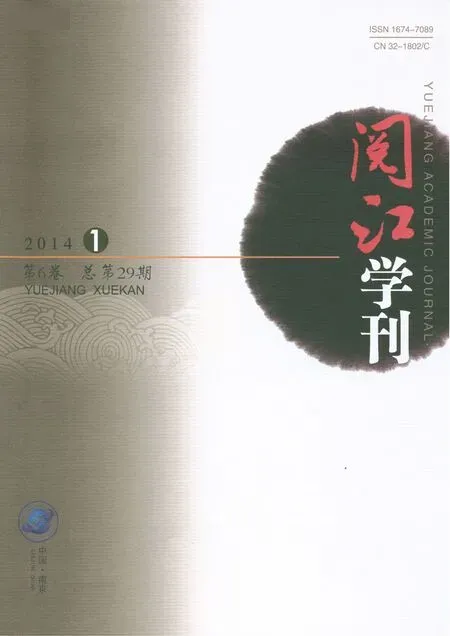阿多诺与德里达比较研究
吴娱玉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240)
阿多诺与德里达比较研究
吴娱玉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240)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以瓦解的思路开启了后现代主义的滥觞,其“内在批判”的否定策略和“星丛”理论与德里达釜底抽薪的“自毁原则”、“延异”理论殊途同归,然而,阿多诺浓厚的现代主义情怀使两者的否定观有本质区别,阿多诺否定之后依然“有”而德里达解构之后走向“无”;对于未来理想的建构,阿多诺认为,艺术是现实的反题,“星丛”是理想化的乌托邦,而德里达的建构则是深度批判、无限开放、走向未来的弥赛亚式的希望。
阿多诺;德里达;“星丛”;“延异”
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里承前启后的核心人物,被称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与巴赫金、本雅明齐名的“最富创造力的伟大的原创性理论家”[1]。在他博大精深的古典音乐修养的基础上又融会贯通了蕴含后现代因子的勋伯格无调式音乐元素,于是,他的哲学思维不自觉地成为后现代思潮的滥觞。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发出令人振聋发聩的论断——“人的死亡——奥斯维辛之后不再写诗。”在对同一性的深恶痛绝,对现代性的爱恨交错中,阿多诺通过绝望使希望存活,用“星丛”和“力场”构建了非中心化、非奴役性,彼此相安无事、相互映照的现代主义乌托邦。
德里达——激进的后现代理论创始人,卢迪内斯库赞誉其在知识界“相当于过去左拉和近代萨特的地位”。在《书写与差异》一书中对“异质性”、“延异”做了深入肌理的阐释,试图还原“不在场的在场”。他追求的写作的无底游戏,符号的“延异”和“踪迹”单刀直入地摧毁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权威,给柏拉图以来到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祛魅,而晚期德里达遭遇了只破不立的尴尬——“当我们拿起武器,却不知道向谁开枪”,“解构就意味着你永远也不必说抱歉”[2]。于是,他的思想愈行愈趋向保守,声称“解构是绝境中的思考,解构是面向未来的责任”[3]。
一
(一)拆解根基、内部攻破
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是他思想集萃的巅峰之作,实现了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作为一种划时代的哲学绝唱,终结了一个时代,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先河”[4]。他对全部史前人类思想发展的中轴线——同一性逻辑证伪,指称任何总体化都必然是一种暴力过程,没有同一性就不会出现惨绝人寰的奥斯维辛。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波兰加利西亚附近建立的最大的集中营和灭绝营。1940年4月,法西斯头目希姆莱下令建立第一个集中营。6月,关押波兰和德国的犹太人的“奥斯维辛一号”建立。1941年10月,法西斯在布热津卡(比克瑙)建立“奥斯维辛二号”,次年5月建立“奥斯维辛三号”苦役集中营。1940—1945年,纳粹将从世界各地运来的犹太人进行挑选,其中,年老体弱者,孩子被杀害,有劳动能力的青年男女被送入劳役集中营。纳粹在这里残酷地用活人进行医学实验,随心所欲地进行惨绝人寰的大规模杀戮。据估计,二战期间惨死于奥斯维辛的人又100万-250万,也有人认为高达400万。阿多诺对同一性不遗余力的批判是继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对形而上学的颠覆,他试图否定整个西方哲学的思想之根、哲学之源:“一”,阿多诺称其为“形而上学的西洋镜”。从柏拉图的“理念说”、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到康德先验架构的主体,再到“同一性”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客观化的绝对观念,“同一性”扮演着西方哲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奠基石的角色。后来,从尼采、叔本华、胡塞尔一直到海德格尔和萨特前仆后继的拆解摧毁,也不过是以隔靴搔痒,只是把“同一性”填衣加冠、改头换面以“权利意志”、“意向性”、“存在”的形式招摇撞骗,其实质仍旧是人类主体的同一性圈套。阿多诺痛心疾首地指认,主体同一性原则是造成奥斯维辛死亡之营的罪魁祸首,惨绝人寰的杀戮是追逐种族绝对同一的沉痛教训。
杰姆逊有言:“《否定的辩证法》中的毁灭观念与德里达的解构观念有着箴言式的家族相似”[5]。阿多诺釜底抽薪式地批判了传统人本主义和一切同一性哲学,与德里达环环解构、层层剥落的否定性拆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的理论建构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德里达没有确凿地指称其理论来源是阿多诺,而阿多诺也无意于后现代的语言游弋和“怎样都行”,但某种程度上,阿多诺的否定式批判与拆解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提供了前车之鉴。正如阿多诺对同一性追本溯源的评判一样,德里达解构的锋芒更是直击要害、一语中的,《播撒》解构柏拉图,《论文字学》结构卢梭和列维-斯特劳斯,《绘画中的真理》解构康德,《丧钟》、《哲学的边缘》解构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文字与差异》、《明信片》解构弗洛伊德,以及《马刺》解构尼采。德里达认为,自柏拉图到索绪尔以来,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它预设了一种静态的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的系统,这个中心常被命名为诸如理念、真理、上帝以及实体化了的物质或精神。德里达正是要刨根究底地拆解西方哲学思维的逻辑起点,从根本上发现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不合理和欺骗性。
不仅如此,阿多诺的深入肌理的“内在批判”与德里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自毁原则”大同小异。所谓“内在批判”即深入被批判对象的内部去揭露它的内在矛盾,通过宏观的自反构架炸开存在本体论的神秘之门,阿多诺说这“不是居高临下地裁判这种本体论,而是出自它自身的成问题的需要来理解它并内在地批判它。”[6]德里达颠覆结构的策略是利用被颠覆对象的潜在矛盾,使其自行瓦解、不攻自破。德里达称这一原则为“自毁原则”,它和阿多诺的“内在批判”不谋而合。在此基础上,两者避其主力、曲径通幽,试图通过边缘领域来获取解构中心,阿多诺在极权笼罩之外的废墟、痕迹、预兆中找寻反抗同一性的元素,德里达通过形而上学的“他者”来反抗形而上学。
(二)“星丛”和“延异”
阿多诺对个体性、历史碎片独具慧眼,对差异性、特殊性见解独到,凯尔纳认为其“坚定性和精彩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后现代理论家”[7],而阿多诺“批判思想的目的不在于把客体放在一度被主体所占据的、现已空出的皇位上。客体在这个皇位上不过是一种偶像。批判思想的目的是废除等级制。”[8]真正科学的唯物辩证法是非强制和非同一性的,完全革命和开放的,即否定辩证法。它不同于黑格尔的肯定辩证法,虽然黑格尔的矛盾论堪称精湛,然而,辩证法的目的却在于同一,否定之否定即是肯定,肯定辩证法的最终目的是调和矛盾。而否定辩证法恰恰剥落了“同一性”的外衣,以一种瓦解逻辑怀疑一切“同一性”。在阿多诺看来,非同一性是想说出某物是什么,而同一性思维则是说某物归在什么之下、例示或表现什么以及本身不是什么。“辩证法的结果是主张思想形式不再把它的对象变成为不可改变的东西,变成始终如一的对象。”[9]了消解“同一性”总揽全局的僵化现状并废除主客体孰优孰劣的等级制度,阿多诺从本雅明《德国的悲剧起源》中,借用“星丛”来建构一种新的主客体之间彼此照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又相安无事的伙伴关系,即“那种没有支配而只有差异相互渗透的独特状态”。把这种“集体主观性”“个体主观性”“客观世界”三星结集的有差别的和平交往称之为“力场”和“星丛”的非构架状态。
阿多诺的以一种瓦解逻辑否定“同一性”与德里达的反形而上学、打破二元对立的否定思维遥相呼应。德里达认为,从柏拉图到索绪尔,“语音中心主义”根深蒂固,潜移默化地对整个西方哲学思维发生着作用。语音是被赋予意义的主体,文字只是语音可有可无的替代物,其实质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文字的二元关系在哲学史上演化为精神和物质、主体和客体、心灵和身体、内容和形式、内在和外在、本质和现象、真理和假象等一系列二元关系。前者处于主导的中心地位,后者处于附属的边缘地位,德里达对这种二元关系进行解构,他认为,能指到所指不是直线对等的:幻变无形的大脑意识进入语言系统发生了变异,作为产物的符号是双重的、不透明的,符号内部是延异的、开裂的,因此,符号所构型的世界是无中心的、多元的。德里达认为,在意义中存在着差异和延宕,意义在任何语言结构中不会如期呈现,它总是受到一定语义延宕的影响,延宕使符号始终无法再瞬息中获得一致性的意义,它作为能指链中的一组符码发挥作用。他在《立场》中指出,“延异是一种无法在‘在场/缺场’这一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来被认知的结构和运动。‘延异’是差异的系统游戏,是差异的踪迹。”这样,意识内部不像过去是统一于一个基点之上,而是开裂的、碎片的,由多种不同的因素构成,在场是靠不在场表现出来的,他瓦解了先验的以言语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同时,他否认中心的坚固不变性,认为中心只是一种功能,“一种使无数符合替换物的活动成为可能的不定点”。值得一提的是,德里达并非以文字为中心反传统,这样只是以一种决定论代替另一种决定论依然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是要打破同一性走向差异与多元化,强调他者,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各种话语相互融合的互文性。正如阿多诺所言,在二元对立中,客体成为被支配的异己物而加以占有,这本身就是主体同一性的秩序的预设,这也就必然造成思想成为总体的内在要求。二元论的最终结果还是同一性。“星丛”理论消除了中心和边缘,第一性和派生性,本质和现象的固定关系。德里达也断然否定了辩证法和总体化的宏观理论,打破以二元逻辑制作的单一世界,强调差异性、片段性、多元性和异质性,两者的思想殊途同归。
二
(一)否定观的差异
有着浓厚现代主义情怀的阿多诺和彻底游戏化、碎片化的后现代哲学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认为阿多诺的哲学理念既是解构性的又是重构性的,这就在本质上区别于受到结构主义思潮影响的德里达的后现代理论。依阿多诺之见,后现代只是作为现代性的极限而出现,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包含了对后现代的批判,德里达解构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游戏形式,无一不在阿多诺理论的批判之列。阿多诺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渊源、与马克思主义的薪火相传使他对后现代主义敬而远之。德里达是在批判地解读胡塞尔现象学、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自成体系,别具匠心的阐释了解构理论。不仅如此,结构主义的先驱索绪尔的能指所指、尼采的隐喻理论为德里达提供了解构的可行性,思想源泉的差异左右了两者否定观的差异,可以说,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是击碎并瓦解主体众星拱月的优先地位,形成大小相当、彼此和谐、非奴役的“星丛”。阿多诺瓦解之后依然“有”,而德里达解构之后走向“无”;阿多诺的“星丛”理论是个体保持独立性之后的平等和平的“力场”,形成集体主观性、个体主观性、客观世界三星结合的场域;德里达“延异”理论质疑能指与所指的等价关系,认为内容在转换过程中无形地附着形式的踪迹,形成斑驳复杂的多重印记,个体的独立性被开裂的内核、传输中的重写、不在场的他者解构,形成彼此相容、缺失固定主体的深渊,科学运作在概念的死尸和躯壳之上,知识基于同一逻辑的僵化书写之上,与真理相去甚远,人类绞尽脑汁对符号的构建不过是走向谎言的圈套。由此,便不难理解阿多诺对真理和主体性在恨铁不成钢地否定中又千方百计捍卫与重构:他对传统真理观和主体性嗤之以鼻,认为不存在关于世界之系统知识的宏大叙事并符合事物本来面貌的描述意义上的“真理”,那只是资产阶级渴求“绝对精神安全”的反映。他击碎了试图以概念方式来把握总体存在的幻想并另辟蹊径地为真理求解,认为只有在逃避了全方位极权势力渗透之外的个性痕迹、废墟和预兆中,才能找到“符合事物的可能状况”的真理。尽管阿多诺反对唯心主义对主体过分夸大,也批判唯物主义对主体性的简单的还原,但他的毕生精力依然在重建主体性,他始终认为主体性是个体认知和实践的基本要素,因而需要构建一种具有自我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的主体性;而德里达对主体性置若罔闻、忽略不计,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阿多诺对个人主体性的信任和看重无非是启蒙理想的影响、精英主义的表现。后现代哲学最受人瞩目的是在话语的层面上批判现代哲学的形而上学,它对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是釜底抽薪式的拆解,它甚至大声疾呼“主体死了”,使得阿多诺对个人的崇拜也一样失去了根基。德里达消解主体性的方法无疑是更为彻底地拆除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甚至斩草除根地泯灭了主体存在的合法性,世界成了碎片化、多元化、无法接近真理的黑洞,接踵而至地陷入了一个自掘坟墓却无法自我救赎的怪圈:在“传统政治哲学中所研究的主体——作为个体的人与民族——都被宣称为语言的伎俩且阴险无比。政治哲学的客体——政治行为的独特领域——也被视为那个并不存在的任何中心的普遍关系中的一部分。”[10]后期德里达遭遇拆解之后的废墟之上的尴尬,什么都批判和否定,就是什么都不否定。后现代哲学之所以迷途深陷,恰恰在于离开了主体性驱动下的实践,消解了个人有所作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德里达身处的后现代哲学语境无意于实践层面而在话语层面用力颇多,就使其理论纠缠在可能性上面:似乎文本的可解释性无穷无尽,“延异”随时随地出没且没有任何限度。当注销个体、忽略实践之后,无根无基的“话语”在可能性中渐行渐远,哲学的所谓“彻底性”便成了文字游戏搭建的空中楼阁。
(二)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和弥赛亚式的希望
阿多诺依然以主体和理性为价值导向,其旨归是恢复真正的启蒙精神,他认同启蒙主义的“祛魅”思想,与马克思在人类实践的目的论维度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他的救赎之路是以作为资本主义反题的艺术建构平等和谐的“星丛”乌托邦;而德里达对差异性的关注并非要恢复启蒙精神,而是要彻底地揭示和暴露西方文化中无处不在的形而上学、声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乃至欧洲中心主义,怀疑西方文化传统和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阿多诺看来,人依然是救赎的力量,是具有批判意识、思考能力和反省精神的个体的人,因此,他的批判不是面向虚无的否定,而是抗争于不能抗争之境,期望于没有希望之中。而德里达坚持较为彻底的否定性,所谓“救赎”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它仅仅是建立在启蒙理想、精英主义基础上的一种权力话语而已。詹明信认为,阿多诺与现代主义一样在怀疑整体和总体的态度中想拯救整体与总体;而后现代则视整体与总体问题为不可能:“唯一被认可或可以接受的‘总体性’,是一个可能从创造性行动和自由选择的个体出现的‘总体性’。”[11]阿多诺不是不要统一和总体而追求和谐(更可能是表面上的、虚假的和谐)背后的那种内在的整体性,这也是“星丛”意义的呈现。正如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所说,“后现代主义对总体化理性的批判与阿多诺对总体化理性的批判是不同的,区别就在于后现代批判断然拒绝了和解哲学”[12]。“在阿多诺那里,和解哲学的前景代表着在非理性主义面前捍卫理性,代表着某种努力不懈的辩证尝试:在蹩脚的理性中彰显某种略胜一筹的理性的微弱印记。”[13]对理性的捍卫,也即否定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连续性;这无疑是否定辩证法至关重要的一面。不仅如此,阿多诺欣赏作品的不连续性、不和谐性和内在分裂。正是因为他崇尚这种内在性的最高价值,或者说是崇尚调和内在的不统一并把形式与内容结合起来的最高价值,而这种最高价值在历史现实中表现为不可能实现。因此,阿多诺认为,内在的矛盾是克服形式矛盾可能性的最后象征。他并不像德里达理论那样欣赏这种不连续性和分裂本身,而是认为不连续性和分裂比起那种虚假的、表面的和谐能够更有活力地说明内在性或调和内在不统一的价值。阿多诺还是古典式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整体性理论与对现实的要求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乌托邦色彩。他所期望的是已经过去的理想,而未来需要另一种思路来思考:从破碎的闲适出发找到现实的未来因素,这是后现代之后的革命,因为后现代本身不可能做到。
德里达势不可挡地一路拆解而来,面对拆除后七零八落的现代现场,又遭遇了人类正义不可解的尴尬,转而开始寻找一种面向未来的解构方法,他认为,“解构是绝境中的思考,解构是面向未来的责任”,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提出,保卫马克思就是保卫解构主义。他把马克思理解为一种异质性的精神、不断激化的批判精神和解放的世纪论:即弥赛亚性。德里达的“弥赛亚性”是一种现实性、革命性和肯定性,超越信念、对终结的超越、对正义的不懈坚持,“弥赛亚性”是不可解构的,它属于另一种模态。他以宗教般信仰的态度来面对“即将来临”,他就如此宣称民主制度,认为民主制度看似即刻来临,但是它始终“在路上”,是一个弥赛亚式的希望。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可能性的条件同时也是他的不可能性的条件。在这里,德里达与彻底否定做了妥协“如果没有这个关于不可能性的经验,我们就会同时放弃了正义和事件”[14]。他一直反复申辩的建构性便浮出水面,“与其说德里达是虚无主义者,不如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克尔凯郭尔式的信仰骑士。”[15]他把民主看作是“即将来临”的无限可能性的制度,是无限开放的弥赛亚式的希望。“星丛”是空间维度的民主,拥有存在的可能性却无法实现,实际是指向“有”的“无”;而弥赛亚式则希望是时间维度的民主,有着实现的不可能性却必不可少,是指向“无”的“有”。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阿多诺与后现代主义的大师德里达所涉猎的领域相去甚远,但是,阿多诺与德里达在对语言的不稳定性和历史性的共同关注、对哲学基础主义的一致拒绝、对形而上学、“同一性”与统治结构之间潜在关系的认识、对黑格尔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以及内部瓦解的批判模式等诸多方面有共通之处。不仅如此,阿多诺的思想同后现代主义有密切的关联,“表现在他对当代文化困境的深刻体会上,表现在他对现代主义的限度的辩证认识上,表现在他对和解不能现实的实现的真切意识上,表现在他对一种可操作性的文化救赎的彻底拒斥上。他自觉地完成了终结现代主义的任务,并且自然地转向对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文化状态的洞见。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思想,他对感性、个性、特殊性、偶然性的强调,虽然是对现代主义特征的把握,但距离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只有半步之遥。因为后现代主义只是把分裂的文化状态看作自然的状态,并且把这一状态同最终的和解彻底分离。”[16]其他理论家也发现了两者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追认阿多诺是后现代主义的“始作俑者”,然而,阿多诺是在进退两难中演奏现代主义的挽歌。德里达在从无底的游戏走向谎言的拆解过程中,面对七零八落的存在之尸、满目疮痍的人类文明,却无法找到一条脚踏实地行之有效的建构之路,两位文化巨人都遭遇到对铁板一块的同一世界拆解后理想主义的禁区,而否定思维、瓦解策略、批判精神是他们留给人类继续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的武器。
[1][英]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M].王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63.
[2][10][美]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M].邓晓箐,王笑红,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131,131.
[3]王晓明.德里达的底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5.
[4]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M].上海:三联书店,2001:15.[5][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9.
[6][8][9][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2,184,156.
[7][美]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300.
[11][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77.
[12][13][德]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M].饮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8,108.
[14][15][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94,94.
[16]陈刚.阿多诺对当代学的意义[J].文艺研究,2001,(5):68.
〔责任编辑:渠红岩〕
Com parative Study on Adorno and Derrida
WU Yu-yu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200240,China)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give rise to postmodernism with disintegrating thinking.Adorno's“immanent critique”negative strategy and“constellation”theory,and Derrida's drastic“self-destructive principle”and“differance”theory,each takes a different path towards the very same goal.However,Adorno's deep modernism feelingmakes the negativism of both fundamentally different.Adorno still keep affirmation after negation while Derrida doesn'tafter deconstruction.With regar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deal life,Adorno regard art as reality's antithesis,“constellation”as Utopia.In contrast,Derrida's construction is deeply critical,infinite and messianic hope towards future.
Adorno;Derrida;constellation;differance
I106.6
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3)06-0105-06
2013-11-20
吴娱玉,女,山西祁县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