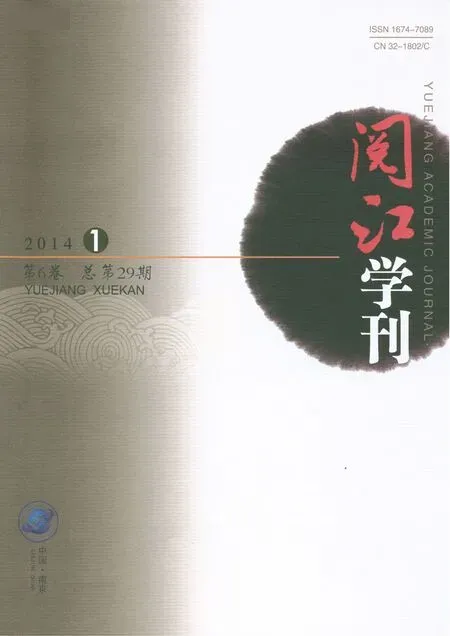论杏花村意象的文化内涵
纪永贵
(池州学院,安徽池州247000)
论杏花村意象的文化内涵
纪永贵
(池州学院,安徽池州247000)
杏花村意象是杏花意象与村意象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出现于晚唐。现存许浑、杜牧、温庭筠、薛能的四首诗不约而同地创设了杏花村文学意象,其中只有杜牧《清明》诗与酒家义项相关。明中叶之后,贵池杏花村被认定为杜牧当年吟咏《清明》诗的地方,从此,贵池杏花村与杜牧、《清明》诗的关系确定,地方风物也日渐丰富起来。康熙二十四年,贵池邑人郎遂编成《杏花村志》十二卷,后被《四库全书》存目书收录。民国四年,贵池人胡子正编成《杏花村续志》三卷。杏花村作为地方文化资源不断地被保护开发。杏花村意象包含四种文化形态,即村诗文化、村酒文化、村落文化和村游文化。
杏花村;村诗文化;村酒文化;村落文化;村游文化
杏花村意象是由杏花意象与村意象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出现于晚唐。现存许浑、杜牧、温庭筠、薛能的四首诗不约而同地创设了杏花村文学意象,其中只有杜牧《清明》诗与酒家义项相关。①关于《清明》诗是否为杜牧原创,学术界多有争议。该诗最早出现于南宋《锦绣万花谷·后集》,未署名,后来刘克庄《千家诗》将该诗归于杜牧名下。笔者颇疑杜牧对此诗的著作权,曾著《重审杜牧〈清明〉诗案》(《池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献疑。但笔者近日读李定广《〈唐诗三百首〉有宋诗吗?》(《学术界》2007年第5期)一文中“由于唐代文献散失之严重,许多唐诗名篇皆首见于南宋以后文献”之观点,很受启发,认为在新证出现之前,《清明》诗归于杜牧名下的说法较为务实。宋代诗词也有20多例咏及杏花村意象,元明清戏曲小说中提及杏花村意象已非常随意,《红楼梦》大观园里就有一处“杏帘在望”。从宋徽宗时周邦彦的词作《满庭芳·忆钱唐》“酒旗渔市,冷落杏花村”之句开始,杏花村意象与杜牧《清明》诗遥相呼应,成为僻村酒家的代称。
作为地理上的村名,今存最早提及杏花村的文献出于南宋,金陵有杏花村,但此村与杏花村文学意象无关,既无酒家之义,也未与杜牧《清明》诗相牵连。明代初年,有文献显示,安徽贵池城西有杏花村。②郎遂《杏花村志》卷十一记录了一份明洪武四年(1371)郎家的《户牒》:“郎礼卿,池州府贵池县杏花村居住。”这份材料被证实是真实可靠的,同格式的户牒今共存19件。参见陈学文《明初户帖制度的建立和户帖格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方骏《明代户帖研究》(2011年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明中叶之后,因杜牧于唐武宗会昌四年至六年(844—846)任过池州刺史,此杏花村被认定为杜牧当年吟咏《清明》诗的地方。从此,贵池杏花村与杜牧、《清明》的关系确定,地方风物也日渐丰富起来。而同时期金陵、徐州、扬州、淮阴、麻城、南昌、玉山等处的杏花村因与杜牧无关,未能沉积相当的文化史料。而今世俗所知的山西临汾杏花村只不过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产生的“杏花新村”,因为它没有历史根据,没有文献积累,没有诗词吟咏,没有文化内涵。
康熙二十四年,贵池邑人郎遂编成《杏花村志》[1]十二卷,后被《四库全书》存目书收录。民国四年,贵池人胡子正编成《杏花村续志》[2]三卷。上世纪50年代开始,贵池开始复建杏花村,早期只是概念复建,即将一些单位或地名冠以“杏花村”字样,21世纪初开始实体复建,十二年来,已经建成两个杏花村文化公园。2012年,池州市政府开始大规模建设杏花村文化旅游区,划拔土地35平方公里,计划建成一个集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为一体的大型民俗休闲度假区。
那么,杏花村意象到底包含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概括地说,不外乎四种文化形态,即村诗文化、村酒文化、村落文化和村游文化。若用当今旅游业界的词汇来说,村诗文化是旅游特色,村酒文化是旅游品牌,村落文化是旅游产品,村游文化是旅游目的地。
一、村诗文化
杏花村文化的内涵首推“村诗文化”。村庄本是客观的民间存在,要让其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则需要中国古典诗歌的推波助澜,而诗歌与村落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一)诗里的村
村是后起字,其原字是“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邨,地名,从邑,屯声。”到了东汉中后期,“村”字开始出现于典籍中,如东汉末年的魏伯阳《周易参同契》“鼎器妙用章”第三十三:“得长生,居仙村。”南北朝时,“村”字被收入字典《玉篇》中,如《玉篇》卷十二“木部”:“村:千昆切,聚坊也。”卷二“邑部”:“邨,且孙切,地名。亦作村,音豚。”可知此时村、邨二字已经通用。至南北朝时期,“村”的主要含义是指比较偏僻地区的老百姓的生活居住点,有“聚落”的性质,村与市往往相对应。
在唐代之前,尤其是南北朝时代,村人群聚的村落已经相当普遍。有人统计过六朝的村名,现存史籍中能找到的有86个村名,如孝敬村、吴村、平乐村、东亭村等,北魏也有38个村名。“这些村名分布于今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等地,此正是南北朝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区。”[3]
唐朝开始推行“村”制度,将所有野外聚落统一命名为“村”,并依据村内家庭户数的多少设置管理者“村正”。“村”正式成为一级基层组织。“村”制度开始于武德年间,至开元年间逐渐完善。《旧唐书·食货志》:“武德七年,始定《律令》。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唐六典》记开元七年:“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家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这些材料已经明确了村与邑、坊的对应关系。村的出现是人口发展、人民生活区域向郊外拓展的相应设置,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赋税管理。在唐代文献中,出现最多的村的组合词汇如村乡、乡村、村坊、村邑、村落等等,都在说明村是向野外延伸的人民生活居住地。
1.诗里的村
魏晋之后,随着村概念的形成,这个概念也向文学意象演化。如陶渊明《桃花源记》:“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桃花源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村庄,但这个村庄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一个没有政府、没有官吏、没有赋税的理想生活境地,这正是作者的写作目的之所在。这个远离凡尘、远离社会不公的村落,是偏远与自由相结合的境界。
陶渊明提到村意象的诗如《归园田居五首》(六首)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首诗反映了陶渊明卜居村野、心甘情愿的诗人情怀。他是第一位将自己放逐村野、重返自然的诗人,因为他能从村野之处寻找到人生快乐与诗意境界,为唐代之后的诗人大规模地奔向村野塑造了一个典型形象。
《全唐诗》数万首诗歌中吟到村意象的诗就有上千例之多,应该说这是一个常用的意象。王维、杜甫、刘长卿、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商隐、罗隐、韦庄等大诗人,均是村诗的写作者,其中以杜甫与白居易二人所写村诗最多。
诗人喜欢写村诗,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美学趣味是密切相关的。如杜甫,长期生活在民间,对民间疾苦和民间温情都有很深的体会。他居住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边,“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其实也是居住于地道的村庄里,名叫浣花村。杜甫有《江村》、《村夜》、《到村》、《村雨》等诗作。
白居易至少有92句诗歌用到了村意象,诗题如《村居苦寒》、《村雪夜坐》、《朱陈村》、《渭村雨归》、《村居卧病三首》、《过昭君村》、《游赵村杏花》等等,一见就知,他到过很多村庄,非常留念那些村落生活。朱陈村就是他发现的一个著名的民间村落,这是一个极为典型的唐代村庄,诗人描绘了村庄的方位、耕作、婚姻、亲情、生死等生活内容,最后表明,自己身为官员,人生却如此艰难苦闷,哪里比得上这村庄里的村民幸福啊!“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非常符合中国村落的实际情况,即使今天依然有这样的村庄格局存在。
当然,这些只是出现了“村”字的诗歌,有些诗写到了村庄但没有点明村意象的诗则会更多。唐代的村诗主要体现了诗人的五种趣味:第一是描写民间疾苦的村诗;第二是对农耕渔樵生活的诗意描绘;第三是向往村落生活的宁静悠闲;第四是表达对村落风景的赞美;第五是对村落偏远荒凉的感叹。唐代诗人从政治寓意出发,发表乡村感慨,多半有政治上遭受打击后,希望到村野之处寻求解脱的心理期待。从这个意义上看,村意象其实只是唐代诗人精神追求的一种写照。正因为乡村具备了那种宁静悠远的品性,所以,容易成为诗人表达情感的意象工具,因而诗人喜欢到村庄去展望,去表达,去郊游,去卜居。
宋人祝穆《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十六,在编排诗歌时,特别设立了一个名目“村”,搜集了因诗歌吟咏而称名于后世的村庄,如花柳村、浣花村、落花村、杏花村、黄叶村、朱陈村、老木村、兴廉村、村鼓村、明妃村等二十余例,这些都是古代诗人所吟咏过的村庄,都已变成了一个一个的文化村落。
2.村里的诗
杜牧全部诗作中就有20余例出现村意象的作品,这体现出他对村落的关怀之情。而《清明》这首诗就像是一个象征,标志着杜牧对村落文化的最完美关注。杜牧写作村诗的用意大体不出以上五种,《清明》诗则是为了寻芳问酒,排忧解愁。而杜牧的忧愁来自何处呢?仅仅是清明时节春困渴酒吗?当然不是。杜牧来守池州正处于其政治上的低潮期,借酒浇理想之愁则是其寻酒杏花村的用意。
自从杜牧来游杏花村之后,杏花村从一个基层管理单元一跃成为唐诗村意象群里耀眼的一员。唐宋元明清,一代一代的诗人经过杏花村,都要为其歌咏感叹,留下了十分可观的同一主题的诗歌大系。这不是一般村落所能拥有的机遇。唐诗中的吴村、赵村、力疾山下都有一团团杏花,但它们都没有获得长久的生命力。而杏花村意象在唐诗里一共只出现了4次,仅杜牧的一次歌咏就让其进入了历史。
《杏花村志》共十二卷,有五卷都是诗词题咏,卷五是七言绝句,卷六是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卷七是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卷八是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绝句及词赋。这是按作者排列的。另外,在介绍杏花村105个景点时,绝大部分都附了历代诗人对该景点的歌咏之作,有的一二首,有的竟达十多首。可以说,仅仅一处杏花村,两部志书所搜集的诗作可以千计,这种情况对全国其它的所有的文化村落都是不可想象的。杜甫居住过的浣花村,咏过的明妃村,白居易钟情的朱陈村,苏轼独创的江南黄叶村等都没有像杏花村那样,日久年深,因为一个主题而汇集成了一个诗歌的长河,从这个角度来看,杏花村真不愧为“天下第一诗村”。
说到杏花村文化,诗文化是其本色。没有诗人的关注,没有诗意的提炼,没有诗歌的抒写,这个村落只会与无数的村落一样,虽然宁静淡远,虽然霜枫雪梅,虽然杏花如火,终不会成为文化的承载者,而只会是一个有山有水有树有花的被遗忘者。杏花村的村诗文化是在唐诗大背景下衍生的新现象,是既可以载入史册,也可以面向现实的。所以,村诗文化是杏花村文化的第一要义。
二、村酒文化
诗人来到杏花村,是什么吸引了他的眼球呢?当然是杏花;是什么搅动了他的内心世界呢?当然是杏花村美酒。可以说,杏花村之所以能引来杜牧,就是他听闻了这里有美酒可以酣饮。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村酒就是杏花村的第一招牌。
(一)文人与酒
在中国古代,文人与酒早已结下不解之缘。唐代之前的魏晋时期,酒对文人的影响已经达到一个极致,最著名的是“竹林七贤”,以阮籍、嵇康、刘伶为代表,他们“一醉累月轻王侯”,逃避政治,娱情诗酒,留下许多饮酒的华章。
东晋时期,陶渊明是一个豪饮大师,他的诗文中提到酒字的就有近40次,他还专门写了一个组诗《饮酒二十首》,其三云∶“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这是他的人生宣言,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他是不愿意的。他认为,“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决然回归田园。从此,村是他的归依,酒更是他真正的知己。陶渊明饮酒作诗的生活模式极大地影响了后代文人。
有唐一代,诗潮涌动,而酒的消费量也是相当大的,诗人们好像无人不饮酒。初、盛、中、晚四个时段,数千诗人各持秉性,诗歌风格不尽相同,但饮酒之风却是惊人的相似。皇帝宴请大臣,朝廷为新科进士开办杏园宴,朋友出门远行要喝酒相送,朋友来了更要喝酒助兴。达官贵人品美酒,民间村落饮村酿,各尽其乐。
唐代初年,王绩仿照《桃花源记》写了《醉乡记》:“其土地旷然无涯,无丘陵阪险;其气和平一揆,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任清,无爱憎喜怒。呼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其行徐徐。与鸟兽鱼鳖杂处,不知有舟车器械之用,并称之为醉乡。”他还写过《酒经》、《酒谱》等书。李白饮酒比陶渊明更加疯狂:“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就连杜甫的诗,也是十有七八要点到酒。白居易晚年曾自号“醉吟先生”,可见其酒兴诗兴之深浓。
杜牧也是饮酒赋诗的高手,其诗中仅提到“酒”字的就有上百次。我们不妨略引数例:
酌此一杯酒,与君狂且歌。(《池州送孟迟先辈》)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江南春》)
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夜泊秦淮》)
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遣怀》)
金英繁乱拂栏香,明府辞官酒满缸。(《九日》)
江湖酒伴如相问,终老烟波不计程。(《自宣州赴官入京》)
潇洒江湖十过秋,酒杯无日不迟留。(《自宣城赴官上京》)
解印书千轴,重阳酒百缸。(《秋晚早发新定》)
腹中书万卷,身外酒千杯。(《送张判官归兼谒鄂州大夫》)
杜牧对酒的态度是再明白不过的了:“落拓江湖载酒行”、“酒杯无日不迟留”、“重阳酒百缸”、“身外酒千杯”。当他来到杏花村前,不问其它只问酒,就不足为奇了。
文人与酒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印记之一。酒可以令人洒脱,可以让人忘忧,可以与朋友共享,也可以与佳人同醉,不一而足。杜牧杏花村寻酒也可作如是观。
(二)诗与村酒
唐代制酒业发达,酒品丰富,所以,遍地均可饮酒。杏花村里的酒其实是村酒,即村庄人家自酿的酒品,比起皇帝的御酒可要差很多。唐代的地方官酒是各州镇官营酒坊酿造的酒。如元稹诗中提到“院榷和泥碱,官酤小曲醨”、“官醪半清浊,夷撰杂腥膻”。白居易在《府酒五绝》中说“自惭到府来周岁,惠爱威棱一事无。唯是改张官酒法,渐从浊水作醍醐”,看来这些酒的质量也不如诗人意。
而民间的酒多来自酒肆、酒楼、酒家、酒舍、旗亭等处。中唐诗人韦应物有一篇《酒肆行》,就曾写到民间酒肆饮酒的盛况。有村酒,就必然会被诗人写进诗中。据统计,《全唐诗》提及“村酒”的诗有19首,《全宋诗》同类诗有140余首。唐诗中除卢纶、张南史、白居易之外,使用此意象的诗人均生活于晚唐。宋诗中只有20首写于北宋,其余120余首全出于南宋,其中陆游一人就有29首之多。当然,村酒并不是迟至晚唐才会有的,孟浩然《过故人庄》里“把酒话桑麻”饮的那酒一定也是村酒,可是,村酒作为文学意象是在晚唐才出现的,如白居易《村中留李三固言宿》:“村酒两三杯,相留寒日暮。勿嫌村酒薄,聊酌论心素。”这说的是自己暂住在村中,只有村酒待客,又怕客人嫌酒味淡薄,所以写诗告白。晚唐郑谷的村酒诗就写得非常有味道,如《张谷田舍》:“县官清且俭,深谷有人家。一径入寒竹,小桥穿野花。碓喧春涧满,梯倚绿桑斜。自说年来稔,前村酒可赊。”粮食丰收了,就可以用粮换酒了。又如杜荀鹤《山中喜与故交宿话》:“远地能相访,何惭事力微。山中深夜坐,海内故交稀。村酒沽来浊,溪鱼钓得肥。贫家只如此,未可便言归。”这些诗都是吟咏民间村酒之乐事。
酒是用粮食酿造的,但是水质好坏是相当重要的,凡是水质好的地方便容易出好酒,江水不如河水,河水不如泉水,泉水不如井水。杏花村里恰好有一口古井,“泉香似酒,汲之不竭”,名曰“黄公广润玉泉”,后来演化出一个“黄公酒垆”的酒店。“黄公酒垆”是《世说新语·伤逝》里的一个典故,杏花村古井借用其名,更能衬托出此地水好酒美的事实。杏花村地处贵池城西,三面环山,村东南是湖,村西边缘地带是秋浦河与杜湖,湖水、河水、山泉水经过过滤,生成这口清泉。杏花村里也有村酒,是村酒引来了诗人杜牧,是酒的力量让村庄在诗人的笔下爆发出诗意。所以,杏花村文化的品牌就是酒,是村酿中的佳品,是解愁的首选之物。
三、村落文化
村落文化内涵丰富,比如村落布局、房舍建筑、道路桥梁、山水命名等都可体现村落文化的特色,此处只就农耕与民俗略作申述,因为它们才是最重要的村落文化要素。
(一)农耕主题
《清明》诗里有农耕生活吗?当然有,杏花就是农耕的一种象征。杏花是杏树的花,结的是杏果,杏果是农耕生活中经济作物与食物之一种,杏果及杏核自古就有多种食用、药用功能。村落之中,除了田地里的粮食作物之外,园圃自古就是村人们赖以生活的另一极,园中种菜,圃中种果。民间很早就已经培植了众多的可食用水果的苗木,桃、杏、李、梅、梨、枣等常见村果,对于村人来说,是生活资料的一部分,但对于诗人而言,它们则幻化成美不胜收的花花世界。来到杏花村的诗人大多被杏花的繁盛所感动,因杏花的凋落而苦恼,却很少有人将笔触伸入那也许饱含着农民种植杏树“棵棵皆辛苦”的生活层面。或者可以说,对于一团一团的红杏花来说,诗人醉心的是花色,村人关注的是果实。从果的酸甜到花的美艳,其实就是让农耕上升到文化的过程。
牧童是农耕生活的另一种写照。牧童在诗中,寄托着诗人的一份理想,那便是无忧无虑的童年与淳朴自由的村野相结合的心境。诗人们对此往往情有独钟,唐代诗人对牧童早有关注。略举数例: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王维《渭川田家》:)
不言牧田远,不道牧陂深。所念牛驯扰,不乱牧童心。(储光羲《牧童词》
无奈牧童何,放牛吃我竹。隔林呼不应,叫笑如生鹿。欲报田舍翁,更深不归屋。(李涉《山中》)
谁人得似牧童心,牛上横眠秋听深。时复往来吹一曲,何愁南北不知音。(卢肇《牧童》)
牧童见客拜,山果怀中落。昼日驱牛归,前溪风雨恶。(刘驾《牧童》)
牧童向日眠春草,渔父隈岩避晚风。一醉未醒花又落,故乡回首楚关东。(杜荀鹤《途中春》)
王维羡慕牧童的“闲逸”储光羲讲的是“童心”,李涉讲牧童的淘气,卢肇说牧童吹笛,刘驾描绘了牧童的天真可爱,杜荀鹤看见牧童便起思乡之情。诗人们各有侧重,都将牧童意象理想化,将其化作一处心灵的彼岸,为自己寻找证词。
牧童其实是村里的放牛娃,他们所牧之牛正是家里农耕的重要工具。他们驱牛出村,或在地头,或在河边,或在山岗,或在路旁,牧童时有吹笛之事,那不过是消磨时光、自娱自乐而已,多半属于白居易《琵琶行》中所说的“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可失魂落魄的诗人却能从中参透禅机。
《清明》诗因为短小,无法展露杏花村里农耕渔樵的丰富主题。上引陶渊明《归田园居》、白居易《朱陈村》以及王维的诗就细致描写了村里景象,王诗说:“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但是,即使是《清明》这首小诗,依然隐隐约约地提示我们,杏花村里有农耕背景,引导诗人进入村庄的是一个牧童,牧童的身傍自然是一群耕牛。这意味着,牧童与耕牛的背后会有一个桃花源般的农耕世界。杜牧进入杏花村之后,一定也会看到像《桃花源记》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的村落景象,他还会看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情景,而引导他的正是一个“垂髫”牧童。
对于杜牧而言,“牧童遥指”自有其精神上的深意。“牧童心”是纯洁而无忧的,牧童所指一定是一个理想境界。
清明时节,杏花开放,是一个春耕即将开始的季节。《文选》李善注曰:“《氾胜之书》曰:杏始华荣,辄耕轻土、弱土;望杏花落,复耕之,辄蔺之。此谓一耕而五获。”宋人称作“杏花耕”,如北宋的宋祁有“催发杏花耕”、“先畴少失杏花耕”、“催耕并及杏花时”等诗句。
《杏花村志》卷十一记载了一份郎遂家的《户牒》,是洪武四年(1371)政府颁发的。郎家的“事产”是“屋五间,基地八分”,这就是活生生的生活生产资料。
(二)民俗世界
村落文化的核心内涵其实是民俗文化,民俗其实就是生产、生活的方式与仪式,民俗理想会让人生活得更有意义。杏花村里的105处景点,其实都是民俗文化浓缩的要点,包含着民间生活生产方式、民间信仰、民间传闻、民间关怀和民间约定等,那些寺庙庵坛就是民间信仰的寄托,那些楼台亭阁、坡驿桥洲、碑井坊园就是民间生活的生动写照,尤其是历代名人的墓葬,体现了民间浓厚的人文关怀。可以说,民俗文化是杏花村文化的主体部分,村诗文化、村酒文化、村游文化都是围绕着它而发生的,而民俗文化又是建立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清明》诗也包含着时代民俗因子,那便是“清明饮”的习俗,甚至可能还包含着一丝对“杏园宴”的回味,杜牧有诗“何事明日独惆怅,杏花时节在江南”,写的就是他对长安杏园的怀念。在唐代民俗生活中,寒食、清明时节的饮酒就是全民性的,这更为“杏花时节”的饮酒提供了现实许可。
寒食节传说是纪念春秋时晋国介之推的,历代都有寒食禁火的规定。在唐代,寒食节禁火三天,即冬至后第一百零四天、第一百零五天、第一百零六天三天。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寒食第三节,即清明日矣。”寒食期间,虽不能生火,但并不禁酒,如韦应物《寒食》:“把酒看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白居易《寒食日过枣团店》:“酒香留客住,莺语撩人诗”,王建《寒食看花》:“酒污衣裳从客笑,醉饶言语觅花知”,等等。
清明是寒食结束后的乞新火之日。清明节期间,节俗很丰富,其中,饮酒也是一件寻常之事,有驱寒逐暖之意。李群玉《湖寺清明夜遣怀》“饧餐冷酒明年在,未定萍逢何处边”,来鹄《鄂渚清明日与乡友登头陀山寺》“冷酒一杯频相劝,异乡相遇转相亲”所写即是,正如宋代诗人魏野《清明》诗所咏:“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
清明没有酒难以避寒,没有花也索然寡味。清明时节有些什么花呢?无非是杏花、李花、桃花、梨花等,其中杏花花期最早,自然也就容易受到关注。吴融《忆街西所居》:“衡门一别梦难稀,人欲归时不得归。长忆去年寒食夜,杏花零落雨霏霏。”罗隐《清明日曲江怀友》:“鸥鸟似能齐物理,杏花疑犹伴人愁。”来鹄《清明日与友人游玉塘庄》:“几宿春山逐陆郎,清明时节好风光。归穿细荇船头滑,醉踏残花屐齿香。”寒食清明时节,正是杏花开放之时,看花与饮酒是极普通寻常之生活内容。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的行人为何欲断魂呢?一定是心境、时境、事境让其精神困倦,而寒食节是不能热食的,雨纷纷更增添了心境的凄冷,于是寻酒取暖、借酒浇愁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不是任何季节来杏花村饮酒都可值得关注,民俗约定,寒食清明之际,可以进村沽酒,即便饿着肚子,也可以肚暖心热、一醉方休。
《杏花村志》和《杏花村续志》也记载了一些康熙年间及之前和民国初年的民俗传闻,这些传闻有的在今天看来已荒诞不经,但它们是当时村民生活与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杏花村志》卷十二记录了许多异闻趣事,如西庙神道坊两石柱相传是从水中浮来,贵池人遇岁旱率众来西庙井中取水、登坛祈祷则大雨立降、咸拜昭明之事;崇祯十一年,灾荒居民在杜坞山掘得白土“观音粉”充饥;崇祯末,三台庵老僧青莲预言明清换代及剃发事;顺治间,杜坞梅雨有蛟;康熙间,乾明寺延高僧数十众三载顶礼千佛忏;杏花村里的孝文化;池阳李氏子前生后世等。《村志》里收录的郎氏《户牒》与世系均是珍贵的民俗资料。
《杏花村志》在记录村西文物“梁照明庙”时还记载:“池人以八月十五日为昭明诞辰,先期十二日,知府率寮属,迎神像入祝圣寺,十五日躬致祭,十八日送还庙所。盖贵池里社无不祀昭明为土神者。”卷九录有一篇《池州迎昭明会记》,详细描述了赛会迎神之事。四乡八傩八月十五朝觐昭明太子的活动是贵池傩祭的主要内容,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地方祭祀的民俗资料。
《杏花村续志》也载有乾隆三十三年夏大疫、昭明神托梦饮水“解厄泉”之事,每岁西庙赛会迎神之事依旧,民国三年胡子正等为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选池阳负郭名胜十二景,拍照用相框制为挂图之事等等。
杏花村民俗可以视为贵池地方民俗的缩影,民俗不会只局限于一村一户,而是有一个相对宽泛的传播区域。所以,了解并研究杏花村民俗,不必局限于杏花村文献,而应关注贵池、池州及皖南的其他文献。同时,民俗具有横向传播与纵向传承的特点,时光流逝之后,地方民俗还在会相当长的时间内延续保存。但是民俗又具有泥沙俱下、鱼成混杂的特点,所以,吸收并发扬优秀的民俗传统,扬弃那些过时荒诞的民俗,是今天开发杏村民俗文化的重要任务之一。
四、村游文化
杏花村地处郊外,本不为外人所知。杜牧来守池州,闲暇之日寻芳西郊,终于酿成杏花村公案。试问,杜牧为何能去?何为而去?因为古代官员有法定的休假制度,他便有闲暇时间去游山水;因何而去呢?因为寄情山水是古代文人的痴绝之处。正因为文人往来山水田园,诗意便油然而生,山水田园得天地之灵气,再得文人墨客之雅意,于是中国山水田园文化获得持久的发展。
(一)休沐制度
唐代之前,诗人都是贵族官员或者曾经阔过的二代三代,那种我们想象中的基层人士是少而又少的。官员兼从政与创作的双重责任,是唐代的一大特色。一处山水,若没有官员去关注题咏,只会是聋哑山水,不会传名入史。而地方官员,杂务烦多,如何有那闲情逸致去玩山弄水呢?
大约从西汉开始,官员就有了休假制度,即休沐制度,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汉书·郑当时传》载:“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休沐。”《汉书·万石君传》说:“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到了唐代,休假制度从五日休一天改为十日休一天,即在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的最末一天休息。唐高宗永徽三年(652),朝廷改“五日休沐”为“十日休沐”,即“旬休”。休沐又称作“浣”,俗称上浣、中浣、下浣。不过旬休规定非常严格,官员若不能遵照执行是要罚俸和丢官的。
休沐制之外,唐代还有其它的节假日。唐代的节日是十分丰富的,除了我们今天还在过的节日外,另有人日、社日、中和、寒食、上巳、中元以及各种诞节(即生日)等,这些节日都要放假,比如每年的“清明”、“冬至”还要放一到三天的假,让官员回家祭祀祖宗。
古代的各级官员都有自己的休息闲暇时间,这些时间有的人用来处理内务,有的人休养身心,有的人探亲访友,而有的人则游山玩水。尤其是地方官员,每到一处,必得先了解附近山水概况,然后择日登山涉水,他们往往与朋友、仆从一道,如柳宗元《小石潭记》:“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不仅要野炊野饮,还要赋诗作文,以记其盛。唐代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都是游山玩水的“顽主”。而他们用来寻幽探胜的时间是由休沐制度提供的,如《杏花村志》卷九陈元钟“官署多暇日,登临兴欲诗”,就是一个极好的表述。
(二)寄情山水
文人寄情山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文人的心目中始终存在着一对互补的处世概念:入世与出世,儒家与道家,拯救与逍遥,朝廷与民间,政治与江湖,这种对立的二元概念是古代文人矛盾心境的不辍情结。在朝之人往往挂念山水,而身处江湖却又难忘政治,杜甫身处民间却“每依北斗望京华”,“是故身处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阙之下”(《淮南子·俶真训》)。
唐代的文人爱酒,也爱山水。山水包含崇山峻岭,奇山怪石,江河湖海,村流涧溪,田园渔樵等等方面。这些就是道家所追求的“与自然万物者游”的“逍遥游”。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柳宗元被贬到湖南永州和广西柳州,政治上陷入苦闷,但却被南方的奇异山水所陶醉,《永州八记》所记景点虽小,但篇篇韵味十足,他竟因此获得另一番出神入化的人生体验,他也因之为我们后人营造了令人无法忘怀的经典山水之作。
杜牧“三守僻左,七换星霜”,从黄州到池州再到睦州,山水田园游是其休沐时间或行路途中的主要功课。杜牧在池州写的诗一共有22题之多,除了7题送人诗外,其余15题全是游池州景物诗,如《池州清溪》、《题池州贵池亭》、《池州废林泉寺》、《游池州林泉寺金碧洞》、《题池州弄水亭》、《赴池州道中作》、《九日齐山登高》、《清明》等。郎遂在《杏花村志》卷四“人物”一章介绍杜牧时说:“《樊川集》中池州诗最多。当其刺池时,喜登眺齐山、清溪诸胜,又尝游历金碧洞、杏花村,皆见诸题咏。明九华吴光锡刻《杜樊川池州诗集》行世,盖池州山水实以牧重也。”可见,杜牧在池州的创作不是送人,就是游历,送人也是需要山水背景的,好像其他官民俗事都不如池州山水能提起他的诗兴。
村落风景只是山水画卷中的一个斗方,这一方水土浓缩了山水田园的所有文化因子,所以,诗人不必远游,只要来到杏花村里,那些奇山异水所能给予的心灵慰藉都一样能在这里获得。《清明》诗虽短,竟然提供了十个意象来营造杏花村:清明、春雨、道路、行人、断魂、牧童、耕牛、杏花、村庄、酒家。清明是季节;春雨是天气;道路指向人生;行人并不孤独,断魂因为忧闷;牧童象征着淳厚天真的心境;没有出场的耕牛能坐实村庄的存在;杏花象征着生机勃发的春天;村庄彰显出村落文化远离尘嚣的品质;酒代表浇灭春愁、获得解脱、通往自由之境的知音。这十个意象在诗人心灵上的叠加,便令其陡增诗兴,出口成章。这一处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理想之境,就是诗人村游的好去处,也是后人留连往返的目的地。
五、结 语
一千三百多年来,杏花村意象有两条发展线路:一条是唐代文人在不经意中创设之后,被后世文人所认可;另一条是宋代之后文献记载的现实存在。这两条线路在明代中叶的贵池相互融合,成为有了领域归属的文学意象。历代文人相互唱和,遂致其文献积累于史册。杏花村意象是有其独特文化内涵的,它不同于其它山水、田园、村镇,它是由一首诗所引发,经过千年的文化裹挟,已经被打造成为一个在现实发展中可以实现“杏花梦”的平台。
那么,针对地方上正在建设的杏花村复建工程来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期待呢?
开发杏花村,既不丢传统,更需要创新。有两种模式的复建思想:一种是按历史上杏花村的原样画瓢,修旧如旧;另一种是利用杏花村的历史文化内涵,重新打造的杏花村景点布局。千年杏花村,不同历史时期的物质村落格局各不相同,村内景点也不断更新,没有一成不变的杏花村。我们今天说到的古杏花村格局其实只是康熙年间的杏花村,在杏花村历史上,它不一定最丰富,也不一定最具有代表性,但是因为历史资料的缺失,所以,康熙杏花村模式已经成为我们认可的标准模式。可是,时光流逝,郎遂所见到的那一切都已消散。今天我们重建杏花村,既不能脱离曾经有过的存在,天马行空,随意描画,也不能按图索骥,固步自封。
建成的杏花村,是村不是城。今天开发杏花村不能延续三十年前贵池县“把杏花村变成杏花城”的思路。杏花村得天独厚的文化品格是,它是一个远离尘嚣、承载农耕文化、饱含民俗因子、在生活与精神之间搭建诗意桥梁的“村落”,是不可以进行“城镇化”的“野孩子”。这里有民间风情,这里有乡村生活,这里有幽山野水,这里有渔隐樵逸。
建成的杏花村,是公不是园。杏花村文化旅游区拟建土地共有35平方公里,这是杏花村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疆域拓展,也是杏花村复建史上最大手笔。杏花村复建完成后,展现给世人的应该是一个开放式的文化观光体验区,而不能再是一个个高墙内的神秘花园,墙里花开而墙外不香。历史上,杏花村从未有过围墙,杜牧可以自由出入,郎遂可以随处寻芳,胡子正也可以踏遍青山,寻古问幽。
文有文心,商有商道。文化是人类存在的价值之所在,文化有独立的品格,文化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化不可以随意涂抹,更不能矫揉造作,取媚于俗。但文化复建离不了商业投入,商业本性需要最大回报。所以,要做到历史与现实兼顾,文化与商业并行。杏花村文化旅游区建成之后,既要让人认可这就是历史杏花村的延续,又不能只在故纸堆里比划推演;既要做到文化先于商业,更要做到商业反哺文化。
(5)开发杏花村,文化是魂,品牌是神。复建杏花村,要尊重杏花村历史文化的内核,要还“杏花村”古朴自然的天性。杏花村作为文化品牌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虽经千年历炼,依然芳香四溢。杏花村生长于贵池城西的青山绿水间,千年等待,千年孤独,终于等到了骐骥一跃之时,应该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如果最后建成了一个缺乏文化品位的杏花村,不仅是对杏花村品牌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会使之难保长存的命运。
[1]郎遂.杏花村志[Z].康熙二十四年聚星楼刻本.
[2]胡子正.杏花村续志[Z].1915年稿本、铅印本.
[3]刘再聪.村的起源及“村”概念的泛化[J].史学月刊,2006,(12).
〔责任编辑:渠红岩〕
On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Image of Apricot Flower Village
JIYong-gui
(Chizhou University,Chizhou 247000,China)
The image of Apricot Flower Village is the result of combination of the apricot flower image and the village image,which first appeared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Four poets of XU Hun,DU Mu,WEN Tingjun,XUE Neng simultaneously created the image of Apricot Flower Village and only DU Mu's poem Qing Ming is related to the semantic item ofwineshop.Aftermid-Ming Dynasty,the Apricot Flower village in Guichiarea was identified as the place where DU Mu recited his poem Qing Ming.From then on,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pricot Flower Village in Guichi area and DU Mu and Qing Ming was determined,contributing to the increasingly abundant local customs and characters.In the 24thof Kangxi Empire,Lang Sui compiled Historical Records in Apricot Flower Village of 12 volumes which was later accepted in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In 1915,HU Zi-zheng compiled Sequel of Historical records in Apricot Flower Village,altogether 3 volumes.As local cultural resource,Apricot Flower Village has been continually protected and developed.The image of A-pricot Flower Village includes four cultural patterns:village poem culture,villagewine culture,village culture and village sightseeing culture.
Apricot Flower Village;village poem culture;village wine culture;village culture;village sightseeing culture
G07;I206.2
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4)01-0129-10
2013-12-01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皖南民俗文化研究中心”重点研究项目“《杏花村志》点校及杏花村文化内涵研究”
纪永贵,男,安徽贵池人,博士,池州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民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