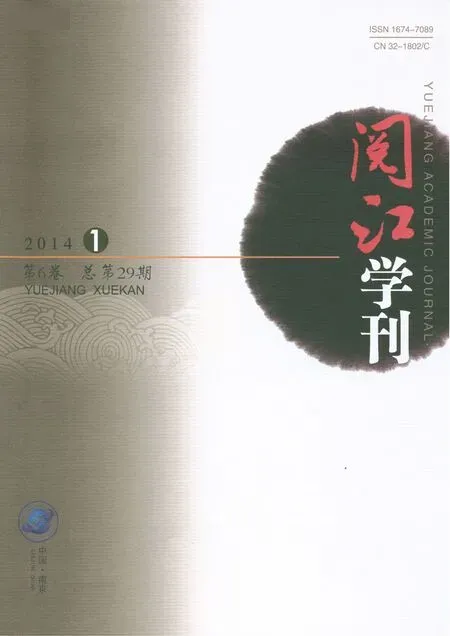菠菜入华考
石润宏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0097)
菠菜入华考
石润宏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0097)
菠菜原产伊朗即古波斯,大约于唐贞观年间经由尼泊尔人传入我国,现在是中国厨房的一种常见蔬菜。菠菜初名菠薐或波稜,这是一个西域国名颇陵的音译。菠菜在唐代栽培不广,文学作品没有表现,只在农书和本草类书籍中有记载。唐诗之所以没有提到菠菜,是因为菠菜在唐代始终是一种小众的菜蔬,食用者只是本草学家、炼丹服丹者、苦于面毒的人以及一些境况不佳的农民。宋代以后,随着菠菜的广泛栽培,地方志开始著录它,菠菜也开始出现在文人诗歌中,并被赋予了凌霜耐寒的坚忍品质,再加上苏轼、苏过父子等名家的题咏,就使得菠菜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据了一方小小的天地。
菠菜;波斯;传播;中国;唐代;宋代;饮食文化
菠菜作为当今中国的常见蔬菜,在某些方面有其特殊性。首先菠菜是自外国传入的,《中国植物志》说它“原产伊朗,我国普遍栽培,为极常见的蔬菜之一”[1],因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说它别名“波斯草”[2]。还有比较特殊的一点是,菠菜是一种味道很有争议的蔬菜。我们知道,经霜经雪的菠菜发甜,口感好,而其它季节的菠菜比较涩口,李时珍说:“波棱八月、九月种者,可备冬食;正月、二月种者,可备春蔬。”菠菜属于冬春季节的“打霜菜”,无论炒烩炖煮皆佳。正因为菠菜有甜涩两种口感,所以,爱吃的人极喜,而不爱吃的人视若凡品。南唐人钟谟就是菠菜的拥趸,宋代陶谷的《清异录》记载道:“钟谟嗜菠薐菜,文其名曰‘雨花菜’,又以蒌蒿、莱菔、菠薐为‘三无比’。”[3]明人王世懋在笔记《蔬疏》中说:“菠菜,北名‘赤根’。菜之凡品,然可与豆腐并烹,故园中不废。”[4]可见,王世懋对菠菜有一种轻视的态度。
菠菜是由外国传入的,口味又比较特殊,然而,爱写诗的唐人却没有提到过这种新奇的蔬菜。杜甫困顿时常食菜蔬,连山野间的杂草苦荬都写进诗里了①“苦荬……又有野者,今乡土有之,僧道菴寺尤多种,可频采食,耐久……杜工部所谓‘春盘生菜细’者是也。”(见宋代谈钥《吴兴志》卷二十,民国吴兴丛书本;杜甫诗“春盘生菜细”出于其《立春》“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见《全唐诗》卷二二九),却没有注意到菠菜,这是很有疑问的一个现象。因此,本文将该问题放在菠菜传入中国后的播散这一历史进程之中讨论一下。
一、菠菜入华的时间及其来华后的境况
菠菜是在贞观二十一年(647)由尼泊尔人带到长安的。史书记载道:“(贞观)二十一年,遣使献波稜菜。”(《唐会要》“泥婆罗国”条[5])“二十一年,遣使入献波稜、酢菜、浑提葱。”(《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上·泥婆罗传》[6])《册府元龟》也记载了这一史事:“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三月……泥钵罗献波稜菜,类红蓝,实如蒺梨,火熟之能益食味。”[7]
泥婆罗和泥钵罗都是外国国名的音译,就是今天的尼泊尔(Nepal)。该国向来与中华亲善,李斌城主编的《唐代文化》总结了一张“外国进献植物表”[8](见表一)。可见,尼泊尔是奉献物品最多的,好多并非其国原产的植物,他们也搜罗来献给大唐。菠菜就不是尼泊尔的原产,而是来自其它国家。“这种新输入的蔬菜的汉文名称,似乎是记录了某种类似‘palinga’(波稜)的外国语的名称。”[9]美国的劳费尔博士(Berthold Laufer)在他的著作《中国伊朗编》里花了数千字的篇幅来论述菠菜的原产地,他引述了上文《册府元龟》中的记载,并推测说:“它证明在当时菠菜不仅对于中国人是新奇的东西,而且对于尼泊尔人恐怕也是新奇的,否则他们就不会把这东西拿来当作礼物送给中国,他们献礼是应太宗皇帝的要求:凡是属国都要把他们所出产最精选的菜蔬进贡。”[10]唐人亦是知道菠菜的原产国的,《太平广记》引中唐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曰:“菜之菠薐者,本西国中有僧,自彼将其子来,如苜蓿、蒲萄,因张骞而至也。菠薐本是颇陵国将来,语讹耳,多不知也。”[11]
对此,宋人孙奕引严有翼撰《艺苑雌黄》云:“蔬品有‘颇陵’者,昔人有颇陵国将其子来,因以为名。今俗乃从‘艹’而为菠薐。呜呼,字书之不讲久矣。”[12]劳费尔也从语源上作了一番考证,他说:“汉语的‘菠薐’肯定是代表某种印度方言的译音。在印度斯坦语里菠菜叫做palak,糖萝卜叫做palan或palak,在普什图语为pālak,显然是从梵语pālanka,palakyū,pālakyā演变而来的。我们字典给这字所下的定义是:‘一种菜蔬,一种甜菜,Beta bengalensis;’在孟加拉语为palun。为了要使这名字和汉语更符合,我们还可以找到梵语的Pālakka或Pālaka,那是一个国名,这名字使得佛教僧侣产生了‘菠菜出产于颇棱国’的说法。尼泊尔人因此把一个本地植物的名字用在新移植来的菠菜上,然后把这名字连同这产品一块传到中国。”[13]最终得出结论:“我们在适当地考虑了植物学上和历史上所有事实以后,不得不承认菠菜是从伊朗某地传到尼泊尔,从尼泊尔又于公元647年移植到中国的。”[14]

表1 外国进献植物表
续表1:

纪年 贡献国家 贡献物品 资料来源 备注贞观二一 647 伽毕失 泥楼婆罗 册府/970/11400即印度青莲贞观二一 647 健达 佛土叶 册府/970/11400新书作佛土菜贞观二一 647 泥婆罗 波稜菜、酢菜、胡芹、浑提葱、桂椒 册府/970/11400天宝五 746 陀拔斯单 千年枣 册府/970/11412
我们有必要再来仔细阅读一下《册府元龟》的记载。唐人看到的菠菜“类红蓝,实如蒺梨”,说明菠菜的植株和种子他们都见到了。“蒺梨”就是蒺藜,菠菜籽和蒺藜的种子相似,形状都是圆体带尖锥,有些像武术中使用的流星。“红蓝”是指某种蓝属植物,就是成语“青出于蓝”中的蓝草。蓝有木蓝、菘蓝、蓼蓝、板蓝等,菠菜的叶子与菘蓝更为相似。尼泊尔与长安相隔万里,他们进献菜蔬,一路走来是如何保鲜的呢?即便是现在,要把尼泊尔的菠菜运到西安,还能使西安人从菠菜没有干瘪的叶子上看出它“类红蓝”,除了空运似乎也别无他法。那么,回到千余年前的唐代,我们只能作这样一番猜测:尼泊尔的使节团带着他们国王交好大唐的使命,带着他们搜罗来的奇珍异品,不远万里来到长安,并没有立刻入朝,而是先居住在长安的某处庭院,将他们预备进贡的植物播种繁殖。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如果他们带来的植物无法在关中平原生长,或者能够生长但出现了橘变为枳的情况,那么就会开罪大唐。伊朗纬度低于长安,南部大片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当地的植物是否适合在北温带的长安生长是尼泊尔人首先需要确认的问题。因此,只有等到尼泊尔使臣们确定了带来的植物可以在中国生长,才会向朝廷通告朝贡。于是,唐人就看到了绿叶红根、青翠欲滴的新鲜菠菜了。使臣还提供了种子,方便中国人繁殖,这样,他们就顺利地完成了外交使命。尼泊尔人是在贞观二十一年的三月进献菠菜及其种子的,那么,算上他们繁殖一茬菠菜的时间,菠菜实际初次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应该在贞观二十年(646)。
现在我们知道了菠菜的来源(包括地源及语源),也知道了它初到中国的时间,那么,它传入中国之后,唐人给予它何种关注呢?事实上,菠菜来华的消息传出不久,有人就注意到了这种植物,他就是研究草药的医学家孟诜。孟诜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卒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其著作《食疗本草》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食疗专著。原书本佚,幸赖敦煌石室残卷得以复见,孟诜在该书中就论述了菠菜的药性。其“菠薐”条[15]曰:
冷,微毒。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服丹石人,食之佳。北人食肉面,即平。南人食鱼鳖水米,即冷。不可多食,冷大小肠。久食令人脚弱不能行,发腰痛。不与蛆鱼同食,发霍乱吐泻。
这是菠菜见于典籍的最早记载,大抵与其入华同时,相差不过一二十年。须得一提的是,成书于显庆四年(659)的《大唐新修本草》并未记录菠菜,可能编者苏敬没有注意到这一新来植物,也可能菠菜算不得药草因而没有著录。孟诜的著作偏重“食疗”,对蔬菜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菠菜刚在长安传播他就注意研究它的食疗功效,经十几年的观察、验证,才总结出菠菜的药性,也符合做研究工作的一般时限。接着出现菠菜的典籍是郭橐驼的《种树书》和上文引用过的《嘉话录》(记刘禹锡(772—842)事)。劳费尔博士以为“就农业方面的文献来说,菠菜第一次出现在八世纪末期的《种树书》”[16],这可能是因为在作者撰写《中国伊朗编》的时候,即20世纪初期,敦煌文献还没有经过系统整理,所以,劳费尔没有见到《食疗本草》的残卷。
柳宗元(773—819)有《种树郭橐驼传》,是文约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803—805),可知,郭橐驼大约生活于8世纪末至9世纪初。郭橐驼在书中说:“菠薐过月朔乃生,今月初二、三间种与二十七、八间种者,皆过来月初一乃生。验之,信然。盖颇棱国菜。”[17]他指出,菠菜的生长习性是有些特殊的,这个月播下种,必得等到来月才生①现代农业大规模栽培菠菜都采用浸种催芽法,将种子浸12小时后,放在4℃低温的冰箱中处理24小时,然后在15-25℃条件下催芽数日,待大部分发芽后再撒播。可见自然条件下的菠菜籽确实不易发芽。,经过检验后确实是这样,说明郭橐驼不是道听途说的,而是自己有种菠菜的实践。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说: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瘘,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18]
将以上材料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知道,8世纪末时,菠菜的栽培已推广至长安西部的农村。因此,我们推断菠菜在唐代京都长安的传播是有一段宫苑栽培期的。唐朝的高层官员初见菠菜以为稀奇,归于禁中,之后逐渐视之为寻常菜蔬,才允许其流波于民间。孟诜在中书省任职,属于高级官员,他得到番邦进贡的菠菜应该不难,当然这也与菠菜本身的普通有关,类似“金桃”②谢弗说:“金桃那金灿灿的颜色,使唐朝朝廷乐于将它栽种在皇家的果园。唐朝的花园和果园从外国引进了大大小小许多植物品种,其中有些植物长久地留传了下来,而有些则只存在了很短的时期。作为这些外来植物的代表和象征,金桃确实是很合适的。目前还没有记载表明,这种金桃曾经传播到长安御苑之外的地方,甚至就是在御苑中,七世纪之后也没有金桃的存在。”(见《唐代的外来文明》,第263页)那样的仙品就只能是皇帝的专属物。郭橐驼虽然是农民,但他种出来的作物博得了长安豪富人家的青睐,他可能从豪富手中得到了菠菜。菠菜的生物学特性使得它易种易活,也没有虫害,但是,它却不能救荒,常食还“令人脚弱不能行”,因而,菠菜没有官方推广的可能,不可能享受到类似明代传入的玉米的待遇,它的播散只能是靠钟谟那样的爱吃者,或者因经济匮乏而种来聊以添菜的农民。
自郭氏而后,唐代典籍中就没有关于菠菜的记录了,菠菜也没有出现在唐代的任何文学作品中。这样,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菠菜在唐朝的境况。菠菜来华以后先在长安小范围种植,之后逐渐向郊区农村扩散,以农家的散点种植为主要生产方式。随着人口渐渐向全国各地播散流动,到了唐朝末年,已经传播到了江苏、浙江、福建(钟谟的活动范围)等地。由于菠菜栽培不广,且并非富贵菜,食用多了还有副作用,因此,文人墨客没有注意到它,注意到它的是一些本草学家、炼丹术士和农民。
二、宋代以后菠菜的流播
到了宋代,菠菜在典籍中的记载就多了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宋人喜著述,另一方面是由于菠菜的广泛栽培。《中国外来植物》“菠菜”条称它“至宋元方广为种植,成为冬春季节常见蔬菜”[19],依据的也是菠菜在宋代文献记录中的突然增加。检阅方志我们发现,大约在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以后,著录菠菜的地方志数量就急速增长,可知菠菜的广布应在南宋以后。我们可以借助下面的表格来了解方志(主要是其中的食货志)记载菠菜的大概状况,亦可窥见菠菜传播的大致情况(见表二)。

表2 方志对菠菜的记载

续表2:
这一表格说明了菠菜在南宋以后确实遍及中华大地,且产量甚丰,因为方志记载的多为当地富产的物种。这也与文学中菠菜的地位变化相吻合。宋孝宗时期的诗人员兴宗有一首《菜食》诗写道:
员子一寒世无有,爱簇生盘如爱酒。菠薐铁甲几戟唇,老苋绯裳公染口。骈头攒玉春试笋,掐指探金暮翻韭。达官堂馔化沟坑,我诵菜君人解否。(《全宋诗》[20]第36册,第22546页)
员兴宗在诗前小序中写道:“东坡谓竹为君,鲁直谓棕栮为君,仆以菜为君,盖不钦其味钦其德也。食之者无后悔,不谓之君可乎?”将菠薐等蔬菜与竹君并提,赋予了蔬菜人文的内涵。苏东坡与黄庭坚在对待植物的审美上都有将植物人格化的倾向,员兴宗在他们的基础上又将此前文人不太看重的蔬菜称为君子,员氏推重的文人“钦其德”这种精神层面的拔高在菠菜“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宋人论述菠菜多引用孟诜和韦绚的说辞,如《证类本草》、《嘉祐本草》、《全芳备祖》等。也有些新语,比如张君房辑《云笈七签》所载:“敢问今数面肿,何也?答:其面肿者只为饮食侵肺,痰水上冲,气壅不行,所以如此。其食中尤忌葫荽、芸苔、韭薤、菠薐、葱蒜,此物皆木之精,能损脾乱气,必不可食。”[21]又如谢维新《事类备要》引《格物总论》云:“菠薐,外国种,茎微紫,叶圆而长,绿色。性冷,食之利五脏,通肠胃,与蛆鱼同食佳。”[22]
《云笈七签》成书于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格物总论》撰者及成书年代均不可考,然《事类备要》成书于宋理宗宝祐(1253——1258)年间,则《格物总论》当约成书于南宋初。这两书所述的菠菜功效均与前人相悖,其原因可能是引书有误,《格物总论》的说法与《食疗本草》差近,然一是一否,当以孟诜为确。也可能是不同人对菠菜的适应性不同,有人吃了通肠胃,有人吃了却损脾乱气,中医本就是人学,人有不同的感受因而医书也有不同的记载,这是可以理解的。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菠菜对人体是很有益处的,是一种健康蔬菜,受到人们的欢迎。金代张从正的《儒门事亲》记录了一位老翁食用菠菜延年益寿的故事:
有老人年八十岁,脏腑涩滞,数日不便,每事后时目前星飞,头目昏眩,鼻塞腰痛,积渐食减,纵得大便,结燥如弹。一日友人命食血藏葵羹油渫菠薐菜,遂顿食之,日日不乏,前后皆利,食进神清,年九十岁无疾而终。[23]
菠菜的这些好处博得了一些老饕的青睐,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春菜》诗说:
蔓菁宿根已生叶,韭芽戴土拳如蕨。烂蒸香荠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宿酒初消春睡起,细履幽畦掇芳辣。茵陈甘菊不负渠,鲙缕堆盘纤手抹。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稜如铁甲。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芽寒更茁。久抛松菊犹细事,苦笋江豚那忍说。明年投劾径须归,莫待齿摇并发脱。(《全宋诗》第14册,第9248页)
苏东坡晚于张君房数十年,他的这首诗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北宋初年,菠菜已经传入苏东坡的家乡四川;第二,苏东坡十分懂得菠菜采食的最佳时机,即经雪冻过之后会“更茁”更香甜。
《全宋诗》中写到菠菜的诗共计8首①作者分别为苏轼、张耒、苏过、刘一止、刘子翚、员兴宗、姚申之和邵桂子。,有些诗提到了菠菜的一些吃法,比如菠菜粥和菠菜饼:
朔风吹雪填庐屋,一味饥寒寻范叔。绨袍安敢望故人,藜苋从来诳空腹。近闻陶令并无储,不独鲁公新食粥。波稜登俎称八珍,公子未应讥世禄。山僧一食不过午,忍饥学道忘辛苦。书生事业乃尔勤,夜然膏火穷今古。要将五鼎同釜铛,箪瓢未可轻原生。肉食纷纷固多鄙,吾宁且啜小人羹。(苏过《和吴子骏食波稜粥》,《全宋诗》第23册,第15474页)
饼炊菠薐,鲊酿苞芦。(邵桂子《疏屋诗为曹云西作》,《全宋诗》第69册,第43461页)
结合另外一些诗我们发现,菠菜在僧侣中很受欢迎,出家人似乎是菠菜的主要消费者,刘一止《寄云门长老持公一首》云:
梦境清游记昔曾,而今双鬓已鬅鬙。此生有分寻云水,到处逢人说葛藤。紫芋波稜真在眼,青鞋布袜未输僧。会投枯木堂中老,只恐诗情罢不能。(《全宋诗》第25册,第16700页)
明代冯梦龙的笑话书《古今谭概》里也记载了一则与菠菜和僧人有关的故事:
松阳(今浙江丽水)诗人程渠南,滑稽士也,与僧觉隐同斋食蕈。觉隐请渠南赋蕈诗,应声作四句云:“头子光光脚似丁,只宜豆腐与菠薐。释迦见了呵呵笑,煮杀许多行脚僧。”闻者绝倒。[24]
“蕈”就是蘑菇之类的食用菌,它头圆脚长,外形像和尚,与豆腐、菠菜同煮,是寺院里的一道斋食。联系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菠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约在整个唐代至宋初,都流行于僧侣、方士等少数阶层,而诗人多数是仕宦之人,生活水平较高,很少吃到菠菜,可能也不屑吃这种普通的蔬菜,有些士人因为生病或荤腥吃腻了才考虑进食菠菜,赵长卿有一首《如梦令·寄蔡坚老》词云:
居士年来病酒,肉食百不宜口。蒲合与波薐,更着同蒿葱韭。亲手,亲手,分送卧龙诗友。[25]
这可能是唐宋富人阶层与菠菜发生联系的一般情景,也是唐宋文学都很少提到菠菜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菠菜的食疗功效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有一首专写菠菜的诗,诗曰:
谁从西域移佳蔬,遍植中原葵苋俱。清霜严雪冻不死,寒气愈盛方芳敷。贯金锐箭脱秋竹,剪罗巧带飘华裾。中含金气抱劲利,穿涤炎热清烦纡。老人食贫贪易得,大釜日煮和甘腴。饭炊香白煮饼滑,一饱尽钵无赢余。空厨萧条烟火冷,可但食客歌无鱼。男儿五鼎食固美,当念就镬还愁吁。(《全宋诗》第20册,第13151页)
这首诗开头两句交待了菠菜的来历,之后两句赋予了菠菜凌霜不凋的坚贞品格,整体上写得颇有闲趣。诗的题目道出了菠菜的来历及其食疗功效,即“波稜乃自波陵国来,盖西域蔬也。甚能解面毒,予颇嗜之,因考本草,为作此篇。”张耒说明了自己喜爱吃菠菜的原因,因为菠菜很能释解“面毒”。“面”就是小麦去皮后磨成的面粉,《本草纲目》“小麦”条引甄权曰:“(小麦)平,有小毒”,李时珍还指出小麦面“(气味)甘,温,有微毒”,又引孟诜言“面有热毒者,多是陈黝之色,又为磨中石末在内故也。但杵食之,即良”[26],孟诜说,古时候小麦多用石磨磨成面粉食用,因而石头中的一些粉末也进入到了面里,人吃了就会发热毒,如果食用木制的杵具就没有问题了。可见,当时制作的面粉不甚精良,保存技术也不过关,放置久了有些泛灰的就有毒素。但古人不能像我们今天这样,食品略有变质就丢弃,他们还是得吃,于是就会中毒。值得一提的是,中医所谓的“毒”范围十分宽泛,但凡对人体不利的皆可称之为“毒”。所谓“面毒”,并不一定会使人出现致命的症状,大抵是一种不太好的成分。
小麦及其制品面粉都有微毒,处理不好对人不利,古人很早就知道。小麦也是外来植物,《永乐大典》引方仁声①方仁声,即方勺,自号泊宅村翁,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哲宗元符(1098—1100)末前后在世。《宋史·艺文志》记其著有《泊宅编》十卷。的《泊宅编》云:
小麦种来自西国寒温之地,中华人食之,率致风壅。小说载“天麦毒”,乃此也。昔达磨游震旦,见食面者,惊曰:“安得此杀人之物?”后见莱菔,曰:“赖有此耳。”盖莱菔解面毒也。世人食面已,往往继进面汤,云能解面毒,此大误。东平董汲尝著论戒人,煮面须设二锅汤,煮及半,则易锅煮,令过熟,乃能去毒。则毒在汤明矣。[27]
董汲的祛毒法颇为费事,但似乎很有效。通过沸水烹煮可以消毒,可见,面毒不是面粉变质易产生的黄曲霉毒素。方仁声说,面毒就是小说中记载的“天麦毒”,这一小说应是指的宋人钱希白的《洞微志》。叶廷珪《海录碎事》“天麦毒”条说:
显德(954—959)中,齐有人病狂,每歌曰:“踏阳春,人间二月雨和尘。阳春踏尽秋风起,肠断人间白发人。”又歌曰:“五云华盖晓玲珑,天府由来汝腹中。惆怅此情言不尽,一丸萝卜火吾宫。”后遇一道士作法治之,云每梦中,见一红衣少女引入,宫殿皆红,多不知名小姑令歌。道士曰:“此正犯天麦毒,女即心神,小姑即脾神也。按《医经》:萝卜治面毒,故曰火吾宫。”即以药兼萝卜食,其疾遂愈。出《洞微志》。[28]
《说郛》引《洞微志》的文字略有差别:
《洞微志》载齐州人有《病狂歌》曰:“五灵叶盖晚玲珑,天府由来汝府中。惆怅此情言不尽,一丸萝菔火吾宫。”后遇道士作法治之,云:“此犯天麦毒,按《医经》芦菔治面毒。”即以药并萝菔食之,遂愈,以其能解面毒故耳。[29]
莱菔、芦菔、萝菔、芦萉、萝蔔等,都是萝卜的别名(见《本草纲目》“莱菔”释名),它的主要药效是“利关节,理颜色,练五脏恶气,制面毒,行风气,去邪热气。(萧炳)利五脏,轻身,令人白净肌细。(孟诜)”[30]。萝卜可以消解面毒,利于五脏,菠菜也有这个功效,元人胡古愚的《树艺篇》引《兴化府志》称:“菠薐:《闽中记》谓叶如波纹有稜道,未知何据。北人呼赤根菜,莆人呼面菜,谓宜面也。”[31]
对于菠菜宜于和面同食,张耒已有实践,且效果颇佳,否则也不会写诗专咏其事。上文所引《泊宅编》提到的“风壅”之症,其实就是风热壅盛导致的一种头痛症,对于该病症的论述,可见明方广(约之)所编的《丹溪心法附余·风热门》。而据现代营养学的研究,菠菜富含尼克酸(又称烟酸),尼克酸有较强的扩张血管的作用,临床常用于治疗头痛、偏头痛、耳鸣、内耳眩晕等症。可见,服食菠菜对于风壅的治愈也是很有帮助的。
四、结 语
通过上文论述可知,菠菜原产伊朗即古波斯,大约于唐贞观年间经由尼泊尔人传入我国,现在是中国厨房的一种常见蔬菜。菠菜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既可作为菜食又可作为药草。唐诗之所以没有提到菠菜,是因为菠菜在唐代始终是一种小众的菜蔬,食用者只是本草学家、炼丹服丹者、苦于面毒的人以及一些境况不佳的农民。到了宋元以后,随着菠菜种植的遍布全国,地方志开始著录它,文人也开始品题菠菜,并赋予菠菜一些耐寒植物的“凌寒独自开”的品质,加之苏轼、苏过父子等名家的题咏,这一切就使得菠菜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据了一方小小的天地。
[1]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25(2)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46.
[2][26][30]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697,620,685.
[3]陶谷.清异录[M].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籍本:卷二.
[4]王世懋.学圃杂疏·蔬疏[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81册[Z].济南:齐鲁书社,1995:647.
[5]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1789.
[6]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14.
[7]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11400.
[8]李斌城.唐代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881.
[9][美]谢弗(Edward H.Schafer).唐代的外来文明[M].吴玉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316.
[10][13][14][16][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M].林筠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218,222,223,217.
[11]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3344.
[12]孙奕.履斋示儿编[M].元刘氏学礼堂刻本:卷二二.
[15]孟诜.食疗本草[A].范凤源,李启贤.敦煌石室古本草[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146.
[17]郭橐驼.种树书[M].明夷门广牍本:卷下.
[18]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473.
[19]何家庆.中国外来植物[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20]傅璇琮,等.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
[21]张君房.云笈七签[M].四部丛刊景明正统道藏本:卷六二.
[22]谢维新.事类备要别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六0.
[23]张从正.儒门事亲[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
[24]冯梦龙.古今谭概[M].明刻本:卷二七.
[25]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1818.
[27]解缙,等.永乐大典:卷二二一八一[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9.
[28]叶廷珪.海录碎事[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七.
[29]陶宗仪.说郛:第十册[M].北京:中国书店,1988:417.
[31]胡古愚.树艺篇[M].明纯白斋钞本:卷二.
〔责任编辑:渠红岩〕
A Textual Research on Spinach,an Alien Plant
SHIRun-ho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Spinach,an alien plantwhich came from Persia,the ancient Iran,is now a common vegetable in Chinese people's kitchen.Itwas brought into China by Nepal envoys in Zhenguan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At that time,spinach was called Boleng,the name was a transliteration of a western country Poling.Spinach wasn'twidely cultivated in the Tang Dynasty,so there was no literary works involved it,only the herbals and agricultural books had some records.After the Song Dynasty,with the propagation of spinach,local history books began to record it,and it began to appear in literary poetry,from then it has been given the character like hard and perseverance.Spinach is also a therapeutic herb,ZHANG Lei,a poet in Song Dynasty had consumed it to detoxicate Miandu.Miandu,which is produced by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flour,is a kind of composition bad for human health.Spinach has its place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written in poems by SU Shi,SU Guo and other poets.
Spinach;Persia;dissemination;China;Tang Dynasty;Song Dynasty;dietary culture
G122;I206.2
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4)01-0139-10
2013-10-20
石润宏,男,江苏丹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