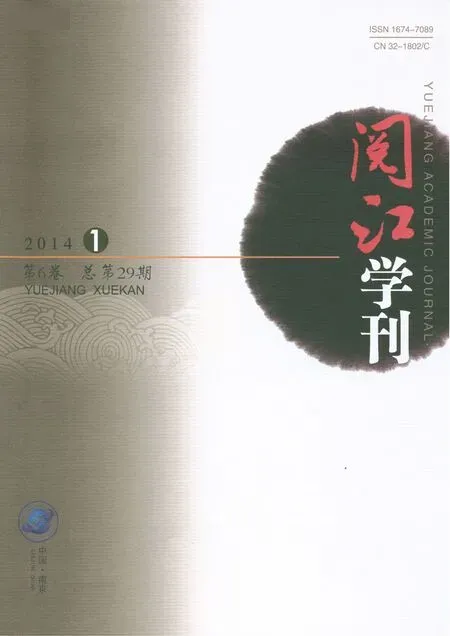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
程杰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0097)
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
程杰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0097)
我国是一个花卉文化极其繁荣灿烂的国度,无论是园艺种植、花事观赏,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极为丰富繁盛。我国花卉文化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的始发期、秦汉至盛唐的渐盛期和中唐以来的繁盛期。从审美认识水平着眼,我们将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为“物质实用时代”、“花色审美时代”和“文化象征时代”,三个阶段间呈不断累积演进之势。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有着我国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广泛的历史基础。我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丰富,给花卉园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我国发达的农耕文明对花卉园艺生产促进良多。我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构成了花卉文化创造的主力,无论是外延的拓展,还是内涵的提升,都主要得力于他们的奉献,也主要体现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文化理想。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念对花卉观赏的影响从来都是正面、积极的,历史上从未出现其他民族那种基于特定教义对花卉使用的严格限制,西方中世纪普遍禁止那样的现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决定了我国花卉文化的民族风格。我国观赏花卉以我国原产的木本和经济应用品种为主,形成了独特的名花、名树体系。我国人民比较重视自然生长、园艺种植的植物生姿,特别欣赏植物的生机天趣,西方社会那种花环、花冠等采结献赠为礼的方式在我国并不多见。在花卉象征上,我国士大夫阶层最终形成了“比德”、“写意”传统,即通过花卉形象寄托人的道德品格和高雅情趣,体现了我国崇尚伦理道德的文化精神,与西方花卉象征多具宗教意义颇有异致。我国花卉象征中的吉祥寓意,体现着我国民众独特的幸福观,有着鲜明的民间、民俗色彩,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系统“花语”。
中国花卉文化;繁荣;发展;历史背景;民族特色
所谓花卉文化是人类围绕花卉所展开的各类社会文化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所谓花卉一般用其广义,指观赏植物,而“花”即观花植物是其重点。文化的范围历来至大无外,虽然花卉文化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或一个专题,但涉及范围是极为广泛的,包托植物、园艺、园林、民俗、文学、艺术、社会、经济及其相应的历史学科等广泛领域,相关研究需要众多学科的广泛参与。我国是一个花卉文化极度繁荣的国家,其发展历史和文化现象尤为丰富复杂,更需要多方面的力量投入。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花卉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但相关学术研究却较为薄弱。就全局、通论性的著作而言,为数不多的成果主要出于园艺学者,如周武忠的《中国花卉文化》(花城出版社,1992)、《花与中国文化》(农业出版社,1999),闻铭、周武忠、高永青合作主编的《中国花文化辞典》(黄山书社,2000),另有文史学者何小颜《花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9)。近见英国社会人类学者杰克·谷迪(Jack Goody)《花文化》(The Culture of Flowers)一书纵论从古至今欧洲、北美、非洲、中东、亚洲等广大地区的花卉文化问题,其中有两章专论中国古代和当代,力求在跨文化和人类社会学、历史学的宽广语境中思考中国花卉文化的特点,所见多有启发。面对域外这样的热心关注,我们有必要立足中国文化的立场和文史研究的成就,对我国花卉文化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回应。本文正是出于这一动机,对我国古代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等全局性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力求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初步而基本的认识。
一、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
我国是一个花卉文化发展历史悠久而极其繁荣灿烂的国家。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陶器、陶片上即有植物枝叶类图案,并有盆栽单株植物的纹样。距今5000—6000年的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多有花瓣、叶片样纹饰,以至有人视为华夏民族得名的由来。[1]可见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我国先民们对花卉已经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并出现了用作装饰的倾向。主要传承夏朝历法的《夏小正》中,就有正月“柳稊”,“梅、杏、杝桃则华”,二月“荣堇(蔬菜),采蘩”,“荣芸”,四月“囿有见杏”,七月“秀雚苇”,“荓秀”,九月“荣鞠(菊)”等物候月令,所谓华、荣、秀,都是开花的意思,说明夏朝先民对植物开花已颇多关注。到了西周时期,被誉为我国先民大合唱的《诗经》中,“草木虫鱼”的“比兴”成了最基本的表达方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何彼秾矣,唐棣之华”,“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都是热情赞扬鲜花灿烂之美的名句,而“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有女同车,颜如舜华”,“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更是把鲜花作为时令美好、容貌光鲜、才能优秀的象征,“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则是男女间以花馈赠传情的习俗,这些都充分反映人们对花卉的喜爱和重视。战国时《楚辞》中“香草、美人”构成了比较复杂的象征系统。汉以来,尤其是魏晋以来,人们对花卉草木的欣赏兴趣和对花朵装饰的需求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普遍,专题的文艺创作开始兴起。唐宋以下,相应的社会文化活动更是云兴霞蔚,不断敷展和积累,日益深化和精细,形成了极为丰富复杂、繁盛灿烂的景观。
我国古代花卉文化的繁盛景象,大致可以从两大方面来把握:
(一)园艺种植成就和花事欣赏活动极为丰富繁盛
首先是观赏植物资源的丰富。据统计,《诗经》出现植物名称近 500次,涉及品种有 143种[2],而其中比较富于观赏价值的就有芍药、唐棣、舜(木槿)、荷、兰、菊、女贞、栗、桃、梅、竹、杨柳、榆、梧桐、梓、桑、槐、枫、桂、桧等。到了初唐《艺文类聚》,所辑草部总名和专名44种,百谷部总名和专名9种,果部37种,木部总名、专名43种,合计133种,这大多是文献记载和艺文作品较为丰富的植物品种。南宋末年的花卉专题类书《全芳备祖》前集为花部,为观花植物,列名著录114种,附录7种。后集为其他植物,分果、卉、木、农桑、蔬、药等部。诸部合计列名著录269种,附录30多种,其中明确属于植物274种(多部重出不计),近一半见于花部,也就是说120多种已被视为观花植物。到了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编定的《佩文斋广群芳谱》,分天时、谷、桑、蔬、茶、花、果、木、竹、卉、药等11类,共100卷,其中花谱最多,占32卷,包括附录在内共辑录以花色著称的植物达234种,其他果、木、竹、卉、药、桑、蔬诸谱中也有不少富于观赏价值的植物,如竹、松柏、杨柳等,合计数量之多不难想象。
不仅是花卉物种丰富,具体园艺品种更是不胜其多。早在唐代,宋单父即能使“牡丹变易千种。上皇召至骊山,植花万本,色样各不同”[3]。入宋后洛阳牡丹甲天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称天圣九年(1031)所见西京(洛阳)留守钱惟演手录“九十余种”,而欧公自叙当时著名者即有姚黄、魏紫等24个。[4]稍后周师厚《洛阳牡丹记》增至46个[5],张峋“撰《谱》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6],这还只是北宋一时、洛阳一地的情况,可见技术发展之迅速、培育品种之丰富。再如菊花也复如此,北宋末年刘蒙《菊谱》所载品种35个,到南宋淳祐间(1241-1252)史铸《百菊集谱》汇集诸家所录,品种已达162个。明嘉靖间周履靖、黄省曾《菊谱》著录222个[7],清计楠《菊说》著录233个。[8]各家所录既有重复,也多有不同,若能进行全面普查,品种数量应该远非二三百种。透过这些极不完全的数据,不难感受到我国花卉品种开发的繁富。
不仅品种资源繁盛,相应的种植技术和观赏经验也都极为丰富。我国古代农书中,观赏圃艺类著述极夥。这些花卉谱录类著述,除品种著录外,多有种植技术、观赏方式、情趣品鉴乃至于艺文作品、遗闻轶事之类的阐述和资料缀录。如北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就包括“花品叙”、“花释名”、“风俗记”三部分。邱濬《牡丹荣辱志》则将所录39个品种按王、后、妃、嫔、命妇、御妻等名目品分等级,又以师傅、彤史、命妇、嬖倖、近属、疏属、戚里、外屏、宫闱、丛脞等名目就其配植之物进行分类,进而以君子、小人、亨泰、屯难等名目对种植环境、花期时令、气候、观赏人物和活动方式等宠辱、宜忌之事进行系统揭示。[9]南宋张鎡《玉照堂梅品》受此启发,亦标举花宜称26条、花憎嫉14条、花荣宠6条、花屈辱12条,就梅花种植、观赏之气候环境和人物事体,区别优劣,明确宜忌,从正反两方面制定条例。我国花卉圃艺汇编、植物专题类书中这方面的内容分量也不小,包括园艺、园林、花艺、民俗、文人生活等广泛内容,凝积了人们长期种植尤其是欣赏活动的丰富经验。我们这里无需就各方面的活动和成果一一胪列,仅以明人王路《花史左编》类目为例,该书分花之品、花之寄、花之名、花之辨、花之候、花之瑞、花之妖、花之宜、花之情、花之味、花之荣、花之辱、花之忌、花之运、花之梦、花之事、花之人等24类辑录花事资料,透过这些名目,不难感受到我国花卉园艺及其文化活动的丰富多彩和观赏经验的细致深厚。
(二)花卉题材文学、艺术的极度繁荣
中国传统比较重视文学,中国文学是一个饱含植物意象的审美世界。从《诗经》、《楚辞》以来,花卉植物就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更是最普遍的意象,相关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构成了极为繁盛的文化遗产。唐以前,花卉植物多见于抒情诗中引发情感,比喻象征的意象,或山水、田园、行旅、游览之作中的写景内容。梁萧统《文选》中虽有“物色”一类,尚未收草木专题之作。魏晋以来,花卉植物的专题赋咏逐步兴起。北宋初年编辑的《文苑英华》专门收集《文选》以来作品,诗与歌行体中便有了“花木”(或“草木”)一类。中唐尤其是宋代以来,随着观赏园艺的发展,专题花卉之作数量激增,花卉题材的作品蔚为大观。据学者统计,《全宋词》诸本所辑21203首中[10],咏物词3011首[11],其中咏植物 2419首,占咏物词80%强,高居首位。在2419首咏植物词中,属于咏花色植物的 2189首,占 90%强,也远居第一。[12]换一种算法,植物专题占《全宋词》总数11%,咏花词则占10%,也就是说每10首宋词中至少有1首咏花之作。这个比例是极为惊人的!也许词体尚属“歌儿舞女”,“花间尊前”娱乐为主的文体,我们再看康熙间编成的《佩文斋咏物诗选》的情况,该书486卷,其中天文、气象、节令类48卷,山水类62卷,建筑、器具、书籍、文物类114卷,民生百业类32卷,植物类140卷,动物类90卷,植物类占了全书的29%。而在植物类中有近100卷是富于观赏价值的植物,占了全书的20%,其中至少有65卷标明属于“花”类植物,占了全书的13%。这一数据进一步说明了我国文学作品中,至少是韵文作品中,描写花卉的作品,无论是广义的植物还是狭义的“花”,都占有很大的比重。
正是基于数量的浩瀚,古代还出现了不少花卉作品的专题汇编,如《全芳备祖》所辑即以文学作品为主。清人查彬《采芳随笔》也是类似的花卉专题类书,所收植物900种,是《全芳备祖》的三倍之多,其中大都是观花植物,所辑资料也几乎都是文学作品。清康熙朝《广群芳谱》由朝臣集体编纂,规模浩大,所辑资料也以文学作品(所谓“集藻”)为主。一些重要的花卉,还出现了不少专题集,如南宋黄大舆《梅苑》,明万历间王思义《香雪林集》、清康熙间黄琼《梅史》都是大型梅花作品总集。其他梅花百咏、千题之类专集更是不在少数。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国花卉文学创作的繁盛、作品数量的浩瀚、遗产积累的丰富。
这些浩瀚的作品,以其语言艺术特有的明确与灵活,充分展示了人们花卉欣赏的广泛兴趣、花事活动及相应文化生活的生动情景,同时也体现了人们丰富的审美情趣,寄托了人们深厚的思想情感。我们仅以梅花“百咏”为例,元代冯子振、释明本《梅花百咏》为古梅、老梅、疏梅(以下诗题省略“梅”字)、孤、瘦、矮、蟠、鸳鸯、千叶、苔、寒、腊、绿萼、红、胭脂、粉、杏、新、早、未开、半开、十月、乍开、全开、二月、忆、问、探、寻、索、观、赏、评、歌、友、寄、惜、梦、移、谱、接、浴、折、剪、簪、妆、浸、落、别、罗浮、庾岭、孤山、西湖、江、山中、清江、溪、野、远、前村、汉宫、宫、官、衙宇、柳营、城头、庭、书窗、琴屋、棋墅、僧舍、道院、茅舍、檐、钓矶、樵径、蔬圃、药畦、盆、雪、月、风、烟、竹、照水、水竹、水月、杖头、担上、隔帘、照镜、青、黄、盐、咀、玉笛、水墨、画红、纸帐,包括了梅的枝干形态、品种花期、风景名胜、环境应用、园艺种植、欣赏活动、名人掌故等丰富题材。窥斑见豹,尝一脔知全镬,透过这“百咏”之题,不难感受到花卉作品内容的多姿多彩和细致复杂。
当然繁荣的意义并不只是作品的数量和题材的多样,更重要的是其中丰富的审美经验,深刻的灵感智慧和美妙的话语表达。花卉文学作品起源早,数量多,加之文学家历来多属社会上层、文化精英,因而多能见人未见,发人未发。尤其是其中的天才之作、精采之语更是花卉文化长河中的璀灿星斗。比如陶渊明《桃花源记》、周敦颐的《爱莲说》,《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唐李正封咏牡丹“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宋林逋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黄庭坚咏水仙“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相传唐杜牧《清明》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等等名篇佳句,或咏物写神,或引发情性,寄托思想,都活色生香,脍炙人口,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审美体验,引发了广泛的情感共鸣,构成了全民族花卉审美文化的经典。
在中国艺术中,花卉也是一个大宗题材,主要表现在花鸟画的繁荣和各类工艺美术中花卉装饰的盛行。中国绘画通分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类,花鸟画源远流长,从中唐开始独立成科,勃然兴盛,无论是院体还是文人绘画中,花鸟总是最常见的题材。我们仅以宋徽宗朝《宣和画谱》进行统计,所录230位画家6407作品中,人物(含道释) 1958幅,占31%,山水(含宫室)1168幅,占18%,花鸟(含龙鱼、兽畜、墨竹、蔬果等)3281幅,占51%。仅就题目所示,在花鸟画中,纯粹的花卉画665幅,题目中含有花卉的1149幅,两者合计1814幅,占55%。再加上人物、山水画题中含有花卉的55幅(古木、寒林一类笼统的题目未计),合计1869幅,占所有作品的29%。这还是唐宋之交花鸟画兴起之初的情况,此后花鸟、山水扶摇直上,花卉题材所占比重应该更大。尤其是在文人水墨写意画中,“梅兰竹菊四君子”以其构图简单、技法近于书写而极为流行,画家画作更是难以数计。而工艺美术中,六朝以来受佛教等外来文明的影响,莲花、忍冬、宝相等装饰纹样开始流行,宋以来更是进入了一个“花草纹时期”[13],带来了陶瓷、服饰、建筑各方面花卉装饰的兴盛。
二、中国花卉文化的发展历程
对于我国花卉事业发展的历史,陈俊愉、程绪珂先生主编之《中国花经》概论《中国的花卉》一文曾划分为四个阶段:一、始发期——周秦时代;二、渐盛期——汉晋南北朝时代;三、兴盛期——隋、唐、宋时代;四、起伏停滞期——明、清、民国时代。[14]这一分期指明了我国上古、中古及两宋时期花卉事业持续发展的总体趋势,但将明清时期称作“起伏停滞期”,有明显附合“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15]这一历史常识之嫌,而就其文中实际所介绍的明、清花卉事业各方面的情况看,比较起唐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将其视为衰落或停滞,都值得商榷。同时,该文所说“花卉事业”,主要着眼于园艺、园林方面的情况,与我们这里所说“花卉文化”概念有所不同。综合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与花卉相关的情况,尤其是着眼于花卉欣赏方式的历史变化和审美认识的发展水平,我们认为,我国花卉文化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一)先秦——中国花卉文化的始发期
先秦时期,通常也称“上古”时期,是中国花卉文化的始发期。与《中国花经》说法稍有不同的是,我们将秦朝划归下一阶段。距今五、六千年的河南庙底沟新石器陶器上即出现五瓣花朵(或叶片)纹饰,表明先民们对植物花叶已有了明确的美感。前文所引《夏小正》、《诗经》中的花卉信息以及《楚辞》“香草美人”“引类譬喻”的系统话语,都充分反映出我国先民对植物花朵的关注和喜爱,展示了我国花卉观赏文化源头的绵远和活泼。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阶段对花卉的观赏尚属自发的、分散的,甚至是偶然的,远未进人普遍自觉的阶段。就人类自然审美的一般规律而言,远古先民以狩猎生活为主,更加重视的是动物,舞蹈模仿动物,各类纹饰多以动物为题材,很少顾及植物。[16]商周时期,对于植物,人们更多关注的也是实用价值。明谢肇淛两段论述颇有启发:“古人于花卉似不着意,诗人所咏者不过苤苡、卷耳、蘩之属,其于桃李、棠棣、芍药、菡萏间一及之,至如梅、桂则但取以为调和滋味之具,初不及其清香也。岂当时西北、中原无此二物,而所用者皆其干与实耶。《周礼》笾人八笾,干与焉,即梅也,生于蜀者谓之,《商书》若和羹,汝作盐梅,则今乌梅之类是已。可见古人即生青梅未得见也,况其花乎。然《召南》有摽梅之咏,今河南、关中梅甚少也。桂蓄于盆盎,有间从南方至者,但用之入药,未闻有和肉者,而古人以姜、桂和五味,《庄子》曰桂可食,故伐之,岂不冤哉。”“菊于经(引者按:经书)不经见,独《离骚》有餐秋菊之落英,然不落而谓之落也,不赏玩而徒以供餐也,则尚未为菊之知己也。即芍药古人亦以调食,使今人为之,亦大杀风景矣。”[17]所说诗人即指《诗经》。《诗经》虽间及芳华,但与《夏小正》一样,主要视为物候,包含着“占天时”“授民事”的实用意味。而所咏植物大多是采集蔬果用于食用、祭祀,“参差荇菜,左右采之”,“采采芣苡”“采采卷耳”“采薇采薇”之类即是。许多后世以花色观赏闻名的植物如梅、李之类,此时仅以果名。诗人于一般植物,也多喜其长势,如“葛之覃兮,施以中谷,维叶萋萋”(《葛覃》),“有杕之杜,其叶菁菁”(《杕杜》),“鳣鲔发发,葭菼掲掲”(《硕人》),“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氓》),“楚楚者茨,言抽其棘”(《楚茨》),“苕之华,其叶青青”(《苕之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采薇》),所谓“萋萋”、“菁菁”、“揭揭”、“楚楚”、“依依”、“青青”、“沃若”,都是指茂盛的样子。这种对植物长势旺盛之美的特别青睐,是《诗经》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透露出一种关注物质利益的审美心态。即使是一些对于植物芳香、色泽的兴趣,也多本于实际应用的背景。《楚辞》中多言香草香木,如所说“兰”,并非后世建兰类观赏植物,而是佩兰、泽兰之类药用、香用植物。对于长江流域的荆楚下泽之地,这些草木的芳香化湿、驱虫防疫功效为日常生活所必需,因而视作美物。专题《橘颂》所赞则是果树。诸如此类都充分表明,先秦时期虽然已有花色观赏取悦之意,但就花卉观赏而言,只能算是一个初起阶段,远未形成普遍之势,人们普遍关心的仍是植物的实用价值。因此从文化认识水平上说,这是一个植物实用意义仍占绝对地位的时期,我们称作花卉植物的“物质实用时代”。
(二)秦汉至盛唐——中国花卉文化的渐盛期
秦汉至盛唐,通常也称作“中古”时期。所谓渐盛,这仍是借用陈俊愉、程绪珂先生的概念,他们认为汉、晋、南北朝时期“花卉业开始从纯生产事业转向以欣赏为主”[18],所谓“纯生产事业”,揣其意应与我们前节所说注重植物的实用价值同义。我们认为,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至盛唐“安史之乱”爆发的十个世纪,虽然国家有大少,政局有治乱,南北有分合,但人们对花卉的欣赏进入了一个自觉的阶段,并且呈现出持续兴起发展的进程,我们称之为中国花卉文化的渐盛期。具体又可分为秦汉时期、魏晋至盛唐两个阶段。
秦汉时期,人们对花卉的欣赏逐步明确起来。在园艺、园林中,花卉的地位开始显露。先秦的园囿多以畜养禽兽为主,罕见有以栽种花木著称的。①宋玉《招魂》:“坐堂伏槛,临曲池些。芙蓉始发,杂芰荷些。紫茎屏风,文缘波些。”汉王逸《楚辞》卷九,《四部丛刊》景明翻宋本。似乎战国楚王苑囿已多花草景观,然宋玉《招魂》或以为屈原作,亦有以为后人伪托。而出现于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的《周礼·天官》始将“园圃毓草木”与“三农生九谷”、“虞衡作山泽之材”、“薮牧养蕃鸟兽”等并列为“万民”之“九职”[19],可见农、牧、林业之外的果蔬种植业具有了独立地位。而作为游憩娱乐之用的园林,花果草木之艺植开始引起关注。汉武帝广开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20]。不仅是御苑,茂陵富民袁广汉筑园“奇树异草,靡不培植”[21]。不仅是物种之罗集,据《西京杂记》记载,“太液池边皆是雕胡、紫萚、绿节之类”[22],汉昭帝“始元元年,黄鹄下太液池,上为歌曰:‘黄鹄飞兮下建章,羽肃肃兮行跄跄。金为衣兮菊为裳,唼喋荷荇岀入蒹葭’”,这已是一种明确的园林游憩、花卉观赏。
魏晋以来,富贵豪奢,竞尚声色,士人清谈,亲近自然,对于山水林泉之乐、花果卉木之美会心更多,追求更甚,相应的园林设施、游赏活动逐渐兴起。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皇室所居之寿丘里“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23]。东晋、南朝、隋唐公私园林好树美竹、名花珍果之种植愈益丰富,民间的花林游赏、折枝佩戴、剪彩相赠、画花妆点也逐步形成习俗。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分草、木、果、竹四类记录了80多种我国南方热带、亚热带植物,东晋戴凯之《竹谱》记载了70多种竹子,同时还有《魏王花木志》一书②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一○,《四部丛刊》景明钞本。该书《隋书·经籍志》未著录,惟《太平御览》辑录多条。,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更是一部系统的农学巨著,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植物学、园艺学的迅速发展。
反映在艺文创作上,汉代以来,植物景观、花卉物色的描写和铺陈成了诗赋创作中的常见内容。而魏晋以来,随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咏花赋开始出现,数量不断增多。如三国曹植有《宜男花颂》,钟会有《菊花赋》、《葡萄赋》,而西晋傅玄除这三题外,更有《紫华赋》、《朝华赋》、《郁金赋》、《芸香赋》、《蜀葵赋》、《蓍赋》、《瓜赋》、《石榴赋》、《李赋》、《桃赋》、《橘赋》、《桑椹赋》、《柳赋》等。在诗歌中,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都是以花卉物色起兴引发情感的,此后专题歌咏花果草木之作较之赋中更多,其他山水、田园、游宴、行旅诗中散见的细节描写更是不胜枚举。东晋时还产生了陶渊明《桃花源记》这样杰出的作品。
艺术领域里也陆续出现了一些花卉题材作品。与诗歌关系密切的乐府,就有《芳树》、《折杨柳》、《梅花落》、《幽兰》、《绿竹》、《桃花曲》、《杨花曲》等曲调,汉时著名的《江南》“江南可采莲”,以及后世《采莲》、《采菱》等也多是演绎水乡荷花飘香,菱歌优荡漾的风景。魏晋以来,随着佛教文化对中土文化的影响渗透,莲花、忍冬藤、天女散花等成了工艺装饰中较为流行的纹样。[24]
隋唐承续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势头,又得国家一统、安定富庶等时代条件,花卉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不断拓展,人们物色征逐、花卉观赏的热情进一步高涨,而相应的园林营造、花季宴游和艺文创作也愈益兴盛。初唐宫庭岁时唱和中芳菲信息比较丰富,长安曲江杏园游赏风气较盛。种植也开始显现规模,初唐王方庆著《园庭草木疏》21卷①欧阳修《新唐书》卷五九,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宛委山堂本《说郛》(百二十卷)卷一○四下辑6条,称《园林草木疏》。,盛唐王维辋川别墅中就有斤竹岭、木兰花、茱萸沜、宫槐陌、柳浪、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名目。相应的山水田园诗派兴起,其中的花木之景和游览之趣较六朝更为丰富。
综观这一阶段,人们对花卉的欣赏兴趣不断提高,相应的文化生活也不断丰富。但就对花卉的观赏兴趣和审美认识而言,人们主要关注花卉的物色美感,欣赏色、香、味、形、姿等客观形象。人们通过鲜花盛开的华艳来体验生命的活力,感受生活的美好,透过花开花落来感知时序的变迁、岁月的流逝,感慨人生的蹉跎、世事的盛衰。“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文赋》)“春花竞玉颜,俱折复俱攀。”(庾信《南苑看人还》)“年年洛阳陌,花鸟弄归人。”(卢僎《途中口号》)“洛阳城中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今年花开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代悲白头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大自然应时而起的无穷芳菲和千姿百态的鲜美物色给人带来无穷的感官愉乐,也激发丰富的人生感触。描写和赞扬花卉物色的美好,感应和抒发生活的欢乐和忧伤,成了这一时期花卉文化的主题。从欣赏心理和思想认识上说,这是一个主要着眼物色美感,偏重情感抒发,带着鲜明感性色彩的时代,我们称之为“花色观赏时代”。
(三)宋元明清——中国花卉文化的繁盛期
在中国历史上,“安史之乱”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此前是中国封建社会明显的上升时期,此后则是一个漫长的逶迤衰落过程,尤其是宋元明清,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都呈现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特征,通常称作“近世”或“近古”。中唐以来,人们种花赏花愈趋普遍,文学中对花卉植物的描写越来越具体细致[25],花卉园艺和花市宴游之风开始兴起,花鸟画蔚然兴盛。入宋后,这些趋势愈益明显,花卉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注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地位和影响明显增强,逐步引起全社会普遍的兴趣,并开始形成独立的文化知识体系。我们看到,初盛唐时编辑的大型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以及宋初《太平御览》等所辑植物内容都称“果木部”或香、药、百谷之类实用名类,而不称“花”或“花卉”。入宋后,情况逐步改变,以“花”为专题的各类编著大量出现,到南宋末年陈景沂《全芳备祖》,以芳(花)为书名,“花部”27卷居先,典型地反映了人们“花”之欣赏意识的高涨和认识水平的提高。随着社会人口的不断增长,社会生活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花卉之在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各方面的价值充分显现,无论是园艺种植、园林施用,还是世情民俗、文学艺术等广泛方面的内容都越来越旺盛,而且是渐行渐盛。第一节中我们所说的种种繁盛景象,实际是到这一阶段才逐步、充分地展开的,因此我们称作中国花卉文化的繁盛期。这其中有这样四个方面最值得注意:
1.士大夫园林、园艺活动的兴盛。宋以来私家园林的兴起与发展是极为显著的一个趋势,士大夫文人园林经营、花木艺植欣赏活动极为兴盛和流行。北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宋末周密《吴兴园林记》、明刘侗《帝京景物略》、王世贞《游金陵诸园记》、清李斗《扬州画舫录》都是这方面记载较为集中的文献。在园林建制中,花卉营景简单易行,因而最为普及。宋苏轼《和文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所咏30景中,竹坞、荻蒲、蓼屿、霜筠亭、露香亭、菡萏亭、荼蘼洞、筼筜谷、寒芦港、此君亭、金橙径等11处属于花卉景点。明欧大任《友芳园杂咏为吕心文作二十五首》中有蔷薇曲、山礬障、丛桂阿、香玉丛、柳竹巷、芙蓉堤、湘云径(竹)、晚香径、牡丹台、桃李园、松月台、友芳桥、凌霄石等11处花卉为主的景观。清李调元《囦园杂咏二十首》所咏自家园亭景物均为花卉。不仅是种植,而相应的观赏活动也是五花八门,极为丰富,限于篇幅,恕不详述。
2.花卉产业化和民众游赏风习的兴起。中唐刘禹锡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可见当时花季宴游之风的兴盛。同时刘言史《卖花谣》,司马扎《卖花者》诗,都写长安郊区农人艺花卖花为生,晚唐来鹄《卖花谣》、陆龟蒙《阖闾城北有卖花翁讨春之士往往造焉……》、吴融《卖花翁》等也都写及村人种花卖花的情景。入宋后这种现象更为普遍,而且逐步显出规模。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北郊马塍就是一个著名的花卉产地,叶适《赵振文在城北厢两月,无日不游马堘,作歌美之,请知振文者同赋》诗称“马堘东西花百里,锦云绣雾参差起。长安大车喧广陌,问以马堘云未识。酴醿缚篱金沙墙,薛荔楼阁山茶房。高花何啻千金直,着价不到宜深藏。”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七也记载:“马塍艺花如艺粟,槖驼之技名天下。”这样的规模产地宋以后就更普遍了。相应的城镇花市也开始出现。最早提到花市的应是五代韦縠《奉和左司郎中春物暗度感而成章》“锦江风散霏霏雨,花市香飘漠漠尘”,入宋后有关花市描写极为常见,成了近古市井生活的普遍风景。各地相应的花市和花田应时赏花宴游渐成普遍的乡土风习。北宋时“西京(引者按:洛阳)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扬州产芍药,其妙者不减于姚黄、魏紫,蔡元长(引者按:蔡京)知维扬日,效洛阳亦作万花会,其后岁岁循习”[26]。到明清时,文人花事雅集和民众郊外赏花之风更为兴盛,台湾学者邱仲麟《明清江浙文人的看花局与访花活动》一文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此间江浙花期文人雅集和民众游乐的空前盛况。[27]
3.各类花卉园艺著述大量出现。中唐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记其洛阳园墅所集花木70多种。晚唐罗虬《花九锡》、五代张翊《花经》则专论花事活动。据园艺史家统计,见于记载和今存宋人园艺书大约62种,其中牡丹14种,菊花8种,芍药4种,兰3种,梅2种,海棠2种,玉蕊1种,这几种花卉就占了一半多。[28]见于著录和现存的明清农书共有1388种,其中园艺类321种。在这321种中,花卉类225种,占70%,占整个农书16%。[29]这些园艺著作,包括品种、种植、园林应用、盆景瓶花、四时花历、观赏宜忌、风雅游乐等广泛内容,连同大量生活百科类著述和大型综合类书的相关内容,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草木编,形成了极为繁富、细密的知识体系,体现了相关科技和人文研究的全面、系统和深入,构成了我国花卉文化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丰硕的历史遗产。
4.文学艺术创作的极度繁荣。花卉文学的繁荣是从中唐开始的,宋初《文苑英华》所收草木赋8卷、花木诗7卷,与鸟兽、草鱼类已大致相当,这些作品中绝大部分都出于中晚唐。进一步的情况无须详述,花卉诗、词、文作品数量堪称浩瀚,花鸟画中“梅兰竹菊”为代表的文人写意极为流行,而在工艺美术中,从唐代,更确切地说应是从中唐开始,由先前的“几何纹时期”、“动物纹时期”进入“花草纹时期”[30],花卉草木成了陶瓷、金属、竹木、玉石、纺织等日用制品和建筑装饰中最常见的题材。诗、画与工艺装饰间相互影响渗透,进一步强化了花卉文化兴盛的浓郁氛围。
正是由于封建文人和广大民众的普遍兴趣和热情参与,花艺花事活动和文学艺术创作的深入发展、全面繁荣,相应的审美认识和文化意识也进入了一个更高阶段。人们并不象早前仅仅停留在对花卉色香、形姿的感知喜爱,而是进一步对各种不同花色品种的个性特征、风格神韵及其观赏价值等有了深入的观察体会和精切的理解把握,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人们也不仅仅满足于花开花落、芳菲盛衰的时序感应和情绪抒发,而是追求花卉品格神韵与人的精神气质投合契应,并借以陶冶人的性情意趣,寄托人的品德情操。宋以来文人雅赏中逐步出现的花卉“十友”[31]、“十二客”[32]、“三十客”[33]、“岁寒三友”、梅兰竹菊“四君子”等说法,典型地体现了“比德”、“写意”的审美趋向和精神追求。与此相应的,在民间也形成了三春“二十四番花信”、一年“二十四番花信”、一年“十二月花神”等知识体系和牡丹富贵、梅花报春,杏花为幸,松菊为寿等吉祥寓意、符号话语。从审美心理和文化认识上说,无论士林还是民间,虽然程度不等、方式不同,但都从侧重于花卉物象的外在形色之美,进入到精神理想和生活信念的比兴寄托,使众多花卉品类逐步形成了系统的象征意义,显示出流行的文化符号色彩,标志着我们民族花卉审美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完全成熟,因此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之为“文化象征时代”。
中唐以来的花卉文化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渐行渐盛的过程,纵向上又可再分为三个阶段:一、中唐至五代。大唐盛世已去,新的社会、文化风气和形态初露端倪,士人阶层开始稳定发展,因而花卉文化迈上了兴旺发展的轨道。二、宋元,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基本定型,伦理道德思潮高涨,封建文化全面繁荣的时期。花卉文化也相应地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比德”、“写意”即品德寄托和情趣寄托形成主流,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花卉文化的精神走向和基本面貌。三、明清,这是一个社会人口急剧增长,社会格局全面铺衍,文化盛极烂熟的时期,花卉文化兼得士林和民众社会的双重人气也进入绚烂至极的阶段。
上述我们通过三大阶段来勾勒中国花卉文化不断发展演进的历史步伐,还有必要进一步强调三点:首先,这三个阶段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民族历史文化是一个悠久而持续的过程,没有遭遇外族全面颠覆、文化彻底中断这样的情景。同样,在花卉文化上,也是一个持续发展、未经中断的过程。第二,这三个阶段是一个活动内容不断拓展、文化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第三,三个阶段之间不是此起彼伏、此消彼长,而是累积叠加,不断丰富的过程。后一阶段并不扬弃前一阶段的内容,而是变本加厉,踵事增华,不断积累,走向繁密精致的过程。这既统一于中国文化富于包容性和连续性的整体特性,同时也与花卉文化无关大局的边缘性质密切相关。与核心文化的大是大非、与时推移不同,花卉文化一直保持着兼容并包,不断发展演进的态势。正是如此悠久持续、生生不息、兼容并包、不断积累的历史过程,最终形成了我国花卉文化极其丰富灿烂的面貌。
三、中国花卉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背景
我国花卉文化何以如此繁荣灿烂,何以有此持续发展、不断丰富的辉煌历程,这有着我国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广泛的历史基础。其中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自然条件
关于我国的自然条件,白寿彝《中国通史》论述中国历史的自然基础时有一段概括性的论述:“土地的辽阔,地形的复杂,气候的差异,以及有关的地区各种不同的自然特点,都使中国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多样。”[34]我国生物资源特别是植物资源极为丰富。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第一卷总论中有这样一段介绍:“中国的国土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跨越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气候带……由于我国土地面积广阔,经、纬度跨度亦大,因此气候条件十分复杂,且全国各地地形、地貌多变,也影响气候的复杂性。更由于中国主要陆块历史悠久,虽经地质地史多次变迁,仍有很多孑遗植物。在第三纪我国大都处于热带、亚热带气候,植物种类丰富。后虽经历了第四纪冰期,中国仅在东北有小面积冰川覆盖,但仍受冰期和间冰期气候冷暖交替的影响,喜暖的植物向南向北后退,某些山地特别是横断山区成为第三纪植物的庇护所,有大量的孑遗植物、活化石和古植被类型被保存,致使近代植物区系与白垩纪-早第三纪古植物区系非常接近,更增加了中国植物区系的多样性。”[35]植物学家进一步称,我国“植物繁生,种类丰富,堪为世界温带国家的第一位。以我国所产的种子植物而论,就有2700属、3万种之多,其中属于我国特产者尤多”[36]。非洲大陆严重缺乏观花植物[37],欧洲和北美植物物种也较为贫乏[38],我国的植物资源得天独厚。正是在这优越的自然条件下,随着人类的繁衍分布,社会生产、生活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人们欣赏需求的不断增长,花卉植物源源不断地被发现和利用,形成了极其丰富庞大的栽培品种体系,中国也因此赢得了“世界园林之母”的称誉。[39]由于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各异,无论是自然生长还是农耕、游牧社会的种植,植物景观都因地而异,形形色色,千姿百态。正如西方学者所说,“花卉是亚洲大陆生态和社会景观的一种显著特征”[40],中国尤然。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首先应该归源于神州大地这地大物博的自然基础。
(二)农耕文明
我国以农立国,先进、发达的农耕文明为花卉文化提供了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这其中与花卉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无疑是园艺业,今人所说的观赏园艺、花卉园艺正是其组成部分。我国园艺种植起源极早,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发现不少果蔬种籽实物,先秦文献中园、囿、场、圃等词出现频率较高,专业的园艺种植和果蔬谷物混种、家庭附属零散园艺种植都极为普遍。
我国农耕文明尤其是园艺业对花卉文化的作用,主要可从这样几方面来把握:一、园艺作物提供了许多具有观赏价值的品种,我国最初出现的观赏花卉大多是果蔬类作物,如桃、李、荷 、菊之类,然后才是以观赏为主的品种。二、农业耕作技术为花卉品种培育、田间管理等提供了丰富的技术支撑,这对我国花卉品种开发和种植传统的长盛不衰助益良多。三、农耕社会的田园风光、乡村生活影响我国园林建设特别重视田园风光的营造和花木景观的种植[41],同时也提供了文学艺术丰富的植物风景题材,从而推动了花卉文学、艺术创作的繁盛。四、城郊、乡村和丘陵山地的花田、果林,其规模化生产为城市及富贵阶层的消费需求提供了丰富的产品,同时其大规模种植的壮丽风景成了封建文人和普通民众乐游胜地,其中不少花海名胜名动遐迩,历久不衰,成了花卉观赏文化中最富社会性、群众性的场景。
(三)士大夫阶层
中国社会历来呈金字塔式结构,上有帝王将相等顶层权贵阶层,这是整个社会的极少数,下层是广大的底层百姓或草根民众,占社会的绝对多数,处于中间的正是士大夫阶层。士阶层在我国至少有2500年的传统,虽有曲折,但从未中断,并且随着体制逐步稳定,数量不断增加,形成了越来越庞大的队伍。从经济上说他们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从政治上说他们是官僚知识分子,是整个统治阶级的骨干。从文化上说,他们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精英,他们既是社会管理、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等领域的“劳心者”,也是人类价值、社会良知和公共利益的“守道者”,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的辉煌成就主要得益于这一精英阶层的贡献。同样,我国数千年花卉文化的繁荣昌盛,也主要归功于士大夫阶层的主力军作用。
植物尤其是花朵对动物的意义是天然的、本能的[42],人类对于花朵的欣赏也是不分你我,随机即有的。但审美并不只是客观的、自然的因素,而是有着更多主观的、社会条件。花卉观赏不是“温饱”而是“奢侈”,不是“生存”而是“发展”。古人曾感慨过这样一种现象:“三吴之间梅花相望,有十余里不绝者,然皆俗人种之以售其实耳。花时苦寒,凌风雪于山谷间,岂俗子可能哉?故种者未必赏,赏者未必种。”[43]这种现象不仅出现于梅花季节,其它花季也都程度不等存在着。“有野趣而不知味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尝者,菜佣牙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达人贵人是也”(陈继儒《花史跋》[44]),这就是不同阶层生活需求的差异。花卉的种植,主要是底层花农、园丁等“劳力者”的任务,但花卉的欣赏与文化创造却主要属于养尊处优、“有产”而“有闲”之士大夫阶层的“消费”行为。私人宅园别墅的花卉种植、日用清供的盆景瓶花制作等属于士大夫的高档生活追求,咏花诗赋和花鸟画的创作更是封建文人的文化职能。正是士大夫阶层队伍的不断壮大,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物质、精神生活的不断拓展,尤其是宋以来士大夫闲适、高雅之生活情趣和风气的兴起,拉动了花卉文化的持续不断丰富和发展。无论是上古、中古时期对花卉物色之美的征逐沉迷,还是宋元以来对花卉品德象征、情趣寄托的追求,都主要地体现着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性格、生活情趣和文化诉求,打着他们的阶层烙印。这其中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隐士一族,他们之于花卉植物的欣赏多有独特的贡献,如陶渊明之以“五柳先生”“采菊东篱下”,发现“桃花源”,林逋之“梅妻鹤子”等等,都是这方面代表。在相关的科技知识上,虽然实际的生产经验出于底层劳动者,但所有农书花谱、药录茶经之类花卉园艺著述——对品种、生产技术的记录和阐释——都几乎出于士大夫之手。西方花卉产业和文化发展中或有商人群体、宗教僧侣集团的作用,西方花园与城市也有着更多的联系[45],而在我国,士大夫阶层是我国花卉文化创造庞大而持久的生力军,纵观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历史,无论是外延的拓展,还是内涵的提升,主要得力于士大夫阶层的“劳心”投入和着意发挥,花卉文化的繁荣主要属于其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流光溢彩。
(四)文化观念
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对于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是助益良多。众所周知,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世界观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认识论和价值观上强调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天理与人欲的交融合一,洋溢着人文主义、实用理性和乐观主义的色彩。与西方宗教主导的思想文化强调神性与世俗对立不同,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来没有西方和中东那种为了维护某种特定教义而拒绝使用花卉的现象[46],更没有西方中世纪宗教禁欲主义下对花卉使用的限制和花卉文化的长期衰退。[47]《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孟子》说“仁民而爱物”,宋儒张载《西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我们的文化强调的都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一体,相通相融。“凡物皆有自然之理”[48],“造化精气,按时比节,泄于草木,各有自然之华”(明江盈科《重刻唐文粹引》),“草木、禽兽皆与吾同生”(明杨守陈《存仁堂记》),草木、禽兽与人类一样,都是天地元气化育的生灵,都是自然生机、天理道心的体现。“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文心雕龙·物色》),“闲来观物到园东,天理流行在在同”(李贤《观物》[49])。在我们的文化中,自然是我们的生命本源、生存环境,同时也是我们心灵赠答的客观对象、性情悟会的亲切朋友、“诗意栖居”的崇高境界。正是这种植根于农耕社会,洋溢着东方智慧的思想传统和文化精神,给花卉审美带来不绝的热情和无穷的灵感。在我国文学艺术中,大自然尤其是山川、草木是最为重要而普遍的表现对象和主题。园林的经营视作对自然的回归,而山水画、花鸟画也多高扬自然的意趣,花草林木是其中最普遍的题材。
我们历史上也曾有过从国计民生出发对花卉奢靡游乐风气的讽谕和抵制。如白居易《牡丹》批评当时富豪买花一掷千金,“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苏轼知扬州日罢举前任的“万花会”[50]。但这只是出于一时一地的社会责任对某些极端现象的不满,与宗教的全面禁止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也有从道德立场出发对“弃实求花”(陆梦发《见梅杂兴》[51]),“玩华而忘实”“徒赏其华,而不究其用”[52]等现象的否定,更有对“华而不实”“玩物丧志”等相关品行的鄙弃,但是就封建士大夫普遍的伦理实践而言,人们面对花卉物色奢侈享受带来的道德困惑,总能找到疏解的理由。如陈景沂《全芳备祖》自序即举两点:一是苏轼《宝绘堂记》所说“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即只持寓心为乐之意而不生占有之心;二是古儒所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学者之当务也”(陈景沂《全芳备祖序》[53]),赏花是为了求知。在整个阶层养尊处优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氛围里,不仅对富贵奢糜的抵制力度微不足道,而且由于花花草草作为生活资源较为普通,人多力所能及,因此,有着更广泛的享受群体,古人所谓“草木果蓏,其华可悦耳目,实可充口腹,皆旦夕之用也,其为善恶,市人能别之,故植者争”(周之夔《与王子功书》[54])。而幽隐、贫居、退闲之士尤引以自得,正如袁宏道《瓶史》序言所说,“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幽人韵士得以乘间而踞”,“欲以让人,而人未必乐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无祸”,花木种植、欣赏是清贫、幽闲者的最宜和最爱。即使是倡导“明天理,灭人欲”最为严格的两宋理学家,对于花卉草木,也难以超然于这一风习之外,多怀着“格物致知”,“即物究理”的热情,表现出同样的兴致。周敦颐不除窗前草,朱熹“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都是著名的例证。因此可以说,在我们的文化里没有对花卉欣赏极端抵制的因素,我们的文化传统对花卉文化的影响从来都是正面、积极的,这是花卉文化在我国持续发展、不断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述四个方面对于花卉文化的影响是一个交互渗透、合力作用的过程。生物资源的丰富、农耕文明的发达、士人文化的活跃、文化观念的通达构成了一个生动有机的人文氛围,天与人,士与农,耕与读,庄与园,果与花,心与物相互交融为一个圆融生息、和合化育的人文机制,使我国花卉文化显示出生生不息,而能圆融充盈的繁荣景象,同时也决定了我国花卉文化的民族风格。
四、中国花卉文化的民族特色
我国花卉文化的民族特色,可以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
(一)名花名树
有日本学者曾经说过:“在无数的植物和花朵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某种花朵与某一特定文化群体之间存在一种亲密的关系,如西方人钟爱玫瑰,中国人偏爱牡丹,而日本人则喜爱樱花。”[55]事实上,中国人所爱的远不止牡丹,花中还有梅花、兰花、菊花、荷花等等,另如松柏、竹子、杨柳等,都是国人特别喜爱的植物。这些植物与我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其中一些甚至获得了一定的民族文化符号、国家精神象征功能,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化植物”。
当然就广义的文化植物而言,还应包括重要的粮食与经济作物,如我国的水稻等“五谷”、桑、麻、茶等等。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植物系统,是在民族独特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历史地形成的。我们这里关注的只是其中的观赏植物,前面所举国人喜爱的花卉植物都可以说是我国的文化植物。今天我国花卉园艺界有“十大传统名花”之类的评比,选推的也是这类重要的文化植物。事实上这类植物远不只是“花”,也远不止十个,但我们很难为此明确一个客观标准和数量范围,这里姑且根据我国几部重要的古代类书的辑录情况开出一个大致的名单。
我们选择这样几部书:一、宋陈景沂《全芳备祖》58卷;二、清康熙间《广群芳谱》100卷;三、清康熙间《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取其中草木典320卷、食货典茶部17卷。就三书所辑资料较多的植物进行统计分析:

植物 《全芳备祖》《广群芳谱》《古今图书集成》4累计茶1 17 22竹* 1.5 3 8 12.5杨柳* 1.5 5 11 17.5梅* 6 11菊* 2 3 1 6 11牡丹* 4 6 10荷* 1 3 6 10松* 1 3 1 3 6 10荔枝1 4 5 10桃* 1.5 5 7.5柑橘1 1 2 4 7

续表:
表中所列为三书中辑录资料所占篇幅较多的植物,前两书以占0.5卷以上(即每一卷只收1-2种植物)为入选标准,后一书部头较大,以独占1卷以上为标准。当然概念大小不一,其中麦、豆、谷、柑橘、杨柳、兰蕙等都指一类植物,因此数量也相应多些。上表所列为三种文献中符合入选标准两次以上的32种植物及其卷数,以累计数量多少为序。它们可以说是我国最重要的文化植物,而其中名称后标有“*”的23种富于观赏价值,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花卉植物。尤其是三种文献中都符合入选标准的竹、梅、杨柳、菊、牡丹、荷、松、桃、兰、桂、海棠、芍药、杏等13种植物(10种花,3种树),更是核心中的核心。在三种文献中符合入选标准一次,也即在前两书任一种占有半卷,或在后一书中占有一卷的观赏植物还有瓜、槐、枣、葵、瑞香、酴醿、琼花、芙蓉、茱萸、石榴、木绵、枫、榆、荆、芦苇、芭蕉、蒿、茅、蜡梅、素馨、茉莉、山礬、紫薇、唐棣等24种(瓜、芦苇、蒿、茅都不是单一的品种),这些也是我国较重要的观赏植物。其中蒿、茅为野草,虽然株体小而几无实际用处,但在我们的文化中多作为土地荒芜、山川萧条、琐屑无用的象征,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我们也归为文化性、观赏性的植物。上述两类合计共得47种。
我们以这47种植物来分析我国花卉植物的品种结构,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1.我国原产占绝对多数。47种植物中,只有石榴、木绵、茉莉、水仙4种有明确的外来背景,其他都是我国原产,如今在我国的分布范围和品种数量居于世界领先。四种外來植物,石榴由西汉张骞通西域时引进,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木绵、茉莉在六朝早期即见种植,水仙五代时传入我国[56],也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从文化上说,这些植物早已完全中国化了。
2.树多草少。47种植物中,木本35种,占74%,草本(包括灵芝)仅12种,不到30%。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特点,“中国栽培的花主要是一些木本花”,“草本花卉相对缺少”[57],显然这主要不是品种资源的问题,而应与我们的观赏花卉多起源于经济应用有关。
3.多出于经济种植。47种植物中,桃、杏、李、枣是我国传统“五果”中的4种,梅、梨、石榴、樱桃也都是重要的果树。12种草本中,早期的兰、芝主要用作药物,瓜、荷、葵都是瓜蔬类食品,菊最初用作蔬菜、药物。松柏、桂、桧、桐、槐、杨柳、枫、榆都是我国分布和使用较为广泛的木材,竹和芦苇则是我国分布和用途极广的高大禾本资源。以上所说已近一半,而且都有2000年以上的种植、应用历史。尤其是13种最重要的植物中,除牡丹、海棠、芍药以观赏为主外,其他10种都富有经济价值,属我国古代重要的资源植物。
这些植物尤其是列表中入选三次的13种植物,其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其中有些从宋代开始就已经出现齐名并誉的现象,如松竹梅称“岁寒三友”,梅兰竹菊称“四君子”,如花中“十友”、“三十客”、“五十客”之类,另如牡丹为“天香国色”、国花,兰称“国香”等等,由此逐步形成了我国传统名花、名树体系。放眼欧美文艺作品,比较常见的植物意象有玫瑰、康乃馨、紫罗兰、郁金香、百合、雏菊、矢车菊、罂粟、夹竹桃、向日葵、睡莲、橄榄、棕榈、橡树、葡萄、无花果、常春藤、水仙(西洋品种)、草莓、风信子等,这些植物我国大都也有,但它们是西方民众的最爱或西方文化的习见之物,打着西方自然、历史的烙印,而在我国文化中则大多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我们的传统名花、名树,带着我国植物资源的区域特色和农耕社会特有的生活气息,体现着我们民族的共同爱好,承载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无论从物色形象上,还是品种结构上,都洋溢着鲜明的中国色彩。
(二)生植观赏
我国人民的花卉欣赏方式也有着鲜明的民族个性,我们以“生植观赏”四字来概括。所谓“生植”,是指自然生长或立地栽培的植物,实际生长着的活生生对象。而在西方,切花、摘朵用于装饰的现象更为普遍。西方至少从古罗马开始,十分“敬重花冠和花环,花环被用作军事胜利后军队的供品。在当地,妇女们将其戴在头发上和胸前,而男人则佩戴花朵和使用香水”[58],编花、卖花的女性成了古代地中海沿岸文学艺术中常见的形象。[59]这种风气虽然在中世纪受到基督教的压制,但迄今仍是西方花卉使用的常见情景。而在欧风美雨袭入我国之前,这类以鲜花编制祭品和礼物的方式,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领域,都极为罕见。我们先民的祭祀多用六畜牺牲和五谷干果,很少用鲜花。先民也有赠花表情之事,如《诗经》“赠之以芍药”,汉魏以下有折花寄远之事,如《荆州记》所记陆凯折梅寄长安友人,但这些多属于表情达意的个性方式或浪漫传说,从未形成普遍的风气。六朝以来节俗游宴中男女戴花较为常见,但这多属节日一时狂欢之举,而一些都市偶有所谓“万花会”之类更被视为浮华作派,为人们所不屑。南朝由于佛教的影响,瓶中插花、缸中养花以为供奉的现象曾一度盛行,此后佛门行之不绝,但也绝未形成普遍的社会风气。
我们民族的赏花,不以剪切鲜花以为铺设和装饰为主,而以自然生长、农田山林和庄园别墅种植之花木的风景游赏、植株观览为主。“天地之大德曰生”,周子不拔窗前草以观生意,也许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我国园林擅长以水、石和草木植被营造自然而又宜居的风景,重在美化环境,营造意境,“种不必奇异,只取其生意郁勃”(王象晋《群芳谱序》)。我国唐宋以来兴起的盆景,“盆花种活自佳色”(马中锡《即事二首》[60]),主旨在于营造天趣、“生意”[61],意在将自然山水和花木生植风景引入庭院、案头、几格之间,使人家常起居而有山间陌上之乐。中国瓶花不只是插花造型,还要蓄水“养花”,求其耐观。这些艺植、观赏方式都有着着眼实际生姿、追求自然生趣的特点。
不仅是审美对象的差异,还有审美态度的不同,如果说西方人注重“装饰”,而我国人民则注重“观赏”。西人所著《花文化》一书谈花卉审美价值,多以“装饰性”(ornamental)一词概括,与“生产性”、“功能性”、“果实性”相对而言。①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4.、12、26、38、48、54、67、122.而在我们的文化中,虽然花朵、植物的装饰性也受到重视,比如我们工艺制作中,植物形象就是最常见的装饰纹样,也有以布帛、纸张剪裁花朵彩胜以为节令之礼的现象,但这些都不是花卉使用的主流。“装饰”一词并不能充分揭示我们民族心目中的花卉价值,而“观赏”一词更能恰切概括我们民族对花卉的态度。“装饰”意在强调花的客观形式美,而“观赏”则重在说明人的主体活动和感觉。我们民族重视的不是外在功用,而是主观感受、内在情趣。花卉植物是我们欣赏、体悟、友爱、交流的生命对象,而不只是用作装饰的物质资料。从客观上说,我们的传统花卉中木本多于草本,切花或折枝装饰代价较大,因而难以流行。在园林种植中,木本的地位也远过于草本。无论是日常观赏还是诗咏图绘,花朵固然重要,但大多远不如草木实际生长的情景来得意境生动,更受欢迎。这些都隐然与我们民族重视生命,泛爱万物,顺应自然的文化传统与审美情趣有关,体现着我们花卉欣赏的情趣爱好和风格习惯。
(三)“比德”寄托
“托兴众芳,寄情花木”[62],应该是全人类花卉欣赏的普遍现象,但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滋养,尤其是中国士阶层精神世界的蒸腾薰染,在整体上形成了体现我国民族性格的情感体验,形成了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体系。
大致说来,从产生自觉的花卉观赏以来,我们民族的花卉审美认识大致经过这样三个阶梯:首先是“感时抒情”,即对花卉物色的时序感应和情绪抒发。继而是“写形得神”,即对花卉物色形象细致认识和对个性特性的精切把握。在此基础上,最后进入“比德写意”阶段,即透过花卉形象来寄托人的道德品格和思想情操。借用古人的诗句来说,“养花须识花性情,爱花更取花标格”(吴嵩梁《蔗山园赏菊赠赵象庵中翰,兼呈谢芗泉礼部》[63])。“性情”即花卉的神韵特征,而“标格”则是品格情操。“取花标格”即“比德”“写意”,是我们花卉审美的最高境界。
“比德”在我国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思想传统。孔子所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即是典范,而后屈原以芳草比贤士,作《橘颂》“行比伯夷,置以为像”,钟会《菊花赋》赞“菊有五美”以比五德,都是著名的例子。宋以来,随着士大夫阶层社会地位的普遍提高,以理学为核心的道德品格意识全面高涨,即事悟理、因物比德愈益自觉。观物不是为了悦其容色,而是要悟其性,得其理,见其德。“举凡山园之内,一草一木,一花一卉,皆吾讲学之机括、进修之实地,显而日用常行之道,赜而尽性至命之事”。“观松萝而知夫妇之道,观棣华而知兄弟之谊”,“观兰茝而知幽闲之雅韵,观松柏而知炎凉之一致”(胡次焱《山园后赋》[64])。物色可以比德,观物可以悟理,自然审美纳入到了即物究理、“格物致知”、修业辅德的道德实践之中。
如果说“比德”、“悟理”是儒家思想支配下的审美追求,而“得趣”、“写意”则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比德”追求。苏轼认为士大夫种树莳草、“接花艺果”,不是物色财用之好,而是君子胸襟的一种体现,“其所种者德也”(苏轼《种德亭》)。他主张文艺家要“达物之妙”,“造物之理”,“合于天理,餍于人意”,要在契合物之肌理和神髓的同时,写出人的性灵和意趣。这种以自然草木“畅神”“写意”的追求,有着更多“儒道互补”的色彩,在士大夫阶层中有着更广泛的心理基础。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封建社会的广大文人,都特别注重透过园墅经营、花木种植以及相应的诗咏图画来寄托人格、陶冶性情,体现出士大夫精神生活的超越、闲适和高雅。宋以来大量出现的与花卉草木友结盟约,名斋称号如松斋、梅屋等现象,在园林别业中大量的种植营景题额,以及文人画“岁寒三友”、梅兰竹菊“四君子”的流行等等,构成了一个“比德”、“写意”的洪流。
由此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士人品德、情趣的象征系统:“牡丹为贵客,梅为清客,菊为寿客,瑞香为佳客,丁香为素客,兰为幽客,莲为净客,酴醿为雅客,桂为仙客,蔷薇为野客……”[65],这是对花卉品格性情的品鉴。“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66],这是对物色陶冶功能的领悟。不仅是明其物性,还要分其等差,定其尊卑,并且在观赏主体、种植环境、观赏方式、使用场合等各方面制定宜忌条例,分别雅俗品格,以充分张扬士大夫阶层超凡脱俗的心理期求和文化品位,从而形成了极其丰富严密、高雅精致的文化体系。
我们的文化没有西方文化那种神与人、主体与客体的紧张对立,在花卉观念上更没有西方那种宗教象征意义扮演重要角色的情景[67],而我们传统中这种花卉“比德”象征和情趣寄托的丰富内容,构成了我国古代花卉审美的独特精神追求和花卉象征的思想特色,体现了我国崇尚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化精神,尤其是宋以来以理学为代表的道德品格建设的思想成就。
(四)吉祥花语
“花语”是指人们用花来表达人的情感、意愿或观念的特殊信息交流方式。从广义上说,上节所说“比德”象征也属于一种“花语”,历史渊源是极为悠久的。狭义的“花语”是指19世纪兴起于法国的一种为“花”编制的一些符号信息和表达惯例,在欧美世界比较流行。[68]严格说来,我国古代没有这类社会交际功能的设置,但我国也形成了一些花卉使用的民俗寓意和表达习惯,我们可以视之为中国传统的“花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吉祥寓意,陶瓷、建筑、服饰、纺织等工艺制作中广泛流行的吉祥图案即属此类。吉祥本指预兆,后来逐步成为人们祝福祈愿的流行用语,是我国民俗文化中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有着悠久深厚的传统。[69]花卉题材的吉祥纹样正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如“牡丹富贵”、“梅开五福”、松竹献寿、“竹报平安”、“寿比南山松柏秀”,“兰桂齐芳”、“喜上眉梢”(喜鹊、梅花)等等,多取一个或多个花卉,利用名称谐音、形象和习性联想等民俗方式来表达喜庆吉祥之意,寄托我国民众流行的幸福观念,如传统“五福”——“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70]之类,当然也有科举、婚姻等方面的祈愿,与西方“花语”乐于表达的爱情、友谊之类情愫颇异其趣,构成了我国花卉文化一道特别的风景。这类花卉吉祥寓意大多有着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双重渊源和悠久历史,体现着我国民众独特的幸福观,而其表达方式则更多我国民间、民俗的习惯和情趣,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系统“花语”。
总结全文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是一个花卉文化极其繁荣灿烂的国度,无论是园艺种植、花事观赏,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极为丰富繁盛。我国花卉文化发展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的始发期、秦汉至盛唐的渐盛期和中唐以来的繁盛期。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有着我国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广泛的历史基础。我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丰富,给花卉园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我国发达的农耕文明对花卉园艺生产促进良多。我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构成了花卉文化创造的主力,无论是外延的拓展,还是内涵的提升,都主要得力于他们的奉献,也主要体现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文化理想。我国讲究“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念对花卉观赏的影响从来都是正面、积极的,从未出现其他民族那种基于特定教义的严格限制,西方中世纪普遍禁止那样的现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决定了我国花卉文化的民族风格。我国观赏花卉以我国原产的木本和经济应用品种为主,形成了独特的名花、名树体系。我国人民比较重视自然生长、园艺种植的植物生姿,特别欣赏植物的生机天趣,西方社会那种花环、花冠等采结献赠为礼的方式在我国并不多见。在花卉象征上,我国士大夫阶层最终形成了“比德”、“写意”传统,体现着我国崇尚伦理道德的文化精神。我国花卉象征中的吉祥寓意,体现着我国民众独特的幸福观,有着鲜明的民间、民俗色彩,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系统“花语”。
(本文参考和引用英人所著《花文化》一书内容,由门下赵文焕、姚梅、鞠俊三君翻译,特志其劳!)
[1]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J].考古学报,1965,(1).
[2]胡相峰,华栋.《诗经》与植物[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2).
[3]曾慥.类说[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三.
[4]欧阳修.洛阳牡丹记》[M].宋《百川学海》本:花品叙第一.
[5]陶宗仪.说郛[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四下.
[6]朱弁.曲洧旧闻[M].清《知不足斋丛书》本:卷四.
[7]周履靖,黄省曾.菊谱[M].明《夷门广牍》本:卷上.
[8]计楠.菊说[M].清道光十三年(1833)吴江世楷堂刻《昭代丛书》本.
[9]吴曾.能改斋漫录[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五.
[10][11][12]许伯卿.宋词题材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7,37,120-121.
[13][24][30]田自秉,吴淑生,田青.中国纹样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191-195,5.
[14][15][18][39]陈俊愉,程绪珂.中国花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4-12,9,5,4.
[16][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39.
[17][43][52]谢肇淛.五杂俎[M].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潘膺祉如韦馆刻本:卷一○.
[19]郑玄(注).周礼[M].《四部丛刊》影明翻宋岳氏本:卷一.
[20][21]佚名.三辅黄图[M].《四部丛刊三编》景元本:卷四.
[22]葛洪.西京杂记[M].《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卷一.
[23]杨衒之.洛阳伽蓝记[M].《四部丛刊三编》景明如隐堂本:卷四.
[25][日]市川桃子.中唐诗在唐诗之流中的位置(下)——由樱桃描写的方式来分析[J].蒋寅,译.古典文学知识,1995,(5).
[26]张邦基.墨庄漫录[M].《四部丛刊三编》景明钞本:卷九.
[27]邱仲麟.明清江浙文人的看花局与访花活动[J].(台湾淡江)淡江史学,(18):75-108.
[28]冯秋季,管成学.论宋代园艺古籍[J].农业考古,1992,(1).
[29]王达.中国明清时期农书总目[J].中国农史,2000,(1).
[31]佚名.锦绣万花谷[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后集卷三七.
[32][65]龚明之.中吴纪闻[M].清《知不足斋丛书》本:卷四.
[33]姚宽.西溪丛语[M].明嘉靖俞宪昆鸣馆刻本:卷上.
[34]白寿彝,等.中国通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36.
[35]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一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
[36]耿伯介.中国植物地理区划[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8:1.
[37][38][40][45][46][47][57][58][59][67][68]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27,350,19,46,27(和49),73-100,350,43,59,242-243,232-253.
[41]任耀飞,陈登文,郭风平.中国农耕文化与园林艺术风格初探[J].西北林学院学报,2007,(3).
[42][法]让-玛丽·佩尔特,马塞尔·马祖瓦耶,泰奥多尔·莫诺,雅克·古拉尔东.植物之美[M].陈志萱,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71-73.
[44]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七一.
[48]胡炳文.四书通·中庸通[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
[49]李贤.古穰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二.
[50]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五.
[51]方回.瀛奎律髓[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一.
[53]陈景沂.全芳备祖[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卷首.
[54]周之夔.弃草文集[M].明崇祯木犀馆刻本:卷四.
[55][日]牧口常三郎.人生地理学[M].陈莉,易凌峰,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41.
[56]程杰.中国水仙起源考[J].江苏社会科学,2011,(6).
[60]马中锡.东田漫稿[M].明嘉靖十七年(1538)刻本:卷四.
[61]朱良志.天趣:中国盆景艺术的审美理想[J].学海,2009,(4).
[62]汪灏,等.广群芳谱[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凡例.
[63]吴嵩梁.香苏山馆诗集[M].清木犀轩刻本:古体诗钞卷七.
[64]胡次焱.梅岩文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
[66]张潮.幽梦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卷下.
[69]沈利华.中国传统吉祥文化论[J].艺术百家,2009,(6).
[70]马总.意林[M].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三.
〔责任编辑:渠红岩〕
On Prosperous Situation,Development Process,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Flower Culture
CHENG Ji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tremendously splendid culture of flowers,whether in the gardening plantation,appreciation during the blooming seasons,or in literature and other artistic creation.Chinese flower cul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which are initial period of Pre-Qin Dynasty;the prosperous period of growth during Qin-Han Period till flourishing Tang Dynasty;and the thriving period since Mid-Tang Dynasty. Judging from the aesthetic level,the period of Pre-Qin Dynasty is a stage oriented toward practical value,while Qin-Han Period till flourishing Tang Dynasty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attern and color of flowers which aroused people's enthusiasm of appreciation.After Mid-Tang Dynasty,especially since Song Dynasty,there is growing emphasis on the verve and specific characters of flowers,serving as themedium of humanmorality and interest.From this perspective,the three stages were known as“practical value period”,“pattern and color appreciation period”and“cultural symbol period”.Chinese culture of flowers prosperously developed,it possesses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natural conditions and extensive social culture.China owns vast territory and abundant resources,including opulent plantation resources,which provide extremely favorable natural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ardening.Chinese developed culture of agriculture and farming greatly promote the horticultural production of flowers.Besides,traditional literati clas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constitutes the main force in the creation of flowers culture,which embodied both in the extension and connotation.Itwas also reflected in their life style,life interest and cultural ideals.Those ideals like attention to“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the integration of things and human”,and“the worship of nature”have always been positive and optimistic,never been rigidly restricted by those special religious doctrines as it did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especially the wide range restraint appeared during the Middle Ages in Europe.These factors jointly promoted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flower culture in China and determined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scope.Our ornamental flowers were mainly consisted of Chinese local woody plants and economic species,which developed into the special system of famous flowers and trees.Chinese peopl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natural growth and posture of the gardening plants,especially enjoy the vitality and beauty.The tradition of weaving garland and wreath in worship is not common in China.On the symbol of flower culture,Chinese literati class help to form the tradition of“figural virtue”and“liberal style”,both emphasize humanmorality and elegant interest,which symbolize our cultural spirit of respectingmorality.It is rather different from mostwestern flowerswithmore religiousmeaning.Chinese flowers possess auspiciousmeanings that symbolize the unique view of happinesswith stark folk colour,which could be regarded as systematic“Language of Flowers”with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flower culture;prosperity;development;historical background;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G07;I206.2
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4)01-0111-18
2013-11-14
程杰,男,江苏泰兴人,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花卉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