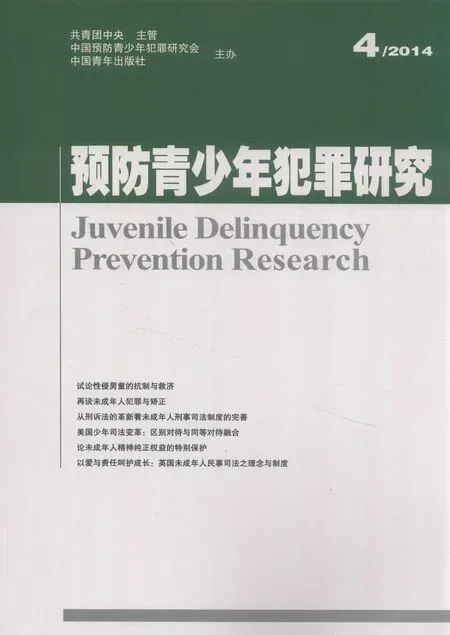美国未成年犯刑罚替代措施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王小光李 琴
(1.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检察院,舟山316000;2. 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法院,舟山316200)
美国未成年犯刑罚替代措施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王小光1李 琴2
(1.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检察院,舟山316000;2. 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法院,舟山316200)
刑罚替代性措施重视教育和改造未成年犯罪人,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美国自建立少年司法系统之后,坚持教育和改造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制定和发展了一系列刑罚替代措施,避免了给未成年人贴上“犯罪标签”,帮助其回归社会,降低了再犯和累犯,有力地解决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我国目前尚未真正建立起针对未成年犯的刑罚替代性措施,为了控制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有必要建立我国的刑罚替代措施。
刑罚替代措施;个体化对待;非监禁刑;改造
刑罚替代措施的目标不是使所有的重罪和轻罪犯都不可能产生,而是在任何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都力争将它们减到最小的数量。[1]
——菲利
刑罚是最为严厉的一种法律制裁手段,但对身心发展都具有特殊性的未成年人来说,单独依靠刑罚的严厉性并不能起到良好的矫治和预防效果,有时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现代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政策也都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重在教育、感化和挽救,而非惩罚报复。为此,很多国家开始对少年司法系统进行改造,转而对未成年犯实行非刑罚替代措施。美国是最早对未成年犯非刑罚措施进行研究和实践的国家,并成立了专门的少年司法系统,在百余年的实践探索中,美国已经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未成年犯非刑罚处置措施系统,这对我国少年司法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未成年犯刑罚替代措施的实施背景
十九世纪以前,在美国,7岁以上的儿童被认为不仅应当为其刑事行为负责任,而且应当承担与成年人一样的结果,并可以对未成年犯判处监禁刑甚至死刑。这种观念对于任何未成年人来说都是过于严苛的。后来,随着未成年人优先发展意识的强化,美国相继采取了建立幼儿园、童工立法、职业教育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为未成年犯建立特别法庭和监禁措施也随之逐步受到重视。改革者们坚信,将未成年犯视同成年犯,过于苛刻。他们认为,建立少年法庭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给未成年犯贴上罪犯的标签,而且如果将未成年犯和其他更严重的成年犯关在一起,让他们成为守法公民的机会就会变得很小。[2]
为了在未成年人触犯严重罪行之前将他们从现有的生活环境中转移出去,方便其改造和教育,1825年,纽约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少年庇护所”( Houses of Refuge),1826在波士顿、1829年在费城又分别建立了两个“少年庇护所”。“少年庇护所”取得的成功,让改革者们更加坚信不仅要对未成年犯实施改造措施,更要为他们提供基础教育,培养他们的生活技能和职业技能,使他们能够竞争到相应的岗位从而立足于社会。这一改革思想也正是1847年马萨诸塞州、1849年纽约市和1853年缅因州建立“少年教养学校”( Reform Schools)的起源。“少年教养学校”在以下5项基础理念上开展工作:(1)将未成年犯与成年犯分开羁押,避免交叉感染;(2)将未成年犯从羁押场所转移到改造场所(改造场所必须是在“少年庇护所”里),并采取相关的监禁和保护措施;(3)在未受到法院审判,并符合最低限度的法律条件的情况下,将未成年犯移交给少年管教所;(4)判决具有不确定性,从而鼓励未成年犯配合并接受改造措施,避免他们因为偶然一次犯罪而堕入了刑事犯罪职业生涯的深渊;(5)明确区分改造措施和感情用事,以防止因掺杂过多个人主观情绪影响改造成效。
1899年,伊利诺伊州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少年司法系统,从而改变了美国少年司法的状况。[3]改革者们提出了国家亲权(parens patriae)理论,为伊利诺伊州少年司法改革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认为,国家的责任是呵护那些不能照顾自己或是得不到家庭照顾的未成年人。应该区别对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因为未成年人的身体条件、精神状况和情感都还是不成熟的,还需要父母的照顾。总的来说,少年法庭分三种情况行使审判权:一是虐待未成年人案件的审判权,审理那些虐待或是无人关护未成年人,以致危害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案件;二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判权,审理未成年人过失犯罪、从犯或是轻微犯罪的刑事案件;三是未成年人监护案件的审判权,审理未成年人实施了一些不符合其身份特征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如果是成年人行使则是合法的,比如旷课。[4]
但是,20世纪80、90年代,美国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问题日趋严重,导致很多州开始对未成年犯采取强硬立法措施,其中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大量未成年犯被逮捕。一般而言,少年法庭逮捕未成年犯主要是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1)未成年犯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2)不准时参加听证会;(3)评估未成年犯的品行。1996年,1800000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大约18%的未成年犯被法庭逮捕,162000个身份违法者(status offender)中,大约6%的被逮捕。[5]1997年,一项以居住地为单位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普查发现,在美国,大约有93000个未成年犯受到公开或是秘密的拘捕和监禁,并且这当中有61%的都是因为暴力犯罪。[6]1998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犯罪报告显示,全国刑事被告人(包括身份违法者)中有14528300人被捕,其中大约有17.7%为10—17岁的未成年犯,即大约有2600000未成年人被逮捕。[7]
很多调查研究都表明,虽然被逮捕的未成年犯逃避审判的可能性小了很多,但逮捕措施将他们与父母、亲人、朋友、学校隔离开来,对未成年犯或罪错少年的生活、教育、将来再就业都产生极大的冲击。当然,不可否认,有些监管场所提供的设施条件、管理制度、服务制度等都非常好。如德克萨斯州的吉丁斯(Giddings State)训练学校里,有专人负责看管和照顾未成年犯,卫生干净整洁,住在里面的未成年犯可以上网,可以接受高中课程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还可以得到生理、心理健康问题咨询。但即便是在条件如此好的监管设施里,仍然存在着剥夺未成年犯权利的问题,更别提在大多数监禁设施里的糟糕情况。1998年,纽约时报报道,路易斯安那州的塔卢拉(Tallulah)少年犯社区矫正中心里存在设施陈旧落后等严重问题:“里面关押着620个11—20岁不等未成年犯,铁窗锈迹斑斑,床铺拥挤得令人窒息,他们吃的很少,以致日渐消瘦,他们穿的很少,以致经常为了抢衣服或鞋子发生打架;未成年犯们手上一本教材也没有,上课的都是些没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而且每天也只能上一个小时的课。”1998年,阿肯色州民主党公报报道,阿肯色州观护中心的未成年犯们,终日暗不见天日,卫生肮脏杂乱,下水道的水和卫浴直接相连,厕所的水四处横溢。未成年犯监禁设施里暴露出的大量问题使越来越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监禁措施对未成年犯的改造成效非常小。
二、美国未成年犯刑罚替代措施的具体表现
强硬立法措施的失败让美国司法系统重新回归区别对待、教育、保护和改造未成年犯的思想,从而逐步发展出大量具有积极改造效果的刑罚替代措施。以下就是一些比较常用的未成年犯刑罚替代措施。
(一)未成年重犯和惯犯的综合刑罚替代措施
为了找到传统改造理论和现代刑罚理论①改造理论认为,不能只注重科处刑罚措施,更应当注重针对每个未成年犯的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干预措施.刑事处罚理论则认为,应当注重发挥刑事处罚的威慑力,通过刑罚让未成年犯认识到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刑罚的威慑力达到预防再次犯罪的目的.之间的平衡点,有效处理未成年惯犯和重犯问题,美国很多州实施了未成年重犯和惯犯的综合刑罚替代措施(以下简称综合措施)。该措施为未成年犯提供咨询、工作场所、工作技能培训、学习教育、戒毒、以及其他相关服务,而这些都是成人刑事司法系统所不具备的优点。该类措施的应用和推广,降低了未成年犯的再犯比例,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总的来说,实施综合刑罚替代措施有5个关键点:(1)将未成年犯监管起来 ;②此处采取的是非传统的监管措施,而是将未成年犯集中到一个固定场所里,方便监视、管理和改造.(2)利用一些小型设备;(3)特别强调未成年犯必须具有刑事责任能力;(4)对综合措施的实行进行全程监控;(5)提供改造服务。其中,监管措施是为了达到刑事处罚和预防再次犯罪的目的,从而告诉未成年犯,应该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负责。运用小型设备是为了给未成年犯创造开放、友好的良好氛围,给他们时间和空间独立思考,或者参加小组,共同探讨他们的犯罪行为,并认识到其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将全程监管措施跟刑事责任能力结合在一起,则是为了保持刑事处罚的连续性,推动改造工作有效进行。
(二)审前分流程序
在少年法庭受理案件或是判决前,未成年犯罪人为初犯或是轻微犯的,可能会受到分流处理。审前分流程序在强调未成年犯的刑事责任能力、行为可谴责性的同时,致力于建立与赔偿事宜有关的联邦(州)立法、以及提供咨询、教育和社区服务等。与监禁刑相比,审前分流程序的司法成本更低,而且有助于将尽可能多的未成年人从进出铁门的恶性循环中解救出来。审前分流程序分为法定审前程序和社区自愿者审前程序两种。法定的审前分流程序中,观察保护官与未成年犯及其父母签订一个期限不超过6个月的协议,约定未成年犯在非正式的观察保护期间,要积极赔偿,定时参加社会团体,继续接受教育。在协议执行过程中,未成年犯进行或试图进行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观察保护官会将之作为此后逮捕或正式观察保护等强制措施的证据。社区自愿者审前程序则是让未成年犯回到之前生活的那个社区,由未成年犯的父母、社区居民等共同监督未成年犯的日常行为,并注重提供必要的咨询服务和告诫他们接受教育确有必要。两种审前分流程序都最终会消灭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避免了由于被贴上“犯罪标签”而导致未成年犯丧失升学或服兵役的资格,甚至产生自我犯罪的暗示。虽然上述两种审前分流程序都没有彻底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但它们采取“改造+处罚”的方式,另辟蹊径地为美国各州提供了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新方式,而且有力地降低了未成年犯的再犯比例。
(三)观察保护
观察保护并不限制人身自由,而是全面的监控未成年犯的一举一动,从而防止其再犯。据统计,在美国,被判观察保护的未成年犯占了少年法院审理案件的1/2以上(占了无罪判决的1/5),其他法院处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该比例也达到了1/3。1996年,除了被判家庭监禁的案件,还有634100名罪错少年、58300名身份违法者被判观察保护。[8]观察保护官主要开展监督、服务和咨询三项基本工作。具体来说,包括:(1)在少年法院和家事法院审理的案件中进行认真甄别、筛选;(2)在处置和判决前,对未成年犯进行调查;(3)少年法院或监管官负责监管未成年犯。未成年犯被判观察保护的,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定期会见观察保护官、按时上学、活动范围仅限于居住社区等规定,对上述条件的具体限定观察保护官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由于观察保护注重了解每个未成年犯及其家庭的情况,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个体化对待措施,可以对未成年犯起到了很好的改造效果。观察保护措施也一度在美国得到广泛的适用,但是近年来的适用率有下降的趋势。
(四)未成年犯训练营
1985年,新奥尔良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未成年犯训练营,其指导理念是:利用威慑力制止犯罪,使之不能再犯,并注重改造教育和成本控制。同时,它借鉴了传统新兵训练营中的一些基本元素:军事化管理措施(将未成年犯与普通囚犯分别羁押)、强制无偿劳动。在此基础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承办法官提出了通过接受教育和培养生活、工作技能来提高未成年犯的生活能力,帮助其回归社会的改造理念。总的来说,未成年犯训练营通过将未成年犯置于军事化环境来实现改造、教育、挽救的目的。不过,实证结果表明,该方式对于提高未成年犯生活能力、降低再犯的成效并不明显,实施效果也只能等到未成年犯被释放出来后才能得到确切的检验。
(五)父母培训计划
家庭是塑造未成年人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础,一旦没有了健康的家庭成长环境,一个人很容易误入歧途。为了能够帮助家长处理未成年犯问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制定了父母培训计划,培养父母处理问题少年和管理家庭的技能,为困难家庭提供照看未成年人、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等必要援助。[9]其中,援助措施可以让那些单亲家庭或有经济困难的家庭拥有更强大的勇气和力量来改造、管束他们的孩子。研究表明,为这些困难家庭提供支援,可以让那些出生在重负之下的未成年犯最终克服认知能力差或是对自己出身耿耿于怀等问题。可以说,父母培训计划是改造未成年犯的良好开端,因为家庭是塑造未成年人品性、陪伴未成年人成长的地方,家长有责任帮助改造问题少年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六)高端学前计划
为了帮助未成年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而不是违法犯罪行为上,美国一些州制定实施了高端学前计划,为那些具有高危犯罪倾向的未成年人提供教育、帮助和咨询服务等,从而改善未成年人的成长教育环境。有关研究表明,参与了高端学前计划的未成年人的IQ在短时间内有了较大的提高,在学校的表现也良好,毕业率上升,留级率下降。由此可见,为未成年人提供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教育能让未成年人有能力做出合理的选择,严谨地分析情况,明辨是非对错,为他们通向成功打开大门。
(七)少年司法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办公室指导计划
为了帮助和引导未成年犯走上正轨,美国一些州设立了少年司法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办公室,主要行使以下四项基本职能:(1)收集和传播改革信息;(2)研究和评估;(3)制定和检查标准;(4)提供培训。该办公室制订了未成年人犯罪指导计划,为未成年犯提供学习教育和改造服务,并鼓励未成年犯遵守《1974年少年司法和少年罪错法》。少年司法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办公室将来自不同拘捕中心、学校和家庭的5—20岁不等的未成年犯集中在一起,让他们互相建立起一个成年犯对应一个未成年犯的一对一关系,由警察、大学生等志愿者共同实施指导计划。指导人员根据以下5个步骤开展工作:(1)消除偏见,不能有先入为主的想法。(2)公平对待,不能单凭样貌或地位对被指导人员品头论足。(3)围绕家庭、朋友、生活等话题建立与被指导人员的信任关系。(4)通过谈话逐步深入的方式,逐步了解未成年人进行违法犯罪行为的原因、作案同伙、个人家庭背景。(5)制定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具体措施。未成年人犯罪指导计划实施过程中,重视告诉未成年犯,不要介意自己的出身或是家庭背景,不要执著于过去的错误,关键是要努力克服目前的困难现状,把握未来。有少年司法官员将未成年人犯罪指导计划的成功归结为两点:为自愿者提供人身安全保护和各项指导技能培训,由专人负责对每一组被指导对象进行监督。[10]有人甚至指出,如果想要从根本上减少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就应该参加未成年人犯罪指导计划。
(八)后期辅导计划
即使是那些在监禁设施里接受了恰当处置的未成年犯,当他们返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想要持续改变自己的行为也是有困难的。为了成功地帮助未成年犯回归和重新融入社会,更重要的一点是要继续采取后续对待措施而不仅仅是监管。为此,美国研究人员进行了很多有关监管和辅导的模型检测,并制定出了大量的后期辅导计划:在传统的假释监督中将监禁措施和将未成年犯送回原来的生活社区两种措施融合为一个整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未成年犯在社区和社会关系网中(家庭、同龄人、学校和雇主)能够实施适应生活的亲社会行为。后期辅导计划强调将未成年犯释放到原来的生活社区时,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设置相应的服务设施,进而对未成年犯的行为进行全面监控,并对可能增加其再犯可能性的危险因素进行评估。1998年,美国学者Lipsey 和Wilson研究表明提供全面的个人技能培训(如社会技能培训)、行为准则和个人行为认知能力咨询的计划最能降低未成年犯的再犯率。[11]
三、美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的启示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探索,我国已经逐渐摸索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司法制度,比如圆桌审判、社区矫正、心理评估机制、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2012年通过的新刑诉法又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改造未成年犯、帮助未成年人回归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少年司法系统还有许多配套制度未建立完善,尚需进一步检讨修正,为了适应新形势下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需要,应当逐步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
(一)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
美国少年司法系统实行的一系列刑罚替代措施都坚持了“教育+改造”的司法理念,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就告诉我们,如果实施少年司法制度是为了降低未成年人的再犯和累犯比例,减轻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那么一味地坚持和采取强硬立法措施和惩罚措施都不是有效的改革措施,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必须坚持改造道路。或者说,对未成年犯科处刑罚并没有错,错在将未成年犯交由成人司法系统处理,成人司法系统并不符合教育、改造和挽救未成年人的需要。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改变的并不仅仅是未成年犯,而是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司法制度。为此,必须牢牢记住,强硬的立法态度或司法措施未必是好的选择。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沃尔夫岗调查发现,在美国,1万名未成年人中,因违法犯罪被警察处理过的有3000 人,经过矫治后,大部分人都改过自新,仅有6%的人成为惯犯、累犯。[12]由此可见,致力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时,改造恢复比惩罚更为重要,效果更为明显。我国在建立和完善少年司法制度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改造+教育”的路径,最大限度地挽救未成年犯,帮助更多的未成年犯回归社会。当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均明确规定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必须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指导原则,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指导方针,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理念。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刑法、刑诉法等刑事法律的适用中更好地融入、贯彻落实上述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司法理念,切实帮助未成年犯罪人回归社会。
(二)注重个体化对待策略
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也主要与其生理、心理还不成熟、社会化尚未完成等有重大关联,但每个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不尽相同,每个未成年人的性格、成长环境也各有不同,为此,对待未成年人的处遇措施必须富有个人特色。美国未成年犯训练营采取军事化管理和个体化对待的双重管理方式来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制定并实施了相应的管理和改造措施,本将会是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理想刑罚替代措施,只可惜实际执行中遗漏了“个体化对待”这一重要因素,导致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功。观察保护措施和未成年人犯罪指导计划则由于注重了解每个未成年犯及其家庭情况、犯罪原因,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个体化对待措施,从而起到了很好的改造效果。因此,制定和实施未成年犯刑罚替代措施,应当具有针对性和个别性。首先,应当弄清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的原因。未成年人犯罪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如出生在问题家庭、无人管教、其他同龄人带来的压力、自身生理或心理问题、性侵犯、社会阅历浅、经验不足、物质需求却又经济不独立等。其次,要做的才是制定有针对性的具体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要注重将所有未成年犯作为一个整体对待,注重给予特殊关照或是提供有关咨询服务而不是过于强调军事化性质的强硬管理。最后,刑罚替代措施的制定者应该根据“儿童最佳利益”原则,选择最合适的时机,确定每个时段的具体措施。只有坚持以“未成年人”这个主体而不是“犯罪行为”这个客体为基本出发点,才能为未成年犯量身打造改造和教育方案,从而达到降低未成年人再犯比例的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社会调查,并且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第28条规定:“法庭调查时,审判人员应当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行为时的主观和客观原因。”根据上述规定可知,我国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时,注重调查清楚未成年人的个人重大事项,以确定符合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措施或是监护、帮教等非刑罚处置措施,强调了个案处理的原则,值得肯定。但是,单独就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而言,我国刑法第17条、37条规定的几种刑罚替代措施是通用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没有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性对适用主体进行区分,也没有突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13]容易导致司法实践中选取的非刑罚替代措施因缺乏“个体化对待”这一因素而效果不佳。
(三)实施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综合刑罚替代措施
美国少年司法系统成功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最大成果在于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刑罚替代措施。如,观察保护、程序分流、父母管教、教养学校、电子监控、训练营地、社区服务等。这些刑罚替代措施有一个共同点:以非监禁刑为核心,通过给予未成年犯适当的惩罚措施,让他们认识到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注重预防监禁刑带来的交叉感染问题,通过“教育+改造”的方式让未成年犯重新获得社会的认可,顺利回归社会,最终实现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以及保护未成年人的双重目的。此外,在未成年犯刑罚替代措施的实施中,应当尊重发挥家庭的基础作用,通过父母的日常言行来影响未成年人、塑造未成年人的良好性格,为未成年人提供基本教育,对于改造未成年人也是必不可少的,父母培训计划和高端学前计划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子。
就我国而言,并不存在独立意义上的刑罚替代措施。一般认为,根据刑法第17条和37条的规定,目前适用于未成年犯的刑罚替代措施包括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责令父母或监护人严加管教,形式较为单一,内容不够丰富,适用范围较为狭窄,缺乏专门立法。司法实践中,实施效果也并不理想,存在着由于根据不同案件设置不同非刑处遇措施的标准模糊导致适用条件不好把握、刑诉法未对非刑罚替代措施设定程序标准导致适用程序不够规范、以及由于配套措施不健全导致非刑罚替代措施适用质量不高等问题。因此,可以借鉴美国少年司法系统中的刑罚替代措施,对未成年犯作出处罚的同时,为未成年犯提供知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后期辅导等各种形式的服务,尽量减少再犯的可能性,并帮助未成年犯更好更快地矫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争取早日顺利回归社会。
[1] [意]恩里科·菲利.郭建安译.犯罪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212.
[2] Candace Zierdt, The Little Engine That Arrived at the Wrong Station: How To Get Juvenile Justice Back on the Right Track, 33 U.S.F. L. REV. 403, 404 (1999).
[3] Christine Chamberlin, Not Kids Anymore: A Need For Punishment and Deterrence in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42 B.C. L. REV. 391, 395 (2001)
[4]Naomi R. Cahn, Pragmatic Questions about Parental Liability Statutes, 1996 WIS. L. REV. 399, 403 (1996).
[5] Stahl, A.L., M. Sickmund, T.A. Finnegan, H.N. Snyder, R.S. Poole, and N. Tierney 1999 Juvenile Court Statistics 1996 .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6] Gallagher, C.A. 1999 Juvenile Offenders in Residential Placement, 1997. OJJDP Fact Sheet, #96, March,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7] Joan McCord, Cathy Spatz Widom, and Nancy A. Crowell, Juvenile Crime, Juvenile Justice, Panel on Juvenile Crime: Prevention, Treatment, and Control,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DC,40(2001).
[8] Stahl, A.L., M. Sickmund, T.A. Finnegan, H.N. Snyder, R.S. Poole, and N. Tierney 1999 Juvenile Court Statistics 1996 .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9] Edward, Mulvey et al., Preven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4:2 The Prevention Reseacher1- 4, 1 (1997).
[10] Grossman, Jean Baldwin and Eileen M. Garry, Mentoring: A Proven Delinquency Prevention Strategy, http://ncjrs.org/ txtfiles/164834.txt.
[11] Lipsey, M.W., and D.B. Wilson 1998 Effective intervention for serious juvenile offenders: A synthesis of research. Pp. 313-345 in Serious and Violent Juvenile Offenders: Risk Factors and Successful Inter-ventions, R. Loeber and D.P. Farrington, e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12] 丁寿兴,刘玉奇. 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措施的理性思考[J].少年司法,2004(02):47.
[13] 刘剑波.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探讨[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36.
2014-06-15
王小光,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李琴,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