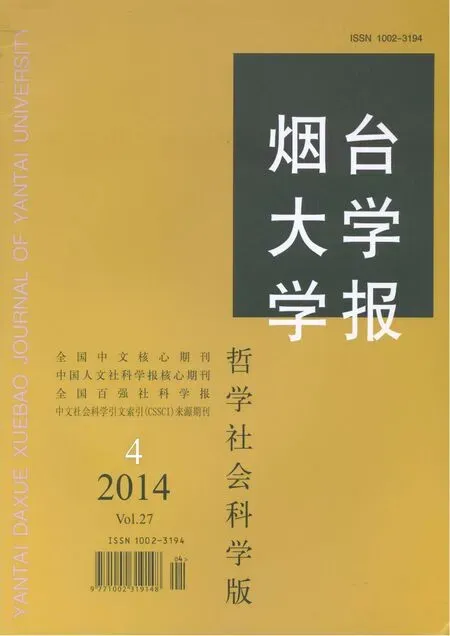新时期文论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引进与移植
邹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89)
新时期文论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引进与移植
邹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89)
新时期文论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引进和移植,拓展了文艺理论建设的视野和思路,对于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长期滞留在古典主义的历史阴影之中,新时期文论在“文革”结束后三十多年的过程中经历了以从“唯情内转”到“唯利外转”为主线的演变转化,审美特性与社会生活趋向统一的现代美学课题始终未能得到理论思维的关注和解决,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引进和移植亦随之出现较大的偏差,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引进和移植上。深入研究新时期文论在引进和移植西方现代美学过程中形成的基本模式和出现的主要问题,从而建立既不同于“西马”又不同于“苏马”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这是中国当代文论重要理论课题和历史任务。
新时期文论;西方现代美学;引进移植;主客二分
一、新时期文论与西方现代美学
广义的西方现代美学,亦即德国古典美学终结之后发展起来的整个西方美学,应当包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狭义的或通常所特指的西方现代美学则指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欧美各国的美学。尽管狭义的西方现代美学并不包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但作为一种与狭义的西方现代美学同时生成、互动发展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整个西方现代美学的关系是必须重视和研究的。
重建不同于古代历史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并由此重建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以及由此提出和解决审美特性问题,这是中西现代美学的共同的历史使命①参阅邹华:《流变之美:美学理论的探索与重构》,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任何属于现代范畴的美学理论,无论在这两大关系中是偏重前者还是偏重后者,都会同时关注相对应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偏重社会和理性,西方现代美学偏重个体和感性,这种不同的偏重不过是现代美学重建上述两大关系的一种必要的方式。20世纪形成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其思想倾向更偏重个体感性,更接近狭义的西方现代美学。本文第二题将专论新时期文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引进和移植,强调建立既不同于“西马”又不同于“苏马”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并由此推动整个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
新时期文论是从自身的历史参照和接受视野出发,引进和移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美学的。但是从中国现代美学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个接受基础并不在重建上述两大关系的现代范畴之内,而属于中国现代美学所特有的“后古典主义”,亦即从王国维开始向现代延滞并以释放负面影响为主的古典主义(在古代历史条件下,古典主义对美学和艺术的影响以正面为主)①参阅邹华:《中国美学的后古典时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为了准确判定新时期文论的接受基础,首先应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美学的两大系统以及多种矛盾复杂交织的格局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包括审美方式的两极对峙是否形成(审美扩展)、审美与功利是否趋向统一(审美特性)、古典主义如何转化为现代形态以及如何形成客观性假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文革”结束前,强调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美学占主导地位,但其又分化出从政治出发和从生活出发的两种形态,前一种形态具有压倒优势,后一种形态则根本没有发展起来。社会生活被隔绝或被修饰,古典主义的功利论以“独尊”现实主义的方式对这种审美方式和文艺思潮进行了长期的政治异化②参阅邹华:《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西方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现代哲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哲学上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在美学上转化或体现为形式主义和情本主义两种倾向,在艺术上先后统合为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20世纪的现代主义。情本主义主要包括唯意志论美学、生命美学、精神分析美学、存在主义美学和接受美学等,形式主义主要包括俄国形式主义美学、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解构主义美学等。新时期文论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引进和移植,前后经历了唯情重心和唯利重物两个阶段,就其内外不同的取向而言,可称之为“唯情内转”和“唯利外转”。“文革”结束后,新时期文论首先是以对认识论的误判和绝对排斥而形成“唯情内转”倾向的,由此出发,又形成了感性缺损(排斥感觉经验)和理性缺失(排斥意义价值),以及返回内心(排斥社会生活)和空灵境界(超绝现实功利)的两种倾向,可分别称之为“欲本论”和“纯美论”③参阅邹华:《流变之美:美学理论的探索与重构》第三章“审美封闭与审美残缺”,其中第二节“古代审美意识的两个基本规定”论述了纯美空灵与功利意欲之间的互补和摆动。。
偏重个体感性是新时期“欲本论”与西方情本主义美学的共同点;两者的差异在于,情本主义在强调生命、情感、体验等的同时,从总体上仍然讲价值判断和意义把握,称其为“非理性主义”并不准确;而新时期“欲本论”对个体感性的理解却大多带有古典主义在其后期阶段出现的理性失控、感性生物化的特点,因而更符合“非理性”的特点。需要注意的是,“唯情内转”尽管断然否定了审美意识连接社会生活的认识维度,但在另一种倾向即“纯美论”上却接受了与认识论密切相关的形式主义。西方现代美学形式主义的侧翼有情本主义的互补和支撑,其情感源自生活的意志和体验,形式与情感两大范畴是相辅相成的。然而营造空灵境界的“纯美论”却以隔绝生活为前提,情感处在无根乏力的状态,难以激活和带动抽象的形式,这种失去生命活力和情感动力的形式结构从一开始就沦为智力游戏的玩具。简言之,“唯情内转”的两种引进移植的模式,再一次疏远了“文革”后本应被召唤回来的真实的社会生活(从上世纪50年代起逐渐淡化至“文革”完全消失);在古典主义空灵论的窒息中,那个本应建立在生活激情之上的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艺术中只是一具没有灵魂而徒有其表的躯壳。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商业消费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新时期文论的“唯情内转”逐渐转变为“唯利外转”。除了外部条件的影响,这种转变还有其内在机制:“欲本论”本身所内含的功利指向,以及“纯美论”与功利论两极互补、周期摆动的古典逻辑,这两个方面的合力也是导致“唯利外转”形成的重要原因。与中国古代美学的教化论传统并不完全相同,新时期文论的“唯利外转”在回归和突显政治功利的同时,还历史创新地将商业消费的经济利益纳入其中,第一次具有了政治功利和经济利益综合化的二重性,就其模式而言,可分别称之为“政利论”和“物利论”。在西方现代美学的引进和移植上,“物利论”与实用主义美学以及审美经验现象学等关系密切;上世纪50年代姚文元的那个“照相馆”美学,其幽灵以新变的形式重现出来。“政利论”则具有重返“文革”结束前“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倾向,文艺附庸于政治的工具论再次成为可能;这种倾向更多地从西方美学的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批评等理论中截取适合其需要的内容。
新时期文论的“唯情内转”无法站在现代的高度上论证和解决“审美特性”的理论课题,“纯美空灵”老庄境界是其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唯利外转”的倾向当然更不具有这种可能,它只能从古典主义的审美论,亦即从纯形式与纯功利两极摆动的逻辑转向社会生活,因此无论它是转向政治功利还是转向商业物利,都应当注意其与西方实用主义美学、审美经验现象和文化研究等理论的深刻差异;不仅是民族地域的文化差异,更主要的是古代与现代的历史差异。
二、新时期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
乌托邦主义或审美乌托邦是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关键切入点。乌托邦主义具有双重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缺陷和独特贡献都由此而生。其主要缺陷在于,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精神,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力和经济状况考察社会现实的基本立场,它的文化转向和意识形态战略,具有唯意志论的主观色彩和浪漫空想的虚幻性;其次,从这种乌托邦主义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虚构了所谓“工具理性”的泛意识形态神话,对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历史的深刻变革和巨大进步采取了偏激的情绪化的贬损态度;第三,由此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形成了偏狭的审美主义立场,以超越社会现实的所谓自律性(疏离性)维护内心世界的纯净,马克思主义贴近现实、再现生活和认识真理的现实主义美学被完全抛弃。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精神同时也有其独特的价值。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在美学和艺术领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他们将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美学融入其理论创建,尤其从个体感性的角度推进和深化了整个现代美学体系;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对于认识和纠正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弊端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文化工业理论对于人性异化和艺术商品化的批判,以及对隐含其中的意识形态向度的揭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偏重个体感性的立场,显示了现代美学大规模地开发人的内心世界的历史趋向,有助于理解和阐释现代主义艺术的审美特质;第四,与疏远物化现实的审美自律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在审美内涵上更趋辩证合理,审美本身就包含着政治的维度,审美性与功利性达成内在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认知性和政治性的两个维度,由此生成马克思主义美学艺术论的两种基本倾向。认知性的意识形态理论强调艺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重视艺术的再现性及其对生活真理的揭示;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理论注重艺术的社会现实的实践作用,苏俄马克思主义美学更强调艺术辅助政治意志的社会功效。这两个维度并非并列对等,从根本上说,认识论的维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具有基础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是从贬义的内涵上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就是试图揭示其颠倒、虚假的认识论根源,并将其建筑在贴近生活真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上述两种倾向,均对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前者形成从鲁迅到冯雪峰、胡风的以生活真实为核心文艺理论,后者形成从瞿秋白到周扬、蔡仪的以政治功利为核心的文艺理论。历史证明,前一种倾向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它长期处在极度衰落的状态;后一种倾向则完全不同,与中国古典文论传统相结合,它占据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发展的主导地位。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双重维度和文艺理论的两种倾向是交织在一起的,以生活真实为核心的文艺理论亦重视艺术的社会功效,而以政治功利为核心的文艺理论亦强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因此,尽管后一种倾向占据主导地位,但社会生活的概念并未消失,不仅如此,即便在文艺的政治内涵被极度简化为党性政策的同时,在文艺从属于政治或为政治服务的范畴之中,生活作为艺术源泉的概念仍然存在,不过生活真实已通过阶级性和世界观的意识形态甄别,被转化为“本质”的真实。由此出发,概念化、公式化在“革命文艺”中泛滥盛行,作家对生活的深切体验已无法正常进行,真实的生活现象已无法进入文艺的视野,“革命文艺”所强调的客观性已经成为一种假象。应当说,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已经极大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轨道。
“文革”结束时,中国当代文论面临着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任务,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就是恢复的艺术的认知性和再现性,重建审美与生活的关系,从而使长期被屏蔽、被歪曲的社会生活真正进入中国当代文艺的视野。然而很可惜,中国当代文论并没有摆脱以政治功利为核心的文艺理论的思维定势,并没有识破上述客观性假象的实质及其产生根源,只不过按照相同的思维定势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其逻辑很简单,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和强调文艺反映认识社会生活是同一个问题,为摆脱艺术工具论的困境,文艺在远离政治功利的同时必须远离现实生活,在远离现实生活的同时必须转向内心世界,于是,将文艺的审美性等同于情感的体验和表现,便成为新时期文艺理论启动重建这一关键时刻的出发点。然而这个简单的逻辑却带来致命的后果。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中国当代美学并没有意识到到从认识论的角度恢复和重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极端重要性,它对意识形态的理解除了政治功利的角度之外只会有肯定或否定的变化。于是,以上述大幅度内转为背景,它从相反的亦即否定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其实质是以审美自律取代或消解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内涵。应当说,从主观愿望和真诚度看,这个理论仍然试图在意识形态的范畴中提出和解决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所看重的认知性和现实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强调再现性和生活真实的美学思想,根本没有进入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视野。这是一个既剪除了政治性维度又完全没有认知性维度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一个被架空了的只剩下纯净之美的“意识形态”,因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那个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都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和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至此已徒有虚名。审美意识形态论在其形成初期并未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此后出现的“审美现代性”概念,却接通了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审美乌托邦相关联的渠道,审美现代性所标示的无功利性,顺势对审美意识形态论做出了后续的论证。
新时期文论中颇为流行的所谓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张力的观点,实际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审美乌托邦理论的翻版;尽管提出这种观点初衷是为了突破审美自律走向消费主义,但将审美等同于鄙视、疏远和抗拒生活的自律性则并无差异。审美现代性理论既适应了新时期文论的审美内转的要求,又迎合了对审美自律的纯净化理解,这就与审美意识形态论形成理论对流和阐释互动。审美现代性理论直接误导了新时期文论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深远背景的理解,在中国现代美学发生和确立的开端上,超功利的审美论和功利性意识形态论被看作是一隐一显并行发展的两条线索,两者最终在新时期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中得到“辩证”结合。审美意识形态论和审美现代性理论的互动,更加剧了新时期文论审美内转的趋向,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审美意识形态论除了打出一面苍白低垂的“人学”旗帜而外,剩下的就是催生出一种截然相反的倾向,即重蹈审美附属于功利的前辙,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转向或文化研究。
但此时的功利性已一分为二,它首先仍然是政治功利,那个被审美意识形态论淡化、消解、架空的政治功利性的意识形态重新回归新时期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论(伊格尔顿、马尔库塞等)使文化研究重新意识到文艺政治维度的重要性。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概念既不同于新时期文论自创的内转空灵的“审美意识形态”,也不同于文化研究顿悟出来的外转功利的政治维度,在“审美意识形态”的概念上,西方马克思主义避开了乌托邦审美封闭缺陷,其对审美与功利两者的关系的理解趋于辩证统一。新时期文化研究对政治维度的关注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就像新时期的审美意识形态论不可能真正达成审美论与意识形态论的“辩证”统一一样。新时期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自律性对社会生活是疏离封闭的,文化研究正是在这种始终未能真正解决审美问题的境地中突入政治功利,非此即彼的灵动转向使之再次回归非审美的功利性,艺术成为政治工具的可能性再次凸现。
新时期文论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存在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新时期文论的发展可分为内转纯审美和外转纯功利两个阶段。在前一个时段中,为批判艺术工具论,新时期文论形成了审美主义思潮,这种内转的趋向使它接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审美乌托邦的主要缺陷;在后一个阶段中,为倡导消费文化,新时期文论重新回到艺术工具论,除了再次成为政治的附属物,就是同时成为商品资本的附属物,这种外转使它排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义审美乌托邦的独有价值。这是一种被“中国化”了的异常奇特的格局,简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精神的主要缺陷,新时期文论以内转的方式完全接受了,而这种乌托邦精神的基本优长,它却以外转的方式全部排斥了。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复兴,有赖于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认识论的阐释和把握,有赖于重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认知性维度。由此出发,新时期文论才有可能走出纯审美和纯功利周期性两极摆动的怪圈,才有可能将新时期之前被长期歪曲践踏、新时期以来又空置久违的社会生活真正纳入审美的视野。认知性是审美意识不可缺少的维度,缺少这个维度,生活现象根本无法进入审美的领域。在审美意识中,认知的抽象性因情感的浸润而转化为现象再现的审美直觉。因此,在重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知性维度的同时,必须重建艺术的再现性维度,在中国,这就是回到鲁迅和胡风,就是回到进入“天地境界”之前的李泽厚;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而言,这就是回到卢卡契。现实主义,这个从未真正进入中国文论和艺术就已完全陈旧并被迅速遗弃的美学范畴,应当从它的悲剧性的失落中真正站立起来。
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排斥个体感性和情感体验,相反,认知性在建立新理性的同时,将促进新感性的生成,再现性在展现社会现象的同时,将为个性主体提供真实具体的生存经验,将为情感的体验和表现开拓广阔自由的艺术空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上述那种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奇特格局才能被反转过来:新时期文论以内转的方式所完全接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缺陷,将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重建意识形态的认知性维度而被克服,那种以再现性向社会生活的外部世界扩展的倾向,将会把审美乌托邦的浪漫激情和主观空想放置在结实而丰饶的大地泥土之上;而由此成长起来个性主体和由此激发出来的情感体验,将会为现代人开掘出一个深邃广阔的内心世界,新时期文论以外转方式所舍弃排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独有价值,将随着这个世界的拓展而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光大,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美学理论,只有在这时才能融入中国当代美学的血脉,而那个在新时期同样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的现代主义,也将与现实主义一道共创中国当代艺术的辉煌①为了完整论述新时期文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引进和移植,本节部分内容转引拙文《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认知性维度》,《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
三、主客二分的四个层次
以上对引进和移植西方现代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阐述,是以中西美学正在经历的古今转换为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的,这就涉及被当前文艺学界所严重误解或曲解了的“主客二分”问题。由于未能深入理解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规律和复杂格局,未能认清长期以来支配中国文论基本构架的所谓认识论不过是由政治功利暗转而来的“客观性假象”,新时期文论总体上对认识论采取了简单化的否定排斥的态度;站在当下所特有的偏狭立场上,这种文论将认识论归结为已经陈旧过时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认为这是导致文艺概念化、公式化的主要根源,主张超越主客二分、抛弃认识论而另创生存本体论。然而这种新潮时髦的观点不仅违背了思想史的基本常识,更严重的是,它造成了新时期文论的全局性误判和根本性失误。实际上,主客二分在哲学上所表达的是古代客体性原则的衰落和近代以来主体性原则的崛起,或者说表达的是古典主义中和封闭之美的历史终结和近代以来大规模开发人的内外世界的审美方式的生成,因而主客二分并不局限于认识论的范畴,更不是一种陈旧过时的理论,相反,它内含着尚未充分展开的深刻复杂的现代性内容,不仅包含着从笛卡尔哲学经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到现代逻辑实证主义等哲学流派的“物我二分”或求真知的认识论,而且包括从叔本华、尼采到萨特、海德格尔的“人己二分”或重生存的本体论;不仅包括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哲学思潮的双向扩充,而且包括现象化再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和抽象化表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两种审美方式和两大文艺思潮的对峙发展。这样看来,主客二分应当包括四个依次深化的层次。
首先是认识论的“物我二分”。这种主客二分指人从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结合的角度自觉地意识到并能动地建立他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面对广阔深邃的宇宙自然和纷繁复杂的社会人生,其认知求真、探索规律的科学意识得以提升和强化。认识论在西方古代哲学中从属于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并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更不占主导地位。近代以来人的感觉经验得到提升和重视,这是认识论得以确立的历史基础,因而这也是一个需要备加珍视的历史成果,即便对当今时代而言,这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推进和深化的历史过程。和认识论不同,在西方古代哲学中,将世界二重化的本体论占主导地位。二重化即现象与本体(存在、理念、本质)两分的柏拉图主义,前者现而不实,后者实而不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二重化既不是近代以来认识论意义上的物我二分,也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人己二分,而是世界本身的现象与本质的二分,以及人性结构的感性和理性的二分。感性对应现象,理性对应本质,其结果是感性现象消融于理性本质,或者说是“我”归并于“物”、“己”沉匿于“人”,这两个方面处在未经分化的原初统一之中,并没有形成主客二分的关系。
本体论的“人己二分”是主客二分的第二个层次。近代以来,柏拉图主义的本体理念世界开始崩塌,感性世界从人间的地平线上逐渐升起,真切的情感体验和独立的价值判断成为建立不同于柏拉图主义的新的本体论的历史基础。所谓本体论的“人己二分”,是指个性意识空前提升的近现代人对古代等级社会的反叛,对冷漠黑暗现实的抗争以及对新的社会理想的追寻,在这个过程中,其关注历史现实的人文精神得以强化。感性世界包括人的内在的感性生命和外在的感性活动两个方面,本体论的重建由此出现两种转向,它们一个为偏重感性生命的生存论转向,另一个为偏重感性活动的实践论转向,两者的形成发展,显示了近代以来大规模地、深入地开发人的内外部世界的历史走向。在这两种转向中,实践论转向因其沉潜于现实人生而具有基础的地位和根本的制约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在实践论转向对社会生活全面开放的情况下,生存论的转向才是有根基的和充满活力的。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生存论的本体论转向并没有像那种否定认识论的观点所推崇的,是对主客二分的超越,它不过是将侧重点从偏重自然的“物我二分”转向了偏重社会的“人己二分”,它不仅仍然处在主客二分的大范畴之中,而且与认识论比较而言,它对主客二分的表达更为尖锐、突显和强烈。
在以上两个层次的基础上,主客二分可以向第三和第四个层次深化和推进。如上所述,认识论的物我二分注重科学意识,本体论的人己二分注重人文精神;前者偏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后者偏主体伦理的实践性,而这两个方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哲学思潮从近代以来的对峙发展,此亦属于主客二分的范畴。“物我二分”的科学意识(认识论)有面向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两个方面,“人己二分”的人文精神(本体论)亦有感性生命和感性活动的两个侧翼,科学意识和人文精神的双向扩充及其内部多重关系的生成建构,属于主客二分的第三个层次。
主客二分的第四个层次是上述“物我二分”和“人己二分”内部多重关系的交叉结合。在美学上,面向宇宙自然的科学意识转化为追求因果规律的形式主义,注重感性生命的人文精神转化为以内心体验为核心的情本主义,而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亦即认识论形式和本体论情感的结合,在艺术上形成包括浪漫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同时,面向社会人生的科学意识转化为直观审视的原生现象论,注重感性活动的人文精神转化为潜入现实人生的社会实践论,而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亦即认识论现象与本体论实践的结合,在艺术上就形成包括自然主义在内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重主观表现,现实主义重客观再现,这两个方面的对峙发展,形成主客二分的第四个层次。
动物没有主客二分,自我意识是人与世界形成主客关系的先决条件。主客二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古代人自我意识的微弱和主体水平的低下,使人与世界的主客关系处在模糊隐匿的状态。因此,近代以来主客二分的突显应当被视为人类思想史的一次伟大变革,它标志着数千年来人类主体性所未曾有过的一次巨大提升。然而这还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历史过程,对于经历了数百年现代进程的西方来说是如此,对于仍在古典主义阴影下徘徊的中国美学和文论来说更是如此;新时期文论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如何超越主客二分的问题,而是如何真正跨入历史门槛,如何真正启动现代性从而将真正属于中国当代美学的课题提到议程之上的问题;在主客二分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美学和文论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刘春雷]
The Introduction to and Transplantation of Modern Western Aesthetics for the Literary Theory in New Period
ZOU Hua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The introduction to and transplantation of modern western aesthetics for the literary theory in New Period not only widens the vision and think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but also impacts tremendousl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However,due to a long detainment in the historical shadow of classicism,the literary theory in new period experienced a change from thequot;internal-rotated emotionalismquot;to thequot;external-rotated materialismquot;,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 and social life,as an modern aesthetic issue,has barely been solved or gotten any theoretical thinking.As a result,the introduc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of modern western aesthetics deviated greatly,which was especially prominent in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of the western Marxist aesthetics.To further study the basic pattern and main problems from the process of introducing and transplanting the modern western aesthetics,thereby build up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theory,is a theoretical subject as well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for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literary theory of New Period;modern western aesthetics;introduc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B 83-06
A
1002-3194(2014)03-0051-07
2013-11-25
邹华(1952- ),男,辽宁岫岩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美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与文艺批评研究”子课题“新时期文学理论对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引进与移植”(12&ZD013);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当代美学审美问题研究”(12ZXB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