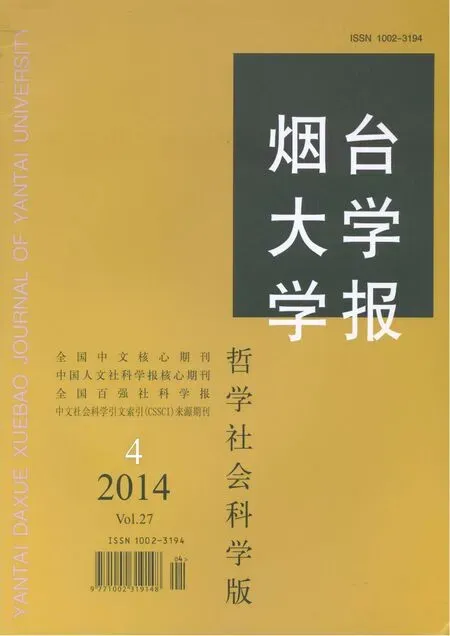论不作为侵权与作为侵权区分的必要性
张玉东
(烟台大学法学院,山东烟台 264005)
论不作为侵权与作为侵权区分的必要性
张玉东
(烟台大学法学院,山东烟台 264005)
不作为侵权与作为侵权的区分在当下仍具意义。二者区分的必要性,尤其体现在因果关系确认上的不同,注意义务负担上的差异,以及作为与不作为共同致害时责任承担的特殊规则三方面。
侵权责任法;不作为侵权;作为侵权;区分;必要性
2011年第十届欧洲侵权法年会上,Helmut Koziol教授做了题为《不作为侵权基本问题》的演讲,其中具体阐述了作为侵权与不作为侵权的区分标准。①Helmut Koziol,“Liability for Omissions-Basic Questions”,in Journal of European Tort Law,2012,pp.129-130.在之后的讨论环节中,Cees van Dam教授认为,当下已无区分作为侵权和不作为侵权的必要。理由在于,侵权责任的成立以违反注意义务为前提,而无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只要违反了注意义务,均要承担责任。Cees van Dam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学者对作为侵权与不作为侵权区分意义的重新思考。
关于作为侵权与不作为侵权的区分,国内学者多予认可。②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页;杨立新:《侵权责任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69页;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2页;王成:《侵权责任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9页。我国在立法上也确认了此种区分。③如《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40条、第91条等均是对不作为侵权的规定。理论及立法上的承认,意味着二者的区分具有意义。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却少有系统而深入的阐述④参见郑晓剑、陶伯进:《论作为侵权与不作为侵权的区分理由及其实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周友军:《交往安全义务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2-184页。。对此,有必要做进一步研究。
作为侵权与不作为侵权区分的意义,即二者区分的必要性。众所周知,侵权责任制度是以作为侵权为典型样态而构建的。因此,对二者区分必要性的分析,就是对不作为侵权特殊性的分析。此种特殊性的分析,从整个侵权责任法的架构上看,应从责任成立和责任承担两个层面进行。在责任成立上,应具体从损害、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和过错四个方面展开。①不作为侵权的成立以作为义务的违反为前提,而在无过错责任中,责任的成立以危险为基础而非在于行为人是否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因此,关于不作为侵权的探讨基本上都是在过错责任的范围内展开。但在严格责任领域,也并非不存在不作为侵权的探讨余地,如产品责任。就此,参见:Pierre Widmer,Ex nihilo responsabilitasfit,or the Miracles of Legal Metaphysics,in JETL,2011,02,p.138,pp.145-146.在此四要件中,损害作为侵权行为所引发的后果,并不因行为样态的差别而存在不同;因果关系的判断,却可能因此而存在差异;关于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是一种纯粹的主观状态,在两种形态的侵权中并无差别。过失,在客观化的认定标准之下,指的是对注意义务的违反,而对于不作为侵权中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同样是指行为人对注意义务的违反。违法性与过失在不作为侵权中名异而实同。但注意义务的不同,是作为侵权与不作为侵权区分的关键所在。在责任承担上,如损害为某一不作为所致,则自然由该主体承担责任,并无问题。但如果某人的作为与他者的不作为相结合而造成损害,应如何承担责任,则需具体探讨。
综上,笔者认为,作为侵权与不作为侵权的区分意义主要体现在因果关系、注意义务和责任承担三个方面。
一、区分意义之一:因果关系的不同
不作为侵权因果关系的特殊性,要从否认不作为可引发损害的观点说起。从比较法上看,不作为可以构成侵权在各国均已获得承认,甚至在一些国家(丹麦、荷兰、挪威)的司法实践中不作为侵权已很常见。②B.Winiger,H.Koziol,B.A.Koch,R.Zimmerman(eds.),Essential Cases on Natural Causation,Springer Wien NewYork,2007,p165;日本学者圆谷峻认为,不作为侵权在学校事故、医疗事故等领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参见圆谷峻:《判例形成的日本新侵权行为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9页。但曾一度有学者认为,不作为不能成为损害发生的原因。如德国学者韦尔策尔认为,“不作为没有行动,绝对无后果可言。”③李仁玉:《比较侵权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1页。前苏联学者沙尔格洛特和安季莫诺夫等人认为,由于不作为不能产生客观结果,所以在不作为及其后果之间是没有客观因果关系的。④马特维也夫:《苏维埃民法中的过错》,北京:法律出版社,1958年,第84页。这些观点似乎很有道理。无疑,从哲学、自然科学的角度,不作为确实不能引发任何损害。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哲学、自然科学以及日常生活中因果关系的含义存在不同。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一个规范概念,是作为责任成立的要件而存在的,其目的在于归责。⑤Helmut Kozio,l“Liability for Omissions-Basic Questions”,in Journal of European Tort Law,2012,pp.130.另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第372-373页。从这个意义上讲,因果关系是侵权责任成立必不可少的要件。当然,仅依因果关系也并不能使得责任成立,尚须其他要件的同时满足。在英美法上,因果关系常被区分为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与大陆法上的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相对应。但因果关系的这种分类,常常会给人带来困扰。⑥EdwrdJ.Kionka,Torts in a nut shell,WestTommson Reuters,p.30.而法律因果关系,实际上指的是责任范围的确定。因此,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次)》、《欧洲侵权法原则》及《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中均以“责任的范围”取代了法律因果关系这一提法。由此,在侵权法上,因果关系应仅指事实因果关系。
在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各国均采取“condicio sine qua non”规则或称为“but for test”即“若无,则不”法则。⑦J.Spier(ed.),Unification of Tort Law:Causati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0,p.127.该规则可具体表述为,若无某行为,则损害不会发生。在该规则的适用上,作为侵权与不作为侵权是存在不同的。在作为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如果没有该作为,则不会产生损害后果。此时,可认定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不作为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如果没有该不作为,则不会产生损害后果。此时,可认定该不作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后者而言,若无该不作为,事实上指的是如果存在某一作为。因此,在“若无,则不”法则的适用上,作为侵权是抽去违法的作为,而不作为侵权则是添加缺失的作为。对此,有学者称前者为剔除法,后者为替代法。①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第383页;刘信平:《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之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208页。
根据替代法,如果行为人为某一合法作为,则受害人应可避免遭受损害。但对损害的避免,也仅是一种基于可能性的判断。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可能性达到什么程度才可确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作为侵权与不作为侵权在可能性的认定标准上是否存在不同?一般而言,在避免损害发生的可能性上,作为侵权相比于不作为侵权要更容易确定。因为,作为和不作为是两种不同的行为状态,作为是指已经发生的事实,不作为是指没有发生的事实。对于已发生的事实,判断其没有发生时所出现的可能性要比判定没有发生的事实在发生时可能性的确定性更大。已经发生的事情要比没有发生的事情更为确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学者圆谷峻认为,“在不作为侵权行为上,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个大问题。因为要正确认定什么也不做的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②圆谷峻:《判例形成的日本新侵权行为法》,第9页。德国学者马克努斯也认为,在因果关系可能性的判断上,不作为侵权因果关系的确定要比作为侵权中因果关系的确定更难,而且,在对可能性的判定上不如作为侵权案件那样严格。③Ulrich Magnus,Causation by Omission,inLubosTichy(ed.),Causation in Law,Praha,2007,p.100.尽管如此,也不能当然的认为所有不作为侵权案件的因果关系判定均难于作为侵权因果关系的判定。个别不作为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可能会较之于个别的作为侵权的案件更为容易。
上述因果关系判定的难易,反映到诉讼过程中,体现为对举证责任标准的不同设定。对此,张新宝教授认为,在不作为致人损害的情形中,受害人不需要证明损害与不作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仅需要证明行为人对受害人负有作为义务和该义务的不履行与损害的发生之间存在高度的可能性即盖然性。④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第60-61页。尽管该观点似乎表明,在不作为侵权中,受害人无需证明不作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实际上,受害人对作为义务的存在及不作为与损害之间存在盖然性的证明,即是对存在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只是,通过盖然性标准,降低了确定因果关系存在的难度,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日本实务也采此做法。⑤日本法上的适用,详见圆谷峻:《判例形成的日本新侵权行为法》,第115-118页。
如上文所述,在不作为侵权中,如果行为人履行了作为义务,损害就不会发生,则认定该不作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有观点认为,不作为侵权因果关系的成立应以作为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甚至有学者指出,不作为侵权因果关系上,最为复杂和重要的焦点就是作为义务的确定。⑥Ulrich Magnus,Causation by Omission,inLubosTichy(ed.),Causation in Law,Praha,2007,p.101.我国也有学者持此观点,⑦参见蔡唱:《不作为侵权行为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刘信平:《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之研究》,第209页。但从责任成立的要件上看,作为义务的确定属于违法性(或过错)要件,与因果关系显然不同。基于此,Koziol教授认为,在作为侵权中,行为致害与行为的违法性是两个问题;而在不作为侵权中,不作为引发损害与是否存在作为义务同样是两个问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没有必要对不作为侵权做出有异于作为侵权的不同阐释。⑧Helmut Koziol,“Liability for Omissions-Basic Questions”,in Journal of European Tort Law,2012,p.131.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在不作为侵权责任的成立上,当我们检视某人是否存在作为义务时,事实上已经对该人的不作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由于作为义务的存在与否在不作为侵权责任的成立上更为关键,因此,人们往往会忽视已经成立的因果关系要件或将因果关系要件与违法性混为一谈。①Zimmermann教授在对欧盟各国不作为侵权因果关系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在一些国家不作为侵权的认定上,并未触及因果关系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要件在责任的成立上是无需具备的,而是在这些国家不作为侵权责任的成立上,同样需要具备因果关系,只是因果关系隐藏在表象之下。参见B.Winiger,H.Koziol,B.A.Koch,R.Zimmerman(eds.),Essential Cases on Natural Causation,Springer Wien NewYork,2007,p.166.当然,该问题的探讨仅具理论意义,并不影响实践中对不作为侵权的认定。
二、区分意义之二:注意义务的差异
根据履行义务的行为形态对注意义务进行区分,可分为作为义务与不作为义务。不作为侵权以违反作为义务为前提。而恰恰是作为义务的存在,相比于不作为义务,前者在更大的程度上限制了行为人的自由。正如Koziol教授所言,如果某人按照要求被禁止为某一危险行为,其仍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去为其他行为;如果某人负有一项作为义务,则其必须按照某一方式为某行为,从而丧失了选择他种行为方式的自由。②Helmut Koziol,“Liability for Omissions-Basic Questions”,in Journal of European Tort Law,2012,pp.131-132.如此,作为侵权与不作为侵权在对行为人自由限制上的不同,成为了二者区分的又一关键所在。
由于作为义务会在更大的程度上限制行为人的自由,所以,侵权法必须寻求行为自由与受害人保护之间的动态平衡。这意味着,法律必须为作为义务的存在找到恰当的基础。因此,为避免对行为自由的不当限制,各国立法均未规定极端的作为义务,即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负有防止他人遭受损害的一般性义务;而是均以行为自由为出发点,在法律中规定,仅于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才认定作为义务的存在。但在何种情况下产生作为义务的问题上,各国的做法极不相同。此种不同,可通过欧洲侵权法小组所做的问卷回答中看出。
D在街上行走,看到一位盲人正走向一个未设置围栏的坑。D未采取任何措施防止盲人掉入坑中。问题是,D的不作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即D是否存在作为义务。
在8份问卷的答案中,赞同存在作为义务的国家有5个,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荷兰和南非;反对存在作为义务的国家有3个,包括英国、意大利和希腊。其中,根据比利时法律,D既需要负担刑事责任也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而根据希腊法律,D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无需承担民事责任。在赞同存在作为义务的理由中,奥地利法认为,在不对自身利益造成危害的情况下,D应存在作为义务;荷兰法认为,D能够认识到危险的严重性,其应存在作为义务;而根据南非法,令D承担作为义务,则是依据善良风俗原则。在反对存在作为义务的理由中,英国法认为,D没有做任何事情,且其与盲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可成立作为义务的关系;意大利法否定作为义务存在的理由与英国相同。③案件及各国具体分析,请参见H.Koziol,Unification of Tort Law:wrongfulnes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8.而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D对盲人并无任何作为义务,因此,对盲人因此而造成的损害无需承担任何民事或刑事责任。
从两大法系侵权法的发展轨迹来看,作为义务均呈现逐步扩大趋势,只是于程度上存在不同。④具体论述参见:European Group on Tort Law,Principles of European Tort Law:Text and Commentary,SpringerWienNewYork,2005,pp.86-87.法律规定、合同及先行行为,通常被认为是传统侵权法上产生作为义务的三大理由。而其中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的范围在以往的数年中被极大地扩张了,如德国法上安全保障义务在判例中的认定与发展。⑤具体论述参见:Ulrich Magnus,Causation by Omission,inLubosTichy(ed.),Causation in Law,Praha,2007,p.103.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对安全保障义务的引入及《侵权责任法》对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无疑也是为了解决作为义务的存在基础问题。在比较法上,关于作为义务,最为值得关注的是《欧洲侵权法原则》和《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中的相关规定。《欧洲侵权法原则》第4:103条规定了保护他人免受损害的义务,具体为:“在下列情形,行为人存在应为积极行为以保护他人免受损害的作为义务,即法律规定、行为人制造或控制某危险的情形、在当事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损害的严重性与防止损害的容易性共同指向应存在某作为义务。”《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第1297条规定:“每个人在以下情形下都有避免他人受到可识别危险损害的义务,即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行为人提供交通或制造、保有某危险源,可能遭受的损害与预防该损害的成本之间不成比例。”两份草案对传统作为义务的产生基础均进行了规定,同时,不仅通过扩张解释特殊关系①依据《欧洲侵权法原则》及《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中对特殊关系的解释,不仅包括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关系,事实上的关系也包括在内,如两个相约爬山的朋友。,而且还通过设置所受损害与预防成本相比较条款规定作为义务的产生。这使得作为义务的产生基础得以极大扩展。毫无疑问,如此规定,存在激烈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所谓“旁观者的救助义务上”,即即便威胁受害人的损害与行为人无任何关系,行为人也会基于损害的严重性及避免损害的成本不成比例这一原因而存在救助义务。上文中的盲人案例,即其一例。显然,这一规定,对于以个人主义为立法基础及以不作为不产生侵权为基本原则的英美法系国家而言,是无法获得赞同的。
依据我国现有法律,旁观者对于他人不存在法律上的救助义务。而对于不予施救者的谴责,也仅限于道德层面。但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上,主张旁观者应予以救助和反对旁观者存在救助义务的观点均有之。赞同者认为,从比例原则出发,如果一个陌生人的微小努力可以避免受害人遭受极大的损害后果,则即使法律令其在此种情况下承担积极的作为义务,对其行为自由也并不构成过度的限制。②朱岩:《侵权责任法通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358页。反对者认为,如果行为人未因先行行为而使得危险升高,就自然不存在救助义务。③参见周友军:《交往安全义务理论研究》,第187页。笔者认为,关于旁观者是否存在救助义务的探讨,不仅涉及立法上的价值判断,也与民众的意识相关,同时也与一国公力救助状态相关。对此,需要学界做出更为细致的讨论。
除去旁观者的救助义务,即所谓纯粹不作为侵权之外,更多的关于作为义务的探讨是行为人与致害原因或受害人之间存在一定关系的情形。对此,可结合比较法上的情形进行总结。在英国法上,作为义务属于过失侵权中注意义务的范畴。法官在裁量是否存在作为义务时的依据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是否具有足够的接近性;其二是理性人标准,即行为人可以预见损害的发生。其中,接近性因素具有关键性作用,但该要素本身在英国法上也并非十分具体明确,同样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据具体情况进行确认。一般而言,在行为人处于保护他人的地位或对某人或某物处于管理地位的时候,即会认定具有足够的接近性,从而产生作为义务。如保护义务、监管义务。因此,英国法上的作为义务产生于行为人创造了危险源(即便无过错),行为人负责原告的福利及行为人处于负担责任的地位(如父母、雇主、土地的所有人或占有人)。④Mark Lunney,KenOliphant,Tort law text and material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446.在德国法上,《德国民法典》颁行不久即发现了在关于作为义务的规定上存在问题。因为,第823条第一款的规定主要适用于因作为致绝对权损害的情形。尽管法院在枯树案的判决中认为,对绝对权的侵害也可因不作为所致,但却不能因此而认为只要造成他人损害,行为人即应承担责任。为此,当时的帝国法院发展了交往安全义务以确定行为人的不作为因违反了作为义务而具有违法性。交往安全义务则基本以作为义务的形式呈现,发展至今已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了。产生作为义务的基础通常为,行为人拥有或占有某块土地、某项动产,或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具有某种关系。⑤Cees van Dam,European Tort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210.在法国法上,通过扩张解释《法国民法典》第1382、1383条规定,将不作为与作为同样适用于因过错致人损害的案件中。因此,依据该规定,法官在认定行为人积极作为义务上,并未存在如德国法上的障碍。在是否具有作为义务的判断上,法国法采良家父标准。①Cees van Dam,European Tort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210.在南非法上,司法实践中一度认为作为义务的产生必须基于行为人的先行行为。但其后此种做法被摒弃,转而采取动态的方法以确定行为人作为义务的有无。据此方法,首先在规范的层面尽量提取出可确定行为人作为义务存在的因素,之后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形,综合考量。这些因素包括:先行行为、为第三人安全的合同、制造第三方利益将获得保护的印象,等等。同时,善良风俗在作为义务的确定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②具体论述,参见:Neethling/Potgieter/Visser,Law of Dilikct,5th edition Duban,2006,pp.51-68.通过比较法上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义务的存在,通常决定于危险、特殊关系、信赖、职业等因素。但判定何时存在作为义务,应对行为自由做出多大程度上的限制是合理的,从而实现个人行为自由与社会安全之间的有效平衡,仍值探讨。同时,我国法上关于作为义务的解释与适用中也存在若干问题需要厘清。如可否基于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认定作为义务的存在;可否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或公序良俗原则等确定作为义务的存在;安全保障义务具有多大的适用范围,等等。
此处,可对上文Cees van Dam的诘问进行简短回答。尽管作为侵权与不作为侵权责任的成立均是以注意义务的违反为前提,但却是因为注意义务范围及程度的不同而使得二者的区分存在必要。③由于Cees van Dam教授任教于英国,其很可能是针对英国法上的不作为不承担责任的原则而提出这一质疑。因为,根据该原则,法院在判案中往往会首先注重致害行为的形态,于是催生了未踩刹车而发生事故是作为还是不作为的争论。但责任承担的重点并不在于行为的形态,而在于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因此,如果从英国法的背景出发而提出这一问题,是具有合理性的。对英国法上不作为认定的批评,参见:JeroenKortmann,Altruism in Private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6-7.
三、区分意义之三:责任承担的区别
在不作为侵权中,如果行为人的不作为是致害的唯一原因则由其承担责任,自无问题。如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一款的规定。但如果受害人的损害是因行为人的不作为与第三人的作为所致,此时责任应如何承担便存有争议。如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二款的规定:“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但从比较法上看,此种情形下,依据德国法、英国法、匈牙利法及奥地利法均会令安全保障义务人与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如何确立作为与不作为共同致害时的责任承担规则,也是二者区分的意义之一。
我国关于作为与不作为共同致害时责任承担规则的探讨,起始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前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六条确立了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并规定了第三人致害情形下的补充责任规则。而争议的焦点也主要集中于补充责任规则确立的合理性基础上。赞同的观点认为,之所以令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主要基于两点:第一,从原因的角度说,受害人损害的发生,究其实质是因第三人的行为所致,而安全保障义务人仅是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其不作为仅是加大了受害人损害发生的几率,而并未如第三人一般实施积极的作为去损害受害人的利益;第二,从结果的角度看,如果令安全保障义务人与行为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则对安全保障义务人而言过于苛刻,如果令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违约责任,则对受害人的保护又过于薄弱。因此,采取补充责任的做法可实现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④关于赞同观点的具体论述,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6-278页;陈现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若干理论与实务问题解析》,《法律适用》2004年第2期。针对该规定,张民安教授提出了四点质疑:第一,补充责任的适用将损害分别由安全保障义务人与第三人承担,违反全部赔偿原则;第二,令存在过错的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部分责任或不承担责任,违背过错侵权责任的基本理论;第三,安全保障义务人仅承担部分责任,与两大法系国家相关制度中所确立的全部损害赔偿责任相违背;第四,安全保障义务人的经济实力及消化责任的能力强于受害人,令其承担补充责任,有违公平原则。①具体论述,参见张民安主编:《侵权法报告》,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第114-116页。
从以上双方的争议点上看,问题主要集中在补充责任独有的特征上,即顺序上的“补充”和份额上的“补充”。是什么决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人在赔偿上处于第二顺位,并且在自己“能够防止或制止损害的范围内”就第三人未承担的份额承担赔偿责任?
对赞同观点的解读,需考虑到当时确立此规则的社会情境。根据当时曾发生的案件,第三人的过错主要表现为故意,而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过错则表现为过失。此种情形下,二者的可责难性存在不同。从致害原因上看,第三人是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而安全保障义务人仅是未阻断该原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该第三人的行为,则损害根本不会发生。同时,令安全保护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可有效平衡其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因此,基于致害人不同的主观状态、致害原因的不同地位及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确定补充责任有其合理性。但是,反对观点指出的,安全保障义务人在第三人对受害人给予全部赔偿的情形下就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有违过错责任原则的观点,也同样具有说服力。行为人须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这是过错责任原则的应有之义。也是基于此,有观点认为,安全保障义务人在承担补充责任后,不能向第三人追偿,因为其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是基于自身的过错行为。②具体论述,参见郭明瑞:《补充责任、相应的补充责任与责任人的追偿权》,《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从立法论上看,笔者认为,可令安全保障义务人与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同时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人可向第三人进行全额追偿。如此规定,一方面避免了批评者所指出的违反过错责任原则的诟病,另一方面也平衡了安全保障义务人与第三人及受害人的利益,同时,将此情况确定为共同侵权也可将《侵权责任法》第37条与第8条规定衔接。
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看,不作为与作为共同致害时的责任承担,并非仅存在于第37条。《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了网络用户的作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共同致害时的责任规则,同时,第40条也规定了教育机构的补充责任规则。那么,从解释论的视角看,以上同为作为与不作为共同致害,为何有的适用连带责任,而有的适用补充责任,其内在机理为何?如何与第8条进行衔接?需要做出解释。由于上文已对安全保障义务中的补充责任规则进行了阐述,且第40条的规定与第37条之规定同其道理,此处仅就第36条第二款及第三款的规定进行阐述。
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分为两种。其一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被侵权人通知后,未采取必要措施,应与网络用户就损害的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其二为,网络服务者知道网络用户侵权,但未采取必要措施,应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两种情形中,网络用户均以作为方式侵权,且主观上通常为故意③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解释与立法背景》,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第150页。在该书中所列举的网络用户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情形中,均为行为人故意。。网络服务者于第一种情形下为故意,第二种情形下可能是故意也可能为过失。未将第二种情形直接界定为故意,是因为条文中使用的是“知道”,“知道”包括“明知”和“应知”两种。前者指故意,后者指过失。但此处的过失应解释为重大过失,否则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过于严苛。如此理解的理由也在于,《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二稿中,此处所使用的是“明知”而非现有的“知道”,目的即在限制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过重的责任。因此,即便现行法规定为“知道”包括“应知”的情形,也应将“应知”理解为无重大过失情形下的“应知”。如此,可将此处责任承担的模式总结为:作为(故意)+不作为(故意或重大过失)=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8条规定,“两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承担连带责任。”而根据参与立法的人员的相关解释,此处的共同包括共同故意、共同过失和故意与过失的结合。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页。当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者存在主观意思联络时,则二者构成共同侵权而直接适用第8条的规定即可。但在第36条规定的情形,二者并非存在共同故意,而是分别存在故意或网络用户存在故意而网络服务提供者为重大过失。从解释论上看,对二者承担连带责任,可有两种理解方法:
第一种方法,解释为共同侵权。共同侵权的第三种情形为故意行为与过失行为的结合。网络用户的故意行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重大过失行为可构成共同侵权。举轻以明重,尽管网络用户的故意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故意间,不存在主观的意思联络,但故意与过失的结合都可以构成共同侵权,两个故意的结合也同样可构成共同侵权。构成共同侵权,自应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种方法,解释为特殊规定。《侵权责任法》采“总则、分则”结构。前3章为总则,其后规定属分则。②梁慧星:《中国民事立法评说:民法典、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344页。规定在第四章的第36条,属于分则规定。分则规定或为总则规定的具体细化,或为总则规定的例外。第一种共同侵权的解释属于前者,而特殊规定的解释属于后者。既然采特殊规定的解释方法,则可认为本章规定基于主体的特殊性而存在特殊的规则。同时,共同侵权也并不是令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唯一原因,而只是确定承担连带责任诸多原因中的一种。我国侵权法上的规定也体现了这一思想,除去共同侵权之外,第51条、第74条也规定了连带责任。因此,即便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但二者主观上均为故意。基于此种主观上较深的可责难性,且为充分实现侵权法的预防与制裁功能,可令二者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民法有谓“重大过失等同于故意”,则可令存在重大过失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存在故意的网络用户,基于上述理由,同样承担连带责任。
以上论述似乎完成了对本条规定的探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尽管网络用户于侵权时,其主观上通常为故意,但仍不能排除其存在过失的情形。此处涉及对第36条中所规定“利用”的理解,即“利用”应理解为恶意使用还是通常所言的使用。如为前者,网络用户于主观上必然属故意。如为后者,网络用户可能为故意也可能为过失。笔者认为,应采后者为妥。无论故意或过失,网络用户均应就其侵权行为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此处关于“利用”的理解,关系到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要在网络用户过失的情形下,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有两点,其一为其主观状态,即故意或重大过失;其二为对受害人的充分救济。在网络用户为过失的情况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观状态的考量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同时,实现对受害人充分救济的目的也并未因网络用户的过失而发生变化。因此,将第36条中的“利用”理解为“使用”更为合适,即网络用户在侵权时主观上可能为故意也可能为过失。
四、结语
综上,笔者认为,作为侵权与不作为侵权的区分在当下仍具意义。当然,尽管作为侵权与不作为侵权存在如上的区别,但我们不可对之过分夸大,从而抹杀二者的共性。事实上,从罗马法上《阿奎利亚法》否定不作为构成侵权,到执法官通过扩张适用《阿奎利亚法》而肯定不作为侵权,是因为人们发现了不作为侵权与作为侵权之间的共性。正如西塞罗所言,“过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做了某事,一类是允许某事发生。”① Cicero,Deofficiis I,7.转引自A.Tunc(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VolXI Torts(1983),p36.
(特别感谢曹险峰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出的诸多宝贵的批评与建议)
[责任编辑:赵守江]
The Necessity of Distinguishing Liability for Omission and Act
ZHANG Yu-dong
(School of law,Yantai University,Yantai 264005,China)
There is still a need to distinguish liability for mission and liability for act.The need to distinguish the tow especially reflects on the different causation and burden on duty of care and the specific rules when the damage is caused by act and omission together.
liability for omission;liability for act;distinguish;necessity
D 913
A
1002-3194(2014)04-0043-08
2013-12-17
张玉东(1981- ),男,辽宁海城人,法学博士,烟台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
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资助项目“不作为侵权制度的基础与司法适用”(J12WB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