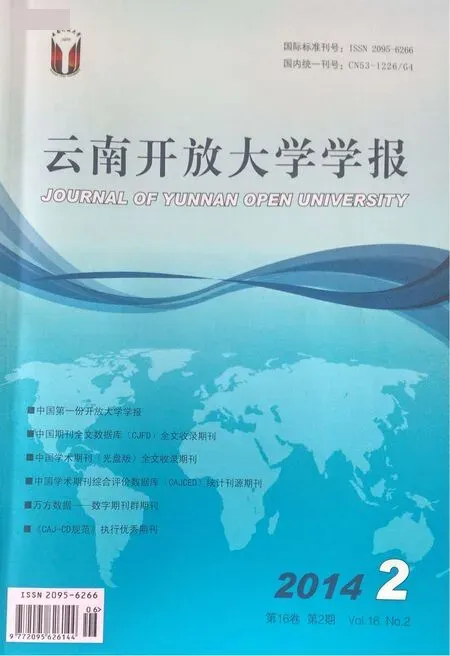幽远长路踏歌而行
——试论冯至《十四行集》的寻路意识
王亚瑾
(云南开放大学文化旅游学院,云南昆明650223)
幽远长路踏歌而行
——试论冯至《十四行集》的寻路意识
王亚瑾
(云南开放大学文化旅游学院,云南昆明650223)
《十四行集》是诗人冯至的巅峰之作,由于诗人对诗艺独特的感受与追求,使诗歌获得了深邃的内涵和幽远的韵味。对人生的深入思考,对生命之路的追寻构成了贯穿诗歌始终的精神脉络,无论是生与死的轮回,还是荣与枯的往复,无论是光明与黑夜的变换,还是流水与桥梁的纵横,无论是梦境与现实的交错,还是风物与山水的互通,它们都是诗人在人生的幽远长路上寻寻觅觅的足迹。
寻路;交流;生死;万物合一
冯至,曾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其巅峰之作——《十四行集》,完成于1941年。这一年诗人在西南联大任教,生活在昆明附近的山中,昆明城和煦的阳光、湛蓝的天空,住所近旁的淙淙山泉、阵阵松涛,都给久未提笔的诗人带来了如潮的灵感,使他写出了个人最具精神内涵和艺术美感的27首诗作。
很多学者把《十四行集》称作“沉思的诗”,认为这部诗集实现了作者诗与生命的“真淳的觉醒”,使诗人从早期忧伤多情的浪漫主义“吹萧人”成长为一个深沉淳厚的沉思者。但我更愿意把这部诗集称为“寻路的诗”,因为在这27首诗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一个寻路者上下求索的背影。诗人从一个普通寻路者的视角出发,与自然对话,与生死交流,驰骋于历史、现实和宇宙之间不断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正如冯至的学生徐开愚所说,自己的老师是一位思索“人在宇宙间位置”的诗人。《十四行集》或许没有宏大的主题,没有蓬勃的激情,但它有敏锐的感觉和洞察力,有从平常事物中挖掘出的独特诗意,有追寻生命意义的哲学意蕴。
一、寻交流沟通之途
人的孤立的生存状态、沟通的渴望与障碍几乎可以说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精神困境。诗人不是圣人,他们只是比一般人更多地关注和思考着我们身边的世界。在《十四行集》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诗人对这个问题所表现出的坦率的忧虑和真诚的思考。
在第三首诗中,诗人描写了田野里的有加利树(即桉树),高耸入云的树木因为自己与众不同的傲立足以升华一个城市中凡俗的喧哗,但这高贵的使命却注定了它必须在晴空中撑起一片孤独,它的高耸成为了寻路者的航标,它的孤独也并不拒绝纵横的阡陌带来的讯息。
第五首诗写了水城威尼斯,这座城市由119座孤立的岛屿组成,只有当所有的岛屿连在一起时,威尼斯才具有了生命,因此流水和桥是这些寂寞的岛屿之间的纽带,是它们彼此间的通路,正如素不相识的你我,可能因为彼此的相视一笑,而找到相互眺望的“楼窗”。
第六首诗描写了原野的哭声。面对农妇和村童的哭泣,诗人说“像整个的生命都嵌在/一个框子里,在框子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我觉得他们好象从古来/就一任眼泪不住地流/为了一个绝望的宇宙。”当人们无助的时候,悲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一种追寻,但是这样的追寻如果将整个生命都“嵌在一个框子里”,那么隔绝将变成一种必然的命运,导致孤独的悲苦的未来,最终通向“一个绝望的宇宙”。
第七首诗描写了人们躲避空袭警报的场景:“和暖的阳光内/我们来到郊外,/像不同的河水/融成一片大海。”在战争时期,敌机、炮火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每一个人的安危,每个人都在经历着相同的苦难。在这样的生死关头,诗人没有渲染战争的硝烟弥漫,没有叙述轰炸的血肉横飞,更没有描写人们躲避警报的仓皇与狼狈,相反,诗人给我们的第一个意境是在“和暖的阳光内”,那些四散奔逃的人们在诗人眼中也变成了汇聚成海的万千河流,危险来临的时刻,相同的境遇似乎消除了人们之间的距离,跨越了个体之间的寂寞屏障,达成了一种紧密地交流与汇聚。当然,诗人也敏锐而清醒地发现,这种毫无挂碍的沟通,似乎也只能在一个短暂而特殊的时光中存在,于是诗人不无忧虑地提醒我们“要爱惜这个警醒,/要爱惜这个运命,/不要到危险过去//那些分歧的街衢/又把我们吸回,/海水分成河水。”战争这个原本沉重的话题,却因为诗人独特的视角成为人与人获得沟通的良机,成为人们应当“爱惜”的“运命”,由此可见,诗人在关注个体之间的交流这一问题上确实有着与众不同的追寻。
从第十首诗到第十四首诗,诗人写到了蔡元培、鲁迅、杜甫、歌德、梵高这五位给予过诗人巨大影响和启发的人物。他们都曾在自己的领域里品尝精神的孤独,都曾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关切作过不懈的努力,都曾为理想的失落而遗憾惆怅。显然,诗人是把他们视为自己征程中的灯塔,希望能用他们的坚持照亮自己的执著。
在第十八、二十、二十五首诗中,诗人一再提到了黑夜和梦境,并将它们作为了这几首诗中的核心意象。黑夜是今天和明天的交集,是过去与未来的衔接,梦境是清醒和沉睡的界限,是现实与虚幻的临界。黑夜或许会让人忧虑和恐惧,但有时也会带给人们彼此坦陈内心的勇气。在梦里,会有人们面对陌生的忐忑与踟蹰,也会有重回往日的狂喜与感激。于是,在这里,黑夜和梦境成为了诗人笔下路的变体,如何面对黑夜和梦,也正映照着人们将如何迎向前路。
冯至曾说:“人到世上来,是艰难又孤单。”孤独造就了人的独立和沉静,但若不打破自我的狭小空间,又无法寻求更广阔的天地和自由。人与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关联,在保持精神独立的同时珍惜每一次相逢的刹那,让相聚和疏离都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自然的一部分,就好像“某某山坡的一棵松树”,又好像“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
二、寻生死交汇之途
人们既然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自然也就不能不思考个体生命的消亡,于是,生与死就成为了诗人笔下的一个终极话题。
在第一首诗里,诗人就带着深深的感激将思考生死这个严肃的使命放到了我们面前:“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紧接着在第二首诗中,诗人又坦然地把自己安排给了未来的死亡,希望自己最终能像一段歌曲,“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
小小昆虫的死亡带给诗人极大的震撼,它们为自己的死选择了一个盛大而庄严的方式,于是反观自身,第一次的拥抱将“过往的悲欢”都凝结于眼前,此在的实存生命得到了肯定,诗人忽然发现了生存的使命是为了“领受”生命中“意想不到的奇迹”。歌声的脱落,就像死亡最终使灵魂摆脱了沉重的肉身和尘世的羁绊,像默默青山一样获得了永久的持存。山是沟通天与地的使者,人们如果真的化作了“一脉的青山默默”,也便获得了倾听生命真谛的可能。
后来诗人在第十七首诗中谈到那一条条原野的小路时联想到了自己的内心:“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也有几条宛转的小路,/但曾经在路上走过的/行人多半已不知去处://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还有些年纪青青的男女,/还有死去的朋友,他们//给我们踏出来这些道路;/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无论是现实中的原野小路,还是意念中的心灵小路,都连接起了过去与未来,连接起了儿童与老人,连接起了风华正茂的青年与生死异路的朋友。第二十一首诗里,诗人在暴风雨中发现了自己与身边万物的遥远距离,从而敏锐的感到了“生命的暂住”。第二十六首诗里,诗人在对熟悉与陌生的辨析中,忽然对自我的存在发出了疑问。
所有的这些都体现出了诗人对生与死的思考,生是不由人选择的降临,死是不让人掌控的离去,正如诗人在第九首诗中写到的古代英雄:“在另一个世界里永向苍穹,/归终成为一只断线的纸鸢。”然而,诗人对于生命的思考并不止于此,他找到了生与死的交汇就是个体生命存在的此刻,每一个现在都像一条道路,连通着清晰的过去和隐约的将来,连通着没有预告的生和不可预知的死。对现存生命的珍视更使诗人看到了死亡的意义,甚至它未必就是真实生命的终结,可以是希望的重生、理想的新貌、道路的选择以及一切从头开始的尝试。
三、寻万物合一之途
人从何处来,欲往何处去?当名利生死的藩篱已不能束缚个体生命对自由的追求,庄周与蝶便不分彼此,人与自然更可合二为一。万物之间本有灵犀互动,大道就在芸芸众生的细微之中,寻常之眼跳不出习俗的遮蔽,也就找不到去往无限的通道。但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几乎是所有中国文人的梦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诗人冯至也不例外。在思考了生与死的交汇之途后,诗人将目光转向了另一个更为旷远的世界,以此寻找对生命的至高敬意和真正意义上的永恒。
第四首诗里,诗人在谦逊的鼠曲草身上看到了另一种质朴而阔大的生命形态。第八首诗里,诗人又将目光投向了辽远的宇宙,去倾听星辰的谈话,赞美将人世与星际交汇,哪怕“化作远水荒山的陨石一片”也百折不回的探索。第十五首诗里,驮马的蹄声使诗人想起自己走过的路途:“我们走过无数的山水,/随时占有,随时又放弃”。这种短暂的靠近又分离,使诗人不禁叩问自己:“什么是我们的实在?/从远方把什么带来?/从面前又把什么带走?”。第十六首诗里,诗人“站立在高高的山巅”,不断将自己化身为景物树木、城市山川、风云浓雾,人与自然都在寻找着生命信息的沟通与关联,追求着万物合一的境界。
经过婉转的歌唱,所有的声音都落在第二十七首的韵律之中:“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形;/看,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它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让远方的光、远方的黑夜/和些远方的草木的荣谢,/还有个奔向无穷的心意,//都保留一些在这面旗上。/我们空空听过一夜风声,/空看了一天的草黄叶红,//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水性至柔,可以化身万物。椭圆之形,虽柔滑但仍有方向的坚持。光与黑夜是昼夜往复的路途,草木荣枯是岁月轮回的形迹,疾风劲吹传来的仍然是时间对生命的意义。风无形,却无处不在,它吹过万物,又不着形迹地化身万物。这正如在俗世中生长的生命,平常而渺小,但只要跳出喧嚣和浮华,以谦虚敬畏的态度走入自然,观看万物,就可以感悟到那些一直被掩盖着的更真实更本质的生命存在,从而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最终走向生命的永恒。
至此,《十四行集》中诗人沿着诗歌寻路,从个体沟通寻到生死交汇再到万物合一,这段长旅在风中到了尾声。在这些诗对平凡进行书写的瞬间,细心的读者看到的是诗人的敏锐与洞见,无论是生与死的轮回,还是荣与枯的往复,无论是光明与黑夜的变换,还是流水与桥梁的纵横,无论是梦境与现实的交错,还是风物与山水的互通,它们都是诗人在人生的幽远长路上寻寻觅觅的足迹。这些足迹不再有年少的躁动与浪漫,但却在凝重的思考中获得了生命的启示。人生丰富而又充满矛盾,正如诗人一面寻求关联,一面又坚守着孤独;一面渴望着死亡的超越,一面又肯定着生命的暂住。但这种矛盾并不影响诗作独特的韵味,反而使诗集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和情感张力。
细细捧读《十四行集》,总能听到一个坚韧的寻路者慧心流淌的歌声,总能看到一个执着的寻路者踽踽独行的身影,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只为寻求一条通向心灵的坦途。或许这段寻路并没有留给我们一个恒定不变的结局,但生命的本质意义莫过于在路上,有谁例外?
[1]崔允瑄.论冯至的诗[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2).
[2]刘纪新.论冯至《十四行集》的超越精神[J].兰州学刊,2012,(2).
[3]吴武洲.存在与超越[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6).
[4]王泽龙.论冯至的《十四行集》[J].贵州社会科学,1995,(6).
[5]唐祥勇.历险与体验[J].理论与创作,2007,(1).
[6]冯至.冯至全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A Long Road Trip by Tage:On Way-finding Awareness of Sonnets by Feng Zhi
WANG Ya-jin
(School of Culture and Tourism,Yunnan Open University,Kunming 650223,Yunnan)
Sonnets by Feng Zhi is the masterpieces of the poet.The unique experience and pursuit of the poet make Sonnets more profound meaning and long lasting charm.Deep reflections on life and pursuit for the way of life always constitute the spiritual context of the poetry.Focus on the way-finding awareness of Sonnets,the unique and rich spiritual connotation is analyzed.
way-finding,exchange,life and death,all-in-one
I207.22
A
2095-6266(2014)02-031-04
2014-5-10
王亚瑾(1973-),女,云南石林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和应用文写作研究。
——冯至《蛇》的一种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