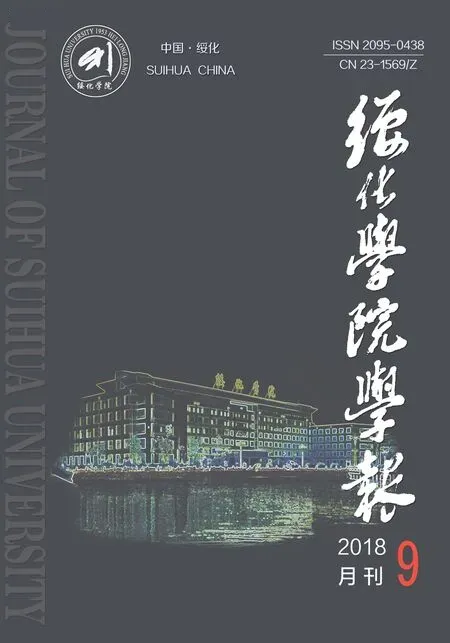从“乡思”的“乡”说开去
——冯至《蛇》的一种读法
郭大章
(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北碚 400715)
对冯至早期代表作《蛇》的解读和评价,一直以来都是多种多样的,从同时代到今天,从官方到民间,从诗歌研究者到普通读者,各有各的看法,得不出一个大致统一的结论。何其芳认为,《蛇》的创作不落俗套和富有色彩,诗的成功源于冯至青年时期对“寂寞”的深切感受,并对诗中奇异的比喻“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冰冷地没有语言”大加赞赏;[1]袁可嘉认为,诗作把蛇的“乡思”化为姑娘“头上的,浓郁的乌丝”,构思精巧独特,着实叹服;[2]孙玉石认为,该诗意象大胆,有现代的超前意识,但诗文后则又具有明显的理智特征;[3]陆耀东则认为,此诗新颖别致之至,兼具中外诗歌之长,既有古代诗歌的那种优美意境,又融化了象征派诗歌的某些东西;[4]等等。诗歌研究专家王珂说,冯至《蛇》的细读史堪称典型个案,文本和解读甚至解读者都有“面具”特征,解读生态奇特,得出结论多样,有说是写“爱”的,也有说是写“色”的,有的说是“思乡”诗,也有的说是“哲理”诗,据此,他还专门写过一篇论文,详细梳理了冯至《蛇》的细读史及其带来的对新诗细读式批评的反思。[5]由此可见,冯至的《蛇》确实具备丰富的内涵,经得起反复推敲,当然,这也是其成为优秀文学作品的必备条件之一。
本文无意于对此作出一种评判,只是在反复研读冯至《蛇》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值得我们注意,但却至今未引起我们重视,甚至未被提及的地方——
冯至的《蛇》有多种版本,有朱自清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版,有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的《中国现代经典诗库》版,还有《冯至全集》版以及高中语文教材版等等,前两个版本采用的是冯至的原作,只是在标点上作了细微的调整,而后两个版本则改动幅度较大,用的是冯至修改后的诗,在首节和末节里,从字词到标点都有了较大的改动,有些改动甚至影响到了诗意:
诗的首节,去掉了“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的“长”字,去掉了“姑娘,你万一梦到它时”的“姑娘”二字,“冰冷地”改成了“静静地”,诗的次节,去掉了破折号前面的逗号,末句的逗号改成了顿号,而诗的末节,则把“潜潜”改成了“轻轻”,“一只”改成了“一朵”,感叹号改成了句号,等等。
但是,在这些版本的改动中,不管怎么改,诗的次节有个地方却一点未动,那就是次节的前两句:“它是我忠诚的侣伴,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尤其那个“乡思”的“乡”字,显得很是扎眼。
使人诧异的是:从以往对此诗的种种解读来看,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也不管是从“爱”的角度还是“色”的角度,此句中“乡思”的“乡”,都更应该是“相思”的“相”,而非“故乡”的“乡”。此是刊载错误,还是原本如此?是冯至的一时疏忽所致,还是他的故意而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究的话题。
可以确定的是,把诗中“乡思”的“乡”写成“故乡”的“乡”,肯定不是冯至的疏忽所致,那么,必定是冯至的刻意而为了。照此来说,《蛇》理应具有“思乡”的成分在里面,可以看成是一首“思乡诗”,但冯至所思之“乡”,肯定不单单是一个“故乡”那么简单,其中必定蕴含着复杂而丰富的内涵,“乡思”的“乡”也必然超越了“故乡”的“乡”,具有多重隐喻及象征意。
这里,还有必要对冯至的早年经历及其精神特质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冯至于1905年出生于河北省涿州市一个衰落的盐商家庭,父亲冯文澍淡泊宽容有思想有主见,却并非雄心勃勃振兴家业的男子,家道中落后,不时在外面的学校机关作点文牍之类的工作来养家糊口,而且还经常失业,但他对冯至的教育可谓费尽了心思,经常在家中为冯至讲解《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中的篇章。冯至在学校里仍然熟读古文,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作品,念得很熟,不少甚至可以背诵,这对冯至以后的思想有一定潜移默化的影响。1913年,冯至9岁,年仅35岁的母亲病故,从此家庭彻底败落,冯至也常受奚落和白眼,这对童年冯至的打击是巨大的,让冯至过早地饱尝了世态炎凉,形成了冯至阴郁的精神气质,很久都走不出来。冯至在北京大学读书寒假回乡时,仍然走不出这种巨大的阴影,面对着衰颓的遥远的“老屋”,冯至无疑是“寂寞”的,而这种“寂寞”,正如“蛇”一般,紧紧缠绕着冯至,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中年丧妻的冯父选择了续弦,为冯至找了一个继母,但不幸的是,在冯至16岁那年,继母也在北京病逝,这让冯至更加感到无法摆脱的寂寞和痛苦。
由此,冯至的“乡思”,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带有对“故乡”的思念成分在里面的,而冯至的“寂寞”,也远非一种单纯的青年对“爱”的向往和渴望所能概括,“寂寞”里面包含着冯至太多的精神寄托,甚至可以说“寂寞”是冯至的一种精神特质。
冯至的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都是在北京度过的,而那时的北京,远非我们现在想象中那么繁华,反而却是一片荒凉。冯至曾说:北京如今作为国家首都足以夸耀全世的一些名胜,那时好像都还埋没在地下……冬季北风吹得黄沙漫天,夏季淫雨淋得泥泞遍地,荒凉啊,寂寞啊,常常挂在青年们的口边。[6]而且,那时的青年口头上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花,没有光,没有爱”,荒凉和寂寞之类的词语,经常挂在当时青年的嘴边。[7]由此可见,冯至的“寂寞”,绝非大多数论者所论及的“寂寞”,也绝非冯至的“寂寞”,而是那个时代大部分青年的“寂寞”,以及那个时代的“寂寞”。
冯至在北京读书时,在潘云超等老师的影响下,接受了很多新思想,使他认识到了现实的黑暗。1919年,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激起了国内规模巨大的爱国学生运动,冯至作为当时的进步青年,理所当然的参与了其中,他和同学们一起张贴标语,走向大街进行宣传演讲,参加罢课游行,在时代的潮流中激荡起了要求进步和热爱祖国的内心波澜。同时,冯至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文化知识,在中西文学中充实自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并开始了新诗的创作。冯至的《蛇》写于1926年,当时未发表,后收录进冯至于1927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里。这里有一个时间节点:1926年。历史上的1926年发生了很多事,现代中国社会极度动荡不安:北洋政府的傀儡总理段祺瑞被迫下野,国民革命军正挥师北伐,势如破竹;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早已退去,作为主将的鲁迅由“呐喊”跌进了“彷徨”的深渊,毅然从北京南下,踏上颠沛流离的避乱之途,茅盾也离开广州奔赴武汉,开始酝酿反映大革命前后社会动荡的《蚀》三部曲……可以说,冯至的《昨日之歌》正是新文化落潮后的产物,是冯至作为一个经历新文化启蒙而觉醒起来的青年,在向往光明的同时,却遭遇到了残酷现实的沉重打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极度苦闷。
这种苦闷,来自于冯至的爱国思想和精神。自从鲁迅对冯至作出那个著名的论断以来,这份荣光(也可称之为标签)便伴随着他的生命和创作历程,但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冯至的光芒,我们应该认识到,冯至不仅是一个歌者,也是一个天才的沉思者,他是极少数能从深刻的精神层面体会到中国的现代困境的知识分子之一,而且,冯至也是个独特的存在,他作为一个身处现代世界的学者,能对自己的时代做出非同寻常的思考乃至批判。[8]王邵军在评价冯至时也谈到:他是一个真正否定型的精神探索者,他一生都在审省,都在寻求精神的故乡。[9]
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冯至《蛇》中的“乡思”之“乡”了:“乡”既是冯至地理符号学上的故乡,更是冯至精神层面上的“故乡”,冯至正是通过对自己精神层面上“故乡”的“乡思”,来激起心中的那份“家国之梦”。
冯至是爱国的,有一份深沉的民族国家观念,他的很多诗都体现了这一点。在冯至看来,当时的中国就像北方那座“事事都成陈迹”的“灰色的城”,当冯至面对这座城时,他想到的便是“我怎能把它,也撕成千丝万缕?”(《孤云》),而且,冯至更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年轻”“勇敢”的战士,在“风吹着旗子,旗子扫着风”以及“满地是战士的骸骨”的战场上“为了死亡,为了秋天”(《秋战》)而兴奋地歌唱。面对着“春日的和平,是那样的辽远,油油的绿草,尽被战马摧残”而且到处充满着“风雨”和“杀声”(《秋战》)的“一齐地沉沦到底”(《狂风中》)的黑暗现实,冯至发出了强烈的呼喊:我不能容忍了!(《不能容忍了》)面对这么“一个绝望的宇宙”(《原野的哭声》),冯至有了“寂对河山叩国魂”(《宴席上》)的哭声,在这哭声中,寄托着冯至反抗现实的决心以及对光明彼岸的渴望:愿有一位女神,用天河的水,另洗出一种光明!(《狂风中》)
于是,冯至在这黑暗的现实中,构筑了一个“新的故乡”:灿烂的银花,在晴朗的天空飘散,金黄的阳光,把屋顶树枝染遍。驯美的白鸽儿,来自什么地方?它们引我翘望着,一个新的故乡:汪洋的大海,浓绿的森林,故乡的朋友,都在那里歌吟。这里一切安眠,在春暖的被里,我但愿向着,新的故乡飞去!(《新的故乡》)
冯至很推崇杜甫,这在他童年读杜甫的诗歌时便埋下了一颗种子,他被杜甫伟大的爱国精神所感佩,多年后冯至在谈到杜甫时曾说:杜甫的死年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1175年,在这长久的时间内,中国经过许多变化,我们眼前的世界自然不是杜甫所看过的世界了,但是杜甫这个名字对于我们却一天比一天更为亲切起来。我们读这些名诗与名句,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我们所处的时代也许比杜甫的时代更艰难,对待艰难,敷衍蒙混固然没有用,超然与洒脱也是一样没有用,只有执著的精神才能克服它。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10]
很显然,冯至对这些民族国家英雄是赞赏的,更是向往的,他也想成为这一类拯救民族国家的英雄中的一员,用他们身上的那种顽强的精神来拯救我们现在的时代。在这里,杜甫等民族国家英雄正是冯至童年和故乡的隐喻,潜藏着冯至那满腔的家国观念,此时的冯至心中,“故乡”早已成了一种精神隐喻,是悲壮和豪侠之风,是足以改变这个黑暗现实一切的精神象征。
由此,冯至《蛇》中“乡思”的“乡”便凸显出其深刻的精神内涵来:冯至故乡这么一个历史上如此雄浑豪迈的悲壮苍凉之地,同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和民不聊生的残酷黑暗现实,形成了一种强烈且巨大的反差,诗中所幻想的“故乡”和冯至真实而虚幻的故乡,在此有了一种深层的完美契合,他们一起构成了冯至的精神之“乡”,更加凸显出了冯至从地理符号的故乡到精神世界的“故乡”的可贵,以及“乡思”之“乡”的深层次内涵——对黑暗现实不满而发出的悲壮豪迈的强烈爱国呼声以及其浓浓的民族国家观念。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冯至《蛇》中“乡思”的“乡”非“相思”的“相”而是“故乡”的“乡”的一种强有力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