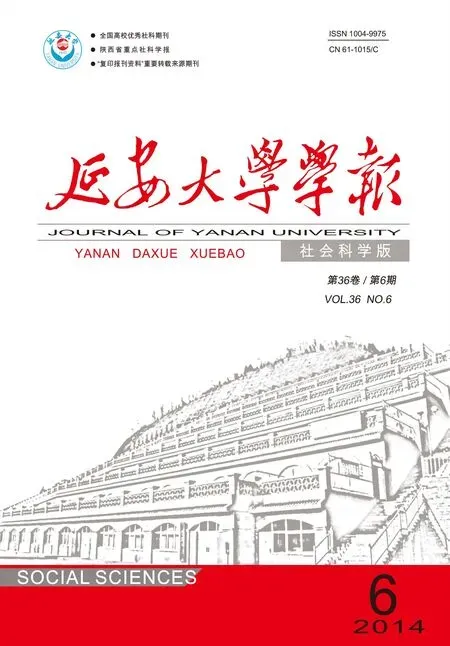从“自我镜像”看《玉娇梨》的双美追求
吴延生
(淮阴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3)
才子佳人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一大类型。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小说古已有之,而才子佳人则必须以才子为男主角,以佳人为女主角,就有了特定的范围。才子佳人型的小说,成熟于唐传奇,宋元说话中的“烟粉”类故事推动着才子佳人小说的发展。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集群式出现,蔚为风气,形成一个势力强劲、影响广泛的小说流派,是明末清初小说界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中天花藏主人是才子佳人小说及其流派的奠基人,也是才子佳人小说创作最多且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其创作的《玉娇梨》、《平山冷燕》、《定情人》等都是才子佳人小说中的重要代表作品。明末清初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虽然流传甚广,但始终毁誉参半。《红楼梦》第一回借石头之口指责道:“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这一评论固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弊病,但也遮蔽了其应有之价值。姜有阁先生曾武断地指出:“类似性质的才子佳人小说,尚有《平山冷燕》、《玉娇梨》、《好逑传》,都不是什么成功的作品。”[1]这有失公允。“才子佳人小说的发展是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的。它是在封建社会的石板缝里钻出来的一枝小花,虽然苍白无力,枝叶柔弱,却反映了历史真实的一个侧面。”[2]239“它在反映和表现明末清初历史状况以及社会意识、士人心态、婚恋文化变迁进步等方面的认识价值,也不容忽视。西方学者曾经以它所展示的独特文化景观,来作为观察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窗口,也是其独特存在价值的证明。”[3]这些论断从某一层面肯定了此类小说具有的独特的价值。毋庸讳言,“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本来是有许多弱点的。主要就是在婚姻制度上反封建的不彻底,或者说是思想上的妥协性。”[2]236但不是一无是处,它在小说史上多少起过一点积极作用,在思想上、艺术上对后来的小说产生过影响,为《红楼梦》这样的爱情婚姻小说开辟了道路。倘如姜先生所言,那才子佳人小说问世以后又为何频频走进论者的视阈并引起持久关注?然而长久以来,学界对于才子佳人小说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类型的批评、叙述的探讨、作者的考辨等,而缺乏对文本的深入解读,造成对小说群体关照有余,个体挖掘不足的失衡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因此,本文选取清顺治初年的长篇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作为分析对象,从中解读作者的深沉的焦虑与凝重的思考。
《玉娇梨》的故事内容并不复杂,写正统年间太常正卿白玄有女名红玉,貌美擅诗。佞臣御史杨廷昭欲娶为媳,而其子杨芳不学无术,遂遭拒绝。于是杨御史阴谋陷害白玄,荐其出使番邦议和,并欲强娶红玉。白玄毅然出使,不接受要挟,将红玉托给妻弟吴翰林。吴翰林将红玉改名为吴娇,养为亲生,告假避祸还金陵。偶见才子苏友白题诗,慕其才,欲招为婿。不想苏友白误将丑女吴颜认做吴娇,不肯屈就。白玄出使归来,亦告病避还金陵,以考诗方法选婿。苏友白赋《新柳诗》应考,却被居心叵测的张轨如掉包,幸被红玉查明真相,又请苏友白题写《送鸿》、《迎燕》二诗,约为婚姻,然后让其进京求吴翰林保媒。另一书生苏友德冒苏友白之名,求得吴翰林作媒信,到白府骗婚,又被红玉识破。苏友白应试进京遭劫,另一才女卢梦梨,慕苏友白之才情,女扮男装,与之相会,并以嫁妹名义与之暗订婚约,且赠金助其进京应试。苏友白中了进士,只选了杭州推官,访梦梨、红玉皆未见,却被抚台杨廷昭逼婚,遂挂冠而去。后改称柳生,与改名皇甫员外的白玄相遇。白玄爱才,欲招为红玉、梦梨之婿。二女不知柳生即是苏友白,守情不嫁。后来,苏友白改授翰林,终与二佳人成就“双美奇缘”。一言以蔽之为才子外出游寻佳人、佳人闺中挑选才子,最终皆大欢喜。然而看似平常的择偶故事中却处处透着人生的焦虑:
苏友白常自叹道:“人生有五伦。我不幸父母早亡,又无兄弟,五伦中先失了两伦;君臣、朋友间遇合有时;若不娶一个绝色佳人为妇,则是我苏友白为人在世一场,空读了许多诗书,就做一个才子,也是枉然。叫我一腔情思,向何处去发泄?便死也不甘心!”[4]51
白公闻言,连忙拭泪改容说道:“吾兄之言,开我茅塞!若肯为小女择一佳婿,则小弟虽死异域,亦含笑矣。”[4]33
这种不得佳人、才子虽死犹憾的执着精神令人惊叹之余也丛生疑窦。这仅仅是爱情的力量、婚姻的向往么?事实上,翻阅全书,男欢女爱的文字少之又少,扑面而来的是满纸才华,呈现出一种超越世俗情爱的高蹈姿态。无论是苏友白还是红玉、梦梨,往往睹人见诗便春心荡漾,心醉魂销。可见,爱情的背后有才子、佳人更为看重的东西。是才华么?非也。用小说中的话来说是“知己”,用现代理论来说是“镜像”。
更有子云千载后,生生死死谢知音。[4]1
冷暖酸甜一片心,各种别自有知音。[4]93
衔杯细究花枝节,又添得诗人一绝,真不负红梨知己也。[4]94
在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动荡,文字狱大兴,价值系统崩溃,挤压了文人的生存空间,使得功名、不朽等儒家所标榜的传统入世生活方式变得极其困难。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才子佳人小说反映了现实的困境。“所谓佳人才子小说中所表现的思想,大都是知识阶级的正统思想。”[5]正是这样的思想传统和文化语境,决定了士人的现实选择。既然不能治国平天下,那么就回到自身,以图修身齐家。而修身的关键便在于“知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此,能否找寻到自我之镜像,并从中发现自我、肯定自我,成为乱世才子、佳人最大的人生焦虑,也是整个社会的最大焦虑。因此,小说开篇引诗便提出了“知音”,并于文中散落照应,可见作者自有深意。
自古以来,我国便有以爱情、婚姻之成功与否来象征“遇”与“不遇”、“达”与“不达”的创作手法,如屈原之于香草美人等。小说《玉娇梨》借鉴了这一手法:
苏友白道:“吾兄柔媚如女子,而又具此侠肠,山川秀气,所钟特异。小弟偶尔得交,何幸如之!小弟初时,去心有如野马;今被仁兄一片深情,如飞鸟依人、名花系念,使小弟心醉魂销,恋恋不忍别。小弟从来念头,只知有夫妇,不知有朋友。今复添一段良友相思之苦,教小弟一身一心,如何两受!”[4]148
苏友白面对一个女扮的假才子竟然产生出了“心醉魂销”、“恋恋不忍别”的情愫,与男女恋情绝无二致。而良友相思之苦亦不逊男女相思之苦。这说明才子佳人小说并不只是表面呈现出的男欢女爱,其背后应有更深意蕴。而唯有将此作为找寻到了自我之镜像,肯定了自我之价值后的欢欣鼓舞的自我认同,方才解释通畅。正所谓“自古至今,自是佳人,合配才子。”一个“配”字道出才子佳人的宿命——用尽一生的追寻,只为找到自己的镜像,只为在镜像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不然,“虽玉堂金马,终不快心”、“情愿终身不娶”。既然所追寻的是自我之镜像,而自我之镜像又不唯一,那么也就无所谓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如此,批评才子佳人小说宣扬腐朽封建婚姻制度之人实是没有真正理解匿名作者之良苦用心。
若夫两眼浮六合之间,一心在千秋之上,落笔时惊风雨,开口秀夺山川,每当春花秋月之时,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为何如?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不幸憔悴以死,抱九原埋没之痛,岂不悲哉!予虽非其人,亦尝窃执雕虫之役矣。顾时命不伦,即间掷金声,时裁五色,而过者若罔闻罔见,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讦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有时色香援引,儿女相怜;有时针芥关投,友朋爱敬;有时影动龙蛇,而大臣变色;有时气冲牛斗,而天子改容。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
上段是《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序》中的话,作者可谓道尽心中甘苦:“发泄其黄粱事业”,“皆胸中之欲歌欲哭”。
夫古人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终以立言。儒者著书立说,必上观千古,下观千古,动有关于世道人心,非徒逞才华于淹博已也。余以为文章根性情而出者也。至不获著书立说,论议古今,策画时事,而抒写抑郁之气,成小说家言,则其性情,大抵忧思多而欢乐少,愁苦常而忻愉暂。积其忧思愁苦,以寓言十九而行文之时,又不欲直写怨愤,必借径于风华绮丽之词。
上段是清代许康甫《萤窗异草三编·序》中的话,作者可谓明示写作用心:“积其忧思愁苦”,“而抒写抑郁之气”。
著有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反映妇女生活的专题小说集的《鸳湖烟水散人》,在其十二卷《女才子书·凡例》中认为作家“以雕虫馀技而谱是书,特以寄其牢骚抑郁之慨耳。”佐证可见,“天花藏主人”写作《玉娇梨》并非只是消遣娱乐、取悦俗众,而是在不得已中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和深刻的人生寄托。故而“小说家创作常常有寄托,文人多以发微揭旨为己任。”[6]149这些“都强调了小说创作需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积累,需要有作家对于社会的洞察、思考和感愤。”[6]179
由是,经过文本内之分析,加上作者自诉甘苦,我们断然可以说,《玉娇梨》一书,虽然才子佳人俱备,谈婚论嫁贯串,但却不是“才子佳人小说”。所谓爱情不过是契合叙述的寓言、扩大销路的策略。在轻松的寓言背后,是作者严肃而沉重的思考——追寻自我镜像以期在乱世安生立命。尽管前途光明,但追寻的过程是困难的,正所谓“道阻且长”。推而广之,明末清初的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有相当一部分,如《平山冷燕》等,都和《玉娇梨》一样,是政治寓言,是人生焦虑,而非小儿女的打情骂俏。
如果《玉娇梨》止步于此,那也不能在浩如烟海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算作翘楚。然而《玉娇梨》在书写焦虑的同时更进一步,揭示了自我镜像的深刻内涵——双美理想。
这红玉生得姿色非常,真是眉如春柳,眼湛秋波。更兼性情聪慧,到八九岁,便学得女工针黹渐渐过人……果然是山川秀气所钟,天地阴阳不爽,有百分姿色,自有百分聪明,到得十四五时,便知书能文,竟已成一个女学士。[4]2
苏友白笑道:“兄不要把富贵看得重,佳人转看轻了。古今凡博金紫者,无不是富贵,而绝色佳人能有几个?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友白的佳人!”[4]52
诚然,“才子佳人小说以‘才’、‘色’作为叙事的核心。这里的‘才’,说的是才华,指郎为才子,才华横溢,也指佳人之才;这里的‘色’,指佳人之色,貌美,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也指才子须美如冠玉、润比明珠。在才、色基础上,形成了才子与佳人相互爱悦的情感。”[7]对于女子来说,有山川秀气、天地精华的绝代颜色也只是成为佳人的前提,而能与男子匹敌相配之才华才是关键。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玉娇梨》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将佳人塑造成令才子都甘拜下风的学士,达到才慕色如胶、色眷才似漆的目的,故而有意隐藏其女性的性别身份。在小说中,我们很少看到对佳人肖像的正面细腻描摹,多半是“姿色非常”等抽象叙述,而多有佳人志向之抒发,如卢梦梨女扮男装劝说苏友白考取功名等。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种女性性别身份的缺失不是作者的疏漏,反而是作者有意为之——“女子男写”。不仅如此,还是将女子当作理想男子来写,这与霍小玉等以往敢爱敢恨的民间女子形象大有不同。事实上,小说中佳人们的家长也是从小就把她们当作男孩子来养的,其方式有二:“一是‘佳人’们小时候家里没有男孩子,父母因其生得聪明伶俐,于是把她们当作男孩子聊以自慰。并且教给她们男子应具备的才学;二是家中虽有男孩子,但‘佳人’比他们更聪慧,于是家中便将‘佳人’视同男孩子,并且比男孩子还受到重视。”[8]显然,红玉是前者,梦梨是后者。虽然红玉、梦梨生长的环境不同、成长的方式不同,但都可以用共同的抽象公式来概括——“佳人=女子貌+男子才”。
至若男子:
内中惟一生,片斤素服,生得:美如冠玉,润比明珠。山川秀气,直萃其躬;锦绣文心,有如其面。宛卫玠之清癯,俨潘安之妙丽。并无纨裤行藏,自是风流人物。[4]41(写苏友白)
正看时,走出一个少年,只好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弱冠,身穿一领紫衣,生得唇红齿白,目秀眉清,就如娇女一般。真是:柳烟桃露剪春衣,疑谪人间是也非。花魄已销焉敢妒,月魂如动定相依。弱教看去多应死,秀许餐时自不饥。岂独儿郎输色笑,闺中红粉失芳菲。苏友白蓦然看见,又惊又喜道:“天下如何有这等美貌少年!古称潘貌,想当如此。”[4]144(写男妆之梦梨)
男子要想成为才子,光有才华还不够,还必须有与此才华相配之形貌,否则终非佳人眼中之完美佳婿。而才子之形貌又不能是铁马秋风的沧桑英雄,而必须是小桥流水的文弱书生。对比苏友白和男妆梦梨的肖像描写,我们惊异地发现,二者是何等相像,宛若一人。无论是“美如冠玉、润比明珠’,还是“唇红齿白,目秀眉清”,最终都归结为“宛卫玠之清癯,俨潘安之妙丽”,流露出浓郁的阴柔之气。男妆之梦梨如此描写尚有情可原,她本就是女儿之身,难脱柔媚之气。而何以堂堂男子的苏友白亦是这等阴柔打扮?并且一见到男妆之梦梨还自叹弗如?这只能说明是作者的苦心安排——“男子女写”,即“才子=男子才+女子貌”。
这就是作者理想的自我镜像,这就是作者理想的双美之人。
尽管才子、佳人都是“女子貌+男子才”,虽顺序不同,其实同焉。小说呈现出对阴柔文化的全面倾斜,像是一群女子的闺中风采,但作者又有意回避了女性的身份,像是一群男子的吟风弄月,使倾斜的天枰又重新平衡。作者将才子、佳人都塑造成为双美之人,使他们超越男女之爱成为可以相配的同一种人,使他们成为知己,使他们在文本中互为镜像,而这种镜像,又何尝不是作者以及那个时代焦虑着的人们苦苦追寻的自我认同的一种婉伤的补偿呢?这或许是《玉娇梨》之所以流传甚广的又一大原因吧。
这个时候,再回首小说书名《玉娇梨》,我们看见的就不简单的是红玉(吴娇)和卢梦梨两个女主人公,而会想到“玉娇梨”背后的《双美奇缘》。“双美”一语双关,既揭示了小说的结局和主要框架,也暗含了作者的深远寄托,窃以为是这部小说最佳的题名。然而不知是作者有意,抑或是无意,沿承着《金瓶梅》命名方式的“玉娇梨”最终遮蔽了“双美奇缘”的双关,也遮蔽了小说中严肃而沉重的思考与追寻。于是,眼泪被收起来了,黄粱旧事被收起来了,才子佳人们换上光鲜的外衣,戴上模糊性别的面具,上演了一出盛大的cosplay。
参考文献:
[1]姜书阁.中国文学史纲要:下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685.
[2]程毅中.明代小说丛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谭邦和.明清小说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39.
[4]荑秋散人.明清稀见小说坊之玉娇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5]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545.
[6]方正耀.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党月异,张廷兴.明清小说研究概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316.
[8]聂春艳.一次不够成功的“颠覆”——评《玉娇梨》、《平山冷燕》的“佳人模式”[J].明清小说研究,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