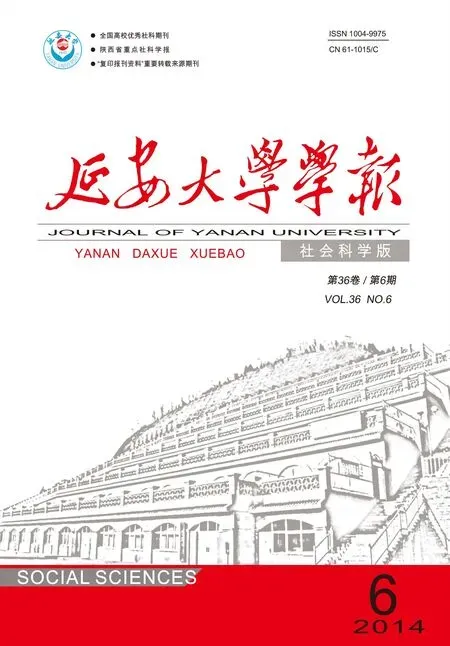论“开发西北”对形成西北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推动作用
赵万峰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西北*“西北”概念所包含的区域,历史上一直在变动,即使现代以来,不同人的理解也不一样,但在今天,该概念基本上已经确定,即包括陕西、甘肃、青海三省及宁夏、新疆两自治区,简称“西北五省区”。本文所引概念即取今天“西北”的概念。地区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但近现代以来,西北地区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实力均落后于东部和南部地区,具体到教育领域,尤其是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方面,西北地区更加远远落后于东部和南部地区。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开发西北”逐渐成为一个民间呼吁、政府主导的社会热潮,在此热潮裹挟下,西北高等教育迈出了现代化的步伐。尽管有学者认为国民政府在“开发西北”的过程中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从目前所接触到的资料来看,“开发西北”热潮对于西北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形成,起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1]。而促使现代西北高等教育形成规模的直接原因,却是抗日战争中被迫进行的东部高校内迁运动[2]46-70。在经过抗日战争之后,虽有内迁高校的“复员”运动,但客观上看,内迁高校的影响,以及留下来的种子,基本上构成了西北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和基本框架。
一、“开发西北”热潮带动了全社会对西北现代高等教育的关注
西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开发较早的区域。高度发达的中原文明,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西部,尤其是西北地区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经营的重点。“历代的西部局势是西北或大规模开拓或急剧收缩,呈极不稳定态势,而西南则是渐进渗透,控制逐渐扩大。这种特点决定了历代西部政策总是以西北为重点”[3]。南北朝以后,随着经济、政治中心的逐渐南移、东倾,以及丝绸之路由陆路向海路的偏移,西北地区逐渐被遗忘,成为偏僻、落后,甚至神秘的代名词。20世纪20年代,西方一些文化学者、探险家对中国西部地区好奇心日益强烈;西方列强俄罗斯、英国等对中国西部疆土新疆、西藏虎视眈眈;国内一些文化、政治有识之士(如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呼吁,要求对西部地区进行开发,等等,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国民政府坚定了“开发西北”的决心,“开发西北”遂成为一种社会“公识”和时代热潮,这成为西北高等教育现代化萌芽的良机。
20世纪初“开发西北”热潮是从类似于探险性质的科学考察之类的活动开始的,这对于有中华文明发祥地美誉的西北地区来说不啻一个讽刺。在这些科学考察活动中,以后内迁高校的专家教授已然成为主力军。1928年,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与中国开发西北协会组建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始对西北地区的地质、地磁、气象、天文、考古、人类、民俗等进行综合性科学考察[4]19。考察团中方队员中的袁复礼,后为西南联大教授。还有一人为以后在西北联大任教的黄文弼。黄文弼分别于1928-1930年、1933年、1943年三次赴新疆考察,他首先发现了西汉纸,首次论证了楼兰、龟兹等古国位置,填补了多项考古空白,他根据自己的考察资料先后出版了《高昌砖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领域影响深远。
20世纪30年代,日本不断在东北滋事,侵略之心昭然若揭,东北朝不保夕。应对更加急迫的日本侵略的大情势进一步激起了国人“开发西北”的急迫之情,随之裹挟而来的是现代西北高等教育体系艰难但迅速的孕育和成长历程。当时国民党许多党政军大员如蒋介石、宋子文、戴季陶、何应钦、孙科、张继、邵元冲等纷纷到西北视察、考察。“中央的人,纷纷到西北,社会的领袖,也纷纷到西北,到西北去已成一种国是了”(宋子文:《建设西北》)[4]31-32。1931年12月18日,《大公报》也发出呼吁:“中国对日必然举国一致为长期的抗争,此即努力一切准备之际,尤其应加紧努力开发西北之时也”[5]。显而易见,开发西北已经成为20世纪20-30年代的一个社会热潮,并且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鼎力支持。
二、“开发西北”热潮直接推动了西北现代高等教育实体的产生
西北地区的教育源起较早,这主要归因于中华传统文明的发祥地——陕西。长安历代历朝作为国家文化中心,必然成为全国教育中心。不仅如此,西北地区的新式高等教育发起也不算晚。在清末戊戌时期,陕西出现了具有一定新式高等教育因素的关中、宏道、味经、崇实四大书院,这个数量在当时是比较多的,层次及水平也颇具影响。
辛亥革命后,随着民国新政府的成立,西安、西北的高等教育也如当时西北在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命运一样,逐渐衰退萧条。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成熟的标志是民国政府在新文化运动后,仿照西方现代大学制度逐步颁行的一系列大学规程:1922年推行“壬戌学制”,奠定了现代教育的学制体系的根基;1924年颁行的《国立大学条例》初步明确了大学科部制;1927年颁行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个层级;1929年颁行的《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分别对大学的性质(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大学与学院的条件,以及“学年学分制”等做了规定;1931年颁行的《学位授予法》规定了对不同层次毕业学生的称呼,即今天仍然沿用的学士、硕士、博士。按照这些规程建立、运行起来或者改造过的大学,可以称之为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大学。依这些标准,1917年西安的高等教育机构有“中等农业学校、中等师范学校,高等专门学校除法政外,他无所见”(参见《秦中公报》1917年5月1日相关报道)。整个西北地区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机构星星点点,不成体系。
20世纪30年代借助“开发西北”东风对西北现代高等教育的“开发”,算得上是对西北高等教育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改造运动。国民政府主导“开发西北”的主要领域不在教育,在交通与水利事业、农业资源、近代工业等领域[6],但在开发过程中,这个热潮也波及到西北现代高等教育领域。1933年7月,开发西北协会在第一届年会上,通过了《西北应施行特殊教育案》、《促进西北民众教育案》;1933年11月,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向国民政府提议,建议在青海边地设立工厂、学校[7]145-148,17-18。1932年7月,安徽大学教授郝耀东在报上发表《设国立西京大学案》的文章,其中认为,西北面积有八、九省大,尚无一所大学,西北的特殊情况,需要造就能适应当地(需要的)人才。如采矿冶金专业、土木工程专业、农艺专业、畜牧专业、森林专业、教育专业等都为西北需要,有这样人才就能带动附属的实业[8]。从民间到协会再到政府政要,整个社会在开发西北,提升西北教育规模层次方面均表现出统一的声音。
“开发西北”的热心人士不仅仅提议加强西北教育,有人甚至提出将西北地区教育基础好、位于西北门户位置的西安建成国内教育中心的设想,这个设想也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32年11月,天津的《大公报》发表题为《西北教育》的社评,其中说:“吾人之见,西北教育之总病原,在于贫穷。然此为整个问题,如何救济农民破产,事属政治,兹姑不论,以教育言,则首望政府在此各省中,至少须各办一完备之专科学校,国家教育经费,动以千百万计,然用于西北者几何?沿江沿海,大学多如毛,而从未在西北省区,创一规模宏阔之国立大学,此政府教育行政上之大缺憾也”[9]。1933年1月,《大公报》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发表《应于西安建立教育中心》的社评。该报经过对当时时局的判断,认为“一旦战事爆发,将有数万失学青年,”希望国府及教育界将西安作为收容大量失学学生的中心,因为“西安市即最适宜地点之一。谓宜乘非常之时,即将西安定为教育事业中心区域之一,而迅速建设之。”社论认为,这个设想不仅仅是解决战争之需的好办法,也是借机使“西安成为新文化市、学生市”,从而改变和丰富西安城市功能的好时机,更是解决长期以来西部高等教育远远落后于东部高等教育不平衡现状的大好机会[10]。两年后出现的《促进西北教育案》(1935年11月5日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该提案中提到:“兴办西北专门教育,造就实际人材,其为当务之急。”这说明,当时包括教育在内的西部开发,的确已经列入国民政府的考虑之列,而且已经在舆论宣传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开发西北”热潮在高等教育领域结出的第一个果实是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建立。1932年秋,国民政府批准了于右任等人提出的筹备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的提议,任命于右任、杨虎城等十五人为筹备委员。《促进西北教育案》中也提到了早前就有建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提议。1934年,陕西呼吁“开发西北”最力的名士安汉,在开发西北协会创办的《开发西北》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对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设施之意见》一文,对具有现代大学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做了详尽的规划与设想,他在文章中指出,为急谋开发西北农业,复兴西北农村起见,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应确定以培养具备农业专门科学知识,掌握农业生产技术,能够经营农业生产,具有刻苦耐劳的工作与生活品质,具有开发西北的兴趣,以复兴西北农村改善农业为己任的人才[11]。同年,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在陕西武功设立,“经十余月以来之筹备经营,对农场力谋开发,现林场已有梅(眉)县、周淄(至)两处”(参见《大公报(天津版)》,民国23年4月30日相关报道),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就此基本建成,成为当时西北地区最高层次的现代高等学府之一。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并不是一所完全由西部地方政府独立创建的现代大学,它有东部大学——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的血统。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史档案中记载:国民政府主导,由于右任、张继、戴季陶三人为常务委员组建成立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其办公地点设在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委员会决议将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部分校产发归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上海的报纸《申报》、天津的报纸《大公报》如此关注一所西北高校建设概况的重要原因。
国立西北大学在西部建校较早,具有现代大学的因素,1924年成立,但是1927年收束改办为中山学院,以后的发展举步维艰。据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结果显示: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全国共有108所高校,大多集中在上海(27所)、北平(16所)、广州(8所)、天津(7所)、武汉(6所)、南京(5所)等地,西北的高校仅有三所,分别为兰州的甘肃学院,迪化(乌鲁木齐)的新疆学院,以及陕西武功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2],这三所学校为西北地区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其中,“开发西北”热潮功不可没。
三、抗战期间,东部高校内迁运动成为落实“开发西北”的具体措施之一,西北成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心之一
抗战爆发后,迫于东部沿海地区战事吃紧,国民政府做出了将西南、西北作为抗日大后方的战略决定,命令东部先进的工业、商业、教育等机构尽可能多的向西部内地迁移,东部高校内迁运动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从发展阶段看,抗战时的高校内迁运动是“开发西北”热潮的延续——利用东部成熟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支援带动西部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从因果关系看,它既是开发西北热潮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抗日御侮建立大后方,保存高层次人才生产的体系与根脉;也是想要达到的一个结果——借机提升西北高等教育的层次与规模,消除愈益严重的东西部高等教育不平衡局面。
随着东北的沦陷,日本渐渐进逼华北,“开发西北”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开发落后、平衡东西的层面,西部已经被时人看作以应不时之需的基础和大后方。如果说,抗战前的“西部开发”主要为舆论宣传及理论研究阶段,那么,抗日战争的正式爆发,瞬时调快了开发西北步伐的频率,许多舆论宣传一夜之间落实为行动。加快西北开发,建设西北现代高等教育的呼声也比以往更加猛烈。1936年1月,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先后两次向教育部进函,第一份函件要求“将北平四所大学迁移一所进陕”,在第二份函件中直接“提议将国立北洋工学院西移”[7]26-28至陕西。这些提议,无疑会对国民政府在1937年做出在西安设立西安临时大学的决定产生积极地影响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陕西成为了全国内迁高校的一大集聚目标区,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组成内迁大学中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他们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安排下落户西安,被称为西安临时大学。
这样的安排,很明显跟此前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省民间的呼吁、陕西省政府的请求有很大的关系,这里面应该也有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提议的呼应,以及平衡国内高校布局的长远考虑。因为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935年,华北局势紧张之时,高等教育战线上的许多专家就开始酝酿高校内迁的事宜。当时清华大学在长沙岳麓山营造校舍新址,南京中央大学在校长罗家伦的动员下,校址选在重庆大学附近的松林坡。其他各校应该也有各自迁校的目标地和自己的计划。在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并没有安置所有高校的计划,他们只确定了两所“临时大学”的去向:湖南长沙的长沙临时大学以及陕西西安的西安临时大学,足见国民政府教育部是做过考虑,已经有了基本的国内大学布局的思考。
四、抗战后,“开发西北”成为一种“国是”,西北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基本成型
经过抗日战争,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在整个国家中的安全战略地位有了深刻的理解,决心要下大力气经营西部、西北社会,将此地作为国家立足的大后方、大基地。“开发西北”没有随着抗战的结束而结束,反而由一种社会热潮转而成为一种“国是”,继续发展提升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数量质量也就顺理成章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实质上,抗战开始,国民政府已经开始谋划西北高等教育布局的事情。西北联大从“移布”西北,到最后大部扎根西北的过程就是证明。1938年4月,教育部下令:“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西北联合大学。”(《国民革命政府教育部给西安临时大学的训令》,1938年4月3日。)在汉中办学过程中,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进一步指示:“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1940年6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曾到西北大学视察,并为西北大学第四届同学会题词:“学成致用,各尽所长,经营西北,固我边疆”。“移布”是迁移进行布局,布全国高等教育之大格局之意,说明从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已经有了让西北联大扎根西北,作为平衡全国高等教育分布的计划了。随后教育部长的指示更加明确:西北联大最好不要离开西北,应在西北扎根。在抗战后期,局势比较明朗之时,教育部长进一步明确了已经“布局在西北地区”的西北大学的办学任务,那就是“经营西北,固我边疆”。至此,在“开发西北”的大“国是”指导下,内迁到西北的高校在国民政府的引导下,逐渐将扎根西部、建设西北的重任扛在了肩上,现代西部高等教育的体系逐渐成型。
事实也是如此,经过八年抗战,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实力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促使长足进步产生的最大变量是西部地区。据统计,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由1936年的108所扩张为1945年的145所,西北地区战前仅有3所高校,战后达到了13所,其中,陕西高校达到8所,分别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安),国立山西大学(陕西宜川县,随后回迁山西太原),国立西北医学院(南郑),国立西北工学院(城固),国立西北农学院(陕西武功),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西安),私立西北药学专科学校(西安),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西安);甘肃为3所,分别为国立甘肃学院(兰州),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兰州),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兰州);新疆2所,分别为新疆省立新疆学院(迪化),新疆省立女子学院(迪化)[2]346-351。通过查看其它资料,我们发现此统计数据还不够详尽,例如,西北师范学院此时在兰州和城固两地同时办学,但在陕西及甘肃均未见统计,陕西省还有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西安),私立知行农业专科学校(陕西户县)也未统计在内,这样算来,西北高校实际至少已有15所(国立山西大学除外),西安、兰州、新疆等地区的高等教育由于内迁高校的留守或影响而获得很大发展。一些高校如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大学前身)、西北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西北工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前身)等,是直接由内迁的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组成的西北联大分化出来的,西北地区现代高校不仅数量上得到突飞猛进的提升,而且起点高、门类全、分布广,他们在西北大地上生根发芽,构成今天西北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和基本框架。
通过20世纪20-30年代开发西北热潮的推动,加上抗战期间高校内迁运动,战后的政府引导,西北高等教育走上现代化之路,真正建立起了全面的、不落后于东部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实现了东西部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平衡。总结本时期西北高等教育发展与“开发西北”热潮的关系,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开发西北”热潮对于西北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也为抗战正式爆发后,国民政府选择陕西作为内迁高校落脚地奠定了舆论基础。
(二)抗战造成的东部高校内迁运动是落实“开发西北”的具体措施之一,真正促进了西北现代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
(三)抗战经历使国民政府对西部地区保护国家安全的大后方地位有了深刻的理解,“开发西北”没有随着抗战的结束而结束,反而由一种社会热潮转而成为一种“国是”。加强西北开发的“国是”促成了西北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备。
参考文献:
[1]杨乃良.一次成效甚微的西北开发——民国时期西北建设研究[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66-69.
[2]侯德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3]李绍强.论秦汉至明清时期的西部政策[J].齐鲁学刊,2002(2):126.
[4]戴逸,张世明.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5]社评.行矣,第一机![N].大公报,1931-12-18.
[6]李云峰,曹敏.抗日时期的国民政府与西北开发[J].抗日战争研究,2003(3):51-78.
[7]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8]郝耀东.提议设国立西京大学案[N].大公报,1932-07-06.
[9]社评.西北教育[N].大公报,1932-11-29.
[10]社评.应于西安建立教育中心[N].大公报,1933-01-29.
[11]安汉.对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设施之意见[J].开发西北,1934(1).
[12]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