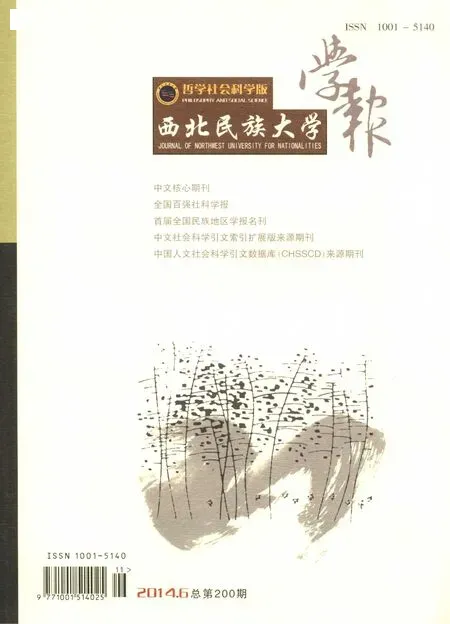试论中国神权法思想的源起、发展与演变
张国妮
(西北民族大学 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1世纪之时的夏朝,夏朝是我国奴隶制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奴隶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利用神权思想进行统治,由此形成了极富特色的神权法思想。商朝时期神权法思想盛极一时,奴隶主贵族对至上神和上帝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到了西周时期神权法思想却发生了一次较大变化,针对神权法思想内容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根据统治者维护其长期统治的需要,周公旦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思想,对夏商神权法思想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发展,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形成之初就弱化了神权法思想,代之而起的是突现了宗法思想,并以宗法思想为核心形成了礼治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神权法思想开始衰落,汉朝之后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所吸收,以“天人感应”给君主至尊无上的地位和实施统治提供理论依据,认为君主的统治顺乎天意,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
一、夏商神权法的源起
夏朝距今历时久远,缺乏确凿的史料来说明夏朝的法律思想状况,但从古籍中的一些片断记载来看,夏朝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利用神权思想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论语》中讲:禹“致孝乎鬼神”[1],说明禹已经通过祭祀、敬献表达对先祖和天神的敬畏。《尚书》中讲:“有夏服天命”[2],夏朝的统治者极力宣扬自己是秉承上天的旨意来统治百姓。这些记载说明夏朝建立后,奴隶主贵族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极力宣扬并利用宗教迷信和鬼神观念,宣称自己是神和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接受“天命”来统治人间,对不服从其统治者施行“天罚”。这种观点在《甘誓》一文中体现得十分具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3]
甘誓一文所记载事情的起因是遵循禅让制,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当禹做了部落联盟首领后也想效仿尧舜,将来能有一个贤能的人接替自己。最初,部落联盟会议推举出皋陶,但是没等接任,皋陶就病亡了,后来经过商议,又一致推举伯益做禹的继承人。伯益曾经是禹治水的一名主要助手,所以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伯益是仅次于禹的一位英雄。当禹的儿子启逐渐长大后,禹开始让启参与治理事务,启也将各类事务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而伯益做为继承人,却没有做出新的政绩。禹过世后,启就理所当然地行使起首领之权来,而多数部落因为启是禹的儿子,也都表示效忠于启。启率军先打败了伯益的军队,公开宣布自己是夏朝的国君。随后又与有扈部落大战于“甘”,启对他的将领士卒声称,有扈氏对上天不敬,不遵天命,上天命令自己消灭有扈氏,所有将士都必须服从这一天命,奋力出击,不可懈怠。战争的结果是打着天命天罚旗号的启完全占据了优势,而被指称背天逆命的有扈氏被打败,有扈部落的成员被罚做奴隶。
商朝时期,神权法思想达到了高峰,奴隶主贵族对至上神和帝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奴隶主贵族不仅继续宣称“有殷受天命”[4],他们还设计出了一个主宰一切的至上神——“帝”或“上帝”,这个至上神存在于众神之上,是创造并支配着一切的最高神,是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不仅支配着自然界的风云雷雨霜雪阴晴,还掌管着人间的祸福。商朝奴隶主还进一步把帝说成是商王的先祖,商王受帝之命来到人间统治一切,死后还要回到帝身边去。《诗经》中记载:“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5],又讲“天命玄鸟降而生商”[6]。这样,商朝奴隶主就从血缘上找到了充当帝在人间代理人的合法依据,人们要服从帝,当然也要服从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商王的统治,违抗王命等于违抗神命,要受到“天罚”。约在公元前17世纪,商汤正式兴兵讨伐夏桀,发表了讨伐夏桀的檄文,声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7]在这篇檄文中,商汤搬出了上帝,指出是上帝不满夏桀犯下的诸多罪行,命令商汤去讨伐夏桀,商汤由于敬畏上帝,不敢不去征讨,同时要求自己的将士辅佐于己,行使上帝对夏桀的惩罚。商朝时期刑罚极为残酷,为了对酷刑的实施有所遮掩,统治者极力宣称代天行罚,《礼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8],还经常利用“占卜”来使百姓“敬鬼神,畏法令”[9]。所有国家大事,甚至是否用刑,都要通过占卜向上帝鬼神祈祷和请示,如“贞:王闻不惟辟,贞:王闻惟辟”,“兹人井不”[10]。这些甲骨文就是占卜决定是否定罪用刑的记录,表示他们使用刑罚是根据天意行事,给商王的审判随意性涂上一层神权的光环。
夏商时期神权法思想的基本情况表明,奴隶主贵族利用“天命”宣称王的统治是由上天所安排的,人们应该无条件的服从,利用“天罚”宣称施行刑罚是上天的意志,是秉承神的指令,从而给刑罚蒙上一层神圣的外衣。奴隶主贵族通过强调天以及上帝的绝对权威,把自然灾害、天下治乱以及生死祸福等现象都说成天行赏罚。宣扬痛苦的产生是因为人们自己犯了罪,只有忍耐、顺从,才能来世得福,其实质是利用神权借以麻痹人们的反抗和意志,成为他们用来束缚、统治百姓的一种思想武器,给王的统治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这就使得“在中国,从未出现过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教会和教权,而突出地表现为神权与王权、族权的合一。”[11]这种只崇尚暴力,专讲刑杀,而不任德教,只笃信上帝,专事鬼神,而不注重人事的天命天罚论虽然维护了夏商时期奴隶主阶级一时的残暴统治,但却无法阻挡王朝的最终覆亡。
二、西周时期神权法思想的发展
神权法思想在西周发生了重大变化,取代商的西周奴隶主贵族虽然在思想上仍然利用神权作为统治百姓的精神武器,他们也尊崇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不过在更多的场合下称之为“天”,声称周王的统治受命于天,“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12]“天亦大命文王殪戎殷。”[13]“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4]周公旦在东征平乱的文告《大诰》中说:“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国。宁王惟卡用克绥受兹命……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15]这些表述都是想说明因为上天垂青于文王,才使得周族能够兴盛起来,并最终取代商而统治天下。
周公旦提出“以德配天”说修正了神权法思想。西周奴隶主贵族在政权建立之初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商汤讨伐夏桀之时,也曾宣称是执行天命,商朝建立后其统治者一再宣扬“帝立商”,可以永世长存,纣王至死仍然坚信他是“有命在天”[16]。那为什么上天会眼睁睁地看着商朝灭亡,周取而代之呢?为了说明周取代商的合理性,把天命从商王那里转移到周王手中,变成周朝的保护伞,就必须对夏商神权法加以修正,以弥补其理论上的漏洞。为此,周公旦提出了天命转移的“以德配天”说,认为天命是有的,但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天命靡常”[17],以此告诫周朝的统治者要牢记天命不常的道理,上天所授予的垂青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转移,天命不会永远地保佑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王朝,统治者必须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否则,天命就会转移。天命根据什么进行转移呢?周公旦认为天以德选君,“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8]只有有德者才可以承受天命,并受到上天的保佑,失德就会失去天命。过去,商朝的先王有德“克配上帝”[19],所以天命归商,后来由于商王失德,商王就被上天抛弃。周族之所以被上天选中取代商,是因为周王有德,既然代商而治是上天的旨意,周王也就不敢放弃天命的保佑。
周公旦提出“敬德保民”说补充了神权法思想。周公旦认为,夏商之所以灭亡,就是由于夏王、商王不敬德,“不敬劂德,乃早坠劂命”[20]。周王要吸取经验教训做到享国长久,就要以德行事,“皇天既付中国民越疆土于先王,肆王唯德用”[21]。德的施行包含对已和对民两方面的内容,对已就是对上天、先祖要诚,对已要严,与人为善,要加强自我克制、自我修养的功夫;对民则表现为“保民”。商朝末年,牧野之战中“前徒倒戈”的严酷现实,使周公旦深切感到民不可轻,对民的力量不能不有所重视。因此,他说:“天惟时求民主”[22],以此说明上天关怀下民,要根据情况为下民求得一个比较好的君主。周公旦认为天命与民情是一体的,只能通过民情才能洞悉上天的意志,“民之所欲,天必从之”[23],“顺乎天而应乎人”[24],对于统治者来说,要想知道能否得到天的佑助,只有体察民情才能得到真实的答案。因此,周公旦主张“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25],要求当政者不能把水当作镜子来照影,而应通过民情来检查自己的政事。
周公旦提出“明德慎罚”说发展了神权法思想。周公吸取了夏商灭亡的教训,感到单一重用刑罚反而会加剧百姓的反抗,危及政权的生存,为了使天命不再转移,他提出了“明德慎罚”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26]说明文王为政,能够崇尚德政,慎用刑罚,不侮欺辱鳏寡,任用该任用的人,尊敬该尊敬的人,惩罚该惩罚的人,只有沿用周文王的德行,王权才能保住。他又说:“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27],意指“明德”就在“慎罚”之中。“明德”就是要加强自我克制,实行德治,推行德政。周公十分重视吸取夏、商两代灭亡的教训,他指出,商朝初期,商王也能“治民袛惧,不敢荒宁”[28],能够理解百姓疾苦,能够谨慎为政,所以能享国日久,但是后来的商王只顾自己享乐而肆意压榨百姓,结果是没有一个能享国长久。作为反省,周朝的统治者必须实行德治。“慎罚”就是主张谨慎用刑,反对滥杀无辜。
周公旦对神权法思想的改进反映了西周时期神权法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针对神权法思想内容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根据统治者维护其长期统治的需要,周公旦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对夏商神权法思想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发展。周公旦将上天依然奉为至上神,但它不属于某一个民族,而是天下各族人所共有;将上天的喜好界定为“德”,上天是关心民间疾苦的,上天把天命交给那一族,要看该族是否有德,是否获得天下之民的拥护;已经获得天命之族要想长久保有天命,也必须有德,必须获得天下之民的拥护。周公旦对神权法思想的改进一方面是延续了自夏商而来的神权法思想,求得上天的保佑,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西周的统治者从夏商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劳动人民反抗力量的强大,使他们感到单纯依靠神权不足以维系其统治,统治者要从单一注重天命转而注重人事,必须重视百姓的力量,重视民心向背。只有勤于修德,慎用刑罚,关心民间疾苦,才可以长久的维持周王朝的统治。周公旦对神权法思想的改进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形成之初就弱化了神权法思想,代之而起的是突现了宗法思想,并以宗法思想为核心形成了礼治思想,运用神权法和宗法伦理道德维护着西周奴隶主的统治。
三、春秋战国时期神权法思想的衰落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变革时期,奴隶制社会开始瓦解,封建制社会开始形成。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的发展,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伴随私田的出现,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取代了奴隶制生产关系。新兴地主阶级经济势力大增,与奴隶主贵族阶级之间矛盾尖锐,他们在政治上要求取代奴隶主贵族阶级掌握政权,从而引发了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社会中经济政治方面的动荡与变革必然要反映到思想领域中,随着奴隶制的瓦解,神权法思想进一步动摇,周公旦对夏商神权法思想改进的成果并没能维持多久,神权法思想逐渐失去人们的信任,呈现衰落之势,代之而起的重民轻神思想,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终于从神权桎梏下解脱出来。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对于天与民、神与人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否定天对人的支配地位,天道与人道分离,人道逐渐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公元前541年,晋国国君晋平公得了重病,为了治病,他听从巫师之言,做法求神,祈求神灵保佑。子产反对这种愚昧做法,他在解释晋平公患病原因时说:“若君身,则亦出于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29]以此说明吉凶在人,而不是由天上的神灵来决定的。公元前524年,中原地区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而此前曾有慧星出现。懂得天象休咎的郑国裨灶预言郑国也将发生火灾,要求子产允许他用珍宝祭祷,从而免除郑国火灾。子产根本不理那一套,他讲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30]子产的观点极富代表性,治国齐家与其致力于飘渺难期的天道,不如脚踏实地在人道上下足功夫,只要人道功夫到家,天道必然酬勤。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都持有相同的观点,主张远天道而近人道,轻神事而重人事。公元前516年,齐国出现彗星,按照当时的说法,彗星出现是灾祸的象征。齐景公马上派人禳祭,晏婴认为,如果国君有好的德政,还怕什么彗星?反之,如果国君像夏桀、商纣一样暴虐,违命乱德,那么既使祈祷又有什么用处?[31]史书记载孔子也以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鬼神,在生活中尽量淡化神事。《论语》记载子路向孔子请教有关鬼神之事,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32]。表明孔子自己不谈鬼神,也不主张别人谈鬼神。春秋时期鬼神迷信仍占统治地位,孔子的回答虽然表面上看没有直接否定鬼神的存在,而实际上已明显地表露了他对不可知世界不予讨论的态度。孔子不谈鬼神,因为鬼神具有不可知性、无法掌握性,因而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子路又请教有关死亡的一些事情,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33]。死亡与鬼神一样,也是不可知的,不能把握的,孔子对超乎此生此世的问题、对象,采取一贯的存而不论的实用态度,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而是主张做能做的事,做眼前的事,做现世的事,做好人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态度,当他的另一位学生樊迟请教怎样才算聪明的问题时,孔子回答:“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矣!”[34]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持有的这种重民轻神的观念和思想对百姓有利,同时也有利于社会进步,一些睿智的治国者由忽略上天鬼神转而十分重视百姓的需求。《古文尚书》写道:“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35]这是史书中最早记载民是立国之根本的思想。管子在齐国为相辅佐齐桓公30年,提出治国首先在于得民心。齐桓公曾经问管仲:“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36]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37]。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后国家得到治理,达到兵强、民足、国富,然后争霸天下。《牧民》开篇即写到:“凡地有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来者,地僻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8]以此说明统治者只有注意农时,发展生产,使国家财物充足,百姓生活有着落,才能使远方的百姓愿意迁来,本国百姓愿意留住。所以管子认为,发展生产是使国家富强的前提,也是使百姓遵守礼义法度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物质基础。如果不注意发展生产,不解决百姓的衣食问题,而空谈礼义法度,国家永远也治理不好。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弑君灭国、僭越违礼与革旧立新之事不断发生,社会动荡不安与变革必然要反映到思想领域中,伴随着神权与反神权,公布成文法与反对公布成文法,礼与法,德与刑的争鸣,伴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王权的失落,神权法思想呈现衰落之势。
四、秦汉时期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确立
法家思想曾在秦朝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国家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推行“事皆决于法”的法治思想对于自夏商延续到周的神权法思想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与颠覆。与此同时,秦朝统治者沿着严刑峻法的方向将法家学说发展到了极端,成为他们实行横征暴敛、酷刑害民的借口,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了秦朝的灭亡。西汉初年面对经济凋零、动荡始平、人心思治的局面,统治者在思想领域推崇黄老之术,并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的统治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到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实力大增,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势力也逐渐强大,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最终酿成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虽然叛乱最终被平定,但它促使统治者认识到,有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重新寻求更有效的理论作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董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吸收各家学说以及天命神权等各种有利于建立和维护君主集权专制政治思想的观点,提出了新儒学思想,这也使得自夏商形成并延续至汉朝的神权法思想最终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所吸收。
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说加强了对君主的神化,给“君权神授”制造理论依据。天人感应之说,源自儒家的《尚书》:“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39]意思是说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这是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孔子也讲“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40]认为灾异是由于国君失德而引发的,因此劝告国君应该“正刑与德,以事上天。”[41]一方面,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说提出自然灾害和统治者的错误是有因果联系的,“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42]。以此说明君主统治是天意的体现,君主必须秉承天意来行事,否则会受到天罚。另一方面,董仲舒借助阴阳五行学发展天人感应思想,董仲舒认为,宇宙由水、木、金、火、土五种不同的属性组成,五行相生相克不仅构成了合理的宇宙关系,也形成了合理的人类社会关系,如果不依据五行之性合理地运行生成就会导致人世间与自然界不应有的灾异,所以需要天人同类,“以类合之,天人一也”[43]。
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至高无上并派生万物的神,“天者,百神之大君也”[44],“天者,群物之祖也”[45]。天为人间派生出两样滋生物,一是天子,“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46],“王者承天意以从事”[47];二是整个封建制度,“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48]。董仲舒重新将天塑造成至上神,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天和人间相通,人应按天的意志来行动,君主就是天命或天意的执行者。君主居于上天和百姓之间,上天的意志通过君主而贯彻到人间,上天与君主就如同父亲和儿子,儿子遵从父命,君主服从天命;君主和百姓的关系也是一样,天下之人都要服从君主,如同孩子服从父母。
董仲舒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以及孟子的伦理道德观念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三纲五常论”,他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且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49]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由此形成三纲的观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臣、子、妻必须要绝对服从于君、父、夫。“五常”实际上是“三纲”的具体化,是指仁、义、礼、智、信5个封建道德教条。董仲舒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三纲五常的核心是维护和巩固君主的权力,董仲舒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不可抗拒的天意,以“天人感应”给君主至尊无上的地位和实施统治制造理论根据,认为君主的统治顺乎天意,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
总之,从法律思想史的起源考证,中国历史上最初确立的法律思想是神权法思想。夏商时期的奴隶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利用神权维系其统治,他们的法律思想也深受神权的支配,统治者宣称自己是神和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接受“天命”来统治人间,对不服从其统治者施行“天罚”,由此形成了神权法思想。到了西周时期,神权法思想却面临思想内容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根据统治者维护其长期统治的需要,周公旦对其进行了改进,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形成之初就弱化了神权法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神权法思想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重民轻神思想,汉朝时期董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吸收各家学说以及天命神权等各种有利于建立和维护君主集权专制政治思想的观点,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不可抗拒的天意,以“天人感应”给君主至尊无上的地位和实施统治制造理论根据,认为君主的统治顺乎天意,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使得神权法思想为随后形成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所吸收,长期起着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重要精神支柱的作用。
[1]论语·太伯[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2][4][20]尚书·召诰[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3]尚书·甘誓[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5]诗经·商颂·长发[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6]诗经·商颂·玄鸟[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7]尚书·汤誓[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8]礼记·表记[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9]礼记·曲礼[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10]刘新.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
[11]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20.
[12]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13][26][27][28]尚书·康诰[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14][17]诗经·大雅·文王[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15]尚书·大诰[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16]史记·殷本纪[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18]尚书·蔡仲之命[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19]诗经·文王之什·文王[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21]尚书·梓材[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22]尚书·周书·多方[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23]尚书·秦誓[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24]易经[Z].
[25]尚书·酒诰[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29]左丘明.左传·昭公元年[Z].蒋翼骋点校.长沙:岳麓书局,2006.
[30]左丘明.左传·昭公十八年[Z].蒋翼骋点校.长沙:岳麓书局,2006.
[31]左丘明.左传·昭公·齐有彗星[Z].蒋翼骋点校.长沙:岳麓书局,2006.
[32][33]论语·先进[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34]论语·雍也[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35]古文尚书·五子之歌[Z].
[36]管子·霸形[Z].戴望点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
[37][38]管子·牧民[Z].戴望点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
[39]尚书·洪范[Z].陈茂国点校.长沙:岳麓书局,1991.
[40][41]商承祚.战国楚竹简·鲁邦大旱[Z].济南:齐鲁书社,2000.
[42]董仲舒.春秋繁露(卷第八)·必仁且智第三十[Z].北京:中华书局,1984.
[43]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义[Z].北京:中华书局,1984.
[44]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北京:中华书局,1984.
[45]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Z].北京:中华书局,1984.
[46]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Z].北京:中华书局,1984.
[47]班固.汉书·董仲舒传[Z].北京:中华书局,2007.
[48][49]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Z].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