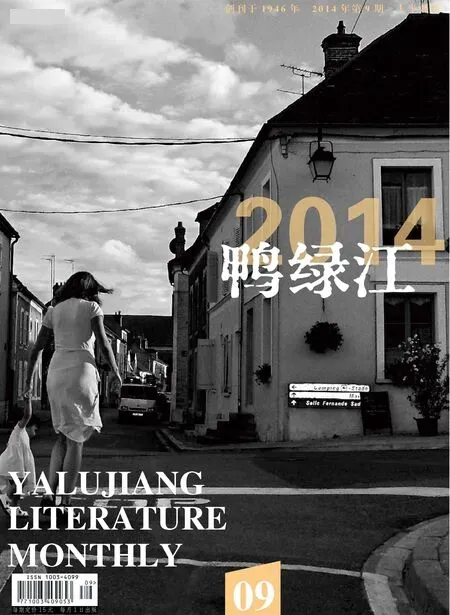亲爱的给我写信吧
潘 洗
亲爱的给我写信吧
QINAIDEGEIWOXIEXINBA
潘 洗

你们现在看到的,跟最终呈现的,也许不尽相同。
——写在前面,这可能跟文本无关
那时候的玉城只有一家浴池,是国营的,在中街满族商场后面。我大概每个月只能洗一次澡,不像现在,没事儿了就跑到桑拿浴去蒸蒸、泡泡,做个足疗、按摩什么的。主要是怕麻烦;当然,那时候我还坚持认为,内心的纯粹远比身体的洁净更重要。虽说整个玉城都是一副灰土缭乱的破旧模样,但空气却是清新的、干净的,似乎身上也没觉得有多么脏。那时候还没有出租车和公交车,甚至连机动车都屈指可数(就连大名鼎鼎的玉城供电局也只有两台车,一台北京吉普,一台大解放),不像现在这样车满为患,饱食汽车尾气之苦。逼仄凌乱的大街上,差不多都是些逛街赏景的闲人。难怪玉城人无所事事,日子过得清贫,兜里没钱是主要原因。那时候的玉器产业还没有成型,没有玉都,没有金龙大厦,没有荷花市场,遑论如今名满天下的中国玉器会展中心了。既没有那么多赚得盆满钵满的玉器商人,也没有如今这么多可以烧钱的休闲去处,像KTV、酒吧、茶楼、网吧、洗浴中心、烧烤店、棋牌室等等,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玉城。
1989年秋天毕业时,我先是被分配到丹东电业局,随即又被分配到玉城供电局。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对“分配”这个词或许是陌生的,按照当时的政策,凡是列入国家招生计划的大中专毕业生,国家都是给分配工作的,这个工作就是所谓的“铁饭碗”。在学校住了四年独身宿舍,工作了还是住独身宿舍,所不同的是,这回我是栖身于局线路维修值班室。那儿本来有一张床供值班人员使用,再塞进一张床,就显得挤巴多了。还有一台彩电,节目只有几个台,偶尔碰到精彩的节目,我也会看得跟他们一样津津有味。那部老式电话是用户报修用的,平时还好,就怕深更半夜打进来,午夜凶铃的感觉相当惊悚。要命的不止这些,老实说,小丁的臭脚味儿我还是能够忍受的,想当年同寝室的老五总也洗不掉脚上的臭味儿,我不是照样熬过来了?最受不了的是小梁的呼噜声。我很纳闷,身材精瘦的小梁怎么会发出如打雷一样的鼾声呢?后来,我对每一个打呼噜的人都深恶痛绝,病根就是从那时候坐下的。
我被再次分配到下面的营业站工作,这可是个要害部门,是专门负责报装接电、抄表收费的,打个比方吧,营业站差不多就像“电老虎”的牙齿。由于供电局大楼正在翻建,营业站暂时搬到工行西侧的电业家属楼一楼办公。当时的工行大楼是这个地段的地标性建筑,可惜几年后工行解体了,那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叫作“云龙碧水”的洗浴中心,没几年洗浴中心也倒闭了,到现在已经闲置多年。如今,隔着一条宽敞的站前大街,街南的贺临假日酒店已经成为玉城新的地标。不过在当时,那地方还没有这家三星级酒店呢,从贺临酒店那个位置向西,都只是一大片尚待拆迁开发的平房区。
玉城是慢节奏的,上班的人们都过着朝八晚五、按部就班的悠闲生活。营业站的同事们基本上也是这样。通常情况下,早上人员是最齐的,说笑了一阵便各自出去抄表、收费了,窗口登记和内勤的同事们大抵只干半天活,然后就停下来扯闲篇。“扯闲篇”是盛行玉城的叫法,就是漫无目的地闲聊。我来得晚,跟他们不熟,融不进他们的话题中去,所以基本上只有听的份儿。我的工作就是换抄表卡片,就是那些旧的抄表卡片已经记满了,要把用户的基本信息如姓名、住址、电表号以及电表示数,都抄录到新的抄表卡片簿上,很琐碎,但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责任心,一不小心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好像从到营业站那天起,整个秋天我一直在干这个。到了下午,营业站里变得比较清静了,我才能偷偷看几眼自己带的闲书,或者拿出信纸写上几页。作为新人,我还是比较注意个人表现的,工作时间轻易不做私事。我基本上是把自己的事情放到宿舍,也就是值班室去做的。那儿的环境虽说有些嘈杂,但总有安静的时候,比如值班人员接到电话出去修理,那个把小时绝对属于我自己。再就是我早早起床,早上也有一大块时间可资利用,最有意思的是,即便像小梁那样的呼噜大王,他早上的鼾声也是很轻微的。我只能这么见缝插针看一会儿书,或趴在床上写点东西——主要是写信,刚刚参加工作,当然不能断了跟同学们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给斯漪写信);也记日记,读书时曾经记了四年的日记,这个习惯,我依然顽强地坚持着。那时候,我的生活轨迹非常简单:住在值班室,去政府招待所餐厅吃饭,去营业站换抄表卡片,去邮局寄信,回局收发室取信。就像上班一样规律,我每天都要到收发室打一站,以至于跟收发室的叶师傅很快就混熟了,他说:小洪啊,全局就属你的信最多了,你放心,我会把你的信件单独保管好。
这是安放回到玉城供电局之前的情形。等过了国庆节,安放回来了,情况逐渐发生了某种变化。安放是我的同届校友,又是玉城老乡,在学校时走得就近。他最后那个学期去市局(我们通常把上级丹东电业局称为市局)物资科实习,本以为他有机会留在丹东,不想还是回了玉城。不管怎么说,我们俩是玉城供电局有史以来分配进来的第四个和第五个中专生,所以,局领导还是很重视我们的住宿问题的。安放的二姨家住玉城,两家过从甚密,所以安放刚回来时,就借住在他二姨家。不像我,在玉城差不多举目无亲,倒是有一个本家的姑奶住在这儿,但素无来往,我怎么好意思主动上门认亲去。其实,哪怕是相处再融洽的亲戚,暂住一段还好,时间长了总不是个事儿呀。
值班室肯定是挤不下了,新大楼尚未竣工,连局领导都是两个人挤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办公,哪里还有多余的房间可以改作宿舍呢。经过局领导的协调,赶在冬天之前,我跟安放住进了玉城丝绸厂的独身宿舍。这下子好多了,丝绸厂是大企业,管理也比较规范,独身宿舍就是厂招待所中最高的那层楼,每个房间四个人,一日三餐也解决了,两个室友,小高和小赵人也不错。这儿还有一个福利,就是我、安放跟丝绸厂的职工一样,享受每周开放一次的内部澡堂洗浴,水挺干净的,澡票每张才一块钱,比去中街浴池便宜一半。
安放回来后,也来到营业站,负责整理营业资料。虽说有点大材小用,但安放的物资管理专业知识有了用武之地,他很快就把营业资料室打理得规规矩矩。我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几万张抄表卡片终于换完了,我就由林师傅带着,记账、对账,跑银行存现金和支票,往市局汇电费款,当时的岗位叫现金整理,现在已经正名为营业出纳了。从某个意义上说,我这个学财务会计的干上这份工作,也勉强算是专业对口了。工作照旧很清闲,一般情况下,一到下午就没什么事儿了,我就去资料室跟安放聊天,或者凑到同事们的堆儿里扯闲篇。安放在丹东实习期间,跟玉城的一些同事早就认识,所以他们很容易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对我来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去处,那就是安放管理的这个营业资料室。不知什么原因,供暖开始后,其他办公室都很冷,唯独资料室暖气很足。那时候还没有厄尔尼诺现象,没有暖冬,在我的记忆里,那年的冬天冷得早,冷得异常,以后许多年都没那么冷过。资料室几乎成了我度过这个寒冬每一个夜晚的唯一去处。开始我还拽着安放一起去,后来他干脆把资料室钥匙交给我。那个冬天,我是这样度过的:吃住在丝绸厂独身宿舍,大半时间都待在营业站,白天自然是在自己的办公室,晚上则去安放的资料室,我就在那儿看书、写信,还有胡思乱想。无论多冷的天,无论多刺骨的风,无论下多大的雪,每天晚上11点之前,我基本上都待在资料室里。

潘 洗,本名姜鸿琦,满族,1969年4月生于辽宁岫岩。工程硕士,文学创作二级。曾在国企从事过共青团、会计、宣传等工作,现供职于国网鞍山供电公司。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发表小说数十篇,出版小说集一部,逾50万字。系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小说北2830”召集人。
我已经不用每天都去收发室了。我早就摸清了投递员到收发室的时间,大概是在每天早上的9点钟左右,我便在那个时间打电话过去,问的都是同样的一句话:叶师傅,有我的信吗?叶师傅显然听出了我语气中的迫切,他打趣道:小洪啊,是不是等你对象的信啊?弄得我很不好意思。通了电话后,就会提前知道是否有我的信来,我就可以在跑银行时顺路到收发室取信。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进账单,然后挨家银行跑去存。紧挨着营业站的是工行,然后往南是建行、农行和农村信用社,建行和农行中间是邮局,路过邮局时我会去把信寄出去,等跑完农村信用社,我再折回来,从邮局的路口向西,到局收发室取信,再继续向西回到丝绸厂的食堂吃午饭。每天上午就是这么度过的。只要不下雪,天冷还没什么问题,从头到脚全副武装起来,骑上单位配发的那辆破自行车,总能赶上食堂的午饭时间。下雪天就不行了,全靠步行,回去时只好吃食堂剩下的残羹冷饭了。
那天,外边嘎嘎冷,偏偏收到的转账支票特别多,进账单写了那么厚一摞还没写完。办公室冻手,我就到资料室继续写。安放在外面跟那帮同事扯什么我也不知道,不时传来嘻嘻哈哈的笑声。我恨不得马上就写完,但却没法集中精力干活。电话铃响了,听出是安放接的,然后他大声喊我的名字,原来是我的电话。是叶师傅打来的,说小洪你有四封信呢,怎么今天没着急呢。看一下时间,都10点多了,怪不得呢。我猜这几封信里一定会有斯漪的,心里就长了草,越急越出错,写错了好几张。等全部写完,都快中午了,安放正好没事儿,就陪我一块儿去存支票。存完了工行和建行的,就中午了,若赶回丝绸厂食堂,恐怕也吃不到热乎饭菜了。哥儿俩索性给自己改善一下,找了一家小饭馆,点了一个猪肉血肠炖酸菜、一盘麻辣豆腐、一个甩袖汤,再加上刚从电饭锅盛出来的热气腾腾的米饭,两个人吃得喷香。
其实我是想吃完午饭先到收发室去取信的,但是眼瞅着1点钟了,银行已经开门营业,我们就按惯常的路线继续去农行和农村信用社存支票,然后才到局收发室把信拿到手。看到这四封信是大师兄、胖子、“亲家”和臭脚老五寄来的,却没有斯漪的来信,心里微微有些失望。叶师傅还让我把营业站同事汪泳的信也一并捎回去。回去是往北走,又是顶头风,我骑自行车,载着安放,累得呼哧呼哧直喘。到了营业站,手冻得像猫咬一样,都麻木了,不听使唤了。先不急着记账,而是把信一一拆开来看。那时候我已经练就了一种拆信的本领,就是用刀片慢慢拆,这样最终几乎能够保持信封的完整。这几封信无非是通报彼此的情况,问问下一步打算之类。最后这封信的字迹很陌生,我拆开以后才发现自己给拆错了。原来是下午汪泳不在,我顺手把他那封信也给拆开了。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去资料室,跟安放说起这件事情。安放说,你又不是有意的,无所谓吧。我俩又开始一起研究这封信。仔细看时,写的是“转汪洋(收)”,原来是写给汪泳弟弟的。字迹很娟秀、工整,我想应该是个女生写的,而且这个女生跟汪洋一定有某种亲密关系。这么一闪念,我被一种好奇心和恶作剧的巨大力量所驱使,也不管那么多了,干脆把信打开来看。果然,先前的一些猜测得到了证实。这女孩文笔不错,通篇都使用一种很温和的口吻,俨然就是在回忆他们俩之间青涩的爱情故事。两个人是高中同学,也很要好,就是早恋的那种关系吧。高考时她考上大学去了外地读书,而汪洋却落榜,正在复读。到后来,没有看到鼓励的话语,却变得有些闪烁其词。在信中,这个大一女生这样写道:“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些什么,我没法给你任何承诺。”“即使明年你真的能够追随我来到这个城市,那又能怎样呢?”她还说:“一切随缘吧!其实只要我们之间有缘分,又何必在乎这些那些呢?”这个女生就像个哲学家,说的全是冠冕堂皇的话,精彩却又空洞。我把这几句念给安放听,安放说,嗨,女人有时候可真是聪明而狡猾啊!我附和道,是呀,所以只有女人能成为母亲而男人不能。当我把信照原样伪装好,忽然觉得这个轻飘飘的信封变得沉甸甸的。

大连鸟语林,作者与张驰、李舒慧、巴音博罗、少梅、万胜等一起参加2830活动
这个寒冷的晚上,我一个人来到营业站资料室,继续写信,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斯漪:见信如晤!
我已经二十九天没有收到你的只言片语了,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也很想你。天真冷啊,你要记得多穿衣服,小心别冻着,别感冒了……
晚上我回到丝绸厂宿舍时,看到楼梯另一头女工宿舍那边吵吵嚷嚷、骂骂咧咧的,有一个穿军大衣的青年在敲门、踹门,还不断高喊着一个名字,好像是“郭艳”或者是“宫艳”的。走廊里冷飕飕的,有人探出头来看看,又赶忙缩了回去。我回到房间,小高、小赵也正跟安放议论这事儿呢,也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据说是跟搞对象有关。
从这天晚上开始,我失眠了。
不管天气如何寒冷,工作还得继续,扯闲篇也得继续。扯闲篇是玉城人悠闲散淡的基本表现形式。在丝绸厂宿舍,小高、小赵、安放和我,时间长了,就混熟了,聊得也很起劲儿,话题不外乎工资、福利待遇、自学考试、女朋友、工作、未来打算,诸如此类。上班时,在营业站,只要我们一闲下来,也会天南海北地闲扯。天冷,感叹暖气烧得不热是最主要的话题。老于说得有些夸张,说今年还不算最冷的,说他有一邻居,那一年赶上了大冷天,出门没戴棉帽子,耳朵都冻僵了,回到家赶紧到火炉边上烤烤,结果一扒拉,耳朵掉下来了。不过今年这天也够冷的,老于开始编排小佟,听说那天你去上厕所,尿还没落到地上,就已经冻成热气腾腾的冰棍了。同事们还张罗要给我跟安放介绍对象呢,看我们俩都不搭腔,才作罢。最关心的是涨工资的事情,这个话题长盛不衰。也谈起过老沈停薪留职对缝儿倒腾钢材水泥古董邮票之类,赚了大钱。等等。
安放讲的这个故事,全营业站的同事们都有耳闻,只是我没有听说而已。虽然各自的版本不同,但事件的脉络却基本一致,他们在安放讲述的时候还相互补充和印证。这个故事是安放在丹东电业局实习时亲耳听到的。
话说骄阳炙烤的六月天,在本溪的某个地方,有个老头儿进山挖药材,发现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吊死在一棵歪脖树上,马上报了警。警方经过现场勘查,发现一封遗书,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最后的结论是自杀。
很快,两个人的身份得到了确认,正是不久前丹东失踪的那两个人。女人是市内供电局营业窗口的一名登记工,她长得又老又丑,性格也很孤僻,常常一整天都说不上一句话,同事们往往会忽略她的存在,用户们找她办业务时也都小心翼翼的。忽然有一天,女人却在一个男人的床上,被男人的女儿无意间窥破私情。从遗书中得知,这种私情已秘密保持了二十多年。男人的女儿于是跑到营业厅去大叫大骂,骂得花里胡哨的,中心思想是这个老丑八怪女人勾引了一个好男人。这让她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她在遗书上写道,多少年来,一直在白眼和冷漠中煎熬,只有他从未嫌弃她,经常给她温暖和安慰,两人堪称知己,跟他在一起她才重具生命,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女人说,既然这世道容不下我们,那么只有一死了之,但我们不后悔,有他对我好了二十四年,我知足了。
不久之后女人和男人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遗书上说,她和他在漂泊的悲凉中享受着爱情的欢愉,直到生命最后一息。用一根绳索悬吊住两条鲜活的生命,那是他们在以死来抗争这命运的不公。他们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是这样的声音:“我不怪孩子,她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亲人们,永别了,保重!”
这故事虽然发生在炎热的夏天,但我如同薄衣单衫站在外边的冰天雪地中瑟瑟发抖,内心似乎坠上了巨大的冰块,感到无比凄凉与沉重。这种感情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所不容,可是最痛的伤害竟然来自家人,两个无辜的灵魂系于一棵树枝上,这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当天晚上,我在营业站资料室,给斯漪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斯漪:见信如晤!
我已经四十六天没有收到你的信了。那天好不容易通过113挂通了你的长途电话,我又听到了你柔柔的、甜甜的声音,知道你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这个冬天太冷了,我不在你身边,你要多多保重自己。不过亲爱的,你还是给我写封信吧,别让我总这么惦念着你……
今天听到同事们讲了一个市局营业女工跟人私奔殉情的故事,这件事情在本溪和丹东都传得沸沸扬扬。心情很复杂也很感慨,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乐府诗集》中的一段,抄录下来,亲爱的,让我们共勉吧: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
我遭遇的失眠,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我通常会在晚上11点之前,裹挟着寒气回到丝绸厂宿舍,有时候安放和小高他们都没睡,就随便扯一会儿;有时候他们已经熄灯了,我就蹑手蹑脚进来,脱衣上床,尽量不发出大的声音,免得影响他们休息。但是,躺在床上,我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开始还尝试着数数羊的只数,后来连这个努力也放弃了。我变得毫无睡意。同宿舍的三个人都不打鼾,所以我睡不着也赖不着他们。其实也许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寒冬的夜晚,房间里很静,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翻身时被子窸窸窣窣的声音。更多的时候,我是一动不动,瞪着眼睛,仰望着天花板。尽管是在冬天,但还是觉得天花板上那个布满灰尘的蛛网上,偶尔有轻微的颤动,我固执地认为,那儿一定是有一只蜘蛛在冬眠,也许在不经意间伸了伸懒腰。我很焦灼,或许很亢奋,不知道什么时候入睡,有时候都能明显感觉到房间里的温度在一点点降低,因为供暖的锅炉到了后半夜就不烧了。连我自己都无法解释,早上我竟然会按时醒来,每天大约只睡四个小时,白天却从来没困过。这不是偶尔出现的情形,而是整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我都会失眠。并且这个冬天,我居然从来没做过梦,而我多么希望,我的爱人能入我梦来……
那天10点多就回到绸厂宿舍了。因为停电,我在资料室点着蜡烛,写了一封短信,还有一首长诗(姑且称为诗吧)。我又一次看到了那个乱糟糟的场景,几个经警挥舞着手电筒,正把那醉醺醺的军大衣男子推搡到楼下去。这成为宿舍里又一次闲扯篇的当然话题。房间里冷,大家就用这个故事来维持温度。小高梳理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这哥们儿是某部的党员司务长,和那个宫艳(不是郭艳是宫艳)谈恋爱没少花钱,两个人的进展很稳定,都要谈婚论嫁了。谁知等到商定的婚期临近时,两家竟然发生了矛盾,女方一家翻脸不认人,跑到部队去揭发他侵吞公款。这哥们儿也不争气,还真让上面给查出来了,他被撸掉军籍和党籍,灰溜溜回到玉城。他不甘心哪,于是他天天借着酒劲儿过来闹,就想要回花在宫艳身上的那些钱。
那边安静下来,他们三个也都觉得大快人心,这下就能睡个安稳觉了。他们酣然入梦,只有我内心在翻江倒海,我躺在没有多少温度的被窝里,瞪大眼睛呆望着天花板上的蜘蛛网,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蓦地,我感觉心脏被一种前所未有的烦躁、亢奋、渴求、忧伤、虚无、憋闷、绝望给击中了,我居然满身大汗,仿佛后来身处桑拿房中,热气蒸腾,溽热难当,张大了嘴,却喘不上气来……
多年以后,我开始经常出入玉城的大小洗浴中心,比较好的包括乐雪、圣水龙庭、潇雅、十洲云水、云龙碧水、祥和等。不知什么原因,无论春夏秋冬,我总是觉得身上黏糊糊、脏兮兮的,唯有不断冲洗,才能保持某种干净,或者平静。每每在桑拿房里蒸得大汗淋漓时,我总会想起1989年那个冬夜,那个寒冷彻骨却让我汗湿被衾的失眠之夜。我的心情以及当时的具体情境,都能从那时的日记和信件、诗稿中得到佐证。在某一篇日记中,我这样写道:是夜停电,在资料室秉烛夜读,并写诗及信各一。翌晨,鼻孔成二黑洞,自诩此亦为爱情也。
所谓的诗,就是《致C的诗之五:祈祷词》,写了一百多行呢,下面是节选:
那夜停电停水还停暖气
我饿着肚子在模糊的四壁里突围
白蜡烛的微光瑟瑟发抖
我幽幽的喟叹也结了冰碴儿
这个夜晚 我一万个心愿
全冻得更坚硬 更顽固
……
请让我 在狂飙摇落之前
化为一件蓝色的风衣 温柔地围裹你贴紧你
请让我 在黎明莅临之际
披散一头蓬乱的长发 在你的山涧里沐浴
请让我 在浪迹天涯的岁月中
栽种一个忠贞的想往 于你丛芜而丰腴的处女地
请让我 在我们共同缔结的生命里
将一切都依托在你胸前 我真想酣睡
在无数的冬夜里 我因此 虔诚地祈祷——
别让我一个人走在北风里
别让我一个人独处这小屋
别让我久久听不到你的声音
别让我久久读不到你的来信
……
(蛛神啊!我向你祈祷,请降隽永的吉祥喜庆顺遂如意……给我和我的爱人吧!只要能,我甘愿进奉我的身体,做你的牺牲……)
那封短信,当然也是写给C的,喏,也就是斯漪。从秋天到冬天,一直持续到春节后,我给她总共写了三十七封信,通常每一封信都在三千至五千字之间,总字数在十三万左右。只有这封编号为34#的信很短,才寥寥数语,抄的是“尾生抱柱”的典故。没有抬头和落款,全文如下:
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庄子·盗跖》
那个春节过后,我中断了坚持了好几年的记日记的习惯。其实,不记日记也罢,有些东西总会刻骨铭心的,而另外的某些东西,还是让它随风而逝吧。多少年来,如果提起跟整件事情有关的,还有这么两桩小事,可以补记如下:
一、安放在第二年的夏天离开了玉城供电局,调到了新组建的盘锦电业局,去的还是物资科,干的是专业对口的工作。这是个很好的归宿。只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哥儿俩从来也没有唠过,他离开玉城,除了专业的考虑,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别的原因。从各方面的蛛丝马迹分析,我认为是有的,比如说,他是到另外某个地方去“安放”他的青春和爱情去了。
二、我还写了一篇小说,故事梗概是:一对恋人在大学期间相爱,毕业后,男生分配回W城某单位,而女生则分配到M城某单位。但是,为了爱情,那个女生义无反顾追随着男生来到W城。因为女生放弃了工作,两个人婚后过着清苦的生活,但在我看来,两个人的日子过得很幸福,很甜蜜。这个故事并非纯粹的虚构,主人公的原型就在玉城的建行,男的姓田,女的姓邰,一个很少见的姓。对于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境况,我不敢妄加臆测,但为了对他们的爱情表达敬意,男的我给取名为田相如,女的给取名为邰文君。这篇题目叫《当爱滴水成冰》的小说,后来并没有发表出来,现在连原稿都找不到了。
责任编辑 铁菁妤
——以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为例
——由“收发室”到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