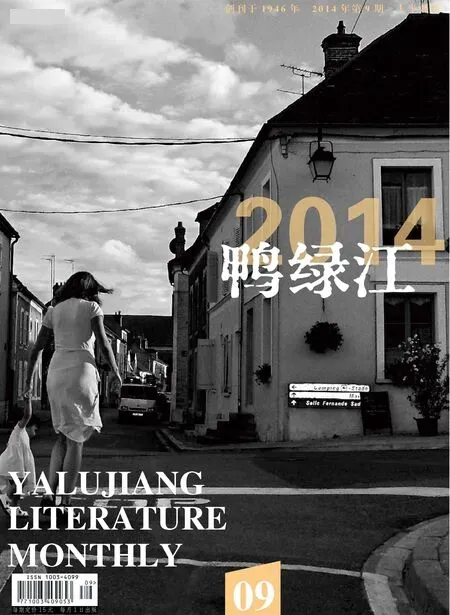关于杨心安的五段叙述
杨献平
关于杨心安的五段叙述
GUANYUYANGXINANDE WUDUANXUSHU
杨献平


1
日光渐烈,南太行乡域内草木竟发。母亲说,村后有一面荒坡分给了咱,除了那一片橡栎树不能动,其他地方可以翻松一下,买些板栗树苗栽上,三五年后就能结栗子了。好多年来,南太行乡村远近各地的山坡上,大都在坡上栽种了板栗树。树多的人家,一年可以卖到十几二十几万块钱;少的,也有个二三万、三五万。这在没有矿上资源和其他企业的偏僻乡村,基本上算是一笔主要的收入。
说干就干,吃了早饭,我跟在父亲后面,扛着钁头洋镐,踏着满河沟的鹅卵石,走到那面荒坡上面。十多年前,政府一声令下,禁止养殖牛羊马驴等家畜。村人听话,一夜之间就把朝夕相伴了几百年的家畜们杀的杀、卖的卖。两年工夫,以前总是被牛羊啃得光滑的山坡上就密不透风、草木参天了。这面荒坡上也是。我和父亲放下钁头洋镐,面对蓬乱群草和张牙舞爪的荆棘,一时间不知道如何下手。
我给了父亲一根香烟,自己也点了一根。我说先歇歇吧。父亲嗯了一声。俩人每人找了一块石头,坐上去,抽着烟,看对面的山坡、头顶的天空。烟抽了半截,父亲说,那个杨心安去年死了,你知道不?我啊了一声,脑子引擎发动,在记忆的众多影像中搜索那个叫杨心安的人。
那人个子很高,眼睛不大,但很圆,看人的时候,一会儿里面好像燃着一团火,一会儿又像结了一块冰。最典型的该是皱纹,不只是额头眼角,而是满脸。头上经常包着一面白毛巾。从我记事起,他就那一幅形象。不仅是他,村里和他年纪差不多的男人都是那样一副形象,以至于他们给我留下的一个鲜明印象是,即使人老了,也还和死亡有着很长一段距离。
关于他,爷爷给我说过。按照年岁和辈分,爷爷和杨心安算是叔伯兄弟。杨心安可能大爷爷两三岁。当然,说他的时候,爷爷是背过杨心安的。当面说别人的往事,说好的行,说不光彩的,伤人不说,对方肯定反驳,互骂几句倒没事,伸胳膊舞脚地打起架来肯定两败俱伤。
小时候,每天晚上,我都和爷爷奶奶一起睡。睡前,叫爷爷讲故事是一门功课。有一次他说到一件事。村里的杨心安以前和他是同学,读同一家私塾。杨心安的娘姓赵,叫蓝妮子。有个毛病就是好吃,哪怕是上茅房,嘴里也要嚼个东西。儿子学娘。上私塾时,先生讲得摇头晃脑。杨心安一边仰着个脸听,一边嚼干柿饼。所谓的干柿饼,就是去年摘下的柿子,在房顶上风吹日晒一个秋天和一个冬天后,水分跟着风和日光私奔了,就成了柿子干。很硬,但越嚼越甜。比糖块好吃。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1973年生。O型血,金牛男。作品见于《天涯》《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山花》《诗刊》等刊,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长篇文本《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丝绸之路》(中英文版)、《匈奴帝国:刀锋上的苍狼》,散文集《沙漠之书》《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生死故乡》等。现居成都。中国作协会员。他对文学的认知是:“文学写作其实就是一个人面对整个世界调情,用各种技巧、语言和角度,把人心中暗藏的水花撩起来,把人的精神和思想当中最幽秘和妖艳的部分逼到纸上来,遣送到文字当中去。”
杨心安吃就吃吧,还偏偏发出声音。每一次,杨心安都是把腮帮子甩得邦邦响。把干柿子吃成了肉!第一次,先生停下“之乎者也”,先是竖着耳朵听,两脚往发声的地方走。明知道是杨心安,但还是在他跟前转了一个圆圈后,戒尺猛地一颤,就啪的一声,落在了杨心安的脑壳上。第二次,杨心安还是没忍住。先生叫他到前面去,站好,伸出俩手心,一个手心一戒尺,敲鼓一样敲了十几下。杨心安咧着个嘴,没敢叫出声来。可往座位走的时候,嘴巴又开始甩着腮帮子嚼起了干柿子。
2
父亲抡起洋镐,当的一声,冒出一串火星。我知道,镐头遭遇到了石头。我也抡起来狠狠刨下,又是一串火星,刺得眼疼。南太行山区一带的山,大抵是第四纪以来玄武岩浆多期溢流后形成的,向阳那面坡上多赤红和褚红色岩石峭壁,背阴的坡上多青色悬崖。只有山坡与河沟交界处,才有些土壤较多的斜坡,算是缓冲。父子俩刨了一阵子,热汗立马围剿全身,手臂酸麻。坐下来歇息时候,父亲指着橡栎树林旁边隆起的一座土墩说,杨心安就埋在那个地方。
南太行乡域,人死之后,还是土葬,且对风水特别看重。父亲说,他小的时候,杨心安是莲花谷评剧团的小生。这和爷爷讲得很一致。当年,杨心安和爷爷等少数几个年轻人一起读私塾。按照各自爹娘的想法,是让儿子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功名,能当上官当然更好,当不上,在乡里也有地位。谁知道,杨心安嘴里的柿子干还没有嚼出味道来,轰隆一声炮响,辛亥革命发生了,皇帝被掀下龙椅,屁都不是了。消息传到莲花谷,爹娘们分别哀叹一声,然后让自家孩子扔了书本,老老实实地当起了“拱地虫”。这个说法,是莲花谷人对农民身份和职业的形象比喻,意思是,当农民,就是弯着腰,抡着钁头锄头,一辈子跟泥土石块过不去。
我一看,不大的橡栎树林下方,斜坡与旱地连接处,有一个凸起的小土堆,不高,但像一个成年人躺倒的形状。不由得心惊了一下。同类之间的死亡总是引发伤悲。所谓物伤其类,大致是这个意思吧。父亲说,杨心安年轻时候也算是咱这里的一个有名挂号的风云人物。不读私塾以后,学唱戏。这人学啥都很快,不几年,就是剧团的顶梁柱了。可他只演一个角色,那就是皇帝。叫他客串一下别的角色,一次都不肯。有一次在外地演《打渔杀家》,一个演员临时拉肚子。还不是一般的拉,直拉得雷声震天,腰如弓,连裤子都提不起来,根本上不了场。团长让他客串一下,先对付过去再说。杨心安哼了一声,脖子一横,头一甩,理也没理团长,抬脚就出了化妆间,到戏台下面和一个认识的人拉起了家常。
团长气得直蹦,他就是不理。没办法了,团长亲自上,才把观众糊弄了过去。晚上吃饭的时候,团长说,你杨心安有啥了不起,不要以为老子离开你这泡狗屎就种不了地!杨心安也不生气,笑眯眯地看着气呼呼的团长说,你说对了,我这泡狗屎就不是用来给你个狗日的种地的。即使下贱到种地,也不给你狗日的长粮食!团长的脸先是红,后是紫,忽地站起来,拳头紧握就要冲上去揍杨心安。副团长一看架势不对,上来拉住团长说,老哥哥,算了算了,心安就那么个脾气,再说,他不演,咱不是还有人演吗?
我笑说,这个人也挺有意思。要是我是那个团长,一脚就把他踢回家了!
父亲说,即使被团长踢回家,杨心安也不怕。他爹是个小财主,光别人见到的银元就有好几大罐子。虽说杨心安弟兄俩,可二弟四五年前跟着石友三当兵去了,都那么长时间了,连个音信都没有。人都说,估计死了。弟弟死了的话,他爹存再多的银元,也有不在人世的那一天。那时候,啥也带不走,还不是他杨心安受了?再说,杨心安那皇帝演得确实是好,一出场,就把人给震住了,掌声和呼声热得能蒸熟鸡蛋,那步子走的是九五至尊,架势拿的是龙凤之态,唱的是响遏行云,念的是江山风流。特别是那些不懂戏乱哼哼的老娘们儿,还有好事的小妇女和大姑娘,开始还坐着嗑瓜子,一看杨心安扮皇帝上了戏台,立马弹簧一样蹦了起来。
3
爷爷还讲过,因为演皇帝,杨心安给自己办了一个好事,却给村里带来一个损失。两件事相比较,一个是个人的,另一个是家族的和国家的。有一次,杨心安随着剧团去山西辽县,就是现在的左权县大南庄村演出。这个村子,和我们莲花谷只隔了一道很高的山岭,差不多一天时间可以翻过去。大南庄村就在山的背面,一色的黄土,只长玉米谷子豆类高粱和土豆。那一带人要想吃面,得背上玉米、谷子和土豆之类的粗粮,翻过山,到我们这边来换。当然,有钱也可以买到面粉。因为这一点,我们村里人都觉得自己的生活比山西那边好。
演了几场戏,杨心安演的皇帝也受到了山西姑娘小媳妇的欢迎。一个晚上,杨心安卸了妆,去茅房时候,经过一个小巷道,尿憋得他没法不夹着屁股快点走,到拐角处,迎面撞上一个人。他人高马大,只是打了一个趔趄。那人却“哎哟”一声,斜倒在对面墙上。听声音,是一个女的,而且年龄不大,声音脆脆的、亮亮的、嫩嫩的,还娇娇的。杨心安立马抢过去,赶在对方身体就要倒地之际,伸出一只胳膊,把人接住了。
没事吧?杨心安说。
怎么没事?对方有些恼怒地说。
你看这,俺不是故意的。杨心安有点示弱地说。
啊……嗯……
对方打了一个缓冲。然后说,你就是那个演皇帝的吧?
听了这句话,杨心安兀自来了信心,说,你怎么知道的?
听声音就是你!
杨心安哦了一声。
俺叫朱月娥。你演得、唱得咋那么好?朱月娥说。
杨心安笑了一下。
不久,朱月娥就成了杨心安的未婚妻;再一年冬天,就骑着毛驴,翻过山,成为杨心安的老婆。
我管杨心安叫爷爷,朱月娥就是奶奶了。
朱月娥是很漂亮,水蛇腰,瓜子脸,眼睛看人一下,魂儿都会跑到头顶上去转三圈才能回到原位。唯一不好的是,朱月娥鼻翼周围有一圈黄褐斑,虽然不明显,可那也是个破坏。可是,哪个人都不能十全十美。十全十美了,老天爷心里也过不去。
至于杨心安带来的损失,大概是一个莫须有的猜测。南太行莲花谷一带,不论是做啥事,都要先找个阴阳先生算算,起房盖屋娶媳妇埋老人之类的人生大事更不用说。很多年以前,一个秋天的傍晚,村里忽然来了一个男人,说话舌头打卷,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半舌头上滑下来一样。
那时候,大概是1937年左右。人的缘分,往往很蹊跷。比如那个陌生人,村里五十六户人家,他偏偏去了族长杨大拿家。杨大拿是杨心安的叔伯爷爷,家境也算殷实,见来人饥肠辘辘,便叫老婆给他做了一顿饭,并留宿一晚。第二天上午,那人走到村口,又折转回来,对杨大拿说了一番话。他说他是一个风水先生,从武安那一带过来,走到莲花谷这里,忽然很惊奇。说这里四面环山,高低参差,错落有致,尤其是莲花谷村后面和左右那山势,那是龙脉。说不好,这个村子里会出一个皇帝。村人历来热心功名,对历朝历代帝王将相的事迹津津乐道,虽然身在山区,与朝代更换、世界大势、从没有半片指甲盖的关系,但要说起成王拜相、状元探花榜眼之类的,一个个比打了鸡血还要振奋。
听那人这么一说,杨大拿来了兴趣,俩眼瞪得好像铜铃铛,又让老婆拿出自己都不舍得喝的清源小茶,给那人沏了一杯。那人说,依照你们村的风水,这个皇帝该是成形了的。这一句话,让杨大拿好生失望。脑袋转了好半天,才想到,自己的亲侄子,杨心安的亲弟弟杨凤喜,也就是参加了石友三部队的那个。除了他,村人男女老少都在村里,一个个比碾盘还老实。旋即对那人说了实情。那人起身,捋着下巴的三根胡子,沉吟了一会儿,神情严肃地说,这绝对不可能!
杨大拿失望地笑笑,对那人说,确实没有!
那人又说,这村里有唱戏的吗?杨大拿说,这个倒是有。也是俺家亲侄子,专门演皇帝。那人呵呵笑了一声,说,那就对了。
4
从这时候开始,杨心安这个名字就从村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假皇帝”。这个绰号里面,有戏谑,也有怨恨。有的人说,好端端一桩美事,让杨心安一个戏子给坏完了。还有的说,即使杨心安不演皇帝,袁世凯完蛋了,日本鬼子都进中国了,到处战火腾腾的,哪儿还有皇帝?
事实上也是。但还是有人不死心。私下说,要是咱村出个皇帝的话,估计全国各地都有人来给咱送奇珍异宝,到那时候,咱就是唯一能够跟皇帝说上话的人。那可就美死了!
可这话还没说完,五十里外的孔庄就被日本鬼子给烧掉了,全村死了三百五十五人。其中,十二户灭绝,四十多个人被堵在洞里烧死,一百多人被鬼子机枪扫射,最惨的是有两个妇女,被鬼子强奸了还不算,临了还把肚子挑开了(即1938年4月11日日军在在河北沙河孔村制造的“孔庄惨案”)。对这样的事情,莲花谷人从没听说过。几乎一夜之间,村子就空了,人都跑到山里,寻石洞躲了起来。杨心安带着老婆朱月娥,还有老爹杨大双、老娘蓝妮子,也在后山躲了起来。可连续几天,天还是一样的天,风还是刮,没一点不好的征兆。
石洞潮湿,也阴冷,还窄小,人都直不起腰。一个傍晚,蓝妮子拿出小铁锅,先到河沟里弄了水,然后爬到山顶上,点火煮鸡蛋。杨大双和杨心安两口子都呵斥她,可蓝妮子说,几天了,连个鬼子毛都没见,再说,咱这里山高林密的,鬼子就是来了也找不到这个地方。说着,就擦着火镰,燃起来茅草。一股青烟就腾了起来。杨大双和杨心安趴在洞口瞪着眼四处张望,凡是能看到的地方都看了个遍,山里确实没有动静,也觉得有点大惊小怪。谁知道,他们刚一回头,就传来一声枪响。
村人没命地奔跑,向着更高的山上。所幸的是,没见有人追来。后来村人才听说,那一次,就十几个鬼子到了莲花谷,要是大部队的话,村人哪里还有命在?命算是保住了,可房子被烧了,鸡鸭猪牛羊和粮食也没了。村人说,房子烧了可以再盖,粮食没了山上有树皮草根,只要有命在,啥事都好办!
这一个情节,是爷爷讲给我的。
当时,我躺下黑夜里,听他的嘴在旁边发出声音。说到孔庄惨案时候,爷爷还多了一句旁白:幸亏咱村里没出事儿。
他的意思我明白。
过了好久,我才说:就十几个鬼子,村里几百个人,怎么也把他们弄死了!
爷爷叹息一声,吧嗒一下嘴唇,说:鬼子大部队来了咋办?
我无言以对。
1942年,杨心安和朱月娥的女儿降生了。取名叫杨爱花。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村里忽然看到,村子对面的山岭上来了一支队伍,稀稀拉拉的,好像是从邢台方向过来的。几个胆大的人多看了一眼,觉着不像是日本人,才长出一口气。即使这样,有胆小的还是栓了门,躲在炕角抖得像米萝筛粗糠。那部队沿着村边向山西方向走了,没有一个人到村子里来。
后来听说,那就是石友三的部队。
可杨凤喜还是音信全无。
这时候,因为兵荒马乱,杨心安所在的评剧团也解散了。杨心安就守着朱月娥,抱着女儿,村前村后地转。有时候来了兴致,就在自家院子里摆开架势,咿咿呀呀地唱上一段《打金枝》《贵妃醉酒》之类的。村里其他人看到了,就说,这皇帝演得还真像个皇帝。要是真的皇帝,那该多好啊!杨心安听了,笑着说,皇帝皇帝,皇帝个屁,这年月,有脑袋还能吃饭比当皇帝还好!
5
顶着烈日回家,吃饭时候,又说起杨心安。母亲说,“假皇帝”也是一辈子的能人,唱戏演皇帝,红遍咱这十里八川。
可是结局不好。
据爷爷说,抗战那些年月,我们莲花谷附近村里倒是没有遭受过太大的杀戮。只是前坡村一个张老头,耳朵聋,腿脚又笨,又是光棍一个,日本鬼子来时没人管,就没跑掉,当场被砍了头,血喷得一人多高。同村的还有智障人,被鬼子用刺刀不知道捅了多少次,胸脯都成筛子了。
其他村里,倒还平安。
解放战争虽然也很激烈,但莲花谷这边,也没受多大影响。
天下太平没几天,剧团又组织起来了。可还没演几场,就又解散了。从那时以后,“假皇帝”杨心安就再也没上过戏台。这倒没啥,最可怜的是,杨心安的家产被充公了,他爹杨大双连病带气,一下子就过去了。一年多后,他娘蓝妮子也还嚼着一块柿子干,闭上了眼睛。
奇怪的是,杨心安和朱月娥生了女儿杨爱花以后,再没生养。
以前富富裕裕的人家,一下子虎落平阳、龙困浅滩。水田充公了,旱地也成了集体上的。银元也被工作队没收了。说是支援国家建设。大概是心里不舒服,一个人到山里干活或者在门前晒太阳的时候,杨心安清清嗓子,拿腔作势地对着空荡荡山谷清唱一段《林冲夜奔》:“欲送登高千里目,愁云低锁衡阳路,鱼书不至雁无凭,今番欲作悲秋赋。回首西山日影斜,天涯孤客真难度,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唱着唱着,忍不住放声大哭。村里很多人奇怪,杨心安不是只演皇帝吗,怎么唱起了林冲的台词?
1960年夏天,莲花谷先是下了几天的暴雨,半个月还不停,山都软了,有的悬崖都倒塌下来。石头乱滚,山洪大得转眼之间就把整座房子冲得干干净净。好不容易等到天晴了,又闹蝗虫,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多,黑压压的,跟乌云一样,凡是路过的地方,草都光了。村人一开始吃榆树皮、橡栎树籽、挖草根,后来吃观音土。观音土能咽下去,可就是拉不出来。
再后来,莲花谷一带人都往山西逃荒。因丈人家在山西,杨心安一家比起其他人要好过得多。到山西老丈人家住了几个月,临回来时候,丈人还给了他几十斤玉米炒面,还有十几斤玉米种子。别人家还在吃了上顿没下顿,孩子老婆饿得嗷嗷叫的时候,杨心安家还有吃的。
也就在这时候,一个小伙子来到了莲花谷。
他以前的名字没人知道,做了杨心安的干儿子后,人人都知道他叫杨家兴。
那是一个个子矮小的小伙子,老家河南滑县,也是闹饥荒,没吃的了,家人各自出外寻活路。误打误撞地撞到杨心安家,杨心安给了他一点吃的,看这个孩子还算可以,就认作了干儿子。
这类情况,在莲花谷有十多个。
杨家兴比我父亲小一岁。我叫他叔。

自从我记事起,就听说,杨心安和养子杨家兴关系不好。谁也不理谁。有时候,杨心安和朱月娥一起,杨家兴和他老婆一起,四个人站在各自的院子里对骂。啥脏话都顺嘴往外喷。村人说,这叫啥老子儿子、婆婆儿媳,还不如个二家旁人呢!我总是觉得,儿子儿媳骂公公婆婆总是不对,即使不是从人家肚子里面出来的,也有救命、养育的恩情吧?再说,杨心安还给他盖了新房,娶了媳妇。一个讨饭跑到这里的人,有人这样对待自己,已经是天高地厚的恩情了,在养父母跟前,还有啥委屈不能受的呢?
可杨家兴不,他老婆也不,和我同龄的女儿也不,直到杨心安癌症卧床不起,杨家兴一家也没去问候一声,直到他死。据人说,临死那天夜里,昏沉了几天的杨心安忽然醒了过来,精神也特别好,还吃了一大碗米粥。到半夜,陪护他的女儿杨爱花和女婿正在鸡啄米似的打瞌睡,忽然听到杨心安口齿清晰地唱《定军山》:“这一封书信来得巧,天助黄忠成功劳。站立在营门传营号,大小儿郎听根苗:头通鼓,战饭造,二通鼓,紧战袍,三通鼓,刀出鞘,四通鼓,把兵交。上前个个俱有赏,退后难免吃一刀。众将与爷归营号,到明天午时三刻成功劳。”
就差 “功劳”二字没唱出来。
下午和父亲再去那里干活,忍不住看了一眼杨心安的坟堆,想起他的事情,不由得叹息了一声。父亲告诉我,杨心安老婆朱月娥还活着,只是不能说话了,一直住在邻村的闺女家。
责任编辑 叶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