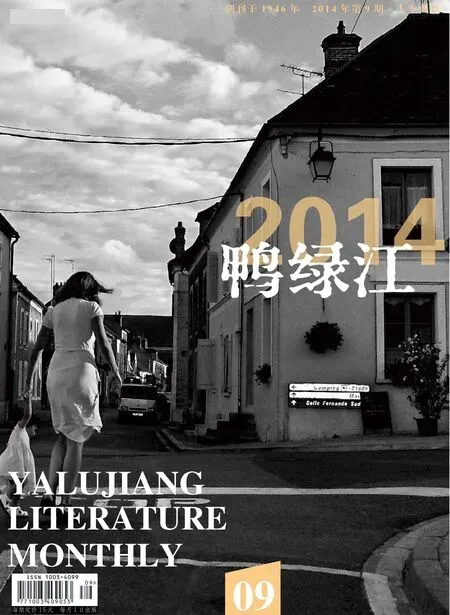云雀·白头翁
韩开春
云雀·白头翁
YUNQUE·BAITOUWENG
韩开春
云雀
云雀:雀形目百灵科云雀属,别称告天子、告天鸟、朝天子等。
从我家去李口街上,黄夹滩是必经之地——过了高松河就是。黄夹滩得名于当年的黄河夺淮,后来黄河改道后就有了废黄河,就留下了这么片河滩地。当年混浊的黄河水汹涌而下,裹挟而来的大量泥沙如今还滞留在这片滩地上,就使得这里的土跟别处的有所不同:细、白之外还很酥软,用手抓一把,会从指缝间簌簌流下;脱了鞋走在这沙地上简直就是享受,一脚踩下去,酥酥软软的,弄得脚底痒痒的不说,细沙从脚趾缝间挤出来,还有按摩的功效。夏天无论下多大的雷雨,雨刚停就能穿着布鞋走路——沙土里存不住水,一点都不沾脚。最妙的是小孩子在上面玩打架游戏,随便怎么摔都不疼,这沙土地就像是层厚厚的海绵垫,除了滚一身溏灰之外,也没有什么大碍了,衣服上沾了溏灰也没关系,爬起来拍拍掸掸也就没有了。所以小孩子们是很喜欢这里的。不好的地方自然也有,不起风还好,一刮风就是漫天尘土,风稍微大点,对面都看不见人,因此这里几乎长不了什么庄稼,大片大片的土地都撂荒了,除了一些杂草外就是一些灌木了。说也奇怪,沙土地上别的庄稼长不好,倒是有一种夏天会开紫花的叫作苦草的植物长得茂盛——农民们种它来做绿肥,用以改良土壤。
孩子们喜欢黄夹滩,除了这沙土地之外,还有这片苦草地和灌木林。因为远离村庄、远离人烟,这里就成了各种小动物们的天堂,各种小虫子们自不必说,偶尔还会从苦草地里撵出一两只野兔来,还有各种各样的鸟儿,比如画眉、云雀、鹌鹑等等,要么在小灌木林里安家,要么就在苦草地里做窝。每年春夏庄子上的大人来耕苦草地的时候,总会有小孩子们跟在后面玩,偶尔能在草丛中发现几个鸟窝,运气好的话窝里还会有鸟蛋,甚至可以抓到一两只刚刚学飞的小鸟。
云雀的家就在这片苦草丛中。那次,我在苦草地里捡到一只它的窝,是用一些干枯的细草编成的,里面垫了一些细软的羽毛和撕成细丝的草茎,像是一只小碗,谈不上精致却感觉很舒服,跟二哥掏出来的麻雀窝差不多。不同的是,麻雀窝是在人家屋檐底下,而这云雀的窝是在苦草丛中。
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差点就把它给认错了,那次近距离的猝然相遇,我差点把它当成了麻雀。这也怪不得我,平时,我都是只闻其声未见其形,至多也就能远远地看到个影子,再说谁让它们长得那么相像呢?是在苦草地的旁边,我看到沙土地上一个麻雀在跳跃——是的,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麻雀,一身麻麻灰灰的外衣,外加圆圆的头、尖尖的嘴,要是躲在枯草丛中,还真一下子不容易让人发现——这身装束、这个特征正是麻雀所具备的。刚看到它的时候我还纳闷,这个麻雀怎么跑到黄夹滩来了?通常它们也就在家门口转悠转悠,一会儿飞到东一会儿飞到西的,像是一群调皮的小孩,要么就一大群飞到生产队里的打谷场上,趁看场的人不注意,偷吃几口摊晒在场上的小麦粒;要么就飞到草堆那边乱刨乱翻,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几粒漏网的麦粒或者稻粒。正常情况下,它们不会飞这么远,再说,这里一片苦草,也没什么好吃的,小虫?草籽?这些东西家旁边都有啊,又不是什么稀缺的东西,也犯不着要跑到这里来。就在我正纳闷找不到答案的时候,这只“麻雀”突然往下一蹲,紧接着就来了个旱地拔葱一跃而起,一支利箭似的直冲云霄,还边飞边叫,的溜——的溜——一长串清脆且带着颤音的鸣叫声不绝于耳,等我再抬头寻它的时候,已是一个小黑点悬停在我头顶上方了——像是一架微型的直升机,要不是两只翅膀一直在扇动,我大概会怀疑这个小黑点居然是一只飞鸟了。它一边振翅一边鸣叫,声音激越且响亮,过了一会儿,像是受了什么刺激或者是要故意向我炫耀它出色的飞行本领,又突然拔高,向着更高的高处冲去,要不是我一直看着它,或者它把嘴闭上,估计我都会不知道它在哪里了。这个家伙,果真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
看来,“云雀”的名字还真不是白给的,这么一手俊俏的飞翔功夫,就足令许多鸟儿望尘莫及了,如果再加上响彻云霄的鸣叫,估计许多鸟儿就只有佩服、崇拜的份儿了。所以,有的地方的人把它叫作“告天子”“告天鸟”或者“朝天子”,鲁迅叫它“叫天子”,都是很有道理的——它这行动,它这叫声,不是要向上天报告什么,就是要向全天下宣告什么啊。
而我老家的人叫它的名字就很特别了,唤作“的溜追”或者“的溜坠”。到底是哪一个或者这三个字到底是不是这么写,我都不知道,但读音肯定是这样的。我现在认真地想了一下,觉得这三个字无论是“的溜追”还是“的溜坠”,用来做它的小名都很贴切,这“的溜”像它的鸣叫,而一个“追”字,也很传神地反映了它一飞冲天的英姿,特别是它这一边飞翔一边鸣叫的本事,简直非“的溜追”莫属了,而“坠”呢?则是它的另一个过人的本领,要是你看到它怎么飞翔的,一定会想到这个字,它降落的姿势,用“俯冲”这个极具动感的词来形容都觉得不够,唯有这个“坠”字,才更形象传神,竟是如一块石头在做自由落体运动。从云雀在我老家的这一别名“的溜追”或者“的溜坠”作个联想,我突然很佩服我的父老乡亲,虽然这个名字很土气很俗气却很贴切很传神,看来,“真正的智慧在民间”果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韩开春,新闻从业人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A型血,摩羯男。江苏“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淮安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散文作品散见于《钟山》《山花》《散文》等刊,多篇作品被选为中高考语文试卷阅读题,入选多种散文年选。出版有散文随笔集《水边记忆》《虫虫》《陌上花开》《时光印记》等,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一年四季中,就数春天来临的时候云雀叫得最欢,站在我家门口,就能听到对面黄夹滩上“的溜追”响彻云霄的欢叫。不是一只,有时是两三只,更多的时候是一大群。它们在天空中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各展所能,尽显歌喉,仿佛是在参加一场盛大的比赛,抑或是一场争夺观众眼球的表演。是的,春天到了,鸟儿们也春心萌动了——它们也该有自己的小宝宝了。
因了它的这种独特的本领,喜欢它的人还真不少,特别受到音乐家与诗人的青睐。仅我所知道的,以它为题材的音乐作品就有这么几个:一个是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海顿所作的D大调弦乐四重奏;一个是同样伟大的舒伯特为它所作的世界名曲《听听,云雀》,据说,这首伟大的作品是一次作曲家在郊外饭店吃饭的时候,忽然听到云雀的叫声,突发灵感写成的;另一个来自罗马利亚作曲家旦库尼,他在小提琴的E弦上运用绝无仅有的颤音技巧,把云雀争鸣的画面表现得惟妙惟肖;英国的雪莱是位诗人,他在那首著名的抒情诗《致云雀》中,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热情地赞颂了云雀,在他的笔下,云雀就是欢乐、光明与美丽的象征。
白头翁
白头翁:雀形目鹎科。又名白头鹎。
家西老舅太是我敬佩的人,那么大年纪了身板还硬朗得像个壮年。通常是在午后,他会背着他那竹编的鱼篓去高松河底竹簖旁边巡视一番,看有没有哪个不长眼的鱼儿误打误撞闯进了他预先设下的迷魂阵,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像个小跟屁虫似的一溜小跑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看热闹。除了逮鱼,他还能耕田耙地,哪怕是生产队牛棚里那条最不服管的黑牯牛,到了他手里都服服帖帖像个听话的乖孩子,要不是他那满头飘飘的银发出卖了他,恐怕谁都不会相信这是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在时庄队,像家西老舅太这样的白头翁还有很多。
黄夹滩的野地里,生长着一种草儿,也叫白头翁,全身密被细长的白色柔毛,每年的二三月份开花,花萼蓝紫色,花瓣似的,有点像木槿花,很漂亮。但这不算什么,春天一到,黄夹滩的野地就成了天然的大花园,漂亮的花儿许多,你追我赶地,次第开放,很有点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的意思,很热闹,一点都显不出它的特别来。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果,许多的瘦果密集成头状,长在茎的顶端,披散着长长的银丝,怎么看都像是个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
通常情况下,时庄的老老少少对上述两种无论是人还是草都不叫“白头翁”。像我老舅太那样的老人,在庄子上辈分高年龄长,受到全庄人的尊重,谁见了都要恭敬地叫上一声“大爹”或是“老太”,不敢造次,要是有小孩背地里喊上一声“老头”,被家长听见了还要挨巴掌,至于“白头翁”,听起来像是古人的书面语,时庄没人这样用来喊老人。草呢?也不叫白头翁,时庄人看它长得毛茸茸的,就叫它“毛姑朵花”。倒是对于一种小鸟,时庄人的意见出奇地一致,异口同声地不分老幼,一概叫它“白头翁”。
这自然是跟它的长相有关,一身橄榄灰的羽衣,头顶黑色,却在两眼上方至后枕部一带,长有一宽条纹状的白色羽毛,黑白相间,十分醒目。年纪不大,就有了一大片惹眼的白发,就像那少年白头,看着都让人心疼,把它叫作“白头翁”,倒像是它生来就是个小老头。
但它真的不是生来就像个小老头,它刚从蛋壳里爬出来的时候,也是和所有刚出壳的小麻雀一样,红通通地光着腚,张着黄丫的大嘴巴,嗷嗷地等着爸爸妈妈来喂它虫子吃,然后才渐渐地长出羽毛。少年时期的白头翁,也没头上的那片白毛,虽然个头都跟父母亲差不多大了,头顶还是一片灰褐色,像那未经世事的少年,在父母双翼的庇护下,还没尝到生活的艰辛,单纯地快乐着。等它真正长成大鸟,能够独立成家了,父母亲狠着心把它从家里赶出去的时候,你看吧,这个时候它的模样已经和父母别无二致,顶着一头的白发,一个人去外面的世界打拼了。
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隐情,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什么事情让它想不开一夜之间愁白了头,是想到了世事的险恶?是想到了前途的未卜?莫非它也有过昭关的伍子胥一样的难处?青年时期看过于魁智的京剧《文昭关》,脑海里一下子就跳出了我少年时期生活过的时庄的那群叫作白头翁的小鸟来。
但我在认真地回想了一下当时我在时庄生活时的情形后得出结论,这些所有的想法都是我自己在杞人忧天,属于一个人的自作多情。那些生活在时庄的长着白头发的小鸟何曾有过一丁点的忧伤与悲凉?它们或三五只一小伙,或二三十只一大队,呼啦一下飞到东,呼啦一下飞到西,这个灌木丛里闹闹,那片草地上玩玩,快乐又逍遥。
是啊,它们没有理由不开心,没有理由不快乐,时庄虽不一定就是它们理想中的天堂,却也绝对称得上是它们生活的乐土了。春夏季节,田野里有虫子爬,空气中有虫子飞;秋冬季节,草籽熟了,樟树种子熟了,楝枣也黄了,一年四季都有食物,吃饭问题根本就不用去考虑。还有住的,时庄的住户,哪家的房前屋后没有几棵大树呢?在上面搭窝,冬暖夏凉,还很安全。
说到安全,又有话说,相对于温饱来说,这个似乎更为重要,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会是快乐的,人是如此,鸟儿也应该一样,要不怎么会有“惊弓之鸟”的说法?鸟窝搭得高自然是比搭得矮要安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也不是绝对的,时庄的树就长在那儿,对于任何一种鸟儿来说,机遇都是均等的,但你不能说对于所有的鸟儿都安全,比如同样的一棵树,喜鹊、白头翁们搭窝就安全,而乌鸦就不安全,还没等这些臭嘴巴的家伙们衔来几根树枝,庄子上人的长竹篙早就伸上去了,所以,乌鸦们只能把窝搭在远离村庄的高松河边的枯树上,村子里没有它们的落脚之地。
我庄子上的人喜欢白头翁,除了因为它们是益鸟(衡量一种鸟是益鸟还是害鸟,在农人的眼中,似乎是以它们是否对农业生产有益为唯一标准,白头翁既吃害虫又不糟蹋庄稼,正符合这一定义)外,它的叫声好听也是其中一个方面,它们虽然也像麻雀那样成群结队,也喜欢叽叽喳喳地叫,却没有人嫌它们聒噪。
我外婆家屋后的老槐树上,搭有两个鸟窝,一个是鹁鸪窝,另一个就是白头翁的家了。我几次想让五舅爬上树去给我掏一只小鸟下来玩,都遭到了我外婆的呵斥,她说小孩子不能干坏事,并且吓唬我们,说掏鸟窝会被大鸟啄瞎眼的。
聪明的你,你说有这样的生存环境,白头翁在时庄会不快乐吗?它们会有什么事情要愁白了头呢?说实话,我是很羡慕它们的,我看它们夫妇相亲相爱的样子,总会想起那个“白头偕老”的成语来,感觉十分美好。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家很上档次的饭店里,看到端上桌来的一盘菜肴前,我都认为白头翁是一种非常幸福的小鸟,也是在那一刻,我才了解了它们的悲哀,它们或许是真的有先见之明,早早地就愁白了少年头。那天,那个被端上桌来的盘子里面,并排躺着两只炸成金黄色的小鸟,服务员介绍,这道菜是用白头翁做成的,菜名叫“白头偕老”。
责任编辑 叶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