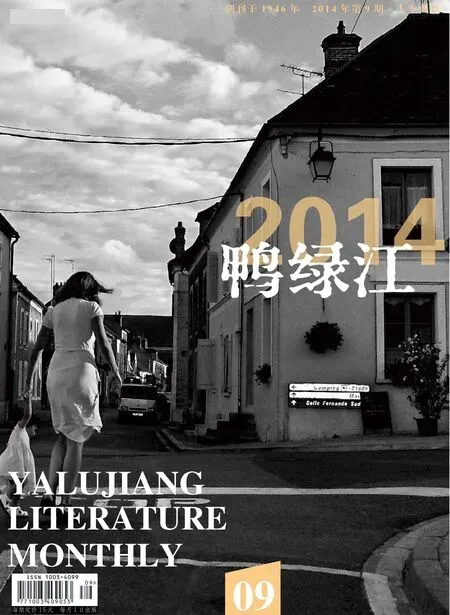倔犟的槐花
毕雪飞
倔犟的槐花
JUEJIANGDEHUAIHUA
毕雪飞

五月的太阳性子急,满把的光,早早地就把天捅了个透亮。窗下的草窠里好像有只蝈蝈,昨晚四福哼哼呀呀时,它还跟晒脸似的陪着唱呢。七婶记得大霞抱着小宽走时,孩子手里就提着他爸给编的蝈蝈笼子,边走边回头说:“奶,你回吧,俺跟妈去溜儿溜儿,过几天就回来,让爸再给俺逮几只蝈蝈……” 这一晃就是三年,估摸着小宽早上学了吧。
七婶擦了把泪,炕那边四福翻了个身,转过来的一张脸瘦得刀削似的。她明白,自己没工夫在这儿抹泪,该干嘛得干嘛。昨晚四福又咯血时她就决定了,天一亮,豁出什么也得去趟城里,找大禄,找三喜,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他们怎么就能眼看着自家兄弟死挺在炕上?

毕雪飞,辽宁沈阳人。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小说北2830”成员。现供职于沈阳市新民团市委。
七婶下了地,从灶坑里撮出点灰,把地上四福吐的左一块右一块的黏痰、黑血都掩上。折腾了一夜,这会儿他倒睡得安静了,只是听得呼吸里还有拉风匣似的咝咝拉拉的声音,像是被极细的线勒住了脖子,一口气要上来又似上不来,听得人揪心。想前些年,四福多好的身板,站在那儿树桩子样结实,心实,手也巧,弄俩草叶、秫秸皮就能变出些虫啊、花篮啊、笼子啊……小宽拿在手里让满街的孩子撵着跑。只这一病,啥都跟做梦似的了。
把昨晚剩的半盆儿粥用锅叉架在锅里,简单烧了个开。自己是顾不上吃了,想赶最早的车,也没有胃口,只是怕万一四福醒了会饿。出了门,正好看见东院的老八弓着腰在自家园子里绑柿子秧呢。七婶隔着墙说:“他八叔,我想去趟县上。四福的饭我放锅里了,烦您帮我盯着点儿。用不了中午我就能回来。”老八直起腰,脸上皱起的纹路菊花瓣一样,他问:“我听四福昨夜好像又折腾得挺厉害?”七婶点点头,眼圈有点红,怕人看出来,紧着咽了几口吐沫。老八叹口气说:“是该找找他哥哥们,净可着你一个人咋行呢,也是奔七十的人哩。去吧,别担心,我这照应着……”
长山乡到县城不到二十里路,早年七婶曾和大帮的娘们儿、媳妇儿们走着去,并不觉得远,如今六十五了,再想省那块八的车钱怕是得搭上老命喽。从车上下来七婶直往南街走。大禄家就在南公园的边上。多少年前,这两口子刚结完婚就闹着要分家。大禄噘着嘴说:“走一辈子地垄沟,最后连头都抬不起来,连线都画不直,吃牲口饭干牲口活,还不如到城里捡破烂呢。”那时七叔还在,烟袋锅子把炕沿敲得哐哐响,伸直了脖子说:“滚吧,恁些年牲口饭俺亏了你,以后你能耐大啦,捡着金瓜银蛋的光彩了,都不用进李家的祖坟哩!”
七叔火大不是冲儿子,他跟七婶说是自己眼拙了,大禄是自家养的,啥样自己能不知道,打死他也没这主意这胆子。这都是他媳妇彩枝在背后支的招儿,这女子心眼儿太多,城府太深了,莫说大禄,就是自己也未必是对手哩。其实当老大的,他们就是不提这家也早晚要分,只是话从他们嘴里说出来七叔觉得这是让儿媳妇牵着鼻子走,儿子这样听媳妇话,刚结婚就跟爹叫上了板,以后啥样谁敢想呢?
大禄没听那个,把分到的地租了出去,和媳妇收拾收拾就进城跟着他舅丈人做装修去了,没几年,就在城里买了房,小日子过得风声水起。逢年过节回家,上了桌满嘴都是城里的好,媳妇彩枝在一旁不温不火地笑,常弄得七叔在他们走后嘬着他那玉石烟嘴儿叹气。
七婶对这些想得不多,她常劝七叔,都是自家孩子,只要日子过得好,在哪儿还不都一样。家里有人混进了城,谁脸上不光彩?七叔说,你个娘们儿家家的,懂个啥?
七叔的担心,七婶是在几年后才明白的。三喜娶秀凤时,家里左拼右凑的还是差了五千块钱。本想着,这不算啥,跟大禄拆借一下就行了。可七叔骑着破车从县上回来时脸都要阴出水了。原来他刚进门还没张口呢,彩枝就破天荒地喊了爹,然后就说自己和大禄看中了一处楼,连定钱都交了,可总算还短一万。自己结婚就分了家,连个房也没落着,这几年又没啥积蓄,看爹现在方不方便,帮着填补点。七叔看看倚着门框闷葫芦似的大禄,一转身水都没喝,咽了口吐沫就回来了。“明摆着有房住,咋就偏赶上三喜结婚时换楼呢?这是堵我嘴呢,是在告诉我没在我这儿得着过啥,让我以后也少惦记人家。分家时我是没给房,可当时也合了两间房的钱给他们,这个窝囊大禄啊,我看是这辈子也别想伸腰了……”
话这样说,但七婶心下还是没怪孩子。她想,儿子、媳妇在外干活赚得也都是辛苦钱,孙女还小,都不容易。当爹妈的跟他们较什么劲呢?直到十多年前,七叔没有任何征兆就在过道时给车碾了。三个儿子一路跟头把式地处理完丧事。出殡回来,亲友都散了。大禄耷拉着脑袋靠门站着,三喜坐在炕梢,四福蹲在地上,一屋子的沉静。七婶从恸哭到红肿的眼缝里瞄见两个媳妇貌似悲痛的神情下掩着的另一重含义,她的腰一下子就挺直了。跟七叔这么多年,大事小情的都在倚着他,如今,她似乎在一瞬间明白只能靠自己了。她不紧不慢地说:“你们爹没了,拿命换来了五万。发送他用了将近一万。剩下这钱,按说分给你们也没啥大说道。可我现在没了倚靠,将来也总有爬挪不动的时候。你爹在时帮你们把家业都支起来了,只剩四福还没娶亲,这老房本也是留给他的。你们满算着都想好,要能养我的老,再给四福张罗房媳妇,就把这剩下的钱拿走。”
七婶的话说完,两个媳妇一扭身都出去了。秀凤没出院门就把胳膊上的孝布扯下来直接扔到了地上。大禄和三喜对了下眼神,没说什么,也都走了。七婶在他们出门后恍惚听到“咔吧”一声,也不知是什么断了。
自那后,七婶总有一种散了的感觉。按说离得都不算远吧,可隔着两趟街的三喜自己竟也很少看见了。有回在街头碰到了三喜家的小常,她疼孙子,给买了串雪糕,看孩子撒欢儿地跑了。可没走出多远就听秀凤骂“你这是得了‘馋痨’了?想吃人家东西也得长口好牙……”七婶觉得脚下有点飘,但她没吱声也没回头,恁些年都惯了,她不愿跟谁在嘴巴上争长短,没有用。早头有话“筷子头修寿禄,口头修儿女”,她不寻思自己还得想着点后生晚辈呢。
好在四福还在身边。种着薄地,守着老娘,四福啥也不说。可晚上听儿子在炕那头翻过来掉过去地“烙饼”,七婶就觉得心疼。四福本来和前街立茹挺好的,可七叔出事后,人家立茹娘说:“就他家那烂事,谁家姑娘恁想不开跟着去蹚那浑水?”没多久,立茹就嫁了,听说是她哥在城里给找的一户人家,去了就住楼呢。就因为多了个寡婆婆,后来说了几户人家也都没成。年轻人谁不想关起门过消停日子。四福话不多,问急了就一句:“要是不要俺妈就啥也别谈!”七婶想,要是七叔还在,这些事一准轮不到自己着急。这样一想,七婶也睡不着了。攥着七叔留下的玉石烟嘴儿,整宿地难受。
隔了两年,四福的婚事还是毫无进展,七婶一咬牙,花钱把房子里里外外重修了一遍,把原来的三间房大通炕隔成了东西屋,然后又花钱买了块上好的布料去找同街的刘四媳妇——全乡有名的大红媒。七婶说:“四福的话你们都别信,孩子能结门好亲,我到哪儿都无所谓,又不是只有他这一个儿子,他爹留下的钱还有不到两万,都给他们……”
大霞嫁过来那年,四福都二十八了,她是刘四媳妇辽西的远房亲戚。七婶总觉得这事就跟中了头奖一样。大霞没有彩枝、秀凤她们俊俏,但人实诚,还孝顺,没过门时就说:“把寡婆婆撵出去,别说旁人戳脊梁,自己心上也落不安生。”她和四福俩人投心对意的,对自己也尊重。隔年生了小宽,一家四口在一个屋檐下,四福领着媳妇把大田拾掇得利利索索的,农闲时摘了前园的菜、后园的果去县上卖,自己就在家里烧火做饭、洗洗涮涮、带孩子,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也够用了。那阵子,七婶觉得窗外的鸟叫都特别动听。
不管旁人怎么说,七婶心里就觉得四福这病是从气上得的。小宽三岁那年的夏天,四福和大霞早起去县上卖菜。可别小看了前面这不大的园子,说不上咋恁高产。可能是因为这山根下的井里打出的水也算山泉吧。东三垄、西四趟地种起来,那豆角啊、黄瓜啊,又青又嫩地满挂在架上,让人看了没得由来地喜欢到心疼。四福和媳妇码了两筐担在车后架上,说“妈,我们出去了。”结果都日上三竿了还不见回来。七婶就觉得心跳,抱着小宽一趟又一趟地站在门口往街头望。快晌午了,才见到人影。四福的脑袋包得跟粽子似的,后架上两个柳条筐只剩下了一个。大霞的眼睛也肿成了一条缝。七婶觉得腿都打战了,放下孩子扶着炕沿问,“这可是咋啦?”四福蔫巴地靠在被垛那儿,再问急了就哭了。
每次卖菜都是到县上的北市场。那里早起是蔬菜水果大批发的地儿,遇上买主成筐包了,比走街串巷省去不少麻烦。可不知啥时候多了一伙人,进去卖菜除了正常交易费外还得另交他们点儿钱。四福不长年卖菜,另外也心疼,两筐菜能有多大利?于是常在市场门口等着,碰上来买菜的,趁人家还没进场搭个话就把菜卖了,两下都省事。也不知啥时候让人盯上的,那早正跟人过秤呢,一伙人凶神恶煞地过来抢过秤砣就把四福一顿打,边打还边骂:“到爷地盘上‘淘地沟’,不他妈打你满地找牙爷白混……”两口子都蒙了,转醒过来时连看热闹的人都散了,菜撒了一地,筐给踢零碎一只,四福头上不知哪儿破的口子血流满面……
七婶定下神来,叹了口气,劝四福说自古就有话,强龙不压地头蛇,这事哪朝哪代哪沟哪坎都免不了。咱要是没恁大财命也不跟着操恁大心担恁大风险。不算啥,别窝火,短了那仨瓜俩枣的咱饿不死。
话是这么说,但四福经了这事后,就跟丢了魂似的,整个人站都站不直了。在炕上一躺几天,吃不下睡不好,一过晌午就发烧,听到啥动静都闹心,动不动就跟大霞发火。七婶劝媳妇,他这是吓出病了,养一阵就能好,甭跟他一般见识。为这,七婶还跟西院当邮递员的大江要了张远道邮过的邮票,晚上等四福睡着后在他头顶烧了。人说这样能把吓人的瘟神送走。她还在半夜时拿着水瓢站在水缸边,边滑边喊来着,想把四福被吓跑的魂给叫回来。可办法用尽了,四福不但没好,病情还一天比一天重了。整个人瘦得跟缩了水似的,有几次发烧烧到说胡话,有时咳到气都喘不上来。找村上的“赤脚”大夫打了几针也不见好。后来人家说:“七婶,别拖了,这病我看不好,你还是领着他去县上的大医院看看吧。”
七婶想求三喜跟着一起去,但秀凤说:“三喜跟人说好了明天去帮工,一天七十呢。四福啥病精贵成这样,不去大医院能死了?”七婶懒得听她说这怪话。说的不怕折寿听的嫌扎耳朵。大禄那边也说有活计走不出去。七婶只好把小宽交给了刘四媳妇,和大霞一起领着四福去了县医院。
肺结核,并发胸膜炎。
七婶听到结果时愣了好一会儿。她问大夫:“是不是弄错了?俺家没这病根啊?”大夫的大口罩捂住了半张脸,不耐烦地说:“这是传染病,说个话打个喷嚏都能染上,啥病根不病根的!去传染病院吧,国家现在有政策,能免一部分费用……”
四福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大夫说:“回家养着吧,定期复查,定期取药。一个疗程九个月。”然后是一大堆的注意事项。大霞说:“您帮忙写到纸上吧,太多了我怕记不住……”七婶拎着药袋子站在后面,听什么都觉得嗡嗡的。四福比原来更瘦、更沉闷了。回去时刘四媳妇抱着小宽站在院子里,孩子见了爸妈急着下地往过跑,可四福闪了个身躲开了,小宽当时脸上那个委屈劲儿让人看着那个心疼。七婶让刘四媳妇进屋坐会儿,人家说:“不啦,家还一大堆活呢。”走时的步子显得风风火火的。
七婶想,自己得挺住了,要不然这个家就真要散了。结核,不就是早头说的痨病?在以前是治不好的,只能等死。但现在不一样,听大夫说,现在治好的挺多,不算啥。注意休息,注意调养,吃些好的,别着急,别生气……得挺到四福好起来。四福只要一好,日子就又能像从前那样了。自己年岁大了,没啥念想,可还有小宽呢,还有大霞呢。
她几乎包揽了所有的活。跟大霞说:“你照顾好小宽,侍候好四福,剩下的不用你管。”早起莳弄园子,黄瓜豆角都倒架了,该种秋白菜了。原本四福一会儿弄完的活,七婶一个人干了大半天,备垄时手上的镐头分外沉。四福靠窗台站了会儿想过来伸手,七婶黑着脸说:“你给我一边儿待着去,再急也不差这一两年,你让妈省点心。”四福看着她眼圈儿红了。该秋收了,七婶自己赶着驴车,看旁人家连换工带帮忙的说说笑笑着把活弄完,她一个老太太,腰弯成了虾米,掰穗、扒皮、装车,滑到嘴里的汗珠子比眼泪还咸。这都不算啥,她能行!大霞有时说:“妈,我跟你一起去吧!”七婶说:“家里不能离人。你得管好小宽。这点活我和四福他爹干了一辈子了,比你们门儿清。”七婶咧着嘴笑。晚上把小宽哄着了,她揉完了腰又揉腿,自己拿着小棒敲后背,疼得咧着嘴不敢出声。自四福生病后,小宽每晚都和她睡。是啊,能注意点儿就注意点儿。谁都不说,可谁都明白,这病是传染的啊。
七婶睡不着时想起七叔,想起大禄还有三喜,想起大人年轻孩子小时那些凑在一起的日子,原本那么多人的一个家,是啥时候开始好像只剩下自个儿了呢?她还会想起二曼——她那个短命的女儿。二曼四岁时七叔领着大禄下地干活去了,七婶肚子里怀着快到月的三喜,孩子每天没完没了地在肚子里翻身踢腾,累得她啥精力都没有只想睡。迷迷糊糊听二曼喊:“妈,我渴。”当时太累了,就说:“自己去舀口水吧。”醒来时找不到孩子,最后在窗前洗澡的大缸里看到漂在水面上的头发……七婶没疯就算捡着,连三喜是怎么生下来的都记不太清了。打那后,她疼孩子疼得厉害,不敢再有一点差眼,也不忍再动谁一下。这事儿成了自己心上的一个死结。后来生四福也是想着再要个女儿,谁想又是个“小蛋子”。天不随人愿啊,注定了她这辈子没有养闺女的命。都说女儿是妈的贴心小棉袄,如果二曼不死,怎么着现在也能惦记着她这个妈,帮衬着她弟啊!
赶上阴历十五,七婶买了点烧纸,天黑后在十字路口画了个圈儿,留了个口。当年埋二曼时她啥也不知道,都是七叔处理的,别说找坟头,连东西南北都确定不了。她边烧纸边叨念:“二曼啊,是妈不好,没看住你,恁些年了你还没投胎啊?你有千个不满万个不满冲着妈来,妈欠你的。可你别作践四福啊……”叨咕完这些,她又在心里跟七叔念叨:“你说走就走了,连一句话也没留下,扔下这样的家给我一个人。你要是觉得我这辈子还算对得起你,就显显灵让四福好起来吧。要不然你让我倚靠谁啊……”七婶的眼泪忽然就跟断了线似的流下来,蹲在深夜的乡村路口,她觉得自己每一声低低的抽泣都带着一种怪异,让人没得由来的怕。明知是自己的声音,可又觉得那是从另一个更凄苦的世界传来的,听得人心发紧,后背发冷。四福得病后她一直没哭,那天不知怎么就跟开了闸似的,直到大霞拿着手电喊着妈一路寻过来,她才擦净了泪。大霞说:“妈,四福都快急疯了,这是咋了?你哭啦?”七婶揉着腿说:“不知咋弄的,走着道就摔了一跤,磕得这疼。”
隔两年的春天,四婶一个人跪在垄上间苞米苗。风卷着沙子又干又热地打在老脸上。这两年的年景不是太好,正常的地有七成的收算不错了。多少人嫌种地赚钱少,都跑城里打工了,自家的地包给别人,干拿直补。三喜就是这样进城的,说是小常成绩好,在县里读高中呢,两口子都过去陪着。没到一年,就卖了前街的房子,看样子是铁了心不想回来了。七婶出不去,恁大岁数了打工也没人要。想多种些地,可哪弄得动呢。就靠着这几亩田。四福的药一直没断,过了九个月,又是九个月,医生说要出啥抗药性,不好。家里的积蓄早掏空了,眼见出得多进得少。四福看不行,就坐炕上编了些小玩意。这阵子开春天好了,城里人都爱领着孩子到公园溜达,晚上在路边摆个小摊,一冬的存货卖得还挺快,总算有些进项了。七婶想,该给小宽填两件衣裳了。别人家的孩子都鲜亮亮的,小宽一直在捡东家凑西家给的旧衣裳。她想着这些,回到家却发现四福躺在炕上,整张脸红得发亮,大霞坐在一旁抹眼泪呢。她问:“咋啦?”大霞说:“妈,四福咯血了。”
医生说四福身体里的病菌真有了抗药性,原来的药都不好使了。现在也不是简单的原发型肺结核了,转成了什么慢性纤维空洞型结核,得复治,但想治好太难了。“没养好吗?怎么就成这样了?”大夫责问时,七婶直想打自己几巴掌。四福心事重,总在上暗火,再加上没事总在编东西,那是费神的活儿最熬心血啊,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
四福没有接受复治,没几天就死犟着回家了。他说这回用的不是免费药,病不一定能治好,靠下去只能卖房子,到最后弄个人财两空。他说要是再逼着他住院他就拿刀自己抹脖子去。回到家没几天,七婶发现四福的脾气又大了,每天摔锅打盆的,居然还动手打了大霞。听人说得痨病的人脾气会变得特别急,可之前也没见他这样啊。七婶想,孩子这是心里太烦了吧。大禄和三喜回来了两次,拎了点东西,扔下几百块钱就匆匆走了。末了没忘了告诉七婶他们来的事别跟旁人说。估计这两人也是背着媳妇呢。不管咋说,总比不来强。
有一天小宽从外面哭着回来了,问怎么了,孩子说同街的小孩都不跟他玩,他去找,人家爸妈还往出撵,说他身上有病。七婶怕四福听到上火,赶紧哄着孙子不让哭。不想四福那天特平静,他说:“妈,你把大霞找回来,咱坐一起我有话要说。”
四福要和大霞离婚!七婶上去给了他一嘴巴,说:“你疯了,脑袋让驴踢了?这样的话也说得出口?”四福说:“妈,你要是心疼我,也该心疼你儿媳妇和你孙子。我这病传染,谁不知道?小宽还小,跟着我能有好吗?万一也染上这病怎么办?你儿媳妇还年轻,可我这病、这身体……咱不能让人家跟着咱守活寡……”七婶说不出话了。大霞抱着孩子哭,说:“四福,我不嫌你,你能好。”四福说:“你别勉强自己了,这不是勉强的事。你要是念咱们夫妻一场就信我的话散了吧。再靠下去总有熬不住那天,趁现在你还年轻,找个人家不太难。只是得受累替我把小宽带大……”

大霞最终还是没拗过四福,走了。临出门时,四福说:“小宽,亲爸一口。”一打得了病,他从没跟孩子亲近过。小宽在他脸上亲了一下,然后看他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个草编的蝈蝈笼子,用草棍挑了挑,里面那只绿头的大蝈蝈就响亮地叫了起来……
七婶一直熬着,她总想着有一天自己睁开眼,四福就好起来了,又树桩子似的站在自己跟前。四福好了,就能接回大霞和小宽,这屋檐底下就又是快乐的一家了。可现实却是,四福真的一天不如一天了。苦挺了这三年,到今春,眼看着没啥精血了,咳起来声嘶力竭、惊天动地的,顶一阵药好一阵,没多久又是咳、喘、烧、咯血,嘶哑着说句话都要用出全身的劲,有时觉得他胖点儿了,可细一看是脸上浮肿了。七婶自己也不成形了。挺过的这几年比什么都漫长,驴卖了,车卖了,地也租出去了。跑村上找乡里,跟村干部哭,跟乡干部哭,眼泪掉得用碗接,好歹弄了个低保,每月百十元维持着生活。两个儿子一年能偷着摸地来两回,扔点米面扔点钱,可谁也没再张罗给兄弟治治病。七婶这回下定了决心,怎么都好,得让四福活下去。
开门的是彩枝,怀里抱着孩子。是啊,她也是做姥姥的人了。这几年只顾着四福的病,大禄有了外孙子,自己都没抱过一下。唉,就是想抱,人家也要肯啊。彩枝一看是七婶也没言语,脸上的神情木木的。大禄出来也愣了一下,说:“妈,咋恁早就来了?有事?要不先进屋吧!”话音刚落,转到屋里的彩枝就咳嗽了两声,孩子也随之哭起来,彩枝喊:“大禄,你看这孩子是怎么回事?不是染上什么毛病了吧……”七婶抬起的脚又硬生生收了回去。她说:“大禄,你出来,妈有话跟你说。”大禄等了半天才从楼上下来。他把七婶领到了一个早点摊,要了碗米粥和几个包子。那香气好久没闻到了,七婶没张开嘴,就想起了还躺在家里的四福。七婶说:“大禄,你得救救你兄弟。”大禄抽了几口烟,说:“都说了,那病到这份上就等于是癌症晚期,没得治,拿多少都得打水漂。再说我这儿也不宽裕。”七婶说:“你再不宽裕好歹还有命呢,你兄弟连命都快没了。”大禄憋了一会儿说:“当年爹没时,是您说的谁拿了钱谁就养你老,现在钱都给了四福不说,还要我再拿钱填这个无底洞,我在彩枝那儿没法说话呢。”七婶说:“你自己兄弟的性命,跟她说什么?哪天你妈死了,她不点头你就任我烂在炕上了?你倒有没有啥事能自己拿个主意?”大禄说:“妈您这是咋个话,恁些年我也没短着您啥。四福要真没了,还不得我和三喜养您。您不能不讲理啊。”七婶哭着说:“我不用你们养,你要认我这个妈就帮帮你兄弟。”大禄说:“我也不跟您犟,咱娘俩在外吵起来叫人笑。这五百块钱是我偷着攒出来的,你先拿回去吧。”钱递过来,他忽然又想起了什么,盯着七婶说:“妈,有句话我可先说到头里,前些时我回去听别人说东院的老八叔没事总在咱家晃?这事本不该我说,我知道爹也走了多少年了,可您也是扔了六十奔七十的人了,差不多得注意点儿,总不能让我们做儿女的跟着丢人吧。您要真是动了啥心思,我也拦不了,但真那样了,等您没那天可别说我这个当长子的不让您进咱家祖坟!”
七婶先前听着觉得有点迷糊,后来明白点儿了,随之就是一阵气。老八本来是七叔的同族兄弟,是个一辈子没结婚的老光棍,年轻时在乡上一个厂子里上班,现在退了每月有几百元的劳保。这几年四福身体不好,大禄和三喜不在身边,自己连个搭手的人都没有。亏得人家没啥说道,春种秋收拾掇园子啥的总帮七婶的忙。人家说自己没牵没挂的,闲着也是闲着,都是自家亲戚,亲帮亲,老帮老,不用见外。七婶心下感激,从没往多想。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怎么就变成这味了呢?不说自己六十五的人了,就是看恁些年自己这困难劲儿,他们怎么还忍心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更可气的是大禄,这话他也说得出口?
七婶跟服务员要了个塑料袋把包子装起来,又拿起桌上的五百块钱塞进包里。然后,她站起来对大禄说:“大禄,家里这些年七灾八难的多亏你这个长子了,妈不用你养老,妈硬着呢,死哪儿埋哪儿没说道,你要真有心就多回去看看你兄弟吧,反正看一眼少一眼!”七婶说不出的委屈。擦了把眼泪,她把大禄留在众人的惊愕里。走出去时想,这是我疼过养过的儿子吗?怎么就成这样了呢?
三喜家七婶只来过一次,记了个大概,进了院子想不起是哪个单元了。她想自己这是让大禄气糊涂了。正想着,三喜和秀凤从楼上下来了。一见她,秀凤就先张了嘴:“您这是给您孙子送上大学的钱来了吧?”七婶愣了,一想到小常的样子脑子里竟有点糊涂:“小常都要上大学了啊?”“是呢。我们孩子长多大您都不记得了。一样的孙子一样的儿,这些年您的水可端得平呢……”三喜在背后拉媳妇,秀凤说着话没管没顾地甩胳膊。七婶想,看样子这是大禄给他们打电话了,秀凤知道自己的来意,早想好堵自己的嘴了。也不能全怪他们,不管咋说自己是对他们想得少。可秀凤这样说话还是让人难受,当年隔着两条街,她一年一年也不到家一趟,连小常她也管着不让来,如今却把错都派到别人身上,咋能说得过去呢。七婶懒得和她计较,她直接跟三喜说:“三喜,妈现在不求你别的,你看看还能不能帮帮你兄弟。”三喜还没张口,秀凤就接过了话茬:“这是怎么个话,当年话是您说的事是您办的,今天倒都成我们的不是了?”秀凤的嗓门大,又正赶上是众人出门上班的时间,几个人的身边已经有了别人诧异的目光。七婶气不过,说:“小常他娘,你将来可也是要当婆婆的人哪,今天这样跟我吼,就不怕明天事都应到自己身上么?”众人的窃窃声让秀凤恼了。她说:“是你偏心疼老儿子,花的用的都可着他,临了还得拖着我们当垫背的,难不成看我好欺侮?”秀凤撒泼的本事在本村是出了名的,七婶从没和她较过真,如今更懒得理她。一旁的三喜说:“妈,您先回去吧。四福的事我抽空回去再和您商量。”秀凤喊:“商量个屁!我看你敢往家拿一分钱……”三喜猛地回身甩出了一记耳光,打得七婶愣了,秀凤也立时没了声音。旁边有人过来拉着三喜,他却甩开众人涨红着脸说:“于秀凤我告诉你,你他妈爱过过,不爱过就给我滚,这些年我给了你脸,别以为谁离了谁就得去死……”秀凤站在一旁捂着腮。七婶看着三喜,眼泪很快流了下来。她明白了三喜还有心,也明白了三喜也难,都是自己的儿子啊。她抹了把脸说:“是我老不经事,给儿女找麻烦,算了,你们好好生生过日子,我不求你们了,我走!”秀凤开始号了,她坐在地上拍着腿哭喊:“这日子没发过了……”七婶脚步有些发颤,但没有回头,哭声就在她身后越来越远了。
从车上下来七婶先擦了擦脸。回想这半天的一切,她觉得像在做梦。自己的两个儿子、两个媳妇,还有他们的孩子,一大家子的人,是几时起都同自己活成了“两重天”呢,好像只有四福是真实的。
回到家,老八正往屋拎水呢。那井啊,死沉死沉的,自己每次压水都累得一头汗,一缸水得折腾二十多趟——没办法,年岁大了,一次只拎得动半桶。老八虽只比自己小两岁,可咋说也是个男人啊。想到这儿,她又想起了大禄的话,一张脸立时冷了下来。老八看着她,只道是跟儿子们生了气,就说:“别上火,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刚才我给四福喂了半碗粥,这不,又睡下了。我琢磨着,他既然还吃得下就应该还能缓缓……”七婶放下包,转过脸对老八说:“让你费心了。他八叔,这些年你帮的忙,我替你七哥谢谢你。以后你就别来了,你年岁也大了,四福这病又不好,你要是有个闪失或是为这让别人说出啥来我不落忍。”
老八听了她的话就愣住了,憋了一会儿起身往出去,可没走到门口又转了回来。他站在七婶跟前老半天,最后一咬牙说:“七嫂,咱都这么大岁数,土埋半截子了,旁人说啥还能把咱咋的?岁数再大也是人,是人总得过点人过的日子吧?”他叹了口气接着说:“我光棍,你守寡,谁想说咱啥也堵不上他的嘴。我其实一直就是想着,能帮你就帮你一把,眼看着你们娘儿俩这样,我心里受不了。不怕你生气,这些年还没啥人啥事让我恁么撂不下的。”老八咬了咬牙,最后说:“陈槐花,今天我把话放这儿,只要你不嫌弃,以后,我就替七哥照顾你和四福。你要是嫌弃,我也不在乎,我手里还有些钱,明儿,你拿去,咋说也得最后救救孩子……”
老八走了,七婶晃晃悠悠坐到了炕沿上。又做梦了?他刚刚在和谁说话?陈槐花?对了,那是自己的闺名,自嫁了七叔,她的名字就变成了老七家的、七嫂、七婶、七奶……陈槐花呀,只是户口本上的仨黑字儿!陈槐花是自己?那老八刚才的话真是在跟自己说?这可叫啥呢?六十五了,六十五了咋还能碰上这事。臊得慌啊。七婶从墙上挂的旧镜子里看自己,太长时间没擦了,镜面上的灰那么厚,晃出来的影瘦瘦小小的,佝偻着,灰白的短发,一时竟看不出是男是女。他还说要替他七哥照顾我,要和我最后救救孩子……七婶看看躺在炕上瘦得没了形的四福,她觉得有点喘不上气来,眼睛、鼻子、嘴里都酸酸麻麻的。
起身到了院子里,一阵阵的香气从后院飘过来。是啊,五月了,一般的桃杏花早谢了,这是后院墙边那棵槐花的香气,白花瓣成串地挂在枝上,香味里有几分霸道。还是嫁过来时从娘家带过的树苗,这么多年树枝铺展了半个后园。每年春天它绿得最晚,总让人怀疑是不是枯死了,但一到晚春,它又总是肆无忌惮地绽叶、开花,香得让人无法忽略。记得七叔出事那天也是这差不多的时候,自己让四福爬到树上去撸槐花,她跟四福说:“这东西成精似的甜,和点三合面,我给你们贴槐花馅的饼子……”她手里攥着那只光滑的玉石烟嘴儿,却想不起七叔走了多少年了,连四福病了多久,竟也一时算不清了。
一年当十年啊,只是想着让四福和自己活下去。恁些年苦挺着腰是在和啥斗呢,大禄、三喜,谁说过能帮自己一把?话说回来,就是真帮,谁又有多大本事?她心里说,咋能这样,让人笑呢。然后是老八的声音:岁数再大也是人,是人总得过人过的日子吧!她心里又想:丢人呢!可很快又想:谁丢着谁的人了?谁捡到谁丢的人了?七婶说不清心里到底是啥滋味啥想法。
她听到屋里有动静,进去后,看到四福在够水缸子。给他喂水时,快四十的四福半躺在七婶怀里,那重量那情形,让人想起了他没忌奶时的样子。四福在盯着七婶看。看得人心里慌!难道刚才老八的话他听见了?那刚才自己想的事,他不会也都知道了吧?过了好一会儿,四福笑了,他抬起枯瘦的手把七婶额前一绺花白的头发掖到耳后,然后哑着嗓子说:“妈,你还挺好看。”七婶愣了一下,很快,脸像个小姑娘样红了起来。四福又说:“妈,我想吃槐花馅的饼子。”七婶听了直了直腰,点了点头“妈给你做……”抬起头,她看到箱盖上放着的老照片,那上面儿子、媳妇们都水灵灵地站在她和七叔身后,还有大霞、小宽留下的合影,所有人的笑容都那么灿烂。原来都有那么开心的时候啊!她笑了,口中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四福说:槐花开了,咱还得好好活下去啊……
隔天,大禄和三喜回来时屋子里只见到昏睡的四福。
长山乡政府的院里,穿得整洁干净的七婶和老八一前一后走了进来,迎光看上去,两人花白的头发都被阳光镶上了一层金晕,明亮得有些晃眼……
责任编辑 晓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