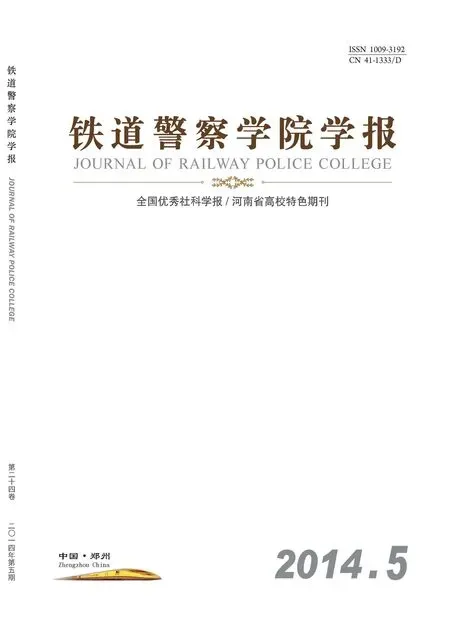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夺罪的界定
——以张某某抢夺案为视角
张玉锋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550025)
一般情况下,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夺罪是很容易区分的,但有一些案件由于行为人作案时使用多种手段,导致案件性质难以区分,罪名难以认定,这就需要我们正确理解并灵活运用法学知识,透过现象分析行为的具体情节,来准确认清行为的本质特征,从而正确认定该行为的具体罪名。笔者以下面一个实际发生的案例,对三者的区别作一简要分析。
一、案情简介
2011年6月的一天下午,行为人张某某到某市一豪爵摩托车专卖店,对销售人员谎称买摩托车,销售人员信以为真。按照交易习惯,买摩托车之前都要先试骑才能确定是否购买。于是张某某向销售人员提出先试骑一下,销售人员就把一辆崭新的豪爵摩托车(经鉴定该车价值7500元)交给了张某某试骑,并告诉他只能在附近试骑。张某某从销售人员手里接过摩托车发动着火,在销售人员的视线范围内进行试骑。当距离该摩托车专卖店有一百多米远的时候,张某某看了销售员一下,之后迅速加大油门,把摩托车骑走了。销售人员立即意识到张某某加大油门有可能把摩托车骑走,于是就立即追赶。但由于出了摩托车市场岔路很多,销售人员没有找到张某某和其所骑摩托车,于是就向辖区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在对该案立案时,对本案的性质产生意见分歧:一方认为张某某的行为属于诈骗罪,另一方认为张某某的行为属于盗窃罪,还有一方认为张某某的行为属于抢夺罪。
二、本案性质认定
综合案情分析,笔者认为,张某某的行为属于抢夺罪。理由在于:第一,在本案中,行为人向销售人员虚构了买摩托车的事实,骗取了销售人员的信任,进而从销售人员处获得了试骑权,之后暂时占有了摩托车,接下来开始试骑,最后寻找到时机将所骑摩托车骑走,成功躲开了销售人员的追赶,结果获得了摩托车。这里将整个行为分成三个阶段,前边是通过欺骗的手段占有摩托车,后边是躲开销售人员的追赶,只有中间在其骑走摩托车离开现场的瞬间,才是决定该案性质的关键所在。第二,销售人员将摩托车交给行为人是让其试骑,销售人员根本无处分摩托车所有权的意思,摩托车虽然在行为人手里,但是行为人仅具有试骑权,因此,此案构不成诈骗罪。第三,行为人骑摩托车的过程始终在销售人员的视野内,说明受害人一直在监视着行为人,其没有失去对摩托车的占有控制,因此行为人不具有秘密窃取的性质,而且也没有哪一个盗窃分子,在明知被受害人注视的情况下,还要实施盗窃。行为人在占有摩托车后,销售人员失去了部分控制权,此时行为人利用占有摩托车的优势,在距离销售人员相对较远而销售人员不能立即追赶上的情况下,乘机加速逃离摩托车销售地点,从这一点看,本案倒更具有抢夺罪的特征。抢夺罪是公开夺取他人财产,公开地、明目张胆地、周围人一目了然地因而是非常粗暴地使财产脱离他人占有是抢夺罪最突出的特点。抢夺犯公开地、以令人发指的卑鄙和粗暴态度侵害社会中业已形成的所有权关系,往往还对人使用身体或精神暴力、示威式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无视刑法的要求,这使他所实施的违法行为的危险性大大增加,同时加重了对其违法行为否定性的道德评价[1]。在行为人明知受害人对财物的转移占有知情的情况下,仍然执意为之,尽管其客观上并没有实施暴力、胁迫等手段,但因其主观方面表现出的行为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将其评价为性质更重的抢夺行为,并无丝毫不妥[2]。本案具有多个事实情节特征,但是除了在销售人员视线范围内公然骑走摩托车逃离现场情节外,其余事实情节均不影响本案性质。
三、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区别
作为侵财类犯罪,三罪的主体、客体和主观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三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客观方面,辅助性地体现在主观方面行为人的认识上。下面以本文案例为例,对三种犯罪的区别予以分析。
(一)对三个罪名概念的理解
“诈骗”的汉语意思即采用欺诈的手段,骗取别人的财物。从字面意义上说,诈骗罪的罪名是由于行为人采取了欺骗手段,使受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继而受害人将自己的财物交付行为人,也就是说将财物的所有权让与行为人。换句话说,受害人在行为人欺骗下,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财物送给了行为人。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3]。从概念上可以理解,受害人是基于对行为人的欺骗方法陷入错误认识,继而把自己的财物无偿地给了行为人,最终自身财产受到了损失。盗窃的本意是秘密窃取,否则便不称其为盗窃。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4]。从盗窃罪的罪名可以明显地看出,行为人是在其自认为秘密的情况下,采取不被受害人发现的方式,获得了受害人的财产。盗窃罪的盗窃要么受害人不在场,要么受害人没有留意行为人盗窃的行为。如果在受害人在场并且已发现的情况下,行为人堂而皇之将受害人的财物拿走,其行为不可能是盗窃。也就是说,盗窃虽不以秘密为限,但是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行为人自己在认识到其他人发现本人盗窃行为的情况下,还实施盗窃行为,换句话说行为人自己认为自己实施的盗窃行为不会被任何人发现。这一点,从法庭审判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也可以推测出来。抢夺的汉语意思是强行夺取,“抢”蕴含着违背受害人意思的含义,“夺”字带有猛然间用力的意思。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方法,公然夺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般来说,盗窃更带有秘密性和短时间内不为他人所知性。也就是说,行为人获得财产与受害人发现财产消失之间有一段的时间距离,即便是受害人很快发现,但是和抢夺罪的公然性相比,盗窃罪从行为人获取财产到受害人发现自己的财产被非法占有的时间距离还是要长一些。在此我们应注意区分行为人以盗窃的故意刚一着手即被发觉,之后采取强拉硬拽的方式夺取财物的行为,这种行为已属于盗窃转化为抢夺犯罪了。而且,秘密性意味着行为人以不被受害人发现的方式将财物从受害人管控的范围或视线转移走。这从行为人行为的公然性上可以区分出,抢夺的公然性意味着行为人一着手实施犯罪行为即被受害人发觉。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和行为人在商场购物时,以夹带的方式将物品转移出去的行为区分开来。商场购物时的夹带行为明显带有秘密性的特点,而本案中行为人骑走摩托车的行为具有公开性。在两罪存在重合的情形时,这也是比较明显的区别两罪的方式。
(二)三个罪名的区别
1.从行为人的认识方面看。(1)诈骗罪中,行为人自始都认识到自己通过编造虚假的信息骗取受害人的信任,从而能够轻松地平和地使受害人自愿将自己的财物交与行为人。(2)盗窃罪中,行为人自认为以不被受害人发现的方式取得财物。如行为人先前已占有财物,并且行为人也认识到受害人知道其占有该财物,且受害人一直在注意着行为人的举动,此种情况下,即便行为人取走财物也不存在盗窃可能性。相反这种行为倒是具备抢夺罪的构成要件。如果行为人先前已占有财物,其乘受害人不注意时,偷偷把该财物拿走,这种行为更符合盗窃罪的构成特征。一般来说,盗窃罪行为人无论是在行为前、行为中还是行为后总是有意躲开受害人及周围人的视线。即使是扒窃行为,行为人也有意以相对秘密的方式实施,由于公共场所人员众多使得这种秘密性相对较弱,甚至易被人发现,但这并不意味着犯罪分子主观上是在公开盗窃。从心理学角度看,行为人实施盗窃时第一考虑到的是其行为不被人发觉,否则他便不会实施。(3)抢夺罪中,行为人一般采取乘受害人没有防备、猛然将物品夺走的方式,或者在受害人虽已注意到行为人但没有预料到行为人可能作案的时候,猛然间把受害人的物品夺走。
2.从案情发展过程看。(1)诈骗罪中,行为人寻找符合自己作案的受害人,然后向受害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受害人因为受骗而信任行为人,最后主动把自己的财物交给行为人,行为人取得了受害人的财物,受害人失去了财物。行为人取得受害人的财物是其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也就是说,其取得财物并没有违背受害人当时的意愿。而抢夺罪中行为人取得受害人的财物很显然是违背受害人意愿的。按照事发时的情景,受害人是不会将其财物交与行为人的。(2)盗窃罪中,行为人寻找符合作案的受害人和财物,然后想方设法躲避受害人的视线,采取不为人发现的方式,悄悄把财物移走。盗和窃的意思重在行为人取得财物的秘密性和受害人发现行为人取得财物的滞后性,包括行为人自认为具有秘密性和事实上确实具有秘密性。从这个方面讲,盗窃罪和抢夺罪二者的作案方式明显有别。(3)抢夺罪的整个行为过程可以分解为:行为人寻找符合作案的受害人和财物,之后在受害人没有注意到行为人之机,猛然发力强行快速夺取财物逃离现场,受害人发觉财物被抢采取补救措施。从“抢”和“夺”的意思可以推测出行为人取得财物的公然性和受害人发现的及时性。抢夺罪中的公然性也就是公开性,行为人不避讳抢夺后被受害人发现。
3.从行为人取得财物的方式看。诈骗罪中,行为人采取看似公平交易的方式得到财物。盗窃罪中,行为人采取隐蔽的、不易被人发觉的方式得到财物。抢夺罪中,行为人采取具有公然性、突然性、快速性的方式得到财物,通常情况下在受害人还未来得及反抗的情况下,行为人已把财物抢在自己手中。换句话说就是:诈骗罪行为人取得财物是不避讳受害人的;盗窃罪行为人取得财物是躲避周围人员的,得到财物后悄悄把财物隐藏或转移走;抢夺罪行为人取得财物是不避讳受害人发现的,得到财物后迅速逃离现场。
4.从受害人失去财物时的认识看。诈骗罪中,受害人是基于对行为人的错误认识,自愿将财产交于行为人所有或支配。盗窃罪中,受害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对财物的占有和控制的,失去财物是违背其意愿的。抢夺罪中,受害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失去对财物的占有,失去财物是违背其意愿的。
5.从行为人取得财产与受害人失去财产的逻辑关系看。诈骗罪中虚构事实的情节与其合法持有受害人的财物之间是充要条件关系,虚构事实对合法占有他人财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二者的因果关系是统一的。盗窃罪中,秘密窃取与占有受害人财物之间是充要条件关系,秘密窃取行为在占有财物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二者的关系具有因果性。即便是扒窃,行为人也是悄悄地,在主观上躲开被害人的视线。抢夺罪中,抢夺情节与其占有受害人财物之间是充要条件关系,抢夺在占有财物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二者的关系具有因果性。
6.从主客观相统一方面分析。主客观相一致是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行为人对罪名的认识正确与否不应当作为判断是否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标准。何况对一些复杂的案件即便是法学研究者或法律工作者也难以辨别清楚,更不应当让那些法律知识欠缺的犯罪分子来辨别其实施犯罪时到底是在实施什么性质的犯罪。犯罪分子对罪名的认识和他实施的行为性质没有直接的关联。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对其行为触犯了刑法规定的何种罪名,应当处以什么样的刑罚,存在不正确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对法律的这种错误认识,并不影响犯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应当按照他实际构成的犯罪及其危害程度定罪量刑[6]。因此,笔者认为,行为人从受害人身上(不包括从受害人口袋内)取得财物时,如果采取不被受害人发现的方式取得财物的,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反之构成抢夺罪。行为人从受害人附近取得受害人的财物时,如果受害人已发现而且行为人也知道受害人发现,其行为构成抢夺罪;如果行为人采取秘密的、不被受害人发现的方式取得财物,其行为构成盗窃罪。
综上所述,判断某一行为属于甲罪、乙罪,还是别的罪,一定要严格按照一国的法律规定,而不能主观臆断、浮想联翩。一国的法律是在本国的文化传统下生成的,一国的法条是运用本国的文化语言词汇进行表述形成的,在对法条进行解释时一定要符合该国的语义文化,同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避免在理解过程中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唯有此,才能对法条作出科学的、合理的、善意的解释,否则任何一个完整的法律规定都会有漏洞,结果对一个法条会出现一百个人有一百种解释或理解的情况。法条自身具有实现法律价值的性质,因此,在解释论中,也必须进行保护法益、维持社会秩序以及保障人权等内容的目的论的解释[7]。而解释者完全可以朝着理想的方向得出解释结论,事实上,解释者的智慧,表现在既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不超过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又使解释结论实现正义理念、适合司法需求。所以,解释者要以善意解释刑法,而不能像批评家一样,总是用批评的眼光对待刑法[8]。
结语
类似本文这样的案件是多发的,办案部门经常会遇到,但是对基层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来说的确是难以判断的,结果往往会出现罪名认定不正确的情况。希望通过分析,能够对基层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办案有所帮助,使他们在工作中遇到此类案件时能够准确快速地作出判断,从而避免在遇见一个案件涵盖多个罪名事实情节的情况下,对罪名发生张冠李戴的情况。
[1][俄]斯库拉托夫,别列捷夫.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下卷)[M].黄道秀,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425.
[2]何荣功.也论盗窃与抢夺的界限——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J].当代法学,2012,(4).
[3]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517.
[4]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511.
[5]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519.
[6]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25.
[7][日]大谷实.刑法总论(新版第2版)[M].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7.
[8]张明楷.刑法学研究中的十大关系论[J].政法论坛,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