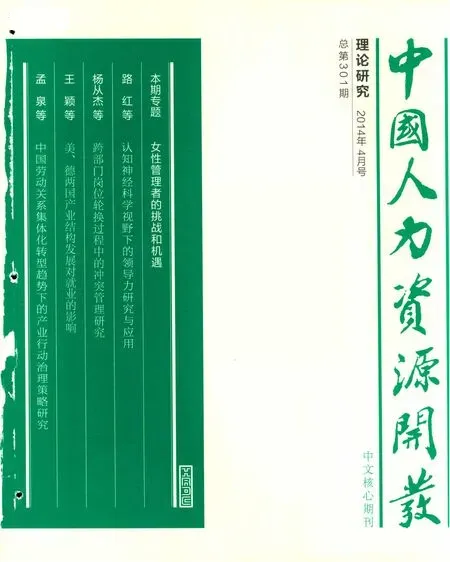中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趋势下的产业行动治理策略研究
●
■责编/张新新 Tel: 010-88383907 E-mail: hrdxin@126.com
一、缺乏规制的产业行动
随着2010年中国沿海地区代工厂工人罢工潮的出现,针对中国新工人抗争的相关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些引发讨论的问题不仅涉及工人团结模式的分析,亦涵盖了在工人产业行动驱动之下,后续工会组织与劳动制度的诸多变化的研究(汪建华、孟泉,2013;吴清军,2012;Chan & Hui, 2012)。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即中国劳动关系已经呈现出集体化转型的趋势(常凯,2013)。对这一发展趋势的判断主要基于中国劳动关系现实中两种变化。一是主体行为的转变,二是因主体行为变化而引发的制度的变化。主体行为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工人大规模的产业行动不断出现,如我国2010年夏季沿海地区爆发的以日资企业工人抗争为主的停工潮,如在广东、大连、天津等地一系列连锁产业行动事件。制度变化主要体现在集体协商再次成为协调劳资关系的重要机制而再次受到重视,以及一些地方性法律法规的出台与改革。
然而,正如陈步雷所指出,目前我国对于产业行动的治理模式仍旧存在“实施模糊与回避策略的问题,导致现有法律所规定的体制内治理方法,无法回应和处理此类尖锐的矛盾冲突。因此,目前的治理方式反映了集体行动规制中“形强质弱”的问题①(陈步雷,2009)。在这种制度匮乏的前提下,工人产业行动无法得到有效的规制,劳资冲突也无法在制度框架内得到有效解决,很容易造成劳资冲突转化为骚乱及社会动荡,对劳资双方都会造成巨大损失。如富士康太原、烟台分厂的大规模骚乱便是例证。而从理论上来说,产业行动立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工人集体谈判权利能够发挥功能的保障是国家对产业行动权利的赋予及确认,其方式就是对产业行动立法。这样就可以避免产业行动升级为劳资对抗、社会骚乱,甚或危机国家政权(刘诚,2011)。另一方面,劳工三权之间的关系亦是密不可分的,产业行动权是集体谈判权有效实施的保障(常凯,2004)。
一些经验研究显示,大多数情况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推行依旧延续了过往指标化管理的模式(吴清军,2012)。尽管国家与工会对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进行了广泛的推动,而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化解并预防罢工的出现,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企业劳动关系。但是,工资集体协商是否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工作场所内部规范劳资博弈,平衡劳资利益的长效机制则值得商榷。一方面,数字化、指标化的管理易出现重集体合同数量,轻员工参与质量的问题。另一方面,有学者指出,2010年以来的罢工暗示出中国集体谈判的启动需要一种“潜机制”,即依靠工人的产业行动才能启动。这样的“潜机制”实际上增加了集体谈判的成本,所谓谈判成本的前置(李琪,2011)。
实践证明,在缺乏产业行动权的法律的保障作用的条件下,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利只能依靠行政力量来保障,结果则造成了缺乏有效参与的集体协商,产业行动则成为了启动有效集体协商的潜机制。本文认为,工人集体权利的立法缺失在现实中则造成了权力运行的倒错。然而,这种制度空间缺乏的现状却又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结构性条件。本文希望通过对产业行动制度化现实基础与治理困境的分析,回答在制度支持不足的状况下,如何从地方应对产业冲突现实经验中发掘治理空间,并依靠何种社会动力机制推动制度产出。
二、我国完善产业行动权立法的现状、原则及现实困境
(一)我国产业行动权立法的相关规定
首先,根据我国现行的《宪法》规定,罢工并不是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虽然我国在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中曾经承认罢工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但是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删除了这一权利。直到现在,罢工权仍然不被立法所肯定,宪法对这一权利行使的保护更无从谈起②。
从现有的劳动法律体系来看,《工会法》第27条提出了“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然而,《工会法》没有明确规定罢工等产业行动作为合法形式,当然也未规定产业行动是违法行为。另外,该法对“停工、怠工”的规定也没有做出详细的解释和界定。只有在劳动者的权益被严重侵害的情况下,工人产业行动的行为才被法律认可。模棱两可的规定导致中国的工会可以支持劳动者离开危险的工作环境,但却无法支持工人合理的产业行动。总之,产业行动的形式在我国劳动法律体系中并没有明确其性质,这导致法律无法对劳动者的行动进行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劳动者权利的实现(涂伟,2013)。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集体停工、怠工的说法与罢工无异,此法条明确了工会在工人发生产业行动之后,应当代表工人向企业提出要求,并能够最终解决工人提出的合理诉求,既部分承认了产业行动权的合法性,又规定了工会代表工人处理产业行动的身份与责任(刘诚,2012)。本文认为,从长远来说,基本法律概念的界定不清,只能降低对工人产业行动权的保护,也不利于对产业行动权的限制。一旦政府对该法条把握不准确,在解决劳资冲突中没有把握好尺度,则会造成更加恶劣的劳资冲突乃至社会动荡。
除了《工会法》中对产业行动权的规定之外,一些地方法律法规也对这一权利进行了规定,如《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52条、53条规定③。这两条相关规定虽然体现了对产业行动权的保护性和限制性的双重规制的特点,但是,第52条实际上是对《工会法》27条的细化与延伸;53条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更加维护社会稳定。总体来看,无论是《工会法》还是地方法规都没有解决产业行动权的基本问题,即对于产业行动权立法的基本原则和法律要件依旧模糊不清、不甚全面。然而,聊胜于无,现有法律至少可以成为目前政府应对、治理劳资冲突的制度资源。
(二)我国产业行动权立法实现的困境与可能性
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发展的规律来看,产业行动的制度化是治理产业行动和劳资冲突的有效手段,导引产业行动走向产业和平。然而我国在经济发展模式、政治体制以及劳资主体的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产业行动权立法造成了障碍,形成了产业行动权制度化的困境。
首先,社会治理与社会维稳之间的矛盾为产业行动权的权利归属问题造成了障碍。从宏观层面来看,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削弱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基本矛盾,不仅体现在现实矛盾造成的治理问题上,也反映在应对这一矛盾的治理机制之中(周雪光,2011)。根据我国治理工人产业行动的传统,产业行动都被归为群体性事件,而工人产业行动则属于职工群体性事件。因此,政府过往治理“职工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基本上就是“消防员”式的镇压与协调(Cai,2008),从而实现社会维稳的目的。社会维稳的治理原则体现了权威体制的特点。然而,政府提出社会治理的理念,意在能够通过长效治理策略缓解社会张力,协调社会矛盾。对于劳资矛盾的治理来说,2010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如广东、大连的经验通过工资集体协商方式解决产业行动问题的经验(孟泉、路军,2012)。这类经验虽然能够在短期奏效;但是,《广东省民主管理条例》的夭折与全总一直以来坚持不支持罢工的态度,说明了在权威体制下产业行动权利的制度化空间是十分有限且处处受限的。地方经验也因制度缺失而具有不确定性。
本文认为,产业行动权利制度化或法制化的根本问题在于权利的归属,即到底是将权利给予工会还是工人。从劳动关系的性质来看,产业行动权利的边界实际上并非是在主体互动之前就已经被确认的,而是通过参与劳动关系的主体之间通过互动与博弈,并随着博弈的环境和博弈参与者各自占有的资源状况、认知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刘世定,2012)。所以,产业行动权应作为一个多方力量介入劳资冲突的过程之后,为实现各方利益平衡而需要规制的权利来看待。但是,这个权利的确立却遭遇了顶层设计与博弈结果的双重影响。政府的权威体制决定了在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产业行动权的确立必然难以付诸实施。一方面,工会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工人组织来代表工人的利益,因此,在通过法律赋权的过程中,工会必然是产业行动权的赋权对象。另一方面,在我国绝大多数产业行动都是工人自发组织的产物,囿于政治上的限制,工会却不能组织工人以产业行动的方式与雇主博弈。但是,真正博弈结果的形成却还是由于工人自身力量的存在。这就造成了常凯所指出的两种劳工力量之间的张力与融合的问题(常凯,2013),也就牵涉到如何找到两种劳工力量的融合,从而将劳工的团结力量转化为制度规范之下的产业行动权利的问题。
其次,地方政府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与资本引入的重视亦阻碍了产业行动的制度化进程。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然而,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仍旧是地方政府的核心原则。加拉格尔认为,尽管《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出台,但是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仍旧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原则(Gallagher,2005)。这也就导致了《劳动合同法》在执行的时候,某些地方政府会根据经济状况而调整执行的力度(Friedman & Lee,2010)。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配合富士康内迁而协助其招工的行为也证明了地方政府对于资本的重视。另外,广东省政府应对2010年罢工潮的过程中,强调要将劳资冲突要去政治化。显然,这一社会治理的策略是非常明智的,但是,这一治理策略同时也是为了配合广东省政府“腾龙换鸟”的经济发展战略应运而生。并且,《广东省民主管理条例》因香港商会的反对而夭折也说明了资本的力量对产业行动权利法制化进程的制约力。
除此之外,劳资双方的主体意识不成熟,也是限制产业行动权的重要因素。一方面,2010年以来在全国各地爆发的罢工事件基本上属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发性产业行动。而从沿海地区的案例来看,这种自发性集体抗争的目的基本上基于工人为工资增长而形成的实用主义团结(汪建华、孟泉,2012)。从工人行动的过程来看,其组织性并不具有良好的延续性,当暂时维持工资增长的机制被满足之后,大多数工人也不再主张产业行动权利。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在权利意识、法律意识、行动意识与策略意识方面都有所提高,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产业行动仍旧是手段而非目的。甚至,对于深圳这样工人产业行动高发的地方来说,农民工的行动在缺乏法律规制的条件下,多呈现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状态(王同信等,2013)。因此,他们对于产业行动权利的认识尚属于非常模糊的阶段,缺乏理性的引导与启发。
另一方面,对于雇主一方来说,对于工人的产业行动缺乏理性的态度。这导致雇主在面对工人的抗争时,多持有不理解、反感甚至对抗的态度。这也致使资方对劳资冲突的处理,出现滞后反应的问题或强力对抗的策略。据笔者调研,在2010年沿海地区发生的罢工潮中,大连开发区相当一部分日资企业之所以会出现罢工主要由于雇主在发觉工人行动的苗头时,并未及时针对工人的不满及时开展集体协商,而最终导致错过了避免劳资冲突的时机。这说明雇主对于工人反抗意识与产业行动的频繁出现并未做好准备,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同时,雇主对于市场经济劳动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并为建立成熟的雇主意识。故而,在劳资双方的主体意识都尚未成熟的条件下,产业行动权的立法必然也会面临缺乏现实基础的挑战。
综上,尽管产业行动权的制度化本质上意在通过对工人产业行动行为进行规范,进而能够降低劳资双方因罢工而产生的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而产业行动权的制度化进程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境下仍旧面临诸多限制与挑战,使得政府在产业行动权立法中必然不会轻易对于产业行动权进行立法。但是,从理论上说,产业行动权立法的最终目的是能够保证劳资双方在博弈过程中,能够实现权利对等、力量平衡,这一点已经逐步为很多劳资冲突多发的地方政府、工会组织深刻的认识。同时,在这些地区也产生了很多治理工人产业行动的策略与经验,这对于缓解大量的产业行动所造成的社会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也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行动权立法的现实基础。
三、我国应对工人产业行动处理方法
承前所述,自2010年沿海地区的连锁性产业行动,一些地方政府和地区工会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意在能够迅速化解并提前预防工人的产业行动。这些策略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的地方治理模式和治理策略。地方经验包括广东经验、深圳经验和大连经验;治理策略则包括集体协商、员工参与、劳资沟通和预警机制等。本文希望能够通过对这些模式及策略的分析,为目前缺乏宏观制度支持的中国产业行动的问题提供一些可资借鉴解决及预防的经验。
(一)应对工人产业行动的地方经验
广东经验的形成有赖于2010年引发珠三角汽配行业罢工潮的代表性案例——南海本田事件的治理经验。在南海本田厂工人发动产业行动之初,雇主的应对主要方式就是威胁与镇压,而这种应对方式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南海本田工人持续的集体抗争。随着劳资冲突的不断升级,广东省委省政府开始关注该事件的发展,并明确指出将“南海本田事件”作为经济性劳资纠纷来处理,不要将事件升级为政治性事件。并且,广东省政府进一步强调,解决该事件的关键之处就是要明确劳方的利益诉求,通过推进劳资双方针对工资增长的集体协商来平息劳资争议。广东省政府对处理南海本田事件所持的态度十分重要,一方面为劳资双方从冲突走向协商打开了足够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广东省政府能够理性对待工人产业行动的基本态度。
在地方政府处理产业行动的原则明确之后,由南海区劳动局、区工会等会同出面调停、斡旋劳资矛盾的两位专家,积极推进劳资双方进行工资集体协商,最终劳资双方在工资增长方面达成共识,工人的产业行动也得到了豁免,企业不予追究工人的责任。在该事件成功平息之后,省工会又积极的介入南海本田厂,指导劳资双方进行工会选举和集体协商,本田工人的工资通过有效的集体协商在2011和2012年都得到了增长。该机制也逐步成为有效预防工人产业行动的机制。
本田经验迅速成为了广东省治理罢工的经验。在本田事件之后,就广州一个城市爆发的罢工就有近百起。广州市总工会在借鉴了南海本田事件平息的经验,积极主动地在第一时间介入劳资冲突现场,支持企业工会说服并组织工人选举协商代表,征求并汇总工人的意见。在整个过程中工会始终保持独立性、自主性和主体性。广州南沙电装厂工人产业行动的解决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证(陈伟光,2012)。
总体来说,广东经验的主要特点就是能够通过地方工会与企业工会的及时介入,在上级工会的支持下,企业工会能够组织工人通过选举工人代表,汇集工人的诉求及意见。而后,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化解劳资冲突。
如果说广东经验更多地体现在事后解决,那么,深圳经验的优势就在于事前预防。众所周知,深圳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为成熟的地区,也是劳动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自2007年以来,深圳地区工人发动的产业行动不断见诸媒体,如2007年的盐田国际码头工人的产业行动,2011年由于康师傅收购百事可乐引发的白领工人的产业行动,同年深圳海量存储女工发动的产业行动以及比亚迪、欧姆、冠星、富士康等一系列工人的产业行动事件此起彼伏。而自2010年以后,深圳市总工会密切注意到了深圳市大量工人组织意识萌发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的劳资冲突问题。于是,深圳市总工会通过对工会组织建设的工作经验的总结和梳理,确定了“民主选举产生、规范化运作、向职工群众负责”的工作思路。并且,深圳市总工会,以理光公司的集体协商和工会组织工作模式为基础,也在千人以上的企业当中开始推行规范化民主建会的工作(王同信等,2013)。
规范化民主建会的核心就是能够通过企业工会组织工人进行选举,将权利交给工人,让工人自己选出能够代表他们权益的基层工会组织。在此基础上基层工会组织在工人和企业双方的公信力同时得到提升,从而可以更加有力地组织工人与资方进行集体协商。最终基层工会规范化民主建设的推进有利于企业内部更加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形成,有效地避免了企业劳资冲突的发生。工人工资可以得到有序增长的前提下,其与基层工会的团结度也得以加强,进而逐步转变为更加理性的工人群体。产业行动爆发的可能性也大幅降低。
大连经验的形成则在北方沿海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其地方经验可以概括为基于本土制度化的“上带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构建。大连经验的产生完全肇始于大连开发区工人产业行动的历史。应该说,在1994年该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劳资冲突,2005年十七家企业又爆发了连锁停工潮。而时至2010年,该地区爆发了连续73家企业工人连锁式产业行动。尽管所有的事件通过工会和地方政府介入,以劳资集体协商的方式平息。然而,2010年罢工平息之后,大连开发区总工会对企业工会开展集体协商机制的工作模式做出了重新的考量和总结,将企业工会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建设最核心的任务定位于两点,即预防罢工和工资增长。
据此,区工会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联合市人社局展开了对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改革。区工会认为,在企业中工会与雇主在展开集体协商的过程中面临双重压力。这种压力一部分来自工人对工资增长的诉求,另一部分则来自雇主对区工会身份与行为的限制。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找到一个策略能够将企业工会从这两种压力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平衡、解决劳资之间因工资问题产生的矛盾。于是,区工会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引入了开发区的企业工会集体协商机制。这一制度实际上已经为很多不同类型的企业作为一种制度资源,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加以再度开发和应用,这一企业工会的行为被视作发展民主参与改革的有效途径(冯同庆,2011)。
首先,区工会认为如果企业工会能够通过职代会制度与集体协商制度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有效地将企业工会从原有面对工人代表性不足的尴尬局面中解放出来。通过工会主导的工人直选,职代会成为了可以聚集工人意见的工会附属组织,但是这一组织对工资增长等问题所形成的最终意见就基本代表了所有员工统一的意见。另外,职代会还成为了工会工作宣传的一个阵地,在职代会上工会主席会让所有参会的职工代表了解到企业工会为工人工资增长所付出的努力。因此,工会通过在职代会表决的过程中,获得了工人的授权,也同时提高了企业工会在工人心目中的地位。这种组织裂变的方式有效的增强了企业工会的内部合法性。
其次,为了保障这一组织裂变策略能够顺利实施,区工会还在工资增长标准方面制定了配套的制度,即由区工会推出的所谓“五年倍增计划”。区工会认为,企业工会过去的集体协商机制的另一个问题就缺乏一个合理的工资增长指导线。所以,“五年倍增计划”就成为了企业工会在职代会上与工人代表商定工资增长幅度的一个基本参考标准。这一标准的合法性部分来自“倍增”二字,即能够让工人的工资得到有序的增长,且是一种具有政府公信力的预期;另一部分源自这一标准是要结合企业本身状况进行调整。这样既可以让工人对工资增长有一个愿景,又可以接受企业工会提出一些调整增长幅度的意见。
除此之外,为了帮助企业工会缓解在集体协商中雇主一方的压力,区工会还会提前和该区日资企业商会展开非正式的讨论和协商,尽量利用其代表政府的身份来让日资企业商会与其在工资增长问题上达成一致。这样就使企业工会在与雇主集体协商的过程中,就工资增长的底线与日方雇主达成默契。而工人代表通过职代会所认定的工资增长幅度,亦成为了工会争取更多工资增幅灵活空间的重要依据和压力手段。
外企联的优化建设也成为了工会制度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支柱。其一,通过区工会与人社局的联合行动,职代会与集体协商结合起来的联动机制得以在外资企业中充分的建立、实施。企业工会不仅得到了上级工会提供的培训和指导,也受到了上级工会的激励与监督。其二,2010年罢工潮发生之前,区级工会也召集了部分在开展集体协商工作中成绩显著的企业工会组成了以区域为单位的非正式工会信息沟通网络。这些经验丰富的企业工会主席成为了不同区域的组长。企业工会组织之间利用这一网络能实现集体协商工作信息相互沟通的机制,从而能够交流策略,确定相对合理的工资增长标准。区总工会以此网络为基础,发展优化了该区的外企联。外企联的组织结构更加正规。总体来说,外企联的建立和运行,提供了企业工会交流集体协商经验、互通有无的一个平台。在这个被制度化了的网络中,企业工会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形成了企业工会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就导致了制度化基础上的模仿机制,并促进了企业工会组织的趋同化(周雪光,2003)。因地制宜的制度化改革将是预防产业行动出现的有效手段。
(二)应对工人产业行动的有效策略
综合以上三个具有典型性的地方经验,应对产业行动的治理策略需要理清产业行动治理的条件与实施机制两个部分。
应对工人产业行动的条件包括开放政治空间、工会尽职尽责。首先,开放政治空间意指政府在面对工人产业行动出现之后,尽量不要以镇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事件升级。并且,政府能够支持地方与企业工会积极介入解决、平息事件。其次,工会尽职尽责包涵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工会的法律职责,即工会介入劳资冲突之后,要秉承现有可以参考的制度资源,如《工会法》第27条、《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52条等。其二是工会的代表性职责。实践经验证明,工会在遇到工人产业行动的问题时,若不能站在工人的立场反而为雇主服务,则很容易引发工人加剧对现有工会的不信任感,从而提出改组工会的诉求;更容易引发工人的不满与抱怨积重难返,进而产业行动有可能上升为对社会稳定产生更大负面影响的骚乱事件等。因此,工会的代表性职责就需要首先站在工人的立场与资方积极通过对话、协商等方式平息罢工。然而,如果企业工会的工作难以开展,则上级工会有责任给予企业工会必要的支持和指导。
机制包括推进集体协商、实行民主建会、日常沟通与预警。第一,在工会介入的基础上,依靠集体协商机制代表工人与资方商讨,满足工人诉求。但是,集体协商机制不仅是解决劳资冲突的有效机制,亦是预防劳资冲突的有效机制。这就需要企业工会在上级工会的大力支持下,在企业内建立有序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通过与企业针对工人的工资、福利、劳动条件等一系列问题的协商,使工人的工资得到合理的增长。然而,集体协商机制的建立与运行亦需要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如企业具备一定的利润空间,雇主与管理者对该机制一定程度上的理解与认同,工人能够积极参与配合工会的工作等。因此,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能够成为一种长效运行的机制,更需要工会能够在工人与资方的利益之间找到合理平衡点。
第二,实行规范化民主建会是工会增强团结能力的重要机制。实际上,民主建会的要求与实施程序并非是一种机制创新,而是进一步将《工会法》所要求的建立工会的程序落到实处。所谓规范化民主建会的内涵,就是严格按照工会法选举工会干部的要求,在企业中推动所有工人进行投票选举工会主席与工会委员。当然,这一机制的建立与实施亦无法离开上级工会的指导与监督。上级工会的职责在于能够提供基层工会主席必要的培训,从而让基层工会主席能够与工人形成有效的沟通,使企业内工会与工人对这一机制达成基本一致的看法,进而更有效的开展工会选举活动。另外,规范化的民主建会机制还有利于在集体协商过程中,工会与工人之间相互的理解,工会得到了工人的信任与授权,工人则能够更加支持并理解工会在集体协商工作中的努力与付出。最终,在工人对工会工作的充分理解与理性判断的基础上,降低了其因诉求无法满足而诉诸产业行动的可能性。
第三,日常沟通机制与预警机制的建立也非常必要。日常沟通机制包含双向沟通机制,一方面,工会与工人建立的沟通机制,意在能够使工会对工人日常的不满、抱怨和意见进行充分的了解,并能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予以解决。工人与工人组织之间形成有效的沟通机制,可以避免工人积怨的形成,并且有利于工会了解工人对于工资增长、劳动条件等问题的预期,以更好的促进劳资双方集体协商机制的形成。另一方面,是工会与资方建立的日常沟通机制,这一机制是针对工人日常提出的一些意见,工会能够及时与雇主沟通,并解决抑或满足工人的诉求。并且,工会可以利用与雇主或企业管理者日常的沟通,及时了解企业的盈利和经营状况,以便可以在与工人进行沟通的时候,让工人更加理性的理解企业的现状,进而促成在集体协商中双方的合意。
预警机制得以建立与运行的基础有二。其一,预警机制基于良好的日常沟通机制。工会劳资双方的有效沟通有利于工会在日常收集重要的有关劳资双方动向的信息,掌握工人不满与抱怨的来源。从而能够在工人群体内部出现产业行动的苗头时,及时反应,并能够进一步说服企业有所应对。其二,就是企业工会能够形成一套工会委员与员工代表或小组长组成的信息工作网络,通过该网络,企业工会可以及时有效地对工人产业行动的动向进行了解。并且,通过日常对工会委员及员工代表的教育与培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各层级的积极分子对工人不理性的行为进行控制。而后,工会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工人的产业行动的爆发。综上,预警机制即依托于建立一套信息通畅的企业工会层级结构。
通过前述分析可知,就目前我国有别于其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来看,在缺乏制度的前提下,建立一套以基层工会建设为核心的应对产业行动的策略体系是相对现实的。这套策略的建立既能够从制度资源和政治空间中获得工会角色与行动的合法性,又可以通过工会工作的开展整合工会与工人的力量,使基层工会真正能够通过有效的应对策略来解决、避免工人产业行动的出现,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然而,产业行动权的制度支持仍旧是需要政府开始重视的一个问题。因为,即便在基层形成了一套可以长期运作且有效的策略体系,这仍旧是产业行动权的现实基础。而只有通过了制度化的规范,才能通过实现劳资双方的权利对等,实现劳资双方的力量对等。值得注意的是,立法时机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刘诚认为,有三个条件是十分重要的,包括人民民主意识的提高与法制观念的增强;工会组织群众化和民主化的提高以及集体谈判机制的普遍展开(刘诚,2012)。就目前来看,如果上述应对产业行动的策略能够广泛的应用于各类企业,那么,产业行动权的法制化就会迎来最佳的时机。
注释
① 本文认为,所谓“实体化”内容就是围绕劳工三权中的“集体争议权”或曰“产业行动权”权利赋予与运用的一系列法律规则。
② 常凯认为“虽然在中国罢工不属违法,但是中国法律是不提倡罢工和不保护罢工的”。参见常凯:《罢工权立法问题的思考》,载《学海》,2005年第4期,第82-86页。
③ 第52条规定:“因劳动争议发生集体停工、怠工的,工会应当代表劳动者同用人单位谈判,反映劳动者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方案。对劳动者的合理要求,用人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前款情形发生时尚未建立工会的,上级工会应当按照职责分工代表劳动者或者指派职工代表与用人单位进行谈判。”第53条规定:“供水、供电、供气、公共运输等用人单位因劳动争议出现集体停工、怠工、闭厂等情形,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下列后果之一的,市、区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发布命令,要求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停止该项行为,恢复正常秩序:(一)危害公共安全;(二)损害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和市民生活秩序;(三)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利益的后果。命令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冷静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此期限内不得采取激化矛盾的行为。劳动行政部门、工会组织和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在此期限内继续组织谈判、调解,促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达成和解。”
1.常凯:《劳权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200页。
2.常凯:《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完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91-108页。
3.陈伟光:《忧与思——三十年工会工作感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4.冯同庆:《中国职代会制度,一个有希望的憧憬》,载《中国工人》,2011年第6期,第13-15页。
5.李琪:《启动集体谈判的‘潜机制’》,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1年第2期,第82-85页。
6.刘诚:《集体行动法》,载常凯(编):《劳动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17-518页。
7.刘世定:《私有财产运用中的组织权与政府介入——政府与商会关系的一个案例分析》,载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60页。
8.孟泉、路军:《劳工三权实现的政治空间——地方政府与工人抗争的互动》,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2年第3期,第89-93页。
9.涂伟:《论我国产业行动的立法——基于德国的经验》,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3年第1期,第100-104页。
10.王同信、李莹、冯力:《深圳职工队伍与工会工作的状况、特点及发展趋势》,载于汤庭芬主编《深圳劳动关系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页。
11.汪建华、孟泉:《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第165-177页。
12.吴清军:《集体协商与“国家主导”下的劳动关系治理——指标管理的策略与实践》,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66-89页。
13.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8页。
14.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第67-85页。
15.Cai, Y.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Suppression of Popular Resistanc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008, No.193: 24-42.
16.Chan, C.and Hui, E.,The Dynamics and Dilemma of Workplace Trade Union Reform in China: the case of Honda workers’ strike,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2, 54(5): 653-668.
17.Friedman, E.and Lee, C.K., Remaking the World of Chinese Labour: A 30-Year Retro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0, 48(3): 507-533.
18.Gallagher, M.,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00.
-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的其它文章
- 情境判断测验的研究和应用进展
- 人力资源开发当前的研究方向
- 诚征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