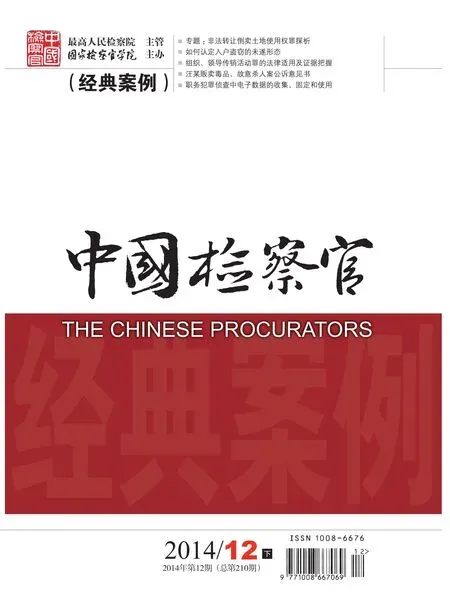主题:《刑法》第37条的适用条件及程序要求
文◎易斌
主题:《刑法》第37条的适用条件及程序要求
文◎易斌*
案名:朱某挪用公款罪案
《刑法》第37条规定的免除刑罚是指对行为作有罪宣告,但对行为人免除刑罚处罚,即不判处任何刑罚[1]。作为一种非刑罚处罚制度,其在发挥功效的同时,也会在适用过程中存在一些亟需厘清的问题。如行为人不具有法定的免予刑事处罚的事由,法院直接适用该法条对行为人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况,不仅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而且在刑法理论界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尤其是直接适用且未经报核程序,成为检法之间多年来始终未能有效解决的分歧点。
下面,笔者试从一起挪用公款定罪免刑的抗诉案件,刍议《刑法》第37条适用的条件及程序要求。
[基本案情]
原审被告人朱某在任某院副院长期间,利用分管院一管理部工作的职务便利,个人决定将管理部公款人民币45万元借给承包该院地下室的某旅社从事经营活动,事隔1年5个月之后,该旅社将所借款项全额归还管理部。在借款期间,朱某之妻到该旅社工作至案发,并取得相应薪酬。该案系9年后案发。
法院审判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朱某犯挪用公款罪,免予刑事处罚。主要理由是:鉴于被挪用的公款已在案发前归还,朱某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结合谋取私利的情节,犯罪情节轻微。适用《刑法》第37条,对朱某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检察机关抗诉理由:第一,朱某挪用公款45万元,属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原审判决在不具备法定的免予刑事处罚条件下,错误适用《刑法》第37条对被告人定罪免刑。第三,原审法院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未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违反法定诉讼程序。
二审结果: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朱某对其妻到某旅社就业所谋取的个人利益情节轻微,挪用公款在案发前已归还,未有严重后果发生,朱某在案后如实供述事实,据此认为朱某犯罪情节轻微,并直接适用《刑法》第37条,对朱某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驳回抗诉。
[争议焦点]
上述朱某案件中,集中反映了检法对《刑法》第37条能否独立适用的不同认识,其核心问题在于,对于不具有免除刑罚法定情节的被告人,能否直接适用《刑法》第37条,是否有相应的程序要求?
(一)《刑法》第37条能否作为独立的免予刑事处罚的依据
这在学界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一是以张明楷为代表的“否定说”认为,不宜直接根据《刑法》第37条的规定免除处罚,即适用《刑法》第37条的前提是具有刑法总则、分则及司法解释关于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2],才能适用第37条,对行为人免予刑罚处罚。二是以何秉松等为代表的“肯定论”认为,如果不具备免除处罚的情节,而又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则应当根据《刑法》(1979年刑法)第32条规定(注:与现行《刑法》第37条相同),判决免予刑事处分[3]。即适用《刑法》第37条不需要具有法定免除刑罚的依据,由法院综合全案情节判断为“情节轻微”,即可单独适用《刑法》第37条而对被告人处以免除刑事处罚的法律后果。实际上,“肯定说”并不是与“否定说”相互排斥,而是“肯定说”的适用范围更为扩大了。
(二)司法实践中,检法对《刑法》第37条的独立适用存在不同的认识与分歧
对于具有法定免除处罚事由,适用第37条对被告人作出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在司法实践中检法并无争议,而且,大多数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也都出自于该种情形。也就是说检法以“否定说”限定的范围来适用第37条,均予认同。
但对“肯定说”的无限定范围的适用,检法确有不同意见,亦有相关的判例,朱某案件便属此类情况。检察机关更加倾向否定说,同时认为不属于“情节轻微”,但法院认为行为人不具有任何减轻、免除刑罚的法定事由下,可以直接适用第37条的规定。对于此种情形的支持,除了审判案例,还体现在高法的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文件中,如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高法沈德咏副院长明确提出:对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能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的,可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三)笔者更倾向于“肯定说”
笔者认为,《刑法》第37条作为免予刑事处罚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原则和行刑经济性等量刑处刑原则,具有独立适用的法律依据和实务基础。但同时认为必须对“情节轻微”的隐含条件有所限定,否则可能导致司法不公正及减轻处罚报核制度的虚置。如果按照“否定说”仅以刑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免除刑罚的事由为前提,方能适用该条款,系对该法条作了限制性规定,未免有所偏狭,且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相关案例置于无据可依的状态中,同时也与高法有关的政策精神相悖。高法就某些犯罪在分则中并无免予刑事处罚的具体事由,但依然能够处以免刑的量刑规定,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于“肯定说”的支持性注释。《刑法》第37条作为总则性条款,是可以根据总则性的刑法规定对各种犯罪共同使用的情节,当犯罪分子不具有具体的免予刑事处罚的事由,经审查认定确属不需要判处刑罚处罚的情形,则可依据《刑法》第37条的规定直接予以处罚。
[抗诉与裁判理由之法理辨析]
适用《刑法》第37条具有理论以及实践上作为独立适用条款的依据,但是在不具有免予刑事处罚情节下,仅凭“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这两个概括性的要件来决定适用该条款,则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上因没有清晰的标准,容易产生分歧意见。以朱某案为例,检法对案件的定罪情节、量刑情节均有相同的认定,但对犯罪情节是否轻微则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对能否直接适用该条款产生分歧。
(一)朱某案件的情节程度评价
法院与检察机关均认定:朱某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具有案发前归还挪用公款、到案后如实供述以及谋取个人利益主观恶性不大等情节,法院据此认定朱某犯罪情节轻微,但检察机关认为朱某仅具有法定、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并不属于犯罪情节轻微,直接适用第37条错误。
首先,该案的数额评价达到了情节严重。该案挪用公款数额45万元,属于挪用公款“情节严重”。如以量刑的数额事实情节评价的角度来看,朱某挪用公款的行为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仅凭此点就不应认定为情节轻微。其次,从谋取利益的事实情节方面评价。朱某在借款初始未有谋取个人利益的想法和行为,在得知妻子到借款单位上班后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可以说,朱某在谋取个人利益方面的情节确实有较为轻微的一面。但此点是否属于对其挪用公款的要件事实有根本性影响的因素,能否决定该案确属“情节轻微”?法院以该情节的轻微性来决定该案事实的情节程度,有所偏颇。再次,从案后的量刑情节方面评价。朱某挪用公款在量刑情节上具有被挪用的公款已在案发前归还,到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等属于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并不具备免除处罚的情节要素。法院仅以法定的从轻量刑情节来直接适用37条,理由不够充分。最后,从法律协调性评价。对于刑法分则明确为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且不具备法定免予刑事处罚的事由时,法院在综合各因素后认定属于“犯罪情节轻微”,造成了一个行为在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之间的两种评价,引起了刑法条文之间的不协调,同时也违反了刑法解释同一性原则。
(二)《刑法》第37条中“情节轻微”的评价标准
从上述朱某案件的情节分析中,不难得出该案“情节轻微”的认定确属牵强,但法院依然有其判断认定的理由,源自于《刑法》第37条中“情节轻微”这一概括性的规定过于抽象与无据,在目前法律没有明确的指导原则与衡量标准下,有必要厘清司法实践中不应逾矩的框架范围。笔者认为,结合朱某案件的情节分析,对于“情节轻微”的考量,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判定:
1.“情节”范围的确定。犯罪情节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定罪情节是指直接说明犯罪构成事实的状况或程度,从而影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影响定罪的各种事实情况。量刑情节是指在某种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前提下,法院对犯罪人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的,据以决定量刑轻重或者免除刑罚处罚的各种情况[4]。
由于《刑法》第37条作为一种有罪宣告,就是在认定有罪的基础上对被告人在量刑上的免除处罚规定。也就是说,适用该法条应当在对定罪情节综合判断并作出有罪认定后,仅对量刑情节进行考量评价,因此该法条规定的“情节”应为量刑情节而非定罪情节。否则,将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5]。
2.确定情节轻微的排除性因素。结合朱某案件反映出的检法对量刑情节的不同评价,笔者认为,在情节轻微没有明确也无法确定明确的衡量标准的情况下,对于行为人具有与情节轻微相悖的排除性因素时,则应当不予认定情节轻微。下面将要讨论的因素都是建立在不具有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的基础上的。
首先,对于加重犯[6]不应当认定为情节轻微。无论是结果加重犯还是情节加重犯,都是在基本犯基础之上加重了法定刑的犯罪,显然与情节轻微相悖,如果对此类情形认定为情节轻微,按照刑法解释同一性原则将产生逻辑混乱。对于刑法分则条款规定的情节严重方可入罪的情节,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属于定罪情节,并不涵盖于此。
其次,对于有数个量刑幅度,而行为人所处量刑幅度高于最低量刑幅度之上的,不应认定为情节轻微。对于这类情况,在不具有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形下,其量刑不能在下一个量刑幅度或更低的量刑幅度内予以判罚,否则将违反《刑法》第63条的规定,对于直接免除刑罚则更加不适宜,且与第63条存在严重失衡。对于确有免除刑罚必要的行为人,则应当通过特殊的程序来予以保障,而不应直接适用《刑法》第37条。
最后,对于基本刑在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个罪,不应认定为情节轻微。这类犯罪起刑高,所显现的社会危害性与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情节轻微所具有的危害程度是极不对等的,二者的量刑内涵要求不一致,且在现有刑罚体系中还有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不可逾越的刑罚种类,对于不具有法定免除刑罚事由的这类犯罪,应予排除在《刑法》第37条适用之外。
(三)对于具有情节轻微排除性因素,但有必要确应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人应当通过相应的诉讼程序确保罪刑相适应与量刑公正并重
在朱某案中,法院以从轻处罚的情节,直接适用《刑法》第37条,将应判5年以上量刑幅度的犯罪跨越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量刑幅度,判决朱某免予刑事处罚。对于朱某是否属于法定刑以下量刑,检法同样产生了较大分歧。检察机关认为,朱某免予刑事处罚属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3条第2款之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从现有刑法来看,对于不应轻判而轻判情形,法律有明确规定应报核,那么对于不具有免罚情形而判免的情况,则更应采取报核的方式加以规制,方能体现刑法条文之间的协调。
而法院对此持有不同观点,正如该案二审法院针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解释:被告人虽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根据案件特殊情况,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按照《刑法》第63条第2款的规定,应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定罪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因行为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可直接适用《刑法》第37条的规定,对被告人判处免予刑事处罚,不需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笔者认为,对于朱案,检察机关的理解更为合理。行为人应处量刑幅度为最低法定量刑幅度时,或具有减轻处罚情节对其处以最低法定刑量刑幅度内时,法院结合全部案件情节,认定为情节轻微,适用《刑法》第37条与现行刑法的其他量刑原则并无太大冲突与失衡,但行为人所处量刑幅度在犯罪最低量刑幅度之上,法院跨越一个或几个量刑幅度直接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将导致《刑法》第37条与第63条第2款的在司法适用上的不协调以及对量刑公正的质疑。该问题并非没有解决的途径,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限制:如果从量刑情节的评价上能达到犯罪情节轻微的程度,该犯罪应当处以数个量刑幅度中最低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的,即使不具有刑法条文的免予刑事处罚的,亦可直接适用第37条的规定,对行为人定罪免予刑事处罚;对于应当在最低量刑幅度之上的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的犯罪,法院如依据《刑法》第37条直接适用判决免予刑事处罚,则需要加以程序上的规制,应当比照《刑法》第63条第2款,即行为人虽不具有刑法规定的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综合全案情节判断,其所犯罪行情节轻微,需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对于高于最低量刑幅度的犯罪,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通过报经高院核准的程序,避免了“举轻以明重”的思维方法遭遇尴尬,也与《刑法》63条第2款趋于协调,避免失衡。在司法实践中,朱某案件的检法分歧通过程序的规制或许就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注释:
[1]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57页。
[2]刑法规定:第10条(域外刑事判决的消极承认);第19条(听说、视觉机能对责任能力的影响);第20条第2款(防卫过当);第21条第2款(避险过当);第22条第2款(犯罪预备);第24条第2款(犯罪中止);第27条第2款(从犯);第28条(胁从犯);第67条第1款(自首);第68条(立功);第164条第4款(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第351条第3款(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第390条第2款(行贿罪);第392条第2款(介绍贿赂罪)。司法解释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1款第2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5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
[3]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页。
[4]同注[1],第502页。
[5]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指在法条中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相关事实,在判断其行为是否构成该当罪责时,既已被考量评价过,即不得再度作为刑罚裁量之事实依据,再加审酌,而以之作为加重或减轻的量刑依据。参见苏俊雄著:《刑法总论(Ⅲ)》,大地印刷厂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414页。
[6]加重犯是指刑法分则条文以基本犯为基准,规定了加重情节与较重法定刑的犯罪,其中又可分为结果加重犯和情节加重犯。参见注[1],第97页。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10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