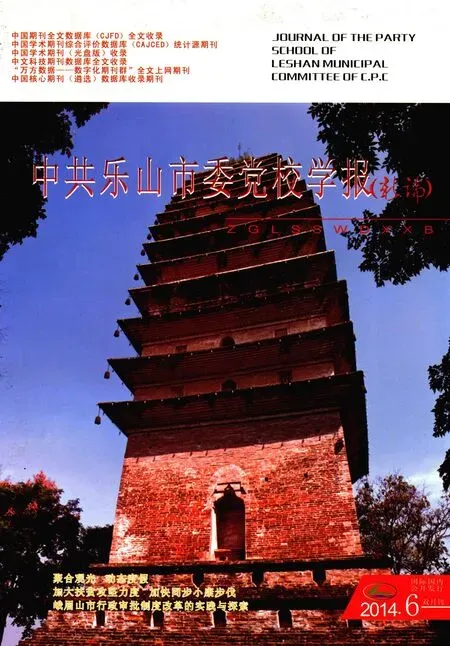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美国个人主义的平等观
吴志成
(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部 江苏 南京 210094)
自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来,自由与平等便成为上帝之城的标签以及国家价值观外推的核心内容。诚然,美国的平等观念挣脱了欧洲大陆传统政治文化的牢笼,却又陷入自由与平等的长程博弈,“独自一人无所谓平等,也无所谓自由,但自由说的是‘别来烦我,让我一个人。’ 平等却说,‘我要和你一样。’ ”美国的平等观显然在群体范畴内讨论自由与平等何者为先,“关于美国社会的讨论主要体现为两种价值观:个人主义和平等。这两种价值观有时候相互对立,有时候又相互补充”。鉴于国外学者曾用“自由主义平等论”指向一切拉平的平等主义,与笔者论述的美国平等观中强调机会均等的要旨矛盾,故使用个人主义的平等观这一说法以避免概念混乱。
一、自由的平等高于一切:美国个人主义平等观的内在逻辑
不可否认,美国个人主义的平等观在历史的沉淀中表现出多个面孔,并大致与传统自由主义发展为新自由主义和保守自由主义的脉络相互平行,呈现为对平等的关注程度变化,“罗尔斯复兴的不只是政治哲学和自由主义,而且使现代政治哲学研究的主题实现了从自由到正义、从自由到平等的转变”。但自由的平等高于一切仍是贯穿其平等观的内在理路。
(一)机会均等:个人主义平等观的逻辑前提
1.起点的平等:基本自由的分配。美国个人主义的平等观主张起点的平等,即人生而平等,人们的竞争须在同一“起跑线”上。这种起点平等的观念似乎并不是美国特色,亚洲国家也将人生而平等写入本国法律之中,但美国人却将这种起点平等深植于基本自由的分配,基本的自由即“政治上的自由(选举和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及言论与集会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和保障个人财产的权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政治自由分配的平等保障政治人参与社会利益的分配,而个人平等的自由争取远高于公权赋人权的荒谬承诺。
2.过程的平等:自由规则的保障。起点的平等是机会均等的重要内容,天赋人权的诺言体现在对自由的分配。然而,过程的平等对于起点平等而言更具有长程效应,是机会均等的关键环节,正如赌场有赌场的规矩,社会的运行必须建立起一套规则体系。相较于英国注重通过繁琐的程序来保障平等,美国习惯于在自由原则中造就形式平等。尤其表现为,美国人对于法律的权威表面上采取漫不经心的自由态度,但在实际运行中却极力维护宪法尊严,因为自由的规则才能保障他们的自由,自由是目的,但更是手段。
(二)个人主义平等观的自由价值维度
1.上帝之光:基督伦理中的个人平等。美国人以上帝选民自居,他们相信上帝仁慈的光芒会照射美洲新大陆和自由的美国人。清教文化是美国文化深层的宗教基因,也是透视美国个人主义平等观的重要视角。清教是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是基督教的一支,清教徒们为避迫害纷纷来到美洲大陆以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需要强调一点,清教伦理并不主张人生而平等,这在《基督仁爱之典范》 中得以体现,即仍然强调等级的稳定,但清教伦理作为基督教的支流仍然继承了欧洲宗教传统。
基督伦理思想中,相对于上帝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总是匍匐在上帝面前,在原罪的天然拥有上都是平等的。“在上帝面前,无论其世俗地位的高低,都是罪人,纵然是等级森严的罗马教会也不能否定基督教内含的这种平等思想。”人首先是罪人,上帝通过职业的分配考验人的赎罪过程,在这一层面上人是平等的。“清教称职业为calling,也就是呼唤,谁的呼唤呢? 当然是上帝的。”
2.凯撒之死:社会契约中的民官平等。“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西方政治政教分离的传统在神权吞噬王权的黑暗中世纪遭到阉割,启蒙运动却以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重新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地位。与上帝之约不同,社会契约植根于世俗领域,规定着公民与政府的权利义务关系。美国人从来不将政府看作是善的化身,而是出于个体权利保障的目的造就了这一必要的恶,他们深知过分依赖政府的后果便是利维坦的肆无忌惮。凯撒之死并非上帝对世俗领域的干涉,而是在世俗领域内政府权力被极大地限制,作为洪水猛兽的生命在社会契约中完结。
正是由于社会契约的订立,美国人在政治生活中习惯于用平等观念来考察参选者的可信任度,他们期待在服饰、语言和动作上与其高度一致,任何表现得犹如英国绅士风度的行为都被视作对大众的侮辱。“在美国,人们对政治平等的要求比政治民主的愿望更加积极,财富并不完全是渴望从政的人的基础,而平等观念则被民众视为从政至关重要的条件。”
3.妥协之魅:宪政精神中的州国平等。由于对中央政府统治的恐惧,美国建国伊始便以邦联制作为政府统治的结构,这种邦联制则表现为中央权力的弱化与地方权力的膨胀。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各州制定的关税条例相互冲突,“尽管这些额外关税对美国本土的产品没有什么影响,但似乎就商业利益而言,美国明显需要建立起一种中央集权来对商贸加以调控”。这种风波以一场起义为巅峰,并坚定了进行邦联制改革的决心。
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与会代表就各州以何种方式加入联邦的问题进行了激烈地辩论。“会上首先出现冲突的是关于国会代表人数的问题,最后通过 ‘伟大折中’ 得以解决,双方都作出了让步。”各州在参议院席位上均有2 个名额,这保证了大小州在地位上的平等,而众议院则以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席位,又不致大州权益受损,形成了折中方案。在州与州的平衡中,州与联邦的关系也是争议的话题,各州虽然不得不将部分权力移交联邦,但他们仍然警惕着联邦权力的过度膨胀,力求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比如,“新的政府框架明确禁止国会通过剥夺公权的法案或追溯既往法律。而且它还保留给各州以大面积的领土主权——宪法第十修正案不久便明确了这一保留。”
二、媚金与寡头:美国个人主义平等观的现实演绎
(一)金钱政治的私人财产崇拜
美国个人主义的平等观自始至终被打上自由主义的烙印,而私人财产决定了自由的限度。美国人同英国人在财产权问题上高度认同,都认为财产权是保障自由的有力武器,私人财产的合法认定和维护是头等大事。英国政治学家洛克在 《政府论》 中也强调在社会契约中,私人财产权不可让渡,这与霍布斯的个人权利的全部让渡的君主专制倾向大相径庭,其描绘了一幅个人以私人财产权为阵地抵抗政府侵蚀的宏大画面,凸显了自由平等精神。众所周知,由于个人禀赋的先天差异,每个人的资源汲取能力不同,最终在财产上的贫富差距拉大。经济上的不平等又导致在政治参与上的弱势地位,政治利益的合理性分配便无从谈起,这形成了恶性循环。在当代美国,政治与金钱高度结合,美国总统选举是一场规模庞大的金钱游戏,并呈现出选举经费不断攀升的趋势。利益集团拥有全美国大部分的财富,他们以政治捐款的方式操控政治的走向,并在新的政治集团上台后攫取本集团利益。显然,美国政治已经成为金钱的游乐场,私人财产权的合法化将贫富差距合理化,并使民众在经济上的不平等愈发明显。原本对私人财产权的认可是为了对自由的保障,这与起点平等中对基本自由的分配看似在同一立场之上,但私人财产崇拜在高歌猛进中伤害了普通民众对政治自由的获取。政治自由的目的本来是为政治平等,但贫富差距的悬殊将政治自由置于虚假的程序民主,在这个层面上个人主义的平等观中对自由至上的认可明显最终愚弄了平等。“美国公民拥有法律上的普选权,但选举团制度和高额的选举经费等,导致了选举权事实上的不平等,造就了美国的精英政治和等级政治。”
(二)精英治国的政治寡头铁律
“克鲁格曼认为,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增长,体现在寡头统治的崛起,底层收入者占有的财富越来越少,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特权精英手中。”这显然是个悖论,美国以大众文化为其国家核心文化,对英国的精英主义传统保持着鄙视的态度,并在国内极力抵制精英主义的泛滥。然而,个人主义的平等观以自由至上,这种自由包含着人们以不同的禀赋参与政治竞争的合法性,过程的自由彰显了结果的合法性,而这种结果绝非实质的平等。美国各行各业都涌现出大批精英,他们在自由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运用他们的先天禀赋汲取政治资源,很快进入权力核心。利益集团同政府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利益集团以各种方式将本集团精英输送到政府中,并为其提供施行政策的环境,使政府如同提线木偶。政治精英的竞争暗藏利益集团的力量博弈,这已经成为美国众所周知的秘密。利益集团的博弈必然产生多个政治寡头,政治寡头的出现则宣告在政治领域的自由垄断,基本自由的分配便不是程序民主的产物,而只是政治寡头的囊中之物。帕累托的精英民主理论就是要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精英集团,在精英集团的博弈之下形成社会进步的潮流。显然,美国的个人主义平等观中的自由主义内核成为精英治国的理论庇护,实质上的平等观念则在寡头铁律中逐步消解。
三、美国个人主义平等观的现实困境
不可否认,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美国政治哲学家曾在理论层面对个人主义的平等观进行改造,诸如补偿原则的提出等等,但却在社会践履中屡遭挑战,社会经济地位的平等被斥为乌托邦。美国个人主义平等观植根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对其现实困境的剖析必然以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为参考对象。
(一)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制度性干预
根据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的论述,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固有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源。自美国成立以来,其并未逃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噩梦,大大小小的危机周期性上演。美国个人主义的平等观与其说是积极自由的平等观,还不如说是消极自由的平等观,平等是在不受外来力量干预下的平等,任何非内生的力量都被视作不平等的源泉。然而,由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国家必然通过“看得见的手”来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人们的市场理性在国家理性面前显然失去了平等地位。经济危机的调整不是简单的货币过程,而是制度性过程。在经济危机传统中,美国政府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套制度性调节措施,这些措施重新调整了生产、流通、销售环节的关系,将计划的力量置于市场效能之上。制度性的经济措施映射在社会关系之中,成为制约公民自由贸易的手段,而公民只能忍受增发货币带来的工资实际购买力的下降,在市场预期下,公民成为信息的不对称接受者。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体现为利益集团在经济危机操纵中赚取额外收益。
同时,经济危机赋予了政府救世主的权力,纵观美国经济危机史,每一次的经济复苏都伴随着总统行政权力的膨胀。行政权力以危机终结者的姿态大肆争夺立法和司法的领地,三权分立的边界越发模糊。富兰克林·罗斯福蝉联三届美国总统便是对美国宪法的挑战,但美国人从来都没有正式看待这一违宪行为,而坦然承认经济危机下扩大总统权力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人的消极的平等观念也成为风中芦苇。
(二)政府创造机会均等的神话破灭
美国个人主义的平等观强调机会的均等,认为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的自由竞争结果必然是合乎理性的。机会的均等在自由主义中尤为关键,而政府本身是机会均等的载体和提供者。保守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应该扮演的守夜人角色已不适应美国的现代化生活,新自由主义反而提供了具有现实操作性的主张,即政府扮演规则制定者和裁判者的角色。虽然新自由主义将政府置于重要位置,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个人主义平等观的价值,但作为补救措施被广泛接受。然而,政府却未能如新自由主义者所愿,即积极创造机会均等的社会环境,反而使这种补丁式的主张犹如美国社会的鸡肋,激起美国右翼分子和众多公民的攻击。
机会均等的创造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无论是就业机会的均等还是就医机会的均等,都需要建立起庞大的信息交流系统,而且不可避免的需要政府与社会组织通力合作。然而,美国近年来出现的“占领华尔街”事件折射出政府创造机会均等的失败。贫富差距的拉大使美国民众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出现严重的不平等,教育资源的优劣程度影响着公民的社会地位,低收入人群相较于高收入人群显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政治自由的承诺并不能保障自下而上的从政渠道畅通。
(三)机会均等与差别补偿的不对称博弈
罗尔斯在其 《正义论》 中提出差别原则,这在长期关注自由甚于平等的美国社会引起革命性的变化。有学者指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本质上就是对平等的论证,而且这种平等还是一种事实上的平等、一种结果的平等。”但是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仍承认自由高于平等,并未在逻辑上颠倒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这种差别原则的提出即使在自由主义内部也免不了遭到冷眼相对,以诺齐克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家对其激烈批判。美国个人主义的平等观在近代显现出对平等关注的提升,但这种“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却从未占据主流地位,其主张的实质平等对美国人而言无非是乌托邦。不可否认,这种对平等的关注有其现实考量,在贫富差距巨大的美国成为心灵抚慰的鸡汤抑或是政客争夺选票的口号。
然而,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在现实操作上并不容易,政治力量的博弈过程清晰表明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的丢失。差别原则主张对弱势群体采取差别化的补偿措施以显示自由主义的正义精神。但对弱势群体的补偿不是政府心血来潮就可以推动的,这在自由的美国社会中显然充满变数。近年来,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动的医疗改革措施始终得不到国会的支持,造成社会保障改革的延缓也使民众对其竞选诺言产生质疑。美国政府与利益集团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微妙关系,任何有损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政策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反弹,普通民众与既得利益集团间的不对称博弈必然捅破差别原则的假象。
美国个人主义的平等观在自由与平等间左右均衡,但保守主义的自由观始终主导美国平等观的历史走向,任何企图规制自由先于平等的原则都将付诸失败,其挣脱欧洲平等观的束缚却又重新陷入自由至上的陷阱之中。美国一直致力于普世价值的推行,但却未能理清其个人主义平等观的内在逻辑和现实困境,这显然是个悖论。
[1]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美]卢瑟·S·路德克.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李新廷.从起点的平等到结果的平等——读罗尔斯 《正义论》 [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
[4]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施袁喜.美国文化简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6]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
[7]翁淮南,王慧.美国社会真的是机会均等吗? [J].党建,2013,(04).
[8]于海青.美国社会平等吗? [J].红旗文稿,2013,(05).
——以《文化偏至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