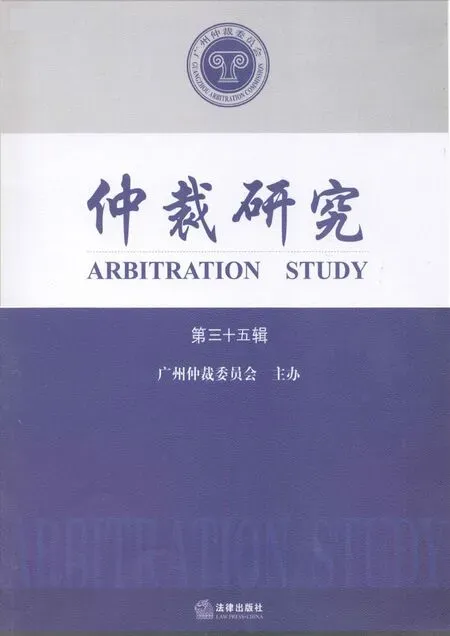商事仲裁从绝对保密到相对保密——以上市公司仲裁公示义务与保密义务的冲突为视角
王伊晋
商事仲裁从绝对保密到相对保密——以上市公司仲裁公示义务与保密义务的冲突为视角
王伊晋*
保密性被长期视为仲裁的属性和优势,仲裁因此而深受重视商业秘密和商业信誉的商事主体的青睐。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和变革,商事仲裁的绝对保密性在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中被逐渐淡化。本文拟以上市公司仲裁公示义务与仲裁保密义务的冲突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全球视野下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反思中国仲裁保密制度如何顺应时代发展,在兼顾商事主体对仲裁保密性合理期待的同时,融入公共利益等必要保密义务例外情形。
信息公开 商事仲裁 公共利益 绝对保密 相对保密
保密性被长期视为仲裁的属性和优势,而公示公信又是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核心要素。上市公司既要信息公开又要仲裁保密,难免处于尴尬两难境遇,这种仲裁公示义务与仲裁保密义务的冲突,反映出我国仲裁制度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缺陷。本文拟以此为视角考察商事仲裁从绝对保密到相对保密的发展趋势,通过借鉴外国仲裁立法、仲裁规则和法院判例中涉及仲裁保密性的最新成果,思考中国仲裁保密制度如何顺应时代发展,在兼顾商事主体对仲裁保密性合理期待的同时,融入公共利益等必要保密义务例外情形。
一、上市公司仲裁公示的法律基础
经过多年改革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运行基础和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为适应经济发展及转型升级的更新、更高要求,有效改善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使市场交易更为公开、公平、公正,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应运而生。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是政府监管部门为保障投资者利益和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依照法律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将财务变化、经营状况等信息和资料向证券交易所和管理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告的一种公示制度。1998年《证券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形成了以《证券法》为主,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全方位、多层次立法框架。2005年《证券法》的修订进一步健全了持续信息公开制度,明确了违反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2007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出台则更为系统、全面地对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加以规范。此外,自1998年起,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出台《股票上市规则》,对信息披露的形式、时间和标准等问题予以细化并不断完善。
虽然修订前和修订后的《证券法》在列举应当披露的重大事件时均只明确包含“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事项”①,而未指明是否应披露重大仲裁事项。但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台的《股票上市规则》,均将重大仲裁事项明确列为上市公司应予披露的重大事件。②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沪股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本)为例,其第11.1.1条规则要求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并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以及董事会基于案件特殊性认为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认为有必要的,未达到上述标准或者没有具体涉案金额的诉讼、仲裁事项。《沪股上市规则》同时规定,上市公司关于重大仲裁事项的公告应当包括案件受理情况和基本案情、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者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仲裁事项以及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此外,《沪股上市规则》要求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的重大进展情况及其对公司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案件的初审和终审判决结果、仲裁裁决结果以及判决、裁决执行情况等。
考虑到修订后的《证券法》在第六十七条列举应当披露的重大事件时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作为兜底条款,且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明确将涉及公司的重大仲裁列为重大事件。因此,对于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仲裁事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相关重大仲裁事项是上市公司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
二、上市公司仲裁公示义务与仲裁保密义务的冲突
长期以来,仲裁的保密性作为其特点和优势受到广泛宣传。然而,证券市场独特的信息披露制度使得上市公司的重大仲裁事项从保密走向公开,凸显出我国不同领域制度之间衔接缺位的尴尬以及仲裁立法的相对滞后。
根据《仲裁法》第四十条,仲裁不公开进行;当事人协议公开的,可以公开进行,但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与诉讼相比,仲裁实行的是不公开审理制度。从理论上说,未参加仲裁的人不能了解仲裁的相关信息,从而实现了仲裁的保密性。虽然《仲裁法》并未明确提及保密性,但学者们普遍认为保密性是仲裁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③此外,中国主要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均对保密义务作以明确规定。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2年版)为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双方当事人及其仲裁代理人、仲裁员、证人、翻译、仲裁庭咨询的专家和指定的鉴定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均不得对外界透露案件实体和程序的有关情况。其他仲裁委员会亦多通过仲裁规则的保密条款为当事人设置严格的保密义务。根据《仲裁法》,合法的国内仲裁仅限于机构仲裁,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因而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这些仲裁规则的字面含义来看,除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外,仲裁程序相关人几乎负有绝对的保密义务,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向任何仲裁案件以外的第三人披露任何相关仲裁信息。
然而,根据前述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相关法律文件可知,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重大仲裁事项,发布重大仲裁公告以披露案件的基本案情、受理情况、重大进展及其对公司的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明确规定,中国证监会可以要求上市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或者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有关信息披露问题作出解释、说明或者提供相关资料,并要求上市公司提供保荐人或者证券服务机构的专业意见。因此,当出现涉及公司利益的重大仲裁事项时,上市公司对公众、证监会等均负有法定的披露义务。
仲裁的保密性在于不为公众所知,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则旨在为公众所知并相信。前者源自商事主体对商业秘密和商业信誉的重视,后者则源自证监会、投资者等对上市公司经营情况知情权和监督权的要求。2001年曝光的银广夏事件即折射出上市公司披露重大仲裁事项的重要性。银广夏公司在上市之初及上市期间,与外方合作者香港密苏尔有限公司涉及标的达160万美元的股权争议。该争议最终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支持密苏尔有限公司。然而,银广夏公司的所有公开信息对此重大仲裁事件只字未提。④这种重大遗漏性陈述促进了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全面性、及时性披露成为学者和证券业部门所关注的重点。⑤遗憾的是,上市公司重大仲裁事项公示义务并未引起仲裁界人士的广泛注意,亦未取得仲裁保密制度的相关回应。
保密和公开是两个对立面,如果法律在某一方面同时存在两者,其冲突就会导致两者或者其中之一无效。如果坚持仲裁绝对保密的立场,上市公司将面临履行仲裁公示义务即违反仲裁保密义务、履行仲裁保密义务即违反仲裁公示义务的两难局面。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上市公司对重大仲裁事项的信息披露制度日渐成熟。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例,在其网站以“仲裁”为检索词进行搜索,即可查阅到自2004年10月19日至2013年8月3日的136项仲裁公告。⑥可见,至少在证券市场,仲裁的绝对保密性已经名存实亡。
随着经济环境的日趋复杂,一些商事仲裁不光涉及主张私密性的商事主体的利益,还有可能涉及主张公开性的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政府监管部门的职责。商事仲裁的保密性固然在维护商业信誉、保护商业秘密方面有重大优势,但不分场合、无涉例外的绝对保密无疑已不能满足当今经济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重大变革。上市公司仲裁公示义务与仲裁保密义务的冲突反映出仲裁绝对保密的不合时宜,是我国在仲裁立法、实践与理论研究方面相对滞后的一个侧面体现。虽然国内部分学者从2003年起就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⑦但时至今日,无论是《仲裁法》还是主要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均未对此作出有效回应。因此,关注和借鉴他国对仲裁保密性研究的最新发展,将有利于更科学、合理地构建与时俱进的中国仲裁保密制度。
三、全球视域的商事仲裁发展趋势
近年来,仲裁保密性这一优势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屡屡遭到挑战。在以国际商事仲裁保密性为主题的国际法协会2010年海牙会议中,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通过考察31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告发现,自从1995年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Esso v. Ploman案(以下简称Ploman案)中作出保密义务并非绝对的革命性判决后,越来越多国家的立法机关、仲裁机构和法院逐步意识到商事仲裁从绝对保密走向相对保密的必要性。
(一)仲裁立法体现保密制度的非绝对性
由于保密性被视为仲裁的固有属性,传统的仲裁立法中并不涉及关于保密性的特别规定。国际法协会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研究发现,31个被考察国家和地区中除意大利和爱尔兰外,其余各国在修订仲裁法时都对保密性加以规定。例如,1998年的委内瑞拉仲裁法第42条仅规定仲裁员负有保密义务;⑧2004年的挪威仲裁法在总则第5项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不具有保密性;⑨2007年的新西兰仲裁法第14条在肯定当事人和仲裁员具有默示保密义务的同时,较为详尽地列举了五项例外以及法院可采取的禁止披露的措施;⑩2011年的香港仲裁条例法案第18条在确定保密性原则的同时亦规定例外情形,包括经双方同意;为保障或体现有关一方的法律权利/利益或为强制执行或质疑相关裁决而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的法院或其他司法当局的法律程序中作出发表、披露或传达;向任何政府团体、监管团体、法院或审裁处作出,而在法律上,有关一方有责任作出该项发表、披露或传达;向任何一方的专业顾问或任何其他顾问作出发表、披露或传达。⑪由此可见,虽然各国对仲裁保密的范围、主体等细节问题态度不一,但总体上都认可仲裁保密性不是绝对的,存在必须披露的例外情形。
(二)仲裁规则体现保密制度的相对灵活性
不同于仲裁立法,大多数仲裁机构在其仲裁规则中都涉及一定程度的保密条款,例如审理的私密性、裁决的发表事宜和机构的保密义务等,而对当事人的保密义务往往设置得较为笼统。一些新近修订的仲裁规则在完善当事人保密义务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例如,2013年4月1日起施行的第五版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第三十五条对保密原则、例外情形、“有关仲裁程序事项”的范畴和当事人违反保密义务的法律后果作以系统规定,2013年6月1日起生效的芬兰中央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第49条亦设置了详尽的保密规则。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仍有一些重要的仲裁规则既不确立宽泛的保密原则,亦不设置具体的保密规则,例如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美国仲裁协会仲裁规则、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等。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负责修订规则的专家们难以对构建适当的一般保密义务和确定例外情形达成共识,⑫因而倾向于通过仲裁庭与当事人对于程序事项的沟通,在个案中确定相关的保密义务。⑬其实,无论是详尽列举保密义务例外,抑或持观望态度以不变应万变,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仲裁保密性不再是绝对而不可动摇的。
(三)法院判例体现保密制度的与时俱进
1、澳大利亚法院判例
1995年的Ploman案⑭被视为仲裁保密性公共利益例外最著名的判例,也是促使仲裁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仲裁保密性进行集体反思的革命性判例。本案涉及Esso公司、维多利亚天然气和燃料总公司(以下简称“GFC公司”)、维多利亚国家电力委员会(以下简称“SECV公司”)和澳大利亚能源与矿业部长Ploman。Esso公司与GFC、SECV两家公用事业公司分别签订了关于天然气的销售协议,其中包含价格调整条款。1991年11月,Esso公司要求涨价,遭到GFC公司和SECV公司的拒绝后,Esso公司提起仲裁。1992年6月,澳大利亚能源与矿业部长在维多利亚最高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确认在仲裁中Esso公司向GFC公司披露的任何信息均不具有保密性。Esso公司则提出确认一切仲裁信息具有保密性的反请求。一审的Marks法官驳回了Esso公司的反请求,要求Esso公司分别向GFC公司和SECV公司提供天然气涨价的细节,并支持了Ploman确认非保密性的请求。上诉法庭的Mason法官撤销了一审要求提供细节的命令以及部分确认令。最终,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以多数票驳回上诉,并发回维多利亚最高法院重新拟定确认令的措辞。
本案之所以受到颇多关注,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的Brennan法官认为,“absolute confidentiality of documents produced and information disclosed in an arbitration is not a characteristic of arbitrations in this country”⑮(在澳大利亚,当事人对于仲裁中披露的文件和信息并不具有绝对的保密义务),这与英国法院传统判例关于默示保密义务的定性截然不同;其二,本案涉及被视为仲裁保密性例外的公共利益情形,法院认为,“the award to be made in the respective arbitrations will affect the price of the energy supplied by the appellants to GFC and SECV and by them to the public. The public generally has a real interest in the outcome, and perhaps in the progress, of each arbitration which the relevant public authority has a duty to satisfy”⑯(裁决会影响Esso公司向GFC公司和SECV公司的能源供应价格,进而影响公众;公众对此结果甚至仲裁进展存在切实的利益,相关政府职能机构有义务实现此公众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还认为,“the duty to convey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may not operate uniformly upon each document or piece of information which is given to GFC or SECV for the purpose of the particular arbitr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duty to the public is unlikely to require the revelation of every document or piece of information. It may be possible to respect the commercial sensitivity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particular documents while discharging the duty to the public and, where that is possible, the general obligation of confidentiality must be respected.”(GFC公司或SECV公司在仲裁中获取的文件和信息对于其向公众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对公众履行义务并不意味着披露一切文件或信息。在对社会公众负责的同时兼顾文件和信息中的商业敏感性或许是可行的;可能的话,应尊重宽泛的保密义务。)由此可见,高等法院在考虑公众利益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商事主体的私人利益。这在要求维多利亚最高法院重新拟定确认令的措辞的举动中亦得以体现。
2、英国法院判例
1996年英国仲裁法并未涉及保密性规定,但英国法院自1880年起的一系列判例表明,英国法院承认广泛的保密义务。⑰然而,自1998年的Ali Shipping案⑱起,英国法院逐渐注意到保密义务的非绝对性,开始有意识地归纳保密义务的例外情形。Potter法官在Ali Shipping案中指出四类仲裁保密的例外情形,包括同意、法院命令或许可、对仲裁一方合法利益的保护合理而必要以及公共利益。后续案件中的法院亦普遍承认仲裁保密例外规则的存在。2003年Associated Electric & Gas Insurance Services Ltd案⑲中,英国枢密院对采取广泛保密义务的优点持保留态度,认为“it runs the risk of failing to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confidentiality which attach to different types of documents or to documents which have been obtained in different ways and elides 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不按照文件的种类和来源区分不同类型的保密义务是具有一定风险的),例如,对仲裁中所获的文件或信息与最终的裁决应该具有不同程度的保密义务。2008年的Emmott案⑳进一步肯定了先例中确立的当事人对不同作出文件、信息负有不同保密义务的区分态度,并重申了保密例外的情形。可见,一贯强调仲裁保密性的英国,对于保密性程度、范围等方面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
3、新加坡法院判例
受英国判例影响,新加坡法院亦认为当事人的仲裁保密义务属于默示义务,并遵循英国法院确立的例外规则。2011年的AAZ案[21]是新加坡首例全面借鉴普通法保密义务理论的案件,[22]法院着重考察了保密例外中“公共利益”的情形。该案中,AAY和另两名申请人均为CCZ(AAZ的全资子公司)的雇员。AAZ怀疑申请人同谋降低CCZ的资产净值,于1994年提起仲裁,但最终决定不再继续。1997年,AAZ的CEO知悉关于申请人同谋一事的新证据,便于1998年以欺诈性的虚假陈述和同谋为依据提起诉讼。原告则以1994年仲裁为由要求停止或驳回起诉。经协商,双方同意法院以同意令的形式终止1994年仲裁并开始新的1998年仲裁。2005年6月30日,仲裁庭作出中间裁决,认为申请人违背了受托义务,并应为欺诈性的虚假陈述和同谋承担法律责任。申请人申请撤销该中间裁决,但以失败告终。在1998年仲裁中,AAZ向新加坡警察商业事务局提交报告,披露了与仲裁相关的文件(包括中间裁决)。此后,AAZ就报告一事通知了申请人。申请人认为,保密性是仲裁的条件,AAZ的报告行为相当于对仲裁的否认,并据此提起诉讼。AAZ认为,向警察商业事务局报告符合公共利益;且中间裁决表明有表面证据证明申请人的犯罪嫌疑,根据新加坡的《贪污、毒品运输及其他严重犯罪法令》第39条AAZ可免除违背保密义务的法律责任;此外,申请人提交法院撤销中间裁决但未申请不公开审理的行为可视为对保密性权利的放弃。
法院认为,与向相关机构检举违法犯罪行为的公共利益相比,仲裁的保密性是一个较轻的利益。对于申请人提出的通过维护保密性来鼓励仲裁的公共利益,以及仲裁一方有可能借此不适当地提升谈判筹码的主张,法院并不认可。法院对违背公共利益的理解是,“covers matters carried out or contemplated in breach of the country’s security, or in breach of law, including statutory duty, fraud, or otherwise destructive of the country or its people, including matters medically dangerous to the public and doubtless other misdeeds of similar gravity but it is not limited to these categories”[23](破坏国家安全,或触犯法律、违背法定义务、欺诈,或其他危害国家、人民的行为,例如对公众的医疗性危险以及其他类似行为,不局限于上述类型)。值得注意的是,法院认为必须通过“balancing exercise”(利益衡量)的方式在个案中衡量保密性利益和涉及的公共利益的轻重,且AAZ案不应被视为确立了宽泛的公共利益例外情形,因为“development of other aspects of public interest exceptions will have to be considered as appropriate cases arise”[24](在适当案件中应考虑其他领域公共利益的发展)。与澳大利亚的Esso案和英国的相关判例相比,新加坡的AAZ案对公共利益例外的分析更为全面深入,不仅明确了利益衡量法,更注意到公共利益处于动态发展的特点,值得借鉴。
四、对中国仲裁保密制度的反思
通过在全球视野下考察仲裁法、仲裁规则以及法院判例的最新进展,可以发现,绝对保密的商事仲裁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在不同情境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公开例外的相对保密。可以试想,在承认仲裁保密例外的国家,上市公司不会处于仲裁公示义务和保密义务夹击的尴尬境地。这归功于这些国家立法者、仲裁机构规则制定者以及法院对社会、经济环境对仲裁制度影响的敏感与关注。马克思说过,“法制作为经济生活的记载,总是植根于一定的经济生活而又落后于变化的经济生活。”[25]我国上市公司仲裁披露义务和仲裁保密义务的冲突反映出国内仲裁基本制度相对于资本市场经济现实的滞后性,国际范围内商事仲裁从绝对保密向相对保密的演进趋势值得重视和反思,如何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中国仲裁保密制度不应是一拖再拖的学术课题。
笔者认为,要实现仲裁保密制度的与时俱进,确立必要的仲裁保密例外情形,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对公开披露部分仲裁事项的要求是必不可少的。其实,一些学者早在2003年就注意到设置仲裁保密例外情形的必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建议修改稿)》[26]在保留当事人合意公开的同时,对仲裁裁决的保密性作出了例外规定,其第九十条规定:“除非仲裁公开进行或裁决进入法院的程序,仲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仲裁庭成员及其雇员、中国仲裁协会不得公开仲裁过程的任何信息。为研究和统计的目的,仲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仲裁庭成员及其雇员经过必要的保密处理,可以公开仲裁中的任何决定。”遗憾的是,修改稿对于例外情况的列举并未提及保护和实现法定权利以及公共利益例外,有挂一漏万之嫌。[27]上市公司重大仲裁事项公示义务的侧面其实是投资者和不特定社会公众对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知情权的保障,受《证券法》保护;从宏观上看,亦可归属于公共利益情形。上市公司的仲裁公示义务仅是此文的切入点,还有更多涉及法定权利或公共利益却与现行仲裁制度相冲突的情形值得重视。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设置必要的仲裁保密例外情形。以公共利益为例,其实质是整个法律制度中的最后屏障:在合同法中违反公共利益会导致合同无效;在国际私法中公共利益也是一个重要的排除外国法适用的理由。因此,公共利益对于仲裁保密也是一个首要的例外。[28]公共利益是一个模糊的范畴,新加坡法院在AAZ案中基于公共利益动态发展的个案利益衡量法值得借鉴,澳大利亚法院在Esso案对仲裁相关文件和信息中商业敏感性和机密性的尊重亦值得效仿,英国法院在判例中逐渐确立在区分仲裁文件、信息的种类、目的的基础上赋予其不同程度保密性的思路值得研究。在未来的仲裁法修订中,立法者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保密义务例外的规定,考虑将“法律另有规定”和“公共利益”补充作为仲裁保密性的例外情形。此外,仲裁机构也应在兼顾当事人对仲裁保密性合理期待的同时,顺应时代趋势适当修改严格的保密义务。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以往只涉及销售合同纠纷的仲裁结果,可能影响到政府预算和公众消费;以往只涉及商事私权主体之间利益的仲裁,在越来越多的情形中与公众利益相联系。在特定案件中,仲裁的保密性会阻碍包括公众知情权在内的公共利益的实现,也可能干扰政府职能机构在日趋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对社会的有效监督。上市公司的仲裁公示义务与仲裁保密义务的冲突仅是此文的切入点,还有更多涉及仲裁公示利益与保密利益的冲突现象值得关注,而其反映出的仲裁制度滞后于社会经济环境的深层问题更值得中国仲裁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和反思。
From Absolute Confidentiality to Relative Confidentiality-Starting from Conflicting Duties of Listed Companies towards Commercial Arbitration
By Wang Yijin
Confidentiality has been long regarded as one of the attributes and advantages of arbitration, which also explains why business people or entities that highly respect trade secrets and business reputation prefer arbitration as dispute resolution. However,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rbitration has gradually lost absolute confidentiality in some cases involving public interest.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problem of Chinese arbitration system regarding confidentiality, this article will start from conflicts between public listed company’s obligation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duty of confidentiality in arbitration confidentiality. With further examination of the trend of relative confidentiality in arbitr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the writer proposes the inclusion of exceptions to confidentiality such as public interest to adapt to times while taking consideration of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n confidentiality by business people/ent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ommercial Arbitration, Public Interest Absolute Confidentiality, Relative Confidentiality
*2011级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国际法学院在读硕士
① 参见1998年《证券法》第六十二条第(十)项和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十)项。
② 参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本)第十一章第一节“重大诉讼和仲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本))第十一章第一节“重大诉讼和仲裁”。
③ 参见郭玉军、梅秋玲:“仲裁的保密性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2期,第26页;马占军、杨玲:“仲裁保密性问题初探”,载《仲裁研究》2006年第1期,第71页。
④ 参见冀文海:“银广夏‘图穷匕现’,法律能把我怎么样?”,http://finance.sina.com.cn/t/20010814/95175.html,最后访问于2013年8月13日。
⑤ 谭立:“浅析仲裁调解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冲突及协调”,载《中国仲裁与司法论坛暨2010年年会论文集》,第378页。
⑥ http://www.sse.com.cn/marketservices/servicesupport/websuport/search_result.shtml?keywords=%E4%BB%B2%E8%A3%81,最后访问于2013年8月13日。
⑦ 参见黄进、宋连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建议修改稿)”,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郭玉军、梅秋玲:“仲裁的保密性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2期;马占军、杨玲:“仲裁保密性问题初探”,载《仲裁研究》2006年第1期;王勇:“论仲裁的保密性原则及其应对策略”,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2期。
⑧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Report on Confidentiality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Hague Conference (2010), p 6.
⑨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Report on Confidentiality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Hague Conference (2010), p 6.
⑩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Report on Confidentiality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Hague Conference (2010), p 6.
⑪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Report on Confidentiality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Hague Conference (2010), p 7.
⑫ K Hober & W Mckechnie, New Rules of the Arbitration Institute of 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 23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261 (2007).
⑬ 参见1996 UNCITRAL Notes on Organizing Arbitral Proceedings.
⑭ Esso Australia Resources Ltd. and others v. The Honourable Sidney James Plowman, The Minister for Energy and Minerals and others,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1995] HCA 19, 7 April 1995.
⑮ Esso Australia Resources Ltd. and others v. The Honourable Sidney James Plowman, The Minister for Energy and Minerals and others,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1995] HCA 19, 7 April 1995, para 42.
⑯ Esso Australia Resources Ltd. and others v. The Honourable Sidney James Plowman, The Minister for Energy and Minerals and others,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1995] HCA 19, 7 April 1995, para 42.
⑰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Report on Confidentiality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Hague Conference (2010), p 8.
⑱ Ali Shipping Corporation v Shipyard ‘Trogir’ (CA) [1998] 2 All ER 136.
⑲ Associated Electric & Gas Insurance Services Ltd v. European Reinsurance Company of Zurich [2003] UKPC 11, [2003] 1 WLR 11.
⑳ Emmott v Michael Wilson & Partners [2008] EWCA Civ 184, per Collins J.
[21] AAY and others v AAZ [2011] 1 SLR 1093.
[22] Michael Hwang and Nicholas Thio, A Contextual Approach to the Obligation of Confidentiality in Arbitration in Singapore: An Analysis of the Decision of the Singapore High Court in AAY and Others v. AAZ, 28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225 (2012), p 225.
[23] Michael Hwang and Nicholas Thio, A Contextual Approach to the Obligation of Confidentiality in Arbitration in Singapore: An Analysis of the Decision of the Singapore High Court in AAY and Others v. AAZ, 28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225 (2012), p 231.
[24] Michael Hwang and Nicholas Thio, A Contextual Approach to the Obligation of Confidentiality in Arbitration in Singapore: An Analysis of the Decision of the Singapore High Court in AAY and Others v. AAZ, 28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225 (2012), p 232.
[25] 蔡奕:“法制变革与金融创新——兼评《证券法》、《公司法》修改实施后的金融创新法制环境”,载《中国金融》2006年第1期,第54页。
[26] 黄进、宋连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建议修改稿)”,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郭玉军、梅秋玲:“仲裁的保密性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2期,第98页。
[27] 马占军:“仲裁保密性问题初探”,载《仲裁研究》第七辑,第78页。
[28] 马占军:“仲裁保密性问题初探”,载《仲裁研究》第七辑,第76页。
(责任编辑: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