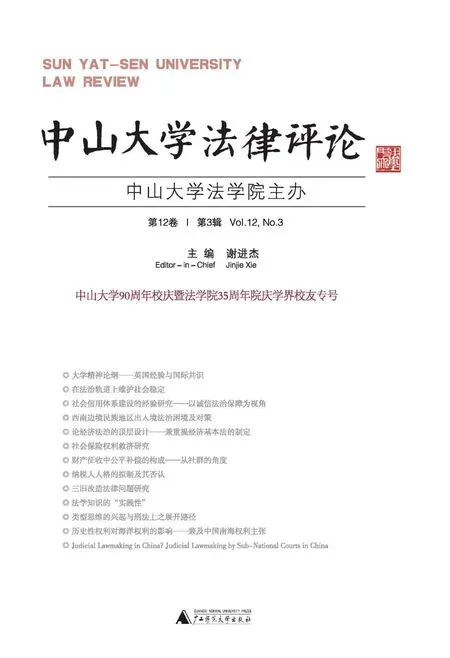纳税人人格的拟制及其否认
叶 姗
纳税人人格的拟制及其否认
叶 姗[1]
纳税人属于税法上的基本课税要素,其人格如何生成是税法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难题。纳税人人格通常经由个体或组织体构造的法律形式拟制,其特殊性在于需要考察拟制者主观上是否不具合理商业目的、客观上是否有减少应纳税额的效果,亦即是否存在避税安排。税务机关可能承认或否认个体或组织体所拟制的“纳税人”,除了外在的法律形式,税务机关还有可能关注“纳税人”是否具有应当承担纳税义务的经济实质。对增值税一般和小规模纳税人、居民和非居民企业、居民和非居民纳税人事先进行资格认定或个案批复,可以减少“纳税人”事后被否认的可能性,促使税务机关合理行使解释、适用税法的权力。
法律拟制;人格否认;实质重于形式;资格认定;个案批复
一、纳税人人格缘何由法律拟制
纳税人属于税法上的基本课税要素,必须经由“法定”。与其他经济法主体一样,纳税人人格是由法律拟制的,准确地说,是由个体或组织体所构造的法律形式拟制的。有关经济法主体的研究与其调整范围的提炼一脉相承:有多少种经济法学说,就有多少个经济法主体体系,每一种学说都有表述主体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论体系。据学者考证,“经济法主体研究沿着一条从自然写实到经济法学范畴化的路径行进的”,“当类型化的、包含着丰富经济法学理论蕴涵的经济法主体概念成立后,就可以大大提升概念确定性”。[1]肖江平:《中国经济法学史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第240—241页。经济法主体的人格经由法律拟制,其之前可能是个体或组织体,亦即,可能是自然人、法人[2]法人拟制说是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创设的法人本质的学说,亦是本文所采的观点。或其他组织。“无论其在经济法的各个具体部门法中被唤作何名”,“经济法的主体可以由传统法上的各类主体转化而来”。[3]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8页。本文选择研究纳税人人格认定问题,以此揭示经济法主体人格拟制的特异性。
“法律主体是一种在自我目的的意义上,由一定历史上出现过的法律所认可的本质。”[4]施塔姆勒的观点,转引自[德]G·拉德布鲁赫著《法哲学》,王朴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民法主体人格生成的逻辑依出生之事实或法律之拟制,而行政法主体人格生成的逻辑依法律之拟制。“凡生理上之人,无一而不具有人格者,此自然人之所由称也”,“法人之人格,全然本诸法律所赋予”。[5]梅仲协:《民法要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页。任何法律主体都是个体或组织体,人格的概念源于民法,“现代法所称的人,就是指权利义务的主体”,“在罗马具备完全的人格须有自由、市民和家族三权”。[6]周枬:《罗马法提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页。人格的范畴是后天创制的,形式上是法律创制的,实际上是立法者创制的,而且,立法者创制后,还可能需要执法者来判断人格能否顺利生成。“人之成为人以及与此相应而生的权利能力是由实在法规定的”,“法人作为一种拟制的产物,必须首先得到法律的承认”。[7][德]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75页。
与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行政法中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等范畴相比,经济法主体的外延复杂得多。“在目前多种所有制形式、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不同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结成了多种多样的经济关系,都需要运用法律手段调整”。[1]佟柔:《佟柔中国民法讲稿》,周大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5页。个体或组织体都可能依法成为经济法主体,而经济法主体的种类繁多,不仅要看其人格生成与否,还要看其生成为何,这就需要考察拟制者的行为的经济实质,有别于传统部门法:“民法典并不考虑农民、手工业者、制造业者、企业家、劳动者等之间的区别。私法中的人就是作为被抽象了的各种人力、财力等的抽象的个人而存在的。”[2][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66页。经济法主体“属于被个别化、具体化的特殊部分的社会团体的成员或团体”[3][日]丹宗昭信、伊从宽:《经济法总论》,吉田庆子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157页。,个体或组织体依据经济法规范取得主体资格的方式不尽相同,“不同取得方式的实质差异在于国家对主体资格取得的控制程度的强弱”[4]杨紫烜:《国家协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7页。。
“人们必须将人这一法律主体的概念视为一种不是建立和限定在法律经验之上的,而是具有逻辑必然性的、普遍适用的法学观察之范畴。”[5][德]G·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经济法主体体系的提炼同样见仁见智,例如,经营者、消费者和经济管理者,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等。笔者将经济法主体分成经济执法者和市场主体两种,纳税人就是市场主体的一种主体形态,纳税人可能是个体,也可能是组织体,后者可能是人或财产的组合。经济法主体人格的生成都是法律拟制的结果,可能依据法律法规、特别授权,经批准、特许及登记注册,或者经认定、按照法律程序等。由于拟制者可能滥用构造法律形式的权利,部分市场主体的人格必须经由经济执法者认定方可生成,结果可能是承认,也可能是否认,这一点在纳税人人格的拟制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法律规定经济活动的法律范围并为经济主体设定法律准绳。但有时法律也必须由经济行政主体来执行”,“行政机关的任务是执行纷繁复杂的经济公法规范并对其进行具体化”。[6][德]乌茨·施利斯基:《经济公法(2003年第2版)》,喻文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135—137页。
经济法主体的特殊性、差异性和模糊性,有别于传统部门法主体的普适性、同质性和明确性。笔者选择研究的是市场主体人格拟制的一种特殊形式——经由经济执法者认定,它通常发生在拟制者构造的法律形式与其经济实质不相一致时,例如,滥用公司组织形式的避税安排、独资公司与其股东的人格混同以及企业集团和关联企业的人格混乱等。经济执法者通常根据拟制者构造的法律形式来判定谁才是适格的市场主体,但是,如果拟制者刻意拟制某一市场主体来转移、改变或减轻其原本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就应当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来认定市场主体生成的结果,亦即根据经济实质而不是法律形式来认定市场主体。经济法主体人格的认定看上去是一种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然而,笔者认为,经济法主体人格的认定更近似于“建构性确认”的法律解释模式,这一范畴是美国学者罗纳德·德沃金提出的。
经济法体系庞杂,且主体种类繁多,笔者以纳税人为例来研究经济法主体人格经认定生成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法律问题。现代国家大多实行复合税制、同时开征多个税种,纳税人在各个具体税种中的名称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安排不尽相同。“税法经常使用‘人’或‘纳税义务人’,但有时这些术语适用于何种情形也并不明确。例如‘纳税义务人’这个术语无需意味着某一人在一个特定年度有纳税的义务。”[1][美]V.图若尼主编《税法的起草与设计》,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译,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4年,第538页。纳税主体,亦称纳税人或纳税义务人,属于市场主体,一般认为,是指依照税法规定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纳税人外,承担纳税义务的还有可能是扣缴义务人或纳税担保人。[2]有学者将税捐义务人分为税捐债务人和税捐缴纳义务人,前者即纳税人,是指税捐债权债务关系中有关财产法上权利与义务的主体;后者包括税捐的扣缴义务人、代征义务人等,陈清秀:《税法总论》(第7版),元照出版公司,2012年,第281页。还有学者指出,后者还包括税捐债务承担人和赔缴义务人等,参见黄茂荣《税法总论(第3册):税捐法律关系》,台北: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2008年,第152页。正因为不同税种的纳税人不同、同一税种也可能有不同类型的纳税人,这就使得拟制者有选择拟制何种纳税人的可能。以企业所得税为例,一般反避税条款、受控外国公司反避税规则、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税制、经批准企业集团的汇总纳税制度等,都是纳税人人格经认定生成的制度设计。
二、人格因滥用法律形式而被否认
纳税人不一定是税收负担的承受者——负税人,两者不相一致的情况是很常见的。“把本来的纳税义务的主体,即把在税之法律关系中负担税之债务者称为纳税义务人或税之债务人。纳税义务人这一概念同担保人,即在经济上来负担税者的概念是不同的两个概念。”[1][日]金子宏:《日本税法》,战宪斌、郑林根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也有学者认为,“税收主体是指缴纳税收的纳税人,以及负担税收的担税人。纳税人与担税人既有是同一人的情况,也有纳税人转嫁税收负担,而不一致的情况。”[2][日]神野直彦:《财政学——财政现象的实体化分析》,彭曦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7页。不同税种的纳税人的纳税义务不尽相同,典型的如,个人所得税的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企业所得税的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纳税人可能通过主体转移的方式来避税,因此,可能被限制或禁止离境,也有可能视同未离境来处理,例如,美国《联邦税法典》规定,如果纳税人以逃避缴纳联邦所得税为主要目的而放弃国籍并移居他国,美国在其移居后10年内仍保留征税权;德国《涉外税法》规定,纳税人移居到避税地或不取得任何国家的居民身份,且与德国保持实际经济联系,将承担扩大的有限纳税义务。
“经济人是各自独立地从事经济职业和各个被法律原则所赋予经济事实关系的规制、权利、义务或法律保护地位的人。”[3][德]沃尔夫冈·费肯杰:《经济法》(第2卷),张世明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110页。如果拟制者主观上不具合理商业目的、客观上有减少应纳税额的效果,亦即存在避税安排,税务机关就有可能否认拟制的“纳税人”。“纳税人”是否被承认以及是否按照其所呈现的法律形式来认定,取决于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实践中依据文本和现实所作的解释。例如,企业集团一般不属于法律主体、也不是纳税人,但是,经批准汇总合并纳税的就可能成为纳税人。[4]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52条规定: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企业之间不得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又如,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13条规定,小规模纳税人以外的纳税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资格认定。小规模纳税人会计核算健全,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可以申请资格认定,不作为小规模纳税人。[1]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总局令第22号),《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2013年第75号)。增值税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除另有规定外,应当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应当”表明销售额达到法定标准的纳税人具有申请资格认定的义务,“可以”则表明销售额未达法定标准的纳税人享有申请资格认定的权利。一般纳税人采用购进扣税法计征,小规模纳税人采用简易征收法计征,后者不能进入增值税抵扣链条,但税收负担相对较轻。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一般反避税条款”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国家税务总局《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列举了滥用税收优惠、滥用税收协定、滥用公司组织形式、利用避税港避税等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避税安排。对此,税务机关应当按照经济实质对企业的避税安排重新定性,取消企业从中获得减让的税收利益。对于没有经济实质的企业,特别是设在避税港并导致其关联方或非关联方避税的企业,可在税收上否定该企业的存在。“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通过滥用组织形式等安排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且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规避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主管税务机关层报税务总局审核后可以按照经济实质对该股权转让交易重新定性,否定被用作税收安排的境外控股公司的存在。”[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698号)。简言之,被用作避税安排的境外控股公司的纳税人身份可能被否定,境内被投资方则可能由非居民企业的身份变成居民企业。
纳税人主体资格的认定,首先,要解决其是否属于“纳税人”的问题。德国《租税通则》第33条规定了“租税义务人”限于“负租税债务、对租税负担保责任、应为第三人之计算收取并提缴租税,以及应申报租税、提供担保、制作账册及会计记录或履行税法所规定其他义务之人”[1]陈敏译:《德国租税通则》,台北:“司法院”,2013年,第50页。。其次,要解决属于哪一税种中的哪种纳税人的问题。依据税收法定原则,税法规定了不同类型纳税人的资格,但拟制的“纳税人”属于哪一种,除了创制者的意志,还要看税务机关是否认为该“纳税人”真的符合税法规定的条件:是否主观上不具合理商业目的、客观上没有减少应纳税额的效果,或称是否没有避税意图。“立法者和条例制定者常常不可能对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和技术的变化作出精确的规定”,因此,立法中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在所难免,它们“同时也包含着自由裁量空间,结果是,经济行政机关根据事实有权作出各种决定”。[2][德]罗尔夫·斯特博:《德国经济行政法》,苏颖霞、陈少康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4页。在诸多税种中,各国普遍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最有可能成为从事跨境投资贸易的个体或组织体想要规避的,避税地更是为避税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两种纳税人,居民企业包括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和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实际管理机构的判断标准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由中国境内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作为主要控股投资者,在境外依据外国(地区)法律注册成立的企业,即境外注册的中资控股企业(简称“境外中资企业”),依据实际管理机构判定为中国居民企业。[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依据实际管理机构标准认定为居民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2号)。境外中资企业居民身份的认定通常采用企业自行判定、提请税务机关认定以及税务机关调查发现予以认定两种形式。[4]国家税务总局《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公告2011年第45号)。境外中资企业的税收待遇因其是否被认定为居民企业而改变,而纳税人主体资格的认定属于税务机关解释和适用税法的行为。
在纳税义务发生前或应税事实发生后,省级税务机关都有可能需要依纳税人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初步审核,或者依主管税务机关初步判定,对纳税人主体资格进行确认。[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依据实际管理机构标准实施居民企业认定有关问题的公告》(公告2014年第9号)修订了国税发[2009]82号文,将“层报国家税务总局确认”改为“层报省级税务机关确认”。这是一种事先裁定制度,即纳税人在从事某项经营活动之前,可以就其是否应当纳税、如何纳税以及怎样计税等问题,要求税务机关进行裁定。这是税务机关对具体纳税事项提出的适用税法的意见,不同于普遍适用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很多国家都建立了这种制度,如美国的税收裁定(revenue ruling)就是针对某特定事项所作的一般解释,从针对特定纳税人的信函裁定(letter ruling)发展而来。在我国香港地区,税务局删除可以识别纳税人身份的资料后,会在官方网站公布事先裁定个案给纳税人参考,同时,提醒纳税人依赖裁定时必须小心谨慎。[1]截至2013年12月,香港税务局已作了53个事先裁定。http://www.ird.gov.hk/chi/ppr/arc.htm,2014年1月1日最新访问。我国税法实践中还摸索出了税收个案批复制度,即税务机关针对特定税务行政相对人的特定事项如何适用税收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所作的批复,类似于司法上的指导性案例。税收个案拟明确的事项需要普遍适用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
税收个案批复是我国税务机关解释和适用税法的一种执法行为。我国税收个案批复从内部规则发展成具有示范意义的外部制度,为解决原先不规范、不公开而导致的滥用自由裁量权、诱发税收执法风险等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税收个案批复工作规程(试行)》(国税发[2012]14号)。税收个案批复必须以税务机关的名义作出,下级税务机关不得执行以上级税务机关内设机构名义作出的税收个案批复。如果超越本机关法定权限、与上位法相抵触、对其他类似情形的税务行政相对人显失公平的,不得作出税收个案批复。税务机关在核税程序中根据事实,公开发布的裁决和意见。如果纳税人的实际经营活动完全符合事先裁定所依据事实,则此项事先裁定对于税务机关具有法律约束力,即税务机关必须按照事先裁定来对该纳税人的此项业务活动进行税务处理,即使事后发现该裁决作错了,也不得更改。[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个案批复工作规程(试行)》(国税发[2012]14号)。
税务机关对境外中资企业是否具有居民企业身份的认定,基本上“一事一议”,属于以事先裁定或称个案批复方式所作的行政解释,既可以减少“纳税人”事后被否认的可能性,也可以促使税务机关合理行使解释、适用税法的权力,降低税收执法的不确定性。只要境外中资企业同时符合“国税发[2009]82号”文规定的条件,就应当判定为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企业。例如,中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等164家境外企业、福耀(香港)有限公司及Meadland Limited、美华实业(香港)有限公司及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高汇有限公司等,都被判定为中国居民企业。[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粮集团所属境外企业认定为居民企业的批复》(税总函[2013]183号),《关于福耀(香港)有限公司及Meadland Limited居民企业认定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10]468号)和《关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境外公司居民企业认定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10]651号)。上述资格认定都在“纳税人”纳税义务发生前,而应税事实发生后的有如下一例:美国沃尔玛公司通过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MMVI China Investment CO.LTD公司收购同在该地注册的Bounteous Company LTD公司(简称BCL公司),实现对中国境内多家好又多公司的间接收购。对2008年1月1日后完成的股权转让交易,依据其经济实质认定为 BCL公司股东(Bounteous Holding Company LTD公司,简称BHCL公司)直接转让中国境内企业股权,BHCL公司负有中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纳税义务。[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沃尔玛收购好又多股权事项的批复》(税总函[2013]82号)。
三、人格生成为何更重经济实质
纳税人人格可能因拟制者滥用法律形式而被否认,其所依据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substance over form)、“穿透理论”(penetration),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揭开/刺穿公司面纱”(lifting/piecing the veil of corporation),都强调经济实质的重要性。“纳税人”被否认时,税务机关可能同时径行认定纳税人。“稽征机关对于滥用私法上法律形式而规避税捐的行为,基于实质课税原则,得加以否认并予以调整,改按照实质的经济活动在通常情形(与经济上事实相当的法律形式)所实现的课税要件进行课税。”[3]陈清秀:《现代税法原理与国际税法》(第2版),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0年,第25页。纳税人人格的拟制主要依据经济实质而不拘泥于外在的法律形式,纳税人人格的生成为何更加注重经济实质呢?“任何法律保障都是直接地为经济利益服务的。即使不尽如此,经济利益也是影响法律创设的极重要原因。”[1][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83页。传统部门法主体人格的生成不考虑个别差异,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而纳税人人格是否生成、有否变动,必须持续考察拟制行为的经济实质。笔者试图为纳税人的异质性、经济性和易变性寻求理论上的解释。
税收执法实践中,“视同**不存在”“**负有纳税义务”是纳税人人格拟制的主要方法。“主体方面的内在局限,是由于纳税主体的现实差异而导致的”,“只要主体之间的差异存在,在税法规范上的差异性就可能长期存在”。[2]张守文:《企业所得税法统合的内在局限》,《税务研究》2008年第2期,第51页。不同税种的纳税人、同一税种不同类型的纳税人,纳税义务都不尽相同,只有外在的法律形式与其经济实质不一致时,才有判断何者更重要的必要性。一般来说,决定承担纳税义务的主体归属的是基础法律关系,尽管经济实质在价值序列中优先于法律形式,但是,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推翻法律形式,就不能“轻易”穿透法律形式而径自认定经济实质。形式理性是法律这种社会规范最大的制度特色,法治和经济利益预期都是经由形式理性保障的。最大限度地承认法律形式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除非有充足的理由而且经过严密的论证,否则,不能动辄取经济实质而弃法律形式于不顾。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务机关谨慎启动一般反避税调查、谦抑行使特别纳税调整权。
税务机关行使特别纳税调整权几乎不受什么约束的同时,也伴随着难以预见、难以克服的税收执法风险。在不违背税收法定原则的前提下,税法的解释和适用可以确立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当税法之解释及课税要件事实之认定上,如有发生所谓‘法律形式、名义或外观等’与‘真实、实态或经济之实质’等有所差异之情形时,应着重实质而甚于形式,并以此作为课税基础之原则。”[3]黄俊杰、邱天一:《税法解释之研究——以释字第420号解释为中心》,载台湾《判决研究汇编》(二),第173页。纳税人主体资格的认定可能是由“纳税人”申请启动的、也可能是由主管税务机关主动进行的,税务机关必须经查明而不能经推定来确认纳税义务承担主体。如果不要求税收执法必须忠实于税法规范文本、不限制税务机关滥用否认“纳税人”或者径行认定纳税人的权力,就可能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影响市场主体的利益预期。“法律规范的解释只有相对于一种特别经由评价性判断予以建构的概念框架背景才成为可能,才可被理解”,“必须加以证明的是该法律确认的价值依赖性何在”。[1][美]安德瑞·马默:《解释与法律理论》(第二版),程朝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0—121页。可能被税务机关认定的,必定是与拟制者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个体或组织体,因此,它实际上是有客观依据的。
税法规定了识别和认定某个税种的某类纳税人的条件,税务机关据此识别拟制者是否顺利构造了某一“纳税人”。通过考察拟制者的行为来判断谁是纳税人、纳税人属于哪种类型实际上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性思路:要么认可拟制出来的“纳税人”,要么径行认定另外一个纳税人,此外,还包括选择按照某一税种的某类纳税人。例如,企业所得税不以在避税地设立的企业、而以其控股企业为纳税人,还可能将控股企业确立为居民企业而使之承担无限纳税义务。简言之,纳税人主体资格的认定是在各种可能的主体之间选择的结果,而经济实质较之法律形式更容易成为可能。笔者将主体间性理论来解释纳税人人格的生成为什么更重经济实质,该理论强调,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而不是传统所称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间性强调的是交互主体性:一个主体怎样与完整的作为主体运作的另一个主体相互作用。[2]主体间性的概念是著名哲学家胡塞尔创设的,后来发展到社会学、认识论和本体论三种意义上的范畴。自此,哲学的本体论从主体性发展到主体间性:前者强调个体性,后者强调群体性。经由拟制者的行为来判断生成什么主体其实是一种法律解释行为。
客观上说,如果不是税法规范具有复杂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税务机关就不需要在如此繁多的纳税人类型之间选择和认定。换言之,如果税法文本制定时没有对纳税人进行具体化、体系化的裂变式制度设计,就不会有需要由税务机关来判断“纳税人”人格是否生成或生成什么纳税人的必要性。某种程度上说,不同税种的纳税人、同一税种不同类型的纳税人,都是立法者创制的范畴,之所以细分纳税人群体,目的在于立法者需要据此设计不同的权利义务体系。“从传统法律制度的真理性判断——陈述句到经济法、社会法律制度中商谈博弈性质的复合条件句”,经济法“为新的法律关系元形式,为形式逻辑为内核的传统法律推理之外的法律论证模式和纠纷解决途径,提供了语言学基础”[1]刘光华:《经济法的分析实证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7页。。相较之下,经济法主体不仅要凭借制定法文本来定义,同时,它们不能一次构造完成、也并非一成不变。纳税人这种市场主体必须经由“法定”,[2]有学者如此进行描述:“在租税法律关系中具有负担义务享受权利之私人,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团体,我国台湾地区现行税法,甚至将独资、合伙之营利事业所得税之课税主体,而与一般国家之公司税法不同。”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111页。而且,其人格的拟制具有多层次性、多阶段性、非均质性。
纳税人人格的认定通常是在税收执法实践中完成的,以至于解释法律的重要性甚至与制定法律不相伯仲。“法律解释的任务就在于:清除可能的规范矛盾,回答规范竞合及不同之规定竞合的问题,更一般的,它要决定每项规定的效力范围,如有必要,并须划定其彼此间的界限。”[3][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94页。立法即便使用填密的法律语言,也不可能没有漏洞、歧义或语义含糊的时候,有的“法律漏洞”是必然出现的——以保持法律规范普遍适用的原则性,可以借由法律解释解决;有的“法律漏洞”的偶然为之的——通常是立法技术不济、利益协调不力甚或权利收放不当所致,可以借由法律修正或法律解释来解决。因此,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然而,法律解释不仅是技术问题,而且带着深刻的价值选择的意蕴。法律解释的方法不止是一种规范性的技术,其如何进行选择实际上会决定法律解释的结果,而解释的结果往往预示着法律执行的时效。法律“制定价值准则,用以决定认可什么利益、确定对被认可的利益的保护界限、判断在任何给定案件中对有效法律行为予以实际限制的重要性”[4][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3卷),廖德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德国《租税通则》第42条规定了“法律形成可能性之滥用”:“税法不因滥用法律之形成可能性而得规避”,“选择不相当之法律形成,致租税义务人或第三人,相较于相当之法律形成,获有法律未预见之租税利益时,存在滥用”,有上述规定所称之滥用时,“依与经济事件相当之法律形成,成立租税请求权”。[5]陈敏译:《德国租税通则》,台北:“司法院”,2013年,第65页。法律解释应当从法律文本可能的语义出发,以有限理性的形式展开,法律解释不能背离法律文本确立的宗旨和原则。“在税法的解释适用上,应取向于其规范目的及其规定的经济上意义”,“在课税要件事实的认定方面,也应把握其表彰经济上给付能力的实际上的经济上事实关系,而非以其单纯外观的法律形式为准”。[1]陈清秀:《税法总论》(第7版),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3年,第188页。无论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税法领域都是成文法,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解释和适用税法时,都要遵循较为严格的文义解释。税法文本的文义不明通常是法律解释的理由,而明确文义则通常是法律解释之目标,某种意义上说,法律解释始于文义且忠于文义。
法律解释的方法有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和合宪解释之分,除了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可以说是另一种常见但备受争议的解释方法,它最有可能突破税法文本的字面含义、却很可能触及“纳税人”的经济实质,也符合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实质课税原则或经济观察法之目的,乃为实现税捐公平原则而产生,故经济观察法或实质课税原则似应属于目的解释方法之一种。”[2]黄俊杰:《纳税人权利之保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页。拟制者主观上不具合理商业目的、客观上有减少应纳税额,属于滥用构造法律形式的权力来避税的行为。“每一天,纳税人都在安排交易以使其纳税义务最小化”,“已经有多种法律技术被用来应对税收规避,没有哪一种方法能单独解决所有的问题”。[3][美]维克多·瑟仁伊:《比较税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2—153页。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一般反避税条款”确立了税务机关特别纳税调整权:对纳税人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避税安排按合理方法调整。“合理商业目的”属于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20条和《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施行)》第92、94条试图阐明其内涵,却可能使条款失去普适性。纳税人人格的生成之所以更重经济实质是税务机关依据税法规范文本和现实所作的选择,是实质课税原则所要求的。
四、结论
对纳税人人格的拟制路径的研究依赖于税法规范文本的支持,理论研究则将有利于有关纳税人的类型及其相应纳税义务的立法技术和执法技艺的改进。纳税人人格的拟制路径表明,拟制者有可能滥用构造法律形式的权力,因此,税法创制了纳税人人格经由税务机关认定生成的建构性确认模式。纳税人人格的拟制不仅要符合税法规范文本规定的条件,而且要履行其所规定的程序。纳税人人格可能经多次博弈才能拟制成功,生成后还可能数次发生变动,其主体人格的认定过程始终受到拟制者的行为的经济实质影响。纳税人人格拟制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多层次性、多阶段性、非均质性,这种建构性确认看上去是一种行政许可,实际上是一种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行为。纳税人人格的认定可能发生在纳税义务发生前或应税事实发生后,都是税务机关依据税法规范文本和现实来进行的。对纳税人事先进行资格认定或个案批复,可以减少“纳税人”事后被否认的可能性,促使税务机关合理行使解释、适用税法的权力。税务机关在不同种类的纳税人之间进行选择和认定,虽然要以拟制者的行为的经济实质为依归,但是,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推翻法律形式,就不能“轻易”穿透法律形式而径自认定经济实质。简言之,税务机关不能随意否认“纳税人”或者径行认定纳税人。
(初审:王欢欢)
[1] 作者叶姗,女,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法学学士、中山大学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研究领域为财税法、社会法、经济法总论等,代表作有《财政赤字的法律控制》《税法之预约定价制度研究》等,Email:uyesh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