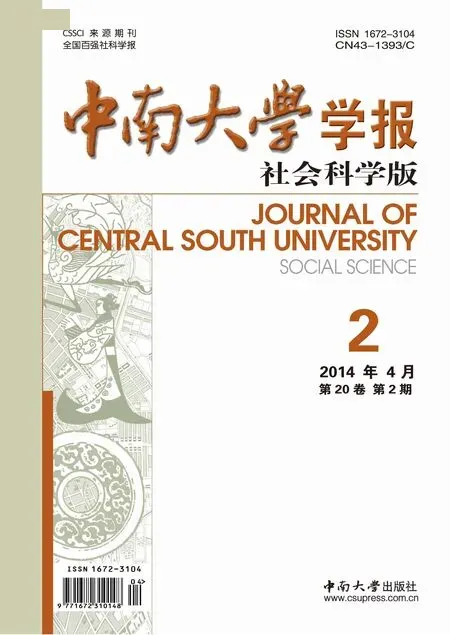左舜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及其治史特色
曾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241)
左舜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及其治史特色
曾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241)
左舜生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左的早期辛亥革命史著作,初具规模,渐成体系,将辛亥革命史研究逐渐提高到学术研究层面,晚期研究进一步发展,更显完备成熟。《黄兴评传》突破了国民党正统学派之藩篱,成为当时最有分量的黄兴传记之一。左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时段、范围、性质、成败均有自己的看法,对辛亥人物及重大事件亦有许多真知灼见。从其研究中,可以发现左氏特别重视史料搜集及整理,注重史学教育功能和历史知识的传播普及以及严谨持重、议论客观独立,擅长归类总结和史实考订等特征。左氏史学亦有研究范围狭小、未做专题研究等缺憾。总体而言,左氏不失为一位多有建树的近代史专家。
左舜生;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史
左舜生,字舜生,别号仲平,湖南长沙人。左舜生是民国政治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曾担任过青年党中执委委员长、民盟秘书长等职。不过,左本质是一书生,从政非其所长,亦非其所好。左真正的志趣则在文艺与史学,故其虽然激于民族危机和时代洪流而涉足政海,但终其一生,并未忘情于史学研究,并且成果丰硕,多所建树,以至赢得港台学界“治近代史有卓越成就”[1](142)“史学界有数的著作家之一人”[1](52)之美誉。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则认为“左舜生为近六十年来,注意研究中国近代史三五先驱之一,与李剑农、蒋廷黻齐名,而各有树立。”[2](8)
颇为遗憾的是,或是由于左政治身份的特殊性,或是由于史料的不易搜寻,大陆学界却有意无意地将其遗忘,更无论研究。目前有关左氏史学的论文,有两篇。其一为香港学者李金强先生之《民国史学南移——左舜生生平与香港史学》[3],另一为台湾学者陈正茂先生之《左舜生之史学特点与贡献》[4]。前文篇幅不长,介绍了左舜生的生平,对左氏各个阶段的著述活动等均有涉及;后文则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探讨,论述左氏史学思想之渊源、特点与贡献,是一篇较为有力的论文。但是,作为左舜生史学研究最重要组成部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两文均未做过专门深入之探究,两文之论点也有不少不甚明了和可商榷之处。因此,仍有诸多疑问尚待探讨。比如:左舜生辛亥革命史代表性专著内容大致如何?这些著作在学术史上有何贡献?左对辛亥革命总体持何种看法?对辛亥重要人物作何种评价?其研究有何特征?左氏史学属于传统史学范畴吗?左之研究有何局限?应该如何看待左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作用?本文即拟围绕这些问题作一深入探析。
一、左氏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主要著述及其成就
左舜生自1920年进入中华书局后数年间,即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辛亥革命亦很早即进入左之研究视野。从此以后迄至晚年,左一直热衷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大体而言,左舜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包括直接以“辛亥革命”命名的《辛亥革命史》以及《中国近代史四讲》中第四讲《辛亥革命》等著作,也包括其为辛亥人物所作的传记、评传,如《黄兴评传》《宋教仁评传》。还包括散见于《万竹楼随笔》《中国近代史话初集》等文集中的史论、读书札记等等。
《辛亥革命史》[5]可视为左舜生早期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原是作者在复旦大学、大夏大学所授中国现代史课程的讲义,书成于1931年1月,1934年1月由中华书局作为中华百科丛书之一种出版。该书共分八章,约5万字,叙述从兴中会成立始,以1912年4月孙文解临时大总统职及临时政府北迁终。辛亥革命前的历次革命运动、同盟会成立、武昌首义与各省响应情形、汉阳南京之战、临时政府的成立、南北议和、清帝逊位等等重要史实均囊括其中,对历次革命运动、同盟会成立等关键性事件均设立专门章节论述。可以说,跟同时期的其他辛亥革命史代表性著作相比,该书已经初具规模、渐成体系。①
辛亥革命爆发后,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就不断涌现。不过,民初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很多都是资料汇编性质,如1912年6月最早以“辛亥革命”命名、署名渤海寿民所编之《辛亥革命始末记》,即是摘录了京津沪辛亥8月20日至12月25日相关文章,汇而成册。有的是回忆录性质,如梅川居士(居正)之《辛亥札记》(出版者不详,1929年)、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张难先之《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等等。这些汇编、回忆录虽然极具史料价值,但这与真正的学术研究距离尚远。还有一些早期著作,已经开始摆脱回忆录和资料汇编性质。但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言,也“大多属于史事记述,往往流于资料罗列,粗疏浅薄。”[6]
毋庸讳言,左之作品也难完全避免此一缺憾。不过从其著作中,可以发现,左已开始逐渐摆脱资料排列和史事罗列的情形,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探究事件的前因后果。左著每章之后均附有问题若干,实际上也即左思考论述中心之所在。如第一章《辛亥革命的原因》后边所附的问题包括辛亥革命的重要原因有哪几个,赞助革命最力的有哪几种势力,立宪派何以卒归失败等五个问题。对第一个问题,左从满汉种族的裂痕、清季政治的腐败、外力的压迫、立宪的失败、新兴势力的抬头五个方面加以剖析,条清缕晰,丝丝入扣,至今读来仍感其说言之甚然。[5](1-16)可以说,左舜生把辛亥革命史研究提高到学术研究层次。
1949年后,左寓居香港,在新亚书院、珠海书院等校教授中国近代史。1962年,他将《辛亥革命史》一书加以增补,从而形成《中国近代史四讲》之第四讲《辛亥革命》。该讲增加到十章,篇幅则增加了一倍,内容更加丰富翔实,有详有略,重点突出,体系更加合理,对一些明显的错误,也进行了更正,从而更显成熟完备。
《黄兴评传》为左氏晚年另一力作。该书分十一部分,以黄兴发起成立华兴会、孙黄携手共建同盟会、黄所领导历次起义、参加临时政府及担任留守等重要事件为中心,评述了黄兴一生的事功,对外界加在黄兴身上的一些不实之词加以辩驳,对黄兴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比如指出武昌起义前历次武装起义,孙中山所领导的除了1895年广州起义和1911年黄花岗起义外,影响“乃不算太大”,而黄兴等领导的萍浏醴起义对清廷的打击和影响反而更大;[7](35)强调华兴会与武昌首义酝酿的密切关系,同时指出黄兴在武昌起义中与“宋教仁、谭人凤、居正同为关键人物”;[7](71)黄兴在二次革命及其后来的表现每每为后人所诟病,左则以为:“克强深知武力非袁之敌,则主用法律解决,但亦作军事准备;其倒袁目的,固与中山无出入”,而战事既起,黄“赴义之勇,殆与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一役无二致”;[7](107-108)关于二次革命结果,左则从国民求安的心理、国民党组织涣散、实力太弱、财政困难等原因剖析“无论由中山或克强出而指挥军事,结果必至失败”。[7](112)总体而言,左舜生认为“克强先生对于创建民国的勋业,其地位仅次于中山先生”,[7](2)其功业“真可以万古千秋”。[7](4)
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大陆学界基于黄兴在南北议和和二次革命等事件中的表现,视黄为妥协乃至“右派首领”,对其总体评价偏低,研究成果也很少。②五六十年代,台、港史学界则是国民党正统学派占据主导,延续其在大陆时的一贯基调,叙述辛亥革命多以孙中山、同盟会(国民党)为中心,重孙轻黄,扬孙抑黄。③由此造成黄兴的事迹隐而不彰,甚至出现许多人只知有孙中山不知有黄兴的境况。在这种情势下,左独抒己见,秉笔直书,无疑修正、突破了国民党正统学派之藩篱。若将此放置在辛亥革命史学术脉络来考察,其意义是显然的。④窥诸当时史学界,可以说,成书于1960年代的《黄兴评传》一书,尽管现在看来仍不免粗糙,但在学术史上是不应忽视的。该书和此前出版的薛君度所著《黄兴与中国革命》及其后出版的《黄克强先生传记》《黄克强先生年谱》⑤一起成为当时研究黄兴的最有分量和影响的著作。
左对宋教仁亦写有评传。为准备写梁启超评传,则写了《梁启超的生平及思想与著作》。此外,左还写下大量关于辛亥人物的史论和读书札记,大多辑入《左舜生自撰集》《万竹楼随笔》《中国近代史话初集》等文集中。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不在此赘述。
二、左氏关于辛亥革命的主要见解
左舜生对辛亥革命总体持何种看法?左并未对此作集中论述,其辛亥革命观可散见于其专著和史论、读书札记中。首先,左舜生所谓辛亥革命史,并非指狭义上的辛亥革命史,从其论著中可以看出,其界定的是从兴中会成立至临时政府成立、北迁期间的广义的辛亥革命史。其研究范围,主要局限在革命人士及其革命、政治活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则未有涉及。
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章开沅先生和张玉法先生曾展开激烈辩论。章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张则提出“全民革命论”。⑥其实,左舜生很早即提出了“全民革命论”,香港学者李金强先生在《辛亥革命的研究》一文中认为“全民革命论”为张玉法先生所提出,并不准确。左舜生在1968年出版的《黄兴评传》中说:“辛亥革命前后,会党分子,海外华工,各省新军中之士兵,牺牲者多至不可胜数;这可看出辛亥革命乃是全国一致的全民革命,而不是属于任何一阶级的革命,共产党乃目辛亥一役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只有他们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应予严斥。”[7](24)左只从革命动力一个方面来论证其说法,未免失之于简单。不过应该看到,左之全民革命说并非一时之语,其来有自。“全民革命”与“全民政治”“全民福利”等实际上是国家主义派的基本主张之一,早在1923年12月立党之初即写入青年党党章。可以说,在全民革命这一点上,左舜生承袭了青年党一贯的看法。
辛亥革命的成败历来众说纷纭。左对此持何种态度?左对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动动机评价很高,认为辛亥革命与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同为“最近的六十年,由中国人自动的,有意识的,指着一个高尚纯洁的目标,结合一部分奋发有为的同志,就整个的中国,实行一度具有规模而极有意义的改革运动”,但是左同时认为:“就当时主持或参加这三度运动的人所怀抱的理想,和希望达到的目的来说,却都是失败的;至少也应该说,其结果绝不符合他们的理想,也并没有达到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8](1013)在左眼中,“辛亥革命是合政治与种族的两个因素而形成的,其成功只限于种族的一面,政治则四十年来并没有表现什么显著的成绩。”[9](265)
左对辛亥革命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说法。比如他认为辛亥革命也有维护中华文化的考虑,认为辛亥革命与明末清初顾亭林、黄宗羲、王夫之著书立说宣扬中华历史文化,曾、左、李为维护中华文化起而办团练斗太平军,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如此之速,是因为“上层知识分子故持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坚强信念,与中国下层社会那种排满的热烈情绪的合流”共同作用的结果。[10]对于辛亥革命与戊戌维新的关系,左舜生认为,维新人士和革命人士的政治主张虽然大不相同,但他们并非只有相克而无相成。[8](1025)还比如认为清室之亡,非亡于辛亥,而亡于庚子一役,因为自此以后,清廷一切腐败愚昧之真相始暴露无遗,革命风潮始日趋激烈而无法遏止等等。[11](183)这些看法还是相当有见地的。
左素喜写人物传记,对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人物,多有评价。对孙中山,左认为他是一个伟大人物,甚至认为“中山先生在中国和世界史上的地位,远在诸葛与伊藤之上。”[9](190)不过,左却反对神化孙中山,对戴季陶把孙中山打扮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继承人,颇不以为然。[7](96)对宋教仁,左著有《宋教仁评传》,对宋一生之事功及对革命之贡献,均有切实之陈述。针对戴季陶在《孙文主义哲学之基础》中把宋说成是“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等责宋之言论,左进行全面的辨正。[11](48-52)同时,左也指出“宋教仁之一生,其人自非绝无弱点:年事太浅,入世不深,对旧人物的估价太低,其一;锋芒太露,易招人忌,其二;以为一部约法,一个国会的多数党,即可制袁的死命,不免书生之见,其三;政治欲望太强,望治的心理太切,至不惜以身为殉,尚不与焉。”[11](61)
对清末民初的几位重要人物盛宣怀、张謇、梁士诒,左认为他们三人均“大抵重实践而不尚空谈,其毕生尽瘁于实业、交通、工矿、水利、金融、教育”,且“于政治以外殆又莫不注意外交焉。”[9](172)左对盛宣怀评价尤异于时人,他认为盛在清末政治上地位之重要,不下于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而所从事建设各端,对于国家关系之大,尤远非李、张辈所能及。左认为“世徒以其铁道国有政策为引起革命之导火线,乃并其一生之绩业而忘之;又以其身后颇为富有,甚至以之与今日毫无建树但有贪污之腐败官僚相提并论,似欠平允。”[9](154)左舜生对黎元洪大体持同情和理解态度了,认为黎元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至于干政治,他自来无此素养;即对他的性格,也是格格不入”。[11](129)左认为黎元洪的生平也有若干应该遭受批评或非议的事项,但是却不能否认他是中华民国开国的元勋之一。[11](130)而对段祺瑞,左舜生认为在一般北洋军人中,“毕竟不失为铁中铮铮,庸中佼佼”。[11](112)
左舜生对汪精卫的评价颇有意思,认为“大抵汪之为人,富感情而易冲动,经不起刺激,偶然也欢喜弄一点小聪明,多少带一点党人的积习,但本质仍不失为一读书人。”[8](1098)左对汪早年宣传革命,勇于赴义等充分肯定,说汪精卫是一个演说家,是国民党内一个了不起的宣传家。[7](7)对1911年汪精卫出狱后与袁克定结为兄弟,并同去彰德会袁一说,左即持存疑态度,“尚待其他可靠资料出现,始能确证其有无。”[7](77)左对汪后来误入歧途甚感惋惜,而对国民党人战后掘汪精卫的坟墓一事颇不以为然。[7](7)汪精卫后来成为汉奸,千夫所指,几成百无一是的众矢之的。左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客观评说,是其是,非其非,实属难能可贵。
左对同盟会、临时政府、立宪派等重要事件及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陈天华、居正、孙武、冯国璋等人物也自有看法。总体而言,由于左舜生接受过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启蒙,更兼有史家的独立客观的自觉,故其臧否人物,品评史事,颇能客观公允,言人之所未言,其中一些言论,即使今日看来,仍如黄钟大吕,空谷足音。
三、左氏治史的基本特征与史家素养
晚清以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绝大多数学者嗜好古史,普遍轻视当代史的研究,梁启超、罗家伦等为此都曾多加批判。就在这种潮流中,左舜生与李泰棻、蒋廷黻、罗家伦、郭廷以等一道,成为开拓近代史研究的少数人之一。从其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结合其他一些著作,会发现左氏治史之若干特征及史学之素养。⑦
首先,从左之论著中,可以发现其特别重视史料搜集及整理工作。史料本为史学之基础,凡是优良史家无不重视史料重要性,傅斯年甚至提升到“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高度,这点本无须多言。但在嗜古成癖的二三十年代,大多数史家无心于近代史研究,因此资料搜集、整理也就无从谈起。罗家伦是比较早意识到近代史料搜集、整理重要性的学者。1926年,罗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曾提出搜集整理近代史资料的粗略计划。1931年,罗家伦又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强调“在中国近代史方面要做任何工作的话,我便认定从编订中国近代史料丛书下手。”[12]蒋廷黻、李剑农、郭廷以也是很早意识到史料搜集及近代史研究重要性之学者。蒋廷黻于1931年编成出版《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上卷),对近代外交史展开开拓性之研究。李剑农则对近代中国政治史展开研究,于1930年出版《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郭廷以先生则在罗家伦、蒋廷黻之影响下,躬行实践,亦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之开拓人物。⑧
在左舜生眼中,要写一部系统的近代史著作,至少有三种困难,其中第一种困难即是“材料不容易搜集”。[13](1)当罗家伦还在设想计划的时候,左舜生就已在从事近代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了,并且在1926年就编成《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上、下册)这样的近代史资料汇编。该资料分为《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太平天国》《中法兵事本末》《蒙藏交涉》《中国革命之经过》等13部分,收入林则徐、罗惇曧等所撰重要史料63篇。⑨这应该是近代史方面最早的正式资料汇编,影响广泛(至1938年已经发行到第八版)。1933年左又编成《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上、下册),内含重要史料26篇⑩。这两部史料集都包含有辛亥革命方面的史料。
其后,1949年,大陆政权鼎革,左先至台湾,但不久就至香港,此后在港居留20年。左舍台湾而就香港,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因为在香港更易搜求近代史史料。为此,左利用香港有利地理条件,广泛搜罗,在经济时常紧张的情况下,还搜藏了近三万册图书资料。长期勤奋搜寻,使得左对史料极为熟稔,也使其研究立足在坚强的基石上面。阮毅成回忆说:“左先生对史料的搜集很勤,分析很明,立论更是很公正。我常怀疑许多史料的正确性,尤其是若干史话,得之于辗转流传,未尽可靠。而左先生却常给我一些批判,说何者应该是真的,何者应该是假的。凡他所说,他皆有坚强的立论根据。”[1] (62)
其次,通观左氏之研究,可以发现其特别注重史学之教育功能及历史知识之普及。近世以来的湖南,“经世致用”学风大盛,左氏生长其间,不无受到影响,更兼其所私淑的梁任公有“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4](7)的论说和倡发,左在著作时就特别重视史学的教育功能,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的阐发。比如《辛亥革命史》中云:“孙文发起兴中会以来……我们有名的与无名的若干先烈,牺牲幸福,牺牲财产,牺牲生命,或者久系狱中,或者逃往海外,以笔、以血、以手枪、以炸弹、以与满族争旦夕之命,这种精神实在是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也就是中华民国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凡属中华民国的人们,都是应该永矢勿忘的。”[5](17)诸如此类言语,在其论著中常能看到。
左同时很注意读者兴趣的培养和知识的普及。他特别反对史著平铺直叙、干枯死板的叙述方式,认为这样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左称“假定我们把这一百多年的大事,依先后次序逐一的讲下去,这会近于一篇流水账,看来应有尽有,实际按之无物,可能引不起听者的兴趣,讲者的责任感也未免过于轻松”。[15](1)左的追求在于把“历史讲的生动活泼,使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把历史人物“说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其成败得失之故,也能使听者心领神会。”[15](1)与左的上述追求相适应,左的著述也就有了一些为他人所不及的特质。比如注重人物研究,特别是湖湘人物研究,其撰述近代史事,往往从描述人物入手,从而构建历史全貌。左又非常擅于叙事,其文字生动,明白晓畅,深入浅出,而且常不拘一格,夹叙夹议,恣意汪洋,收放自如。
其三,以辛亥革命史研究为切角,从其所议所论中,可以感知左氏严谨持重,独立超然之史观。左对一般传说或单方记载,往往持慎重存疑态度。比如对汪精卫出狱后与袁克定结为兄弟,并同去彰德会袁一说,即持存疑态度。[7](76)关于孙黄会面由谁引介的问题,左最初从杨度口中得悉杨度为引介人,但持存疑态度,“当时固未敢深信,仅存其说以待证”,直到后来见了章士钊所著《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有关记载,左方始确信。[7](25)还比如关于谋刺吴禄贞为何人问题,左先是不确定地讲“或曰主谋刺吴者为良弼,或曰即袁世凯,以当时情势言之,其为出自良弼似较可信”。[15](323)后来写《黄兴评传》有足够证据时,又修正原来看法,“近来乃确实知道系出袁世凯。”[7](77)
研究历史难,而研究当代史尤难。这不仅因为资料的不易搜寻,还在于是非恩怨尚存,著者主观难免,更在于动辄有得罪在位者及各种政治势力而受种种打击的危险。因此,能否超越个人、地域、种族、宗教、党派乃至国家,以超然独立的态度秉笔直书,成为考验史家良知和史德的大问题。左舜生也有这样的顾忌。他在给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写书评时道:“现在这样一个多忌讳的时代,想要据事直书,也有动辄得咎的危险。”[13](1)但是诸多忌讳并没有使得左放弃他的追求,他曾讲到:“一个理想的中华民国国史馆,必须超出于一切党派与政治力量之外,让一部分的纯粹学人专力图之;研究编写的机构,也必须集合若干志同道合又确有研究的朋友们来分工合作;否则绝不会有一部真正可靠的信史出现,即有也不过是一种无聊的宣传品而已,如何能信今传后?”[15](3)左舜生独立超然、追求信史的原则,使得其辛亥革命史研究迥异于众多“无聊的宣传品”,从而显得颇为公允客观。比如突破国民党正统史观对黄兴贡献的肯定;比如关于武昌起义谁放第一枪的问题,左首先根据史料认定是程正瀛(程定国)而非熊秉坤,但左同时也充分肯定熊秉坤的劳绩。[7](61)另外左对汪精卫、盛宣怀、黎元洪、段祺瑞、立宪派的评价等等,均颇为客观,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溢美,不隐过,如今读来,仍让人信服。
其四,左特别注重、擅长归类总结和史实考订。左长期浸淫于近代史,对近代史史料、史事极为熟稔,因此能时相比较,并归类总结。比如对三个湖南少壮人才(谭嗣同、宋教仁、蔡锷)都断送袁世凯之手的总结;比如对清末四个那拉氏(指慈禧、光绪之母、隆裕太后及端王福晋)的总结,并认为慈禧掌握中国的政权47年,其基础便大体建立在这一血缘与亲戚的关系上面;[8](1046)还比如对孙中山先生每隔十年革命事业便迈进一步的归类(1885年立志反清;1895年第一次起义;1905年成立同盟会)。诸如此类,不禁让人耳目为之一新。左专擅史事考订,行文中往往不忘做些史事考订,如对李云汉《黄克强先生年谱稿》所记慈禧寿辰的更正等等[7](17)。
左自1913年进入上海震旦学院研习法文,三年后因经济原因辍学。左在大学期间并未受过史学方面的严格训练,后来走上史学之路,完全是自学他人所致。对左治史影响最大的,一为章太炎,一为梁启超。九一八事变后两年间,章太炎居上海同孚路同福里,与左居所不远,左必每周一次或两次前往,向其请益,左自称“此实生平亲受前辈教益最多之一时期。”[9](272)梁启超对左的影响更大。左自己坦言:“五十年来,支配我精神生活者,以任公为第一人。”[8](1056)因此,左向来是以梁私淑弟子自居,梁逝世后还以私淑弟子的身份前往致祭。[16]假如对梁、左史学特质进行比较,会发现梁对左的影响确实无处不在。
四、简要的评论
香港学者李金强先生在论及左舜生史学之局限时,以唐德刚先生所定传统史学之标准来衡量⑪,称其“仍然未能脱离传统中国史学之局格”。[3](92)台湾学者陈正茂先生则基本沿袭此一说法。笔者以为,此论值得推敲。首先,唐之衡量标准即不无问题。强调“英雄造时势”、以通史为主的泛论史学及注意小考证固然也是传统史学若干方面的特征,但很难说是传统史学的本质特征,我们不能仅以此来作衡量。至于“接受传统儒家观念”一条,确为传统史学之要核,但左氏著作并未见儒家观念的束缚。
其实,由于左受新史学先驱梁启超、章太炎的影响,其史学尽管也受传统史学的影响,但已经很难以传统史学范畴来涵盖。就体例言,左著如《辛亥革命史》等已采用章节体,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来叙述历史过程,这已不同于传统史学之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体例;就表达方式而言,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中侧重记述,很多是千篇一律的平铺直叙[14](10),而左之著作则采用言简意赅、明白晓畅的白话文,有记述也有解释;就史学功用言,左的著作发扬爱国主义和知识普及的目的非常明显,与传统史学为帝王“取鉴资治”和在儒家观念主导下的“善善恶恶”的“垂训”教化功能异乎其趣;就史观言,左受进化史观的影响,有意识地探求事件因果关联,这也与传统史学的循环史观、倒退史观区别开来。
当然,从史学发展趋势和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衡量,左氏著述也有不足。这从其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可窥见一二。自从梁启超打出新史学的旗号,批判旧史为一人一家之谱牒、宣扬以民史代替君史以来,史家著史时开始有意识地超越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政治史、军事史,目光由上至下,把范围拓展至与更多人息息相关的社会史、文化史领域。比如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李泰棻、孟世杰的近代史著作中,已经加进了文化史、社会史的内容。⑫与一些先觉者已经在追求普遍史相较,左舜生的著作就略显陈旧,可以发现,其辛亥革命史研究以政治史为中心,研究的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等均是重要人物,对普通大众、社会结构、社会风俗、社会思潮、社会团体等等则未有论及,这是一大遗憾。
左从三十年代后,激于内忧外患,卷入政治洪流中,渐至不能自拔。先是九一八后参加上海各种救亡运动,接着重整青年党党务,并担任委员长,促成国、青两党合作。抗战爆发后活跃于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民盟,战后则奔走于国共间,居中调停,参加政协、国大,直至官拜部长。十几年间,左忙于党务政事,俗务繁剧,自难专心于其喜爱的文艺与史学。左晚年居留香港,虽然专意教学著史,勤于笔耕,但囿于材料和研究条件等限制,也未做精深的研究。故观其著述,多为《中国近代史四讲》这样由教学讲义集成的通论性著作和《中国近代三度改革运动的检讨》这样的史论、散论,缺少进行系统阐述某一问题的专题性研究,也没有写过一篇规范的专题论文。若以严格的学术标准衡量之,确有所限。其晚年力作《黄兴评传》,也仍显简单粗糙。对此,左自己也有意识,故其在文中屡有“以供他日为克强先生正式写一篇详传者的参考”[7](113)等语 。
左史学以上种种局限,既是其个性使然,也是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及有限的研究条件所致。唐代史家刘知几曾有才、学、识“史才三长论”,清代史家章学诚在此基础上又添有“史德”。以此考诸左舜生,发现其四点并不缺乏。论才,左舜生谋篇布局、行文造句的能力都是一流的,其文字生动流畅,简洁精炼,且颇有神韵,常能使人感染;论学,左知识渊博,每让其身边的人赞服;论识,左氏搜集、鉴别史料的功夫,还有左之观察力、判断力以及知人论世的能力亦不亚于他人,故屡有真知灼见;论德,左秉持超然独立的原则,善善恶恶,风骨凛然,一如其党号“谔公”(取“千人诺诺,一士谔谔”之意)。左又是一个相当勤奋自励的人,晚年仍以“一天至少要当一天半来用”的精神,发奋读书,勤于笔耕,以期“再完成几部历史著作”[1](7)。假如不身逢乱世,天假以年,给其一个良好的研究条件,相信左舜生在史学上应当有更大成就。
注释:
① 1923年高劳所编写之《辛亥革命史》,总共约32000字,只简单分《革命战争时代》《革命成功时代》《临时政府成立时代》三章,内容叙述甚为简略。辛亥革命爆发前之内容,仅560余字,使得该书几与武昌首义史无异。郭真所著《辛亥革命史》则更为简单,全书三章《辛亥革命的由来》《辛亥革命略史》《辛亥革命的结果》,仅2万多字,对兴中会、同盟会、临时政府成立、南北议和、清帝逊位等等标志性事件着墨甚少,未能作为章节突出,把辛亥革命内在发展阶段与逻辑呈现出来。见高劳:《辛亥革命史》,东方杂志社,1923年;郭真:《辛亥革命史》,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
② 据萧致治先生统计,从1949年到1979年间,总共只出版了两本小册子,三篇论文,十多篇回忆录与资料。本统计及大陆此一时期对黄兴的研究,参看萧致治:《黄兴的历史地位与黄兴研究的回顾》,《益阳师专学报》2000年第21卷第4期。
③ 关于正统学派,可参看李金强:《辛亥革命的研究》,“中研院”近史所编:《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下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9年,第751-809页;朱英:《海峡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和学术交流》, 《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225-234页。
④ 当时除左舜生外,少数人如张朋园在六十年代对梁启超的系列研究,张玉法先生在七十年代对清季立宪团体的系列研究,也修正、突破了国民党正统史观,促使辛亥革命研究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参见李金强:《辛亥革命的研究》,中研院近史所编:《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下册),第751-809页。
⑤ 《黄兴与中国革命》原为英文著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后为杨慎之译出,由香港三联书店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分别出版。陈维纶著《黄克强先生传记》及李云汉撰《黄克强先生年谱》均由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3年出版。
⑥ 关于章张之争,可见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以及张玉法《辛亥革命史论》(台北:三民书局,1993年)等论文、著作。
⑦ 关于左氏治史特征,李金强先生简略地总结为“擅长史事叙述”“留心史实之考证”“注重人物研究”“注重湖南人物及史事”“评骘人物,尤能应用‘知人论世’此一原则”这五点。陈正茂先生则基本沿袭此一分析。见李金强:《民国史学南移——左舜生生平与香港史学》,第91页,及陈正茂:《左舜生之史学特点与贡献》,《中国青年党研究论集》,第101-103页。
⑧ 三人之中国近代史研究,可参看下列论文:沈渭滨:《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72-79页;萧致治:《李剑农:世界级大史学家——纪念李剑农逝世40周年》,《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56卷第1期,第46-53页;李金强:《南港学派的创始者——郭廷以的生平志业及其弟子》,李金强主编:《世变中的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194页;吕实强:《辛勤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郭廷以先生》,收入张朋园等:《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241-260页;李金强:《传承与开拓——一九四九年后台湾之中国近代史研究》,收入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趋势》,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4年,第37-76页。
⑨ 详见左舜生选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中华书局,1926年。
⑩ 详见左舜生选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中华书局,1933年。
⑪唐德刚先生认为传统中国史学特征,包括三点:(一)接受传统儒家观念;(二)重视“人治史学”,强调“英雄造时势”;(三)以通史为主的泛论史学及注意小考证。见唐德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台北:《传记文学》1987年第51卷第4期,第26页。
⑫李泰棻编著的《新著中国近百年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包括三编,其中第三编为《文明史》,共分《制度》《宗教》《学术》《社会》四篇。孟世杰所著《中国近百年史》(天津:百城书局,1932年)也包括有社会史、文化史内容,比如第二编之第十、十一、十二章分别为《光宣时代之文运》《清季之政治组织》《清季之社会状况》。
[1] 周宝三. 左舜生先生纪念集[C].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1.
[2] 陈正茂. 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上册)[C].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6.
[3] 李金强. 民国史学南移——左舜生生平与香港史学[J]. 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刊, 1989(3): 85-96.
[4] 陈正茂. 左舜生之史学特点与贡献[C]//中国青年党研究论集.台北: 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8.
[5] 左舜生. 辛亥革命史[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4.
[6] 章开沅. 5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J]. 近代史研究, 1999(5): 223.
[7] 左舜生. 黄兴评传[M].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8.
[8] 陈正茂. 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中册)[C]. 台北: 中研院近史所, 1996.
[9] 春风燕子楼——左舜生文史札记[C]. 北京: 学林出版社, 1997.
[10] 左舜生. 左舜生自撰集(政论, 时评)[C]. 台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8: 86.
[11] 左舜生. 中国近代史话二集[C]. 香港: 文艺书屋, 1969.
[12] 罗家伦.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C]//汪朝光. 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近代史卷.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0: 51.
[13] 左舜生. 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者介绍一本好书[J]. 复旦大学政治学报, 1931(1): 1-5.
[14] 梁启超. 新史学[C]//桑兵, 等. 近代中国学术思想, 北京:中华书局, 2008.
[15] 左舜生. 中国近代史四讲[M]. 台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3.
[16] 左舜生. 中国近代史话初集[C]. 香港: 文艺书屋, 1969: 115.
Zuo Shunsheng’s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s works
ZENG Hui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Zuo Shunsheng was one of the pioneers of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His early works on the 1911 Revolution possessed a preliminary scale and gradual system and had stronger academic significance. Furthermore, his late study appeared more mature.The Commentary Biolgraphy of Huang Xin, which broken the KMT'S orthodox view,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ooks about Huang Xing. Zuo had his particular opinions on the famous people and events, as well as the period, scope, nature, result of the 1911 Revolution. His study showed his ow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aying a special attention to source col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focusing o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the knowledge spread of history, his strict attitude, independent and objective discussion, are good at the classification, conclusion, investigation and corr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so on. Some defects, can be found in his study, such as narrow range of research and not making topic study. In general, Zuo was still an accomplished historian.
Zuo Shunsheng;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K257
A
1672-3104(2014)02-0271-07
[编辑: 苏慧]
2013-06-27;
2013-09-23
曾辉(1982-),男,江西赣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华民国史
——以近代史所为中心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