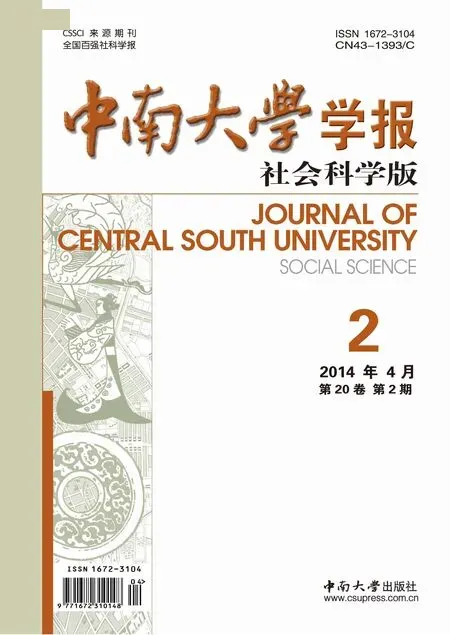论陈献章及其门人的隐士传统
董铁柱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广东珠海,219085)
有明一代,隐士风气有式微之势。《宋史·隐逸传》中记载了近50位隐士,有学者统计,宋代知名的隐士至少有300多位。而《明史· 隐逸传》中却只有12位传主。根据《明史·隐逸传》之序,文学行谊可称者,已散见诸传,《明史·隐逸传》只选取了“贞节超迈者数人”,因此以张海鸥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明代的隐士风气不如前朝即是不争的事实[1]。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代广东儒生中所呈现出的一股隐士趋向就显得尤为独特。虽然这些人并没有被收录于《明史· 隐逸传》,但是其所为与一般定义上的隐士并无不同。根据《明儒学案》卷八《白沙学案》的记载,这一批隐士几乎都是白沙先生陈献章(1428—1500)(以下简称白沙)的追随者。以白沙为代表的岭南儒学在明代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早已为学者所公认。这一隐士群体有着什么样的特点?究竟陈献章的思想对于这一隐士群体有着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发现他们对仕途态度的思想原因。
一、陈氏之作为隐士的基本理由
白沙作为明代广东儒学的先驱,“上承陆象山,下开王阳明,是程朱理学向心学过渡的转折点”[2](39), 其哲学当然是这一隐士群体的思想之源。而白沙之学的要点,正如黄宗羲所指出的那样:“其吃紧功夫,全在涵养。”[3](79)至于涵养的内容,则是所谓的善端。白沙曾对学生说过:“夫养善端于静坐,而求义理于书册,则书册有时而可废,善端不可不涵养也。”[4](975)这明确指出涵养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善端,而涵养的功夫则是以“静”为最基本的途径。
白沙云:“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4](133)这意味着道德境界的涵养与提高之关键并不在于外求。尽管几乎每一个研究白沙的学者都曾指出“心”和“静”在其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性,也肯定其通过“反求内心”的功夫达到超道德自然境界的主张之意义[5](252),更有人因此认为他是明代思想创新的先驱[6](244),但是据笔者所知,似乎并没有学者将陈献章视为隐士。众所周知,自求学于吴与弼后,白沙“归即绝意科举,筑春阳台而居,静坐其中,不出域外者数年”[2](79)。这一段经历人人皆知,但学者多将这看做是其悟道的一个过程,强调的是“静坐”而非“隐居”。黄明同在《陈献章评传》中认为白沙的这一段经历是为了创立“自得之学”[7](37),苟小泉在《陈白沙哲学研究》中也基本持此论[8](50)。
为何学者一方面重视白沙的“静”与“自得”,另一方面却很少肯定其思想与行为中的隐士之风?从宋明理学的源流来看,从周敦颐、二程到朱熹都推崇静坐[9](230),而白沙静坐之学与周敦颐思想的关系也早已为学者们所承认[7](61)。如果将静坐的思想归为隐士之风,那么“共同承担并体现了这一时代的民族精神”的宋明理学[4](14),就面临着有可能被定义为有隐逸趋向的危险。虽然有学者认为朱子之学重内圣轻外王的态度造成了不少隐士[1],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理学家们的思想和行为是积极入世的,他们不断“寻求士人阶层的支持……同时也逼迫朝廷与皇帝承认他们对圣人之学的理解是正确的”[10](80)。因此不少学者煞费苦心地指出,白沙“主静”观的实质是主“动”[11](184−191),与佛教的“寂灭”和道家的“虚空”不同,表现的是“儒家的积极有为的‘刚健’特征”[7](56)。简而言之,作为明代理学的开拓者之一,白沙若是被贴上隐士的标签,那么理学的积极性就有可能被削弱,毕竟根据陈来的理解,理学“以儒家的圣人为理想人格,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的终极目的”[7](61)。
但在笔者看来,白沙的思想和行为可以说与隐士之风相符。根据传统儒家的定义,“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荀子·非十二子》)。白沙可以说完全符合这些标准。尽管当代学者对隐士的定义颇有争论,张海鸥、肖玉峰、谢宝富等人先后都曾撰文进行剖析,然而基本都认为“德”和“不仕”是隐士的两个基本要素,谢宝富就直接把隐士定义为“看破仕途而不仕的拥有一定学识才德的人”[12](53),更以陶渊明为例,指出即使在某段时间出仕,但在归隐后就可以算是隐士。按照这些标准,白沙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隐士。
如前所述,白沙早年也曾参加乡试、会试,但在经历了落第的挫折之后,遂绝意科举。他在江门“暨归杜门,独扫一室,日静坐其中”[3](807),行为上已经做到了“隐”。更重要的是,白沙之“隐”是为了参透为学之路,并不是为了出仕,在其静坐期间,发生了明朝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掳,在全国震惊的情况下,白沙不为所动,依然独处春阳台,可见其心确实不再关心政事。因此可以说,从行为到目的,白沙都可以称得上隐士。
从思想来看,白沙对于功业的态度也颇具隐逸色彩。白沙对功业的态度与其老师吴与弼一脉相承。美国汉学家包弼德(Peter Bol)指出,吴与弼的理学重视内心的道德修养,“从科场与当代政治社会抽离,拒绝迎合皇权”[1](132)。 尽管白沙在按照吴与弼践履笃实的功夫路子修炼后无所得而从“敬畏”转向“洒落”,进而主张在“静”中自得其心,但是其自得功夫的目的和吴与弼主“敬”的目的并无二致,两者最终都指向个人道德修养,而这种道德修养并不需要以政治上的功业作为前提。这便为白沙不热衷于出仕奠定了思想基础。
白沙不以功业为挂碍,但决不是完全否定功业。白沙云:“人心上容留一物不得,才著一物,则有碍。且如功业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业上,此心便不广大,便是有累之心。”[2](85)他并不是绝对反对功业,而是反对因追求功业而使心有了束缚不能自得。而对于普通人而言,在追求功业的过程中几乎必然会迷失自己,故白沙一方面教学生必以静为先,另一方面则教导学生不要执着于为官,这都是为了让学生知道不以“外物累己”。因此,隐逸对于白沙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为学的必要阶段。他说:“学者先须理会气象,气象好时,百事自当。”[2](84)而静坐隐逸则是理会气象不可缺少的过程。白沙在《论学书》中说,通过长时间的静坐,“然后见吾心之体,……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这也是白沙之所以教学生要从静坐入手的原因,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经历。如果学生突破了这一阶段,那么无论是出仕还是不仕,都可以做到自如;而如果还没有突破这一阶段,那么就应该继续“隐”,若是勉强出仕,则难免会碰壁。白沙诸学生的经历对此作了很好的注解。
二、陈氏隐逸之风对门人的影响
白沙一生大多居于岭南,其门下弟子也多为岭南人士[1]。其学生中不乏像湛若水这样曾任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的成功人士;而曾涉足官场而后无心功业的也不少。其弟子这两种不同的选择,正是白沙对于功业辩证理解的两方面的体现。无心功业的弟子正是本文所讨论的对象。在他们当中,既有做到了进退自如随心所欲的,也有待人接物有所欠缺者。前者应该是突破了隐的阶段,而后者则属于尚未在静坐中找到气象的。这更加说明白沙门下,隐作为必要阶段的重要性。
根据上文所说“德”与“不仕”的隐士标准,白沙的岭南弟子中,共有张诩、林光、陈庸、李孔修、谢祐、何廷矩等人可以算是隐士[2]。其中,只有张诩一人可以算是出处皆自得的理想典型;其余五人中,李孔修和陈庸二人性格似有欠缺,林光不该出仕而出,谢祐与何廷矩则拘泥于隐。由此可见,白沙之教学生,“其初必令静坐,以养其善端”[2](106),这样的功夫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要突破这一阶段,实在并非易事。笔者将通过考察上述六人的隐士之行,以发现白沙之学对他们的影响。
张诩的“隐”被很多学者所忽视。如张学智在《明代哲学史》中介绍白沙弟子时,说:“张诩字廷实,号东所,广东南海人,成化进士,官至南京通政司左参议。”[1](55)这显然是一种故意的忽略,因为到此为止,张诩的生平与普通儒者无异。然而,《明儒学案》中明确说张诩“养病归,六年不出……寻丁忧,累荐不起”[2](95),可见张诩虽然仕途顺利,但是却不仅有隐逸之心,亦有隐逸之举,对于功业的态度与白沙并无不同,是典型的出入于官场但不为功名所累的隐士。
张诩对于岭南学术的传承有着强烈的自觉性:“天旋地转,今浙闽为天地之中,然则我百粤其邹鲁与?”[2](97)面对当时浙学的兴盛,张诩认为自己的老师白沙才是堪比孔子的一代圣贤,“其学圣学也”[2](98)。在张诩看来,白沙与孔子相似之处甚多,隐逸观点即是其中一处。张诩认为白沙选择隐居,并不是因为在科举考试中遭受打击后不得已的选择,“或者以其不大用于世为可恨者,是未知天也”[2](98)。他认为自己老师之所以安心居于白沙村,是由于天性使然,所谓天生圣贤,而“圣功叵测,其可以穷达限耶?”[2](98)
和白沙一样,张诩对于隐,持两可的态度:“出处无常,惟义所在,若坚守不出之心以为恒,斯孔子所谓果哉也。”[2](98)可见他觉得隐不是目的,在需要隐的时候,则应该做一个处士,而需要出仕的时候,则重新为官。张诩多次往返于归隐和出仕之间,尽管没有相应的史料说明原因,但大约正是其基于义的选择。如谢宝富所指出的那样,“隐士是个变量,意即某人某段时间当官了,他就不是隐士,某段时间他厌仕且归隐了,他就是隐士”[9](61)。当张诩因为义而选择不仕时,我们完全可以把他视为一个隐士。
张诩对“隐”的态度,与他的为学宗旨紧密相关。白沙如此评价张诩:“廷实之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即心观妙,以揆圣人之用。”[2](95)值得注意的是,刘宗周对于白沙的评价也正是“学宗自然”[2](46)。因此张诩在治学上可谓与其师一脉相承,讲究对于内心的探求。
所谓自然,就是“即心观妙”,也就是说世间的乐处,完全靠自己内心的体验。张诩他说自己早年跟随父亲宦游,见烟雨杨柳,境与心得,但不知为何而乐;后稍长,读前人诗句“柳塘春水漫”,则句与心得,但仍不知乐之根源;及至养病后主静,才发现境与诗都并非乐之本源,“所谓至乐与至妙者,皆不假外求而得矣”[2](97)。换言之,张诩和白沙一样,隐逸之趣向的存在是因为他们都对“心”的重视与肯定。
和张诩相比,李孔修的“隐”却更加明确,做到了不出仕与独居。李孔修字子长,广州人,由张诩推荐入白沙门下,一直不曾追求功名,且二十多年不入城,以性格特立独行闻名于当时,因此出门甚至会被围观,可以说是一位另类隐士。
根据《明儒学案》所载,李孔修父亲过世后,庶母出嫁,诬陷其夺财产,将其告上了县衙。县令询问他,李孔修用笔回答说“母言是也”。县令因此反而对案情有所怀疑,并花时间查清了真相。这则轶事首先说明了李孔修不扬母恶的“孝”行,是儒家孝道与亲亲相隐的实践者;更重要的细节是,李孔修并不愿意直接和县令对话。这可以理解为他对官员的排斥和不屑。李孔修在另一则轶事中同样透露着对官员敬而远之的态度:有一次他送粮食到县衙,县令觉得他仪表非凡便问他姓名,他却不回答只是拱手。县令大怒说:“何物小民,乃与上官为礼。”李孔修依然只是拱手。发怒的县令鞭打了他五下,李孔修最终还是无言离去。
李孔修的守礼还体现在平日里也戴管宁帽,着朱子深衣。朱子深衣是典型的礼服,在祭祀时都可穿,平时穿朱子深衣说明李孔修严格地以礼来约束自己的日常行为。这当然和白沙对于礼的肯定相一致。白沙云:“弃礼从俗,坏名教事,贤者不为。”[3](236)在守礼的同时蔑视官员,李孔修可以说结合了儒家和隐士的双重传统。他对于官僚体系的排斥是白沙无意于功业思想的极端体现。但是其特立有余、圆通不足的性格就本质而言反而是一种“显”。有学者指出,有的隐士其实是希望通过自己的“隐”来表达自己的思想[13](86−89)。在这个意义上,李孔修可以算是一位成功的隐士,因为当时的儿童妇女都知道这位“子长先生”,以至于他死后甚至当地人祭社还会配以李孔修。
与李孔修齐名的谢祐同样过着更加极端的隐居生活。谢祐字天锡,南海人。他“筑室葵山之下,并日而食,袜不掩胫”[2](107),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却“名利之事,纤毫不能入”,最后过世时甚至无钱入土,靠同门的帮助才得以下葬。虽然明代南海人霍韬对李孔修和谢祐评价甚高,说“白沙抗节振世之志,惟子长(李孔修)、张诩、谢祐不失”[2](107),认为他们和张诩一样继承了白沙之风,但是在笔者看来,白沙对于隐和仕的态度是温和而不执的,如果说张诩很好地发扬了白沙的思想,那么李孔修和谢祐则走的是更为激进的路线。所谓抗节振世,实在是两个有机的部分:抗节自然是指保持节操不出仕,而振世则是保持对社会的关注,张诩可以说确实做到了这两个方面,但是李、谢二人却抗节有余而振世不足,让人觉得他们对于出处的理解有失偏颇,以至于当时甚至有人认为李孔修是“废人”[2](107)。
同为白沙门人的陈庸对李孔修评价甚高,认为“子长诚废,则颜子诚愚”[2](107),将李孔修的奇特之举与颜回相提并论。有趣的是,陈庸自己也是一个缺乏社交能力之人。陈庸字秉常,南海人,成化进士,张诩正是由他介绍给白沙的。但是与张诩在仕途的成功不同,陈庸五十岁时才以荆门州同入仕,而为官仅五天,就因为不能屈伸而解官。在应该知天命的年纪而不知如何在官场应对,可见陈庸并没有达到其师白沙日用洒扫进退自如的境界。在官场失败之后,陈庸选择杜门不入城郭,开始了隐居生活。当时的督学王弘想要拜访他,陈庸也坚持不出。这也许是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官场受挫,是因为还尚未经历白沙所主张的“必要”的隐居阶段,还远未达到义理融液与操存洒落的统一。
林光,东莞人,成化乙酉举人。会试入京遇白沙后,归江门在深山中隐居治学二十年,白沙称其“所见甚是超脱,甚是完全”。和白沙、张诩一样,林光认为:“所谓闻道者,在自得耳。读尽天下书,说尽天下理,无自得入头处,终是闲也。”[2](105)既然闻道在于自得,那么就和功业没有必然关联,林光不欲仕也就和他的哲学观点相一致。后来林光为了赡养母亲而出仕,白沙对此严厉批评,认为“因升斗之禄以求便养……胸中不皎洁磊落也”[2](105)。既然如前文所言,白沙并不全然反对功业,之所以如此指责林光,应该是因为他认为林光尚未通过隐居达到自得之境,以无挂碍之心出入仕途。《明儒学案》说白沙对林光指责严厉是因为之前对他赞许有加,这多少于理不通:既然白沙不否定功业的意义,就不应对林光出仕如此反对。只有理解成白沙觉得林光境界未到,才较为合理。毕竟,虽然白沙称赞林光,但是“所见”超脱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身体力行。如张学智所指出的那样,白沙所强调的能力“重要的是在实事上体悟……须以道德实践为主”[1](49)。尽管林光是公认的白沙门下得意弟子,但是在白沙看来,其境界依然不足以出仕。
从白沙对何廷炬归隐的态度上,可以推测出其对于林光的批评应该源于林自身的境界。何廷炬字时振,番禺人,为郡诸生,入白沙门后,即弃举子业。即使是学使胡蓉挽之秋试,何廷炬也坚持拒绝。为此白沙写诗云:“孟轲走四方,从者数十车。出处固有间,谁能别贤愚。”言下之意,似乎倒是在规劝何廷炬不必拘泥于隐逸,态度不必凝固僵化。尽管何廷炬并没有因此出仕,但由此可见,在白沙心目中,何廷炬的境界其实已经超过了必须“隐”的阶段。
三、结语
《明史·隐逸传》之序说:“夫圣贤以用世为心,而逸民以肥遁为节,岂性分使然,亦各行其志而已。”白沙的思想,却正是要把这两种不同的性与志有机地合二为一,因此注定会陶冶出一批具有隐士情怀的儒生。但是能真正做到出处自如的门生,却实在是凤毛麟角,这是由于白沙之学在实践上的难度所造成的。正如张学智所指出的那样,“义理融液与操存洒落的统一……是儒家功夫的最上乘,因而最难达到”[1](49),这便是白沙隐逸思想的悖论所在。
[1]张海鸥.《宋代隐士隐居原因初探》[J]: 求索, 1999(4): 85−89.
[2]张学智.《明代哲学史》[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3]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4]陈献章.《陈献章集》[M].北京: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5]陈来.《宋明理学》[M].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6]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7]黄明同.《陈献章评传》[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8]苟小泉.《陈白沙哲学研究》[M].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9]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M].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10]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M].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11]简又文.《白沙子研究》, [M].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70.
[12]谢宝富.《隐士定义及古称的考察》[J].江汉论坛, 1996(4): 53.
[13]肖玉峰.隐士的定义、名称及分类[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6): 8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