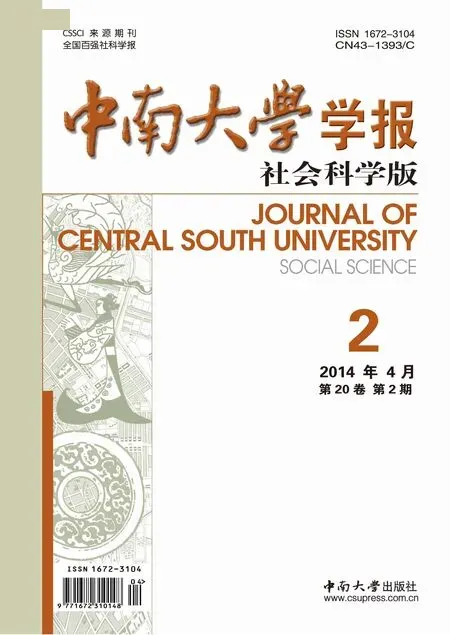论《失乐园》的末三卷
彭晓娥,吴玲英
(湖南商学院外语系,湖南长沙,410004;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对基督教史诗诗人兼基督教神学家弥尔顿而言,其史诗创作的实质在于再现《基督教教义》①中有关堕落之人精神再生的神学思想。弥尔顿在《教义》里反复强调,堕落之人可通过忏悔和恢复信仰达至“人之再生”,而在其史诗《失乐园》里、尤其是最后的第十卷、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中,弥尔顿将这一神学教义加以高度细节化和艺术化,呈现了亚当夏娃从堕落再生为基督式英雄的过程,并使亚当夏娃在史诗最后三卷的经历成为每个堕落之人再生的必经旅程。换言之,在弥尔顿的史诗里,“人的堕落与人之再生永恒纠缠,无法分离”[1];堕落之人通过忏悔其罪孽而悔悟,通过回归和坚定对上帝的信仰,通过将外在的力量内化,建构和完善再生所需的“内在精神”,并凭借它“以善胜恶,以小事成大业”(PLXII.566),最终从精神死亡中再生,成长为基督式精神英雄。
一
正因为史诗(尤其是末三卷)在很大程度上是弥尔顿神学思想的艺术形式,因此,有关《失乐园》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史诗的前九卷,其中特别是撒旦的人物塑造、亚当夏娃的天真状态及堕落过程。很多学者抱怨,《失乐园》的最后三卷,尤其是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平淡乏味、令人失望。艾迪生(Joseph Addison)认为,“弥尔顿太关注其神学思想而忽略了诗歌艺术”[2];牛顿(Thomas Newton)说,“史诗的最后两卷缺少《伊里亚特》等其他史诗的崇高美”[3],但牛顿分析,这是由于主题的改变,并指出,最后两卷的主题是历史而不是诗歌。还有学者认为,史诗的最后三卷与其他诗卷“没有连贯”[4]或“脱节”[5]。拉詹(Balanchandra Rajan)的观点尤为极端,他评论说,“整个场景(史诗最后三卷)没有任何作用”[6]。这些学者还设想了多种解释,认为,弥尔顿在创作史诗的最后三卷时已才思枯竭,想象力空乏,因而导致诗歌创作失败。如,刘易斯(C.S.Lewis)感叹,“这一叙述部分(指史诗的最后三卷)糟糕得令人好奇”,并写道,“弥尔顿的才能,如华兹华斯晚年的才能一样,已离他远去……这或是因为弥尔顿身体欠佳,或是因为他年纪已大,或是受到一种灾难性的自然烦恼之影响”。[7]当然,也有少数学者为弥尔顿辩护,如,普林斯(F.T.Prince)将史诗的最后三卷视为史诗必不可少的部分[8];赖特(B.A.Wright )认为,第十卷、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都是亚当故事的必要组成,是亚当认识的转折,“是诗歌的主旨”。[9]
仅从本研究所关注的史诗主题来判断,史诗的最后三卷便构成史诗不可分离的部分。具体而言,史诗的第六卷、第一卷和第二卷追索撒旦之流因自傲而发动天庭叛乱,失败被贬地狱后撒旦为报复上帝而决定引诱人类堕落。史诗的第三卷、第七卷和第八卷旨在宣扬天理和公正的存在,既解释随后亚当夏娃堕落的不可饶恕性和他们受惩罚的不可避免性,也为他们的精神再生埋下伏笔。史诗第四卷、第五卷和第九卷集中呈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幸福生活和受诱惑而堕落的过程。史诗第十卷描述堕落的亚当夏娃在惩罚后开始忏悔。史诗的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展示亚当夏娃堕落后艰难的精神再生旅程。史诗通过向世人阐明和昭示“永恒的天理”和“天道的公正”(PLI.25; 26),探寻人精神追寻过程的四个阶段:天真状态、堕落过程、惩罚时期及精神再生。由此,“包含整个人类的亚当夏娃”自然是史诗的主人公和英雄,也自然成为《失乐园》的中心。②也就是说,一切场景为亚当夏娃而变换,一切人物为之而塑造,一切行为之而发生。总之,史诗里的一切都为之而存在。
此外,宏大史诗《失乐园》共有十二卷,但其中最有意义、诗人本人最欣赏的是史诗的末三卷,因为这里呈现了亚当夏娃如何从堕落走向再生的过程,而这对于旨意在于塑造基督式英雄的诗人弥尔顿而言乃是关键所在。弥尔顿曾在《第二次辩护》中强调,史诗诗人必须严格遵循既定原则,不可能、也不应该包含史诗主人公的一生,而往往只聚焦其人生的“某一特定事件”(WJMVIII, 253)。弥尔顿在史诗里将亚当③一生中的“特定事件”限定为“堕落”,具体包括其堕落前乐园生活的一瞥、堕落时的历史性时刻及堕落后的精神再生旅程。而就“堕落亚当夏娃再生为基督式精神英雄”这一过程而言,史诗又将之分为三个阶段,具体体现在史诗的第十卷、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
二
首先,史诗第十卷生动地刻画了亚当夏娃“从堕落走向再生”的第一个阶段:“虔诚忏悔”阶段。史诗描述,亚当夏娃因屈服于撒旦的诱惑而堕落,并被判决赶出伊甸园。面对正义的判决,亚当内心深感痛苦,逐渐认识到堕落带来的可怕后果。史诗里的长段独白(PLX.720-844)披露出堕落亚当的羞愧和绝望。亚当意识到,自己未来的人生将充满痛苦,其后代也将因此遭受同样的罪。一时间,亚当,如深陷困境和绝望中的参孙一样,期望尽早解脱,说,“让我去死,变成/无知无觉的泥土”(PLX.776−777)。比较亚当的第一次独白和此时的独白,我们可以看出堕落给亚当造成的变化。在第一次独白中,亚当将所有的赞美辞和荣耀都归于上帝,而这时的亚当虽已决定与夏娃同罪,但和夏娃、甚至撒旦一样指责上帝,字句里都是自我。亚当在第 867−888诗行和第 949−959诗行里分别将“我”和“我的”重复10次和11次,将“你”和“你的”分别重复7次和6次。亚当最初以“他”(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转而由“我”(亚当自己)和“你”(夏娃)取代。亚当和撒旦一样因自傲和以自我为中心而堕落。但亚当通过与自己论辩、通过自我审视和自我反思,于独白的最后幡然悔悟,接受现实,勇敢承担责任,自责道,“一切腐败的源头在于我,/一切罪责,从头到尾都在我身上”(PLX.833−834)。
夏娃希望安慰亚当,但亚当严厉以斥:“别让我看见你,你这条蛇!”(PLX.867)。在这之前,亚当一直称呼夏娃为“人类的母亲”或“上帝的女儿”,这是亚当第一次别称夏娃。④在基督教中,蛇自然指诱惑者和万恶之源撒旦。亚当在长达42行的段落里愤怒地表达了对夏娃的厌恶,包括夏娃蛇一样的体态、诡诈的内心、骄矜和虚荣的本性等。关于这段责骂,尤其是其中称女人为“祸水”(PLX.896)和视女人为“惹起人世间无穷灾害,/破坏家庭和平的原因”(PLX.905−906)等诗行,从约翰逊开始,就有评论者将之解读为弥尔顿对包括自己妻子在内的所有女性的攻击。⑤但不可否认,是夏娃的爱让亚当开始忏悔,学会谦卑。夏娃本人首先开始忏悔,因为她已充分认识到自己罪孽的深重,也认识到自己诱惑亚当与她同罪的严重性。面对亚当的责骂,夏娃没有反驳,而是不停地流泪,头发散乱而谦卑地伏在亚当的脚下,祈求亚当“不要这样抛弃我”,并希望“把全部罪名,/从你头上转移,全部归在我身上”(PLX.910;935)。“谦卑”是基督教的关键美德之一。爱默生认为,“(一个人)真正的伟大就在于其完全的谦卑”。[10]谦卑的人才会顺从,面对自己的罪孽时也才会忏悔。弥尔顿在夏娃的身上刻画出堕落世界里堕落之人再生为精神英雄的潜在品质,如谦卑、顺从以及为所犯之罪而忍耐的决心。
面对虔诚忏悔和谦卑的夏娃,亚当怜悯地说,“我们不要再互相责备,从此互相爱怜,/把所负担的悲愁减轻”(PLX.960−961)。基督教认为,夫妻是世界上最温馨和最亲密的关系,夫妻间的相互理解、帮助和呵护往往代表了更好更高的精神英雄生活。基督教还认为,在堕落世界里,生活本身已充满诱惑、悲惨和罪孽,夫妻间的相互指责只会更加剧生活的痛苦。亚当最后建议,俩人共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企求相互间和上帝的宽恕,表示“真正的悔改之心,/谦卑的歉意”(PLX.1090−1091)。
赖特指出,如果说是夏娃背叛了他们的爱,那么也是夏娃修复和拯救了他们的爱,[11]将亚当从“宿命论”[12]中挽救出来。也就是说,虽然亚当已开始忏悔,但夏娃的爱才是亚当精神再生的关键,因为它消除了亚当心中的仇恨,使亚当的心重新充满爱。此外,如达比希尔(Helen Darbishire)所评论,夏娃的爱不仅和解了自己与亚当间的关系,也续接了他们与上帝间的纽带。[13]两人在忏悔的同时一同祈求上帝的宽恕,由此而重新坚定信仰。史诗第十卷结尾的段落只有8个诗行,但有6个表示“悔罪”之意的同义词。这反复强调了亚当夏娃忏悔赎罪的决心,而这种决心将亚当夏娃与撒旦相区别,是堕落之人再生为精神英雄的第一步和关键一步。撒旦堕落后仍死不悔改,被贬地狱后变本加厉,纠集反叛溃军通过诱惑人类堕落而对上帝展开复仇,由此而沦入万复不劫、永无再生的绝境。相反,亚当夏娃堕落后彻底放弃自我中心,如基督教所倡导的完全将自己打开,让史诗前十卷中的宣讲教诲进入内心,将外在力量予以内化,在忍耐中积累和增长“内在精神”,最终获得精神再生。弥尔顿认为,只有亚当夏娃这样的形象才具有成长为堕落世界里真正精神英雄的潜在品质,包括坦诚认罪、虔诚忏悔、谦卑和顺从。换言之,“谦卑、顺从和忍耐”[14]正是亚当夏娃的英雄主义体现。用萨特的术语来表述,基督式英雄实为存在之精神英雄,而非战争等行动之英雄。和平时代需要的正是基督式精神英雄,而非战争英雄。
亚当夏娃的虔诚忏悔和谦卑感动了代表爱的“圣子”,也平息了代表正义的愤怒中的上帝。“圣子”主动请缨作为“中保兼救赎者为他(亚当)解释”(PLXI.34),并恳求上帝让亚当“和我/合而为一,好象我和父合而为一”(PLXI.44)。史诗及时地陈述了最后两卷的目的,即,让堕落后的亚当夏娃“悲惨而平静地”(PLXI.117)离开乐园,既要让亚当夏娃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罪孽的深重和毁灭性的影响,也要向亚当夏娃揭示上帝为拯救人类而奉献“圣子”的旨意,由此让将被赶出乐园而被贬至人间的亚当夏娃满怀希望和坚定信仰,学会坚强和忍耐,用“内在精神”装备自己,勇敢地去面对乐园失去后“孤寂”的未来,为再生为“英雄”做好准备。
三
但在弥尔顿看来,堕落的亚当夏娃要成为史诗英雄,仅有忏悔远远不够,他们还必须有“英雄知识”(heroic knowledge)的装备。弥尔顿将“英雄知识”视为英雄品质的关键,弥尔顿称之为“正确的知识”(the right knowledge),以区别于撒旦“错误的知识”观。《复乐园》里的撒旦视知识为愉悦的来源和通向财富、权位及名声之路,耶稣蔑视地对撒旦说:“这些知识都是错误的”(PRIV.291)。弥尔顿认为,一个人只有在具备“正确的知识”后才能确保其人格,才能善用知识,其中尤其包括对自我的认知(self-knowledge)和对上帝(真理)的敬畏,苏格拉底视这种知识为“英雄对人与上帝间正确关系的根本性了解”。[23]史诗《失乐园》的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便为亚当夏娃成长为英雄装备必要的这些知识。
为获取“英雄知识”,亚当夏娃“谦卑地站着忏悔,/祈祷”(PLXI.1−2)。弥尔顿在史诗第十一卷的开头重申他在《教义》第二卷第三章中所陈述的宗教主张,即,堕落之人的再生包括四个阶段:首先是认罪,即忏悔,接着是承认自己缺乏神的正确的引导,即在上帝面前的谦卑,然后是不断真诚地祈祷,最后获得上帝赐予的恩典,以消除心中顽石般的自私和自傲。这样,忏悔的罪人从精神上复苏,将心打开去接受“英雄知识”(WJMVII, 51−73)。
史诗描述,刚做完忏悔和祈祷的亚当夏娃“只觉得身上增加了/从天上而来的力量,从失望中/迸出一股新的希望和喜悦”(PLXI.137−139)。根据基督教,“忏悔和祈祷”是堕落世界的人应该坚持的日常修为,因为只有从虔诚的祈祷中,人才能获得所需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俗世无法给予,唯有上帝赋予他帮助和救赎的希望,让他去面对人生的危险和困难。弥尔顿通过亚当之口说,“祈祷能使信念从我心中滋长。/和平回到我的胸中”(PLXI.152−153)。“祈祷”因此在基督教中被视为堕落之人再生的前提。
垂听到亚当夏娃的“忏悔和祈祷”,上帝的愤怒得以平息,指派天使米迦勒为迷茫中的亚当夏娃送来“英雄知识”,提供他们急需的指点和引导。米迦勒首先向他们确认,“善和爱”(PLXI.351)会跟随、围绕和保护他们,但他们“离开(伊甸园)之前需端正信心,/坚定信仰”(PLXI.356−367)。亚当从米迦勒那里接受自己到堕落世界里去生活所需的知识,坚信救赎者的顺从将洗涤他的罪,也意识到,他必须用行动表达自己的信仰。米迦勒的一段教诲极富哲理思辩,也为弥尔顿的后两部诗作《复乐园》和《斗士参孙》埋下伏笔:
善恶要兼听;超凡的恩惠
和人的罪恶永相斗争;但由此
学到真正的忍耐,调节欢乐和恐怖、
虔诚与悲哀;习惯荣枯、兴衰
不同的境遇。这样,可以安然
度过你的一生,做最好的准备,
迎接死的来临。 (PL: XI.360−366)
为了让亚当充分了解堕落之人要承担的责任,以便亚当能勇敢地“迎向灾难”(PLXI.378),米迦勒在夏娃熟睡后引领亚当走过幽谷曲径,来到山顶“视界”(377)。⑥在视界里,亚当看到诱惑者撒旦将第二亚当耶稣引诱到荒野,⑦目睹后人的罪孽,如“不义的杀了有义的”(456),看到人类未来生活的悲惨、凄凉、污秽、丑恶、可怕,感受到人类的挣扎和痛苦……艾略特将这一长串的名录视为游戏,而不是诗歌。但普林斯坚信,这一序曲为后面一连串的意义深远的异象拉开序幕,因为随后展现在亚当眼前的极尽历史的悲沧,[24]其中每一个事件都与亚当夏娃说犯的“人类原罪”相关,特别是以下两大罪孽。其一是战争和杀戮,如“该隐杀兄”和军队的建立。这不仅暗示亚当犯罪基因的延续性,同时也影射人类历史上父子兄弟相残的事实,如同混乱而战事不断的十七世纪英国一样。其二是美色诱惑,因为正是在美色的诱惑下,一代代的人性堕入享乐至上和自我毁灭的循环,克罗斯曼的论调——“历史是人类堕落的循环,是人面临诱惑无法抵御或抵御毫无意义、因而总是被诱惑所打败的一个循环”[25]——一次次被证实。而亚当夏娃,作为历史循环里的首位罪犯,反复经历了“被诱惑、滥用特权、受惩罚”的堕落三步曲。通过第十一卷里的“视界”和米迦勒的解释,亚当不断认识到自己罪孽的深重,一次次失声“痛哭”(762)。
史诗从第十二卷一开始随着“毁了的世界和恢复了的世界”便笔锋逆转,由“视界”(vision)转为叙述(narration),亚当也从伤悲转向对未来的希望。米迦勒对亚当说:
这样,你看到了一个世界的
开始和终结,又从第二个始祖⑧
繁殖……
你必须好好听,并加以注意。 (PL: XII.6−13)
米迦勒向亚当强调,面对一个由“罪孽”和“死亡”主宰的堕落世界,他和后人该如何选择。堕落的世界里已不再“唯有永恒”,也不再只有美好,善与恶并存其中,且更多的是邪恶。人在复杂的诱惑面前,身处历史的十字路口,选择变得尤为艰难,但正是这样的艰难才能缔造出区别于“伪英雄”的真正英雄。米迦勒在叙述中将生动的历史例证与枯燥的清条戒律相结合,并通过两种英雄的对立,将“英雄知识”逐一传述于亚当。
米迦勒的第一课是“节制”(temperance),其反义词“无节制”实质上正是希腊式战争英雄的特点。米迦勒指点亚当,要成为真正的英雄,必须遵守“节制”的原则,这样,人生才能自然地尽其天年,瓜熟蒂落。米迦勒的第二课是“忍耐”。既然人生乃自然之过程,那么,人能掌握的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生活的质量,米迦勒因此总结道,“不要过分爱你的生命也别恨它”(PLXI.552),要忍受人生的种种际遇,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心境永远平和。“忍耐”是弥尔顿式精神英雄的又一品质。
米迦勒对信仰的强调尤其让亚当意识到“因信称义”的真正内涵,尤其在米迦勒的指点下领悟到,“顺从是最好的……/对有信仰的人,死是永生之门”(《马太福音》7:14),而不顺从将死亡引入世界、从此失去乐园而顺从通过实施在信仰和行动中的恩典复得乐园。在史诗前十一卷中总共重复19次的“信仰”也成为第十二卷(总计 649个诗行)中重复频率最高的词,达19次。⑨“信仰”帮助亚当完成了堕落之人再生为基督式英雄所需要的“内在精神”之建构,米迦勒为亚当这样总结:
你学会了这个,就说明你到了
智慧的顶点……
加上实践,配合你的知识,加上
品德、忍耐、节制
还有爱,就是一切的灵魂
这样,你就不会不高兴离开
这个乐园,因为在你的内心
另有一个远为快乐的乐园。(PL XII.578−588)
弥尔顿在《教义》里写道,人生就是在诱惑面前、困惑之时对“信仰”和“顺从”的试探(WJMXVI.357)。此时的米迦勒就如同撰写《教义》的神学家弥尔顿一样将“信仰”视为“英雄知识”的最核心,将“信仰”及基于“信仰”的“自律”和“顺从”,加以“忍耐、品德、知识、节制、爱”总称为“刻在心里的‘内在精神’”(PLXII.521)。史诗叙述者再次强调,堕落亚当再生为基督式英雄的前提是“正确的知识”或“英雄的知识”,以敬畏上帝为开端。米迦勒的知识平静了亚当的思绪,亚当相信自己“将从此出发,饱求知识,满载/而归”(PLXII.560)。随着亚当“内在精神”建构的完成,“一个远为快乐的乐园”自然随之而来。
在米迦勒向亚当传输“英雄知识”的同时,夏娃进入睡眠。虽然夏娃和亚当间的认知似乎因此出现巨大的鸿沟,但睡梦中的夏娃得到相同知识的充实,内心变得强大,用毫无愁苦的语言对归来的亚当说,“领我走吧,我决不迟疑。/和你同行,等于留在乐园。/没有你,留也等于被放逐”(PLXII.615−617)。这说明,弥尔顿在史诗的结尾处将“心智稍欠的”夏娃提升到与亚当相同的知识高度,夏娃本人也表示,“上帝在睡中/用梦境教导我”(PLXII.613)。可见,诗行本身已将夏娃归类为弥尔顿在《教义》里所诠释的基督式英雄,因为夏娃通过自我认知,能够独立自行地与上帝达成个人的交流。夏娃曾经因自恋、自傲、自我而堕落,现在因自主和自信而领悟到堕落之人再生的真谛,也认识到,她的未来与亚当不可分离。弥尔顿早期分别在《沉思的人》和《快乐的人》里所刻画的个人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将在再生之夏娃身上达到统一。
四
史诗《失乐园》的意义不只是在于塑造了从堕落走向再生的个体英雄形象,更重要的是从婚姻角度树立了从堕落走向再生的英雄伴侣形象。在《失乐园》的所有意象中,“手牵手”是其中最简单却最美丽和最有深刻意义的意象,它象征着婚姻的纽带。亚当夏娃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对婚姻伴侣,他们的婚姻结合、变故和最后的复合都是通过“手”来体现。当亚当夏娃首次进入史诗读者的视野之时,俩人在伊甸园里“手牵手地走,/自从他们相遇拥抱做爱后,便成为最可爱的一对”(PLIV.320-321);当夜回到庐舍休息时,俩人依然“交谈着,手牵手”(PLIV.689)。在史诗的结尾处,当亚当夏娃最后从读者的视野里消失、踏上前方未知的流放之旅时,俩人“手携手,慢移流浪的脚步,/告别伊甸园,踏上他们孤寂的途路”(PLXII.649-650)。然而,在这两个场景之间的堕落场景里,即史诗第九卷的“分开情节”中,象征性的一幕依然是“手”,但这次不是“牵手”,而是“松手”。当时,夏娃执意要独自一人前去整理乐园,由此给诱惑者撒旦留下可乘之机。史诗描述夏娃“把手从丈夫手中轻柔地抽回”(PL: IX.385),英文原文为“…… from her husband’s hand her hand / Soft she withdrew……”,“她的手”和“丈夫的手”本并列一起,但下一诗行的闯入将两人的手分开,两者的和谐被打破。根据英语语法,语句的顺序应为“Soft she withdrew her hand from her husband’s hand”。亚当夏娃婚姻中这三个历史性的时刻代表着人类婚姻的三个典型阶段:牵手、分手、携手。
当亚当夏娃二人第一次出现在史诗的读者面前时,史诗叙述者如此形容他们的形象:“他被造成机智而勇敢,/她柔和、妩媚、有魅力;/他为神而造,她为他里面的神而造”(PL: IV.297−299)。关于夏娃的被造,《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创造夏娃完全是因为上帝认为“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4:15)。但弥尔顿改写了圣经传统,让亚当主动向上帝提出为他创造另一半的要求,并对另一半的标准也提出要求。有学者指出,弥尔顿本人婚姻的失败使他对另一半的要求过于苛刻。[26]对于史诗里的亚当,尽管上帝为他创造的伊甸园已完美富足,但亚当认为缺少和他分享苦乐的人,于是对上帝感叹道,“一个人孤单,有什么快乐!谁能独乐?”(PLVIII.365)可见,亚当急需另一半的首要原因是排遣孤独。第二便是平等交流。亚当对上帝说,“不平等之间能有什么交际,/和谐和真正的快乐呢?……我所说的和所寻求的伴侣,/是能相互分享一切出于理性的愉悦”(PLVIII.383−391)。亚当的言论经常被解读为弥尔顿本人对理想婚姻的诉求。第三,由于夏娃外貌美丽,亚当一见钟情,坠入爱河不能自拔。此外,“婚姻床笫”(PLVIII.598)、“优美的行为”“千万种风情”“甜蜜的依从”使亚当感觉他们俩人“真心结合,二人同心”(PLVIII.604)。最后上帝如亚当所愿,为亚当创造了夏娃,对亚当说,“是你(亚当)所喜欢的,形状/象你,你合适的助手,你的另一半,/中你的意”(PLVIII.448−450)。
就夏娃而言,她在《圣经》中完全是没有形象和话语权的“他者”。弥尔顿首先遵照当时广为人接受的基督教思想,将《失乐园》里的夏娃塑造为顺从和依赖的形象。史诗里的夏娃对亚当说:“我是你的肉中肉,我为你而造,从你而造……你是我的引导,我的头”(PLIV.441−443)。但同时,诗行里的比喻通过暗指潘多拉、海伦等神话传说中有毁灭性的女人而反复强调夏娃那“睡时醒时同样有特殊魅力的美丽”(PLV.14)。在亚当见到夏娃时的描述中,有关夏娃的“美色”及美色带给亚当的变化和欲望等词汇重复11次(PL VIII.526;527;530;530;531;533;534;534;539;545;546)。此外,弥尔顿还暗示了夏娃复杂而任性的性格,尤其是夏娃潜在的叛逆性格最终使她成为撒旦诱惑人类堕落的突破口。夏娃作为婚姻毁灭者(destroyer of marriage bond)的作用可见一斑。
但最后婚姻的维护者 (preserver of marriage bond)是夏娃,其作用在史诗的最后两卷中尤其得到强化。天使米迦勒的告诫对于所有如夏娃一样堕落的女人无疑起着警示和教育意义:
不要悲伤,夏娃,对于你
该失去的东西,要忍心舍弃;
不要为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
过分留念;你这一去并不孤单,
和你同去的还有你的丈夫,
你当跟从他。他在哪里,
你就当做你的故乡。(PLXI.286−292)
亚当夏娃作为史诗的主人公和英雄,他们的婚姻纽带(创造时形成、堕落时破裂、史诗结尾时复合)象征着人类婚姻的状况。史诗展示,亚当夏娃经历天真、堕落、忏悔,直到最后真正理解并连接彼此以及自己和上帝。亚当从米迦勒的叙述中通过看和听,尤其通过自己的错误判断,而不断学习。如,当他误以为“一群美女从帏帐里出来”(PLXI.582)是“自然的倾向”(PLXI.597)时,米迦勒却告诉他说,“你所看见的帏帐,如此快乐/乃是罪恶的帏帐”(PLXI.607−608)。对于亚当,米迦勒的叙述是他学习的机会,认识自己的过程,重拾堕落失去的理智和信仰的过程,以及了解更高更复杂知识的过程,如对夏娃的爱和对上帝的信仰。夏娃在创造时因“自恋”和虚荣而爱上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又因为急于证实自己而与亚当分离前去独处,这才给诱惑者撒旦以可乘之机而沦入堕落。但当夏娃最后对亚当说“你是我的一切”(PLXII.618)时,她再也不会视自己为“完美无缺的夏娃”(PLIV.634),也不会因个人的虚荣而让理智受蒙蔽。通过堕落,夏娃意识到,世界并不是为她一人的眼球而创造,她也不可能是撒旦口中的“人间女神”(PLIX.732),而只不过是一个名叫“夏娃”的女人。夏娃为失去乐园而痛苦,但同时相信,内心的乐园远为快乐,因为那里有爱、有信仰。
亚当夏娃不再是堕落前伊甸园里“幸福的一对”,天真地说,“与你交谈我总是忘记时间”(PLIV.641),也不再如堕落时“貌合神离的一对”,虚伪地甜言蜜语道,“我离开你便思念你,觉得好久/没有见你的面”(PL: IX.856−857),而已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爱人伴侣,他们坚信,有神意的引导,有内心“远为快乐的乐园”,他俩“手携手”,勇敢地迎向孤寂艰难的未来,直到死亡。这是基督教视野里理想的婚姻伴侣。
亚当夏娃“包含整个人类”,其经历具有极其普遍的意义。换言之,《失乐园》里的原型内涵不只局限于亚当夏娃,每个人都如他们一样,良知就是他的乐园;禁果即是对浮云般世间荣华的强烈欲望;而撒旦即是永远要将人们诱惑出乐园、阻碍人们做出明智选择的那条毒蛇。而史诗叙述的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俗的世界,身处其中的人物就是我们读者本人。亚当夏娃的天真状态,如同读者的懵懂岁月一样,是人性发展中的必经阶段。但只有经过这种阶段,人才能成熟,才有可能实现人性的理想。史诗《失乐园》为堕落世界里那些已经堕落或可能会堕落的人们树立了“英雄精神追寻”的范式。读者,如同堕落的亚当一样,面对诱惑和罪孽痛苦而迷茫,急需米迦勒式的指点,也如同亚当夏娃一样,虽然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抛弃了上帝的围墙禁锢他的外在乐园,但也通过坚定信仰和坚持忍耐而找到自己内心“远为快乐的乐园”。
注释:
① 本文所引弥尔顿诗文皆出自18卷本《弥尔顿集》(The Works of John Milton.New York: Columbia UP, 1931−1938).因卷轶浩繁,援引复杂,故文内《弥尔顿集》缩写为WJM,其后数字为卷数加行码;PL指《失乐园》,PR指《复乐园》,其后数字为行码。所引诗文参考了朱维之和金发燊的译本,略有改动。但由于《教义》还没有中文译本, 选文的中文翻译均为笔者的拙作。为免繁琐而影响阅读,以下只视需要出注。
② 笔者不认同克伦普的分析。他将史诗分为三个部分,且每个部分有各自不同的中心人物,如第一部分包括史诗第一卷至第四卷,撒旦为史诗的中心人物;第二部分从第五卷至第八卷,“圣子”为其中心人物;第三部分从第九卷至第十卷,亚当为其中心人物。参见Galbraith Miller Crump,The Mystical Design of Paradise Lost(London: Associated UP, 1975)96。
③ 若无特别说明,下文中的“亚当”实为“亚当夏娃”之整体,代表整个人类,相等于中世纪道德剧中的“人人”。
④ 此后,亚当在史诗里直接称呼夏娃为“夏娃”(PLX.1013;XI.141; XI.226)。称呼的变化说明,他们的关系从此真正亲密起来。
⑤ Samuel Johnson,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 A Selection(London:Oxford UP, 1986)85; David N.Dickey,A Study of the Place of Women in the Poetry and Prose Works of John Milton(Lewiston: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0)5−26; Diane Kelsey McColley,Milton’s Eve(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1;Louise Flavin, “The Similar Dramatic Function of Prophetic Dreams: Eve’s Dream Compared to Chauntecleer’s,”M Q4(1983): 132−38; Hermine J.van Nuis, “Animate Eve Confronting Her Animus,”MQ2 (2000): 48−56.
⑥ “视界”(vision)往往预示未来之事。《圣经》里多处用“视界”预示未来,如《但以理书》记载,“现在我来让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未来的日子”(10:14)。在《失乐园》的最后两卷里,米迦勒用“视界”预示亚当及其子孙的事。
⑦ 这将是史诗《复乐园》的场景。
⑧ 基督教视耶稣为第二亚当,即人类第二始祖。在史诗《复乐园》里,主人公耶稣通过坚守信仰而复得第一亚当失去的乐园。虽然埃尔伍得吹嘘说,他在归还弥尔顿《失乐园》的初稿时建议弥尔顿续写《复乐园》为续篇,但弥尔顿已经在这里为续篇埋下了伏笔。
⑨ 分别参见《失乐园》2.36; 2.690; 3.104; 4.520; 4.954; 6.115; 6.143;8.325; 9.286; 9.298; 9.320; 9.335; 9.411; 9.1075; 9.1141; 10.129;11.64; 11.485; 11.807; 12.127; 12.128; 12.154; 12.295; 12.306;12.409; 12.418; 12.427; 12.442; 12.449; 12.488; 12.527; 12.529;12.531; 12.536; 12.571; 12.582; 12.599; 12.603;
[1]Isabel Gamble MacCaffrey.Paradise lost as “myth” [M].Cambridge: Harvard UP, 1967: 41.
[2]Joseph Addison.Spectator [J].Los Angles, CA.: The Division,1987: 369.
[3]Thomas Newton ed., Milton’s poetical works [C].Edinburgh:Donaldson, 1772: II.455.
[4]Boyd M.Berry.Process of speech: puritan religious writing and paradise lost [M].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 UP, 1976: 262.
[5]J B B roadbent.Some graver subjects: an essay on ‘paradise lost’[M].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0: 279.
[6]Balanchandra Rajan.Paradise lost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ader [M].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6: 84.
[7]Lewis C S.A preface to paradise lost [M].New York: Oxford UP,1961: 129.
[8]Prince F T.The italian element in milton’s verse [M].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4: 131.
[9]Wright B A.Milton’s ‘paradise lost’ [M].London: Methuen &CO LTD, 1962: 190.
[10]James Thorpe ed.Milton criticism [C].London: Routlege &Kegan Paul Ltd., 1965: 366.
[11]Wright B A.Milton’s paradise lost [M].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2: 184.
[12]John S.Tanner.Anxiety in eden [M].Oxford: Oxford UP, 1992:119.
[13]Helen Darbishire.Milton’s paradise lost [M].London: Oxford UP, 1951: 65.
[14]Thomas Greene.The descent from heaven: a study in epic continuity [M].New Haven: Yale UP, 1963: 403.
[15]Stanley Eugene Fish.Surprised by sin: the reader in paradise lost[M].London: Macmillan, 1967: 206.
[16]Dennis Saurat.Milton: man and thinker [M].Hamden: Archon Books, 1964: 220.
[17]David Masson.The life of john milton [M].7 vols.New York:Peter Smith, 1946: VI.
[18]E M W Tillyard.Studies in milton [M].London: Chatto &Windus, 1951: 51.
[19]Bowra C W.From virgil to Milton [M].London: Macmillan,1967: 200.
[20]William J.Grace.Ideas in milton [M].Notre Dame: Uni.Of Notre Dame Press, 1968: 72.
[21]Davis P.Harding.The club of hercules: studies in the classical background of paradise lost [M].Urbana: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2: 51.
[22]Woodhouse A S P..“Patterns in paradise lost,” UTQ, XXII(1952-53): 115.
[23]Manavalan A A.Epic heroism in milton and kamban [M].Coimbatore: Kamban Trust, 1984: 154.
[24]Richard Bradford.Paradisel lost [M].Buckingham: Open UP,1992: 38.
[25]Crosman, Robert.Reading paradise lost [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239.
[26]Hamilton K G.Paradise lost: a humanist approach [M].London: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21: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