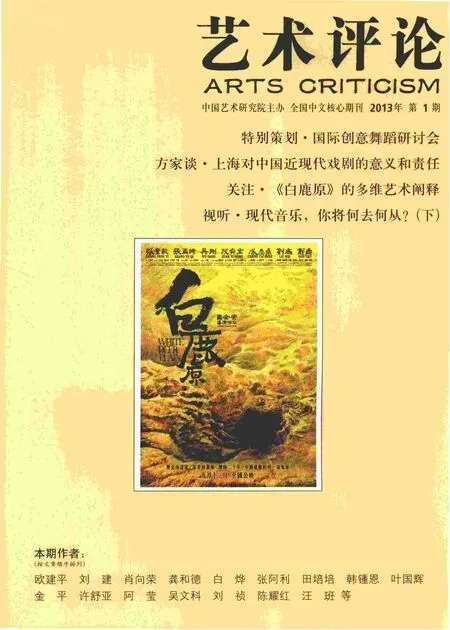当之无愧的“民族秘史”——陈忠实与《白鹿原》漫说
白 烨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白鹿原》是真正的厚积薄发之作,因其“厚积”,所以“厚重”。
陈忠实从1965年发表短篇处女作到1992年发表长篇小说《白鹿原》,期间整整相隔了二十七年。不能说这二十七年他都在有意为长篇小说创作做准备,但二十七年间他在社会生活中的磨炼和在文学创作上的探求,无疑都给他的长篇创作在内蕴上和艺术上不断地打着铺垫。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何以如此姗姗来迟,而这个晚生的产儿又为何一呱呱坠地便那么不同凡响。
作者在《白鹿原》开首所引述的巴尔扎克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给人们理解作品留下了一把钥匙。它以白鹿原的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为主线,既透视了凝结在关中农人身上的民族的生存追求和文学精神,又勾勒了演进于白鹿原的人们生活形态和心态的近代、现代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其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回响。在一部作品中复式地寄寓了家族和民族的诸多历史内蕴,颇具丰而厚重的史诗品位,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当属少有。
然而,这一切都有一个孕育与产生的过程,了解这个过程,无疑有助于人们读解《白鹿原》,深谙《白鹿原》。
一、蓄势
我们当代作家的出身,大致上可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从学校里走出来,一类是从生活里滚出来。陈忠实之为作家,显然属于后者。
陈忠实1962年中学毕业后,由民办教师做到乡干部、区干部,到1982年转为专业作家,在社会的最底层差不多生活了二十年。他从1965年到70年代的创作初期,可以说是满肚子的生活感受郁积累存,文学创作便成为最有效、最畅快的抒发手段和倾泄渠道。他那个时期的小说如《接班以后》等,追求的都是用文学的技艺和载体,更好地传达生活事象本身,因而,作品总是充溢着活跃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泥土芳香,很富于打动人和感染人的气韵和魅力。
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关注陈忠实的。1982年,《文学评论丛刊》要组约当代作家评论专号的稿子,主持其事的陈骏涛要我选一个作家,我不由分说地选择了陈忠实。因为我差不多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心里感到有话要说也有话可说。为此,与陈忠实几次通信,交往渐多渐深。嗣后,或他来京办事,或我出差西安,都要找到一起畅叙一番,从生活到创作无所不谈。他那出于生活的质朴的言谈和高于生活的敏锐的感受,常常让人觉得既亲切,又新鲜。
陈忠实始终是运用文学创作来研探社会生活的,因而,他既关注创作本身的发展变化,注意吸收中外有益的文学素养,更关注时代的生活与情绪的替嬗演变,努力捕捉深蕴其中的内在韵律。这种双重的追求,使他创作上的每一个进步,都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了较好的和谐与统一。比如,1984年他尝试用人物性格结构作品,写出了中篇小说《梆子老太》,而这篇作品同时在他的创作上实现了深层次的探测民族心理结构的追求。而由此,他进而把人物命运作为作品结构的主线,在1986年又写出了中篇力作《蓝袍先生》,揭示了因病态的社会生活对正常人心性的肆意扭曲,使得社会生活恢复了常态之后,人的心性仍难以走出萎琐的病态。读了这篇作品,我被主人公徐慎行活了六十年只幸福了二十天的巨大人生反差所震撼,曾撰写了《人性的压抑与人性的解放》一文予以评论。我认为,这篇作品在陈忠实的小说创作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在艺术的洞察力和文化的批判力上,作家都在向更加深化和强化的层次过渡。1987年间,我因去西安出差,忠实从郊区的家里赶到我下榻的旅馆,我们几乎长聊了一个通宵。那一个晚上,都是他在说,说他正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我很为他抑制不住的创作热情所感染、所激奋,但却对作品能达到怎样的水准心存疑惑,因为这毕竟是他的第一部长篇。
1991年,陈忠实要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一本中篇小说集,要我为他作序。我在题为《新层次上的新收获》的序文里,论及了《地窖》等新作的新进取,提及了《蓝袍先生》的转折性意义,并对忠实正在写作中的《白鹿原》表达了热切的期望。忠实给我回信说:
依您对《蓝袍先生》以及《地窖》的评说,我有一种预感,我正在吭哧的长篇可能会使您有话说的,因为在我看来,正在吭哧的长篇对生活的揭示、对人的关注以及对生活历史的体察,远非《蓝袍》等作品所能比拟;可以说是我对历史、现实、人的一个总的理解。自以为比《蓝袍》要深刻,也要冷峻一步……
二、出炉
1992年初,陈忠实完成《白鹿原》后,先交由几位亲近的文友帮忙把关。陕西的评论家李星是其中之一,他看了《白鹿原》的完成稿,告诉我《白鹿原》绝对不同凡响。后来参与编发《白鹿原》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贤均又说,《白鹿原》真是难得的杰作。这些说法,既使人兴奋,又使人迷惑,难道陈忠实真的会一鸣惊人么?
《白鹿原》交稿之后,出书很快确定了下来,但在《当代》杂志怎样连载,连载前要不要修改等,一时定不下来,忠实托我便中了解一下情况。经了解,知道是在《当代》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连载,主要是酌删有关性描写的文字。在我给忠实去信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给陈忠实电告了如上的安排,忠实来信说:
我与您同感,这样做已经很够朋友了。因为主要是删节,可以决定我不去北京,由他们捉刀下手,肯定比我更利索些。出书也有定着,高贤均已着责编开始发稿前的技术处理工作,计划到八月中旬发稿,明年三四月出书,一本不分上下,这样大约就有600多页……
原以为我还得再修饰一次,一直有这个精神准备,不料已不需要了,反倒觉得自己太轻松了。我想在家重顺一遍,防止可能的重要疏漏,然后信告他们。我免了旅途之苦,两全其美。情况大致如此。
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一室的主任高贤均给我讲了他与《当代》的洪清波去西安向陈忠实组稿的经过,那委实也是一个有意味的故事。1992年3月底,他们到西安后听说陈忠实刚完成了一部长篇,便登门组稿,陈忠实不无忐忑的把《白鹿原》的全稿交给了他们,同时给每人送了一本他的中短篇小说集。他们在离开西安去往成都的火车上翻阅了陈忠实的集子,也许是两位高手编辑期待过高的原因,他们感到陈忠实已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在看取生活和表现手法上,都还比较一般,缺少那种豁人耳目的特色,因此,对刚刚拿到手的《白鹿原》在心里颇犯嘀咕。到了成都之后,有了一些空闲,说索性看看《白鹿原》吧,结果一开读便割舍不下,两人把出差要办的事一再紧缩,轮换着在住处研读起了《白鹿原》。回到北京之后,高贤均立即给陈忠实去信,激情难抑地谈了自己的观感:
我们在成都呆了十来天,昨天晚上刚回到北京。在成都开始拜读大作,只是由于活动太多,直到昨天在火车上才读完。感觉非常好,这是我几年来读过的最好的一部长篇。犹如《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样,它完全是从生活出发,但比《桑乾河》更丰富,更博大,更生动,其总体思想艺术价值不弱于《古船》,某些方面甚至比《古船》更高。《白鹿原》将给那些相信只要有思想和想象力便能创作的作家们上了一堂很好的写作课,衷心祝贺您成功!
1993年初,终于在《当代》一、二期上一睹《白鹿原》的庐山真面目。说实话,尽管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心理铺垫,我还是被《白鹿原》的博大精深所震惊。一是它以家族为切入点对民族近代以来的演进历程作了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多重透视,史志意蕴之丰湛、之厚重令人惊异;二是它在历史性的事件结构中以人物的性格化与叙述的故事化形成雅俗并具的艺术个性,史诗风格之浓郁、之独到令人惊异。我感到,《白鹿原》不仅把陈忠实的个人创作提到了一个面目全新的艺术高度,而且把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本身推进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基于这样的感受,我撰写了《史志意蕴、史诗风格——评陈忠实的〈白鹿原〉》的论文(见《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盛夏七月,陕西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在文采阁举行了《白鹿原》讨论会。与会的六十多位老、中、青评论家。竞相发言,盛赞《白鹿原》,其情其景都十分感人。原定开半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下午五点仍散不了场。大家显然不仅为陈忠实获取如此重大的收获而高兴,也为文坛涌现出无愧于时代的重要作品而高兴。也是在那个会上,有人提出,“史诗”的提法已接近于泛滥,评《白鹿原》不必再用。我不同意这一说法,便比喻说,原来老说“狼”来了、“狼”来了,结果到跟前仔细一看,不过是只“狗”;这回“狼”真的来了,不说“狼”来了怎么行!
此后,关于《白鹿原》的评论逐渐多了起来,这些评论大都持肯定的态度,但也有一些评论着意于挑毛病。对出于文学角度的善意的批评,人们都不难接受,惟有那些并非出于文学也并非怀有善意的批评,颇令人疑惑和惊悸。比如,有人胡说什么《白鹿原》既如何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欣赏、所推崇,又如何以严肃文学的身份向商品文化“妥协”,向大众情趣“献媚”。另有一种怪论,则从另一角度作政治文章,说什么《白鹿原》有意模糊政治斗争应有的界限,美化了地主阶级,丑化了共产党人。真是左右开弓,怎么说都有理。但只要认真读过《白鹿原》并全面地理解作品,这些意见都是不值一驳的。对于这些看法,作为作者的陈忠实能说些什么呢?今年十月,他出访意大利两度路过北京,听到这些风言风语,他先是皱着眉头惊愕:“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看作品的?”继之坦然一笑,“还是让历史去说话吧!”
是的,历史比人更公正,评价一部好的作品,也有赖于公正的历史,因为,历史决不会亏待不负于历史的人们。
三、评说
在我看来,《白鹿原》在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结构框架中,始终以人物为叙述中心,事件讲究情节化,人物讲究性格化,叙述讲究故事化,而这一切都服从和服务于可读性。有关的历史感、文化味、哲理性,都含而不露地化合在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之中,比较好地打通了雅与俗的已有界限。一部作品内蕴厚重、深邃而又如此好读和耐读,这在当代长篇小说中亦不多见。这些突破,使得《白鹿原》把陈忠实的个人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艺术层次,也把当代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从而具有了某种标志性的意义。
其一,由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纠结勾连起来的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在作品中最具分量也最为显见,那实际上是作者由白鹿原的角度,对近现代以来的国史在社会层面上的一个浓墨重彩的勾勒。
白鹿原的斗争从清朝改民国、民国到解放的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一刻也没有消停过。先是督府的课税引起了“交农”事件,其后是奉系镇嵩军与国民革命军的你争我斗。当事态演化到国共双方的分裂与对抗之后,白鹿原就更成了谁都不能安生、谁也无法避绕的动荡的旋涡:农协在“戏楼”上镇压了财东恶绅,批斗了田福贤等乡约;乡约和民团们反攻回来,在“戏楼”上吊打农运分子,整死了倔强不屈的贺老大;尔后,加入了土匪的黑娃又带人抢劫了白鹿两家。及至“革命”进一步深入到家族和家庭,白家的孝文进入了保安团,白灵参加了共产党;鹿家的兆鹏成为红军的要员,黑娃则摇身成了保安团的红人。这些大开大阖、真枪实弹的阶级抗争,连同白嘉轩和鹿子霖那种勾心斗角的家族较量,使得白鹿原成为历史过客逞性耍强而又来去匆匆的舞台,而白鹿原的芸芸众生们被裹来挟去,似懂非懂地当了看客,不明不白地做了陪衬。在复式叙述这些上上下下和明明暗暗的复杂斗争时,作者一方面立足于历史的现实,写了纷乱斗争之中的是是非非、善善恶恶以及革命力量在艰难困苦中的进取和社会演进的客观趋向;另一方面又超越现实的历史,让更为冷静、更为宏观的眼光,审视发生在白鹿原的一切,大胆而真切地揭示了革命和非革命的、正义和非正义的斗争演化成为白鹿原式的“耍猴”闹剧后,给普通百姓的命运和心性带来的种种影响。
作品第十四章写到国共分裂,田福贤等人重新整治了对立一方后给白嘉轩还“戏楼”的钥匙时,白嘉轩用超然物外的口吻说:“我的戏楼真的成了‘鏊子’了。”田福贤后来又从朱先生口中听到同样的话,“白鹿原成了‘鏊子’。”洁身自好、与世无争的白嘉轩和朱先生,作为事态的旁观者确比别人看得更为清楚,“鏊子是烙锅盔烙葱花大饼烙馍的,这边烙焦了再把那边翻过来。”黑娃在“戏楼”上整了田福贤等人,田福贤等重新得势后一定要再在“戏楼”上回整黑娃的同党;你对我残酷斗争,我对你也无情打击,在这种翻过来又翻过去的互整中,白鹿原成了谁都没有放过的“鏊子”,白鹿原的乡民成了吃苦受累的不变对象。他们既是当时的历史所不能缺少的陪客,又是过后的历史随即忘却的陪客。这种付出了不该付出的、又得不到本该得到的的无谓结局,是比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的相互戕害的悲剧更为深沉、也更为普遍的悲剧。
“鏊子”说一出,把白鹿原的错综纷繁的斗争史,简洁而形象地概括了、提炼了。它既生动地描画了白鹿原式的斗争因“翻”而构成的烈度和频度,又深刻地喻示了这种“翻”来“翻”去的闹法给置身其中的乡民们造成的困苦。即就黑娃和田福贤在戏楼上你来我往的较量来说,就是谁也没占到上风的平手戏;而先后被整死的老和尚和贺老大,却切切实实地做了代人受过的替罪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鹿原成了鏊子”,实质上是正剧幌子掩盖下的闹剧,以闹剧形式演出的悲剧。
其二,白嘉轩作为一个居仁由义、心怀大志的族长,被社会的浪潮挤到舞台的一角,家业难兴,族事难理,与老对手鹿子霖的较量始终难分胜负。可以说,他的一生是时乖命蹇的一生。然而,他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种种行状和心态,却构成了秘史中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隐含在一个传统农人身上的独特的文化精神和民族心史。
作为一个敬恭桑梓、服田力穑的农人,白嘉轩身上有着民族的许多优良秉性和品质。他靠自力更生建立起了家业,又靠博施众济树立起人望;无论是治家还是治族,他都守正不阿,树德务滋。尤其是对文化人朱先生、冷先生的敬之、孝之,对老长工鹿三的重之、携之,更以对小生产意识的明显超越,表现了他在一代农人之中的卓尔不群。白嘉轩始终怀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热望:按照自立的意愿治好家业,按照治家的办法理好族事,使白鹿原的人们家家温饱,个个仁义,从而也使自己的声名随之不朽。但当这些想法在现实中刚刚开了一个头,他便遇到了种种意料不到的难题和挑战。起先是没有了皇帝,使他六神无主;接着是民国建立政权,鹿子霖以乡约的身份与他平分了秋色;随后便是各家的混战蜂起,家事和族事都乱了套,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每况愈下,只有儿子孝文在最后做稳了县长,他才稍稍有所慰藉。从未放弃过个人的私欲和名誉,却也不错过任何可以急公好义的机会,把自己的价值实现寓于家族和乡里事业发展,这是白嘉轩这个形象的独特所在。
作为独特的白鹿原的独特产儿,白嘉轩离不开白鹿原这个舞台,白鹿原也离不开白嘉轩这个主角。他首先立了乡规、乡约,确立了他的族长的地位又使乡民们有规可依;他修祠堂、建学堂,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也使孩子们上学读书有了保障;他与鹿子霖明争暗斗,守住了族长职位,也阻遏了恶人的势力膨胀。他处处救助受难者,使自己的人缘、人望大增,也使频繁的混战对人的伤害得到了不小的减缓。他的“仁义”为怀、自立为本的人格精神,最典型不过地表现了中国传统农人基于小农经济和田园诗生活的文化意识和人生追求。
不难看出,对于《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的塑造,作者既把他当作较为理想的农人典型,也把他当作一面可以澄影鉴形的“镜子”。用他,照出了鹿子霖的卑猥和丑恶;用他,照出了朱先生的睿智和清明;用他,还照出了乱世沧桑的悲凉与悲壮。一个世纪,如若使仁人君子都惶惶不安、悻悻不乐乃至倍受折磨和煎熬,那这个时世还不可叹可悲么?反过来看,也可以说作者也经由白嘉轩写出了传统的“仁义”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有用性和无用性,尤其是白嘉轩不无欣幸地把儿子孝文当了县长认为是白鹿“显灵”的结果,更是以一种悖论性的内容,暗示了白嘉轩仁义追求走向意愿反面的最终破灭。在这里,作者在白嘉轩人格精神的悲剧结局里,不仅映现了社会生活在急剧变动之时难分青红皂白的某种冷淡性、无情性,而且表达了他对传统的文化精神肯定与否定参半、赏赞与批判相间的历史主义态度,尽管那样更像是一曲略带忧伤色彩的挽歌。
其三,《白鹿原》里少有缠绵悱恻、催人泪下的情与爱,有的多是缺情乏爱的性发泄。白嘉轩先后娶了七房女人,同哪一个都没有太深的感情;白孝文娶妻之后,先耽于床第之事,后又移心别恋;只有黑娃和小娥的相恋带有真情,却又棒打鸳鸯散,各奔了东西。是作者没有兴致、没有才力去抒写人间情爱么?当然不是。我以为,这只能理解为关于白鹿原上的性事与性俗,作者别有自己的看法。尤其是通过白嘉轩的冷待女人和小娥的放纵沉沦,作者实际上向人们揭示了白鹿原人们游离了性爱主义的畸恋性史。
白嘉轩所娶的七房妻子中,有六个都没有给他留下什么,他也只有同她们初次交欢时的印象。他娶了第七个妻子仙草后,相处日渐融洽,其因在于她既连生三子,发挥了传宗接代的功用,又带来罂粟种子,起到了振兴家业的效能。然而,白嘉轩并没有想到他人财两旺的光景同仙草有什么切实的关系,他把自己的发家致富主要归结为“迁坟”后“白鹿逞灵”。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东西的女人在他心目中没有任何地位,给他带来“人”和“财”的女人,在他心目中仍然没有什么地位。女人作为人在白嘉轩的世界里被遗忘了,她们或者只是他泄欲时的对象,或者只是他干事时的帮手。男女之间应有的情性相悦,到白嘉轩这里一概被淡化、被消解了。正是出于这种传统的婚姻观,他对六个死去的妻子只有在初婚之夜如何征服她们的感受,而且常常“引以为豪壮”。他看不惯儿子和儿媳的过分缠绵,教唆儿子孝文使出“炕上的那一点豪恨”,不要“贪色”,他认为小娥是“不会居家过日子”还要“招祸”的“灾星”,拒阻黑娃和小娥到祠堂成亲。作为正统社会的一个正统男人,白嘉轩只把婚姻看成是传宗接代和建家立业的一个环节,可能纷扰最终目的的卿卿我我、情情爱爱之类的东西宁可少要或不要。这样不讲对等意义上的互爱和超越功利意义的情欢,把婚姻简单地等同于生孩子、过日子,正是长期以来民族婚俗中少有更变的传统观念。它是正宗的,却也是畸恋的。
而小娥有关婚爱的想法和做法,与白嘉轩恰成鲜明的对比。她不计名利、不守礼俗,只要是两心相知、两情相悦,她就交心付身,没遮没拦,而且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她一旦爱上黑娃,便死心塌地、一心一意,哪怕他位卑人微,也在所不惜,把一个重情女子的柔肠侠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小娥的情爱观里,显然不无贪情纵欲的成分,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她有力地超越了传统的功利主义婚恋藩篱,带有一种还原性爱的娱情悦性本色的意味。然而,这必然与以白嘉轩为代表的正统道德发生抵牾,从而为白鹿原的习俗所不容。因而,当她失去了黑娃的佑护之后,便像绵羊掉进了狼窝,在政治上、人格上、肉体上备受惩罚和蹂躏,从而也变成了白鹿原皮肉场上的一只“鏊子”。鹿子霖乘其之危占有了她,并以此作为对黑娃的某种报复;她又听从鹿子霖的调唆以美色诱引孝文走向堕落;白嘉轩打上门来找小娥被气晕在门外;鹿子霖“气出了仇报了”又来寻小娥“受活受活”。在这里,正言厉色的白嘉轩把她当成伤风败俗的“灾星”,不顾伦常的鹿子霖把她当成搞垮对头的“打手”,而对她似乎不无情意的白孝文,也实际上把她当成是除治阳痿、激性纵欲的“工具”。在她那里,也是你上来我下去,翻着另一种形式的“烧饼”,场面虽然如火如荼,却谁也没有付出真情实意和爱心,她一如白鹿原的“戏楼”,是男人们互相角力和私下放纵的“演练场”。他们既没有轻易放过她,也没有把她真正当成人。
小娥由追求真情真性的爱恋而走向人尽可夫的堕落,当然有她自己破罐子破摔的主观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白鹿原的男人所逼就的。她爱黑娃不能,洁身自好也不能。为人正直又守成的白嘉轩压制她,为人伪善又歹毒的鹿子霖威诱她。她在场面上要忍负正人君子的唾骂,在背地里又要承受偷香窃玉的人的蹂躏,还要兼及拉人下水、诱人起性,试问面对这一切,她作为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又能怎么办呢?她别无选择,只能按照白鹿原的道德与需要,在随波逐流中走向自戕又戕人的悲剧结局。这难道仅仅是小娥个人的命运悲剧么?
有意味的是,小娥死后闹起了鬼,白鹿原的人们又在白嘉轩的主持下建造了砖塔专以对付小娥的鬼魂,从而使小娥以物体的形式重又站立在白鹿原上,那说是镇妖塔,又何尝不是纪念碑。人们看到砖塔不能不想起小娥,而小娥则以她不屈的身影,述说着自己的坎坷与不幸,指控着白鹿原性文化的虚伪与戕人,从而把隐匿着她的遭际的个人的和民族的畸恋性史昭示给人们,引动人们去思索,反刍其中所包含的诸多意味。
《白鹿原》作为一部有积累、有准备的长篇杰作,不仅表现在内蕴一方面,而还表现在形式一方面。可以说,与它丰厚隽永的史志意蕴相得益彰,它在意识形式上气宇轩昂,具有鲜明的史诗风格。它以一个村镇、两个家庭为载体,把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作了缩微式的反映。在这一反映过程中,它又以显层次的运动、斗争勾勒和隐层次的人心与人性的揭示,立体交叉式地全部揭示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历史变动。作品既立足于历史,又超越了历史。读着这样的小说,我很想借用狄德罗赞扬理查生的话对作者说:“往往历史是一部坏的小说;而小说,像你写的那样,是一篇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