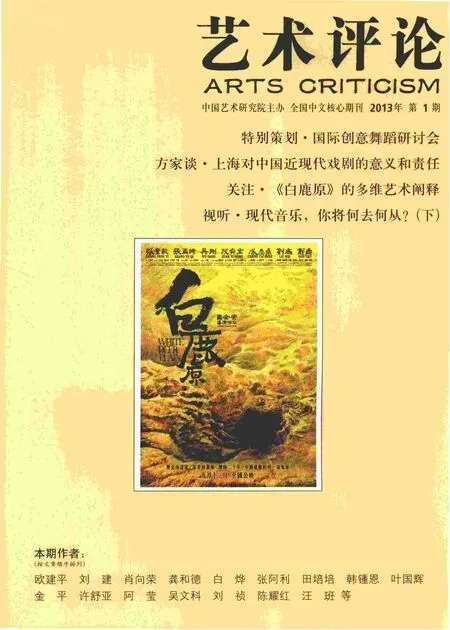探索民族化、个性化的戏剧表达 ——反思话剧《白鹿原》的创作得失
胡 薇
胡 薇: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

自上世纪90年代发表以来,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一直拥有着极高的关注度。由于原小说的情节线索纷繁、人物众多且关系复杂以及时间跨度较大等原因,很多人都认为:长篇小说是《白鹿原》最好的艺术承载形式,任何试图将之改编为其它艺术形式的工作都必将极为艰难。然而,20年来围绕《白鹿原》所展开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的改编,如秦腔、陶塑、连环画、话剧、舞剧、电影等,却一直都在前赴后继地进行着,对其改编的重视以及由此所经历的种种波折更是被坊间所津津乐道。其间,历经数年打磨,由孟冰改编、林兆华执导,集结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政话剧团、陕西华阴老腔和秦腔艺术团等众多艺术家们的话剧《白鹿原》一经呈现于舞台,就因其透过鲜活的地域特色、独特的艺术风格所突显出的颇具民族化、个性化的戏剧表达,成功赢得了极佳的现场演出效果。
不过,诸多对于改编的忧思并非完全是杞人忧天。陈忠实的这部小说虽然主要围绕发生在白鹿原上白、鹿两家之间的故事,描绘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村生活,但是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其在展现陕西关中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变迁的同时,对于个人、家族乃至民族的历史和命运的审视和反思。因而,将这部近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搬上话剧舞台的改编工程之所以艰难,就在于其已经不仅仅是艺术体裁、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转换,而是要将几十年的沧桑、两代人的沉浮所浓缩和投射出的一个民族的心灵苦难史,全部收纳和呈现在舞台这一方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之内,意味着改编者必须在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在两个半小时之内完成对原著内涵的一种“现在时”的重构。而在小说与戏剧二者的转换过程中,对于改编者最大的一个挑战和考验也来自小说对于这一素材所具有的先天优势:小说的文字属性,令之可以纵横捭阖、不拘于时空的限定,可以并置多条线索、运用多种叙事方式,随时可以“花开多朵”或是“各表一枝”而不显突兀,即使是在情节发展的同时穿插以描写、议论等也都属正常;戏剧则更多地强调集中和凝练,事件必须借助人物的行动直接展现出来,是一种需要借助独特的戏剧场面来展示和深化人物已有的个性的艺术创作。于是,在改编的过程中不仅要将小说的内容舞台化,将平面的、文字的描述变成立体的、空间的展示,而且人物的情感逻辑的表现也必须脉络清晰。因而,话剧的改编者不能只是简单直接地将原著小说的内容影像化、舞台化,而是需要根据舞台艺术的特点,重新梳理和结构原著的事件、人物以及相互关系,并配以适合的舞台表现手段,力求以精心调配和增减的戏剧场面,更好地展现出原作的精髓。

可以说,用三十多个戏剧场面来展现五十年的变迁,原本已非易事,何况还要在忠于原作精神的同时进行艺术上的再次创作与提升。戏剧,毕竟不是通过舞台来复述小说故事的说书场,改编改变的也不只是一种表现模式的转换,更是一种不同思维的表达,必须通过运用各种舞台手段,综合创造出立体的舞台形象以彰显剧作的文学性,并张弛有致地将剧作的思想情感传递给观众来引发思考。因此,如何在舞台上塑造出独特的《白鹿原》,也成为话剧版本的主创们殚精竭虑的终极目的。
舞台的呈现方式,也的确直接反映出了主创们的创作意图。在导演林兆华的率领下,为了营造那种扑面而来的古朴苍凉的史诗感,全剧不仅要在横亘绵延、几乎占据了整个舞台的“白鹿古原”上展开,要虚实相间地、划分不同的表演区来实现空间调度上的纵横穿叉以及时空的迅速转换,还需要濮存昕、宋丹丹、郭达等主演们都操起陕西方言营造氛围,并依恃贯穿始终的老腔、秦腔来凝聚出白鹿原人的灵性与魂魄,以便在舞台上浓缩却又是全景式地勾勒出这块日渐成为你争我夺的“鏊子”的古原上的人生百态。最终,话剧的主创们以其对于舞台节奏大气流畅的有效把控以及对多种舞台表现元素的娴熟运用,为演出带来了赞誉。但同时,关于话剧《白鹿原》的改编策略以及舞台处理方式,也引发了颇多质疑,可谓是毁誉参半。不过,当我们重新解析这部被称为拥有中国话剧最强编剧、最强导演和最强演员阵容的改编作品的时候,不妨先抛开定论、抛开对于艺术作品成败的评价,而是将之视作中国剧坛上一次探索民族化、个性化戏剧表达的有益实验,进而对话剧《白鹿原》在改编创作上的得失进行总结和反思,似乎更具现实意义。
总体而言,话剧《白鹿原》对于原小说所进行的删改、修整与舞台呈现,可谓是得失双刃、利弊共存。这也是林兆华等主创们在融入传统的、民族的审美诉求的过程中,在突出话剧内在民族性、打造话剧民族化的不懈努力中,创作意图与表达呈现的矛盾和犹疑所致,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不够彻底和自信所造成的。
毫无疑问,主创们对于《白鹿原》的改编是狠下了一番功夫的,对原著中素材的筛选和提炼、故事情节的铺排、发展和转折等,显然也都颇费思量。而他们对于舞台时空间的叙述方式、对于舞台整体的把握和控制以及在舞台呈现的诗意表达上的匠心,也首先就体现在:遵从戏剧凝练集中的处理方式,通过对小说中一些人物、情节的合并、删减和重构等各种方法,令全剧的情节更为精简、节奏更显流畅和紧凑。先是,以白嘉轩换取鹿子霖家那块风水宝地这一事件切入全篇,不仅迅速地跳过了原小说娓娓道来的第一章而直接入戏,铺展了整个故事的发展线索、纠结起人物的相互关系,还以最为经济的方式向观众点明了白鹿原的来历与相关的传说、背景。随后,小说中原本或顺序、或并列发生着的事件,或是靠着倒叙、插叙才令读者理清的前因后果,都被压缩、重置和扭结在了一个又一个具有着特殊意义的时刻里。也正是话剧的主创们于原作中提炼出了这些特殊的时刻,从而让全剧得以迅疾地切入小说的肌理,而他们对素材进行延展和生发所营造出的戏剧场面,又让白嘉轩、鹿子霖、鹿兆鹏、鹿黑娃、田小娥等主要人物的登场更具目的性和主动性,此起彼伏的拜祠堂、砸祠堂、美人计、镇妖娥、三角恋、祭英魂等戏码伴随着白鹿原的风云变幻也更为集中和浓烈,舞台效果也更为强化。

原本,全剧以情节的整一性和集中等为原则,将纷杂的人物、叙事线索等加以删减、扭结或合并,以立体、简洁的舞台语言展现小说的诸多情节,令话剧《白鹿原》以其节奏之快、各情节段落间的衔接之紧,尽显现代质感。但是,与之俱来的也有弊端。比如,为了迅速地推进剧情,令开场的换地风波匆匆忙忙,略去了白嘉轩故意的反复与斟酌,使人物的出场亮相少了重要的展现其心思与谋划的戏码,而代之以白、鹿二人为争买寡妇家的地打架被劝和后,当鹿子霖要骂还白嘉轩六个“狗日的”、白嘉轩心里多骂了一个找补回来的戏,这样做显然分量不够。实际上,这也与话剧《白鹿原》的改编过程中,对于人物的定位有关。在话剧中,白嘉轩形象高大,他的仁义、忠厚和好强被突出,算计和狡黠则完全被屏蔽。这在主创删除了白嘉轩是靠种罂粟成为白鹿原最为殷实的人家的背景,而为之加上了在农协批斗鹿子霖时挺身而出扶走鹿、主动在深夜坐等黑娃来找自己为田小娥报仇,以及主动提出自己家人先鹿子霖一步拆掉被白孝文卖掉的老屋等设计中,就可以窥见。而鹿子霖的形象,也同样被简化了,鹿子霖的贪婪与阴险被放大,也不再顾及他未泯的一丝良心。因而,原作中兆鹏媳妇得“淫疯病”的段落,在话剧的表现中,不仅让人感觉确是鹿子霖做下了亏心事,还让他语带威胁,成为了冷先生给女儿下猛药的直接原因。虽然,全剧紧紧围绕着主人公白嘉轩的生命轨迹来展现出创作意图,但当作为对抗人物存在的鹿子霖完全沦为白嘉轩陪衬的时候,不够势均力敌的争斗也自然就少了许多色彩,同时也必然带来整体布局上的一种失衡。
这种对于人物的简化处理,也体现在对于白孝文一线的处理上。原作中白孝文人生的起伏、生死的转机源于诸多的偶然,而话剧版剪除枝蔓,改为白孝文对于鹿子霖的陷害有着明确的认知以及誓报此仇的态度,因而他在投身保安团的时候就已经是为复仇迈出的第一步,再到后来以营救为名故意敲光鹿子霖的钱财,都属于其连续的行动计划,因而他对保安团张团长所道出的那段关于“脸面”的台词也才更显入木三分、极富个性。这样,改编以重新赋予人物行动的目的性,让剧情得以更为紧凑。还有黑娃拜朱先生为师读书,本是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因而也才有了他后来回原祭祖、到祠堂叩拜谢罪之举,但在话剧版调整和合并之后,黑娃读书的目的变得更为简单乃至于颇具功利性:弄清以后谁坐天下。而为了点染人物性格的光彩,话剧版还强化了人物的行动性和主动性。如白灵和鹿兆鹏、鹿兆海之间的情感纠葛,变为了三人当场直接摊牌。又如田小娥,其在祠堂的当众表白、诉说自己对于黑娃的勾引以及被族人排斥后拉着黑娃“奔月”的主动,虽然让戏剧场面变得生动、人物的整体质感得以丰富,但却让这个有着“秀才女儿举人妾”出身的女人面对世俗、乡约显露出了太多的无畏。而原作中的田小娥一直都是被命运、情势所迫使着,才不得不做出自己的种种选择的,因而只能算是一种被动之下的主动和反抗。实际上,白鹿原人也大多都是在一种被动之中的选择。即使是鹿子霖,也曾因白鹿原淳朴的民风而压制住了内心的算计和贪念,是不断变为“鏊子”的环境激发出了他天性中的邪恶,以致自身在不断的错误选择中彻底迷失。在他的身上,照鉴着的是很多人的人生与浮沉。因而,当戏剧人物的主动性和行动性得以强化,令这些一直被动反抗命运的人都开始变得过于主动的时候,虽然会使人物的戏剧性在有限的戏剧场面中得以更多地开掘,但代价也是巨大的:消减了环境对人的裹挟,以及人在命运面前、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泯灭、被吞噬的偶然性与无力感。这其实比去除白鹿原以外的支线,更能影响全剧历史的、宏观的视角的表述,因为,原作中不论是神秘还是象征,都是在营造一种命运感、一种情势迫人的情境,是以一种造化弄人的表述方式,展现出人在历史面前的无力与渺小。正是人物在命运之下的无奈与无力,才会令全剧始终笼罩在一种苍凉的悲剧氛围之中。这与在台上搭建起苍茫的古原、真牛真羊爬上山坡,或是粗犷悲壮的老腔、秦腔无关。这些外在的地域、民族元素,虽然浓烈,却只能将观众暂时带入而无法让他们的心真正驻留。而这种对于舞台的处理,同样反映出的是主创们的创作意图与叙事呈现之间的一种矛盾。
正如原作中虚实相间的笔法,为作品带来了引人遐思的空间,祭祖、求雨、祭灵等仪式化的民俗场面,令舞台上无形的白鹿祠堂,反而更清晰地笼罩在了古原人的心上,也赋予了这一极具文化象征感的舞台空间以无尽的灵韵。而斥巨资打造出的那座有形的古原,难道不是应该同样以无形之力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过实的舞台,虽然在视觉上营造了黄土地、关中农村的感觉,却直接导致了全剧在呈现上虚实比例的失调,令全剧整体的悲剧基调丧失了空灵的韵味,倒是不如效法中国戏曲景在人身、情中见景的艺术手法,打破以情节为中心讲述完整故事的格局,让空间和时间的变换紧跟着人物的内心体验和心理变化行进,以使那些关键性的戏剧场面带给观众更大的心灵震撼力,从而真正地、最大限度地探索话剧民族化、个性化舞台表达的可能性。
实际上,话剧《白鹿原》为实现原汁原味、全景式地复现原作,对于情节的重视大大超越了对原作内涵的传递,而情节的迅速推进与戏剧性的刻意强化,在吸引了观众注意力、获得良好剧场效果的同时,也让主创们忽视了许多有价值的场面。而重场戏,又恰恰需要让情节进展暂停下来,才能加以开掘和深化。由于忙于推进情节,令原本很多可以带有象征意味的重场戏都被轻易放过,以致全剧在整体上缺少了对于主要人物以及人物之间情感状态的细致表达,这也必然带来作品层次感和递进性的缺失,导致平面化。虽然,主创们设计由老腔、秦腔作为舞台上的贯穿亮点,但这终究属于一种外在的影响。如果,那份厚重苍凉的历史感不是从剧作自身、不是从剧中人物自内而外地升发出来,那么,即使艺人们以独特的声音营造和开拓出了新的舞台空间,将老腔和秦腔吼得多么地有味道、所选取的唱词穿插在剧情中多么地契合人物心理,也依然还是渲染氛围的一种手段,而非全剧的灵魂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全剧拥有着豪华的演员阵容、高度浓缩的故事情节以及对于多种形式和元素不乏精彩的运用,却难以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显然,在舞台艺术的实践中,对于民族化和个性化的探索,理应是对于民族内在精神和气质的审视、提炼与展现,绝非仅仅是靠方言、布景、音响以及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多种元素的营造——这只是完成了一种表、导演在形式上的、外在的探索和实践,而如果没有思想的芬芳和丰厚内涵的闪光、作品的灵魂不能从剧作本身破茧而出,那么,即使是老腔、秦腔等传统艺术元素被运用得更为淋漓尽致,也依然无法真正凝结成白鹿的精魂。这,无疑也成为我们反思话剧《白鹿原》创作得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