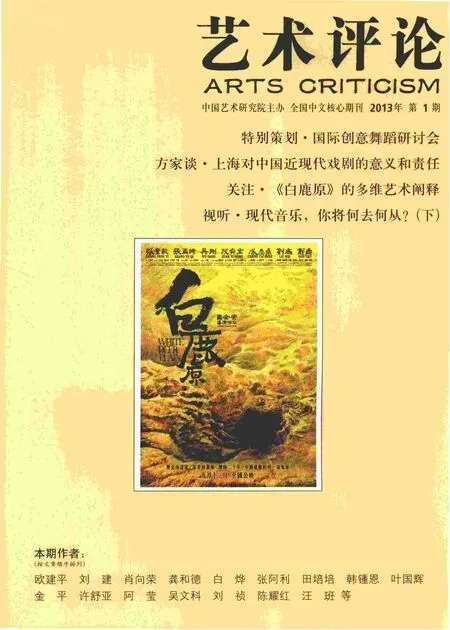漂移在文学、艺术与商业之间——评电影《白鹿原》
张阿利 张 黎
张阿利:西北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张 黎:西北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系2011级电影学研究生

本文希望透过这些现象纷扰,以国内公映156分钟版本为对象,探析影片《白鹿原》在文学改编、艺术表达与商业诉求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影片文本自身所具有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以就教于方家。
自1993年小说《白鹿原》正式出版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间,中国多位著名电影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或试图参与到把这部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巅峰”、“奇迹”之作搬上电影银幕的工作中来,但又因为种种原因与之失之交臂,这也造成了这部影片的命运多舛。直到2012年9月,被出品方冠以“中国最难拍的电影”之名的影片《白鹿原》在全国影院公映。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看,电影《白鹿原》都堪称2012年度中国影坛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它之所以如此引人瞩目,不只是由于其改编自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的经典同名小说,因而拥有相对广泛而深厚的受众基础,而且也源自影片本身在剧本创作、立项、拍摄制作、发行放映各个阶段艰难曲折的历程,更是因为影片在文学改编、文化内涵、艺术诉求、影像语言以及商业运营等多方面所做出的有益尝试和暴露出的突出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给正处在全球化、民族化、产业化语境之中的中国电影带来启发和警醒。
随着影片的上映,围绕这部影片前世今生的各种是是非非逐渐烟消云散,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一片争议声中,一些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前任编剧对影片的炮轰,到审查制度对影片的删减;从扑朔迷离的版本问题,到不如预期的票房成绩等等。
一、文学改编——从小说到电影
自电影诞生之日起,这门年轻的大众艺术就与历史悠久的文学 “前辈”(特别是小说)“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导演张艺谋不但将文学称作电影离不开的拐杖,而且坦言“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美国学者D· G温斯顿在其著作《作为文学的电影剧本》中更是断言“小说的侧重点是讲故事,正是这一点给予了电影这一艺术的发展以最大的影响”。中国电影一百余年的发展历史是与文学相伴走过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是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早期电影就得到了传统古典小说和通俗文学的滋养;建国后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更是成为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创作最主要的源泉之一;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创作的繁荣不但激活了谢晋、吴天明、吴贻弓等老一代导演,更是助推了第五代电影人所创造的电影新时代,《黄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活着》等一大批影片站在文学的肩膀之上走向了世界。据统计,我国每年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片占整个故事片产量的30%,而代表中国电影艺术最高成就的金鸡奖,自1981年创立以来,前二十六届最佳故事片奖获奖影片中有13部是根据小说改编的。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之间的紧密联系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国电影史,也是一部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相互作用的关系史”。
小说《白鹿原》的经典性和其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但拥有极高的艺术水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肯定,而且20年来陆续出版了7个版本,印数超过130万册,在几代中国读者心目中占据特殊的位置。所以,小说《白鹿原》在电影改编方面存在一些先天优势。首先,小说的史诗品质、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饱满的人物形象为电影赋予了坚实的剧作基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白鹿原》的内容说明就很好地印证了小说的这一特点:“这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战栗……”其次,小说本身的文化内涵十分丰沛,能够为日后电影作品的艺术厚度奠定基础。第三,小说所拥有的深厚受众基础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电影在商业上的风险。因此,这只“白鹿”足以让中国最优秀的电影人为之魂牵梦萦。
但是,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名著,小说《白鹿原》的电影文学改编也必然面临一些共同性的困难。首先,经典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文学作品越好就越难改编”基本上已经成为业内的共识。长篇小说是文字性艺术,文化含量较高,而电影则是通俗性视觉艺术,多属于大众快餐型文化。对文学名著进行电影改编很难在保持精英文化的艺术品质和体现出大众文化的通俗性、娱乐性、商业性之间求得平衡。对此,电影《白鹿原》的编剧兼导演王全安也有同感:“优秀的小说,在整个世界这个范围来看,(改编)没几个成的……《白鹿原》就像陷阱”。第二,小说《白鹿原》49万余字的篇幅大大超出了当前常规电影的容量,这给改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小说涉及60多个人物,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在常规影片有限的时间容量里,很难透彻地展现小说的精神全貌。如果剧本不能够把握住小说的内在精神实质,不能够把小说的核心内容很好地浓缩在两个半小时的电影里面,那对小说反而是一种破坏。第三,小说《白鹿原》的经典性对于电影改编来说不啻于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如何成功地运用电影视听语言对文学作品做出一次新的诠释,使之能够同时满足读者与观众这两类不同受众的双重期待视野,也是摆在电影文学改编面前的一道难题。对于以上这些困难,电影《白鹿原》的导演和编剧王全安有着基本清醒的认识:“《白鹿原》小说是很重、也很大的一部著作,内容繁多,而电影只有两到两个半小时,小说改编最大的难度是把作品压缩在两个半小时,还要保留原著的气质和精髓,这个最费思量。如果剪掉那么多,还能不能维持原著的精神?在做与小说的关联性以外,我还要考虑怎么改得好看,怎么满足大众口味”。
从电影《白鹿原》大陆公映版来看,影片在文学改编方面可以说毁誉交加,有得有失。影片改编的成功之处,诚如文艺评论家肖云儒所言:“电影抓住了原著之魂,并且通过电影的可视性和独特的艺术手法,提炼和强化了原著之魂。”电影《白鹿原》以“土地与繁衍”作为影片的主题,并以此作为基础结构情节,塑造人物,可以说不但成功地抓住了原作的精髓而且“把握住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社会超稳定结构”。
对于传统中国农民而言,“土地/粮食”、“繁衍/性”是头等大事,影片选择“土地”作为主题,体现出了对于原作精神的忠实。小说《白鹿原》以土地命名,着重表现的就是形成于黄土地上的黄土文化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的精神的塑造以及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之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的命运沉浮、生活变迁。为实现这一主题诉求,影片中大量出现的麦田、劳作、饮食等与土地相关的场景正是对“土地”这一主题的镜语呈现,特别是影片中那大片的麦田,作为主题意象多次出现,贯穿始终,不但反复申明“土地”这一影片的主题,而且表现出一定意义的超越情节之上的独特意蕴。另一方面,“繁衍”作为影片的另一大主题则表现出了影片改编对原作在一定程度上的延伸。影片并没有拘泥于原著,而是对人物设置进行了大胆的改造。为凸显“繁衍”这一主题,影片删减了白孝武、白孝义、白灵、鹿兆海等人物,只保留了白孝文与鹿兆鹏作为白鹿两姓第二代唯一的后人。人物设置的改变和新的情节的加入,共同将“繁衍”这一主题逐渐从幕后推向前台,将之置于与“土地”同等重要的位置。在这一主题的统驭之下,白嘉轩教子、白孝文与鹿兆鹏娶亲、黑娃与田小娥相爱、白孝文性无能(妻子不育)、田小娥怀上白孝文骨肉、白嘉轩毅然封塔等情节被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如果说,影片对“土地”这一主题的表现主要是通过大量写意的镜语,那么支撑“繁衍”这一主题的则是浓烈和集中的矛盾冲突。这两大主题一张一弛,使影片不但拥有较强的外部冲突和可看性,还具有了一种对民族命运的影像化思考,不但有利于电影的视听表达,还能够表现出对于原著精神的一定传达。
影片在文学改编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整体建构格局较小,没能完全体现出原作的史诗品质、剧作结构不完整、主副线比例失衡、部分细节铺垫缺乏呼应等方面。也许,以上问题部分是由于审查制度所导致的删减而造成的,但是公映版本作为一个自足文本已经是一个独立的艺术整体,其编导应该也必须为其存在的问题负责,而不是一味地将其全部归咎于审查制度。首先,影片整体格局较小,没有完全体现出原作的史诗品质和恢弘气势。小说《白鹿原》堪称一部民族史诗,它“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打开了夕阳西下的中国宗法社会,展示了中国古典村社文明的终结,提供了许多民族精神的信息和文化心理素材、人物感情素材,极大地拓深了我们民族对自身的认知。”影片《白鹿原》显然不具备原作如此恢弘和强烈的史诗品质。从公映版本来看,影片在土地与人的关系、新时代与旧传统的冲突、对立这些原作所着意呈现的宏大命题上表现相对较少,开掘相对较浅,而将笔墨较多地集中于男女情感纠葛。这种改编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原作的高度,削弱了原作的力度,使其与原作相比显得整体格局较小。第二,影片叙事不完整,尤其主要人物命运走向模糊。例如影片的主要人物黑娃、白孝文与鹿兆鹏三人的结局在影片结尾中均未有明确交代,这不但与原著相去甚远,而且违背了基本的剧作叙事原则。第三,田小娥相关情节比重偏大,作为副线有喧宾夺主之势,致使影片主线不明晰。影片前20分钟在向观众展现白鹿原基本风貌的同时,奠定了父与子、旧与新的故事主线,可是20分钟后随着田小娥的粉墨登场这条主线开始出现偏移,原本的副线一度居于主导地位。尽管影片后段有意识地向主线回归,但由于“子一代”三人结局集体地语焉不详而导致这条主线不够完整,缺乏高潮。两相比较,倒显得副线丰满、扎实,更加吸引观众。这一问题直接导致了影片思想游移不定,诉求不明,对影片造成了极大伤害。在网络上有网友更是戏称该片应该改名叫《田小娥传》,这种看法不无几分道理。
二、电影文本——镜语特色与地域文化
虽然影片《白鹿原》在一些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是作为一名长期拍摄文艺片的导演,王全安的艺术功力还是相当深厚的。本片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文本在视听语言等方面具备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具备独立于小说之外的艺术价值。
首先,导演王全安在影片中沿袭了自身电影影像风格中最为显著的外在特征——长镜头/景深镜头。小说《白鹿原》作为一部民族史诗,表现出极强的现实主义特征,电影《白鹿原》不但在剧本改编上最大程度地忠实于流淌在同名原著小说体内的现实主义血液,而且在镜像语言方面,在以巴赞和克拉考尔为代表的写实主义和场面调度电影美学理论的指导之下,大量运用长镜头和景深镜头,在银幕上营造出一幅关中平原数十年发展变迁的真实画卷。影片不但在处理对话场面时极力避免正反打镜头的运用,而且其他场面也主要依赖长镜头和景深镜头。这种技法一方面能够在银幕上呈现出相对完整而真实的时间和空间,又给观众带来以一种异常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审视历史的感受。同时,这种技法有利于对人物内心情感的揭示、对空间张力的呈现、对影片情绪的铺排,而且还能够引导观众进行超越剧情层面的深度思考。总之,影片的这种影像风格在好莱坞式蒙太奇技法大行其道的今天,显得具有一定的特色。
第二,影片在空间形象的建构与表意方面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影片中,麦地、牌楼、戏台、祠堂、宅院、窑洞等场所和建筑共同建构起了白鹿原的空间形象。这些场所与建筑作为人物活动的空间兼具写实、叙事、表意多种功能。一方面,这些场所与建筑真实地营造出了影片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氛围,成功地将小说的文字描写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在银幕上。另一方面,这些场所与建筑还通过象征和隐喻等艺术手法被赋予了一定的叙事功能和表意功能。影片中多次出现的,被摄影机镜头着意呈现的那片波浪翻滚的麦田,“代表着维系生存与稳定的因素”。这样一来,子一代兄弟三人放火烧麦田的场面在叙事之外又可以读解出与父辈以及传统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断绝的象征意义。影片中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空间形象就是祠堂。作为宗法礼教的外在表征,祠堂象征着传统、秩序,成为了白嘉轩内在精神力量的一种外化。影片中,进祠堂、砸祠堂、行刑等情节均发生在祠堂之中,使之表现出了超越空间环境之上的文化内涵与意义。
第三,作为一部中国西部电影,影片对陕西传统民俗,民间艺术以及习俗礼仪的镜语展现,增强了影片浓郁的民族特色和艺术美感。影片影像文本的另一大特点是巧妙地将地方戏曲文化、地方饮食文化、地方民俗文化编织进影片的叙事链条之中。这样不但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民族文化自身的韵味和魅力,而且可以使当代观众对于民族历史文化遗存有了更为直观的认知和了解。例如,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华阴老腔在影片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呈现。片头响起的沉郁顿挫、苍凉豪迈的《薛仁贵征东》为影片奠定了悲剧的总体基调,影片中段众多麦客吼出的《将令一声震山川》更是对关中人的文化性格、心理做出了极为成功的艺术展现,能够使中国观众在心灵深处重温本民族久远历史文化的深层记忆。此外,影片对于传统饮食文化(面食文化)的镜语展现也独具匠心,许多重要的情节以吃面作为演员的外在表演依托,在吃面中展开对话,推进情节,巧妙地找到了饮食文化与民族性格内在的关联。
三、两难抉择——文化诉求与商业票房
被称为“第七艺术”的电影艺术毫无疑问是艺术大家庭中的一员,其自身所具有的审美属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之成为当今世界具有最广泛群众基础和巨大影响力的艺术门类。同时,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和一种“消费艺术”,电影又具有极强的商品属性,以大量的资本投入为生产前提,以影片商业价值的实现(资本增值)为进一步发展(扩大再生产)的根本途径。特别是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后工业时代,电影自身的这种商品属性越发显著。因此,电影既“是艺术创作又是商品生产……不仅受社会历史和艺术规律的支配,又受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支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影界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长期将电影内在的这种艺术、商品二重属性割裂开来,忽视电影的商品属性。这造成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在实践中对电影的商品属性认识不足,把握不够。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电影在崎岖艰难的产业化进程中迈出了第一步,中国电影人开始真正地接受市场的洗礼。从2002年《英雄》拉开中国电影大片时代帷幕至今,已经整整十年过去了,中国电影经过艰苦探索,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但是总体来看,在把握市场规律和艺术创作规律方面还存在很大的欠缺,在平衡电影的文化品质和商业诉求方面做得还很不到位。许多导演将电影的文化品质与商业诉求视为不可兼容的单项选择题。他们要么选择独自呓语,沉溺于个人表达;要么选择无视电影的艺术属性,完全以商品价值的最大化为导向。面对这种状况,电影《白鹿原》并没有随波逐流去做选择题,在艺术品质与商业诉求二者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抉择,而是尝试二者兼顾求得平衡,而小说《白鹿原》自身的艺术价值和广泛的读者群体恰恰为这一尝试提供了成功的可能性。对于这一点,影片的导演兼编剧王全安不但了然于心,而且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我的野心是《白鹿原》在市场上能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同时还能保持住品质”。
但是,从电影《白鹿原》的公映版本来看,王全安“鱼与熊掌兼得”的“野心”显然是落空了。在文化品质与艺术价值层面,影片虽然遭受到了过度删减的伤害,但是仍然保有相当的艺术品质,有其脱离原著小说而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品的艺术价值和存在动因。较为深邃厚重的主题意蕴、细腻丰满的人物形象、卓尔不群的视听语言、沉稳大气的影像风格……共同构筑起影片的文化品质和艺术价值。
反观商业层面,导演王全安却存在着过度依赖自己以往拍摄低成本艺术片经验而忽视当下影院主体观众的客观现实,“既为经典改编,又有巨资投入,这样的电影项目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普通受众。只有在最大限度地尊重普通受众的基础上兼顾自己的艺术追求以及国际影展的奖励和各路名人的称许,才能使影片锦上添花;但王全安似乎并没有把更多的精力和才能用到这156分钟的国内公映版本……两年都没有从整体结构、人物关系和具体细节等方面准备好面向本土观众的最终版本。”这直接导致了影片票房表现不如预期理想,很可能无法收回成本。
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影片在艺术性与商业诉求两方面没能达到平衡,进而导致影片受众定位不清,类型模糊。作为对经典文学名著的改编,电影《白鹿原》或许有两条路可走:其一,走商业大片之路,彻底地娱乐化、商业化;其二,走传统文艺片的类型模式,尽可能实现影片艺术价值的最大化。如前所述,电影《白鹿原》并没有对这两条道路进行单项选择,而是试图两相兼顾。可是,作为一部投资过亿元,拥有多位明星的“大片”,影片显然要以票房回报为基本诉求,而艺术追求只能是排列在商业效益之后的第二追求,这才应该是本片所追求的平衡。可是,电影《白鹿原》显然是将艺术诉求凌驾于商业价值之上,影片自身所具备的商业元素和娱乐性明显不足,故事情节相对沉闷,影像叙事节奏缓慢,无法吸引普通观众的目光。而影片的宣传用语“文艺大片”正好彰显出其在定位方面的模糊性和矛盾性。毕竟,以当前中国电影市场的成熟程度而言,“文艺大片”的时代尚未到来,将文艺片做得过“大”一定会遭到市场规律的惩罚。
第二,影片的编剧兼导演王全安此前从未真正经受过市场的检验,缺乏面向国内电影市场的经验。按照中国导演的代际划分习惯,王全安一般被归为“第六代导演”的范畴。从1999年创作的第一部影片《月蚀》开始,到电影《白鹿原》之前,王全安陆续执导了《惊蛰》(2003)、《图雅的婚事》(2006)、《纺织姑娘》(2008)和《团圆》(2009)共五部影片。纵观这五部影片,可以发现它们均呈现出“国际上风光,国内票房惨淡”的特点。这五部影片在为王全安捧回多个国内外大奖的同时,几乎谈不上任何商业上的建树,其中《月蚀》、《惊蛰》、《团圆》没有正式进入院线发行放映,而《图雅的婚事》和《纺织姑娘》两部影片虽然进入院线,但是作为艺术片,票房只能用惨淡来形容。因此,可以发现,王全安导演在执导《白鹿原》之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走国际电影节路线的小成本艺术电影导演,不但对执导《白鹿原》这种投资过亿的大制作影片缺乏相关经验,而且也从未真正接受中国电影市场的洗礼,缺乏对普通观众审美趣味的深刻认知。在这种情况下,他兼电影《白鹿原》的导演、编剧、制片于一身,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违背“游戏规则”的作法。那么,影片出现定位不清,艺术诉求与商业诉求失衡的问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结语
小说《白鹿原》的经典地位和中国电影当前所表现出的阶段性特点共同决定了电影《白鹿原》这道试题的难度。显然,面对这道题目,以王全安为核心的主创团队得分并不高,从整体上来看,影片很难称得上优秀。但是,无论是影片所表现出的一些症候,还是取得的成就,对于当前中国电影创作和产业而言都极具启示和警醒意义。截至2012年,恰逢以《英雄》为代表的国产大片历经十年与好莱坞大片抗争,寻求本土化、民族化电影突破的关键时期,在这十年中,中国电影人学习好莱坞的先进制作理念和商业运营模式,使得中国电影的创作和制作水准有了大幅度提升,在电影的产业化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以此为契机,中国电影的民族化叙事和商业化表达、产业化运营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十年艰辛的探索期,其间有较多成功的范例,也不乏大量失败的教训。在这样一个文化、艺术与商业交融的语境之中,电影《白鹿原》的出现显然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这部影片承载了一定的民族文化情感和思想内涵,它对于民族文化和历史、心灵与性格的探索态度,显然是时下诸多国产娱乐大片所普遍缺乏的精神风骨,这部作品使得国产电影的本土化、民族化文化特征得以鲜明的凸显。当然,作为一部大片,影片的确对市场运营缺乏足够的经验,对于当下观众缺乏一定程度的重视。这种艺术与商业失衡的症候在当前全球化、产业化、民族化交织的中国电影机体上频繁发作,只不过由于这次关涉到电影文化与产业关系、电影艺术与市场关系、电影体制与审查制度等诸多复杂问题,而使得电影《白鹿原》的症候更为典型。这一典型症候向王全安导演以及其他中国电影人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如何在体制内既坚持发展自我文化和艺术品质,又能够尽可能地面向市场实现双赢。或许,对于这个问题的提出和探索就是电影《白鹿原》对当下中国电影如何真正将文化、艺术、产业等相互交融、达到平衡的启示所在。
注释
:[1]“《白鹿原》不论在作者个人的创作上或是在当前长篇小说创作上,都被认为是一个巅峰。甚至带有突起的奇迹性”。见朱寨《评<白鹿原>》, 《文艺争鸣》1994第3期。
[2]按编剧芦苇接受《东方早报》采访的说法,吴天明、谢晋、张艺谋、陈凯歌、芦苇等电影人都曾与电影《白鹿原》产生过关联。详见 《东方早报》2012年9月19日 B02版 《以电影人的现状,还是不要 碰<白鹿原>吧——专访<白鹿原>第一任编剧芦苇》。
[3]根据李道新 《<白鹿原>的四个版本与王全安的四种可能》一文所说,电影《白鹿原》至少有四个版本,详见《中国艺术报》2012年9月24日版。
[4]碧鸥 《电影改编学术讨论会小记》,《电影艺术》1983年第8期,第14页。
[5]转引自陈墨 《新时期中国电影与文学》,《当代电影》1995年第2期,第45页。
[6][美]D · G温斯顿:《作为文学的电影剧本》,周传基、梅文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3年版,第27页。
[7]程惠哲《电影改编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3期第126页。
[8]采访者:赵晖,受访者:李道新 ,《中国电影的文学性要走向何方(上)》,《电影》2006年第2期第28页。
[9]、[12]、[20]统计数字及相关主创陈述来源自 《东方今报》2012年2月25日版 《<白鹿原>从小说到电影的挣扎》。
[10]见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内容说明。
[11]路易斯 · 贾内梯《认识电影》。 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胡尧之、胡晓辉等翻译,第250页。
[13]参见网易娱乐 2010年10月9日《从小说到电影:8年波折<白鹿原>重上白鹿原》 http://ent.163.com/10/1009/07/6IHOK8EN000300B1.html
[14]、[16]肖云儒 《银幕上的白鹿精魂——初谈电影<白鹿原>》,《城市经济导报》2012年9月12日版。
[15]、[17]详见《<白鹿原>四人谈》 胡克 语 《当代电影》2012年第10期 第38页。
[18]邵牧君语,参见《西方电影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9]钟大丰《中国民族电影产业的历史与现实》, 《文艺研究》2006年第7期 第120页。
[21]李道新《<白鹿原>的四个版本与王全安的四种可能》,《中国艺术报》2012年9月24日版。
[22]根据统计数字《白鹿原》票房约1.3亿元,而投资高达1.2亿元,预计票房要达到3亿元才能盈利。
[23]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 年 3 月 1 日第 7 版《〈团圆〉:尝试穿越60 年分离的隔阂》一文,记者文依。
[24]《月蚀》获第 22 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惊蛰》获第 23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图雅的婚事》获第 57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 ;《纺织姑娘》获第 33 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大奖和国际影评人奖 ;《团圆》获第 60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