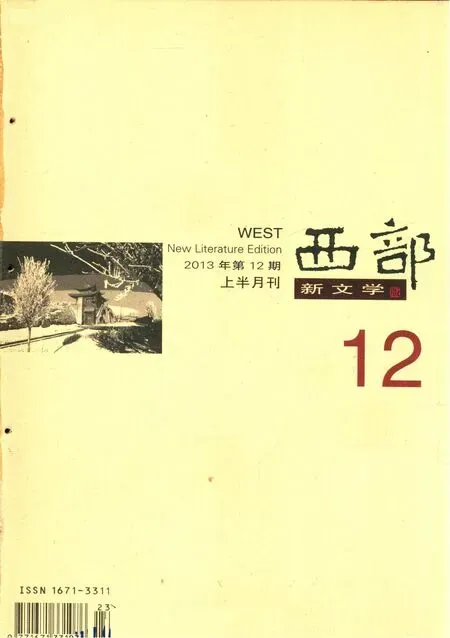蠕动
朱子青
下午时分,天空中那些散落的云慢慢地粘结在了一起,很快就在头顶撑起了一个幔,世界顿时灰暗了下来。风摇着路边的树,那些伸向天空的枝桠不能自已地在风中摆动着,像一个个疯子在手舞足蹈。他站在窗前,觉得自己的心就挂在这些枝桠上,慌慌地不知所措。良久,他将目光从窗外的马路上收了回来。房子里更加昏暗了,每一件家具上都落了厚厚的尘土,灰蒙蒙的一片。门口的鞋柜上放着一把钥匙,这是他刚才进门时顺手放的吗?鞋柜上方是一排衣帽钩,上面挂着一件黑色夹克,他认得出是得雅牌的,这是他刚才脱下来的吗?这一切,恍如隔世,怎么都记不清了。
“这是我的家吗?为什么这般陌生,是自己离家太久的缘故吗?”
其实,无论他在那间白房子里呆多久,他都没有忘记自己是有一个家的;无论医生护士怎样虐待他、呵斥他,希望他快快地死去,当然这也许是错觉,他都记得自己是有妻子女儿的,她们一定牵挂着他,在等待着他出去。
“这肯定是我的家!”
他在楼下草坪中央,在一棵丁香树下,藏了一把钥匙,他正是用这把依然明亮的钥匙打开家门的。当他第一步踏进家门时,略微有点激动与亲切,但更多的却是陌生。房子里弥漫着一种很冲的尘土味,有些呛鼻。也许再过一个小时,或者再过几分钟,这种陌生感就会消失,就像与一个陌生人交往一样,只要交谈十几分钟,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或者从事的职业,或者只谈谈天气与时事新闻,两个人很快就能熟悉起来。现在,他要做的就是重温,重新认识这个家,或者说是重新找回自己的家。
从什么地方开始温习好呢?也许坐沙发上等一等,等妻子回来,等女儿回来,只要一见面,只要有一点久别重逢的笑声或者哭泣声,家的感觉就会回来的。他这样迟疑的时候,突然,在眼前的墙壁上,发现了一条蛆虫,白白的,细细的,小心地往前蠕动,又似乎一动不动。
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这条虫子吸引了过去。
哪里来的蛆虫呢?这让他困惑:“难道妻子没有发现,女儿也没有发现?”她们都是有洁癖的人,一进门,见到如此恶心的东西,一定会接连地惊声尖叫。现在,得想办法将这东西搞下来,冲下马桶。“难道在我离开家的时候,她们也出了远门?”她们一直计划着要去北京、上海,她们好多次埋怨他的无能,不能带她们去,这让他感到羞愧。她们还埋怨房子太小,埋怨车太廉价,埋怨他什么也干不了,真是个窝囊废,这大约都是她们的气话。确实,他无用,他没能有关系与钱让孩子上一个重点初中,他没有能力调动弟弟的工作,他没有能力让父母安享晚年,他甚至想换一个工作都没有如愿。有时候,他感到气馁,觉得活得太憋屈。其实,他已经很尽力地在工作了,像一条听话的狗,而且被套上了锁链。他担心公司会解雇他,这样他就没办法向妻子女儿交代,没办法向父母兄弟交代,如果失去了这份收入,他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他爱亲人,爱这个家,大多数时候,他愿意做他们的仆人,愿意为他们做饭、洗衣、跑腿儿。他一点儿怨言也没有,只希望他们不要嫌弃他就好。他没有高大的身材、英俊的相貌,没有权势背景,没有更高的学历,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司员工,甚至不幸的是,他这个可怜的普通人患了抑郁症。他觉得自己没有病,只是很难高兴起来而已,但很多人都避而远之地说他有病,那样子就像他这种病是可以传染的似的。
也许,她们确实没有发现,这东西那么小,注意不到也是可能的。他向前走了几步,在通往玄关的墙壁上,在厨房的顶棚上,在卫生间的门框上,一只,两只……他一共找到了七只,他浑身不自在起来,仿佛这些蛆虫正在他的身上蠕动。难道这是错觉?或者是梦?他眨了下眼睛,没错,是蛆虫!蛆虫的头顶有两个针尖儿大的黑点,那一定是它的眼睛了,可是,它们却对他视若无睹。“为什么,它们难道看不到我?难道自己在一只虫子的眼里也是渺小不可惧的?”他心里喃喃地说。
“抑郁症能死人吗?难道我已经死了吗?是灵魂回到了这个家?”他对自己的死亡没有一丁点儿印象,因为病床前没有一个人哭过。“要说有人哭过,那只能是自己,人能哭着为自己送葬吗?”他踮起脚又靠近了一点儿,并轻轻地吹了一口气,这小东西仍无动于衷,不紧不慢地往前蠕动。他有一点儿生气,便仰起头对着其中一只使劲地吹了一口气,但没有将它吹跌下来。它分明感觉到了什么,愣了一下,又向前爬了。他不知它们要爬到什么地方去。
他想一定是什么东西放坏了,这说明家里不是没有人住,他这样一想,就感到有些欣慰,也许妻子与女儿很快就回来了,在她们回来之前,他要找到这生虫的源头来,将房子弄得干净明亮,然后继续中断了好久的日子。
返身走进卧室,他想从卧室开始排查。他拉开左边床头柜的上层抽屉,里面有一盒珍珠粉,他认得出,这是妻子曾经用过的。她将珍珠粉与鸡蛋清和成泥状,像白色的涂料,让他帮她慢慢地、均匀地涂在脸上。有好几次,她也给他涂了,他们像两个白脸无常一样静静地躺在床上闲聊。下层抽屉里有两本相册。一本是他们婚后去三亚度蜜月时的照片,他们一起在海水里嬉闹,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一次次地相拥……那是一个多么美好、让人留恋与回味的蜜月。另一个相册是女儿的,都是些艺术照,每一次翻阅那些成长瞬间,都让他激动而幸福。相册的下面,是许多证本:房产证、土地证、出生证、身份证、学生证、记者证、教师证、会计证、户口本,以及一些过期的票据,有车票、物业管理收据、电器发票等。每一个证本和票据都记录着他们生存的方式与历史,这几乎是一个家庭的档案。在右边的床头柜抽屉里,他看到了一瓶未打开的法国香水,还有几盒避孕套,都是他陌生的牌子,他有些心虚,但又不敢多想。“也许,也许是妻子在为我的归来而准备的!”他这样想的时候,内心出现了一种久违的悸动。
没有找到可以生虫的东西。
合上抽屉,他起身打开了衣柜的门。衣柜里散发出熟悉的力士香皂的气味,这让他感到亲切,他真想把头埋进这衣服里,多闻一会儿。妻子的衣柜里有那么多的衣服,每一件都是一个美好的记忆。他自己的衣柜竟然空荡荡的,他那么多的衣服都到哪里去了呢?只有套男式睡衣,看样子是新买的,还挂着商标。“难道,这也是妻子为我准备的?”他这样一想,真想立刻就换上这套新的睡衣。好长时间了,他一直穿着白底蓝道道的睡衣,一套又一套,都是那种款式,那些蓝道道像绳子一样捆绑着他,他不愿意穿这样的睡衣,可是除了这样的睡衣,他几乎找不到可以穿的衣服。他被关在白房子里,有时他们还将他绑在白床上,每每这时候,他的大脑就一片空白。他当然会安静地躺下来,一动不动,他感到自己已经死去。有时候,他觉得死亡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大脑里一片空白,内心里一片空寂,没有烦恼与忧愁,没有恐惧与危险,没有欺骗与谎言,没有伤口与疼痛,没有压抑与桎梏……他想,还是尽快找到生虫的源头,将房子收拾好后再换衣服,彻底摆脱掉这身捆绑了自己好久的蓝道道睡衣。
转过身,他看到了书桌,他曾经心爱的书桌。以前,他坐在这里读小说,偶尔也写一小段散文。他内心里是想当一位作家的,虽说作家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群,在生存竞争的生态链里几乎是最低端的,但他还是悄悄地写,偶尔给一些报刊寄出去,只是从未发表。书桌上有几本小说,整齐地摆在电脑旁,他突然想,这些蛆虫会不会是书里面的文字变的,会不会是从电脑游戏里、从QQ农场里跑出来的?他也认为这样的念头不可思议,但并不可笑,现在,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比如自己吧,自己觉得没有病,但别人说你有病,渐渐地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病了。那一天,有一个人说他的神经有问题了,接着又有个人说,三个人,四个人,后来,他就被送进精神病院了。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变成了这样。有人说是因为老板给了他一巴掌,有人说是因为他的妻子有了外遇,还有人说是因为他的女儿离家出走了……久而久之他就神经错乱了。其实,他也不能确定,一个巴掌、几个传言就能将一个人搞疯吗?
也许真能。
好在,他现在回来了。他翻墙逃出了医院。他早应该回家了。
书桌上方是窗户,窗台是粉色的大理石,上面是一盆红掌,花叶枯落,盆土板结,早已死了。他走过去,看了看花盆,发现里面只有几只飞蛾,并没有蛆虫。他转身退了一步,趴在地上查看床底下。床下有几个鞋盒子,盒子里有几双旧皮鞋,都落满了尘土,其中一个盒子里有几部旧手机,以及耳机、充电器和两部传呼机,还有两部小灵通……这让他想起了那些逝去的岁月。记得恋爱的那阵儿,他的腰间别着传呼机,他多么喜欢听到嘀嘀嘀的声响,那是恋人发来的信息。另外一个盒子里有女儿的玩具,一个缺了角的魔方。记得女儿玩魔方时,玩着玩着就无法恢复了,哭着要原来的样子。他费了好大的工夫,却越玩越乱,最终不得不拆了魔方,拆的时候不小心弄坏了一个角。
看来,床下也不会生蛆虫的。
他又返回了客厅,客厅里有两组沙发,一组三人座,一组两人座。三人座前是茶几,距茶几一米五的前方是电视柜,电视柜有三个抽屉,挨着电视柜右边是一个花架子,左边是一个角柜,角柜上有一个鱼缸。鱼缸里还有半缸浑黄的水,一条鱼也没有了。他小心地推开两组沙发,沙发下也积了许多尘絮,还有女儿的一块橡皮、几颗跳棋子、几张扑克牌、几枚杏干。这让他想起了过去,那些花花绿绿的鱼在鱼缸里快活地游来游去,他们与亲朋好友在家里吃火锅、打牌、下棋、看电视、嘻嘻哈哈地闲聊。有时候,他一个人睡在沙发上,将一部电影或一场球赛看到深夜。看了看沙发下的这些东西,他就觉得那么多的日子过去了,剩下的就只有一层尘絮下的几颗棋子与扑克零星的几点记忆,大多都不存在了。他看了看,想顺手把它们捡起来,但犹豫了一下就又放弃了。他知道,每干一件事,都得心无旁骛,一个细小的东西,一个小小的岔子,都能把人引上歧路,都会影响事情的结果。
他将沙发复位,蹲下来,拉开了茶几抽屉,里面有几把剪刀、一卷旧报纸、几瓶药,其中一瓶是降压药,这是他为父亲买的,但父亲还没用得上就去了另一个世界。抽屉里还有一些葡萄干、杏干、龙眼、枸杞、瓜子……这都是节日时为客人准备的。过去家里来过多少客人呢?一张又一张面孔很快就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依次又在他的眼前消失了。过去的,都归于尘絮,都已面目模糊。他将这些干果一袋袋地拿了出来,仔细地寻找,也没有发现蛆虫的影子,他又将这些干果凑到鼻尖,也没有闻出异味来,这让他怀疑自己是在梦中。他想抓一粒瓜子或葡萄干尝尝,以证实自己味觉的清醒,但想到尽快要找到蛆虫的源头,就又放下了这个念头。
天色更灰暗了,风大了起来,看样子要下雨了。“下点雨多好啊!”他感叹到。他觉得自己就像一粒浮尘飘在空中,一场雨会让空气、让他的心情湿润起来。
他起身拉开电视柜的第一个抽屉,里面有很多的药,感冒药、退烧药、治拉肚子的、治胃炎的、治胆囊炎的、治前列腺的、治颈椎的、治失眠的……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的营养液、保健品。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东西都已过期,成了一堆垃圾。看到这些药,他就能想起自己的每一个内脏器官,它们或多或少地出过事,让他难受过、疼痛过。他每拿起一个药瓶,感觉对应的某一个器官就会有异样,比如拿起颈椎宁痛膏,他就觉得颈椎突然不适起来。他转动了一下脖子,听到了“咯巴咯巴”的响声。他放下药,内心掠过一道闪电般的惊慌,他弄不清药与所治疗的器官之间有什么关系。放下颈椎宁痛膏,他的手碰到了妇科千金片,他突然想到了妻子,想到了他们曾经流产过的一个孩子,他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产床上的血,以及惊慌地奔波在家与医院之间的自己……
拉开了另一个抽屉,里面是他们结婚的相册,还有他与同学、朋友的影集。每一页都让他想到了一个幸福的瞬间。他翻了几页,开始悲伤起来:过去的,是多么美好的岁月,那时候自己是那样年轻,妻子是那样美丽,朋友是那么可亲,生活是那么美好,世界是那么让人迷恋……可是,这一切只几下就翻过去了!在他合上相册的一瞬间,他感到,过去的一切太短暂了,短暂的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放下相册的时候,他意识到,如果继续翻弄这些照片,他很可能会沉溺在往昔的岁月里不能自拔,因为每一张照片都有一个美好的故事。如果这样,到下个世纪他也找不到生虫的可疑物,永远也翻不遍这个小小的家,说不准会老死在一本相册旁呢!确实,时光的速度,几十年几乎是一眨眼的事儿。想到这,他便关上了这个抽屉。
他拉开了第三个抽屉,里面有几盒茶叶,包装都没有打开。他一直想着送领导,办事的时候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却连几盒茶叶都没有送出去。他感到自己有些窝囊:“什么样的人不窝囊的呢?无权无势无地位的人天下一大堆呢!难道只有自己活不下去?”想到这,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穿过玄关,进了女儿的卧室。卧室里有一架黑色的钢琴,每逢周末,女儿就会叮叮咚咚地弹个不停,比如《献给爱丽丝》、《童话》、《秋日的私语》……他则静静地躺在沙发上,或者在厨房忙活着,内心充满着甜蜜与惬意。女儿的卧室还是那么温馨漂亮,双层床,带有书架,书架上有那么多书籍,她最喜欢的是《意大利童话》。夜晚,月光照了进来,他坐在床边给女儿读童话、讲故事……他打开女儿的衣柜,也是好多的衣服,每拿起一件衣服,他就能想起女儿穿上它的样子。衣柜里没有蛆虫,他又看了看女儿的小床,床上有很多的玩具,巴比公主、小熊维尼、喜羊羊……每一个都似乎对着他在笑,他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觉得它们在笑自己傻,它们大约觉得自己的行为是不可理解的,那么认真,那么专注,眼神焦急,像在寻找什么,又漫不经心……
女儿喜欢吃零食,该不会是没吃完的零食放坏了吧!他在房间里仔细进行了搜寻,什么也没有找到。女儿的书桌上有几幅铅笔画,画上的少女长着蓝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非常漂亮。记得有一次,老师们安排她们做墙报,要让她们画春天,要求找一找春天的词,找一些春天的色彩。女儿说她找不到,他说我们到外面去找吧!柳树发芽了,“发芽”算不算春天的一个词?不算!老师说要找像“万紫千红”这样的。当时,窗外突然刮起了沙尘暴,他说“沙尘暴”算不算春天的一个词?女儿说不算!他们又想了很久,外面开始下起了雨夹雪。他说“雨夹雪”算不算春天的一个词,她说不算!她最后一次说不算的时候,眼泪就出来了。为了使她的眼泪很快止住,他只好依据画里的印象替她画。他画了燕子,画了柳树,画了小河,画了红花与绿草,画了矮矮的房子,画了斜飘的细雨……
一切都过去了,女儿呢?应该上几年级了?初中、高中,还是大学?自从那一天女儿无缘无故地出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可爱漂亮的女儿。大街小巷贴满了寻人启事,电视台、广播电台都在播寻人启事,他就是那时突然发病的,他发疯般地在街上跑,大声地叫女儿的名字……这似乎只是一个可怕的梦。
夜幕已经下来了,星星看得见了,马路上的路灯也亮了起来,过往的车辆川流不息,冲过来的气流撞击着玻璃。他有些慌乱,他想就此作罢,先弄掉墙上的蛆虫,但他却怎么也停不下,他变得执著了起来。
他走进了卫生间,打开洗衣机,里面什么也没有。他拧开了水龙头,打开了热水器,还顺手摁了一下马桶,做完一连串的动作后他突然觉得可笑,他不知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看到洗衣机就想洗衣服吗?看到热水器就想洗澡吗?看到水龙头是想试一下是不是停水了吗?确实,他平时不堆积脏衣服,脏一件洗一件,他心里头容不下一件脏衣服。刚才他一看到热水器,说真的,他就感到背上有些痒,就想洗澡。但是他开了热水器后,接着又摁了马桶一下,这让他自己也感觉不可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发现自己可笑的举动后就关了水龙头、热水器。不过,他突然想起了母亲,有一年,母亲千里迢迢地进城来,因不会用热水器,大冷天的竟洗了个冷水澡,以致于患了重感冒,后来,回到农村老家,过了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他一直痛悔,如果他给母亲好好看看医生,也不至于这种结果,他恨自己,真想迎墙碰死。他拿起拖把想拖干卫生间地板上的水,一提起拖把便发现拖把上有好多长头发。这是妻子与女儿的,他分不清到底是妻子掉的头发多,还是女儿掉的多。他想起了妻子经常对着镜子拔白头发的情景,想起他给妻子拔白头发的情景……
卫生间没有发现生蛆的可疑物。也许问题出在厨房。他转身走进了厨房。
记得有一段时间,厨房出现了蚂蚁,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他家住在十三层,这么高的楼,难道它是从一楼爬上来的吗?女儿埋怨道:“它们为什么要爬到我们家来,非要破坏人家的食欲!”有时,这些小东西会爬在案板上,爬在刀面上,爬在燃气灶的周围,无论锅台洗多干净,它们总是要来走一走,似乎这里成了它们的操场或游乐园。有一段时间他担心蚂蚁爬进面袋子、米袋子,万幸它们没有发现米面的储藏地。后来他终于发现了蚂蚁的穴口,便用透明乳胶糊住了穴口,再后来,这一窝蚂蚁就不知到哪里去了。有一回他梦见这些蚂蚁们纷纷钻进了他的耳朵、鼻孔、嘴巴,甚至钻进了他的肛门,他吓得惊叫,但身子却像死了一样,一动也动不了,那些蚂蚁似乎都是些聋子,听不到他的尖叫,它们不慌不忙地排成队伍,一直往他的身体里钻,浩浩荡荡……
米袋子是空的,面袋子也是空的!他打开冰箱,里面有几个鸡蛋,他拿起了一个摇了摇,咣咣当当地响,显然是坏了。恍惚中他看到了一只蛆虫从鸡蛋里露出了头,张牙舞爪的样子!他眨了一下眼,才发现这是幻觉。接着他又在壁柜里查找,发现了好多豆子,那是刚买回豆浆机时买的各类豆子,黑的、黄的、红的、绿的,五颜六色,还有玉米、燕麦、薏仁……那时候,电视上每天都播豆浆机的广告,似乎全国人民都在喝豆浆,不喝豆浆就落伍了。买回豆浆机后,早晚都打豆浆喝,变着各种花样,但很快大家都厌倦了那种味道,于是豆浆机就闲置起来,成了一个摆设。他看了看剩下的这些豆子,都是干豆子,没有生虫。他打开抽油烟机上面的橱柜,里面有些辣椒,还有两袋花椒,绿色的。花椒是岳父从云南带回来的,说是金沙江崖壁上的野花椒。他打开燃气灶下的橱柜,看到了许多双筷子,还有碗碟,其中有一双银筷子,是专门给女儿买的,有一只碗上面画着鲜红的苹果,是从农村老家带回来的,有几个碗边上磕了豁口,记不清是什么时候磕的了。橱柜里还有许多刀具、爪篱、勺子,还有烧得发黑的钢精锅,其中有一把锰钢刀,黑色的面,这是他在一位哑巴手中花了五十多元买来的,上面竟然生了红色的锈。他记得有一回,不知是做饭烦了还是因为妻子从不洗碗的原因,他气得想用刀砍自己的手,心想如果自己做不了饭,成了残疾人,妻子会不会因此而精心地伺候他呢?后来,他又想到妻子也许会因此离他而去,扑进别人的怀抱,因为那一段时间,关于妻子有外遇的流言很多。他一气之下,刀就砍在了大理石上了,刀刃崩了一个大豁口。想到这,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心想,自己为什么那么狭隘呢?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心态不好,说穿了,就是心太小了。 心态的“态”字,拆解开来,就是心要大一点。
他发现了一盒红枣粉!在冰箱上面的另一个橱柜里。
“啊!肯定是这个坏了!”他又惊又喜。
红枣粉是远在另外一个城市的岳母寄给他的。为什么一小勺都没有动呢?真是辜负了岳母的一番心意!
他轻轻地打开盒盖,先是有很多蛾子飞了出来,枣粉变粘结成块状,但上面没有一条蛆虫!他又断定是枣泥生的蛆虫。他小时候见过蚕,他知蚕虫是会变成蚕蛾的。他将这盒枣泥拿出来,等了好一会儿,果然就看到了一条小白蛆虫从泥缝中探出了头,接着又探出一只、两只来,它们扭动着身子,显得不慌不忙,他在惊喜之余大为骇异。
“这些蛆虫是如何产生的呢?它们为什么要爬出来,为什么不呆在枣泥里面呢?这是怎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他喃喃道。他因此联想到了人类的来历,联想到很多生命的变异过程。他觉得一棵树生长久了也会变成精怪的,一块石头说不定时间久了也会变成河龟,一条河时间长了会生了翅膀飞走的……关于神,关于鬼怪,关于一切的荒诞不经与不可思议,一切他曾经半信半疑的东西,突然间都觉得是有可能的。比如一个男人可以变成一个女人,一只狗可以变成一头猪,驴会说话,马会笑,牛会流泪,羊有智慧,每一朵花都有爱情,每一根草都有性欲,每一块砖头都有思想……
他呆呆地望着,那一条条的蛆虫像香烟一样一缕一缕地冒了出来,从它们不慌不忙的姿态里,他断定它们是有智慧的。看吧!现在,它们正笑着从枣泥中探出头来,滑过盒沿,从橱柜的黑暗处爬了出来,一直爬啊爬!“这些愚蠢的东西,要爬向什么地方,它们在追求什么?”他觉得有另一个人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形,骂出了声,但他看不到这个人,转念又觉得这话是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的,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立刻就闭住了嘴。
这时,他听到了钥匙孔里有转动的声音,看样子妻子回来了。他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想藏在门后看看妻子,他想给妻子一个惊喜。就在这时,防盗门轻轻地一响,年轻漂亮的妻子就进了门,他没有想到,妻子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一个他不认识的老男人,他突然有些紧张,也有些愤怒,看来妻子有外遇的事是真的,他想扑出去,砍了这个男人。
“他真的死了?”男人问。
“嗯,死了!”妻子回答。“翻墙逃出了精神病院,等人发现时,在西河坝的树林带里,身上长满了蛆!”
“自杀的?”
“这种病还能有什么好的结果!”
“真是难以置信,好好的人。这房子你打算怎么办?”
“卖掉吧!不想再回来了!”
……
后面的话他一句都没有听清,他只从门缝里看到,那男人和妻子搂抱着走进了卧室,他听到了高跟鞋掉在地板上的声音,听到了那男人粗重的呼吸声。
他感觉头有些晕,几乎在一瞬间,眼前的一切就恍惚了起来。他看到,整个房子里爬满了蛆虫,锅盖上、碗沿上、灶台上、消毒柜上、冰箱上、地板上、垃圾桶里、床单上、沙发上、电视机上、空调上、电脑上、孩子的书包里、书本上、鞋子里、天花板上、窗玻璃上……他看到有几条蛆虫爬上了他与妻子的结婚照,爬上了妻子的脖颈,爬上了他的嘴唇,爬进了他的眼睛、鼻孔、耳朵里。它们变得疯狂了起来,有的站在他的头发上跳舞,像个醉汉;有的站在发梢上大喊大叫;有一只像跳水运动员一样跳下了他的额头……他感到了它们通过了这些窍孔,包括自己的肛门,很快就进入了他的腹内,它们有节律地蠕动着。他还看到了床上,看到了被子里的妻子与那个男人,变成了两只大蛆虫,在不停地翻滚、蠕动。被子上面有很多小的白色的蛆虫,一个爬在一个身上,也起劲地蠕动着。很快,蛆虫们像潮水一样涌满了整个房间,整个世界变成了蛆虫的世界,整个世界的节律变成了蛆虫蠕动的节律。
很快他就淹没在这些蛆虫之间了,他感到自己也变成了一只蛆虫,与这些白色蛆虫的样子并无二致,他慢慢地被这种节律所控制,身体也不由地蠕动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