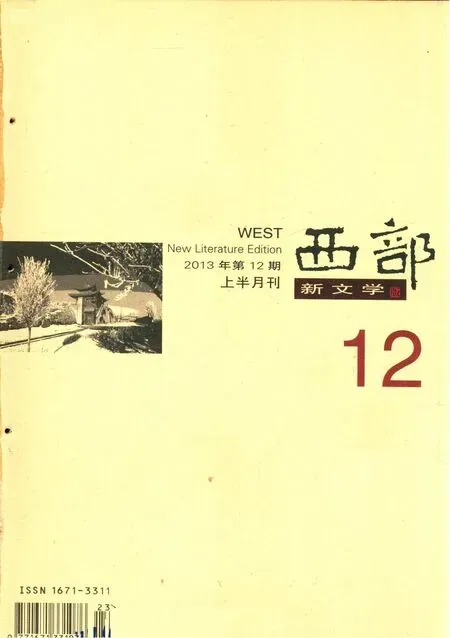博格达峰(节选)
刘江波
2004年6月9日星期三
时间: 6:45
天气现象:薄云如絮
风力情况:西北风4级
温度:14℃—24℃
远景:远处五六重山峰重叠,余重山峰可见。
其实,那道若隐若现、出现在云彩间的“天河”并不算宽。“天河”,由今天出现的一些片状层云组成,层云与层云,层层相隔,平行分隔成十几层;它们明暗相间,如绸若丝,就位于我对面地平线尽头的东北隅与博格达峰之间那条低洼的地带里。
太阳刚一露出天际,一个失足,就跌入了这道“天河”之中。
“天河”之“水”,若泉,若波,若流,若烟。时而静谧不动,却只是片刻;时而潺潺流动,亦流淌有声。时而九曲百折,涡流回旋;时而微风掠过,涟漪遂自散开。
稍有一纵,太阳已经静躺在“天河”中,坦然接受着“河水”沐浴。微风轻盈,吹起云带;太阳被浸入水中,水流款款漂漾。只是看不分明,这个沐浴着的太阳,是金童?是玉女?亦或全不是。微风,若无其事地,顺手拉过一丝薄云,将太阳的一副裸体遮掩了起来。
天地间总在演变着天旋和地转。一轮月亮,尚有月盈月亏,阴晴圆缺;月亮的故事,层出不穷。日月轮回,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年过后又是新的一年。
今日里,半片太阳,格外温柔,犹如一个初生的婴儿,任由微风的女人似的玉手,轻轻摆弄。太阳,一会儿被浸泡,静静地,沉在水下,一动不动;一会儿,水波在其表面滑过,水中折射出的太阳肤肌,似乎在上下粼粼起伏;一会儿,水波荡漾,流水潺潺,在那只“玉手”轻搓之下,太阳脸面上的些许光斑和黑点,全都被轻轻褪去;再一会儿,太阳被倒着提出水面,体香四溢,水声滴答。
许是浸泡得过久,太阳在水中,渐渐地溶化,似一团金黄色黏黏的蜂蜜,溶解在水中。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甜蜜的蜜香气味,那准是一块能解了极馋的上好蜂蜜。
“天河”之水,仍在流动。不一会儿,太阳又起变化,成为一枚正在孵化的半透明、扁圆、尚没有蛋壳包裹的发亮的软体卵子。博格达峰东北隅,那里是一处天然的“暖阁”。人们希望着,能从这样一枚尚未成熟的卵子里,孵化出一只远古时期初生态的“原始太阳”。人们想象,远古蒙昧时期的太阳,一定是一个光彩逼人、天生丽质、体态优雅、堪绝一世的美女。如若不然,为何数十亿年过去了,太阳系的八大行星,这些远古时期的追求崇拜者,至今仍在日以继月,年复一年,围绕着太阳这个心目中的女王,追求如初?太阳的“爱情”,却是情有独钟。正是因为在太阳系中的八颗行星和难以计数的小行星及卫星,这些众多追求崇拜者中间,地球,以其一份虔诚如水、肝胆若铁、苦苦的追求不懈,独自博得了太阳的一颗芳心。太阳的“芳心”,就是一颗暖红色的“绣球”。那枚“绣球”从天而降,散开为“花蕾”,蒲公英似落地,形成了每一个人都分得的一份“心花”,有人一时怒放,有人一时遮蔽,还有人只是矜持,半掩其心。
地球上的万物,太阳柔和有加,恩赐垂顾。沐浴着地球上适宜万物生长的温暖阳光,我们人类及万种生灵,千百万年中,在“适者生存”的大自然里,方才得以代代相传,繁衍生命。
只是,太阳这个远古时期的美女,一俟月夜降临,倒也透出一分羞涩,二分矜持,三分孤独,四分无奈。数十亿年过去了,太阳仍旧待字闺阁,无意正式下嫁太阳系八位如意情郎中的随便哪一个,私定终身。
生活在地球上人们,难得一窥太阳闺秀的窘羞之态。太阳姑娘每日傍晚,便匆匆回到太阳山,虚掩起羞脸一张。
天空之中,原本没有是与非,对与错,好与坏,黑与白。天空没有一道“规矩准绳”:规为圆,矩为方;圆者不可为方,方者亦不可为圆。天空里的“宗教”,崇尚的依然是:“我存,故我在”。太阳的意志,就是太阳系里一种潜在的“宗教”。
太阳的形状,处于一种原始动态,或滚圆,或椭圆;或方墩,或细腰;或长鼓,或枣核;或扁形,或滑溜。其柔软之状,宛若一团发面。
在乌色云层的羁绊下,太阳,演变为一只平摊在空中,正在油煎中的白里透黄的“天鹅蛋”。“天鹅蛋”的周边一圈,呈现出不规则的锯齿状。
太阳,继续攀升。此一阵儿,太阳被极薄的橘亮色云层这把锋利的刀子,切成上、中、下三层,如若一块奶油蛋糕,拦腰切作三片。奶油蛋糕的四周,被涂抹上一层焦黄,乳汁顺着云层边缘,垂滴而下,有几滴就悬挂在云层的下檐,欲断还连。
再过了一会儿,太阳终于躲入云层,不再露面。其尾翼一角,被阻于云层之外,宛若一根细长的豆芽。其上端圆弧状的豆冠,亮晃晃地,悬挂在云头边缘,其下端只显露出一丁点豆芽的白嫩身子。
在我眼里,这一时刻,太阳的窘态,犹如一个趴在墙头上的三岁顽童。顽童赤着屁股,上半个身子已探过墙头,一只光脚,却依旧垂吊在墙内,进退脱身不得,一般滑稽。
今日的日出,是如此无奈,原来,太阳亦有难处。
2004年6月22日星期二
时间: 6:50
天气现象:东南风徐徐,天空少量碎云。
风力情况:3级微风
温度:22℃—32℃
远景:能看到六重山峰,其余山峦皆清晰可见,唯独看不清博格达峰峰顶。
博格达峰前的日出,总也有故事——这是一处精彩故事纷纷繁繁、变幻不停、每日上演新故事的“舞台”。
天空,若一片汪洋大海。几峰云彩的“波峰”与“波谷”,十分开阔,荡漾个不停。博格达峰,远远地被挤在天空东边一隅,只若在那些云谷“浪峰”余波轻轻拍击下,悬浮在“大海”海面上的一座并不起眼的“小丘”。
天空里的碎云,如“海面”上的一滩泡沫,一片,又一片。金色的“草芥”和蓝里泛绿的“残叶”,杂夹其中。这些泡沫和杂物,在“云海”间,就散布在博格达峰这堆“礁石”之前。
日出,将要显露。一层淡淡的橘黄色晨曦,斜抹在博格达峰的轮廓上,晨曦朦胧,清浑虚实莫辨。
从观景台上,远远望着博格达峰,这外乡的过路人,他感觉,自己犹如站在一幅精巧别致的大型沙盘前。
“沙盘”上空,由升起的几块彩云形成一个身躯竖挺着云的“山神”,有几朵灰色云变幻出数个赤裸上身的“半人半马神”。在山峦里,有一些时隐时现的一堆白云“树神”,还有雪峰深处来去无踪的一群散云“山盗”出没。
“沙盘”下方,则是那些个懵懂不知的下界芸芸众生,在奇怪地抬头仰望着天空异象。
“诸神”和“众生”,各自扮演不同的神与俗,灵与生。二者角色,泾渭分明,天人各异,互不相混。眼前之景,天贵地俗,巨大差别,一览无遗,皆显露在眼前的这一座摊开在博格达峰前的大型“沙盘”之上。
三重山与四重山之间的山峦,一道又细又长的白练,轻轻掠过。这是山涧的潮气和雾团,被风卷起,飘在半空所形成。“白练”,那是一条拴牛的“缰绳”。“白练”的另一头,一头青里透墨、脊背长有白色花斑、体态颇大的“水牛”,在山涧深处,被缰绳牵住了鼻子。鼻子上钻上了一圈铁箍鼻环。“水牛”憨厚,懵懂,墩实,身躯朦胧。山涧深处,水牛“哞”叫有声,其声甚为哀怜,隐约可闻。
二重山,是一道横卧在地平线上的平顶山。其上有一处人工开凿出的豁口。从山脚下,有一条上行的山道,蜿蜒直上,直通豁口,乍一看,好似缰绳的尽头。博格达峰,这一头“水牛”,正被一个胆大包天、贼艺过人的“牛贩”,打算通过那处豁口,缓缓牵下。如此体大的“肥牛”,何把钢刀,何只屠手,能抹以一刀,鲜血迸溅中,宰杀剔得鲜肉上市?
“牛贩”,乃是风也。
山前,风比起观景台强劲出许多。山道弯曲处,几辆汽车驶过,扬起几道尘土,卷曲着,只道是那头“水牛”,乍走乍停,不肯轻易就范下界。山坡斜道,“水牛”足蹄猛力蹬地,溅起了几脚尘埃。
风,吹抖着空气,眼前景象,有一种动感,亦惑还真。远处高空的碎云,与近处低空盘旋着的一群白色鸽子,交相辉映,宁静一隅,别一番闲雅情趣在眼前。
风依旧。远处扬起的白练,与近处袅袅升起的晨曦,相融在空,似风伸出一只纤手,抓起云的乳白色粉末颜料,轻轻撒在了天空之上。一切,都笼罩在一层淡淡的飘动着的白色气流之中。
稍后,博格达峰东北一隅,扬起白练如串,十几条白色“幡条”飞扬,蔚为壮观。
难道,是天地庙中的地藏菩萨亦在作法祭祀:博格达峰,忒是任性,由着一道好奇,冒死下山,一探人间?
2007年6月27日星期三
时间:10:35上路,开始了五天徒步探险活动。
天气现象:晴空万里
风力情况:微风3级
温度:22℃—32℃
地点远景:乌鲁木齐——柴窝铺——三个山口
穿越博格达峰的路线:柴窝堡——博格达峰——天池,在新疆的徒步探险路途中最经典的一条旅游线路,全程五十五公里。
柴窝堡,位于乌鲁木齐通往吐鲁番的柴窝堡湖畔,属于达坂城镇的一部分。这里是唐代“丝绸之路”新北道上南北咽喉要道“白水涧道”的一部分,是北疆地区通往吐鲁番盆地的一条穿越天山的狭窄通道。
10:35,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 12:00,到达柴窝堡。
这里今年连一场雨都没有下过。
偶尔,在远处的山脚下,出现一道细如羊肠的砾石土地,风吹过去,扬起细细一长线灰白色的尘土。远看过去,就像是风在用一把锋利的“剃刀”,沿着山脚,贴着地皮,吝啬地刮下干巴巴的地层表面多余的汗毛与尘埃。
所谓道路,其实就是沿着干燥河床上的旧汽车印痕,往山脚下行驶。短短路程,耗时一个多小时。四面透风,租用的“乌龟壳”面包车,像只火柴盒,支在四个轮子上,在颠簸的鹅卵石滩地上,晃动如筛。车上的人只是因为属于实在筛漏不下筛眼的沙子,这才勉强能继续呆在车子里,恍若又是几只竖起的萝卜,左摇右晃,终是不倒。车中的空气,只是一个“呛”字了得。
直至快接近沟口,沿途才出现稀疏的树木,先是一棵,接着又是一棵,渐渐地多了起来。这些树木,就仿佛非洲热带沙漠中间的树种,树干粗壮,虬枝若龙。树冠形状,似一只又一只细而又小、上窄下宽的梯形。枝叶稀稀拉拉,如几根瘦长的甜菜叶子,长在干秃秃的树干之上。
这里的风向,永远只是西北风,风大且遒劲。
柴窝堡的人们开口便如此自嘲:这里“男人们的胡子,全都是歪斜着长的”,以此形容风大。此言虽略嫌夸张,观看此地生长着的榆树,倒是再贴切不过。此种说法,就是达坂城人津津乐道的本地特有的那些多姿多彩的“歪脖树”。
谁知,离开三个山口水管站之后,就再也看不见一个人影,偌大的山谷中间,就只有我和同伴——“侠客”一般的梁木齐,以及拖在地上的我们自己那两条又细又长、弯弯曲曲的影子。索性听天由命,全凭着朝拜博格达峰的意志与自己的艰难体力充数。
那个来自遥远“斯巴部落”,探寻着地球秘密的“过路人”,站在沟口,四下里张望——“过路人”,你在作甚?
远远看去,博格达峰,此位魔女的真实面貌,真是莫辨其衷。
博格达峰,究竟是一个纯情的少女,还是一个恶毒巫婆?只在进山朝拜“香客”的苦苦求索之中,可解得其中奥秘。其秘诀写在拜伏其脚下的朝拜者索得飘落自天空的一方黄绢上,此人的虔诚程度亦印证其间。心诚者,赏得一个“仙”字;心乱者,只可讨回一个“巫”字。或明或暗,或清或痴,或醒或醉,或亮或黑,区别,只在一个“诚”字。每一个进山朝拜者皆心知肚明,一点即透。正是这样一道难解的贞节或邪恶的神符,诱得进山者铤而走险。
博格达峰,这一远古时期的魔女,其作抖袍,只是精彩:那个“过路人”,从这里望过去,出现在博格达峰前的那些层层叠叠的光秃秃山峰,就像是魔女坐在最高的山头上,两只手撩起了自己宽大的羊皮袍子,白色羊毛朝外,款款向外一个抖擞,皮袍便被甩开了去。袍子一道接着一道,慢慢低垂下来,在空中形成了几道波浪形的轮廓,便实现了山前诸道山势的铺设。
魔女,抖着三撩皮袍。
一抖:山前耸岭,突兀伸出;再抖:中山斜岭,倾斜铺开;又抖:近前低岭,蜿蜒如泥。
最细微处,莫过于眼前如高低坟头的一片土丘,由皮袍扬起的灰尘落下形成。
皮袍的最上部,是皑皑的雪山和冰川,那是博格达峰和高度超过五千米的其余高峰。
半山腰间的几座山峰,山脊陡峭,只在山的背阴处,分布着不多的几条细长或是零星的斗状冰川。雪水汇聚于山体之下,形成细流,如一条条的羊肠小道,流淌下来,湿润着博格达峰的一双粗笨的“裸脚”。每一只脚上,五根“脚趾”清晰可数。
山体下部的低矮山丘,形成裸露成片的荒原丘陵,那里是一片荒漠,只生长着稀疏的耐旱植物。山脚下干涸的旧河床,是不毛之地。宝贵的水流,渗入地下,从遥远的下方河滩,渗露出来。这些地下水与新建的一条明渠补充着柴窝堡湖的水源。柴窝堡湖的水,又是补充乌鲁木齐乌拉泊水库的水源,一环扣一环,一水连一水,形成一条维系生命循环的绿色走廊。
鹰窠,建在沟口石崖半山腰。石崖,陡直上下。沟口,生长榆树,单株断续,呈为一线。一进了山沟,逐渐出现阔叶混交林:遮阳的柳树、高大的杨树与粗壮的榆树。沟中的林木,越走越多,越走越密,终于密布整条山谷。我们进入山沟后的头三天,就根本没有再见到一个人影,只看到随沟放养着的一些牛、羊和马,自由自在,啃吃野草。大山里的牧民实行粗放式放牧,只要把守住了大山的两面出口,整个夏季,牲畜便完全任其散放。
一进入山谷,我便弄迷了方向,不清楚风从何方向吹来,只觉得是顶头迎面而来。好不容易,才算弄清楚:原来,我们是绕到了博格达峰的南坡上,由天山之南,往北行走。因此第一天,我们一直是顶着西北风往博格达峰的南坡爬去。
第一天走得很远,幸亏有了前几天去乌鲁木齐南山甘沟的徒步热身,一天走下来,并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什么不适应。中午就走到了一号羊圈,一号羊圈是沿途的四座羊圈之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这里山沟两边,给人印象最强烈的就是满山遍野的巨大石头:房子是石头筑建,羊圈用石头垒成,院落围墙用石头堆砌而成,脚下的路也是一溜踩在坚硬的石头上。牧民们转场去了夏牧场,放牧的房子和院落全都是空荡荡的。
我们一路沿着最终流入柴窝堡湖的三个山河,往河流的源头走去。山谷间的河水,冰凉刺骨,这是地道的博格达峰冰川融化流下的天然雪水。雪水能通脉,脉连着地,地接冰川,冰川覆盖博格达峰。我们已经触摸到了博格达峰的脉搏。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得一点儿不错。自进了山后,几乎很少能看到博格达峰的真实山体。因为总有这样一座、那样一座横在其前的浅峰,遮挡住了人的视线。脚下,不停地在作出丈量,一步一步,地势只在抬高。爬越途经的这样一座又一座并不唱主角的山峰,便耗去我们大半天的光景。博格达峰,实在是博大深沉,令人叹为观止。
16:20,到达了火烧石沟。此地海拔二千四百五十米,一沟皆是赤褐色,油光发亮,像是被火烧灼过的石头,故称其为“火烧石沟”。这些满山遍野的巨石,散布四野,看来不属于山体自然分化后地表裸露所致。
一眼望过去,偌大深山野谷,如被“开膛破肚”:遍谷荒蛮,糙石裸露,原始粗野,凄凉一地。眼前之景,不由让我联想起远古那位大地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之景。
远古时期的大地母亲,作何模样?她头枕着昆仑山,身子平躺,南部陆缘“塔里木台地”凸起的地表,是她的酥胸和隆起的肚子;沙漠,是她裸露在外的柔软皮肤。她的双腿,搭在准噶尔盆地同样凸起的台地上。准备好了的用来包裹山峰“新生儿”的一堆襁褓,尚被放置在一条夹在两块台地之间的狭长海槽中。后来隆起山峰的地方,当初只是一片凹陷的海洋。天山山峰,就是上述两块台地相互挤压的产物。天山山脉众多的山峰“兄弟”,一座接一座,在大地母亲肚子颤动中诞生。“子宫口”,就是喷发出岩浆的“火山口”——原始的博格达峰,亦诞生于此。大地母亲的血液,是她肚腹中喷发出来的炽热的赤色岩浆。这些面团一般柔软的岩浆,伴随着山峰“婴儿”的出生,在大地的抖动和炸雷声响中,源源不断,喷射而出。岩浆的碎屑和粉尘,被抛向了数公里的高空,最终浓厚的烟雾随风飘散,碎屑与尘埃便坠落一野,逐渐冷却,形成了表面光泽黑中透褐、赤黑闪亮、如斗若房的光滑巨石。隆隆之声,是大地母亲分娩时的痛苦呻吟。这呻吟,曾伴随着年轻的天山山脉最初地质形成时的整个过程。
我们此行走了整整五天,“火烧石”亦相伴着我们的整个行程。眼前身后,只望不到边,犹如一处古战场上战死的身穿青铜铠甲的士兵,在阳光之下,泛出在青铜铠甲上一道沉重的历史色泽。
一路上,有几处泉水,清澈冰凉,水质极佳,完全不用烧开,我们直接饮用。那些分布在泉眼附近的苔藓,翠绿得纯洁,泛着阳光入水的折射,灿烂得明媚,就像是翡翠玉器浸没水中,莫辨真伪,几可乱真。水草的叶子,浸没水下,在一股股泉水的涌动中,如一把散落水中的绿色“手指”,在抓着细小如苗的游鱼。这些泉眼的水,皆渗透于博格达峰脚下的大小冰湖。
18:50,海拔两千九百米,这里是典型的高山荒漠草甸地带,植被又细又低,紧贴背阴山脊。一层薄薄的藻类植物与一种开着白色小花蕊的地衣,一丛丛约有巴掌大小,呈现半枯黄色,随处可见。藻类植物与地衣统属孢子植物。藻类植物是最简单、最古老的一类植物,可细分为十一个门类的藻类植物,光合作用后释放出的氧气,竟占至地球空气中氧气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地衣,亦是独特的一类植物种群,地衣分作壳状、叶状、枝状三种类型。这里生长的地衣有雪地茶衣等。
我睁大双眼,吃惊再三,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些在如此高寒地带也能伏地生长的植物“小家伙们”。
第一个晚上的宿营地,选择在海拔三千多米的山谷河流边,一处巨型赤褐色石块的背风处。这里经年累月堆累下来的羊粪,厚度足有半米,经过一天的日晒,夜晚颇为暖和。
第一夜根本无法入睡,姑且不说近在身边,陡峭流淌而下的三个山河,其声哗哗,淘淘野野,在山谷中,发出很大的隆隆回音,高山缺氧造成的不适也难适应。加上傍晚时分,见到的被狼吃掉的羊只尸骨残骸。尽管我们快步越过那一片山地,那些“狼们”其实就在离我们并不远的荒山山洞中,以逸待劳。我一直后悔,为减轻负重,不曾随身携带一把锋利的匕首。山壑谷狭,疾风甚大,风吹着帐篷,发出呼拉拉的响声,似凶残的公狼徘徊在附近坡滩,气急败坏,仰天长啸,气浪直喷过来。有时,好像母狼在啃咬我们的帐篷绳子。
我心紧缩,梦中彷徨。整整一夜,基本上是在半是清醒半是迷糊中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