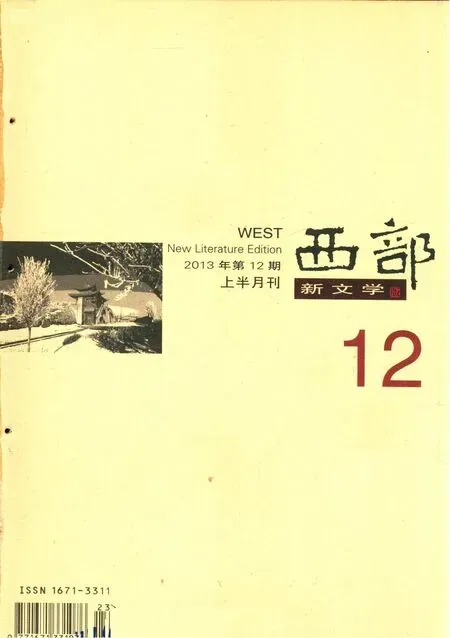戈壁、毡房、酸马奶
戈壁红柳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每当唱起这首歌,都让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在天山的崇山峻岭间找矿的日子。那时,我正年轻,刚刚从下乡知识青年成为一名光荣的地质队员。1976年春天,在天山东麓一条怪石嶙峋的小山沟,在一顶随着呼啸的山风抖动的帆布帐篷里,伴着一盏晃动跳跃的小油灯,一个带着浓郁安徽乡音的老地质队员,给我们几个年轻人一句一句地教唱着《勘探队员之歌》,歌词将我们带进一个神圣的意境,歌声点燃了我们火焰般的热情。怀着为祖国寻找富饶宝藏的壮志豪情,我们开始了艰苦寂寞的野外找矿生涯。
夏季,我们转移到了将军戈壁,这是雄伟的天山山脉和浩瀚的准噶尔盆地的结合部,是一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在这片广袤的亘古荒原上,没有村庄,没有人烟,没有树木,没有飞鸟,甚至难以见到牧人的踪影,只有蓝天白云岩石沙砾和我们相伴。如果说地质事业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踏勘工作就是地质队的尖刀,是远离文明走进旷野的最初拓荒者。踏勘组一共六人,在整个野外工作期问,能见到的就这几张面孔。白天,每两人一组,分头勘测不同的路线。夜晚,六人同宿一顶帐篷。我和师傅小王一组,他大我两岁,朝夕相处,无话不说。由于远离社会,没有新的信息,每个话题都像车轱辘般重复好多遍。听得多了,耳朵就很挑剔,比如师傅讲如何暗恋班花的过程,任何一个小细节有变化,我都会立即认真地指出。好在我俩都不奢望有什么新鲜内容,在死寂的原野上,能听到人的声音,已经是很不错的享受了。
每天早晨,我们带着地质三件宝:罗盘、锤子、放大镜,迎着朝阳,向茫茫戈壁走去。按照分工,师傅负责记录地质现象,我负责采集岩石标本。夏季的戈壁滩像一片茫茫火海,阳光无遮无挡地倾泻在地面上,又从黝黑的砾石上反射出来,泛起一片令人炫目的白光,空气中弥漫着灼人的热浪。一天,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和我们相邻的地质队有三个队员殉职了。他们在戈壁滩上迷了路,苦苦挣扎跋涉了八十多公里,在烈日的暴晒下耗干了体内所有的水分,筋疲力尽倒下了。给我们送给养的司机在路上看到了装着三个年轻生命的灵柩。噩耗令我们感到了物伤其类的切肤之痛,但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工作日程。那年代有句时髦的口号叫“化悲痛为力量”,还有一句话叫“越是艰险越向前”。
那天,天气格外的热,清晨出发时地面就热得烫脚。我们一边走,一边观察采样,汗水很快就湿透了全身。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烈日肆虐着大地,旷野上没有其他任何生灵的踪影,只有我们在顽强地跋涉着,工作服湿了干,干了湿,留下道道白色的碱印。随身携带的一壶水,尽管每次都是很珍惜地抿上一小口,润润嗓子,也眼见着愈来愈少。中午,借助最后的一点水,勉强吞咽了两个干馒头,饭后,开始沿着一条新的工作路线返回。虽然已经非常疲劳,我和师傅仍然一丝不苟地工作着。标本袋越来越重,满满一袋石头压得肩膀生疼,我咬牙坚持着。在布满砾石的戈壁滩上负重行走非常吃力,一脚高一脚低,一脚硬一脚软,砾石间的沙土很软,无情地消耗着每一步前进的努力。由于缺水,嗓子干得冒烟,汗早已流干,全身像被烤着了。
夕阳西下,连续七八个小时的暴晒、缺水和跋涉,我和师傅都感到阵阵眩晕,眼前恍恍惚惚的,步履蹒跚。我俩相互搀扶着,拖动着极度疲劳的双腿,步伐愈来愈慢,而前方仍然是一片火海似的望不到尽头的戈壁滩。在奋力攀上一个小山丘后,奇迹出现了!我们看到了一片绿地,一座哈萨克牧民的毡房。是海市蜃楼吗?经过仔细辨认,我们确认那是真的!我们激动地欢呼起来,所谓欢呼,实际上只是大口地呼气,干涸的声带已发不出声音。水的诱惑极大地调动了体内的潜能,亢奋中我们骤然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奋力向前走去。但此时已无力正常行走,只是一种竭力的快挪,是一组舒缓的分解动作:两条腿互为支点,一条腿缓慢地沿着不规则的曲线移到前面,另一条腿再重复同样的动作,像一组独特的双人圆规舞。眼前的绿洲使心中奔涌而出的幸福感如此强烈,瞬间浸润了全身的每一根神经,使我们暂时忘却了极度的疲劳和焦渴。
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前,一只大黄狗迎着我们高声吠叫着。多么亲切的吠叫声啊!它总让人联想起炊烟袅袅的座座村落。尽管眼下这吠声只是来自一块小小的绿地,却让我俩有如回到人类社会。随着吠声,一个年迈的老年妇女从毡房里钻了出来,黝黑多皱的脸上挂满了笑容,她做着手势,将我们热情地让进毡房。狗不愧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看到主人的态度,眼中的敌意迅速地褪去,摇动着尾巴表示热烈欢迎。
毡房里弥漫着浓烈的酥油和羊毛的膻味,环绕四周放置着箱柜和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穹顶的中间有一个小天窗,阳光像探照灯似地投射进来。男主人放牧未归,毡房里就老阿妈一人,她请我们坐在毡房中央一块漂亮厚实的大地毯上,兴奋得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儿子,一边说话,一边用那慈爱的目光毫不掩饰地凝视着我俩,又一边忙不迭地取出几样食品,放在面前的小木桌上。最多的是酸奶疙瘩,这是牧民的主食,很酸很硬,需要慢慢啃。还有一种叫“乌鲁木其克”的甜奶疙瘩,在晾晒时没有撇去酥油,非常好吃,是奶疙瘩中的上品,只有稀贵的客人才能享受到。最稀罕的是方块糖,在那个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里,即便是城里人也难以吃到,何况在这个偏僻荒凉的戈壁草原上。老阿妈呀!您一年才能吃到几回方块糖?您是用几只羊换来的?您将这几块糖珍藏了多久?您把一颗最真诚最善良的心捧到了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的面前。
此时,虽然我们已坐在帐篷里,避免了太阳的直射,可身体仍然像火球似的,我们最渴望的是“水”!由于语言不通,我们比划着手势,要喝生水,被老阿妈坚决地拒绝了。一会儿,牛粪火上的茶壶吱吱作响,老阿妈沏了两碗滚烫的奶茶,又撒了一小撮盐。我们接过茶碗,迫不及待地喝起来,滚烫的奶茶难以下咽。正当我们心急火燎的时候,只见老阿妈从门边一个阴暗的地坑里,拖出一个鼓鼓的羊皮口袋,又将一根木棍探入口袋,使劲地搅动着,口袋里发出咕咚咕咚的闷响。随后,老阿妈将皮口袋中的白色液体盛了满满两大粗瓷碗,递到我们面前。我懵懵地猜测着这是何物?到底是师傅见识多,他小声说,酸马奶子,好东西。我小尝一口,又酸又凉,还有一股强烈的酒味。虽然口感比较刺激,身体的感觉却爽得难以言表,强烈的酸凉和极度的焦渴真是绝佳的搭配,丝毫感受不到平时喝极酸凉饮品时后脊梁升起的那股寒意和冷战,却有效地中和了体内过多的热量,解渴降暑的功能远胜于普通的白开水。我俩不约而同地痛饮起来,简直就是在灌,直着脖子往下倒。一大碗下肚,放在桌上,阿妈盛满,又一饮而尽,再盛,再饮尽。如此三遍,三大碗酸马奶子下肚,灼热的身体凉下来了,焦渴的器官滋润了,浑身上下透着一个“爽”字。我们用手掌在茶碗上方虚罩一下,按照哈萨克族牧民的礼性,表示不再喝了。
老阿妈一直慈祥地注视着我俩,见我们恢复了生气,开心地笑了。多么熟悉的面容啊!每次母亲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时候,也是这么开心。不知何时,大黄狗也悄悄地卧在了我的身边,用脑袋乖巧地在我的腿上蹭来蹭去。显然,它已经把我当成了自家人,没有丝毫的隔阂和戒备。我拣起一块甜奶疙瘩放进嘴里,细细地咀嚼着,品尝着那浓郁的奶香。我望望阿妈,瞧瞧黄狗,环顾毡房四壁,沉浸在浓浓的亲情之中。这是我的家吗?我真的有点不忍心和阿妈告别了。我知道,今天分别后不会有再见的日子,也许明天阿妈就会随着老伴游牧到他方。我取出了随身的一小袋莫合烟,这是牧人喜欢的一种力量很大的土烟。我双手恭恭敬敬地捧到阿妈的面前,请她转交给没见面的老阿爸,此时的心情绝不是送礼,而是虔诚的孝敬。阿妈欣然接受了。我想,当阿爸拿到戈壁滩上难以得到的莫合烟,有滋有味地抽起来时,阿妈一定又会开心地笑起来。
多少年过去了,老阿妈那慈祥的面容常常浮现在我的梦乡里,让我重温人与人之间那种纯朴的真诚和友善。我虔诚地祈祷能再给我一次孝敬阿妈的机会,真诚地祝愿哈萨克族老阿妈能永远地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