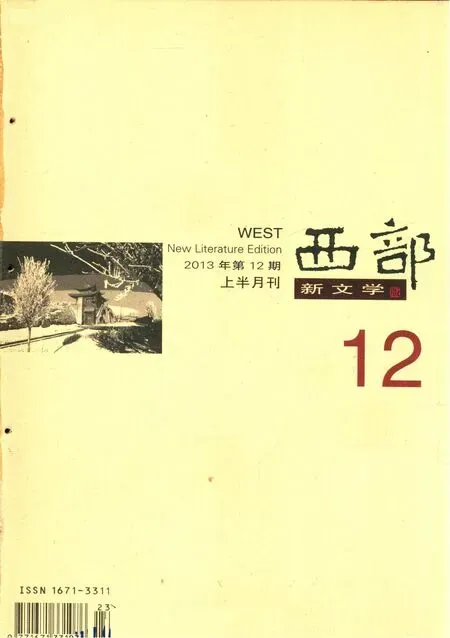老屋
六月冷雪
老屋其实也不算老,80后。要是80后的人,正当风华正茂,但土木结构的80后房子,已经是风烛残年,破败不堪了。即使它摇摇欲坠,也充满了深刻内涵。它是我童年的摇篮,也是我们颠沛人生的记录者、见证者。尽管我已有了新家,心却常常以飞翔的姿势抵达目所不及的老屋,如果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就是随我一起遁入天堂……
据说东方女人对娘家的心理依赖深入骨髓,无可救药,无论她的婚姻如何,无论她的财富怎样,父母亲的家,永远是她的避风港,甚至是百科全书,由此可见,为老屋写一段文字,情有可原。
风残烛年的老屋
深秋,父亲的祭日,一个夕阳晕醉的傍晚,携久别老家十年的母亲,来到了这个养育过我的家。
这个“家”,实际上成了贮存废旧物件的地方,斑驳陆离,体无完肤。钥匙一直由邻居大哥保管着。打开上锈的锁子,推开门的一刹那,女儿脱口一句“还是姥姥家的味道……”,刺激了我某个敏感的神经,翻江倒海般的滋味涌上来,伤感、悲痛像图钉一样扎进心里。
潮湿的房间,地上长满了青苔,借助一丝光线,依稀可见完美的蜘蛛网网住的大苍蝇,悬挂在大衣柜上面的墙角。女儿拿了数码相机,在阴冷的屋子里拍照。
母亲立在衣柜前,絮絮叨叨地说,这个柜子上的水银镜,是你姥爷坐在毛驴车上,用毡裹着从县城抱回来的,就怕一路颠簸打碎了。女儿好奇地说,打开来看看里面有没有宝贝。母亲说,哪里来的宝贝呢,里面是你姥爷穿过的一件棉衣,再就是些乱七八糟。
母亲一面说着一面找钥匙。我说,钥匙早就丢了吧。母亲回答道,不会,就在那个茶叶盒子里。
果然,在写字台上盛茶叶的硬纸盒子里找到了衣柜的钥匙。
双开门的衣柜,各有两把钥匙,不打折扣地帮母亲开了柜子。离开这个家,只弹指,不敢一挥,十年还是没了。十年间,那么多是是非非都忘了,只有我们长年累月在电话里陪伴的母亲帮我们记着;那么多该丢的或者不该丢的东西都丢了,母亲仍然帮我们收藏着。
透过被蒿草尽情攀爬缠绕的老屋,犹见当年父母在家忙碌的身影,弟弟们打闹的喧哗,牛羊撒欢的欣欣向荣。还有月季两三朵,各色菊花几盆,倒挂金钟一盆……檐前青石被滴水侵蚀,虽少了几许大宅门里的奢华,却也不乏温馨和质朴,同时也蕴藏着一个家族的风风雨雨。
生活在流年里改变,我们背叛的同时也诋毁着自己的所作所为,唯有母亲替我们坚守着……夕阳渐渐消失,正如再也回不去的那些年,感觉就像一场节目已到剧终,幕布缓缓拉过来,掩盖了一切精彩。
忠贞不渝的百花草
因老屋的铁栅大门日夜紧锁,那些被雨水冲进来、随风刮来的草籽,跋涉千里万里来老屋的院子里落户。
夏天随工作组下乡时,特意来老屋看了一次。茵茵绿草还有各色小花,像哈萨克族能工巧匠的绣花地毯,被院子里夏潮的特殊土质精心滋养着,就是人工草场也未必如此旺盛、如此绚烂。
那些茂长的蒲公英、灰灰条、芨芨草、太阳花、艾草,还有油菜花等等,知名的不知名的,爬满了所能爬上的旮旯拐角,不择手段地疯狂蔓延,就像顽皮的孩子,烂漫天真,争先恐后地以强大的力量在水泥地缝隙、裂开的墙角、房顶上、屋檐下肆意绽放。
让我肃然起敬的小草,我们不居住的这些年里,在家的每个角落,撒播芳菲。也许,花草知道我们不会再有第二个童年,也不会有第二个故乡了。它们忠贞不渝地为被我们冷落的家园贴上特殊的标签,花花绿绿,红红火火,以便我们归来时还能感受生命的气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想为老屋的院子里开放的或者已经走向生命尽头的小草流很多很多感激的泪,浇灌那些意犹未尽的明媚,使它们长长长,使劲长高成天下一方永恒快乐的绝唱,长成一个季节不死的灵魂。
我弱弱地问小草,这是一种温柔的自我囚禁吗?之所以不能理直气壮地追问,是因为与小草相比,人类要脆弱得多,冷酷得多,也无情得多,我们对小草不求回报的守候是有歉意的,至少,我要代表所有家人,向尊敬的小草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和问候!
其实,弟弟们陆续迁移到哈密的新家以后,就有人上门来买房子,出于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母亲和弟弟执意不肯出卖,结果这里就成了小草们诗意栖息的好地方。
母亲小心地踩着衰草枯萎的枝叶,房前屋后看了又看。最耐人寻味的是后院里那些东倒西歪的棚圈的名字,什么花羊圈、黄牛棚、耷拉耳朵驴的槽,雪花母鸡下蛋的窝……几乎每个生灵都有特点、有名字。母亲一边自言自语念叨着,一边探进半个身子挨个查看。其实里面除了铺天盖地的草、灰尘、蜘蛛网,或许还有乱草丛里偷窥的老鼠,荒芜得令人心寒。如果说有,那就是随着母亲叫出的名字,黄牛、花羊、雪花鸡的影子在脑海里鱼贯而出……
盘根错节的白杨树
在母亲的眼里,老屋的每一个物件都是有故事的,就像那一排白杨树也有来历。
“这些白杨树是你从学校里拿来,你爹种上的。”母亲悠悠地说,并仰视十多米高的白杨树。它们在空中泛着金黄,相互缠绵着。
没错,那些年,父亲每年夏天都要砌院墙,砌得快,也倒得快。因为房子建在大河四渠泉水溢流的地带,春天地下水上升,院子里毛驴车走过也会渗出水来,人走在上面,晃悠的感觉很玄妙。当初修房子的时候,队长就建议父亲把宅基地移到干燥的沙梁上去。父亲看中老屋东边的一片空地,说空地便于弟弟们停车,宁可不辞辛苦砌院墙,也不挪窝。后来,事实证明,父亲的决策有前瞻性。
不知父亲听谁说,院子里种上树就会把地下的水吸干,房子和院墙就有了安全稳固的保证。刚开始插了些柳树枝,结果全军覆没。后来学校购进五年龄的树,校长特批了十几棵,父亲精心管护,施肥剪枝,不几年,灼灼长势迅猛,茂盛成林,院墙果然不倒了。大树根深叶茂,不仅吸纳了地下四周的水分,也招来了麻雀、喜鹊、布谷鸟,路过的大伯婶子也要进来在树下乘凉、聊天,院子里鸡鸣狗吠,好不热闹。
母亲贤惠好客,迎来送往邻里乡亲,不在乎进进出出端茶送水。父亲在树下用芨芨草编筐子,编能编的所有,包括鸽子笼。这个画面牵动了我跃跃欲试的写作冲动,无奈笔力乏弱。假期,大树下,恶补读书不多的缺失,痴迷张笑天的《回来吧,罗兰》。暗夜,为躲开妈妈催促睡觉的唠叨,头顶一床被子,拿上手电看至天明,又至夕阳西下,碎碎阳光斜斜穿过树叶,洒在书上,晃得眼花。母亲下地除草已归,我居然忘了母亲让我也一起去除草。母亲埋怨了一阵儿见我没反应,顺手将我捧着的书甩了出去。看着大鹏展翅一般飞向房顶的书,我大哭,捶胸顿足,就像翻搅五脏六腑。那种伤筋动骨的痛,何以承受?父亲无言,上了房,在邻居的草垛上找到了书。破涕为笑的我拿了书依旧沉醉其中,不过,多少有了些收敛。立志做文学梦的我,感谢母亲那红颜一怒,若是当初投身进去,日后必将备受煎熬,不能自拔,每每想起就不寒而栗。
在生于斯长于斯也养育斯的村庄里,父亲仙逝,老屋终究也会成为废墟。想想经年后,再也没有吸引我的那一盏灯,再也不会有温暖我的人为我做一切,遥望里,只剩刻下幸福、爱和被爱年轮的白杨树,盘根错节,犹如我的家族,更像我复杂、苦恋、破碎、无处安放的心,还有无法释怀的眷恋依依……
写到这里,心太痛,不能继续……唯有老屋山一样的念想在心中屹立,就像看完皮影戏里的《长恨歌》,散场时,怅惘而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