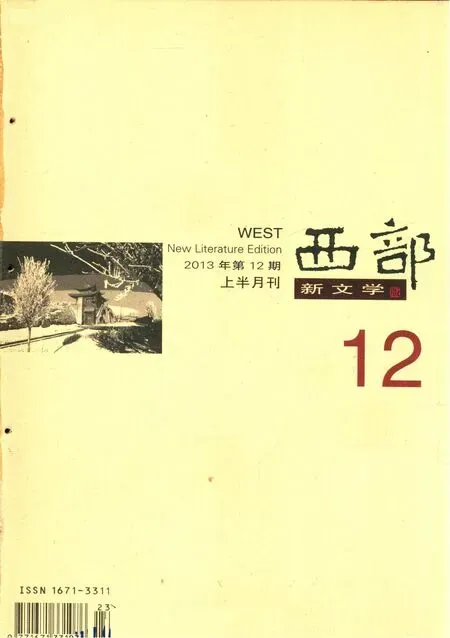剧场里的世界
孟潇
《斯特林堡的世界》
斯特林堡,作为一个多重身份的艺术家,他的整个创作构成了一个路途遥远的迷宫。瑞典导演沃尔夫·德拉肯博格则为我们修筑了一条通往百年前斯特林堡剧场的隧道,通过那一古老铃铛的响声,领我们回到那个充满魅力和焦灼的剧场。我们扮演了一百年前悄悄潜入剧场的观众,通过他们,小心窥视斯特林堡与演员排练时的情景。
他们是斯特林堡最真纯的后裔。想到一个族群以他们的诗人和艺术家为珍贵,就让人心神摇动。这种世代的精神传续让我想起另一个族群的一首古歌:“我从城堡带回珍宝,我把它们放在手绢里带回来了,这手绢里有悲伤的味道,我把悲伤放在手绢里一起带回来了……”年轻的演员奥曼小姐和古斯塔夫松先生在剧场里捡拾并且玩味斯特林堡的那些珍宝,他们的排演把我们带到了百年前斯德哥尔摩的亲密剧院,也把他们此刻的忧伤与欢乐带给了我们。
这出剧俨然是那些文本片段的小型集会,《朱丽小姐》、《父亲》、《鬼魂奏鸣曲》、《一出梦的戏剧》、《奥洛夫老师》、《古斯塔夫三世》,斯特林堡的这些著名戏剧的片段在这出戏中的缀合似乎遵循着一个不断破裂的情感逻辑,“我”与“你”不断地分崩离析,而后辈的演员们却在典雅的突围中一点点理解自身,一点点知解对面的人。
斯特林堡那些谜语般的戏剧纸条在讲述着怎样的秘密呢?
一个身着黑色礼服、戴高顶礼帽的人等在散场的出口处,等待着每一个从他身旁经过的人,从他盛满斯特林堡戏剧纸条的礼帽中拿到一张。斯特林堡总是通过写小纸条的方式指导批评演员的表演,他直率、不留情面,让演员难堪。此刻的礼帽里有:“整个生活就是重复。(《一出梦的戏剧》,1902年)”;“人活到二十岁时,已经解开世界之谜,到三十岁时开始思索它,到四十岁时发现它是不解之谜。(《福尔孔家族的故事》,1899年)”……我拿到的纸条上句子很短:“一只聪明的老鼠一定有很多窝。”是1884年他写给一个叫卡尔·奥托·伯尼尔的人的。我不知道这个卡尔是谁,我对这个有关老鼠的纸条有些沮丧,尤其是听到有人对着手中的纸条念出:“我的火是瑞典最炽烈的。”我把纸条揣在兜里快步出门,不再作深想。
但一转弯,在那个有点凉的夜空中,我分明看见了一双狡黠的眼睛冲我嬉笑着——生命中的某刻,总该有大地上最平朴的领受吧。愿你度过惊奇而安稳的一生。
《椅子2.0》
观众席空置,暗灯。表演场上旧椅子围坐呈环形。不同式样、材质的椅子——明式的、意式的,木质的、布面的,方形的、圆形的,小板凳、靠背椅、轮椅、摇椅。还有沙发、垫子、蒲团、婴儿推车……错落摆放着。
“你可以选择一把自己喜欢的椅子。”领座人说。
于是,我有了一场轮椅上的观看。几百把面目不同的椅子,来自不同的故事境遇,在剧场真实纪录的时间里,静静地等待着遇见另外的故事。在椅子故事开口说话之前,观看者并不知道谁将开口讲述,以及谁是下一个讲述者。隐于观众中的演员和法官一样的导演坐落在椅子故事的一个个节点上,尤内斯库的《椅子》仅仅被导演王羽中保留在开头和结尾两个微小的段落,而整部戏的主体部分却继承了尤内斯库或者说戏剧文学之于人类情感最深切的几个问题:童年忆旧可以夺回暴力的青春期丢失的尊严么?记忆和叙述能够挽留住亲人的生命么?最私密的情感经历可以被公开叙述么?一个生者可以如何讲述自己的死?戏剧可以伤害演员么?戏剧的伦理是什么?
法官导演起初逼问,最后遭遇反诘。没有人预先知道戏剧的反方向行走会有怎样的结果。这是一次对纪录式戏剧的用心探索,《椅子2.0》提供了一个私密的空间,人们重新面对面,重新拥有对面交流的欲望,还有耐心。在离开那把陌生的椅子之前,那些生命中无助、不知所措的时刻重新回来。在戏剧的无数次上演之时,讲述者一点点把自己从溺毙的时间与情感中救起。戏剧时间不再是供演员挥霍的时间,而是猛枭般反向扑来,一点点销蚀你性命的时刻。
你是下一个讲述者么?你如何可以抗拒时间和情感对你的磨损,还是你只是接受它?忠实于变幻的记忆就是忠实于真实么?选择性记忆或者选择性失忆是可能的么?语言会是你与自身永恒的距离么?你真的能够听见自己以至听见别人么?内心的声音可能被讲述出来么?你是一个真实的人么?你真的可以选择如何度过你的一生么?
人生是有命运的,还是并无命运可言?
《美好+安妮的肖像》
可以这样弹出或者唱出,或者舞蹈。两种不同形式的自传性表演,通过音乐摩擦形体来呈现自己的状貌。
从未见过有人这样弹奏钢琴,当佩尔·格朗杰把钢琴这个中等体量的乐器当作一座“山”来“攀登”或者“翻越”时,我无法想出演奏会始于哪一个动作、哪一枚琴键,甚至暗想也许不会有什么弹奏了,隐晦艰涩的步履、呼吸、节奏就是有关“美好”的全部,一个轻薄享用的身心遽然沉重,而处于一个可视的哲学命题中。但是,但是,当第一个乐音响起时——尽管它无比艰难,跋涉千山万水才被艰难地按下,这个来自安徒生故乡的《美好》(I want it to be so well)还是显出了它与《小美人鱼》的亲缘关系。那种美与艰难,背反式地互生。肢体与乐音延展出新型的关系,以一种私人的、与身体和乐器为伍的孤独方式,略显艰难的行为与有呼吸的音乐一并生长而出。可以用光打出一张凶暗的脸,发出自天而出的音乐人声。
《安妮的肖像》(Aline not alone)则以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更轻松地呈现了一个旅居丹麦的舞者的生活状态。她灵巧的舞步,似乎是在六弦琴琴弦之间跳跃,在琴弦的颤动中灵活地躲避,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如羽毛飞舞,她的挫折、喜悦,跟随者音乐摆动的肢体,凝成一个个美的瞬间,被剧场里的眼睛所铭记。
这不仅是作者的自传,也该是我们的。
两个人的《常识游戏》
《常识游戏》试图探索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可能性。在市场关系之外的封闭剧场里,进行一次实验。开场舞台上摆放了大大小小的物品:一斤手擀面,自行车链锁,半块大西瓜,水龙头,布熊娃娃,不锈钢菜刀,一小块粉水晶,马桶刷,马桶刷底座,一枚胸针,一个钥匙扣,跳绳……一对只穿着内衣的男女开始逐一询问,并赠予看起来最需要的人,然后向观众租借衣服,支付报酬,之后以更高的价格偿还……似乎是传销的模式,观众不断地用自己的“常识感”积极响应。高潮段落是剧本的拍卖,通过契约精神,传递一部戏剧的非独家演出权。
其实,在入场前被朋友提醒“今天会有礼物”时,就开始想象那种剧场里的赠予会是怎样的。当我收到可以壁挂储物的长竹筒时,就隐隐预设着这个竹筒礼物在剧场情境里特别的流动。一直忐忑地以为拿到手里的礼物最终会回到戏里,但那出想象的戏从未开始。赠予在他们询问“谁要这个?”并递出去时就结束了。而这样的结束直到有人端着小型电饭煲礼物提前离场时我都无法相信。惊异于戏剧的扮演与假定性被如此打破。《常识游戏》作为戏剧并不好看,但体验却极其特别。
可以送出几十样礼物,可以把卖剧本收入的使用权让渡给在场投票的观众,这出戏引来欢笑、紧张、怀疑、惊喜,却如此严肃、准确地测试出了创作者和参与者的“常识”指数。这个由瑞士的劳拉·克劳兹与马丁·希克两个人组成的剧团在各个国家的剧场演出中拍卖着剧本的演出权,《常识游戏》以这样的方式展开、传递并延续,实在是对虚构与真实最特异的重写。在演出的结尾,我内心的忐忑变成了对劳拉和马丁这两个创作者的羡慕。是怎样的相遇和交谈让剧场诞生了开放剧场边界的《常识游戏》?又是怎样的观看以及或意外或理性的参与赋予了这个大的戏剧礼物真实的流动?最终,其实并无终点,拍卖剧本的所得的钱,两位演员征询意见,获得了在场的观看者的十多种提议,而“把拍卖所得分给所有在场的女性”这一提议票选获胜。尽管我很希望“大家一起去购物”的提议被票选通过,但二十五元钱,当我攥着分得的二十五元离开剧场的时候,我感到我获得的是有关艺术自由最真实的确证。
在演后谈里,演员说起在一个地方,那里的观众最终通过的提议是“大家一起租车到海边游泳”,于是在离开剧场后,演员和所有愿意的观众一起到了海边,一场真实的海中畅游让戏剧在无尽的生活真实里蔓延开来。这实在是一场令人欣喜的畅游,即使是在异地此刻的想象中。一种更切肤、更诗意的确证该是如此吧。
妈妈给竹筒顶了一只南方的斗笠,这会儿它像小妹妹一样立在窗口。
小丑角高拓的《想象的世界》
世界一流的小丑剧!
即使是电影里出现的小丑,与这个法国演员比起来,也会灰头土脸败下阵来,因为跟剧场相比,影像太冰冷了。一个人,靠精彩绝伦的口技和动作,虚拟出一个想象的世界,却如此真实地拨动着每一个观众的心弦。无论是嚼泡泡糖、打球,还是英雄救美、大战老怪,都是一个小丑,或者一个小孩儿重要的内心戏。而从观众席随机挑选出的女孩、小孩儿、青年、老人在朱利安·高拓(Julien Cottereau)的渲染下对角色的迅速进入,完全构成了小丑剧的游戏精神。这出口技默剧是完美的。它无时无刻不在宣布着人也许微小然而美的可能性。它无时无刻不在显现着超凡而有控持的自由。没有任何布景和装饰的舞台有着最多重的世界,这个自由变换的世界在高拓这里却奇异地单纯。每个人都在创造着独一无二的相遇,他不断地邀请偶然的观看者走到台上与他一起开启世界,而我那时多么希望自己被选中,成为那无限可能的一部分。
高拓的小丑剧表演抵达过地球上最贫困的地区。这个地球上许多地方的大人和孩子都因为高拓的表演而开怀大笑,无数人童年时依靠想象构筑的巨大世界在记忆深处被唤醒。高拓请每一位观众用食指抽打手心,啪嗒啪嗒的响声让剧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小丑高拓在“雨”中不停地旋转舞蹈,他明亮的旋转引领着我们返回曾经亲历过的最快乐的游戏时光。
当高拓让所有人的食指与手心合鸣出一场“雨”时,我意识到从进入剧场的那一刻我就和所有的观众一样被选中了。这从来的、最初的对人的信心,只是被避匿,却从未远离我们自身。高拓相信,并且看见它们。高拓轻轻地划开这个世界,指给我们看——他只是这样,轻轻地,走到你的面前,微笑着,把你请出来——你就像他一样自由了。抛球,瞄准,打扫,看见狗,或者舞蹈,你就是这世界终将自由的确证。剧场里升腾的美感被所有人共同造出的一场“雨”保有。无与伦比的高拓!
《如梦之梦》的套层空间与牵引人
讲述梦是难的,因为梦往往难以追索。多重而变换的空间,以及特有的时间节奏是梦境通常的特点,在梦中清晰的线索在梦醒时往往变成谜题。大多数的梦都是会遗忘的,不被遗忘的梦只有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才会被讲述。梦的捉摸不定与它谜题一般的属性成了人生最通常的隐喻。几乎没有人能越过对梦的着迷。《如梦之梦》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对人生这多重而变换的梦境做整一搬演的尝试。
四面八方的舞台,东西两方的套层,让分属不同时空的人并置叠合、相与交错。较赖声川之前不同时空并置的戏剧作品《暗恋桃花园》更为复杂的是,《如梦之梦》把一部分观众投置在戏剧梦境的中心,而剧中所有时间的流动与空间的发生都围转在观看者的四周,并上下腾挪。需要不断旋转座椅的观剧体验也许是前所未有的,但置身于戏剧梦境中心的不安被外场更大的观看强化并放大。
一个偶然的因素使得我观看上本与下本时分别坐在“莲花池”与外场前排。理想的观剧点“莲花池”本就是这出戏的起点,但外场观看的庞大存在使得身处庐山中心的观剧体验变得滑稽了——作为特殊的一“池”人中的一个,我时时感到来自不同方向目光的复杂意涵,以及此种处境中天然的表演性。我是在下本外场自在的观看时才真正体会到了多层时空于戏剧舞台上的自由流动,因着外场观看拥有着身处中心无法全视的立体全景。这出戏意义的草图受启于在印度菩提伽耶赖声川对信众围转舍利塔的观看,“一个更属于心灵的场所”是赖声川对这出戏最初的想法,因而,《如梦之梦》本就是一出为戏剧中心的置身体验定制的环绕立体梦境,但艺术与梦想的现实间距为这个令人向往的心灵场所提供了更复杂的姿态和颜色。
我无法判断这种复杂性是丰富了戏剧梦境,还是间杂了它。但对下本的外场观看让我最终安然入梦,清晰堕入连套故事的牵引里。医院与妓院,本是生死、离别最职业、最惯常的地点,但好的故事却是从惯常处起波澜。从医生严小梅开启了五号病人的故事时间开始,五号病人成为这个套层空间所有故事的牵引人,他连缀出了他妻子的故事,他与妻子的故事,偷渡到巴黎的江红的故事,他与江红在诺曼底的故事,伯爵与上海女人顾香兰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像梦的空间一样,互相牵引,互相叠合,一百多个不同命运的人物,因由一个又一个故事互相关联、互相映照,相遇或者分离。无论是江红的故事,还是顾香兰的故事,她们的被讲述都起自于——一个刚工作的医生剥离冷硬的职业外壳,以一个人的面目来面对一个终日卧床的五号病人。
演员将虚弱苍白、满腹生命创痛与疑惑的五号病人扮演得淋漓尽致,在一个洁白意诚的新人面前,他像是一个被唤醒的传灯者,将人世代传续的心灯于熹微之刻重新启明。如果说那个寻找病因、追索顾香兰的自己更像是梦境的话,这个医院里虚弱的讲述者则更接近此刻的现实。因着他的讲述,所有已经死去的人都重新活了过来,他的妻子和儿子,杜象伯爵,顾香兰……而五号病人更像是生与死的节点,他于濒死的边缘,以娓娓叙述牵引出北京、巴黎、诺曼底、上海不同世代的微末个体于大时代中的生与死,他以自身死日的隐然可见托出了他人生一世最可记忆的生死故事,而这些连缀而出的故事最终遇合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都给不断新生的人以生的启示。
生的启示在这出戏里最具体的物象是烛。这一物象是这个多重戏剧空间与故事讲述者心象的最显在凝结物。五号病人请新医生下班带来的蜡烛是这出戏剧心灯烛照人生的起点。那片杜象古堡旁“看见你自己”的湖水是心灯的另一种映照,伯爵、顾香兰、江红、五号病人,都在那里接受过生之训示。最终,故事最初的讲述者五号病人带着死的坚定给予新生者生的意义,在五号病人的一吸一呼间,一世的烦恼与不快都被接纳了,人与自身最终达到和解。
最后,《如梦之梦》留给我们的是,那个环形舞台上所有人手执的一柄柄烛。那烛照虽是微弱的,却是世代传续且不息的。而执灯者的目光,正如同那烛照。
盼望另外一种《柔软》
《柔软》上演了,我看见装束打扮都近似黑暗的人拥进剧场。去观看孟京辉、廖一梅的戏剧成为都市文艺小众互相辨识的小标志。尽管保利剧院的名号、形制让一些亲近小剧场的观者有些尴尬,大剧院还是以一个天上地上近乎满座的难见盛况宣告了孟京辉制作的巨大效力。然而在剧场角落里观看这个庞然大物,我还是感到一阵阵的虚弱。庞大的场景装置,旋转转场的翻雨覆云,冷硬地分割着并也连接着微小,像一片巨大、通透而机巧的空洞。廖一梅尖厉且坚毅的自语,人心直指,却恍然贴错了意义形式。无疑,这是孟京辉和廖一梅互相赠予的最好礼物,一想到世上共同生活的人可以这样一起生活,就让人觉着生活是值得期盼的,可我在心底仍隐隐地盼望着一种另外的《柔软》。
无可否认的是,场景装置、光影声响与演员们的肢体腾挪,造梦一般拼合出异质于日常的情绪境域。开敞的二层隔间,圆周相接的病室与问讯窗口,层层套叠地出与进入,让戏场成为谜一样的宫殿。但是,廖一梅的心里并不居住着一个公主。在《柔软》中站立着的是一个对生命谜题充满知觉与提问的小动物。她剖开心门让你短暂窥见心尖上的一点,从这一点说,灵兽一般的女演员是好的,我感到她在柔软的通路上一点一点地向敞开走;她需要微小细密的时间节点来止息,从这一点说,玄空而有节度的音乐是好的,巨制的场景旋转因了它而有些轻盈;她需要静极而小的场地来庞大旋转,从这一点说,形制的大物是无须的,它并不会强化坚毅,它只洞开虚弱,肿胀至碍手碍脚,其中的人只显现无力和微小。这样讲来,它倒是像为大剧场量身定制的景观剧。于是苛刻的我试着理解这种定制,与众多景观剧不同的是,它精致,节制,内源细密,但是,但是——那些心底里的句子是需要被小声说出,小声被听见的,我不知道廖一梅在惊讶与喜悦之后是否会有一点别的想象。或许那种微小与虚弱正是导演所意于凸显的?或许对可见之灵的障碍是逼至极处而至虚空的外化彰显?我不知道。
如若不是看完《柔软》后的第二天,我又看了一场英国TNT剧院的莎剧《奥塞罗》,或许就不会有这篇文字。那个来自戏剧故乡的《奥塞罗》繁重而轻盈,生命腾挪的轻盈呈现,沉厚的历史无掩于新鲜的生命,有想象力的灯光准确干净,舞台简洁却饱满。我想象着廖一梅会在安闲的某刻小声对孟京辉说“也许《柔软》还会有别的样子”。
当那些身体最隐秘的地方被分割、被裸露,置于发着白光的叙述中的时候,孤独的凉意在荒原的幽暗之地也会开始发光,一种生命意志的微光最终是暖色的,它将给予一种微弱的暗示。小声说出,以及小声被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