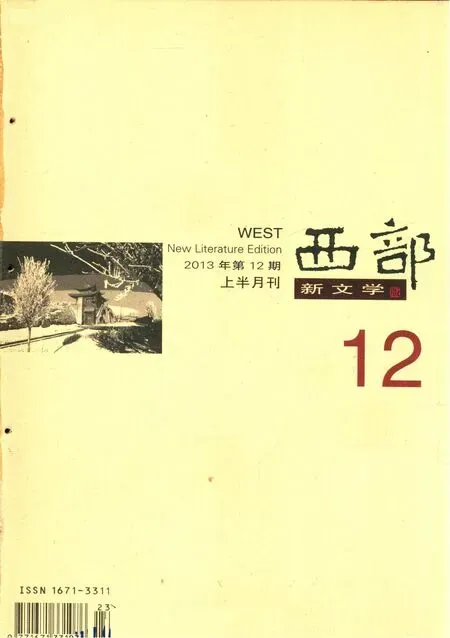与狼为邻(节选)
杨春
一
我们那排房子的人是勤劳的,勤劳又勇敢。
最西边三间,住着一家放牧的。大家都是一家一间正房,想盖个偏房、门房什么的,都得自己想办法,见个缝插个针,还得赔着笑脸跟左邻商量,再跟右舍讨论。他家独占三间正房,愣是没人有意见,不但没意见,见了他家的人,特别老李叔,都是三分谦让七分赔笑的,就是连长、指导员见到老李叔,也先把笑容挂在脸上:“老李,山上又闹狼灾了,你带几个人去看看?要注意安全。”
“老李,食堂没肉吃了,去戈壁滩弄几只?”
老李青海人,大人管他叫老李,老婆婆也管他叫老李,孩子管他叫老李叔。老李叔长得高,从他家门房出来进去都得低下头猫着腰,他老婆得伸出手踮起脚才能够着门框上方。我爸一米七,总是站在远处跟老李叔说话,因为我爸不喜欢仰视人的感觉,但我知道,我爸一样佩服老李叔。
大伙出门都步行,或者骑自行车,老李叔出门骑马,枣红色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
大伙去大田里锄草耕作,脸朝黄土背朝天。老李叔去戈壁滩放羊,羊群吃草不用人管,老李叔四处游荡,自由自在。
大伙一年四季吃萝卜白菜,难见荤腥。老李叔家一年四季都能飘出肉香。这肉可不是老李叔放牧的牛羊肉,羊是连队里的公有财产,是有数的,处置权不在老李叔,就是病死了一只、被狼咬死了几只,羊肉可能进了连队的食堂,也可能流窜到连长、指导员家的锅里碗里,老李叔却不能随便拎回家,也不能想送给谁就送给谁。
老李叔的老婆张姨是甘肃人,喜欢吃洋芋,野兔肉和洋芋一起炖,呱呱鸡肉也和洋芋一起炖,黄羊肉也和洋芋一起炖,狐狸肉也和洋芋一起炖,炖得肉烂汤浓,别说吃了,远远闻着都受不了。何况我家锅里碗里除了包谷窝头,就是萝卜白菜,清汤寡水的。
一次,张姨在我碗里盛了一些土豆,又加了几块暗红色的肉,我一咬:嘿,又滑又嫩,真香,赛过天上的龙肉,赛过地上的驴肉。我问是什么肉,张姨说:“小鸡肉,吃吧,好吃。”我吃了一碗还想吃,一点儿也没用脑子想想,才刚春天呢,母鸡都还没抱窝呢,哪里来的小鸡吃?我吃饱了走到水井边喝凉水,李家的大闺女牛牛喊住我说:“吃了老鼠肉喝凉水会拉肚子。”
二次,我赶紧折回去问牛牛:“吃的是老鼠肉?”
牛牛的两条鼻涕正越过嘴巴,流到下巴,她用力吸了下鼻涕,用力咽下,又用力点头,又忙着用手比划:“老鼠这么大,和猫差不多大。”
我一阵恶心,想吐,可胃里反出来的东西还是挺香的,我不舍得吐,又咽了下去。我想,这么好吃的肉怎么能是老鼠肉?牛牛是傻子!
又一次,我五岁的弟弟去李家叔吃肉回来,一晚上不睡觉,就在屋里蹦,从地上蹦到床上,打几个滚,又从床上蹦到地上,又从屋里蹦到屋外,到屋外抓雪吃,吃雪也不管用,还一直喊热:“热呀热,妈,我热死了,心里着火了。”半夜还流鼻血了。我妈急得去敲卫生所的门,半夜卫生所哪有人?我妈又要去敲卫生员家的门,我爸说:“别去了,去也没用,热性散了自然好了。”我妈只好自己想办法给我弟止血,用凉水冼身子,用棉花塞鼻子。到天亮,我弟的鼻血止住了,我家半床被子的棉花没了。
到天亮,我妈去找张姨,我妈说:“这么大一点儿孩子,能给吃狼肉?狼肉热,吃坏你赔我儿子?”
张姨说:“我没给他吃,肉煮在锅里,我喂猪回来,肉没了一半……”
张姨说:“我也怕呢,叫老李再别打狼了,狼肉又腥又不好煮,可老李说,狼是祸害呢,要除害……”
二
“狼肉能吃吗?”我问。
“狼肉香,就是不能多吃,身体受不了。”我爸说。
“狼心不能吃,吃了要命。”老展叔说。说着,老展叔瞪了我爸一眼,又瞪了老李叔一眼,又瞪了老刘叔一眼。我爸、老李叔、老刘叔就都笑了,哈哈大笑,都快笑到桌子底下去了。老展叔急了,抡起板凳要跟人拼命。我爸一看,赶紧放下手中的扑克牌,跟老展叔夺板凳,然后四个人就打成了一团。
他们四个本来一起打扑克牌,说说笑笑得挺高兴,我问了一句话,就打起来了。
祸事是我惹的,还是“狼肉能吃吗?”这句话惹的?我可不明白,等我明白了,我已经长大了。
我爸说:“我翻过字典,狼心狗肺是形容人的心肠像狼和狗一样凶恶狠毒,却很少有人知道狼心真的有毒,不能吃。”
我爸、老展叔、老李叔、老刘叔,文革的时候,他们站在两派,我爸、老李叔、老刘叔一派,是老牛是被斗争的一派,老展叔是革命派,手里有枪,是造反的那一派。我爸说那时的老展叔威风着呢,厉害着呢。老牛们打土块,每天三百块,老展叔做监工,一块也不能少;老牛们打柴禾,老展叔不仅不打柴,还把我妈给我爸煮的鸡蛋抢去吃了;老展叔还给人带高帽子,还批斗人,还打人,还不让人睡觉,还不讲理,还霸道。我爸、老李叔、老刘叔天天想着治老展叔。
一次,有人打了一只狼送到食堂,狼肉煮了大家分着吃了,狼的心肝肚肺按惯例埋了,埋在食堂边的林带里。为什么埋?谁也不说,谁也不问,反正都是这么做的:狼的肠肚下水一准不吃,挖坑深埋,当肥料,人不吃,也不让狗吃,给树吃。
吃狼肉的时候,没见老展叔,一问,开会去了,明早回来。我爸朝老李叔挤挤眼,又朝老刘叔歪歪嘴,老李叔、老刘叔心领神会,埋头吃饭,笑藏在心里呢。
夜里,老李叔放风,我爸打手电,老刘叔挥铁锹,狼下水没埋太深,三下五下就挖出来。老李叔从一堆大粪烂泥中捡出狼心,拿到水井边洗了,又连夜煮了,单等天明老展叔回来。
狼心本来是极大的一坨,一煮缩了,变成暗红色,像一只加大号的羊心,也像戈壁滩的一块花石头。狼心摆在盘子里,盘子放在窗台上,太阳照在窗台上,也照在我爸的眼睛里。
早晨,我爸一睁眼看到狼心,觉得那狼心还“怦怦怦”地跳呢,血管的暗影在狼心表皮枝枝丫丫乱走乱拐,莹亮莹亮的,好像有液体在里面跑来跑去。我爸惊出了一身冷汗,一蹦子从床上跳起来,用盆子扣住狼心。
狼心切成了薄片,老展叔拍拍老刘叔的肩,说:“不错,知道了孝敬领导了。”其实,老展叔比老刘叔还小呢,个子也比老刘叔矮。老展叔拍老刘叔的肩膀,手抬得老高,还得踮起脚。我爸和老李叔躲在窗户后面偷看,好笑得不得了,又不敢笑出声,就都抱着肚子蹲在窗下,憋着笑。
老展叔说:“不错,羊心切得挺薄。”
老展叔说:“拿瓶醋来,我就喜欢吃羊心。”
老展叔说:“他妈的,这羊心真有嚼头。”
我爸、老李叔、老刘叔不敢走开,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人吃了狼心会怎样。狼心和狗肺有毒,不能吃,那是口头上的传说,没人真正吃过,也没人见过吃完狼心会是什么样。
我爸他们害怕出人命,老展叔再不好,也是一起来新疆,一起开荒一起打柴火的战友。再说了,杀人偿命,这道理人人都懂。
我爸、老李叔、老刘叔轮流到老展叔屋里探视。老展叔住平房单间,我爸、老刘叔、老李叔都是“老牛”,一起睡地窝子的大通铺上,“老牛”进老展叔的屋子得喊报告。
“报告,水开了?”
“报告,要下雨了。”
“报告,狗跑了。”
“报告,树上落了几只乌鸦。”
我爸、老刘叔、老李叔轮流去喊报告,一个人喊报告进去看情况,另两个人守在门口听动静。
开始,老展叔还应几声,一会儿就只有哼唧声了,再一会儿就趴到床上去了,在床上也不老实躺着,滚来滚去,哼唧声也是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像杀猪,一会儿又像是咽气了。
我爸他们吓坏了,也不喊报告了,都冲进屋子。
眼看着老展叔的脸胖起来了,先是起来一点儿,又起来一点儿,像是给自行车车胎打气,又像是在吹气球,眼看着就要冲破皮肤爆炸了。说要爆炸,也并不真炸,有篮球那么大时,老展叔的头停止膨胀了,“脸色”的变化却一直在继续。老展叔原先皮肤黑,被太阳晒成黑红色,间或几个红疙瘩,间或几块肉瘤,间或几个黑痣,还有几处麻子。渐渐地,那脸由黑红到酱紫,到紫红,渐渐地颜色变浅,有些透明,又有些光亮,连皮肤后面的血管也隐隐约约地瞧得见,这些疙瘩呀、肉瘤呀、黑痣呀、麻子呀,凸的不凸了,凹的也不凹了,全都平平展展的,就像气球上洒满了红的黑的染料。
我爸说,头膨胀时只注意头,怕老展叔的头会炸开,心提到了嗓子眼。头没炸开,才看到老展叔的身子也一起胖了起来,撑得衣服都快裂开了。
老展叔圆咕隆冬地躺在床上,像一只刚刚吹饱了气的,准备刮毛的死猪。一般这时,猪都安静了,一声不吭,老展叔不是,他一直在哼唧,时大时小,一直在喘气,时粗时细,腿脚乱踢乱动。
我爸赶紧去找医生,也不去连队卫生所找:卫生员感冒发烧都不会治,还能瞧这病?我爸跑去大田找。“老牛”中间有一个学医的,姓徐,私下里大伙叫他徐医生,据说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家庭成份不好,走资派,被下放到新疆兵团,大伙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找他治。
徐医生一看就知道是中毒了,问吃什么了,谁也不敢说,都说不知道。徐医生急了:“不知道怎么治?”我爸才说是狼心。徐医生松了一口气,说:“送团医院打两天解毒针吧。”
我爸不信:“打吊针能好?”
方案一:给爷爷做的小台灯利用了家里报废的旧台灯做外壳,将内部的零件都拆掉。在灯罩内用硬纸板固定两排并联的led灯泡用来照明。led灯泡亮度高,省电。将导线从支撑杆内连到底座里。底座里面固定废弃的手机电池,电池串联开关、二极管2后再和led灯连在一起。二极管2是用来分压的,大约分掉0.7V。没有二极管2,手机电池电压为3.7 V,led灯泡电压3.0V左右,led会很快烧掉。太阳能电池板是两块串联使用,连接二极管1后直接接到电池正负极上就行了。太阳能电池板用线固定在底座和支撑杆之间。图2和图3是给爷爷做的台灯的正面和背面照片。
“能好!”徐医生说。
三
不久,我就见到了狼,一只小狼。
我不知道那是小狼,以为牛牛家的狼狗新生了狗娃子。那小东西真漂亮,眼睛大大的,耳朵挺挺的,身子软软的,跟一只猫差不多大。我跟它玩了好一阵子,还把它抱在怀里揉来揉去,用嘴亲来亲去。它嗷嗷地叫着,伸出小舌头舔我的嘴巴,露出小牙齿咬我的鼻子。
那个时候,我们可没那么多事做,不练钢琴,也不学书法,也不做奥数题,我们就是玩儿,在树林在戈壁滩疯跑,抓蛐蛐,捉蝴蝶,抓四脚蛇,该吃饭时,自有妈站在家门口喊:“回家吃饭了!”妈妈们不喊名字,但我们一下就能听出是谁的妈妈在喊谁吃饭,听到的人自会跑回家吃饭,吃罢饭,又跑出来玩儿。
傍晚的时候,我们玩捉迷藏,一个人站在门房前闭上眼睛数数,数到一百就去捉人,捉到所有的人才算赢。躲藏的人各尽所能,有躲柴火垛后面的,有爬上房顶的,有跳下兔子坑的,有蹲在鸡窝里的,不管藏在哪儿,越隐秘越好,越难找越好。
那天,我蹲在鸡窝里,鸡粪味很臭,母鸡们不喜欢我,用嘴不停地啄我,还跑到我脚上拉屎,我憋着气,等着人来找我。可直到公鸡母鸡都睡了,我的腿蹲麻了,也没人来找我,他们忘记我了,各自回家睡觉了。我爸我妈也没来找我,他们以为我在家睡觉昵。
我爬出鸡窝已经半夜了,我看着天上有一个月亮,圆圆的,像一只白盘子。我路过牛牛家的柴火垛,听到一阵嗷嗷嗷的叫声,那声音又细又小,像婴儿哭,又像小狗叫。我借着月光寻着叫声,在牛牛家柴火垛后面的栅栏里,看到了一只小狗。
我摔了一大跤,我腿疼,坐在栅栏里哭,可我哭了一会儿发现没人听也没人理,就不哭了。小狗也不撞栅栏门了,小狗跑到我身边来,蹭我的脚,舔我的脸,咬我的鼻子。
我睡着了,可是我睡得很不踏实,我似乎听到什么地方有不少的人在讲话,一阵喊声,又一阵喊声,却又听不清,只觉得是在北边羊圈,或是在西边养猪场,或是在猪场和羊圈之间的马号。到底是在哪儿,是在羊圈、猪场还是马号,那都不大清楚了。
我似睡非睡地听了一会儿又听不见了,大概我睡着了,小狗在我身边也睡着了。
我是被人摇醒的。开始我以为是小狗在咬我,等我睁开眼,才发现是我妈在摇我。我妈的样子很奇怪,一边摇我还一边哭,好像怎么了似的,好像我要死了似的。
我听我妈在骂我爸:“怎么能让孩子跟狼睡在一起?幸亏昨晚人多,把母狼打跑了,母狼找来了,还不把孩子吃了?”
我越听越糊涂。
什么?狼来了?
什么?狼要吃小孩?
我糊里糊涂地从我妈怀里爬起来,跑去外面看究竟。二高第一个告诉我:“你跟小狼睡了一晚,母狼找来了,到羊圈咬死了几只羊,又在猪圈咬伤了一头猪,又跑到马号什么也没咬着,一晚上全连的人都出去打狼了,可热闹了,就你不知道,你和小狼睡在一起呢。”
“小狼呢?”我问。
“小狼放了,连长让放了,说如果不放小狼,我们连的羊就要遭殃了,我们连的人也要遭殃了。”二高说着,还向我眨眨眼。
“小狼呢?”我追问。
“不告诉你了吗?小狼放了,母狼把小狼带走了。”二高气呼呼地走了,他好像对放小狼这件事很生气,可我很开心。
“好呀,小狼放了。”我跑去柴火堆看,又跑去树林看,又跑去羊圈看。
我听牛牛妈说我:“那丫头命硬,跟狼睡了一晚,母狼都没找着。”
我又听红明妈说我:“这孩子大难不死,你想呀,哪有母狼找不着小狼的,一闻就能找着。”
我又听我外婆说我:“女娃胆大,能跟狼睡,走到哪里都不会被人欺负。”
可是,我又奇怪了,我看到的明明是只小狗,它还舔我的嘴巴,咬我的鼻子呢,如果是小狼,我的鼻子还能在吗?我摸摸鼻子,有些后怕。又想想那个小东西,月光下,眼睛亮亮的,耳朵尖尖的,身子软软的,真可爱,分明是只小狗,怎么是小狼呢?
我想了一天也没想明白。
后来,我不想了,因为电影来了。
放电影的叔叔开着小四轮,拉着放电影机,拉着胶片来了。放电影是全连每个人的大事喜事。我欢天喜地去俱乐部门前的操场占位子,又欢天喜地地搬凳子,又欢天喜地地嗑瓜子,一点都不管别人看我的眼神,也不听别人说我的声音。
那天放的电影是《马兰花》。“马兰花呀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儿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小兰多漂亮,大兰多懒惰,老猫多可恶。
突然有人喊:“狼来了!狼来了!”接着露天电影院就乱起来了。
“狼?狼在哪里?”我在荧幕上找狼,可是,荧幕上只有雪花,连老猫都没有了,电影也不放了。
场面特别乱,有人喊:“狼来了!快打狼呀!”有人喊:“看好孩子,别让狼叼走了!”有人喊:“母狼找小狼来了!”
这时,我反应过来了,是真的“狼来了”,母狼来找小狼了,就是昨晚跟我一起睡觉的那只小狼。可是,小狼不是放了吗?母狼不是把小狼带走了吗?
“二高是个骗子!”我恨恨地想。
我一下兴奋了,跑着跳着去看狼。别的孩子也都兴奋了,乱哄哄地往林带边跑,跑到林带边就都站下了,先跑到的再不敢往前,站在那里张望,大呼小叫:“狼!好大的狼!”后跑到的也站下,伸着脖子踮起脚想看个究竟,可是前面有大人挡着,有高个子挡着,也大呼小叫:“狼在哪儿?狼在哪儿?”
不仅孩子,大人也都兴奋了。大人们有急急忙忙跑回家拿棍子、拿刀子的;有大呼小叫喊孩子的,怕母狼把孩子叼去了;有慌慌张张跑回家看猪圈鸡圈兔子圈羊圈的,怕母狼咬死自家猪鸡兔羊。
不仅人,狗也兴奋了,全连的狗都在狂叫,在操场上串来串去的,拴在家门口的也叫。狗狂乱的汪汪声,人乱七八糟的叫喊声,相比之下,母狼长一声短一声的嗷嗷声,倒显得较镇定。
我跑得快,先冲到林带边,想走近些看个仔细,可大人挡着我不让我过去。手电的光亮在夜空上晃来晃去,空中和地上一样乱,大人们已拿来了刀子棍子绳子准备杀狼打狼绑狼,还有人高叫着要去找枪。
母狼站在林带边的高埂上,嗷嗷地叫着,强光照着它的眼睛,反射出绿莹莹的光,让人心里一阵哆嗦。谁也不敢靠近狼,大人也不敢。狼的身后是黑漆漆的树林,树林后面是广阔的大戈壁,狼只要一转身就能跑掉。我心里对狼说:“那么多人,那么多狗,你打不过的,快跑吧!”可狼没听见我心里说的话,它不跑,它就站在高梗上,它嗷嗷叫着,向人要自己的孩子。
这时,广播里喊:“谁抓了小狼,快还给母狼,快把小狼还给母狼!”“老李!小狼没放吗?快还给母狼!”
“快还给母狼!”
“还给母狼,母狼就走了!”
“老李,小狼呢?小狼呢?”
“小狼不是放了吗?”
杂乱无章地有许多声音,然后广播里老李叔喊:“庆庆,你个兔崽子,让你放了小狼,小狼呢?”
“小狼呢?”“庆庆,你个兔崽子,快放了小狼!”人们在喊。
庆庆急急忙忙在人群里跑,后面紧跟着二高和大明。庆庆嘴里乱七八糟地喊“让开,快让开”,怀里有一只嗷嗷乱叫的小东西。
立即有一条道让了出来。
庆庆一个趔趄摔了个嘴啃泥,小狼崽从他怀里挣脱出来,奔向妈妈,欢快地叫着。
我还不知道小狼崽能跑那么快呢,小狼崽长大了,才一天功夫。
母狼对着夜空叫了两声,嗷嗷嗷的声音吓退了每一个人,拿绳子来的人不敢上前,拿棒子来的人也不敢上前,拿刀子来的人来不敢上前。后来,听我妈说,连长是尸人呢,连长找来了一支小口径步枪,连枪栓都没打开。
母狼叼起小狼,走了。
四
不久,我又见到了一只狼,一只公狼。
狼被五花大绑着,四条腿绑着绳子,嘴上拧着铁丝,右腿还拖着一个大铁夹。带铁夹的腿好像是折了,软软地耷拉着,腿上脚上后屁股上全是血,血和泥的混合物凝结在一起,黑乎乎的。
我们都去看狼,都不敢靠近,在七八米之外围成一圈。两个胆小的孩子爬上门房,从房顶上居高临下看狼,他们说:“牛眼看人大,所以牛怕人;狼眼看人小,狼不怕人,狼吃人。”
“狼吃人?”我听着很奇怪,我们总是吃狼肉的,却从没听说过有人被狼吃了。
我去问我妈,我妈只是笑,不说话,问急了就打我一顿,还推我出门。我妈总是这样,她不懂的事,就不让我问。我又去问我爸,我爸说:“狼很厉害,又残忍又凶恶,狼吃羊还吃人。”
“可是,我们总吃狼肉呀?”我还是不明白,我爸就不理我了,我爸被老李叔叫去商量剥狼皮的事。
我又跑去看狼。
狼一动不动,也不去舔腿上的伤口,也不看人,也不看狗,狼只睁眼着睛望着天空,好像腿受伤了没什么,被人绑了也没什么。
我们一堆孩子围在一起看狼,都站得远远的,谁也不敢走近。我听庆庆说:“你们谁敢用棍子戳一下狼的屁股?”
二高说:“怕什么,狼嘴绑着呢。”二高就去柴火垛找了根长棍子,去戳狼屁股。二高一步一步靠近狼,我们的目光一步一步靠近狼。棍子碰到了狼屁股,狼动了一下,抬了一下头,眼睛转向二高。二高的棍子一下了掉在了地上,狼的眼睛转向我们,我们轰一下后退了几步。我感觉我的两腿抖得厉害,都快站不稳了。又有人用石子打狼,狼又动了一下,眼睛转向打它的人。打它的人一个趔趄,差点儿被脚下的石头绊一跤,我们又轰一下后退了几步。
狼的眼睛可厉害了,它只看着你,就够你心惊胆战的了。
我问庆庆:“狼哪儿来的?谁抓的?”
庆庆说:“当然是我爸,我爸一个人不行,还有二高他爸。”
“狼那么厉害,你爸怎么把狼绑住的。”我还是很奇怪。庆庆说不清,我又去找我爸问。我爸和老李叔、老刘叔他们在一堆说话,是在说捉狼的事,我就站在一旁听。
狼有狼道,蛇有蛇踪,每只狼都有自己的领地。老李叔、老刘叔放牧的那片戈壁东边一个狼窝,西边一个狼窝,平日里,两家狼各过各的日子,相互不侵犯,也不去对方家探访做客,也不去对方的领地捕食。
牧人在戈壁放羊,也不怕狼来吃羊,戈壁有的是黄羊野兔呱呱鸡能捕食,又有老鼠四脚蛇来果腹。狼知道保护自己的家园,一般不去招惹牧人,也不去袭击羊群。
老李叔说:“狼最怕牧人捉他的狼崽子,只有饿极了,没办法了,才会来捉羊吃。”
可人不那么想,人不会想:“狼不侵犯我,我就不侵犯狼。”人也不会想:“人和狼和羊能和平共处,共享大戈壁。”
人愿意捕捉狼,狼肉可以吃,狼皮被褥真暖和,狼骨可以入药,狼牙狼髀石挂在身上做装饰,是无上的荣耀。人愿意当狼是敌人,人愿意相信“狼是戈壁的祸害”、“狼的本性要吃羊”、“狼和人和羊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这类的话,这样,人捕狼杀狼吃狼肉就是保护羊群,就是行善事为民除害。
老李叔说:“我们和狼相处得好呢!我们不去惹它,它也不来惹我们,远远看见,我们还打招呼呢!晚上听不到狼叫,我还睡不着了呢!可我爹的老寒腿犯了,得有个狼皮褥子。”
我越听越奇怪,老李叔的爹老寒腿犯了,干狼什么事?难道是狼让老李叔爹犯了老寒腿?
老李叔要捉狼,要做狼皮褥子孝敬他爹。老李叔在泉水旁下铁夹子。
戈壁中的泉水不是裸露在表面,也不汩汩而流。第一次到戈壁的人弄不清哪里有泉水,泉眼在哪儿,第一次到戈壁的人渴了也不知道挖开泉眼找水喝,即使看到一片梭梭红柳比四周的都要茂盛,也找不着泉眼的位置。
泉眼在哪儿,牧人知道,黄羊知道,狼知道。
老李叔在泉眼周围下夹子,一天夹到一只野兔,一天夹到一只黄羊。黄羊带走了夹子,老李叔追了五六公里才找回夹子,带回被夹伤了的黄羊。又一天,李叔只在夹子上捡到半只野兔,另半只没了。老李叔断定是狼来了,狼来喝水,吃了半只野兔。
老李叔决定抓到这只狼,剥狼皮给爹做褥子。老李叔换了一个大铁夹,把铁夹藏得更加隐蔽——狼比野兔比黄羊可聪明多了,不容易被夹上。
狼上了牧人的圈套,夹子夹住了狼,狼带着夹子跑了。老李叔不敢让狼跑太远,狼跑远了,狼得空就能咬断自己的腿,重新获得自由。牧人们都知道,三条脚的狼再也别想捉到,狼不会上第二次当;老李叔也不敢一个人去追狼,狼可大可凶呢,一个人肯定没办法对付狼,捉不上狼反被狼咬伤的事发生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老李叔喊了老刘叔一起去,两人拿着棍子绳子刀子鞭子,寻着狼夹子的拖印,寻着狼血的印迹去捉狼。
老李叔、老刘叔追了十几公里,才追到狼,狼还没得空咬断自己的腿。人和狼对峙了片刻,人先败下阵来。人不敢冲上去打狼,即使狼拖着铁夹子,即使狼受了重伤,即使狼疲惫又虚弱,人也不敢直接去打狼。
但人比狼聪明,人有的是办法。两个人骑着马赶着狼走,狼拖着铁夹,铁夹后面带着沉重的铁链,走得慢,人拿着大棒子,吆喝着,不让狼向着它愿意去的方向走。他们把狼赶到一所房子里,或者一处石头垒的羊圈里,或者一个山角的死角处。
那天,老李叔没有把狼打死,因为老刘叔说:“活狼剥皮,毛顺。”他们决定先把狼打晕了,活着带回连队。
打晕了狼,老李叔、老刘叔可不敢大意,带活狼回去他们还是第一次,如果狼半路醒了呢?如果狼半路跑了呢?老李叔、老刘叔花了很大功夫把狼五花大绑,狼腿狼脚都捆结实了,狼头也用马笼头套住了,老刘叔还不放心,又用铁丝在狼嘴上拧了一圈又一圈。
老李叔、老刘叔把狼抬上马背,绑好。也不敢像驮一只黄羊回家一样,人羊共骑,快马加鞭一会儿就到家了,他们牵着马慢慢走回家。
果然,狼半道醒了,挣扎得很厉害,在马背上乱动乱踢,马受惊了,挣开缰绳撒开腿跑了。狼掉下马背,绑狼的绳子却没有松开,马就拖着狼跑。老李叔心疼狼皮:“再拖,狼皮就毁了。”老李叔跳上另一匹马猛追,老李叔马技好,一下子就套上了惊马。
老李叔、老刘叔又抡起大棒,把狼打晕,总算把狼活着带了回来。
我不听他们讲捉活狼的故事了,因为我听不懂。我又跑去看狼,狼瞪着血红血红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我心里一个哆嗦,后退几步,蒙上眼睛藏在门背后。
我站得远远的,替狼想事。我想狼可能会想:“我在自己的家里活得好好的,也不招惹你们人,也不吃你们的羊,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打我杀我?抓我打我杀我剥我的皮吃我的肉,却又骂我,骂我凶狠,骂我残忍。”
“谁更残忍呢?狼还是人?”我想不明白,可能狼也想不明白。
那天,我家分到了一块狼肉。
我妈煮了狼肉,给我一块,给我姐一块,我不吃我姐也不吃,我弟就笑我们胆小,就把我们的都抢去吃了。
那晚,我弟又流鼻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