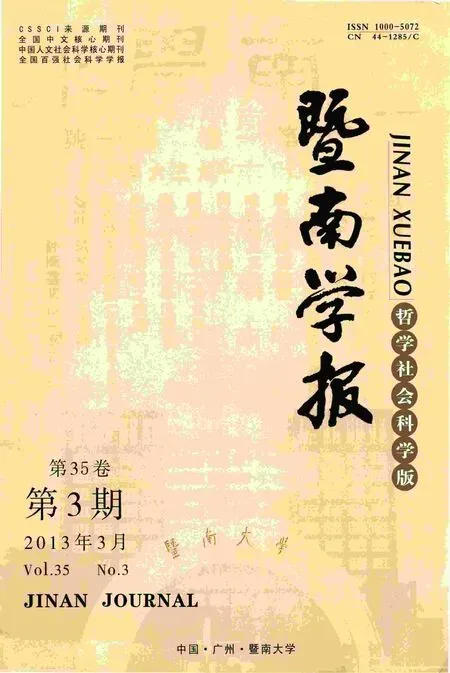《九歌》“离居”取向探微
邓妙慈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九歌》以其丰富的内涵催生了文本解读的多样性。许多人以“人神恋爱”或“神神恋爱”作为《九歌》的解读主线,诚不失为一种见解,但却有将其平面化、庸俗化之嫌疑。恋爱情节仅是《九歌》的表层书写,不足以概括《九歌》的深层内涵,能够深入展现《九歌》内涵且成为其研读主线的应是《九歌》的“离居”取向。所谓“离居”取向,表层上指《九歌》诸神由对现居地的不满而衍生的远游的渴望及行动,在深层上则是由爱情理想、生命意识、求知情结和自由诉求交融而成的产物。“离居”取向不仅是探究屈原内心世界的指南针,同时也是一枚记录上古时期楚文化的活化石。
一、“离居”取向的三种模式
除了天之尊神东皇太一外,“离居”取向是《九歌》诸神之共性,然而此共性却因众神的性格与遭际的不同而有迥然相异的表现形式,笔者大致将其分为三种:
首先是因觏人间声色之美而对重返天庭生出抗拒心态的,这以云中君、东君、大司命、少司命为代表。他们都是于人间一番周流遨游后,顿起红尘之想,却又不得不返回天庭,当此之时,他们感喟深沉忧伤莫名。当云中君“猋远举兮云中”之际,发出了“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的悲怨之音。东君出场气挟风雷,但当他的人间之旅结束时,竟“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太息将上,言神若有所感而不暇留。低徊顾怀,言神若有所恋而不能去。”“思灵保兮贤姱”,和云中君一样,东君已对人间祭巫动了真情而不愿离去。“乘清气兮御阴阳”的大司命同样有着儿女心肠,“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王逸注云:“离居,谓隐者也。言己虽出阴入阳,涉历殊方,犹思离居隐士,将折神麻,采玉华,以遗与之。”洪兴祖云:“离居,犹远者也”。王注强调了大司命情感上的“思”,洪说则从空间上点明了大司命距所思之人的“远”。凌厉英武的大司命于离合聚散之际亦无计可施,乘龙冲天,离别所思,空余远者“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之慨叹。有女如云的祭坛前,少司命独与一祭巫目成心许,但他“入不言兮出不辞”、“倏而来兮忽而逝”的举动却令祭巫无限伤怀,当祭巫问他“君谁须兮云之际”,他道出了自己的心愿:“与汝沐兮咸池,晞汝发于阳之阿。”可见他先前的离去确是情非得已。他居住于凡人无法企及的“云之际”,而他所向往的却是“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且芳菲袭人的人间堂室,正可谓所居非所愿。
此四篇中神祗的“离居”取向颇为相似,诸神因邂逅人间声色而顿生红尘之念,而他们的爱情追求又无一例外地以悲剧收场,《云中君》和《大司命》更是明显地笼罩着一层怅惘悲怨的生命哀感。它们共同传达的是人神均不能逾越自己的地域和职守,这其实就是人间礼法在虚幻神界的真实映射,情礼冲突下的自由诉求和爱情追寻终以悲剧收场。
“离居”取向的第二种模式是因约会而产生的离居行为以及由这种行为衍生的更强烈的离居心态。这以河伯和山鬼为代表。《河伯》按照陈子展的说法,当是“男水神约女水神同游九河,而企待女水神之即至。”久等不至,河伯发出了“灵何为兮水中”的疑问。水中何所有?不过“鱼鳞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同为水神,河伯所描述的女神的居所不过是他自身住所的同调,尽管光耀华美,却不是理想所在,一句“灵何为兮水中”就透露出了河伯对清冷水宫之不满。他终于把女神等来了,但短暂的欢娱后他们最终还是要各自回到寂寥的水宫中。《山鬼》爱情悲剧产生的根源在于凡界与“饮石泉兮荫松柏”的神界的交通之难。“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的山鬼好不容易与心上人相约会面,却因路险难而后来,当她到达的时候,爱人早已远去,空留山鬼一人自怨自艾。“怨公子兮怅忘归”,“忘归”容或有之,但更多的怕是不愿归,她必定对搁浅了她的幸福的居所大为不满。
代表第二种模式的诗篇同以“等待”作为母题,等待之久与欢聚之短(甚至是等待无着)间形成的强烈反差凸显了主人公迫切的“离居”企愿,居所的阻隔还造成了情人之间的怨念与隔阂。但此二篇亦有差别,若说《山鬼》中的人神交接之难尚在意料之中,那么《河伯》中的神神恋爱之苦就更强化了外在环境之压迫与束缚,从而体现出“离居”取向的必然与合理。
第三种模式是重新筑室所表征的“离居”心态,这以湘君和湘夫人为代表。“望夫君兮未来”的湘夫人不是如山鬼般翘首以待自怨自艾,她选择了远游以追寻爱情。她“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湘君则“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金开诚先生以为:“偕逝,同往,指与湘夫人一同去过美好的生活。”清代余萧客《文选纪闻》言:“(湘君)言己朝驰夕济,不离湘夫人所降之地,果闻来召,许余以腾驾偕逝。”湘君以毫不犹豫的“离居”行为积极回应湘夫人的热烈追寻,这除了是爱情的感召力外,还与湘君对其居所的不满有关,故言“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林云铭曰:“不处山泽,不潜深渊。所见之物,又皆失所宜,则所期者益不可得矣,安可不前往北渚而迎之乎?”湘君与湘夫人会合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筑室兮水中”。他们把遇合作为重新筑室的契机,“离居”是他们对原先生活的一种叛离,而“筑室”其实就是构筑一种新生活的隐喻,但很快他们就梦断南柯。“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往下,古来注家多有歧解,而笔者以为姜亮夫与林云铭两先生的解释较诸家之说更为允当。姜氏言:“上段言夫人方与湘君成室水中,而九嶷之神忽迎舜而去。”林云铭在《楚辞灯》中言:“不意山神率众,纷然迎归九嶷,暂留不得,可谓大失所望,把闻召后许多布置,尽付一场梦幻,岂不闷绝?”林氏所言被迎之人乃湘夫人,与姜亮夫所言的湘君略有出入,但相同的是,“九嶷之神”在他们的阐释中皆成为礼法与规范的表征,而湘君(或湘夫人)的“回归”也就宣示着二人爱情的悲剧落幕。
比之前两种模式,第三种模式中的男女双方无疑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但惟其坚决、热烈与果断,才显“回归”结局之空漠悲凉,也才更凸显出生命个体在礼法社会的巨大磁场中之渺小无力。三种“离居”模式可以串联为一种渐进的生活过程:偶遇——等待——偕逝。随着这个过程的演进,“离居”的企愿越来越强烈,“离居”的行动从隐到显,但礼对情的战胜、理想对现实的投诚使“回归”成为了男女主人公的必然宿命,而物失其所、所居非所愿的困境表达则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主题。
二、“离居”取向的文化心理内涵
论及《九歌》的文化心理层面,我们应该首先明确《九歌》之性质。王逸将《九歌》定性为屈原在沅湘祀歌的基础上创作的托喻讽谏之诗篇,此说至今仍有其合理之处。我们不能胶柱鼓瑟地坐实《九歌》中每句话均有微言大义,但承认《九歌》除祀歌的性质外,还有屈原自我抒情的成分,则是非常必要的。林云铭先生认为《九歌》乃《九章》之变调,“非他人祀神者所能取用”,正是敏锐地捕捉到了《九歌》的这一性质。这使《九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代言抒情之作,“代言的抒情方式造成了抒情内涵的双重性,抒情性作品中主人公的抒情是外抒情层;作者的情感表现是内抒情层。”具体到《九歌》,诸神的情感抒发是外抒情层,而屈原的主体情感则成为内抒情层。《九歌》除了爱情体验的外抒情层外,还蕴含了由生命意识、求知情结和自由诉求交融而成的内抒情层,后者构成了“离居”取向的深层文化心理内涵。
首先是生命意识。“生命意识包含浅层次的生存和深层次的生命价值意识”,在屈赋中,前者表现为对年华易逝的深切感喟,而后者则是由前者衍生而来的时不我待、功业无成的生命之痛,它们同时都是《九歌》中的内抒情层。而与此相对的外抒情层,则是相恋的人神有感于岁月不居而产生的及时追寻爱情以安顿生命的心愿。山鬼言“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大司命言:“老冉冉兮既极,不寖近兮愈疏”,都是由一种年命短暂的忧伤所带来的“但愿人长久”的强烈企愿,而爱情的失落与无奈的“回归”却使这种企愿带上了颇为浓重的悲剧色彩。爱侣难觅,纵使生者无亏皆得寿考,亦不过独听雷雨填填猿狖夜鸣。诸神之生命意识源自屈原之切身体验,强烈的生命意识贯穿于屈原的所有作品中。“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岁忽忽其若颓兮,时亦冉冉而将至。”(《悲回风》)。最典型的是《远游》:“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远游》是否屈原的作品,迄今仍无定论,笔者以为以仿作的成份较大。但无论如何,它都真切地体现了屈原由年岁之不吾与而生的“离居”渴望,当然,屈原的“离居”心愿并非出于对仙界的向往,而是渴望远离佞臣当道的楚国而到达一个可让他一展抱负的国度,“恐修名之不立”是屈原生命意识的精神内核。随着春秋代序岁月蹉跎的沉痛现实,屈原“离居”的愿望可谓日甚一日,这是屈原与《九歌》诸神精神相通之一。
其次是求知情结。卓雅在《从“九歌”中看屈原的婚恋观》一文中提出《九歌》诸神的爱情是以“心相知”为基础的,其实不然,“心相知”是作为一种理想的却不可企及的情感状态出现于文本中的。《楚辞集注》在注释《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时道:“其起兴之例,正犹越人之歌,所谓‘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湘君》有言:“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而造成“君不知”、“心不同”与“恩不甚”的窘境主要源于空间和情感的双重阻隔,空间的阻隔使得恋爱双方之间的信任感流失殆尽,如王夫之所言,乃“望之迫,疑之甚。”“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这是湘夫人对湘君发出的怨言。根据湘君对湘夫人的情感回应来看,怀疑湘君“不忠”、“不信”实在有失公允。若说“心相知”的爱情关系是九歌诸神所向慕的理想状态,那么“心相知”的人际关系则是屈原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朱熹认为《湘君》一篇是“以求神而不答,比事君之不偶”的寄寓之作,其实这是就人际关系中君臣遇合的这个层面而言的,而且范围不应仅限于《湘君》。缪钺先生认为,求知之难和感知之切,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刘绍瑾先生也称:“‘不遇’、‘不得时’,在进与退之间的选择以及选择中所带来的心理波动和痛苦,就成为中国文人最普遍、最共通也是最深刻的心理情结,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最大主题,因而也是中国文学所要表现的一个最主要、最中心的内容。”而在文学作品中肇此情结表述之端的则是以《离骚》为代表的屈赋。“求知”情结之导源首先是“士不遇”的个体遭际和群体悲剧。“忘儇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惜诵》)“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重华不可迕兮,孰知余之从容!”(《怀沙》)屈原屡屡对历史上的圣君贤臣的风云际会报以歆羡之情,以此反衬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可悲处境。胡文英云:“期不信而告以不闲,即‘黄昏为期’、‘中道改路’之意。”另外必须注意到,屈原更大的悲剧在于他与整个社会的对立,不仅是国君,而且是举世之人对他的不知不谅。“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涉江》),“夫惟党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怀沙》)就连对屈原关切有加的女媭、避世江潭的渔父都对屈原的操守与行止深不以为然,人物形象容或虚构之,但它们折射出来的人生际遇却是真实的。作为举世皆醉之下的孤立无援的独醒人,屈原处境之蹙迫与内心之孤独可以想见。可见不论是《九歌》中爱情的“求知”之难,还是屈原自身的“求知”之艰,它们皆是由于他者“莫察余之中情”所致,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离骚》)的可悲现实,也即空间上的“邃远”与情感上的“不悟”的双重阻隔,那么“离居”就成了摆脱困境的唯一选择。
复次乃自由诉求。赵辉在《楚辞文化背景研究》中有言:“在古代中国,从来没有人像道家,尤其是像庄子那样强烈地去追求自由……活跃于楚民族心目中的龙和凤不过都是庄子所仰慕的鲲鹏的置换变形。”其实不止龙凤,《楚辞》中的所有坐骑均具备着充沛的神性与灵性,它们驰骋纵横的态势本身就给人一种超世拔俗、追求自由之联想。《九歌》诸神“龙驾兮帝服”、“驾飞龙兮北征”、“乘龙兮辚辚”、“驾龙辀兮乘雷”、“乘白鼋兮逐文鱼”、“乘赤豹兮从文狸”;《离骚》抒情主人公麾蛟龙诏西皇以周流上下,亦如《九歌》诸神有着一股高蹈八荒之气概。屈原渴望如具挥戈返日之术的东君、少司命一样在楚国的政坛上自由驰骋、补罅弥漏,但楚国昏君佞臣阻塞贤路的现实使他的人生价值面临着必然落空的命运,而当时楚材晋用的社会风气又向屈原指明了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所以不论是追求抱负的施展还是寻觅精神的自由,屈原产生“离居”想法都是自然而然的。
爱情理想、生命意识、求知情结和自由诉求,它们使“离居”成为诸神和屈原最佳的人生选择,但不论是文学作品中的神祗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屈原,“回归”却成为了他们殊途同归的抉择,个中缘由,是很值得深思的。对众神而言,这是道德理性对情欲本能的超越;而返观屈原自身,则是家国伦理对个体价值的压制。中国在大一统国家出现之前,“忠”的观念还是相当宽泛灵活的,而君臣之间也是孔子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的对待性关系,且自春秋中后期始,楚材晋用、士无定邦的风气愈演愈烈,士人早已不以去父母之邦为非,但身为楚室宗亲的屈原却始终无法在情感上接受干禄异邦的人生道路。在他看来,橘树尚且“受命不迁”,何况自己身为楚国宗亲而又曾受怀王知遇呢?“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正是这种狐死首丘的宗国情怀使得他的“离居”终以“回归”为结局。
由以上分析看出,情与礼的冲突、现实与理想的内在张力形成了《九歌》中“离居”与“回归”的二重书写,这其中包蕴着屈原强烈的身世之感,于是《九歌》诸神的失恋之叹就一转而为屈原的失志之悲。
三、“离居”取向反映的社会语境
《九歌》中血肉丰满至情至性的众神形象,对中国上古神话中刚直严正、理性有余而柔情不足的神灵和英雄形象是一个极大的颠覆,它以一种全新的“离居”取向转为对人间声色和男欢女爱的向慕与追寻。不论是“人神恋爱”,还是“神神恋爱”,“神”都成了可亲可近而不复是可怖可敬的存在。姜亮夫先生从《九歌》文本出发列出《九歌》神祗特异于北土之三点:一、留恋人间。二、非可怖之神,乃与人相亲之神。三、神之爱情生活乃现实之人类生活情感也。杨纯先生在《〈九歌〉与希腊神话》一文中指出《九歌》与希腊神话在精神上的相通,其实都是着眼于《九歌》中神的“人化”而言的。从这种“人化”处理中,可窥见其时人们宗教观念和人生意识的基本态势。
这首先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天神观的变化。《礼记·表记》有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西周和春秋战国之时的天神观又有区别。“西周时期‘敬天保民’思想中的保民还从属于神,春秋时期人们无疑还相当敬神,但先进的人们在思想上有一个大变化,这就是人重于神。”《左传》桓公六年有言:“夫民,神之主也”,僖公十六年又言“吉凶由人”,可见春秋以降,神不再是万物的主宰,故无论在社会生活或文学作品中,人们都不需要再对其顶礼膜拜,神性与人性也因此取得了沟通的可能。《左传·僖公十年》记载晋申生屈死后因不满其弟晋惠公之无礼,其魂灵请于上帝,欲以晋畀秦。狐突义正辞严地驳斥了他的这种想法,他欣然改过。在这里,神反不如人正直理智,而其有仇必报的心理其实还是“人性”之自然流露,可见《九歌》中众神的“人性化”面孔确是其来有自。
其次,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九歌》中珍惜年命、追求自由、渴望爱情的诸神既然是世间俗子之写照,那么可见时人对自身存在的诸种问题都有着一定高度的理解,战国时代的诸子学派都把“人”和人格的完善作为最重要的言说主题。在重人轻神的时代大潮的裹挟下,兼之社会大变革时期政治动乱带给人们对生存的深切渴求,信巫重祀的楚人也开始了从敬畏神祇到重视人生的转变。与屈原同时代的包山大冢出土的漆奁盖圈上所绘的《车马人物出行图》是反映楚贵族现实生活的画卷,它的写实性与现实感均非常强烈,人在艺术表现中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它表明了楚人对神话世界的艺术热情已经让位于对现实人生的真切观照,同时它也标志着楚人作为人的理性的觉醒。李泽厚说:“《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原始神话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人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若将此话施之于《九歌》,也不失为中的之论,只不过在《离骚》中,屈原的人格和情操是一种显性表达,而到了《九歌》中则成了隐性表述,但它们都共同指向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最后要提出的是,神的“离居”使神人化、情感化,而他们的“回归”却是对这种人化、情感化的一种反拨,《九歌》中的这种言说语境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呢?这反映了当时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刻交融与冲突。《九歌》中情与礼的矛盾在深层上体现的就是享乐纵欲的楚文化与讲求理性节欲的中原文化的冲突。楚人是享乐主义成风的一个民族。《大招》、《招魂》极言声色之乐和人间奢华的背后,折射出楚民族对满足欲望的渴望和肯定。《左传·昭公四年》载称霸中原的楚灵王会诸侯于申,为了显示大国风范和对中原文明的敬慕,楚王还特地问礼于左师与子产,但在会盟中,却出现了“楚子示诸侯侈”的一幕,可见其纵欲享乐的意识已是深入骨髓,难以礼教文明改造之。赵辉先生就把楚民族的享乐狂欢的风气与强烈的自我意识称之为“酒神精神”。相较于楚文化享乐至上的自我意识,以儒家学说为骨干的中原文明更注重的是欲望的节制和人格的完善。翟振业在《〈天问〉与中原文化》一文中指出:“夏商时楚与中原已有较密切的联系……春秋以来,楚国的文化基本上是中原化的,当时楚国贵族对北方经典十分娴熟。”那么生活于战国时期且身为楚室宗亲的屈原当然不乏机会接受中原文化的濡染熏陶。朱熹认为屈原的辞赋“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朱熹这种论调实在有失偏颇。屈原在《离骚》、《九章》、《天问》中提及的古代圣贤,多是中原文明的杰出代表;后世班固、扬雄等人对屈原颇有微词,多缘于他们认为屈原沉江举动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也是原始儒学的题中之义,而屈原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担当精神更是与儒家文明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的教诲一脉相承。但在楚文明的土壤上孕生出来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又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屈原,所以他的“离居”之愿常在文学创作中喷涌而出。赵辉在《楚辞文化背景研究》中提出“次生形态的文化精神”一语,它的特征是“既和那种一味追求享乐的传统文化精神相对立,反对对于声色淫逸的过于追求;也和中原的那种理性精神相冲突,否定着它对于人性严酷束缚的价值取向。”屈原身上正是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次生形态的文化精神”。就“回归”结局而言,无疑是强调道德与秩序的中原文化占了上风。但回归是表层的理性,而最美丽丰满最摄人心魄的还是对离居的向往与远游所带来的生命大欢喜,尽管这种大欢喜在《九歌》诸篇多是瞬间的绽放与短暂的灿烂。
《九歌》以“离居”为线索,以爱情理想、生命意识、求知情结和自由诉求为内涵,以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融冲突为历史语境,神的地位的下降与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则是此语境的两大支点。屈原作为生命个体、伦理个体、情感个体的多重身份使《九歌》中的“离居”取向有了多元而厚重的包蕴,也让后人从中窥见个体生命在历史长廊中渺小的身影和伟大的抗争。
[1]胡文英.屈骚指掌[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79.
[2]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陈子展.楚辞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4]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屈原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余萧客.文选纪闻[M]∥陈建华,曹淳亮.广州大典·碧琳琅馆丛书:第六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
[6]林云铭.楚辞灯[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二.济南:齐鲁书社,1997.
[7]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8]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9]刘彦彦.论九歌的悲壮美[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6,(3).
[10]卓雅.从“九歌”中看屈原的婚恋观[J].知识经济,2008,(7).
[11]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2]王夫之.楚辞通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3]缪钺.两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两个情结[J].中国文化,1991,(1).
[14]刘绍瑾.文人的“表现”与文学的“表现”——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J].暨南学报,2003,(2).
[15]赵辉.楚辞文化背景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16]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7]杨纯.《九歌》与希腊神话[J].云梦学刊,1998,(1).
[18]刘泽华.中国通史教程·先秦两汉时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0]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21]翟振业.天问与中原文化[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