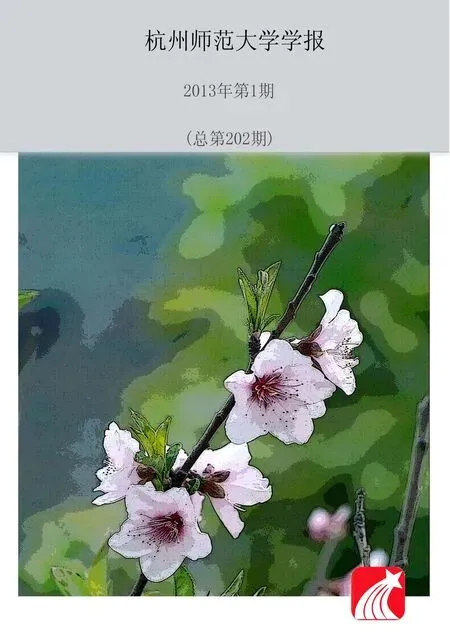滇缅公路·“摩登”·共产党人
——《纽约客》之《土司与他的秘书》系列小说
叶 子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滇缅公路·“摩登”·共产党人
——《纽约客》之《土司与他的秘书》系列小说
叶 子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华裔作家黎锦扬1958年在《纽约客》小说栏发表了系列小说《土司与他的秘书》。对照二战期间该杂志对滇缅公路的多次报道,以及赛珍珠与张爱玲小说中极其相近的文学想象,可以明晰地展现黎锦扬作为第一代《纽约客》华裔小说家的文学建构。
《纽约客》;黎锦扬;《土司与他的秘书》
《纽约客》(TheNewYorker)是一本综合类的文化周刊,它拥有全美同类杂志最高的发行量(103万,2010年数据)。从1925年2月21日创刊至今,它的热点时评、通讯报导、文化评论及每期必有的短篇小说栏目,始终保持着对地缘政治的紧密关注,引导培养读者群的自由主义文化倾向。二战中法西斯的横行使得大量作家离开故土迁徙美国,投身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在战后更为自由的媒体氛围中,这些作家的投稿得以进入曼哈顿编辑部的视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57年,黎锦扬(Lee C.Y.)*黎锦扬在家中的11个孩子里排行老幺。兄弟中,大哥黎锦熙曾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二哥黎锦晖是谱写《桃花江》的作曲家,六哥黎锦明是左派作家,七哥黎锦光谱写了《夜来香》。1926年,黎一家搬去北平。参看[美]黎锦扬《我的回忆》,载《旗袍姑娘》,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19-237页。成为第一个在《纽约客》发表小说的华裔作家。
黎锦扬1916年出生于湖南湘潭晓霞乡。1936年考入山东大学外语系,后因日本人入侵逃回长沙进入联大,再随联大文学院迁徙至云南。1940年从昆明毕业后,他在边疆芒市土司衙门应聘为英文秘书。日军攻至缅甸,趁着蒋介石政府鼓励毕业生留学,黎决定出洋。1943年,他从印度辗转至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念比较文学,因为语言上的困难,一年不到,便转入耶鲁攻读戏剧创作的艺术硕士。1947年,黎从耶鲁的MFA毕业,学了西方的基本写作技巧。此时耶鲁上演了他的两出戏,也出版了他的两篇独幕剧。黎的毕业剧作,写的是在云南为土司当秘书的经历,成为后来《土司与他的秘书》(TheSawbwaandHisSecretary, 1959)*在英国出版时被改名为《天之一角》(Corner of Heaven),黎锦扬认为此名好过《土司与他的秘书》,因多数人不知何为“土司”,“他的秘书”又让人误以为这是个艳情故事。英文初版参看Lee C.Y., TheSawbwa and His Secreta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Cudahy, 1959。台湾版参看[美]黎锦扬《土司风情》,欧阳佩君、彭中原译,台北:皇冠出版社,1969年。大陆版参看[美]黎锦扬《天之一角》,刘满贯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的雏形。
1957年3月30日,《纽约客》将黎锦扬处女长篇《花鼓歌》(FlowerDrumSong)的开头改名为《守旧之人》(“A Man of Habit”)发表。《花》很快轰动美国文坛,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这之后,黎的《土司》系列小说陆续在《纽》发表。小说共十二章,其中的五章,第一章《方土司的摩登计划》(“Sawbwa Fang's Modernization Program”),第二章《方土司的正义观》(“Sawbwa Fang’s Sense of Justice”),第三章《方土司与共产党人》(“Sawbwa Fang and The Communist”),第五章《方土司的家庭纠纷》(“Sawbwa's Domestic Quarrel”)和第十二章《方土司,斯垂蓬医生和水蛭》(“Sawbwa Fang, Dr. Streppone, and The Leeches”),自1958年7月起连载至12月。
一
《土司》系列故事发生在滇缅公路刚刚开通的西南中国。1940年,“我”来到中缅边境未开化的掸邦部落,给喜好摩登的芒市(Mangshih)土司方玉池(Fang Yuchi)做英文秘书。系列中首篇发表的《方土司的摩登计划》围绕公路开通后芒市以及芒市人的种种变化展开,“最近完工的滇缅公路从芒市穿镇而过,土司一定已经意识到,对于那些初入此地外来者,他的领土很可能被看作是一块蛮荒之地。”[1](P.50)
修建不到一年,滇缅公路便于1938年8月穿越中国最坚硬的山区,跨越最湍急的河流,在千难万险之中正式通车,它是当时最重要的一条国际高速路,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中国对外的海上通道被全面封锁,随着日军在中国入侵的脚步,滇缅公路的开通意味着“瓶子底打开了”,“后门开了”,“万里长城击通了一个洞”。*此处借助赛珍珠的短篇《泥金菩萨的面孔》中的比喻。Pearl Buck, “The Face of Gold”,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August 24,1940.中文本译名为《滇缅公路的故事》,参看[美]赛珍珠《滇缅公路的故事》,以正译,新评论社,1940年,第8页。这条高速路支撑着抗日战场的战备物资及大后方的经济供应,运输着赴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在当时的抗日文学创作中,有不少围绕滇缅公路的建设与开通展开。*更多内容参照易彬《“滇缅公路”及其文学想象》,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4期,第221-235页;李光荣《中国现代文学的劲旅——文聚社》,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第88-95页。香港《大公报》曾连载萧乾的报告文学《血肉筑成的滇缅路》(1939),而杜运燮的诗歌《滇缅公路》(1942)成为活跃于西南联大的文聚社的代表作。1940年8月,与《纽约客》相比较为大众的刊物《周六晚邮报》(TheSaturdayEveningPost),发表了赛珍珠的短篇《泥金菩萨的面孔》(TheFaceofGold)。这则西南中国人抗日救国的故事中,有大篇幅惨烈的筑路图景,“这条新路像一阵暴风雨似的席卷着这个区域,她似乎每隔几天就要加长十余里。实际上几千个满身尘埃,褴褛不堪的老少男女,好像耗子钻洞一样工作着,他们所用的锄头和竹篮担子原与儿童玩具差不多,但他们仍把这条公路迅速地而且不断地开拓出来”。[2](P.14)疟疾的盛行导致“每隔几天就要换一批工人,因为他们死得太快了”。[2](P.19)“那里,一群弱小的人类仍在工作,但衣服已半不蔽体,又都在发烧。在他探视的当儿,他还看见几个人病倒了下来。倒下去的再也爬不起来了。一个带病的身穿制服的中国人慢慢地走来,他的干枯的眼睛在那顶泥污的制服帽下显出患着热病。”[2](P.15)1940年至1942年间《纽约客》的闲话评论与新闻报道,也频频关注这条公路的种种动态。1940年3月8日“热门话题”栏的《中国记者》(“Chinese Reporter”),通过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的卢祺新(David Lu)的闲谈,透露中国苦力在滇缅路上的巨大作用。*卢祺新(David Lu)出生在纽约,12岁回到中国,先后在广东的岭南大学,北平的燕京大学及美国密苏里大学学习新闻学,是1940年唯一一个驻美国的中国报社记者,随后成为中央社华盛顿办事处主任。滇缅公路中横跨湄公河与怒江两座重要的吊桥,曾遭遇日军战机多次空袭,“日军通过炸桥来延缓交通,但总会有一两千个苦力立刻架起浮桥”。同样是这些苦力,“运送三十万吨机械深入内地。拆除了纺织厂,兵工厂,铸铁厂,将这些重工业的工厂车间一点一点从被日军占领的沿海城市迁移到内陆”,这种浩大的工程就好比“上千个劳力将肢解了一个新奥尔良的工厂,每人背一块零件,搭顺风车到明尼苏达,再组装整个工厂”。[3](P.10)
1942年1月,“档案”栏连载了上下篇的人物专访《胡适的火枪手》(“Hu Shih’s Musketeer”),记叙了传奇的货车运输专家丹尼尔·艾斯坦(Daniel Arnstein)如何使用美国的货运方式管理滇缅公路,使租借给中国价值十亿美元的物资得以运送至战火前线。[4][5]因贡献卓越,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将艾斯坦描述为三个火枪手中的硬汉“波尔多斯(Porthos)再世”。[4](P.22)胡适称,“当我撰写中国历史时,艾斯坦先生的名字一定会在里面”。《纽》记者随即补充,“既然有人认为胡适博士是孔子以来最伟大的中国学者,这番称赞确实令人钦佩。”[5](P.32)在描述滇缅公路的艰险时,记者形容在“比纽约到诺瓦克(Norwalk)*诺沃克(Norwalk),康涅狄格州的城市,南临长岛海湾。距离还短”的四十英里之内,“从七千两百英尺的海拔突降到两千五百英尺。”[5](P.23)专访不仅感叹中国苦力同建造万里长城一样,徒手建造了滇缅公路,同时震惊于这条现代公路的非现代管理方式。在中缅边境的小镇畹町(Wanting),一个和黎锦扬笔下的芒市极度相似的地方,当地土司私
自设立重重关卡,管理层混乱腐败:滞留卡车排着四分之一英里的长队,办公室里的行政人员却在阅读杂志。替政府开车的司机将国有卡车的零部件私自倒卖,“一个月挣一千到一千五百块,比部长的薪水还多”。[5](P.25)这些来自文明世界的报道对于西南中国的落后并不十分友善,虽然在战火纷飞的严酷背景之下,无数苦力正完成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毫无纪律的管理层却以极度的散漫消耗着美国给予的支援。《纽》给了读者这样一种印象,“摩登”正沿着滇缅公路涌入内陆深处,中国却并不具备与之相应的现代理念去迎接。

《纽约客》“档案”栏,《胡适的火枪手》,1942年1月10日,第22至27页;1942年1月17日,第23至33页。
在《土司》系列小说中,对于文明世界的洗礼,却有一种与《纽约客》评论报道完全不同的态度与判断。20世纪50年代身处美国的黎锦扬,将这块西方视野中的野蛮之地描绘为一个战乱大环境下的理想国。掸邦的自然条件优越,本是富庶之地,而“掸邦人是地球上最幸运的”。[6](P.209)公路确实带来了改变,“芒市突然成为滇缅公路上一处舒适的经停地”。[1](P.52)电线和电话铺设起来;原本尘土飞扬的市集开设了餐馆和公共浴室;土司娶了欧亚混血儿做小妾,开新款的别克轿车。与《纽》所记录的土司不同,方土司起初是个“改革”派,心怀摩登的改造计划。为了筹集资金,方土司启动了庞大的农业项目,征募克钦人在荒山上种植油桐树,炼桐油卖给大量需求油漆的美国人。只是克钦人因忌讳山神的集体罢工而引出种种的风波。土司对摩登规划的热情骤降,又退回到“懒惰和守旧”中去。[1](P.62)“摩登”计划是失败的,而“我”作为一个精通英语,来自摩登社会的人,本有开化原始部落的梦,对掸邦有诸多制度性的构想,却逐渐理解芒市百姓的生存方式。在《方土司的正义观》中,种种非现代性的社会制度,比如审问罪犯还用清朝衙门屈打成招的老办法,比如“监狱是不上锁的”,最后都证明比文明的法制系统更为合理有效。“三十多年芒市没有一起罪案,是卡车司机们带来了有害的影响。”[6](P.216)在赛珍珠的小说中,就提到“如今在滇缅公路上开一趟卡车比做强盗还要有利可图。在路上开两趟来回车就可一辈子衣食无忧”。[2](P.18)同样,黎锦扬用汹涌而入的卡车司机改变了掸邦男少女多的局面,掸族姑娘遭受卡车司机的引诱,搅乱掸邦小伙温和守法的性情。卡车司机不仅带来外来人“邪恶”的因子,还有中央政府发行的花哨的随时可能贬值的纸币。只信银元作流通的芒市人与“外来人”和“外来物”不断地抗争。小说的最后一篇《方土司,斯垂蓬医生和水蛭》中,和疟疾作斗争的斯垂蓬(Streppone)医生,千方百计帮助当地人减少血液中的疟疾病原虫,而掸邦人只相信延续了几千年用水蛭吸毒血的土方。分发的奎宁药片被孩童们当做打弹子的筹码,喷雾灭蚊又被看做是杀生触犯佛祖之事,西医的疗效始终没有体现,水蛭倒成了“中缅边境地区营养最充足的动物”。斯垂蓬医生与被困缅甸莽林的中国远征军一样陷入了拉锯战,1943年日本人占领芒市时他不幸染上疟疾,在逃难中丢了医疗用品,最后是被水蛭疗法“不可思议”地治好了病。
二
继续讨论《土司》系列之前,有必要再看一眼赛珍珠早了18年发表的《泥金菩萨的面孔》(1940)。这曲赛珍珠对抗日英雄的高歌,已经具有了《土司》系列最核心的人物要素。来自美国的青年传教士史坦恩作为叙述视角,和黎秘书一样是来自摩登世界的外来者,作为基督教的传教士却在佛教徒供菩萨的寺庙一住就是十年。赛珍珠当然挑选了1937这个重要的年份作为《泥》的起点,因次年便开始修建滇缅公路,而“五百年以来,大理城从未有过什么新的事情”。[2](P.7)史坦恩的父亲是卖武器给日本的军火商,史坦恩为了缓解内心的愧疚,便从父亲那里买了一万五千支枪,打算与老和尚的儿子土匪黄狼一起,从缅甸北部的腊戍运入中国,助抗日一臂之力。《泥》中最重要的便是一票绿林好汉的土匪角色。竹林寺抽鸦片烟的当家老和尚,不仅同时结合了黎锦扬笔下方土司和白云寺慈心大师来自庙堂的政教力量,前土匪帮头目的身份使他体现了一股神秘且强大的民间声音。整个故事都由当家和尚出谋划策,他通过观星预言了战事,又在关键时刻调遣了一票女土匪抢修路段,为困在滇缅公路上的史坦恩和黄狼解了围。
也许黎锦扬并没有读过赛珍珠的这部短篇,他在《方土司和共产党人》中也设置了一个故意误读的“土匪”角色。1942年,虽然战火蔓延至整个云南,在内陆深处的芒市,却“无人知晓‘共产党人’。它的字面意思是‘主张财产共享的政党成员’”,黎锦扬写道,“芒市的人们管他们叫‘土匪’(Bandit)”。[7](P.69)“共产党人”和“土匪”当然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革命”、“平等”、“共享”这样先锋的观念在芒市过于新鲜了。因此,共产党人唐同志来到了边远的西南传播共产主义,必须极具因材施教的智慧,既严肃谨慎,又亲切开朗,因地制宜地为自己设置了两个假面:面对芒市的百姓,他穿肥大不堪的紧领制服,拎着旧皮箱扮落魄;同时,他懂得取悦宠妾影响君主的老策略,陪土司的爱妾娱乐,又切换为外国军官在东方的扮相。他既有上层人脉,有省长写的介绍信,又有下层朋友,和茶房都能打成一片,称他们为“真正的无产者,社会的脊梁”。他在两个身份中切换自如,假意在芒市养病,实则暗中记录土司政权的种种黑暗面,力图全面改造掸邦人的信仰。在一篇《封建领主统治中缅边界》的考察报告中,唐同志把土司写成是“无可救药的鸦片瘾君子,有十几个老婆前呼后拥”,而“相对摩登的黎秘书,想法却远说不上进步,因他在蒋介石的反动大学中接受了西式教育的毒害。”[7](P.79)

《纽约客》“小说”栏,黎锦扬的《方土司与共产党》
唐同志得知小妾爱跳舞,便教她秧歌(Yanko Dance)。在中国南部,秧歌不是传统。这里鼓动全民性狂欢的秧歌运动,直接呼应同一时期1953年张爱玲在香港用英文写成的《秧歌》(TheRiceSpoutSong)。当秧歌喧嚣的锣鼓出现时,总是伴随着“咬啮人的饥饿”。*1953年张爱玲在香港用英文写《秧歌》(The Rice Spout Song),1955年春季在美国出版。参看张爱玲《秧歌》,台北:皇冠出版社,1976年。张爱玲的秧歌舞队被“饿”击得溃不成军。“年轻人头上扎着磺巾,把眉毛眼睛高高地吊起来,使他们忽然变了脸,成为凶恶可怕的陌生人……不分男女都是脸上浓浓抹着一脸胭脂。在那寒冷的灰色的晨光里,那红艳的面颊红得刺眼。”[8]在张爱玲笔下,秧歌舞的荒诞在于表演的集体性,在这样的集体性中,个体悄然丧失。“但是在这一群旁观者之间,渐渐起了一阵波动,许多人被挤了出来,尽管一方面抗议着,仍旧给推了出来,加入了舞者的行列……月香吃吃笑着,竭力撑拒着,但是终于被迫站到行列里去。她从来没有跳过舞,她的祖先也有一千多年没跳过舞了。”[8](P.76)相比黎锦扬温暖色调的理想国,张爱玲冷涩荒凉的中国乡村有更多无奈的表达。《纽约客》偏爱黎表达中的欢快与戏谑。唐同志将秧歌上升为农民的民间艺术,诉诸于阶级话语,因西方的民间舞蹈“已堕落为资产阶级的消遣,丧失了劳动人民的精气神”,秧歌是“耕作的舞蹈”,“用大量的活力给舞蹈注入生命力,旨在给予农民一个表达他们感情的机会”。[7](P.74)被“进步”和“革命”要挟,土司允许唐同志办秧歌舞训练班。黎锦扬笔下的秧歌舞有种滑稽的热闹,“欢腾地跳跃、踢腿、弯腰,看上去像一种英国民谣舞曲和中国太极拳的混合,再加入一点哥萨克骑兵的风韵”。[7](P.75)秧歌被善歌舞的掸族姑娘所接纳吸收,但其中的政治教化全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土司并不担心掸邦人会信他的主义,因为“阶级斗争和新思想对掸邦人民全无益处”。唐同志最终失败,因为宣传“宗教是封建主义蒙骗百姓的勾当”而犯了大忌。掸邦人的肉体服务于土司,精神上依赖宗教领袖白云寺的住持慈心大师。住持敲打法器念经,革命者东躲西藏,最终憔悴离去。唐同志宣扬先进的共产主义,最终被芒市人千百年来积累的质朴经验所抵抗。
作为围绕滇缅公路所展开的文学想象,黎锦扬“风俗录”的写法似乎有现代抒情小说的因子,也有主题上“外来的”与“民族的”、“现代的”与“传统的”对立。但黎本身又不对“国民性”、“现代性”这类大负担负责到底,他的现代意味,似乎很难被追认至五四后某一种具体的现代文学谱系中去。尽管在系列小说中大量地描写西南民间生活,但黎出身良好,始终接受着最正规的高等教育,他的“民间”混杂着笔记小说里的文人气,甚至略带一股学生腔。虽然在写作时间上与美国的“反共”相叠加,《方土司与共产党人》未必有多么深远的政治诉求。黎锦扬的写法有“将文化的鼻子伸进政治的烂泥中去”[9]之嫌疑,但也不过滚了一滚,沾点零星的泥巴便也作罢。
《纽约客》一向重视野轻立场的作风,与黎锦扬轻松的“奇谈”风格相吻合。黎认为自己在美国写中国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相对自由。20世纪90年代,黎将自己用中文写的小说编撰成集,附上几篇回忆与漫谈。《漫谈中国人的写作自由》开头便说“中国的文艺,一向有个框框,人物也有样板,说话像台词,在电影电视和舞台上,看起来不很自然。我留美四十余年,写了十一本英文小说,为讨洋人喜欢,有时也把人物写得过火。但绝不是西洋人写中国人的那种样板,驼背、暴牙,见人就鞠躬,说话也是西洋人替我们发明的英文。”[10](P.264)这番话至少说明一个问题,虽然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在耶鲁经受的戏剧创作训练中,黎锦扬似乎储备了一种夸张的舞台风格,但黎自认自己的写作是在诚恳地忠于事实地表达中国人。
黎锦扬甚至更为诚恳地表示,“凡事都有运气,尤其是写作”,自己早年写长篇,“手气”总是好的。[10](P.267)《纽约客》的倍受青睐立刻使黎锦扬在英美文学界有了立足之地。董鼎山先生曾几度表达过自己的钦仰之情:“(我)年轻时也尝试过用英文写作投稿,目标是当时最具声望的文学杂志《纽约客》。几度被退稿,我很失望。有一段时间发现《纽约客》连续发表了数篇署名C.Y.Lee的有关中国人的故事,羡慕不已。后来,我获悉C.Y.Lee的中文名字是黎锦扬。”[11]“黎锦扬的英文隽永简洁,恰合《纽约人》风格。我当时对所谓‘纽约人作者’(即在《纽约人》登载作品的作家)极为拜服,以为中国人中居然也出了一个能够入高标准的《纽约人》作家之林的写作者,而且所用的是第二语言,值得兴奋。”[12]在《土司与他的秘书》之后,一直到90年代,黎锦扬都反响平平。在今天华裔小说家与离散主题大热的中国文学批评中,已很少有人再提及他的名字。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中美关系中,回过头来重新认识《纽约客》对《土司》系列小说的关注,研究黎锦扬在这一系列命题中到底生长重塑了抗日时期西南中国怎样的一种历史整体观,就变得尤其重要。在20世纪中期美国反共的知识大语境下,《纽约客》自觉走入了一段意识形态的真空,它能够在政治领域与私人情感表达之间灵活中转。正如1957年11月30日《纽约客》边栏里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一句话:“我不认为《纽约客》的角色有那样关键,或主动。相反,它是有指涉性的——它代表了进步的中产阶级的个人态度;非常温和的态度,尽管有些松懈与单薄。”*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1975)是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此话出自他给英国作家约翰·韦恩(John Wain)的信中,摘自《观察者报》(The LondonObserver)。参看The New Yorker, November 30,1957.p.163.
[1]Lee C Y. Sawbwa Fang’s Modernization Program[J].TheNewYorker,1958-07-26:50-62.
[2]赛珍珠.滇缅公路的故事[M].以正译.武汉:新评论社,1940.
[3]Alexander J.The Talk of the Town: Chinese Reporter[J].TheNewYorker,1941-03-08:10.
[4]Bainbridge J.Profiles: Hu Shih’s Musketeer Ⅰ[J].TheNewYorker,1942-01-10:22-27.
[5]Bainbridge J.Profiles: Hu Shih’s Musketeer Ⅱ[J].TheNewYorker,1942-01-17:23-33.
[6]Lee C Y. Sawbwa Fang's Sense of Justice[J].TheNewYorker,1958-12-06:209-221.
[7]Lee C Y. Sawbwa Fang and The Communist[J].TheNewYorker,1958-08-30:69-82.
[8]张爱玲.秧歌[M].台北:皇冠出版社,1976.47.
[9]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18.
[10]黎锦扬.旗袍姑娘[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11]董鼎山.浅谈美国移民文学[J].华文文学,2006,(1):7.
[12]董鼎山.美国文坛的一件神秘故事[J].读书,1982,(9):134.
TheBurmaRoad, “Modernization”andtheCommunists—TheNewYorker’sSerialFictionTheSawbwaandHisSecretary
YE Z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Lee C.Y. is the first writer of Chinese origin who publishes fiction inTheNewYorker. In 1958, five parts of his novel,TheSawbwaandHisSecretary, were published as a serial fiction related to “Modernization” on the new Burma Road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Comparing this serial fiction with the correlated reports in the same magazine and and the writings of Pearl Buck and Eileen Chang on the same subject will give a clear demonstration of Lee’s literary construction a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American Chinese Writers ofTheNewYorker.
TheNewYorker; Lee C. Y.;TheSawbwaandHisSecretary
2012-09-23
叶子(1984-),女,江苏南京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
I106.4
A
1674-2338(2013)01-0094-06
(责任编辑吴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