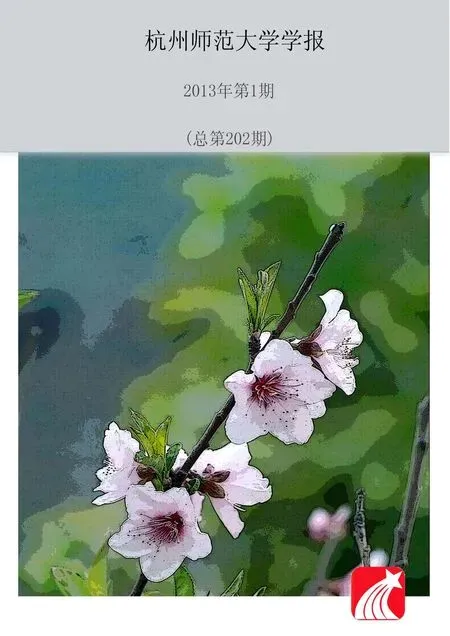当代国际舆论环境与中国形象传播
潘一禾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当代国际舆论环境与中国形象传播
潘一禾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成功的国家形象塑造可以提升国家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的正面影响力。当代信息科技和传播媒介的变革已经促使国际舆论环境发生巨变,大众传播由单向转为双向后,再次从双向转为复合传播模式;国外受众对新闻和信息的认识也出现深刻变化,主要体现为从被动获知信息到主动参与制作和发现有价值信息、组织活动、制造舆论、亲身参与讨论以影响公共事务等。“人人参与”的现代舆论环境已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跨文化交流条件,也必将促使我们更深入地研讨国内外受众的各种需求,更好地尊重中外新闻体制存在差异的客观事实。
国际传播;国家形象;新闻体制
一国的国际形象,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其综合国力与行为表现,但“从传播的角度看,则国家只有通过国际传播才能争取国外公众的理解、支持与共鸣,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树立预期的国家形象”。[1]
一 “虚拟”国家形象的内涵与塑造
现实中的“国家”除了客观物质基础,如领土、人民、国家机器、社会制度等之外,对于国内公民和国外公众来说,同时也是诸多感受、感知、印象、想象、联想,是诸多信息和符号的复杂集合。问题是,当各国人民都以相似的“我族中心主义”思维方式进行国家话语和国家形象的向外传播时,就难免出现相互误解、沟通困难和存在交流障碍的可能。如当代西方国家的新闻报道习惯于“事件取向”和“坏新闻”模式,所以他们对中国的相关报道极易让中国受众感觉是在专门挑刺、别有用心。反过来,“我们传给(西方受众)的是对国内传播、中国的普通受众最容易接受的一套方式和内容,只是处理上略微灵活了一点,西方受众对此会非常的反感”。[2]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英语专家戴维·拉思本认为,很少有人关注中国的外宣刊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于不同观点的争论很重视,但是中国的外宣刊物争论比较少,往往是一边倒地说好话。中国一向外国宣传自己,往往都会拍摄雄伟的长城,壮美的故宫,以及那些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高速发展的经济,但是外国观众对于创造这些奇迹的中国人,却很难留下直观的印象。他们更喜欢看人性化的故事。[3]
从国际传播的角度看,可以将“国家形象”理解成一类不断向国际社会传播的信息产品, “就一件信息产品而言,其价值可以分为使用价值、宣传价值、新闻价值和国际传播价值等四个层次。使用价值是指信息具有满足某些消费者商业需要或其他特殊要求的功能或效用。宣传价值是指信息具有满足某些政治或经济集团的特殊利益的功能或效用。新闻价值是指信息具有满足社会大众新闻需求的功能或效应。国际传播价值是指信息具有满足国际受众新闻需求和传播主体宣传诉求的功能或效应”。[4]可见,对于传播者而言,认识和塑造国家信息的国际传播价值,不仅要注意“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也需要注意“外外有同”和“内外有同”,还需要学习如何让这些差异和相似性通过受众理解、语言转换、符号运用、价值观体现、媒介选择使用、传播战略与策略等,得以有心应用和有效运作。
首先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期望国外受众在短期内就产生对本国形象的“客观”认识。从立体的大传播的角度看,对于国外的绝大部分受众来说,也许家里用着众多国家的众多产品,也许住处与中国大使馆同属一个社区,也许平时生活和工作中有一些亚裔邻居或同事,也许看电视电影时会看到一些银幕上的“中国人”或中国影视剧,所以当他们想起“中国”时,脑海中浮现的是中国产品、中国制造、中国功夫或者李小龙,以及由这些符号、具象和影像所共同构建的抽象意义集合。一方面大众传媒通过新闻、娱乐等方式将某国的信息传播给受众时,它们也把媒体眼中的该国形象传播给了受众,另一方面受众又会根据自己的信息需求和生活经历对这些大众传媒信息进行取舍,逐步形成对该国的一种相对固定的认知。因此,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国外受众也可能经由对某国现实的足够认识,进而实现对该国形成全面的客观认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国家的概念是无比广阔和多层面的,无论是国内公众还是国外受众,想“客观公正”地对某国“国家形象”进行把握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跨文化交流学所强调的一个基本概念。
正是基于国家形象本身既具有现实基础又具有丰富想象维度,有意从政治、外交、商贸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舆论引导和国家形象塑造,也将产生丰富的实际功能和传播效果,甚至关系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段鹏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一书针对“国家形象”的差异性建议将之分为三类:国家实体形象、国家虚拟形象和公众认知形象。他认为:对大众传媒来说,国家实体形象较为稳固,公众认知形象则难以控制,国家虚拟形象因此成为国家形象构建的主要方面。[5]郭可的《当代对外传播》一书也从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角度提出:国家虚拟形象可以概括为由国际性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和言论来塑造的媒体国家形象。[6]作为一种观念形象和信息聚合体,国家虚拟形象可以在短期内发生极大的变化。由于不同社会制度、文化因素的影响,国外受众的解码模式可能与国内受众完全不同,此时即使国内媒体根据受众需求已经定制了传播信息,也可能会因为受众原有信息符号的干扰而削弱传播效果。因此,国际传播中必须注重信息流的控制和安排,保持好适当的节奏,以应对国家虚拟形象的具体塑造。
强调国家形象的“虚拟”与实体之别,的确有助于我们通过信息和符号的有意复合与国际传播,影响国外受众的感受和感知、印象和想象。比如新加坡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成功。一般国外受众对于新加坡的国家形象,第一时间浮现在脑海的往往是“花园国家”、“清洁城市”、“小国大外交”等正面印象和想象,而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是一个政治上长期高度集权的国家。这固然与新加坡“高薪养廉”的政策和清廉的政府声誉有关,与新加坡国土狭小、对周边国家和国际事务影响有限有关,但是新加坡媒体长期以欧美人熟悉的话语方式和共享价值观,对新加坡进行正面阐述和美化包装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换言之,国家的虚拟形象也是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应该包括观念形象、媒体形象、影像形象、生活印象、产品印象等等,需要政府和民间的协同,知识界、商界与媒体业的配合,各行各业的参与和重视。
二 “虚拟”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
任何国家,包括该国的不同业界在以虚拟方式塑造自我形象时都难免会有种种美化和夸张,这种自我美化和修缮技巧也是被普遍理解和接受的。但国际传播中的策略主要体现在媒体信息的语言转换、符号创造和叙事手法之上,也就是要善于驾驭语言和信息符号而不是被符号所限制。比如类似中国红、中国功夫、李小龙、舞狮、大红灯笼、大熊猫等等,虽然是国外受众比较熟悉的中国信息符号和具体影像,但国家形象的塑造需要利用这些国外受众熟悉的符号,但又不能简单地重复或强调这类已知信息和固有印象,而是需要不断地在原有的信息符号基础上创新和扩展。尤其是根据新的国际环境变化和国际民心需求变化进行符号新意的捕捉和把握,进行符号内涵的创新和扩展。比如中国的功夫片与美国的西部片,都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类型的创新与推进,引起国内观众和国外受众的关注和新认同,这中间既有华裔李安导演对西部片的全新演绎、技惊四座,也有好莱坞《功夫熊猫》的异军突起、震动中华。
与此同时,通过丰富的文艺语言和信息符号对国家形象进行修饰或提升,也要尽可能的有理有据、合情合理,即便有基于相似的“我族中心主义”思维的优势夸大和缺陷掩饰,至少也不能引起国内外受众直觉上的反感,并要在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新导向建立和去除原有不良印象。比如中国电影《英雄》虽然在海内外均获得不俗票房和一些赞赏,但也遭遇国内外相当多的受众对其价值观表述的强烈不满和质疑。虽然现实中的中国外交反复强调自己将坚持“和平崛起”和提倡“和谐世界”,但在“观念形象”和“影像形象”上是否仍给人以传统印象则需引起重视。
仍以《英雄》为例,其故事就明显带有中国传统的“家国观”和“天下观”,展示了个人之间和团体之间的古代等级意识和君主臣仆关系模式。电影对于这些重要观念和中国概念的解说与表述,虽有票房和评论文章数目的保证,但显然未能真正获得普遍的说服力、也未能获得国内大多数观众的认可。国内外受众更赞赏的是这部电影在艺术手法上的丰富的中国元素和有力呈现,而从真正体现国家正面价值观和国家正面形象的角度讲,无论是国内观众还是国外受众都显得意见分歧,核心概念理解相当混乱,只能期待有更好的力作相继问世来予以修正和改进。
注意国家形象的“观念”、“想象”与实体之别,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外普通受众对国家形象“他者”的认知方式。比如许多国外受众都有“我不一定爱日本人,但是我爱日本产品”的表述。即使是与日本有很深历史宿怨的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大众,也会有此矛盾心理。因为作为国外受众,大都只会根据自己的日常现实需求和切身生活体验,逐步形成对该国商业品牌系列的一种认知。上海交通大学和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刘康撰文指出:“国家形象”(National image)一词在英语中往往是指特定国家的商品品牌,如奔驰、宝马车作为德国的“国家形象”等。[7]“国家形象”在英语与其他语言中并无对应的词汇。相关的概念包括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交流传播领域里的“perception of the nation” (对国家的认知)、“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nation”(国家文化的再现或表述)等,以及公共关系、广告、市场营销、品牌形象等商业领域的观念。*参见瑞典营销学学者Eugene D. Jaffe 和Israel D. Nebenzahl(2006)所著National Imag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untry-Of-Origin Effect,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1。
所以,重视国家形象的正面价值传播,也广泛地涉及一系列的国家品牌建设和营销,无论是商业品牌、旅游品牌、媒介品牌、教育品牌、文化娱乐产品的品牌,都更多更广地与国外受众的日常生活发生着每时每刻的联系和互动,也更易与新闻信息产品一起,逐渐形成他们心中的他国印象。这就提醒我们:国家形象往往也要通过生活观念、日用商品和消费产品的塑造,以及对这些商业产品、娱乐产品、文体产品的成功公关和危机处理机制来维护和建构。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品牌和品牌形象的打造与维护,不能仅仅作为一种经济工作或政治经济事宜,目前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连外交也要紧紧围绕这个中心而运转和做好服务与配合,这一方式是可能产生观念和理解上的误区的。针对国家形象的虚实之分、内外之别,有意塑造才能争取主动、改变被动局面等问题,刘康的文章《如何打造丰富多彩的中国国家形象》更强调要理解这种区分背后的现代西方哲学争议和整体效应:形象与实质或实力、“体”与“用”、外在与内在,这些理论问题,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义,同时也是现实性、应用性、实践性的问题。一个世纪以来,哲学界、思想界对于“本质”、“现象”命题的反思是最引人瞩目的。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以早年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为标志的哲学思维的“语言转向”,关注的焦点就是外在形象与内在本质的命题。这些理论思维有一个相当清晰的脉络,就是越来越强调媒介(首先是语言,再就是大众传媒)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7]这一倾向不仅仅呈现在哲学和理论层面;政治领域里的选举策略、政治公关策略、情感政治策略越来越成为后里根、后撒切尔时代西方“政治秀”的重心;亚洲、东欧以及南美洲等民主化转型社会里,公众舆论、政治家形象、政治秀也越来越成为政治的核心。*参见《环球时报》深度报道:“信息化要求应变更快,转型期民众期望太高,现代国家领导人越来越难当”,《环球时报》2008年7月11日第7版。在经济层面,尤其是服务业和金融业这两大当代信息时代经济的支柱行业,对品牌信誉即形象的依赖更是无以复加。品牌和信誉已经成为当代国家政治与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类似的文章和讨论提醒我们:重视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必须重视“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复杂、多样多元的形象,涉及政府与各行业的各种公关、文化表述、传媒实力、学术力量等,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社会价值观、历史传承、民间风俗的综合反映,是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整体呈现。现代媒介之所以对现代社会产生着“核心作用”,就是因为到了现代科技支持的信息和网络时代,语言与对象、信息与实体、符号与现实之间,就不再是传统的因果关系,不再是单向度可轻易掌握的传播与反馈关系,而是随时随地、复杂互动的相互建构、相互作用关系,由此,必须重视大众传媒与国家、政治、社会和各行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各行各业、各国政府都必须学会适应语言和大众媒介起“核心作用”的现代社会的交往和互联方式。
三 国际舆论环境的变迁与国外受众理解
正因为“国家”与“形象”两个概念都有多重涵义,国内与国外的公众对一国的认知又有客观差异,所以,成功的国际传播必然涉及如何认识当代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如何认识和理解他国受众、如何认识国家形象之塑造手段和传播过程等问题。
关于当代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学者们首先聚焦的一个缺憾就是不仅中国目前的传播实力与西方传媒大国相比尚属弱旅,而且更重要的弱项在于:我们的对外传播内容也常常文不对题。如清华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者陆地和高菲合作撰文指出:“毋庸讳言,中国的媒体,无论是电子媒体还是平面媒体,在世界上的影响都与中国的大国身份不相称。在很多时候,要么扮演国内宣传放大器的角色,要么充当西方媒体‘传声筒’的工具,唯独缺乏的就是自己的声音。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是,最重要的一种就是信息营销错位,即只有对外宣传,没有国际传播,而国际市场需要的是后者。……中国的对外传播还停留在对外宣传的理念上,基本不谙国际传播的规律。而实际上,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传播活动。”[4]
若需体察当今世界形势和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就得经常审视萌发于19世纪中叶的“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概念及当代变迁。“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8]换言之,大众传播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与传统的“宣传”与“接受”方式的主要不同,就在于出现了“职业传播者”对“机械媒介”的使用,使得大量复制的传播内容能够影响人数众多的传播对象。这里的“职业传播者”主要指两类,一类是“特定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团体;另一类则是各种媒体组织。这两类职业传播者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体制中有十分不同的定位。而“机械媒介”作为“规模庞大的专业化传播工具”,不仅经过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而且“大量复制的传播内容”和深受影响的内外“受众”都经历了丰富的渐变和激变。传播者、媒介和受众三者之间有着不断变革的相互作用关系。
一般认为,14至16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手抄新闻”是近代报纸的萌芽。1814年英国《泰晤士报》采用了蒸汽机动力印刷,“廉价报纸”使得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大众也能成为报纸的广大受众,大众传播的时代由此到来。随着报纸影响范围的迅速扩大,为报纸提供大量新闻信息的通讯社也在19世纪中叶纷纷出现。通讯社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使信息生产过程逐渐成为分工明确的系统工程,也使“职业传播者”有可能行使对报业的商业垄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包括计算机、光纤通讯、仿真技术、集成电路等在内的声势浩荡的新技术革命,使广播、电视的节目制作、播放、控制等技术日益完善;另一方面,广播电视的个人拥有量急速增加,其影响力与书籍报刊一起,也让信息制作和传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产业性力量。随着大众传播作用的加强,各种媒体组织不再只是简单地报道新闻、传递信息。它们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积极主动地介入各种国内外重大事务,有意无意地影响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现代发展进程。赵雪波、展国龙的文章举例说:“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一名资深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在访问越南战场归来后,态度180度大转弯,预言美国的越南战争不会取胜,于是整个美国国内舆论沸腾,群情激愤,壮大了美国国内的反战呼声,从而开始影响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并加速了越南战争的结束。从大处讲,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国际关系在许多方面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大众传播的穷追猛打之下,国际关系领域里决策过程中的黑箱操作越来越少;新闻传播时效的提高同时加快了外交等其他国际关系领域中活动的节奏;因特网的诞生使得普通个人直接进入国际关系成为可能。”[9]就在人们担心国家和世界的各类事务越来越多地依赖媒体和信息产业之际,20世纪末诞生的新型传播工具“互联网”,标志着大众传播的又一新时期的到来,因为网络作为一种交互式的传播工具,意味着大众有可能真正以自立主体和自由选择的方式进入传播的领域,换言之,大众将不再仅是信息的受众,而且同时也可能是职业传播者,是传播主体,是信息制作者和复制者,是媒体本身。
上述简单的大众传播历史回溯,让我们清晰可见,从印刷报纸到广播电视、再到电子网络,今天的大众传播方式已由单向转为双向、并从双向转为复合传播模式。今天的大众传播过程不仅是特定社会集团和媒体组织促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而且是各种受众也可能在同一时空中,运用各种现代传播媒介,影响政府、社会、媒体和他人。今天的大众传播是“人人即媒体”,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复合传播。
2008年,41岁的韩国歌手金长勋与其合作伙伴自费在《纽约时报》A15版上刊登了有关独岛领土主权的整版广告,内容坚定地表示独岛属于韩国领土。2010年7月25日,近9万份美军在阿富汗战场的秘密作战记录被一家名叫“维基解密”的网站公布于众,其中包括未曾公开的阿富汗平民遭屠杀以及美军对塔利班据点展开的秘密行动等。这一行为让美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政府和最高领导人感到震惊和遗憾。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29日说,驻阿富汗美军秘密档案遭泄露事件可能造成严重影响,威胁美军士兵及阿富汗盟友安全,国防部将彻查此事。“维基解密”网站创立者澳大利亚记者朱利安·阿桑奇则称,这些资料是在2004年到2009年期间通过多个军事部门搜集而成。其中大多数都是由士兵和情报人员通过前线士兵发回的广播报告而撰写的。
所以,今天人们担心的问题是:“传播主体复杂化、‘话语权’垄断困难、信息‘把关’缺失,这类大众传播诸要素的‘质变’,以及互联网对人类传播的深刻影响还未充分显现出来。因为互联网不是小的技术,而是20世纪最重要的创造发明,互联网开辟了大众传播新天地,引发了传播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改变了传统大众传播格局,而且为人人参与大众传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这是新时期舆论环境的鲜明特征。”[10]
四 中外新闻体制的差异与良性互动
新时期国际舆论环境特征其实也提醒我们:中国形象的对外传播,不仅是中国人进行的国际传播,而且同时可能是国外受众与中国传播的密切互动,我们对如何有意迎合国外受众积极参与的需求和愿望,必须要有主动呼应和积极接纳。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蔡雯教授在《试论中美两国公共新闻传播的现实差异》一文中强调了“公共新闻”浪潮对美国公众“共同参与”新闻信息制作和发布的重大变化。文章说:“‘公共新闻’为什么能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一场波及全美、影响世界的浪潮?为什么在美国会引起巨大的争议?因为它不只是一场局限于学术界的学术论争,而是一场反潮流的新闻改革运动。我认为,这场运动在美国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远高于它所获得的学术价值。……网络技术为‘公共新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公共新闻’已经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进入到社会公众可以不依赖传统媒体,自主发表观点、形成舆论甚至组织、进而影响媒体、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新的阶段。通过对美国‘公共新闻’十几年来所取得的代表性成果的了解和分析,我认为,‘公共新闻’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报道对象是公共事件或问题,二是报道方法以发动公众参与、共同讨论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为主。它在美国引起争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与美国的新闻传统一贯强调‘客观’、记者不能介入报道客体的要求相违背。而‘公共新闻’的实践者恰恰是要通过主动地‘介入’、发动、组织,来完成对公共事件或问题的报道,其目标已经从单纯的‘告知’转向了寻求对策、促进问题的解决。”[11]
《风度》杂志执行总编李荣霞的文章《受众研究:理论与实践》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在对外宣传中真正意义上的受众研究几乎是空白。对受众的了解,仅限于读者来信及很少的交流,以及外宣这支队伍中有些人曾经有过的国外经历,缺乏科学性和理论性。……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越来越重视对外传播媒体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地位与作用,受众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外文局有了专门机构做舆情研究,特别是近几年‘本土化’的推进,促进了受众研究的发展。比如,《北京周报》成立了北美分社,在最前端了解国外受众的信息,每周与后方视频对话,使对外报道更加有针对性,更贴近他们的需求。”[12]
由此可见,当代信息科技和传播媒体的变革已经促使国外受众对新闻和信息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为从被动到主动以至自主的变化,即从被动获知和接受信息到主动参与制作和发现有价值信息、组织活动、制造舆论、亲身参与讨论、切身感觉自己作为公民能够影响公共事务的进程等。所以我们的一个深入民心的口号曾是:“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向中国”,必须要认清这个口号背后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本身已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开放实体,世界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充满舆论与行动的世界。
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注意到中外政治、社会和新闻体制的不同,而让国外许多受众的信息接受呈现为多层次的媒介使用与受众分布,如上述“职业传播者”主要指两类:一类是“特定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团体;另一类则是各种媒体组织。比如这两类职业传播者的关系在中美之间就有复杂的差异,“美国新闻界自认为是一种独立于政府的力量,虽然他们搞的‘公共新闻’本质上是在帮政府的忙。……而在中国,我们从不讳言新闻媒介的政治倾向性,与执政党保持一致、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是我国主流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11]
所以已有学者有针对性地建议:“要善于多方位多层次地运用西方新闻媒体。我们对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特别是美国主流新闻媒体的借用要有针对性、工作要细化。比如,我们要面向美国的上层社会和精英人士传播信息,可以多用美国的全国电视网和日报等新闻媒体。如果想要向美国普通民众传播信息,则要更多地考虑利用广播电台和地方媒体;如果要针对某些美国众议员传播信息,直接针对其所在选区的地方媒体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多层次地运用西方媒体有利于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13]
类似建议虽然已经十分具体和“细化”,却也忽视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目前新闻媒介的声音总体呈现为不存在重大差异或价值分歧的“官方话语”,仅让这种主流官方话语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对外传播,只是策略和技巧上的改进。而真正的困难仍在于,国外的一些受众基于自身的体制认同和文化习惯,希望听到的是中国除“主流话语”以外的各行各业的、公民个人的独立的声音。这些独立的声音既可以是与官方主流话语相一致的,也可以是不一致、不相干的,或部分相同、又若即若离的。而如何让这样的中国声音以分流、分类、分化的方式传播出去,对中国的国际传播而言,仍是全新的课题。
二是当我们了解国外受众时,也需要尊重国外媒介的多层次性和分工模式。换言之,许多西方国家是不存在“中央台”和中国式官方统一管理的媒介体系的。在他们对中国的报道中,往往并不存在“集体”的声音和行动,而且有意回避的就是类似的媒介导向太“集体”一致问题。由此,中国对外界报道的接受也需要学会理解他者对我们特别强调的“统一协调”的不接受或不习惯,学会忍受和承受杂音和不和谐场面,因为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和谐”社会关系理解。
[1]黄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J].新闻传播,2007,(4).
[2]刘继南,何辉,等.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242.
[3]陈萌沧,商汉.新世纪如何包装中国 对外宣传思路有待改变[EB/OL].http://news.sina.com.cn/c/2003-08-04/15581475540.html.
[4]陆地,高菲.如何从对外宣传走向国际传播[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3).
[5]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8-11.
[6]郭可.当代对外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12.
[7]刘康.如何打造丰富多彩的中国国家形象[EB/OL].http://unn.people.com.cn/GB/22220/142506/8626045.html.2009-12-01.
[8]梅尔文·德弗勒,等.大众传播通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2.12.
[9]赵雪波,展国龙.历史的结合——从国际关系和大众传播的历史阶段划分看二者的关系[J].现代传播,2000,(5).
[10]刘正荣.“人人即媒体”与大众传播要素的质变[J].国际新闻界,2007,(4).
[11]蔡雯.试论中美两国公共新闻传播的现实差异[J].今传媒,2005,(6).
[12]李荣霞.受众研究:理论与实践[J].对外传播,2009,(6).
[13]明安香.关于国家形象传播的思考[J].对外大传播,2007,(9).
ContemporaryInternationalMediaEnvironmentandChina’sImageCommunication
PAN Yi-he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Successful national image building can improve the country’s positive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edia changes have prompted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environment to take great changes. Mass communication has changed from one way to two way, and to a compound mode of communication; foreign audiences’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s and information have changed profoundly, mainly from getting information passively to participating actively in making and discovering valuable information, organizing activities and creating public opinion, as well as personally engaging themselves in the discussions, in order to influence public affairs. “Everyone’s participation” in the modern media environment has created unprecedented conditions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will prompt us to discuss in greater depth the diverse needs of the aud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better respect the actu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news systems.
international media; national image; news system
2012-06-04
教育部2009年重点课题“国际传播的理论、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的子课题研究成果。
潘一禾(1959-),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社会思想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政治与美学、世界文学、跨文化交流研究。
G206.2
A
1674-2338(2013)01-0112-07
(责任编辑吴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