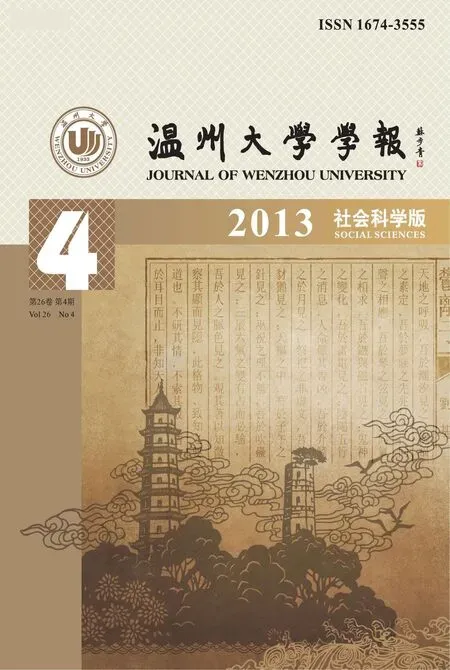社会权
—— 社会法的基石范畴
李炳安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社会权
—— 社会法的基石范畴
李炳安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社会权是社会法的基石范畴。一个学科的范畴通常可以分为普通范畴、基本范畴和基石范畴三个不同的层次,其中,基石范畴是把一个法的部门从法体系中相对地独立出来的核心范畴。“私法公法化”、“社会问题”、“社会整体利益”及“社会安全”等范畴都难以成为社会法的基石范畴。问题群中属于本源性的问题才能成为基本问题,功能性范畴、目的性范畴只是解决本源性范畴所导致的结果和目的,而本身不是本源性范畴或基石范畴。社会权和社会法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社会权的产生和发展催生和推动了社会法的产生和发展。社会权作为社会法的基石范畴,既能制约、控制和引导社会法的发展目标,也能很好体现权利本位的法的价值和理念;既有利于构建一个有内在逻辑的社会法体系,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社会权;社会法;基石范畴
基石范畴,又称逻辑起点、初始性范畴、理论基石、逻辑基石,或者称为学科的开端、学科的出发点,是该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也是在历史上的起源“凝结”为理论叙述起点的逻辑范畴。社会法的基石范畴是反映、概括和把握社会法现象的最本质概念,是社会法区别其它法的最基本的属性,其科学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反映并决定着社会法学科的存在基础和发展前景。2006年,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正式成立,2011年3月,社会法进一步被确认为七大法律部门之一①包括宪法及相关法律、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法七大法律部门.,2012年7月,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正式成立,由此,社会法的研究也成为国内研究的热门话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已有的社会法的基石范畴观点进行梳理和评析,从发生学的角度来探讨社会法产生的历史逻辑。
一、社会法基石范畴几种代表观点的评析
基本概念蕴含着基石范畴,任何一门学科的基本概念都要直接或间接反映其基石范畴。对基石范畴认识不同,该学科所体现的基本概念也就自然不一样,也就是说,从该学科的基本概念中应该能够推断出该学科的基石范畴。根据这一思路,从学界对“社会法”这一基本概念的界定来看,可以大略推断学界关于社会法的基石范畴有“私法公法化说”(也称“第三法域说”)、“社会问题说”、“社会利益说”和“社会安全说”等几种观点。下面对以上几种观点进行粗浅评析。
(一)私法公法化说
该说认为,私法公法化形成了第三法域,第三法域就是社会法[1]11,“社会法是与公私法相并列的法域。”[2]于是,私法公法化形成第三法域的“自身逻辑”就成为社会法“观念上”的逻辑起点[1]22。这种观点成为社会法学界当前的主流观点,也对社会法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社会法是与公法、私法并列的第三法域,是社会法学者的普遍认识。”[3]但该观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还需要继续寻找理论支持。
第一,第三法域不能等同于社会法。理由主要有二:首先,“法域”为法的“域”,而不是指“域”中的法。公法和私法是法域,是部门法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一种学理划分,而且学界划分标准也不尽不同,不同的标准所导致的公法私法各自所含内容也不完全一样。公法与私法划分只是一个粗略的分类,不同的分类标准有不同的意义,便于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各个部门法的不同属性。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学说可以完全解决公法和私法区分上的困难[4]。再者,公法和私法本身也没有共同的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如刑法和行政法尽管都属于公法,但其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就迥然不同,再如,商法和婚姻法均属于私法,其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也相差很大。所以,第三法域不等于社会法,就象公法不等于刑法,私法不是只有民法一样。总之,“法域”是“法”的“域”,强调的是域的边界,而不是指“域”中的“法”。
其次,“域”是一个集合概念,根据“包含集”不能等同“子集”的逻辑,第三法域也就不能等同于社会法。从逻辑角度来看,第三法域就是社会法,将“包含集”简单等同于“子集”,然后,又将某一“子集”的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直接提升为“包含集”的基本原则和调整对象,导致法域与部门法趋于混同,逻辑上出现混乱。其实,第三法域是一个集合的概念,集合中任意两个元素都应是不同的对象,即具有互异性。互异性使集合中的元素没有重复,两个相同的对象在同一个集合中时,也只能算作这个集合的一个元素。从目前研究的成果来看,第三法域这个“集合”至少可以包括经济法和社会法,由于二者同属于第三法域这个“集”,自然也有诸多相同之处,如国家在这一领域都要发挥主导作用,但二者各自的调整对象、基本原则以及国家发挥作用的方式,都是不同的。
第二,无论是私法公法化,还是公法私法化,即使能作为范畴,也是一个过程范畴,强调的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状态的范畴。当事物的量与质一定时,该事物就处于一定的状态,当事物从一个状态(始态)变成另一个状态(终态)时就经历了一个过程。“过程”是“变”的过程,所以,“变化”与“过程”常常不分离,称“变化过程”。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体现的是变化,是一个变化过程,强调公法和私法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过程,而不是专指一种“状态”。状态范畴是体现一个事物本质的范畴,能够吸纳过程范畴的成果并不断巩固,而过程范畴本身需要状态范畴的肯定和确认,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能完整体现一个事物的“质”与“态”。私法公法化难以成为社会法的逻辑起点,就如同“商品”能成为经济学的基石范畴而“产品的商品化”就不能这个道理一样。
第三,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本身也不具有按照一定层次有系统地将社会法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统领和建构社会法理论体系的内在属性和能力,实体的权利义务结构不能依此而展开。因此,其不具备逻辑起点应该具有的“生成元”功能。
第四,如果以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作为一个学科的逻辑起点,就会产生与其他学科(如经济法)共享逻辑起点的尴尬局面,导致学科的混同而无法相对区分,失去学科存在的意义。
(二)社会问题说
该说的基本逻辑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了社会问题或社会弊害,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或社会弊害,就产生了社会法。该说直接突出社会法的主要功能,认为社会法是为了解决社会性问题而制定的各种有关社会法的总称①参见: 陈国钧. 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M]. 台北: 三民书局, 1984: 112. 这种观点也较为普遍, 如贾有土教授认为, 社会法是为了解决许多社会问题而制定的有关各种社会法规的总称. 参见: 贾有土, 樊启荣. 社会保障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7: 75.。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法因社会问题而产生、存在,由于现实的逻辑自然应成为观念逻辑的基础,因而,社会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法的基石范畴或逻辑起点。
该说从功能角度对社会法进行界定,无疑对解决社会问题有着积极意义。但将其作为基石范畴,仍然难以令人信服。
首先,“社会问题”,在西方国家也翻译为社会病态、社会解组、社会反常或社会失调等②功能学派认为, 社会问题的产生是因为社会系统中的某一部分不能正常地发挥它的社会功能从而产生社会问题. 功能主义关于社会问题的成因有: 社会病态论、文化堕距论、社会失范论、差异交往论. 冲突学派认为, 社会问题是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冲突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冲突学派关于社会问题的成因有:价值冲突论、群体冲突论、阶级冲突论. 社会心理学派对社会问题的成因, 局限于解释犯罪和越轨行为等社会问题.。从涉及的面来看,社会问题是“社会的公众问题”、而非“个人困扰”;从所处的状态来看,有了社会问题的社会关系的社会状态偏离了社会公认的正常状态[5]。根据这一解释,各个领域都会产生社会问题。根据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社会问题的行为主体、社会问题的个体性或群体性、社会问题分布的领域、社会问题的性质等标准可分为结构性社会问题、变迁性的社会问题、越轨性社会问题、道德性社会问题,等等。“婚姻问题”、“都市问题”、“卖淫嫖娼”、“赌博吸毒”、“青少年犯罪”以及克隆技术的运用等都会产生或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任何一个环节、层面都可能出现故障而产生社会问题。可以说,多数法律制度都有从某一层面和角度解决社会问题的功能和任务,如刑法有解决青少年犯罪的社会问题的功能,婚姻法有预防因离婚而产生社会问题的效果,但我们不能说刑法、婚姻法都属于社会法。再者,教育法始于义务教育法,属于社会法乃为共识,但教育法并不是因为解决社会问题而产生的。
当然,从社会法功能来看,社会法的确解决民生问题,也包括解决因民生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法既解决有关民生的社会性问题(如社会保险法),也解决有关民生的个人困扰(如社会救济法)。社会法关注民生,保障民生,但不是所有民生问题都由社会法来解决,如物价法常有关于民生的内容,财政法、税法也有民生问题的调控,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也涉及民生问题。因此,通过社会法功能来预测社会法的产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从因果关系来看,“社会问题”相对社会法而言,是外在原因而不是内在原因,仍属于现象范畴而不是本质范畴,本身也是本质性原因引起的“果”。从哲学角度来说,原因是指引起一定现象的现象,结果是指由于原因的作用而引起的现象,先因后果是因果联系的特点之一。但在探讨事物因果关系时,往往是根据内在原因引起的“果”去探素其内在的原因和根据,这一过程称为“执果索因”,体现了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功能是指“社会法干什么”的问题,从社会法的功能角度来看,社会法确实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功能,但功能不能等同于本质,功能性范畴只是解决本源性范畴所导致的结果,而本身不是本源性范畴或基石范畴。只有问题的根源,或者说能够引起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最根本性问题,才能成为本源性的问题。“社会问题”仍然是表象性的,属于功能性质,具有多样性,不属于社会法存在及其变化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原因。因此,用“社会问题”来界定社会法,至多只是“功能定义”而不是“发生定义”。
再者,以“社会问题”作为社会法的基石范畴也不能体现社会法的基本精神。社会法的基石范畴体现着社会法的本质属性,体现着社会法的人文标志、重要品格和文化内涵,是社会法的价值归属。从“社会问题”范畴层面来看,只能读出社会法的控制功能,怎么也读不出社会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和理念。
除了“社会问题说”以外,从社会法功能角度来解读社会法基石范畴的还有“不协同说”。此说认为社会法就是解决社会的“不协同”,“除此,很难再概括出若干社会法观念的共同基础亦或说理论基础”[6]。其实,“不协同”是“社会问题”的另外一种表述,仍然是一种外在的表象。只不过“社会问题”是从病态社会学的角度来认识,而“不协同”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观察的。
(三)社会利益说
该说认为,社会法相对体现个人利益的个人法而言,就是“以个人的利害从属于社会的统一整体利益为基本法理的法”[7];“社会法是通过对社会弱势群体权益的倾斜保护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2]。这些观点认为“社会利益”或“公共利益”是社会法存在的基础,且社会法是“社会的法”,当然要以社会利益为基石范畴。
首先,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既有各自独立的一面,同时也有相互融合的一面,可以说,每一部法律都要着眼于这二者之一并影响着其对立的一面。社会法发生作用的着力点是个人,影响面是社会,如果个人得不到社会法的保护,会影响到社会这个“面”的稳定和和谐。这与经济法是不同的。经济法的“着力面”是社会,通过宏观调控社会这个“面”来影响作为“点”的个人。显然,尽管二者发生作用的路径不同,但都相互影响着其对立面。那种从法所保护的利益角度出发,认为公法保障国家利益,私法保障个人利益,而只有社会法才保障社会利益的逻辑过于僵化和简单,找不到现实的支撑依据。即使“社会利益”能够作为基石范畴,也只能是经济法的基石范畴[8]。可以说,经济法是从社会整体利益维护的角度来促进个人的利益,而社会法则是从个人利益的保护的角度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尽管二者的路经和着眼点不同,但在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个根本目标上并无二致。
其次,社会法虽然是“社会的法”,也不必然导致要以社会利益为本位或基石,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里的“社会”,从范围来看,是专属意义上的社会,不同于“和谐社会”中的“大社会”,小于社会整体利益所涵盖的范围;从内容来看,是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相并列的“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主要指民生问题的建设,社会法制建设是社会建设中的内容之一,所体现的利益也只是社会整体利益中的“部分利益”;从体现的社会关系性质来看,社会法体现的是一种强弱共生性社会结合关系,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社会法是对这一社会关系的认可和巩固。这与社会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所体现的关系性质完全不同。
再者,社会法仍然是个人法。无论是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还是教育法,其权利主体都是公民个人,“从个人法到社会法”的观点是对社会法的一种误解,会导致社会法外延的无限扩大,最终会成为无边无际的“法”。如果以“社会”作为社会法的权利义务承载体,还会导致承载主体的“虚化”。既然社会法本身就是“个人法”,那么以“社会整体利益”作为社会法的基石就难以令人信服。
(四)社会安全说
台湾学者大凡都认同社会法是社会安全之法,如王泽鉴教授认为:“社会法即系以社会安全法为主轴展开的,但凡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职业培训法、就业服务法、职业训练法等均属社会法研究之范畴。”①转引自: 蔡茂寅. 社会法之概念、体系与范畴: 以日本法为例之比较观察[J]. 政大法学评论, 1997, (58): 372-374.郝鳯鸣教授在考察国际条约和英、美、德等国的相关制度后认为,社会安全是“对于个人或家庭因生、老、病、死,伤、残、失业与职业灾害等社会风险所造成之危害,以集体或国家力量针对危害或可能产生之危险,採行补偿与预防措施;基于上述目的所建构之组织,称之为社会安全制度。”[9]虽然风险为个人风险,但因具有普遍性,且是拟以团体的力量协助个人解决困境,所以称为“社会风险”[9]。该说在德国、法国为主流观点[10]。此说中的“社会安全”中的“社会”是指“普遍性”,因具有普遍性,所以不称“个人安全”而称“社会安全”。
从台湾学者对社会安全的界定来看,实质上是指的个人安全,之所以称为社会安全,主要是基于类似的这些个人风险具有普遍性,而且解决途径是需要依靠社会互助机制、风险转移机制来实现,与我们所理解的实体的社会安全还不是一回事。就二者的关系来看,社会安全与个人安全是一种互构谐变关系,个人与社会互生,个人安全与社会安全互存,个体安全是社会安全有机形成的本体性内容,是实现社会安全的前提和基础。社会法对社会稳定和安全的追求,在保障社会安全时的着力点仍然是个人安全,是遵循从个人安全的保障到整个社会安全的逻辑,通过对个体安全的保障来促进整个社会的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甚至政治安全。
那么,安全对象为“社会”的社会安全能否作为社会法的基石呢?诚然,社会法当然要追求社会安全,也就是说,社会安全是社会法追求的重要目的,可以视为社会法的目的范畴。逻辑起点是对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进行回答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有独特性并能够涵盖变动性,不是研究的任务、意义、目的等。尽管起点之美在于终点,在于社会安全的实现,但起点毕竟不能等同于终点。仅就目的而言,对社会安全的追求,也是行政法、民法和刑法的目的之一,不仅仅只为社会法。
二、社会权:社会法的基石范畴
(一)社会权的基本属性及其产生的原因
尽管学界对社会权的理解以及不同国家对社会权的定位都有所不同,目前尚无统一的概念,将来也不会有,但对社会权的以下基本属性的认识还是较为一致的。
其一,从性质来看,社会权属于第二代人权,是一项基本权利,俗称“吃饭权”。与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古典自由主义哲学为主导的自由权不同,社会权根源于福利国家的思想,其实现需要国家的积极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计划应把满足公民的最低限度的基本需要置于优先地位[11]。
其二,从权利义务关系来看,社会权体现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间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有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义务[12],国家需采取适当的立法、行政(包括预算)、司法措施来实现公民的社会权,是人权价值在宪法上的具体体现。其中,立法部门的立法义务是实现和保障公民社会权的重要步骤,立法部门应该根据国际人权法和国内宪法的要求,进行相关的立法,使得社会权获得部门法律的保障。社会权经立法权将宪法权利具体化为法律权利之后,还需国家行政权的积极作为才能实现,否则,会成为一种“纸老虎”式的权利[13]。
其三,从所包括的具体权利内容来看,世界各国宪法中所确认的社会权,频数最高的是社会保障权、劳动权和受教育权,环境权作为社会权的一项重要权利内容,近年来也为世界各国宪法所确认[14]。当然,社会权作为现代法治社会基本人权体系的重要内容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15]。
社会权的产生有其思想、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
其实,济贫思想与济贫法的产生和实施由来已久,约四千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有要保护寡妇、孤儿,严禁以强凌弱的规定。古代中国也有“以恤民为本”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保障法出现以前,对待贫穷、灾荒等社会问题,各国一般是通过教会和私人慈善行为、行会内部互助互济、亲友邻里间互济互助以及政府的一些施舍性救助等方法予以解决,欧洲一些国家的教会甚至把济贫助残看作是自身的赎罪方式。这种救助在性质上通常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恩赐——君主对臣民的恩赐、富人对穷人的恩赐、救世主对芸芸众生的恩赐;或体现为一种亲友邻里的怜悯、同情。其基本理念是,贫困是穷人的道德问题和个人问题,是个人责任,社会救济也只是基于对同类的同情和怜悯而产生的一种施舍性行为。这是个人主义贫困观的具体表现。由此看来,起初的济贫、自发的互助互济、慈善都不具有权利的性质。
劳动、救济成为一项权利在观念上最早源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权论著中。傅立叶从人的情欲出发①他把人的情欲分为三类: 物质的或感觉的情欲; 依恋的、感应的情欲; 高尚的、分配的情欲.,设计了建立在“情欲”基础上的“和谐制度”,并得出劳动权是人的“最主要的天赋人权”的结论[16]。随后,天赋人权理论、福利国家理论、社会连带思想等都促进了社会权理论的产生并极大解放了人们千百年来禁锢的思想。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贫困和失业等社会问题应运而生,社会矛盾加剧,近代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自由权体系对市场经济竞争中的弱者无异于画饼充饥,不能保证他们应有的尊严和生存条件,原有的以传统自由权为核心的权利体系开始动摇,以纠正极端个人主义为目的的社会权思想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和需要。这种对济贫、劳动的观念从个人主义贫困观向社会贫困观、从“施恩论”向“权利论”的转变为社会权的产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从政治层面上来看,社会权的产生是无产阶级不断斗争的结果。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尤其是欧洲的三大工人运动高举“为面包和工作而战”的旗帜,劳动者的社会权渐次为资本家所容忍并获得国家法律的保障,这直接推动了社会法的产生和发展。如 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工人阶级迫使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在其颁布的法令中承认了劳动权。“对工人作出的最重大的让步是共和政府在二月革命后几天内就发布保证工作权利的宣言。”[17]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颁布的1848年宪法首次确认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劳动权和救济权等社会权利[18]。由此看来,社会权本质上是源于社会经济结构中各阶层的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等,而且,这些不平等从经济领域又延伸到了政治、社会领域,并引发了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威胁到有产阶级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威胁迫使有产阶级做出让步,渐次承认无产阶级的生存权利。
从根本上来说,个人的生存问题,从自给自足的自我生存、个人责任上升为一项社会性权利,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使得人的社会性生存成为可能和必然。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法也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迈进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人类社会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19]。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已使旧的依靠基督教会和行会承担的慈善救济保障方式无法解决贫困人数扩大和贫困程度加深的问题,无法行使稳定社会的职能,社会保障不得不由个人、行会和教会的“慈善”事业转变为国家责任。
(二)社会权作为社会法基石范畴的证成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20]逻辑起点是历史起点的反映,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思想进程”,必须与客观事物本身发展的“历史进程”相一致。一门学科的体系,首先应当确认它的逻辑起点,然后从其逻辑起点出发,借助逻辑手段,去论证以后的概念演绎都是该逻辑起点的“符合规律和性质的发展”[21]。也就是说,科学的命题都可以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方法予以证实(或否证),可证实性决定了理论或命题的有效性、可确认性。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对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可以甄别因果关系的真实性、有效性,否证一些暂时的、偶然的、非根本的因果关系。社会权和社会法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社会权的产生和发展催生和推动了社会法产生和发展。下面可从社会保障法和劳动法的产生为例加以证明。
第一,社会权和社会法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社会权的产生和发展催生和推动了社会法的产生和发展。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事物或现象在历史起点上的原初形态往往体现的是最本质问题,也是我们研究的逻辑起点。下面以社会保障法和劳动法的产生为例加以说明。
首先,以社会保障法的产生来说明。英国是社会保障法的发源地,英国的济贫法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6世纪以前,英国也存在贫困等社会问题,但那时解决穷人的救济问题多是通过基督教会、寺院、教会医院、基尔特、个人慈善捐款等方式。例如,在 15世纪的大城市中,就出现过许多分散的、拥有基金的养老院和救济院,如圣芭塞洛缪救济院、圣托马斯救济院、圣克罗斯救济院[22]。16世纪,英国开始了“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的结果之一就是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失业、伤残、疾病、年老等社会问题接踵而至。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1601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布了《济贫法》(史称旧《济贫法》)。该法案用征税的办法向圈地运动中流离失所的贫民实行救助,济贫资金开始实现由“募”到“征”的转变,这表明国家开始初步应对贫困,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因贫民过多而产生的社会动荡等社会问题。
但是,该法兼有强迫劳动和法律救济的性质,是惩贫与济贫的结合,并以惩贫为主,所有行为不检的游民一律作为罪犯看待,过于强调对不劳动者的惩罚而忽视对劳动者的帮助,不承认救助事业是一种国家与社会的义务和责任,也不承认要求救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社会保障的理念还远远未达到“接受救济是公民的一项正当权利”的程度。因而,学界并未称旧《济贫法》为现代社会保障法的雏形。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是以英国颁布新《济贫法》(1834年)为起点的。新《济贫法》标志着现代社会救济制度的形成,它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初级形态。学界做出这个判断的主要理由是新旧济贫法在性质上的区别。新《济贫法》规定,社会救助属于公民的合法权利,对贫民实行救助是政府应尽的义务,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福利措施来履行保障公民生存的责任。新《济贫法》规定成立济贫法管理局,负责济贫工作,可以说政府从传统社会济贫的恩赐性质转变为现代社会中的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实现了从“施舍”到“责任”的转变。
新《济贫法》把社会救助权第一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使社会救助成为一种制度。随后,欧洲其他工业化国家纷纷仿效英国,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救济制度,如丹麦、挪威和瑞士分别于1803年、1845年和1847年颁布了《济贫法》。这样,在西方“近代”便逐步形成了“现代”社会救济制度。
古今中外,各国都曾发生过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如果以“社会问题”为社会法产生的逻辑起点,那么不仅旧《济贫法》属于社会法,甚至四千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也能成为社会法的源头。这显然与社会法产生的历史不符。
新《济贫法》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救济制度初级形态,就是因为将社会救济上升为公民个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并给以制度的保障,社会保障已被法定为一项国家的社会职责,开始走上国家化、社会化的轨道。也就是说,社会救济成为一项法定“权利”之时,也就是社会法的诞生之日,权利内容的不断丰富也不断推动社会法制向前发展。从英国的历史演进来看,社会法的演进是伴随着社会权利的不断演进的过程,是保障权利得以巩固和实现的重要手段,因此,社会法的发展史也就是社会权的发展史。
其次,以劳动法的产生来说明。从14世纪到18世纪中叶,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颁布了许多强迫劳动的法规,被称之为“劳工法规”。劳工法规立法的理论基础是劳动是公民个人的义务,国家有强迫劳动的权力。于是,国家用血腥的法律把他们驱赶到资本主义作坊和手工工场,变为雇佣工人,以满足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要。例如,英国 1530年的法律规定只允许年老体弱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行乞,发给乞食证,身强力壮的“流浪者”要受鞭打和监禁;1536年的法律规定有劳动能力的游民第一次捕获要游街,第二次捕获要割去半个耳朵,第三次被捕则要处以死刑。1547年的法律规定,拒绝劳动的人判为告发人的奴隶,如逃亡14天,就判为终身奴隶,如三次逃亡,就要当作叛国犯判死刑[23]802。这一时期的法律,赋予资产阶级以特权,用鞭打、烙印、酷刑等手段强迫公民劳动,对劳工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繁重的劳动折磨着每个劳动者,劳工权利毫无保障。
学术界公认的现代劳动法始于英国 1802年的《学徒健康与道德法》,也称“工厂立法”。继英国之后,瑞士于1815年,德国于1839年,法国于1841年,挪威于1860年,瑞典于1864年,丹麦于1873年,意大利和俄国于1886年也先后颁布了限制童工工作和夜工的法律。这些“工厂立法”是社会法产生的标志,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劳工法规”有着本质区别。“工厂立法”视劳动为人们的一项权利,对劳动者的各项权利加以保护。“现代的工厂法强制地缩短工作日,而当时的劳工法力图强制地延长工作日。”[23]300尽管这些立法十分有限,但为以后社会权的法制保障奠定了基础。劳动从“义务”向“权利”转化,这是现代劳动法制产生的基础。
如果不是以“权利”作为分界线,那么,用法律甚至最严厉的刑法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法律也就是劳动法,也就说,现代的劳动法就不是始于 1802年,其本质也就不是劳动保护法,至少那些强迫劳动、加重剥削的“劳工法规”也属于劳动法范畴。这显然与现代劳动法的现实和基本精神不符。
社会保障法和劳动法的产生也表明,社会权作为社会法的逻辑起点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矛盾运动的产物,历史本身就成了社会法范畴的化身,社会权的产生、发展促进了社会法的产生、发展。“由于确立社会权的需要,国家制定了经济法与社会法。”[24]当然,“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此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5],社会权的产生具有客观性,是一种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结构内生的关系特质,只有在 19世纪末,人类进入社会化大生产以后,工业化带来了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千百年来依靠土地和血亲家庭获得生存安全保障的基础不复存在,社会性生存的权利被认同和保障的迫切需要,才会出现社会法。社会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顺应社会权保障的要求进行不断立法并提高立法层次,从立法到立宪再上升到国际人权法的保障过程。可见,社会法的范畴不是“造”成的,而是符合历史规律而“长”成的。
第二,社会权作为社会法的基石范畴或社会法的存在基础,既能内显社会法的本质,也能外显社会法的边界与系统,决定着社会法其它范畴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
首先,社会权能内显社会法的本质。“范畴本来的意义是指存在物的本质性。”[26]社会法的实施和实现也就是社会权的展开和外化,社会权所蕴含的价值标准内在地决定了社会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是社会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本质特征的集中反映,能够引导、控制社会法保障人权的基本性质,使社会法朝着社会权所内含的特定价值要求不断修正已有的规范体系,创立新的规范,不断地向前发展。
其次,社会权能外显社会法的边界。社会权作为社会法的基石范畴,能与经济法较好区别开来。第一点,从产生的角度来看,因社会权保障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法,能体现社会法的权利本位。以“权利为中心”的社会法追求人的权利保障,弘扬人的主体性和权利意识,是关心人、尊重人、为了人的制度,是现代理性在人权方面的重要体现,可以说,社会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人学”。经济法是为了克服市场和政府失灵而由国家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产生的法律,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注重社会整体的均衡发展,是调整国民经济运行的法律,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促进并保障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并使之由低质态向高质态发展[27]。相对而言,经济法可视为“物学”。
第二点,从调整的手段和功能来看,保障社会权的社会法客观要求在调整方式上主要体现为国家给付或保护,预防和尽量减少市场竞争中的贫富分化并对已经分化后的弱、贫者提供保障。而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宏观调控是主要的调整手段,“经济法与管制是必须联手的”[28],主要功能是保障和维护公平的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
第三点,社会权的实现客观需要社会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国家也对这种社会组织进行保护和促进,并通过这种中介性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对民生问题的协调、引导和介入。而调整国民经济运行的经济法客观需要国家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直接调整经济领域中的经济关系。
第四点,社会法保障的是公民个人基本生活的权利,因此,从量值上来看通常表现为定值控制模式了,如最低工资制度、基本医疗制度、九年义务教育、各类安全生产条件和标准等。而经济法主要是增值控制模式,通过国家的调控来提高初始值的控制方式。
基于社会权保护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法与传统民法也不同。传统民法以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为起点,以“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为灵魂,以任意性规范为主导,仍然强调财产权绝对,“对价等值”仍然是交易中的基本法则,相差甚远,既为显失公平的情形,也为民法所不许。总体看来,民法强调的是形式平等而非实质平等,侧重对富人、强者的财产权保护。而基于保障社会权的社会法则不然,强调实质平等[29]。它是以维护市场竞争的实质公正,追求实质平等为其目标,对民法中的财产权绝对性作了相当程度的修正,即所谓的“所有权社会化”,可以说,社会法的演进过程,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权而不断调整民法财产权的过程。
再次,社会权能构建社会法体系。从社会权产生的根源来看,社会权体现的强弱共生关系的关系特质是由社会化大生产所决定,具有客观性,不以强者或弱者的意志为转移,属于“应然权利”。这种应然权利要转化为实然权利,在法治国家里,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立宪、立法转化为宪法权利、法律权利。社会法就是顺应社会权保障的要求,不断将“应然权利”转换为“法定权利”,将“宪法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并围绕着社会权体系构建起来的法律部门。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从权利的派生关系来看,宪法权利、法律权利所表现的法定权利来源于应然权利或者说是由应然权利所派生的;在法定权利的体系内,宪法权利又能派生法律权利,或者说是宪法权利的具体化、法律化。社会权作为应然权利、母体权利①社会权是母体性权利, 或第一性权利. 这是根据权利的作用和地位的不同来划分的.,能够派生出诸如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环境权等。劳动权又可以派生出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劳动保障权等。社会保障权同样也能派生出社会保险权、社会福利权、社会救济权、社会优抚安置权。不同的子权利可以构建相应的子权利保障制度体系,如劳动法制度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和教育法制度体系等。可以说,社会权是对整个社会法的逻辑体系进行推理和论证的出发点,就好比找到一个顺流而下的源头并由此逐层推导各个阶段及研究内容,由此构建整个权利内容体系和整体结构。反过来说,客观上如果没有社会权这种应然权利,劳动权、社会保障权等宪法权利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同时,公民的社会劳动、社会保障如果不成为一项宪法权利,劳动法、社会保障法也就成为无源之水,也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权利保障法,前面所述的“劳工法规”、旧《济贫法》因不具有权利保障的性质而不能成为社会法就是很好的例证。
图1可以粗略反映社会法体系的静态衍生关系。

图1 社会法体系的静态衍生关系
最后,社会权决定着社会法其它范畴的基本性质。社会权作为社会法的基石范畴,也能统领和建构社会法的范畴体系。根据范畴体系内部各个范畴反映法律现象的深度、广度以及抽象化程度,社会法范畴可分为普通范畴、基本范畴和基石范畴三个层次。普通范畴是对社会法现象的某个具体侧面、某种具体联系、某一具体过程的比较简单的概括,属于初级范畴,如社会救助、工伤保险、最低工资、就业援助、社会福利,等等。基本范畴是对社会法现象的基本环节、基本过程或基本属性的反映,以社会法现象总体为背景,属于高级范畴,如社会正义、社会安全、社会合作等。基石范畴是对社会法现象总体的普遍联系的最高抽象,在范畴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规定着基本范畴和普通范畴的实质内容和相互关系,是基本范畴中的主导范畴,是整个社会法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基石;离开基石范畴,基本范畴和普通范畴就会失去目的和存在的价值,成为空洞无物的抽象。社会权作为社会法的基石范畴,决定着社会法基本范畴的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
社会正义是社会权合符逻辑的价值判断,社会权本身就是社会正义的判断尺度。社会权是体现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社会性生存的权利,内在需要倾斜保护,促进实质平等。而社会正义就是一种矫正的正义,是衡量社会法及其社会法调整的社会分配秩序的基本准则和价值尺度,是促进实质平等的价值评判标准,本身内含着社会权的保障要求和发展方向。因此,社会正义本身就是体现社会权本质的正义观,是由社会权所决定并顺应社会权保障的要求构建起来的一种价值范畴。
体现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合作共生的社会合作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是社会系统同样向弱势群体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是一种强弱相互关系的共生性社会结合。社会合作以及社会合作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是社会权关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30]。社会法将基于社会权利保障的社会合作理念化做具体的法律制度,反映着社会权保障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要求,为社会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搭建一套共生的法律机制(如集体谈判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慈善制度、社会救济制度等),无一不体现强弱主体之间的合作。因此,社会合作既是社会权实施的重要方式,也是社会法的重要实施机制。
社会问题作为功能性范畴、社会安全作为目的性范畴,这些都是社会法的基本范畴,均围绕着社会权而产生,前面已有所论及,不再赘述。社会法范畴的基本体系如下:

第三,“权利”本身就是法的中心范畴,以社会权为基石的社会法,也能很好体现“权利本位”的法价值和理念,把保障公民权利作为社会法的重心。
“法律的一种任务,是确立或保障权利。”[24]权利乃主观之法,法乃客观之权利。其实,法就是对权利的确认,权利就是法产生的目的,权利是法的最重要的核心颗粒。从历史的演进来看,社会权和社会法现象的出现是人的权利理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社会权的制度化是社会权价值和理念逐渐注入社会法规范的过程,体现人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倡导社会权利本位,重点在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权利,使社会中的人得以最大限度地获得生存和发展。就我国目前的现实而言,社会法越来越承载着保障公民诸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险、教育、环境、保障性住房等社会权利,所以,以社会权为基石范畴,能很好地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能够体现社会法的根本价值追求和社会法存在的目的。这一点,国外的立法也能得到佐证,如德国《社会法典》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围绕着社会权而展开的制度体系,日本在生存权保障原理指导下建立起了日本的社会法体系[31]。从其它法律部门来看,一般都把应保障相应权利作为本法律部门的基石范畴,如 “人权”是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和基石范畴[32],“公平竞争权”是竞争法的基石范畴[33]。国内的一些社会法学者也开始关注社会权在社会法的形成和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社会权是社会法的本位”[34]。
其实,人的社会性生存这种最大利益在文明社会里也只有通过人权和权利来保障才最为可靠。这种人权与权利的度在于社会强势主体所担当的经济发展利益与社会弱势主体所承载的社会安全利益之间的平衡点。过去,我们强调经济发展这一根本利益,崇尚效率优先的价值理念,切合了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特定需要。但如果长期忽视社会弱势主体所应享有的社会权利,也会反过来拖累经济的发展和效率价值的实现。
此外,社会权能否作为社会法的基石范畴,还看它能否涵盖变动性。社会权的产生和发展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开放的权利体系,从劳动权到教育权,从环境权到健康权,从仅仅体现生存权利的社会权发展为也体现发展权的社会权,体现了社会权的内容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为社会法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
三、社会权作为社会法基石范畴的意义
(一)有利于构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社会法部门
从一个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来看,往往是先确定基石范畴,然后再通过它的推演、拓展,逐步产生理论的分支体系与范畴体系。同任何一门学科一样,社会法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理论形态上要求有一个由基石范畴决定的、具有内在联系的逻辑结构。从作为逻辑起点的基石范畴出发,推演出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内容,最终构建成学科的研究对象、本质特征及其内容范围的理论体系。
如前所述,社会法是一个由社会权内在本质决定的有逻辑结构的制度体系,而不是一个“群”的概念。作为一个有自身体系的部门法,制度之间能够内含一种由上而下的逻辑关系,并按照这种逻辑关系依次展开,能体现整体性和相互之间的关联程度。而作为一个“群”的概念[35],社会法就很难有一个能够独立其它部门法的标准和内在的逻辑关系。作为“群”的成员,主要体现成员之间的相似性而不是同质性,无法构成一个内部统一、外部独立的有机整体。因此,社会法作为“群”的概念,与“法域说”的社会法并无两样,各种沾亲带故的法都可以包括进来,最终导致总论和分论的脱节,各走各的路,总论是总论,分论是分论,总论无法包容分论,也不能很好解释甚至无法解释分论所含的法律现象,分论所含内容也不是总论自然而合乎逻辑的结果。社会权作为社会法的基石,就要求社会法按照社会权所蕴含的价值和派生权利体系来构建制度体系,不会出现庞杂无章的乱局。
(二)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人以劳动为本,社会以人为本。”[36]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目的是以人的发展统领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的基本权益,并通过人的发展来达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社会权是以人为本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的集中表达,内在包含着对人的价值的积极肯定和生存状况的深沉关怀。过去,市场经济的泛化使人不断地走向“物”的层面,把人矮化为物,“见物不见人”掩盖了人作为人的特殊存在方式所具有的人性向度。
社会权观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观和发展观,强调人是社会的中心,人是衡量社会的尺度,按照“人的尺度”来开发世界、建设社会,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促进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满足人的生活保障和社会发展需要,促进人的尊严的维护和价值的发挥。社会权作为社会法的基石,内在要求社会法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取向,关注人的现实存在,关注人权保障,尤其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和社会贫困人员,凸显人文关怀的特有品质,实现社会平等与公正的价值目标。
(三)有利于树立权利本位的理念
社会法就是以权利为中心,以权利为基本观念、基本目的和基本任务构建起来的制度体系。社会成员皆为权利主体,都能平等地享有各种社会权利,社会法以对社会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为宗旨去设定和分配义务,能更好地体现国家的责任。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认的社会权主要包括劳动权(第6条)、社会保障权(第9条)、健康权(第12条)、受教育权(第13条)等。当然,这些权利体系并不是封闭的,而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的开放体系,如在 1972年《斯德哥尔摩宣言》中确立了基本人权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联系之后,环境权也成为世界各国宪法所确立的基本权利。社会权作为社会法的基石,成为社会法的基石范畴,有利于弘扬权利本位的理念和维护公民个人的生存权利。
此外,动态把握社会权范畴的历史地位及其时代发展,对于理顺社会法学界思想,明确理论研究方向,加快我国社会法研究创新步伐,促进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改革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董保华. 社会法原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2] 吕世伦, 马金芳. 社会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研究[J]. 北方法学, 2007, (6): 5-16.
[3] 单飞跃, 甘强. 社会法基本范畴问题析辩[J]. 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3, (4): 1-6.
[4] 卡尔•拉伦茨. 德国民法通论: 上册[M]. 王晓晔,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3.
[5] 朱力. 社会问题的理论界定[J]. 南京社会科学, 1997, (6): 12-19.
[6] 汤黎虹. 协同论: 社会法的理论基础初探[J]. 当代法学, 2008, (6): 78-83.
[7] 毛德龙. 近年来中外社会法研究述评[J]. 东方论坛, 2008, (1): 112-118.
[8] 李昌麒. 经济法的社会利益考辨[J]. 现代法学, 2005, (5): 16-26.
[9] 郝鳯鸣. 社会法之性质及其于法体系中之地位[J]. 中正法学集刊, 2003, (10): 1-8.
[10] 郭明政. 社会法之概念、范畴与体系: 以德国法制为例之比较观察[J]. 政大法学评论, 1997, (58): 375-376.
[11] Meron T.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Legal and Policy Issues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238.
[12] Eide A, Krause C, Rosas A.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 Textbook [M].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37.
[13] Fudge J. The New Discourse of Labor Rights: From Social to Fundamental Rights? [J]. Comparative Labor Law and Policy Journal, 2007, 29(1): 29-79.
[14] 莫纪宏. 论对社会权的宪法保护[J].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 (3): 1-14.
[15] Jung C, Rosevear E.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in Developing Country Constitutions [J].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TIESR Dataset, 2011, (1): 1-53.
[16] 傅立叶. 由非精确的科学的可笑方面所证明的理性的谬误[C] // 傅立叶. 傅立叶选集: 第3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135.
[17] 卡尔•兰道尔. 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 上卷[M]. 张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113.
[18] 赵宝云. 西方五国宪法通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 233.
[19] 史探径. 世界社会保障立法的起源和发展[J]. 外国法译评, 1999, (2): 42-53.
[20] 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C] //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22.
[21] 黑格尔. 逻辑学[M]. 杨一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 60.
[22] 赵静. 英国济贫立法的早期发展[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06, (3): 32-34.
[23] 马克思. 所谓原始积累[C] //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4] 佐藤孝弘. 社会法法律范畴区分之我见[J]. 财经界, 2007, (1): 278-280.
[25]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C] //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12.
[26]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上卷[M]. 贺麟, 王玖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157.
[27] 刘瑞复. 经济法学原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33.
[28] 李昌麒, 单飞跃, 甘强. 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考辨: 兼与董保华先生商榷[J]. 现代法学, 2003, (5): 3-11.
[29] Wesson M. Discrimination Law and Social Rights: Intersections and Possibilities [J]. Juridica International, 2007, (8): 74-82.
[30] Patulny R. Social Rights and Social Capital: Welfare and Co-operation in Complex Global Society [J]. Australian Review of Public Affairs, 2005, 6(1): 60-75.
[31] 毛德龙, 王燕. 近年来中外社会法研究述评[J]. 东方论坛, 2008, (1): 112-118.
[32] 曾祥华. 人权: 行政法的逻辑起点[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3): 33-36.
[33] 刘大洪. 论公平竞争权: 竞争法基石范畴研究[J]. 西北大学学报, 2008, (6): 138-143.
[34] 王广彬. 社会法上的社会权[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9, (1): 64-73.
[35] 朱海波. 论社会法的界定[J]. 济南大学学报, 2006, (5): 33-36.
[36] 刘俊祥. 人本政治论: 人的政治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3.
Social Right—— Social Law’s Cornerstone Category
LI Bing’an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Social right is social law’s cornerstone category. The categories of a discipline can usually be classified into common category, basic category, and cornerstone category of three levels, among which cornerstone category is the core category separating a law department independently from a law system.“Making private laws public”, “social question”, “whole social benefits”, or “social security”, among others, cannot become social law’s cornerstone categories. Only original questions in a question group are likely to become basic questions, while functional categories and purposeful categories can only solve results and purposes resulting from original categories, and they themselves are not original categories or cornerstone categories. Social right and social law’s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are synchronous, and the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right created and forced the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law. Being the cornerstone category of social law, social right can not only restrict, control, and guide the developmental target of social law, but also better embody the value and ideas of a right-based law; it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construct an internally logical social law system, but also embodies the people-centere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Social Right; Social Law; Cornerstone Category
D92
A
1674-3555(2013)04-0021-14
10.3875/j.issn.1674-3555.2013.04.004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付昌玲)
2013-01-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FX017)
李炳安(1964-),男,湖北荆州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