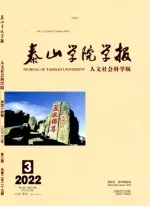“宗经”矫讹的《文心雕龙》——兼议“托古改制”思维模式
刘 凌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拙文尝试探讨如下问题:
身为一介寒士的刘勰,为什么对南朝讹滥文风那么深恶痛绝,并呕心沥血撰书痛击之?在儒学日益仪式化,文士“多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干宝《晋纪总论》),以及佞佛日盛的时代,刘彦和“矫讹翻浅”,为何偏要“宗经”、“征圣”,以周、孔为师?应该怎样评价刘勰“宗经”矫讹,以及“托古改制”传统思维模式?
一、刘勰深恶讹滥文风的主客观原因
南朝形式主义文风愈演愈烈,已是学界共识。不过还应指出,齐梁恰是这一恶化的转折点。《南齐书·文学传论》就曾指出当时文坛诸如“巧绮”、“酷不入情”、“辑事比类”、“职成拘制”、“崎岖牵引”、“雕藻淫艳”等弊端。隋代李谔也曾指出:“竞骋文华”之风,江左、齐梁“其弊弥甚”(《随书·李谔传》)。章太炎《文心雕龙札记》也言:“至齐梁以后,渐偏于华矣。”[1]这一文风,甚至影响到民歌。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即云:乐府之“淫艳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萧齐,流风益盛”。此风也波及文论。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即谓:论文、集文“拘形貌”之弊“实盛于齐梁之际”,慨叹“古学之不可复,盖至齐梁而后荡然矣”。《文心雕龙·序志》对“近代之论文者”的批评,即与此有关。不良文风的极度恶化,必然会引起包括刘勰在内一些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清人纪昀有评:“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2];“齐梁文胜而质亡,故彦和痛陈其弊”[3]。足见《文心雕龙》实乃有所为而发。
刘勰只是看到,不良文风违背圣训,却看不到它与特定社会关系,以及与作者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密切关联。南朝不良文风,实源于士族特权及其腐朽生活。王瑶先生《中古文学史稿》对此曾有论述:“士大夫的生活由逃避而麻醉,而要求刺激,一天天地堕落下去,文学的发展也自然变成了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了”;“对偶和数典用事的追求”、“辞采声色和永明声律的调谐”、“题材逐渐转换到宫闱私情”,这些“浮肿的,贫血的,堆砌的,和病态的”文风,“都是士大夫生活堕落的象征和自然表现”;“而文学内容的空虚,又亟需一种浮肿的形式的繁缛华丽来装潢”[4]。此种不良文风,已危及风教及王权。《晋书·裴頠传》即谓:由于“位高势重”的士族大多“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遂至“风教陵迟”。《晋书·儒林传序》称:“崇饰华竞,祖述玄虚”的讹滥文风,已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裴子野《雕虫论》,斥其“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全梁文》卷五十三)。王羲之慨叹:“虚谈废务,浮文妨要”(《世说新语·言语》)。今辑挚虞《文章流别论》论,批评不良文风“背大体而害政教”。李谔上高祖书也称:“文笔日繁,其政日乱”[5]。由此也便引起帝王的警觉。齐武帝就“颇不喜游宴、雕绮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顿遣”(南齐书·武帝纪)。明帝诏也对“礼让未兴,侈华犹竞”表示担忧,责令“自今雕文篆刻,岁时光新,可悉停省”(《南齐书·明帝纪》)。这些反侈表态,对刘勰或有所鼓励。
关于刘勰身世,至今仍有争议。但祖辈身份,毕竟有别于后代实际社会地位。而刘氏宗族人士至宋已号称“贫贱”(《宋书·刘穆之传》)、“孤贫”(《宋书·刘秀之传》);刘勰也是“早孤”、“家贫不婚娶”(《梁书·刘勰传》)。不管怎样,刘勰实际处境确与显赫士族迥然有别。过着清苦寺院生活的刘勰,不可能不对建筑在贵族腐朽生活之上的浮靡文风产生反感。另外,南朝王权为制约士族,不得不借助寒门。陈寅恪曾指出:“江南社会处于从东晋贵族制向南朝贵族制的质的转变之中。这一转变以皇权的强化和寒门、寒人的抬头为主要特征。”[6]而雄心仕进的刘勰,只能寄望于王权起用。因此,他对“虚谈废务,浮文妨要”、“背大体而害政教”,有可能危及“军国”的不良文风,必然高度警惕并极力抨击。这正是他对讹滥文风深恶痛绝的深层动机。
二、《文心雕龙》为何以“宗经”作批判武器
任何社会批判,都需要批判武器。当时的思想资源,有儒、道、法、佛、玄多家。但道家主张“灭文章,散五彩”(《庄子·胠箧》),全盘否定“文”;法家主张“好质而恶饰”(《韩非子·解老》);玄学导致“寻虚逐微,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功”(李谔《上隋高祖书》),均难符刘勰要求。而孔子及儒经关于以“质”为主,“质”、“文”兼顾的主张,诸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诗可以“兴”、“观”、“群”、“怨”(《论语·阳货》)一类论断,则可为刘勰提供得力理论支撑。
魏晋南朝的某些佛经翻译述评,也时有“文质”议论。为既忠实原意,又能吸引信众,每每倡导译文“质”、“文”兼备。慧远为僧伽提婆所译《三法度论》序,就反对“文过其意,或理胜其词”,主张“以裁厥中”[7]。刘勰导师释僧佑《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也称:“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8]。东晋佚名《首楞严经》后记认为,“饰近俗,质近道,文质兼唯圣有之”[9]。梁武帝《註经大品序》,也力主“质而不简,文而不繁”[10]。释慧皎《高僧传经师篇附论》主张:“夫篇章之作,盖欲申暢怀抱,褒述情志。”[11]释道安《合放光光赞略解序》则批评竺法护《光赞》译本“事不加饰”、“辞质胜文”[12]这些强调“质”、“文”兼顾的主张,很可能对录序定林寺藏经的刘勰以启发与鼓励。但凡此毕竟非出佛经原典,并多借助儒家表述,尤其不具儒经权威性,因此不可能以此作为典据。
以孔子为领袖、以五经为载体的儒学权威的确立,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学派内部也即孔门弟子对孔子的尊崇。其言论诸如:“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学而》子贡语);“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子贡语);“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引宰我语);“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引有若语)。二是汉代王权对孔子及儒经权威地位的钦定。西汉孝宣甘露三年和东汉章帝建初四年,讲议“五经异同”,均由官员主持,帝王“亲称制临决”(分见《汉书·宣帝纪》、《后汉书·章帝纪》),儒士反而成为配角。堪称白虎观会议纪要、班固承命整理之《白虎通德论》,则成为古代官方哲学。它称颂孔子为“独见前覩,与神通精”的“天所生”圣人(《圣人》章);奠基于孔子君臣父子之论的“三纲六纪”(《三纲六纪》章)成为此后的政治纲领。稍后灵帝又于熹平四年三月,“招诸儒,正定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后汉书·灵帝纪》),“使天下咸取则焉”(《后汉书·儒林传》)。儒经本为诸子之一,而诸子乃“入道见志之书”(《文心雕龙·诸子》)。但至此,汉王朝已将儒经判定为“于道为最高”(《汉书·艺文志》);孔子其人,也被尊为“素王”[13]。于是,孔子和五经便由民间道德、思想权威,一变为官方意识形态权威。儒学“仁”、“礼”同构,温情脉脉的“君臣”、“父子”等级观,既适应血缘宗法社会结构,又极助维护皇权统治,故能长盛不衰[14]。魏晋南朝,儒学地位虽有所下降,但毕竟仍为统治思想根基。魏晋间“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魏志》卷十《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言论,不过是少数人的偏激之辞,难干主流。佛教虽也偶有“儒道九流皆糠秕”(释慧皎《高僧传》卷六)的自负,但总体上还是讨好、攀附儒家风教。进入南朝,尊儒更有强化趋势。特别是当王权需要抵御士族和佛教挑战时,每对孔圣和五经有特殊礼遇与倡导。因此,“南朝文学在评价人物、选择事件上不再以老庄之隐退、阮嵇之放诞为高,而是回到了儒家忠孝礼制的轨道上”[15]。
还应看到,刘勰年少“笃志好学”和撰写《文心雕龙》前后,恰逢南齐王朝频频尊孔。牟世金先生《刘勰年谱汇考》对此有顺年考索。其谓:刘勰十三岁时,适值“齐高帝少好诸生”、“儒学大振”[16];十六岁时,齐高帝“志阐经训”、“精选儒官”[17];十七岁时,已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18];十九岁,“诏复立国学,释典先师用上公礼”,“王俭领国子祭酒……言论造次必于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术”[19];二十一岁,萧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20];二十三岁,武帝诏曰:“宣尼诞敷文德,峻极自天,发挥七代,陶钧万品,英风独举,素王谁匹”[21]。明帝也曾下诏赞孔:“仲尼明圣在躬,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训生民,师范百王,轨仪千载。”(《南齐书·明帝纪》)刘勰的老乡臧荣绪,则于孔子诞辰庚子日“陈五经拜之”(《南史·臧荣绪传》)。章学诚谓:“服膺六艺,也出尊王制之一端也。”[22]在这种时代氛围中,刘勰感梦而撰《文心雕龙》,称颂“玄圣”、“素王”,以“宗经”、“征圣”相号召,正不无“尊王制”并借助“王制”权威之意。
三、“托古改制”与“宗经”、“征圣”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这种创造工作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并不是在由他们自己选定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切死亡先辈的传统,好像噩梦一般,笼罩着活人的头脑。”[23]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也说:“相信人类曾经生活于一个‘黄金时代’”,“一个遥远的历史时代能够成为人们憧憬和崇敬的对象,并能够用以示范和评断当前会流行的行为范型、艺术作品和信仰范型”,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常见主题”[24]。由于特殊国情,这一主题无疑在中国更为突出,“托古改制”即为一例。它作为近人依据古代社会变革实践概括出的政治范畴,是指改革者依托或假托古代政制或古圣思想,以尊崇圣人、圣言为方法特色,改革不良社会体制的思维、运作模式。梁启超就指出:“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25]。后汉王莽和清末康有为“新政”,就被视为典型的“托古改制”。即使倡言“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也仍以《三经新义》为理据“法先王之政”,不过是“法其意而已”(《宋史·王安石传》)。每当社会面临困境、危机,改革者又势单力薄时,往往会采用“托古改制”模式。
由于南朝不良文风乃是依附士族文坛垄断的体制性现象,似可将彦和之“宗经”矫讹视为文艺领域的一种“托古改制”。此种“托古改制”,含有“依托”、“假托”两义。刘勰对周、孔、五经确有真诚信仰与崇拜一面。由其感梦“随仲尼而南行”,可知其大有担当孔学传人大任的抱负,也确有后儒认为《文心雕龙》堪称“六经之余绪”[26]。本先儒“道”论,倡“原道”之旨;标举“情信”、“词巧”、“足志”、“足言”圣训,抨击楚汉以降“异乎经典”的“浮诡”流弊,就是一种“依托”。而今视之,刘勰从儒学“文质彬彬”观引申出的“文质相称”(《才略》)、“衔华佩实”(《征圣》)论,也颇具普世性、永恒性理论价值。在当下这个新闻、学术、文艺均已高度娱乐化,人们陶醉于感官声色之快的消费时代,强调一下“为情而造文”(《情采》)也至为必要。文学艺术不能只是愉耳悦目,还应陶情冶性,参悟人生,提升精神。
但应看到,刘勰并非一味崇古,亦能与时俱进,充分肯定魏晋以来“缛”、“丽”、“采”的合理性。为此,便以“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序志》)概括文章特性,将“圣文”五经赋予“丽”色,以为“雕缛”提供合法性和权威性。但如此一来,就导致章实斋所谓“以意尊之,则可以以意僭之”[27],将己意强加经典。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足见对狭义之“文”并不看重。昭明太子《文选序》言:“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28]此论也完全适于周、孔。孔子主张“辞达而已”(《论语·卫灵公》)。朱熹《四书集注》注曰:“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苏东坡释之:“使是物了然于心者”和“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者”,是之谓“辞达”(《与谢民师书》)。总之,并不太重文采修饰。因此,将周、孔树为文章“雅丽”典范,就未免过于牵强。人们很难相信,刘勰会真以为《易经》、《书经》、《礼记》、《春秋》,完全符合“以雕缛成体”、“衔华佩实”、“丽而不淫”等规范。他不过是为倡己说,而“附会经义”和“假托”罢了。“托古改制”者无不“假托”。清人纪昀在评论王安石变法时也说:“安石以周礼乱宋,学者类能言之。然周礼之不可行于后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尝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真信周礼为可行。”[29]刘勰如此“托古”,也非“真信”五经“衔华佩实”,而为“以钳”逐奇者和墨守者“之口”。以此而言,这种“托古”矫讹,实有其不得不然、无可奈何的历史合理性,应予同情之理解。
然而此种“征圣”、“宗经”式“托古改制”,毕竟给《文心雕龙》带来一系列局限。以圣训、五经作为文章最高典范,必然无法客观评价后来文坛,似乎文学发展史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追讹逐滥的历史。《辨骚》篇对楚辞“异乎经典”的批评,《史传》篇对司马迁“爱奇反经之尤”的指责,就无不显示出“宗经”偏执。已如前述,很难说孔子之文均符“衔华而佩实”标准;即使符合,也决非圣文独有。章太炎《文心雕龙札记》在承认圣文“雅丽”的同时就指出:“晋宋之前之文,类皆衔华佩实,固不仅孔子一人也。”[30]纪昀则尖锐批评其文体概出五经、“百家腾跃,终入环内”之论:“至刘勰作文心雕龙,始以各体分配诸经,指为源流所自,其说已涉于臆创”[31];“此亦强为分析,似钟嵘之论诗,动辄源出某某”[32]。此论流毒广远,近则有《颜氏家训·文章》“夫文章者,源出五经”之论,远则有刘熙载《艺概·文概》“六经,文之范围”之议。而《文心雕龙》的真价值,恰恰在于能突破“宗经”藩篱,从艺术实践中总结出大量“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序志》)的写作、评鉴原理。纪昀称其“於文章利弊,穷极微妙”[33];黄叔琳赞为“於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遗”[34]。但刘勰的“宗经”思维模式,毕竟与“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原理相冲突,大大削弱该著科学性。刘勰“征圣”、“宗经”论,虽然奠定了后世“文统”论推尊三代和周、孔之文的基础,但毕竟过于偏狭。唐代韩愈,就把“两汉之文”笼括在内(《答李翊书》);明前七子,也提出“文必秦汉”的口号[35],他们均比刘勰更具识见。
至于吾邦为何盛行“托古改制”,古今多有解说。《淮南子·修务训》释为:一因“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二为“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前引纪昀,则谓“以钳儒者之口”。康有为解释:“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孔子改制考》)。殷海光则认为:“即令存心改变制度的人,也不敢和所要改变的制度正面去碰,而在战术上必须抄到这一制度的后面,利用这个制度来打击这个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康有为要‘托古改制’。”[36]诸说即或有理,也可再事深究。鄙意以为,似需从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处深挖。依赖经验承传、分散的小农生产,缺乏组织依托和独立思想,必然“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在等级森严的集权社会,改革者缺乏可与保守者相颉颃的政治实力和话语权,也不得不借重官方承认的圣人、圣言。也正因社会条件不足,“托古改制”难有成功,孔子、王莽、王安石、康有为率皆如此。《文心雕龙》尽管获“贵盛”者沈约“大重之”,也未见“为时流所称”(《梁书·刘勰传》)。即使刘勰后来位登东宫“清选”之职,也难行其志。“深爱接之”的萧统,和湘东王萧绎,无不标榜文章采丽特性。萧统《文选》以“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文选序》)为选编标准,萧绎将文学本质界定为“流连哀思”、“绮縠纷披”(《金楼子·立言》),均不见彦和“六义”之旨。直到唐代韩、柳、白居易等,才开一代新风。此种重大转变,非因尊“经”重“道”,而根于中小地主崛起并走上政坛、文坛,以及加强中央集权的时代需要。
郁达夫《怀鲁迅》曾谓:“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雅斯贝斯则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是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37]对于轴心时代奠定我民族文化根基的“圣人”及其经典,理应给予应有尊重,珍惜其“精神动力”。但“圣人”无非比常人更为“聪明睿智”(《易·说卦》孔颖达疏),且“亦时会使然”而非其“圣智能使然”(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上)。因此,对圣人圣言又不可盲目推崇乃至迷信。“妙极生知,睿哲惟宰”(《征圣》)断语,即已陷入迷途。马克思曾呼吁在伟人面前“站起来”,而且不“仅仅在思想上站起来”,还应“现实的、感性的”站起来[38]。而要“现实的”站起来,就需改良社会土壤,创建一个较为公平的经济、政治体制,培育相对均衡的利益群体,以结社、言论自由为保证,让各利益群体顺畅、理性地表达利益诉求,在平等协商中寻求改革共识。若此,就不至出现“托古改制”的尴尬。而只要不良土壤还在,哪怕是部分存在,就仍会生长出名目繁多的“托古改制”。当今时代,不就有“返本开新”、“儒家宪政主义”、“儒家马克思主义”、“天道自由主义”、“中道自由主义”种种舆论吗?以此而言,刘勰等人“托古改制”的教训,对改革深化期的中国,或不无历史启迪。
[1][2][3][30][32]黄霖.文心雕龙彙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68、102、108、168、20.
[4]王瑶.中国文学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84.
[5]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145.
[6]陈寅恪.南朝皇帝权力与寒门、寒人[J].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7).
[7][12]王铁钧.中国佛典翻译史稿[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89、61.
[8][9][10][11]朱志瑜,朱晓农.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63、33、71、78.
[13]汉书·董仲舒传.淮南子·主术训.论衡·超奇篇.北堂书钞卷五十二引《论语谶》等.
[14]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99-300.
[15]焦桂美.南北朝经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30.
[16][17][18][19][20][21]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M].成都:巴蜀出版社,1988:15、17、19、21、22、25.
[22][27]章学诚.文史通义[M].长沙:岳麓书社,1993:29、28.
[2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3.
[24][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220.
[25]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A].清代学术概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89.
[26][33][34]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附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724、739、426.
[28]萧统.文选(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9][31]四库全书提要[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106、1048.
[35]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52.
[36]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139.
[37]卡尔·雅斯贝斯.智慧之路[M].柯锦华,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出版社,1998.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4-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