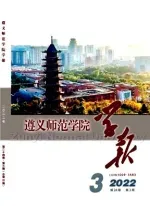小城的文化记忆——读石永言的《遵义往事》
夏 希
(遵义师范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上个世纪30-40年代,遵义是个典型的西部小城:人口不足十万,方圆不过十里,一条湘江河,连起新旧二城。小城不大,故事却多。“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遵义”的盛名又给小城增添了浓郁的文化色彩。
《遵义往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上下两册,收文200多篇,洋洋40万言,是著名作家石永言退休后献给故乡的心灵之歌,为正在向200万人口发展的“大遵义”留下珍贵的“小城文化记忆”。作为以长篇巨制闻名全国的“长征文学”作家,石永言“解甲归田”,心气和平,操刀短篇,自然游刃有余,别有一番风景。难怪他在《月是故乡明》的后记中说:“浮生近七十载,信笔涂鸦,我写下的文字,大多是关于故土的。无论长篇,还是短文。有一点影响的《遵义会议纪实》,不也是关于故乡昔日那段闪光岁月的回顾么?除了这本书外,《遵义往事》上下册,便是我比较喜欢的文字了。”
平民视角 故土情怀
《遵义往事》的装帧设计颇为考究,淡绿色的封面,影印一幅遵义城二十年代的老照片:群山环抱,一水中流,依稀可见湘江河上的跳蹬,曲折蜿蜒的城墙,鳞次栉比的瓦屋,丛林古木掩映的寺观庙宇,楼台亭阁……封面折页上有短短的几行作者简介:“石永言,贵州遵义老城小十字人。十六载学子生涯,半载舌耕,卅六载琵琶桥畔行走。解甲归田,虽年近古稀,仍不谙社会,书生本色,百无一用。”
读完全书,回头一望,重看封面,感受作者的心声,其间透露的是朴实的平民视角,浓烈的故土情怀。
故乡的树,记下生长的年轮;故乡的水,记下流逝的光阴。石永言出身平民之家,终身未离故土,成为著名作家,本色依然是一介书生,一介平民。1999年6月,雨季来临,铿锵的雨声翻印出儿时的苦境,引出了作者的《深夜听雨》:
髫龄之时,家居老城四方台一茅屋,只要一下雨,父母便叫苦不迭,特别是大雨,一家人便无法安睡。记得我常常在凄风苦雨的夜里,被母亲唤醒,说床顶的茅屋漏雨,朦胧中我翻身爬起,见地上的大小脚盆全积着深黄色的扬尘水,还一个劲的“叮当”“叮当”地嘀嗒个不停。……后来,我家搬进一间瓦房,……故屋面上的小青瓦受风雨、太阳、雪凝的隳蚀,逐渐有所损坏。雨小不要紧,雨稍大,瓦片断折的地方,便会浸滴下水来。如遇滂沱大雨,这瘦弱的、薄薄的、历经风雨折磨的小瓦片,不堪暴雨的欺凌,像一个羸弱无助的孩子,便会嚎啕大哭,屋内便落下它们的眼泪。……[1]
从茅屋到瓦房,风雨连绵,床头屋漏,瓦片流泪。深夜听雨,唤起儿时苦涩的回忆,文章一起三迭,联想到“世上定然还会有像我儿时与少年时居住过的茅屋与瓦房的人家,遇上这样连绵不辍的雨夜,他们也定然不得安眠。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恼人的雨夜的羁绊呢?”远方无尽,心事无穷,作家推己及人,悲天悯人,借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愿诗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不致于在夜雨中落空。进入小康,身居广厦,能有这种悲悯的作家不多,能写出这样文字的作家更是稀少。
童年苦涩,也有欢乐;小城荒寒,记忆温馨。《旧街印象》,留下小城遵义街头一景:
早晨七、八点钟,那坑坑洼洼的沙石路上,很少行人往来,只有背着书包上学堂的儿郎在那儿漫步。街檐,或有一两家卖泡粑、碗儿糕的人家,打开那热气腾腾的蒸笼,迎接儿童的到来。这时东家喂养的狗,西家饲养的犬,便纷纷破门而出,在大街游荡。玩得高兴了,它们便汪汪汪汪地疯狂起来,斗殴起来。彼此追逐着,狂吠着在街心奔窜,惹得上学的小儿郎也忘了上学的迟早,纷纷伫立街檐,看狗儿们打架。……[1]
生在小巷元天宫,长在老城小十字;故园山山水水,随手拈来,都是文章。《湘江漫步》,回忆儿童时代,江水清澈,曾用稚嫩柔弱的双肩,挑回一担担饮用的清水。《流连大龙山》,踏上古城墙,激起思古的幽情。《凤山极顶》,问莽莽青山,何处是亲人埋骨之地?《魂兮归来》,为诗人廖公弦周年作祭,长相忆,中学同窗,青春不再……
琵琶桥畔36年行走,永言先生“解甲归田”,重返童年。退休生活,天地广阔,心灵不被世俗干扰,将猥琐的东西暂时忘却,有了时间的自由支配,空间的自由行走,头脑的自由思考,从“知天命”而“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写小城的春夏秋冬,写百姓的油盐柴米,写人生的喜怒哀乐,事事都有自己的切身体验,笔下都有质朴的情愫淌流。底层的立场,平民的视角,故土的情怀,确立了《遵义往事》的文化品位。
唤醒往事 寻找“矿脉”
正如眼前的风雨唤醒儿时的往事,湘江的流水记录小城的沧桑,当岁月的新痕与历史的旧迹不期而遇,自然折射时代的变化。遥望当年,故园风景依依。岁月摧人,时间留下记忆,也剥蚀记忆。回忆使小城的文化得以延续,回忆把小城潜藏的文化矿脉寻找,以期有新的发现。《遵义往事》正做了这样的工作。
文化是活生生的历史,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背景。就文化而言,既有显在的物质文化,也有潜在的精神文化。(两种文化有时也互相融合)小城的文化记忆自然包括了这两种文化。作为典型物质形态的“三街六巷”,以及典型精神形态的民风、民俗,都沉淀于“遵义往事”的文化记忆之中。
“卅六载琵琶桥畔行走”,“琵琶桥”自然是《遵义往事》中具有标志性的“文化意象符号”。写于1998年8月的《琵琶桥》和写于2000年1月的《琵琶桥畔》,一短一长,虽有些微的重复,但仍各有千秋。琵琶桥— —“天顺酱园”——黔军师长柏辉章(后来的抗日名将)的官邸——遵义会议会址:一幢小楼牵动历史风云。琵琶桥——子尹路——三官楼——协台坝:一座小桥串连遵义“文脉”。琵琶桥,遵义还有几人知道?“而琵琶桥呢?早已被埋在宽宽的坦平的大道下面。琵琶之身以及它的弦轴、弦枕呢?也因城市的沧桑巨变几乎不复存在了,一如《遵义景致》所言:‘琵琶桥把琴弦断’……”
琵琶弦断,遗韵犹存,文脉深藏,待人找寻。就从琵琶桥畔,沿子尹路行走,遵义老城处处是一脚踩得出好多文化的地方。石永言用他的“街巷觅踪”、“旧景依稀”展示故园的“沧桑留痕”:纪念乡贤“西南巨儒”郑子尹而命名的子尹路,纪念开创遵义现代教育的清朝知府袁玉锡的玉锡路,湘江河畔的豆芽湾,和北京胡同媲美的捞沙巷……
雅有阳春白雪的风韵,俗有下里巴人的情怀,这些独具遵义特色的地名,比起时下流行的“南京路”、“香港路”、“幸福巷”等处处通行的标准化称谓,蕴含了更多的文化意味。
在街巷中探寻人生的足迹,唤醒小城往事,寻找文化“矿脉”,石永言用朴素的纪实和淡雅的抒情为遵义这座小城留下悠悠的“文化记忆”。
昔日遵义有“三街六巷九狮子”之说。三街即梧桐街、杨柳街、朝天街,梧桐街,朝天街早己消逝,惟有杨柳街还存留到今日。“杨柳街宽不过一丈……小巷中央的路是由一块接着一块的青石板铺筑的,日夜摩挲,成千上万只脚把青石板踩得极为光滑,几乎油光可鉴,形同古镜。”(《杨柳街》)杨柳枝、青石板、青瓦楼、标准小学、天主教堂、吴桥夜月、寻梦桃溪……有如晚来的清风荡起遵义人记忆的涟漪。
“洗马滩鸣”的卷地涛声早已成为山中的绝响,时下的洗马滩已无观赏的景色,逝去的不单单只是“八景之一”,还有小城的两座碾坊——罗家碾坊和柏家碾坊。石永言笔下的碾坊“简陋而阴冷。”它终日不知疲倦,“依着固定的轨迹,周而复始地忙碌着……”这两座碾坊位于湘江河畔,却是那时不可或缺的农业生产的作坊,因碾米修筑的堤坎又成了小城的两处天然浴场,深藏在小城美好的记忆之中……(《洗马滩》、《碾坊》)
“抛粱粑”是遵义人过去建房的习俗,此情已成笔下的追忆:当房屋要安放大梁时,“主人要工匠爬上安放大梁的两侧,将费力抬上去的葵花子、包谷花、泡粑之类的食品向房屋内外、四周簇拥着的人群抛洒”。围观的人们则在下面兴高采烈的接受“梁上君子”的馈赠。(《抛粮粑》)正月十五闹元宵,遵义城从十四的晚上就开始热闹了,一对对龙灯天一黑便上街了,玩龙灯的人赤裸着上身,举着一条条火龙,在蜿蜒的窄窄的街上翻腾。(《玩龙灯》)街道,巷子……彰显了小城文化的物化形态。羊肉粉,凉粉,炒米糖开水,烙粑……勾起“吃的回忆”,引出民风民俗,可以说,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形态凝聚了小城的集体记忆。
“中国传统处境的特征之一是‘匮乏经济’……在匮乏经济中主要的态度是‘知足’,知足是欲望的自限。……‘知足安分’凝成一种态度,成为处事要诀,得到了生存和平安。”[2]文化既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小城的生活方式无一不留下文化积淀的痕迹。百姓的日子是艰难的,小城的生活是安宁的。仿佛进入“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境界。石永言总是从自己的童年记忆里,把那些看似碎屑的日常小事,一丝一丝地抽出来,写出小城百姓一步步艰难走来的历程,也留下自己成长的脚印。炒菜锅上巴的那点油汁,母亲也要用一瓢白饭拿起锅铲来回焙干,这样的焙锅饭两个姐姐还没有资格来争。(《焙锅饭和淘米水》)“舀时是冒碗,筷子一撬是平碗,水一泡则是半碗,嘴一喝便成空碗的‘冒儿头’。”(《冒儿头》)“连有几个钱的财主也要节省一匹衣领来做布鞋,穿着形同无领的和尚服。”(《唠叨衣服》)一个瓷碗破了也要补好,就像鲁迅《风波》中六斤捧着的“十八个铜钉”的饭碗,“不像现在,再好的瓷碗哪怕是正宗景德镇的,打破了,一扔垃圾桶了事。”(《补碗匠》)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本源之处。”[3]《遵义往事》是诗人的心灵还乡,儿时记忆的种子历经几十年的尘封,终于回归故土,在古稀之年开出灿烂的花朵。
触摸历史 追寻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4]著名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那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4]《遵义往事》触摸历史,也是对文化传统的追寻。
借用著名作家汪曾祺的说法:“‘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是个边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5]小城遵义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一个文化概念。作家的小城,是印上特殊审美记忆的心灵情感的小城。逝者如斯,时间却为遵义文化留下一段光彩熠熠的黄金时代。
抗日军兴,遵义成为紧邻陪都重庆的京畿之地,大后方的文化重镇。浙江大学西迁,创建“东方剑桥”的奇迹;众多学校团体的涌入,众多文化名人的到来,遵义城头星光灿烂。竺可桢、梅光迪、张荫麟、费巩、吴宓、田汉、丰子恺、熊佛西、金克木、端木蕻良……他们在小城播下文化精神的种子,《遵义往事》留下他们的足迹。
《竺可桢与傅梦秋》写浙大校长竺可桢抗战期间要求师生“竭尽智能之有裨于黔省”,为遵义的文化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在碓窝井与房东傅梦秋结下的深厚友谊。傅梦秋对遵义文化颇有建树,却命运多舛,错划右派后仍忍辱负重,写出受到著名学者何其芳和吴世昌称赞的书稿。竺可桢对身处逆境的老朋友,关怀备至,一如既往,体现人之为人的宝贵品格,君子之风,山高水长。
浙大在遵义办学期间,条件艰苦,学生夜间学习连电灯都没有,只能用陶土烧制的土灯。费巩教授亲自动手改良,制作出光线明亮的铁皮油灯,并用自己节省的薪水定做了800多盏分送学生宿舍。“费巩灯”由此得名,进入了遵义寻常百姓家。费巩,这个闪着光亮的名字,遵义城中,又有几人知道?读读石永言的《费巩灯》:
出生在“上有天堂,下游苏杭”的苏州城中的费巩先生,在烽烟滚滚的1940年来到遵义小城,度过了他一生最有意义也是最光辉的数年!他主持正义,不畏强暴,在反动派前毫不妥协。“费巩灯”照耀着他和同学们一起奋斗。今天,每当历史文化名城遵义的夜色降临,湘江河畔一片万家灯火。这闪闪烁烁的万千灯火中,可晃动着五十多年前浙大学生学习时用过的“费巩灯”的影子……
1944年秋冬之交,著名学者吴宓在客居遵义的一个月,作过数次学术讲座,《红楼梦人物分析》更是吸引了普通的遵义人。中学教师、职员、店员,甚至泡茶馆的老头被都吴宓先生精彩的演讲所吸引;字正腔圆的语言,渊博的学识,听众无不为之惊叹、折服!(《吴宓的红楼梦讲座》)田汉在遵义期间,多次参加在杨柳街“悦来茶馆”由端木蕻良、熊佛西、丰子恺、蹇先艾、秦牧等人举办的文学讲座,他主讲戏剧,给小城的文学青年灌输戏剧知识。(《田汉在遵义》)抗战时期,生活艰难,学术大师让文学名著雅俗共赏,各路名家的讲座让偏僻小城视野开阔。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开启民智,凝聚民心,振奋民气,文化显示无坚不摧的力量。
《菩提寺下熊佛西》更是感人,不仅写著名戏剧家熊佛西抗战时期率领“西南文化垦殖团”来遵义,和妻子著名演员叶子改变山寺的艰苦生活为风雅的“诗意栖居”,还提及秦牧对端木蕻良的回忆。端木来到西南小城时,身体较差,常来这里“躺在梨树下的躺椅里……当雪白的梨花飘落下来,铺满他的身子,端木也不把落花拂去……在玉屏山菩提寺留下他病弱的身影。”[6]《协台坝里的端木蕻良》写他居住在协台坝16号时,曾寄出一封信给著名诗人戴望舒,除了在信中表达1942年离开香港连累友人入狱的致歉之外,还拜托他“分神照料一下浅水湾的萧红墓”。戴望舒接信后,“不负老友重托,独自一人长途跋涉,去浅水湾谒萧红墓。戴望舒十分珍惜端木这封发自遵义的信,……托付给老友施蛰存保存。直到1988年,这封铭刻着端木情与爱的书信,才终于被整理出来,编入新版《现代作家书简》。”[6]时局艰危,人情珍贵,“科尔沁旗草原诗人”由遵义寄出的这封信,联系着几位著名的作家,历经几多灾难的年月,谱写了一段文学的佳话,让我们听到了文学史轻轻翻动的声音。
除了外来的名流名家,石永言把更多的笔墨交付遵义的父老乡亲,其中既有进入史册的文化名人,也有不见经传的芸芸众生:如著名作家蔚豁楼主蹇先艾,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家王燕玉,历尽沧桑写沧桑的小说家石果,四中校长詹健伦,民国才女卢葆华,田园诗人廖公弦……如补碗匠、补锅匠、剃头匠,卖打药的“武林高手”,甚而吓唬小孩哭闹的“王疯子”,飞檐走壁的大盗“宋三”……从小城的人物世相,民俗民风中追寻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
土生土长,乡里乡亲,笔下充满乡土的气息;知根知底,亲身亲历,心灵流淌故园的温馨。唤醒记忆中的一件往事,一幅图画,一缕情思,《遵义往事》是石永言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文化思考和文学记录,具有特殊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反思,为远去的小城留下珍贵的文化记忆,为减少城市的文化失忆做了一份值得赞许的工作。
[1]石永言.遵义往事(下)[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189,29.
[2]费孝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115,118.
[3]海德格尔著,郜元宝译.人,诗意的安居——海德格尔语要[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87.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1,42.
[5]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五卷)[M].北京:北京师范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43
[6]石永言.遵义往事(上)[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4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