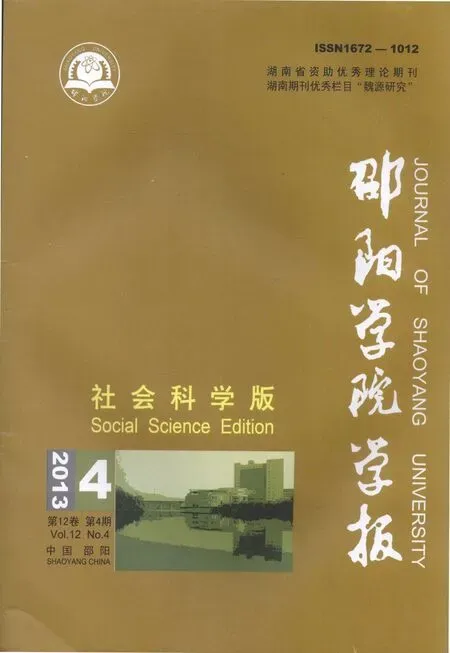译者审美趣味与诗歌中意象的创造性翻译
刘爱兰,龙玉梅
(广州大学 松田学院,广东 广州 511370)
一、引言
我国明代胡应麟总结中国诗歌的创作特点时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1](P121)。亚瑟·韦利认为“意象是诗歌的灵魂”。可见意象无论是在中国诗歌文化还是西 方诗歌文化中都是诗歌审美的重要范畴。意象的本质就是“意”与“象”的主客观统一,即诗歌情景的交融的审美意象。“美在意象”[2](P38),诗歌的美主要是通过诗歌的审美意象而实现的。因此,在翻译中能否再现原诗歌中意象是传达诗歌美的关键。郭沫若说“好的翻译等于创作”[3](P263),从而肯定了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译者翻译诗歌意象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译者对诗歌意象的审美认识和意象审美创造的过程。亚瑟·福尔柴尔Arthur H. R Fairchild 曾说:“诗人通过创造,读者通过欣赏新鲜的意象关联来发掘潜能、实现自我。[4](P125)在这个审美活动过程中,译者个人的审美趣味可定会影响他对诗歌意象的处理策略。“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语译者作为翻译过程的主体,意象之美还是要通过译者的审美活动才能生成。审美趣味是一个人的审美偏爱、审美标准、审美理想的总和(叶朗,2009)。审美趣味决定一个人的审美取向,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次的审美体验中的意象世界的生成。也就是说,审美趣味不同的人,在审美对象相同的审美活动中,如欣赏同样一首诗歌时,他们所体验到的美是不一样的。审美活动体验的不同,也决定了译者在翻译中是对诗歌意象不同审美情趣和不同的表现方式。译者的审美趣味是译者在审美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受到译者的家庭出生、阶级地位、文化教养、社会职业、生活方式、人生经历等多方面的影响。
二、译者个人审美情趣和意象的创作性翻译
本文旨在通过对苏曼殊(1884—1918)对罗伯特·彭斯的A Red,Red Rose 的译文来探讨译者的审美趣味是如何影响译者在翻译中对诗歌意象的审 美过程和译者对意象的创造性翻译。
A Red,Red Rose
O,my luve is like a red,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O,my luve is like the melodie,
That's sweetly played in tune.
As fair art thou,my bonie lass,
So deep in luve am I,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my dear,
Till a'the seas gang dry.
Till a'the seas gang dry,my dear,
And the rocks melt wi'the sun!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life shall run.
And fare thee weel,my only luve!
And fare thee weel,a while!
And I will come again,my luve,
Tho'it were ten thousand mile!
颍颍赤墙靡
颍颍赤墙靡,
首夏初发苞。
恻恻清商曲,
眇音何远姚。
予美谅夭绍,
幽情申自持。
仓海会流枯,
相爱无绝期。
仓海会流枯,
顽石烂炎熹。
微命属如缕,
相爱无绝期。
掺祛别予美,
离隔在须臾。
阿阳早日归,
万里莫踟蹰!
苏曼殊(1884—1918)译(1909)
英文诗歌中诗人主要是通过西方文化中一些传统的意象,如用“rose”来抒发自己对爱人的爱慕之情,用大海变枯竭(seas gang dry),石头与太阳融化(rocks melt wi'the sun)来烘托诗人爱之深沉。用生命之沙(sands o'life)来衬托超越时间的爱情。诗歌的意象清晰,语言纯朴自然。诗人罗伯特·彭斯在成为诗人之前是一个在苏格兰高地劳作的农民,诗人的灵感来自挥动的锄头和在劳累后的休息中,其语言充分利用了苏格兰民间歌谣,以农民的身份抒发自己对家乡、爱情、友情、自然和家乡人民的热爱。这首A Red,Red Rose 的爱情诗歌其风格与诗经中的《关鸠》一样以一种纯朴而自然的方式抒发对爱人的赞美之情,诗歌流露的是一种浪漫而乐观的趣味。诗歌的节奏可用下图表示:

诗人的情感开始是舒缓的,用玫瑰和音乐来表达对爱人的赞美,然后情感不断升华,最激昂时用大海枯竭,太阳把石头融化来表明爱的深度,然后情感逐渐缓下来用千里之隔来烘托爱情的忠贞。诗人的情感能够很好与诗歌中的景物相结合,情景交融,生成了鲜明的意象。
在译文中,苏曼殊采用是归化的翻译策略,没有读过原文的中文读者会误以为这是一首中文古诗。整个译文诗歌中风格就是典型中国传统爱情诗歌所流露出的哀怨趣味。“微命属如缕,相爱无绝期。”表达在生命即将结束时对爱情的哀怨,与原诗歌中流露的对爱情乐观情绪截然不同。苏曼殊的译文让读者想到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悲情和“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5](P10)译文的风格是哀艳的,伤感的,这种风格是很符合中国传统爱情诗歌的审美趣味。译者的个人审美趣味就是要把这首诗歌翻译成他所希望的那种传统的爱情哀怨诗。诗歌哀怨的趣味也很好与诗歌中的“蔷薇”和“清商曲”的意象相结合,生成译者所期望的审美意象。
可见译文诗歌中意象的生成是译者在审美活动的过程中生成的。这个过程中译者的审美价值、审美趣味、审美格调、审美理想都会影响到译者对诗歌意象的诠释和对诗歌的审美。
苏曼殊作为译者,在翻译中已经加入自己审美趣味。在他看来,这样悲情而哀艳的爱才是美的,是符合其审美趣味的。而他的这种审美趣味和审美价值也是和自己不幸的人生经历和爱情经历分不开的。苏曼殊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广东人,苏曼殊在出生3 个月,母亲就离开了他,由父亲带回广东。童年的苏曼殊没有家庭的温情,倍受冷漠,族人对这个异族所生的孩子总是看不顺眼。12岁时苏曼殊大病一场,被家人扔在柴房里气息奄奄,不过他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一经历给幼小的曼殊以沉重的打击,以至他小小年纪竟然看破红尘,出了家。然而因为年少不懂寺庙的规矩,被驱逐了庙门。十五岁那年,苏曼殊去日本横滨求学,与日本姑娘菊子一见钟情。然而,他们的恋情却遭到苏家的强烈反对,斥责苏曼殊败坏了苏家名声,并问罪于菊子父母。菊子父母盛怒之下,当众痛打了菊子,结果当天夜里菊子投海而死。菊子的命运让苏曼殊深感悲痛和无奈。回到广州后,他便去蒲涧寺出了家,法名博经,法号曼殊。后来,他以自己与菊子的初恋为题材创作了情爱小说《断鸿零雁记》,感慨幽冥永隔的爱恋之苦。在诗歌《樱花落》中写道:
十日樱花作意开,绕花岂惜日千回?
昨来风雨偏相厄,谁向人天诉此哀?
忍见胡沙埋艳骨,休将清泪滴深杯。
李荣融担任国资委主任时期,就遇到过乘坐某央企航班晚点,通过秘书希望得到晚点的解释时吃闭门羹的情况。而不兼任党委书记的国资委主任,虽然是行政一把手,但党务还要倚重党委书记及其主持的党委委员会。这也是为什么在蒋洁敏被调查及被免职后,国资委仍能平稳运行、不受太大冲击的原因之一。
多情漫向他年忆,一寸春心早巳灰。
诗歌以樱花来写逝去的恋人,悲伤之情读来令人柔肠寸断。可见苏曼殊本身还是一个多情之人。1909 年,他在东京的一场小型音乐会上认识了弹筝女百助。因相似的遭遇,两人一见如故。但此时的曼殊已了却尘缘,无以相投,便垂泪挥毫,写了一首诗:“鸟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爱情的破灭让苏曼殊对人世间的爱情已经不抱任何的希望,在他的眼里,爱情只是痛苦,是“相爱无绝期”的生死两茫茫。这种悲情的爱情也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苏曼殊对爱情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价值,在他的眼里,一首乐观而浪漫的爱情诗歌,也被蒙上自己悲情的色彩,也许在他看来天底下所有爱情的故事都像他的爱情故事那样令人心碎,悲情使爱情更具有审美价值。
三、译者所处时代的审美情趣和意象的创作性翻译
当然,苏曼殊作为一个文人,其个人的审美趣味,必然受到其反映时代、民族、文化教养、文化传统、习俗的社会审美趣味的影响。美和审美活动是社会性的,每个时代对美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每一代的美都是应该是为那一代而存在”(叶朗,2009)。在中国爱情诗歌文化中更多是推崇爱情的悲情哀怨,而这就是爱情美的本质。这也是中国古代爱情诗歌的一种时尚。所以当苏曼殊用一种归化的策略来翻译这首诗歌的时候,诗歌呈现的就是一种悲情和哀怨的爱情,这符合译者的审美趣味,也符合中国传统爱情诗歌的审美趣味。爱的美是通过爱悲剧而不是喜剧的方式来体现的。两千年前诗经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表现出来的甜蜜而浪漫的爱情在后来传统封建文学中已经是寥寥无几。在传统诗歌文化中,爱情一般都是割断柔肠的悲切:从“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苏武《结发为夫妻》)(文箐、肖乐阳,2010),“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上邪》),“结发公枕席,黄泉共为有。”(《孔雀东南飞》),“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苏小小《苏小小歌》)直至“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汉乐府《上邪》)。
正是译者的个人审美趣味和社会审美趣味,决定了他在诗歌的情感处理上没有重现原诗歌中浪漫而乐观的爱情观。因此,从诗歌意象的翻译来看,译文中情感(意)已经与原诗歌中情感不一样了,一种乐观的趣味变为一种伤感的趣味。在这种审美趣味下,诗人对原诗歌中“O,my luve is like a red,red rose”的翻译没有保留诗歌明喻的修辞。原诗歌中是意象“rose”来赞美爱人(my luve)的美丽和歌颂爱情的美好。“rose”是一个鲜明的意象,它是“luve”爱情的象征。玫瑰在拉丁语系中的读音为“洛斯”。此名的由来在罗马神话中有这样的传说:花神佛洛拉(Flora)对爱神阿摩尔(Amor)并没有感情,而且长期以来躲着他。一天,狡猾的阿摩尔用爱情之箭射中了她,从此佛洛拉为之倾心,可是爱神喜新厌旧,最后抛弃了佛洛拉。女神佛洛拉失望之余决心创造一种会哭会笑,集悲喜于一身的花来自慰。女神看到自己神奇的造物,惊喜得不禁喊出心爱的人的名字“厄洛斯”(这是希腊人对爱神的称呼)。但由于生性腼腆,心情激动,她讷讷喊成了“洛斯”,把“厄”喊漏了,从此这种花就得名“洛斯”(英语为“ROSE”)。因此西方文化中“rose”就是一种爱情的象征,成为一个文化意象。Rose(玫瑰)也是西方诗人爱情的宠儿,不同颜色的玫瑰赋予不同的内涵,但其本质还是love(爱情)。如John Boyle O'Reilly (1844-1890)的A White Rose在诗人的眼里,a white rose(白玫瑰)所代表的是爱情a red rose (红玫瑰)代表的是更纯洁、更温柔芬芳。
A White Rose
The red rose whispers of passion,
And the white rose breathes of love;
Oh,the red rose is a falcon,
And the white rose is a dove.
But I send you a cream-white rosebud,
With a flush on its petal tips;
For the love that is purest and sweetest
Has a kiss of desire on the lips.
一朵白玫瑰
红色的玫瑰呢喃着爱的激情,
白色的玫瑰呼吸却是爱的芬芳。
哦,如果红玫瑰是一只猎鹰,
那么,白玫瑰就是只和平鸽。
愿送你一朵雪花白的玫瑰花,
花瓣上还带有一丝丝的羞涩;
因为最纯洁最甜蜜的爱情
是期待给嘴唇送去一个吻。
(笔者译)
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玫瑰”并不是一种象征爱情的文化意象。玫瑰名字的由来据《说文》中有:“玫,石之美者,瑰,珠圆好者”,就是说“玫”是玉石中最美的,“瑰”是珠宝中最美的。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也有“其石则赤玉玫瑰”的说法。即使后来玫瑰变成了花的名字,在中国诗歌文化中也没有西方文化中的那般柔情万种。如诗歌“千万枝,恰似红豆寄相思。玫瑰花开香如海,正是家家酒熟时。”诗歌中“玫瑰”虽然与思念有些关联,但是与爱情没有密切的关联。
可见苏曼殊在翻译“rose”的时候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它,玫瑰失去了象征爱情的意象。译者是采用归化的策略,把rose 翻译成了“墙靡”。墙靡就是蔷薇,在《本草经》中蔷薇也叫墙靡,因草蔓柔蘼,依墙援而生,故名墙靡。从植物学的角度蔷薇和玫瑰虽然都属蔷薇科,但并不是同一种花。当然译者更多是从文化上的考虑,因为在中国诗歌文化中“蔷薇”比“玫瑰”似乎有更多的韵味。如秦观的诗: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诗人通过芍药和蔷薇等春花遭受摧折而油然产生怜香惜玉之感。而李白的《忆东山其一》: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
诗歌中也是通过自然景色蔷薇、白云、明月的变换来抒发诗人对东山的美景的留恋。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蔷薇的景色可勾起人的怜爱和回忆之情,但是似乎与男女间的爱情无关。
而对于melodie 的翻译,译者翻译成“清商曲”,失去了原诗歌中所体现的诗歌的悠扬和甜美(sweetly),其翻译的策略和翻译rose 是一样的。在中国文化中清商曲为古代五音之一,其调凄清悲凉。在传统诗歌中情商曲流露的是悲切的哀怨趣味。如:
玉柱泠泠对寒雪,清商怨徵声何切。谁怜楚客向隅时,一片愁心与弦绝。(杨世源,《雪中听筝》)
清商欲尽奏,奏苦血沾衣。他日伤心极,征人白骨归。相逢恐恨过,故作发声微。不见秋云动,悲风稍稍飞。(杜甫,《秋笛子》)
在中国传统诗歌文化中清商曲就是让人心碎,能撕人心肺的声音。应该说译者苏曼殊把melody翻译成“清商曲”,就给整个诗歌蒙上了一层感伤的趣味。“蔷薇”、“清商曲”与诗歌中“仓海会流枯,相爱无绝期。”所流露的伤感之情应该是很好的结合起来,做到了情景交融,译文中诗歌的意象也得以生成,也能够让人体会到译文诗歌的情景交融而生成的诗歌美。
译文中其他的所用词汇也是采用归化的手法,用的都是古诗歌味道的古文。对原文中对爱人的称呼“thou”翻译成“予美”,“予美”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汇。《诗·陈风·防有鹊巢》中有“谁侜予美,心焉忉忉。”和《诗·唐风·葛生》中的“予美亡此,谁与独处。”指代的都是所爱的人。译文把“fair”(美丽)翻译成“夭绍”,“夭绍”取自《诗经》中“桃之夭夭”美丽而娇艳的意思。而对于诗歌中“fare thee weel”中的“farewell”(再见)翻译成了“掺祛”。诗歌《送倪正父尚书守南徐》有:友朋罕有心相照,兄弟惟应姓不同。此别未知何日见,掺祛无语对西风。其中“掺祛”就是告别的意思。可见译者苏曼殊对整个诗歌的翻译采用的是一种归化的策略,毕竟苏曼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人,当时诗歌基本还是文言文创作,这也是符合当时读者的审美趣味。
四、结语
从苏曼殊译文可见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其个人的审美趣味对诗歌意象翻译创作的影响。当然,其个人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价值和当时整个社会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价值是分不开的。译文使用了归化的策略来处理诗歌,让诗歌的意象呈现出中国古诗歌爱情的悲切和凄美的审美意象,这本身就是译者的再创造活动。译者对诗歌意象的理解和诠释蒙上浓厚的个人审美趣味和文化审美趣味,从而让译文加入了很多自我的元素。茅盾先生曾经说过:“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境界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诗歌意象的美感在翻译中由于不同语言本质和文化意象的差异,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的流失,因此“译者必须为译作增加新的美感。”[7]舒曼殊在翻译中增加译作的美感,尽管这些美感是来自译者个人和其社会的审美情绪和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歌意象翻译中的“美”原则就是求“真”。这种“真”不是机械地在译文的语言里找到原诗歌意象的对应物,而是追求艺术审美效果的一致,因为“美在意象”,意象的本质在其审美价值。
[1]胡雪冈.意象范畴的流变[M].南昌:白花文艺出版社,2009.
[2]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4]黎志敏.诗学构建:形式与意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文箐,肖乐阳.中国古典爱情诗歌[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
[6]曹明伦.关于弗罗斯特若干书名、篇名和一句名言的翻译[J].中国翻译,2002,(4):52-55.
[7]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岭南历史文化名人图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