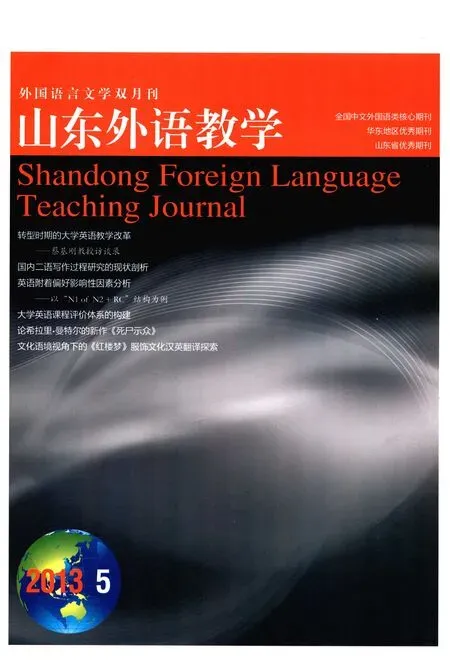英语附着偏好影响性因素分析
——以“N1 of N2+RC”结构为例
王军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
英语附着偏好影响性因素分析
——以“N1 of N2+RC”结构为例
王军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
句中的某一语言成分C在既可能修饰A也可能修饰B的情况下通常都是用来修饰A或B,这种对所修饰对象选择的倾向性即为“附着偏好”(attachment preference)。附着偏好有多种类型,但本文主要关注英语“N1 of N2+RC”结构,从句法结构、释义原则及假设几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地回顾并分析了前人的相关研究,认为“N1 of N2+RC”结构本身不具有任何的附着倾向性,是语言实际使用过程中的某些特定的因素,如RC的长度、复杂名词短语类型、性及数的一致关系、搭配频率、隐性韵律等,导致了附着偏好的产生。
附着偏好;关系从句;影响因素;“N1 of N2+RC”
1.0 导言
所谓“附着偏好”(attachment preference),是指当句中的某一个语言成分M在既可能修饰语言成分A也可能修饰语言成分B的情况下,M通常都被用来修饰A或者B。如图1所示:

图1 附着偏好
在某一特定的句法结构中,如果M通常都是用来修饰线形距离较远的A,就被称作“高附着”形式(high attachment);反之,M若通常都用来修饰临近的B,则被称作“低附着”形式(low attachment)。无论是高附着还是低附着,一般都是指一种相对较高的附着概率,并不一定意味着始终只存在一种附着取向。例如:
(1)Laura ran away with the man wearing a green robe.(分词短语)(O’Brien et al.,2012:1)
(2)Tap the frog with the flower.(介词短语)(O’Brien et al.,2012:3)
(3)Someone shot the servant of the actress who was on the balcony.(关系从句)(Jun,2010:1202)
(4)Jack met the friend he had phoned yesterday.(副词)
英语通常被认为是低附着的语言(Jun,2010: 1202;Carreiras&Clifton,1999),尽管这一倾向并不突出(W itzel et al.,2012:422),但却很容易在表达中形成歧义结构。在(1)-(4)中,有直下划线的词语是修饰语,而有波纹线的词语是被修饰的词语,修饰语可以是分词短语、介词短语、关系从句或者副词等,而被修饰的成分既可能是名词,也可能是动词,甚至是其他词类。附着结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语法修饰关系结构,但由于其最明显的表现特征是修饰语与被修饰语之间在线性距离上的远近对照关系,于是就被形象地标示为“高附着”或“低附着”结构。附着偏好现象非常复杂,形成原因涉及句法、语义、一致,甚至语言文化心理等方面。例如,有研究发现(Gilboy et al.,1995;另见Traxler et al.,1998:562),对于英语及西班牙语中特定的复杂名词短语后面跟修饰语的结构来说,复杂名词短语的类型不同,修饰语附着偏好也可能会完全不同。这会导致不仅笼统地谈论某种语言具有哪种附着偏好不恰当,而且较为笼统地谈论某一种可引起附着偏好的句法结构(如复杂名词短语后跟修饰语的结构)也存在较大风险。较为稳妥的办法是进一步限定附着偏好结构,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正因为如此,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仅限英语的“N1 of N2+ RC”(名词1 of名词2+关系从句)结构。
2.0 句法结构性因素的作用
检验句法关系偏好的一种常用方法是对语义歧义进行检验(Gilboy et al.,1995;Cuetos&Mitchell,1988),为此,Traxler et al.(1998)设计了一个实验,让受试对(5)中所代表的三种情形的句子进行语义可接受性的判断,通过记录受试眼睛注视目标句时间的长短来确定该句的语义可接受性以及句法结构的正确性。根据以往的研究(如Clifton,1993),当受试对句子语义的解读出现问题时,他们的视线就会在目标句上停留相对较长的时间,而视线的停留时间越短,说明目标句的可接受性就越高。
(5)a.The driver of the car that had the moustache was pretty cool.(高附着)
b.The car of the driver that had the moustache was pretty cool.(低附着)
c.The son of the driver that had the moustache was pretty cool.(高/低附着)(Traxler et al.,1998: 563)
实验表明,与(5)a和(5)b相比,受试在读取(5)c时所花费的时间(reading time)相对较短。虽然这一结果与最初的预测相反,即原本在出现相互竞争的被修饰对象时受试的读取时间应该更长,但实验者认为这恰恰说明受试在解读时并未受到歧义结构的干扰,而是直接选择了个人最热衷的被修饰对象N2,并据此认为这体现出这类结构具有较强的低附着倾向。然而我们认为(5)c的设计存在一个很大的语义缺陷,因为在父子之间,长胡子的更可能被认为是父亲而非儿子,所以受试多选择低附着的形式并非是结构使然,而是语义搭配关系造成的。
此外,对于(5)a和(5)b来说,虽然它们分属于高附着和低附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但在可接受性上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关键原因就是特定的语义关系(the driver-that had the moustache)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类似的情况还包括性(如(6))、数(如(7))等的一致关系。例如:
(6)a.The son of the actress who shot herself on the set was under investigation.(低附着)
b.The son of the actress who shot him self on the set was under investigation.(高附着)
(7)a.The bottle of the capsules that have bright color is very popular.(高附着)
b.The bottle of the capsules that has bright color is very popular.(低附着)
因此,英语即便属于低附着的语言,这种低附着的取向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弱的,或者说句法制约因素在低附着取向方面的作用是很有限的(W itzel et al.,2012:422)。
句法结构、词汇语义以及语境等因素在附着结构中的作用还与语言使用者的自身条件有很大的关系。下面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和较高水平的二语学习者为例进行说明。
根据Clahsen&Felser(2006),母语为英语的儿童与成年人的解歧策略上存在很大差异,儿童不太善于使用词汇语义及语用信息,而是更多地依赖句法结构信息,即便在通过语义信息获得的解释不恰当的情况下也会如此(Traxler,2002)。当然,儿童所依赖的句法结构信息并不复杂,而是选取了最为简单的以邻近原则(locality princip le)为基础的低附着结构,而且对于那些工作记忆相对较小的儿童来说更是这样。而对于母语为汉语的较高水平的英语学习者来说,研究发现(Witzel et al.,2012)他们的解歧策略较少依赖句法结构信息,而是更多地依赖词汇语义信息,以高附着解读为主。Clahsen&Felser (2006)曾为此形象地提出过一个“低位结构假设”(Shallow Structure Hypothesis,SSH),意指二语习得者的句法结构使用水平较低,对语法了解不细致,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语义、语用等非结构性信息进行解歧。
此外,关于“N1 of N2+RC”本身结构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结合其他内容进行分析。
3.0 就近原则与述谓临近原则
跨语言对比研究可能让研究者在语言的差异和相互影响中发现某些单一语言研究所发现不了的规律。为了找到解释附着倾向性的原因,人们除了研究歧义结构外,还进行跨语言对比研究。
Gibson et al.(1996)在研究英语和西班牙语时发现,附着取向的跨语言差异源于两个对立原则相对作用的大小,这两个原则是:“基于结构的就近原则”(the structured-based locality princip les of recency)和“述谓临近原则”(predicate proximity)。如果遵循第一个原则,语言使用者在语法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往往会把新的语言信息与刚加工过的成分联系在一起,这在“N1 of N2+RC”结构中就表现为低附着的形式。如果RC与N1和N2之间存在歧义,语言使用者倾向于选择低附着的形式。而如果遵循第二个原则,语言使用者会把修饰语与在结构上最靠近句子谓语的成分联系在一起,即与谓语的论元联系在一起,由此获得一个高附着的解读。
与英语通常被认为是低附着语言不同,希腊语、德语和汉语都被认为是高附着的语言。Felser et al.(2003)通过对母语是希腊语和德语的英语学习者进行研究发现,当他们在解读英语中的歧义附着结构时,既没有像母语是英语的人那样表现出低附着的倾向性,也没有受母语的影响而表现出高附着的倾向性。W itzel et al.(2012)的研究对象是母语是英语的语言使用者和母语是汉语的高水平英语使用者,对比研究结果显示,母语是英语的语言使用者普遍表现出低附着的解读倾向,而母语是汉语的英语使用者却表现出与汉语相同的高附着的倾向性,说明他们似乎在遵循“述谓临近原则”。两项对比研究的结果相反,同样母语是高附着的语言,但对英语附着歧义结构的解读方式却不一样。“低位结构假设”虽然能够解释汉语二语习得的情况,但却无法解释希腊语和德语。这里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母语的附着倾向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不能简单地用正负迁移来解释,而必须弄清楚母语附着结构与英语存在哪些差异。以汉英语为例,英语的附着结构可以表达为“N1 of N2 +RC”,但汉语一是几乎不会出现后置条件句的情况,二是没有类似英语的“N1 of N2”结构。汉语的所有格结构是“修饰语+(的)+中心词”,这在英语中也有类似的结构。但即便如此,其中的修饰语在英汉语中也具有不同的特点:汉语的前置修饰语可短可长,而英语前置修饰语的长度却要受到很大限制。考虑到种种不确定的因素,我们就很难弄清楚在附着偏好问题上母语的干扰究竟有多大。
有研究(Felser et al.,2003)发现,在“N1 of N2 +RC”结构中,介词of的作用不容小觑,这可以从与介词with的对比中看出来。例如:
(8)The doctor recognized the nurse of(w ith) the pupil who was feeling very tired.
当例(8)中的介词of被替换成w ith时,受试都会认为who was feeling very tired修饰的是the pupil,原因是with作为一个语义内容丰富的(semantically contentful)介词可以在其后面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辖域,受试对后续修饰语的解读也被限定在这一辖域之内(Frazier&Clifton,1996)。而介词of就无法产生这种效果,of只是提示两个成分具有所有关系,无法建立类似with那样的辖域,这就使得“N1 of N2”之后的修饰语既可以根据“N1 of N2”的结构重心关系修饰N1,也可根据就近原则修饰N2。
4.0 调谐假设
“调谐假设”(tuning hypothesis)原本是用来对跨语言附着取向差异进行阐释时提出来的(Mitchell&Cuetos,1991),其基本含义是:结构性的歧义可以通过以往所遇到的解歧结构的出现频率来解决,换句话说,当你以往不断地遇到某一歧义结构,而且总是使用相同的方式进行解歧,这种解歧方式使用多了,就会慢慢稳定下来,形成一种特定的解歧模式(Witzel et al.,2012:446-447)。因此,对于低附着偏好的语言来说,正是由于人们在语言使用中不断接触这种低附着的结构,人们的思维就倾向于在遇到附着歧义结构时首先选择低附着的解读方式。
大量证据显示,选择某一个结构关系而非另外一个的决定会受到刚刚完成的一个类似任务的影响(Branigan et al.,1995),即便这一任务是两星期前完成的也是如此(Cuetos et al.,1996),这说明个人以往的语言接触史会让某些语言结构特征固定下来,成为解读新接触的语言材料的指南。然而,任何基于以往经验的决策机制都必须有赖于对相关经验特征进行记录和储存(Mitchell et al.,1995:470),以便于把当前的材料与先前储存的材料进行比对。对于先前储存的材料是以精细记录(fine-grained records)还是以粗糙记录(coarse-grained records)的方式存在,是更多地以词汇语义的形式存在,还是以结构的方式存在,长期以来存在很大争议。Mitchell et al.(1995)根据前人的研究总结出三种模式:精细模式(fine-grained model)、混合模式(mixed-grain model)和粗糙模式(coarse-grained model),并且在经过详细论证之后认为,对于“N1 of N2+RC”结构来说,在对以往个人接触过的各种实例的记忆中,不可能包含名词的各种语义信息(这就否认了精细模式),所保存的能够对将来的语言任务起作用的信息主要是句法结构信息。
如果调谐假设支持的是粗糙模式,这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未能表现出低附着偏好的问题,原因就在于与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相比,二语学习者接触“N1 of N2+ RC”结构的机会要少得多,难以形成以结构关系偏好为基础的一般解读模式。这类似于“低位结构假设”效应,因为两者均认为二语学习者句法结构知识偏弱是导致他们与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但不同之处在于,“低位结构假设”所说的句法结构是指语言使用者当前所掌握的句法结构知识,而粗糙模式所说的句法结构是指语言使用者通过对包含特定句法结构(如此处所讲得“N1 of N2+RC”)的语句反复使用后所抽象出来的结构。只有弄清楚结构性因素的性质,才能够进一步去思考母语的结构特征对二语学习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5.0 韵律与隐性韵律假设
所谓“韵律”(prosody),指的是在音高、音响、语速及节奏方面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与话语的声学特征相关。有研究认为,说话者在进行表达时,会使用某些韵律特征把某些句法成分聚集起来,为语句增加一套基于韵律的结构关系。(Nespor&Vogel,1986;O’Brien et al.,2012)当然,增加的这套韵律结构关系要与原有的句法结构相吻合,其最大的作用是能够让有歧义的句法关系或不甚清楚的句法关系更加清晰可辨。最为典型的韵律特征是停顿(pause)。很多研究都认为,“停顿是英语中最为可靠的解歧线索”(O’Brien et al.,2012:4;另见Cooper&Paccia-Cooper,1980;Snedeker&Trueswell,2003)。Lehiste(1973)(见Wagner&Wagner,2010: 907)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持续时间(duration)对于区分句法歧义最为可靠,包括三种情况:边界前语音拖长(pre-boundary lengthening)、停顿(pauses)和前辖域语音强化(domain-initial strengthening)。Lovric et al.(2000,2001)也发现,在N1 of N2+ RC结构中,说话者会把RC前的韵律空缺(prosodic break)(即停顿)视作一个强烈的句法边界标记,进行高附着解读;如果没有这一韵律空缺,则进行低附着解读。
与一般的韵律研究以口语材料为主不同,Fodor (1998;2002)使用的是书面语材料。她通过实验手段发现,受试在默读书面文本时,某些韵律特征与口语是一致的,而且也往往符合实际的句法结构划分。这些韵律特征体现的是一种在一般或称中性聚焦条件下所形成的韵律短语结构(the p rosodic phrasing produced in broad/neutral focus condition),或者说是脱离特定篇章语境时的短语结构(Jun,2010:1203)。简单地说,就是任何一个句子都有一个常规的韵律短语结构(default prosodic phrasing),它不受语境变化的干扰。由于这种韵律结构内嵌在书面语中,所以被称作“隐性韵律”(implicit prosody)。大量的英语书面语料显示,RC越短,低附着的可能性越高;如果RC比较长,则往往需要高附着的解读,这种现象具有跨语言的共性特征(Fodor,2002:121;Jun,2010:1203-1204)。Fodor(2002:122)经实验发现,RC在较短的情况下(如who cried),其前面出现韵律空缺的可能性较小,而当RC较长的时候(如who cried all through the night),其前面出现韵律空缺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原因是较短的RC结构“自身无法自然构成一个像样的短语”,所以需要同与其相邻的名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较长的RC结构不存在这一问题。对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如果RC在较短的情况下修饰N1,则RC(经过简单的结构调整后)使用前置的方式更为合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RC后置,则往往意味着不修饰N1,而是修饰N2。如果RC较长,它就很难(经过结构调整后)采用前置的方式去修饰N1,复杂RC的后置是修饰N1的最佳选择,而由于RC较长的缘故,在RC之前稍作停顿会使语气更加平缓。这种停顿与人的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较小有关,工作记忆的容量与短语结构的长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见Fodor,2002:121),而停顿是标示短语结构的一个重要手段,即便在对书面语的默读过程中也是如此。
6.0 评述及研究展望
根据前面的分析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我们可以把那些影响附着结构的因素归纳如下:
1)结构性因素:包括RC的长度和复杂名词短语的类型。RC的长度越长,高附着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低附着的可能性就越大。伴随着RC长度的增加,RC前面出现韵律空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成为高附着取向的一个重要标记。
2)语义因素:性、数一致关系以及常规语义搭配关系会对附着偏好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3)韵律因素:说话的人可以通过停顿、加大音长、使用重音等手段标示句法结构制约关系,而听话人也可以根据这些韵律特征更准确地把握句法修饰关系。即便在书面文体中,韵律特征也在起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句法结构的形态和限定关系。
3)语言使用者的个体差异:母语为英语的儿童和成年人对附着结构具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其中儿童,尤其是工作记忆相对较小的儿童,较多地依赖句法结构信息,更容易选择基于邻近原则的低附着解读方式,而成年人会综合考虑句法、语义、语用等各种相关因素。另外,母语为英语和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成年人也表现出了不同的附着解读模式。
4)语言知识储备:个人的英语语言接触史会对当前的附着结构解读带来一定的影响,因为以往的经验会逐渐沉淀下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解读模式。二语学习者英语知识的匮乏,尤其是句法结构知识掌握得不牢固,会让他们很容易受到母语解读模式的干扰。
我们可以把前面所提到的各种阐释原则、理论及假设分成两大类,即结构决定论和经验决定论,前者包括句法结构因素、就近原则、述谓临近原则,后者包括调谐假设、韵律与隐性韵律假设。结构决定论是从共时的角度看问题,旨在描述附着结构的现状;而经验决定论则是从历时的角度看问题,探究当前附着结构的成因。两者并非是矛盾和对立的,都是对语言事实的一种概括,只是概括的路径不同而已。语言的使用能够创造某些句法结构,但是当某一语言已经发展到成熟稳定状态以后,这种创造性就会受到很大的制约,而最为常见的现象是语言使用不断强化或削弱某些句法结构特征,使得不同的句法结构特征在语言使用中的突显程度千差万别,这表现在“N1 of N2+RC”结构中就是附着偏好的问题。
英语“N1 of N2+RC”结构本身体现不出任何附着偏好,原因有两点:一是“N1 of N2”结构中N1的中心词效应(即中心词更容易成为被修饰的对象)与“N2+RC”表现的就近原则效应相互抵消,使得RC无法与任何一个名词建立强势的结构联系。二是介词of的语义内涵贫乏,仅仅表达一种所有关系,无法像前面所提到的with那样能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语义范畴,即无法对“N1 of N2”之外的结构施加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RC就与N1和N2之间维系着一种较好的结构性修饰平衡关系,也就是说,单纯从结构上讲,RC修饰N1或是修饰N2均属于正常情形。以往的研究之所以得出英语属于低附着或无附着偏好语言的结论,完全是语言使用导致的。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可能并未意识到“N1 of N2+RC”结构本身无附着偏好的特点,而是更多地使用RC必须修饰中心词(即N1)的策略,从而导致高附着偏好的产生。母语是英语的低水平学习者所表现出的低附着偏好也是与他们坚持单一的临近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RC修饰N1这一中心词既是一种结构修饰关系,也是一种语义修饰关系,因为对后者来说,处在结构中心的词语其语义突显程度也比较高,更容易成为被修饰的对象。由于汉语重意合轻形合的特点,选择语义中心作为被修饰的对象是件比较自然的事情。
国内对附着偏好的研究极少,潘欣、张文鹏(2007)只是简单介绍了国外的一些相关研究,而周英、敖锋(2009)的实证研究也只涉及with介词短语结构,未提到研究得最多的of介词短语结构。
国外对附着偏好的研究大都使用心理实验的手段从歧义结构入手来进行,或者采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手段来统计分析附着偏好的概率,还有就是采用跨语言对比的方式来揭示不同语言的附着偏好特征,这些都是我们将来进行研究时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国外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重语言使用,轻结构分析,较少把结构分析与语言使用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在跨语言的对比分析中,国外很多研究似乎都未注意到“N1 of N2+RC”结构在不同语言中的表现方式实际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果缺乏一个共同的对比基础,后续的对比分析就会误入歧途,这在英汉对比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对“N1 of N2+RC”结构的研究也需要与其他附着结构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发掘其中存在的共同的理解及表达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把对附着结构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1]Branigan,H.,M.J.Pickering,S.P.Liversedge,A.J.Stewart&T.P.Urbach.Syntactic priming:Investigating the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language[J].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1995,24:489-506.
[2]Carreiras,M.&C.Jr.Clifton.Another word on parsing relative clauses:Eyetracking evidence from Spanish and English[J].Memory&Cognition,1999,27:826-833.
[3]Clahsen,H.&C.Felser.Continuity and shallow structures in language processing[J].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2006,27:107-126.
[4]Clifton,C.Jr.Thematic roles in sentence parsing[J].Canadia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1993,47:222-246.
[5]Cooper,W.E.&J.Paccia-Cooper.Syntax andSpeech[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6]Cuetos,F.&D.C.M itchell.Cross-linguistic differences in parsing: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the Late Closure strategy in Spanish[J].Cognition,1988,30:73-105.
[7]Cuetos,F.,D.C.Mitchell&M.Corley.Parsing in different languages[A].In M.Carreiras et al.(eds.).Language Processing in Spanish,Mahwah,NJ:LEA.1996.145-187.
[8]Felser,C.,L.Roberts,R.Gross&T.Marinis.The processing of ambiguous sentences by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of English[J].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2003,24:453-489.
[9]Fodor,J.D.Learning to parse[J].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1998,27(2):285-319.
[10]Fodor,J.D.Prosodic disambiguation in silent reading[J].NELS,2002,32:113-132.
[11]Frazier,L.&C.Clifton.Construal[M].Cambridge,MA:MIT Press,1996.
[12]Gibson,E.,N.Pearlmutter,E.Canseco-Gonzalez&G.H ickok.Recency preference in the human sentence processingmechanism:Evidence from English and Spanish[J].Cognition,1996,59:23-59.
[13]Gilboy,E.J.,M.Sopena,C.Jr.Clifton&L.Frazier.Argument structure and association preferences in Spanish and English compound NPs[J].Cognition,1995,54:131-167.
[14]Jun,Sun-Ah.The imp licit prosody hypothesis and overt prosody in English[J].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2010,25(7/8/9):1201-1233.
[15]Lehiste,I.Suprasegmentals[M].Cambridge,MA:M IT Press,1973.
[16]Lovric,N.,D.Brad ley&J.D.Fodor RC attachment in Groatian with and without preposition[N].Poster presented at the AMLaP Conference,Leiden,2000.
[17]Lovric,N.,D.Brad ley&J.D.Fodor.Silent p rosody resolves syntactic ambiguities:Evidence from Groatian[N].Presented at the SUNY/ CUNY/NYU conference,Stonybrook,NY,2001.
[18]M itchell,D.C.&F.Cuetos.The origins of parsing strategies[A].In C.Sm ith(ed.).Current Issue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C].Austin,TX:University of Texas,Center for Cognitive Science,1991.1-12.
[19]M itchell,D.C.,F.Cuetos,M.M.B.Corley&M.Brysbaert.Exposure-based models of human parsing:Evidence for the use of coarsegrained(non lexical)statistical records[J].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1995,24 (6):469-488.
[20]Nespor,M&I.Vogel.Prosodic Phonology[M].Dordrecht:Foris,1986.
[21]O’Brien,M.G.,C.N.Jackson&C.E.Gardner.Cross-linguistic differences in prosodic cues to syntactic disambiguation in German and English[J].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2012,1-44.doi:10.1017/S0142716412000252.
[22]Snedeker,J.&J.Trueswell.Using prosody to avoid ambiguity:Effects of speaker awareness and referential context[J].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2003,48:103-130.
[23]Traxler,M.Plausibility and subcategorization preference in children’s processing of temporarily ambiguous sentences:Evidence from selfpaced reading[J].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2002,55A:75-96.
[24]Traxler,M.,M.J.Pickering&C.Jr.Clifton.Adjunct attachment is not a form of lexical ambiguity resolution[J].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1998,39:558-592.
[25]Wagner,M.&D.G.Wagner.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advances in prosody:A review[J].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2010,25(7/8/9):905-945.
[26]W itzel,J.,N.W itzel&J.Nicol.Deeper than shallow:Evidence for structure-based parsing biases in second-language sentence[J].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2012,33:419-456.
[27]潘欣,张文鹏.含挂靠歧义的英语关系从句认知处理研究[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2):75-78.
[28]周英,敖锋.中国英语学习者with介词短语挂靠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6):49-54.
On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Attachment Preference in English—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N1 of N2+RC”Structure
WANG 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006,China)
In caseswhere component C has possibilities ofmodifying either component A or component B,C in real situations ismore frequently used tomodify A or B.This choice preference between C and A or C and B iswhat is called attachment preference.Attachment preference consists ofmany types,but this paper focuses on“N1 of N2 +RC”only.A lot of literaturewill be reviewed and analyzed concerning syntactic structure,interpretation principles and hypotheses.It is proposed that“N1 of N2+RC”itself does not contain any biasof attachment,and what determines its bias is related to the factors that only take effect in the actual use of language,including the length of RC,type of noun-phrase complex,agreement of gender or number,frequency of collocation,implicit prosody,and so on.
attachment preference;RC;relevant factors;“N1 of N2+RC”
H043
A
1002-2643(2013)05-0030-06
2013-01-20
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概念匹配、释义与连通的衔接功能语用研究”(项目编号:13BYY149)和2012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模糊照应的功能认知研究”(项目编号:12YYB004)阶段性成果。
王军(1966-),男,汉族,山东荣成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