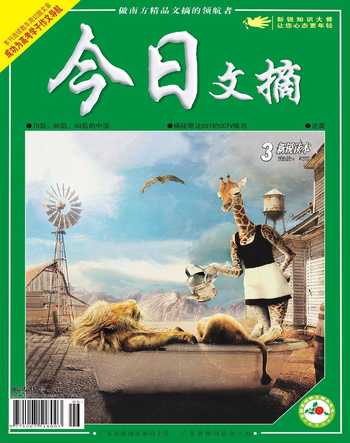北京四中的自由氛围
张宇凌
最具神话特色的中国式教育来自名牌中学而非名牌大学。由于产业化和严进宽出的制度,中国高校如今乏善可陈,而高考制度的相对公正,使得高中,尤其是名牌高中为荣誉而战的尊严感代代延续。在每年的高考季,都会有一份中国中学百强名单在民间流传,这些中学无论地处首都还是小城镇,都集聚了当地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他们聪慧、勤奋、坚韧、专注,取得的成绩也如此巨大。如果说中国的基础教育独具长处的话,那么,这些学校就是代表,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精英教育。
出生在四川外公外婆大家族溺爱娇宠的环境中,我小时候是基本靠家教,常常满山跑的野孩子。初中来到北京,进入爷爷奶奶生活的军事大院,经历了从南到北,从野放生长到机械化大规模培养。
后来考上了当时只有高中部的四中,我的感觉和别人不一样,没感到有多少竞争威胁,没感到有什么高人一等,也没感到什么雄心大志更进一步,而是觉得,终于找到我想要的自由了。
首先,四中的教学非常有效率,老师不会留大量课外作业,而是要求你课内的高度专注。记得我崇拜的数学老师是瞎了一只眼的瘦小老头儿,他是最有武侠效果的一位,常常单手一挥,就在黑板上画出一个比用圆规还圆的图形。他常常是边写题目,就边嚷嚷着:“快说答案,谁知道了谁站起来说。”如果有同学站起来说对了,他也就不讲解了。英语老师语速奇快,一堂课除了讲解新的知识要点之外,有时候要做两三张卷子,他觉得没必要留到课后去做,课后多看点外国电影比较有帮助。连我喜爱的体育课也是高密度的,上来先来个八百米之类的,来例假的女生也必须到场,不许在旁边坐着,要保持轻度运动。
语文老师则觉得除了古文课和鲁迅的小说要好好讲解之外,其他很多篇幅也没什么太多值得唠叨的,所以语文课上得最轻松灵活。比如有段时间每堂课要请一个同学来讲自己喜欢的古诗词。记得一位父母离异的女生,上台讲元稹的一系列悼亡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怪来醒后旁人泣,醉里时时错问君”……她讲完了好几首之后,加了句结语:“不过,元稹在夫人苇丛死的当年,就跟薛涛在成都同居了,两年后又纳了别的女子做妾。”她说那句话时并无特殊语调表情,我却再也不能忘怀。之后她又是我的北大同学,爱上一位总是穿着长衫布鞋的中文系师兄,每当这对著名情侣走过校园,只有我在心中默念,那是她的元稹吧?
作文题目十分宽泛。我自己就常常写诗,写童话,最受欢迎的一篇是纯粹用对话来表现,把班上同学都写成各种虫子,因为吃了不同的书而有不同的语气和说话方式。
课堂效率高,课后自由时间就特别多。学校不占用自由时间,只在体育方面有要求。高三时要求同学们三点后必须离开教室去锻炼一个小时。不论男女,必须学会打篮球和游泳才能毕业。学校不开办课后辅导班,同学们也不去参加课外辅导,奥数是真正属于数学天才们的兴趣小组。
还有很多供自由挑选的兴趣小组,最有影响的要算学生电视台。电视台节目每天不同,所以工作量相当大,课间常见到有人在采访。有个学生摄影师还学《红高粱》里拍棺材板子的手法,躺在地上拍被四个旗手擎起的旗帜。我当时只参加了生物小组,做了不少无土栽培送到天安门作为装饰盆花。我还参加了《北京青年报》的学通社,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到不同的地方去玩。那时候的学通社,就是一帮不安分的孩子,想有个正式名头去看他们自己无法打开的世界。学通社的大本营在朝阳门内的九爷府,我常常放学后(作业必须在课间赶完)一车从厂桥骑到九爷府,跟着大家四处采访,再一车骑回甘家口的航天大院,到家已经是睡觉时间了。老师们都很支持我的兴趣,发表文章的报纸常常被张贴在报刊栏,或是拿来当堂诵读,连理科老师们都来跟我讨论。
四中给学生的自由,还体现在对情感的尊重上。我们班上有两对高中恋人现在已经成为夫妻。当时就有很多人出双入对,没老师在的时候牵个手,只要不影响学习,不在公众场合过分亲密,老师一点儿也不会干涉。一位师兄曾经在老师询问他是不是早恋时回答,没事的,恋着恋着就不早了。记得我因为家远而有一段时间住宿,后来因为不能晚上熬夜看书和写东西而退住了。那时住宿生对冬天六点起来晨跑都唉声叹气,只有一个姑娘总是精神百倍,提前半小时摸黑爬起来把自己梳妆得性感给力,高高的大马尾左一摆右一晃。我问她怎么能那么有动力,她咧着大嘴一笑,说了句:“爱情呗。”原来她每天都会在晨跑的时候远远和另一队中的男友眉目传情,而且晨跑后他们要一起去食堂吃早饭。这个叫肖丹的姑娘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就因为她在还没开灯的幽暗宿舍里让我第一次正式听到那个词,而且是作为她自己的宣言。
回想起来,四中在当时作为一个资历比北大还古老的学校,确实有一种成熟宽大的大家风范,对很多小事不会莫名惊诧纠结,也把它的孩子们都当作大人来对待。
就是在上四中期间,在这个学校给学生的自由和尊重之中,我才有机会去认识北京这个城市,去采访白血病患者、少管所的少年犯、弥留的老学者、年轻的武打明星……给摇滚歌手写歌词,在电台做夜间节目,参加电影拍摄……甚至为了毕业舞会而一口气学会了所有的交际舞。也正是在这三年中,我结交了许多直到如今都联系紧密的朋友。
今天,人们常常提起四中是个高干子弟汇集的地方。我是在高二时读图书馆里的陈凯歌自传《龙血树》时才有一点点了解,后来在同学聚会上又听说薄瓜瓜成了学弟时加深了一点印象。我没有资历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古,或是论21世纪的今,只能以自身的经历来负责地说,1991年到1994年在那个学校的时候,没有一个孩子是来拼爹的,我们全体同学都是通过正规考试进入学校的,也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校门上大学或出国的。我们平时的相处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以家庭背景而自傲,或是更受其他人欢迎。我们都骑自行车上下学。这真不是在标榜自己的同辈,只是庆幸自己的青春,还属于一个比较单纯的年代。
痛心而坚定地说,今天我不会再期待即将出生的孩子去四中读书,因为不知道需要参加多少蹲坑班、奥数班,要被迫利用多少家庭社会的各方力量,才能熬到那个我熟悉的校门。而在这过程中间,可怕的并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孩子在人格上成为一个体制性竞争中的势利小人。
从四中毕业后,我始终对人的社会位阶、财富指数反应非常迟钝,对许多所谓的野心和大志也提不起兴趣。后来从北大去法国学了八年中世纪艺术史,回国后没进高校而是去了成都山野里一间专门搜集西南中古石雕的博物馆,现在则专心地做家庭主妇。我心目中最精彩和英雄的人物,一直是那些不懈努力寻求自由,去投入他们自己选择的生活的人。如果亲爱的读者非要问北京四中这学校有什么精英观和理想主义,“自由”这两个字,其实是人生最奢侈的两个字,这就是当年的四中给我的精英观和理想主义。
(作者系1994年北京四中毕业生,后来在北京大学与巴黎索邦大学学习艺术史,现为自由撰稿人)
(杨源荐自《经济观察报》)
责编:小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