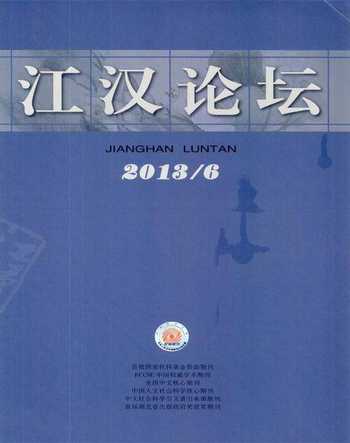论旷达之美
黄丹纳
摘要: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必须走出“以西释中”的历史性误区,从事实出发,独立地探求中国古代美学独有的概念、范畴的哲学基础、人生底蕴及其在艺术实践中的创造规律,以确认中国古代美学特有的民族特征、历史特征,还原中国古代美学的固有面貌。“旷达之美”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审美形态。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里,士大夫文人着意追求的一种生命境界。它根本不能纳入以张扬感性为特征的西方近代美学体系。旷达之美的美学内蕴是以老庄、儒家哲学为基础,以中国古代士大夫生命追求为底蕴,在艺术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游戏人生”、“回归自然”、“自我超越”和“超越自我”等四种生命境界及相应的审美创造。
关键词:“以西释中”误区;旷达之美;生命境界;回归自然;超越自我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6-0102-05
一、旷达之美的哲学基础
起源于中国本土的以道家、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都共同地把宇宙看作是“生生不息”、“变化无穷”的生命流程和自然而然、不可名状的宏大系统。《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云:“生生之谓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天地之大德日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里的“生”是“自生”;“化”是“自化”。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都是广义的生命的不同形态,都是自生、自化、自然而然的,既非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创造,也“不是某种绝对的精神实体的自我展开”①。这种举世无双的大生命宇宙哲学就是中国士大夫文人生命观、人生观的经典依据。具体来说,中国古代的大生命宇宙哲学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
第一,人的生命从哪里来?人的生命是在自然而然形成的宇宙大生命流程中,自然而然生成的。《老子》云:“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的“生”,自生也,是指自然而然的生成。人的生命同宇宙万物一样,也是一个从“无”到“有”,又归于“无”的自然而然、自生自化的流程。老、庄和儒家都认为,万物以及人的生命。都是由阴阳二气自然而然生成的。《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之“道”,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最高实体,而是宇宙万物的终极本原,是一种超越人的感知能力之上的终极性的真实存在,故谓之“无”。“道生一”就是“无”生“有”,“一”是一团内含阴、阳而尚未分化的混沌的大气。“二”就是由“一”分化而成的阴、阳二气。“三”就是阴阳二气交合而成的冲和之气:它是生成万物的基质。也有人说“二”是天和地。其实,天、地就是阴、阳二气凝聚成的最大的有形之物。《庄子》云:“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这就具体描述了“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自然而然的过程。宣颖在注解这段话时说:“阴阳互为其根。”可见它不是西方哲学中的二元对立之物,而是互涵、互动、互变的,既有分别而又终归一体的、两种属性不同的“气”。作为万物之一的人。也不例外,《庄子》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儒家的经典中,也表述了和老、庄基本相同的大生命宇宙观。《周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乾坤,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这生动的性隐喻,更具体地揭示了“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宇宙万物都是在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中自然而然、自生自化的真谛。
第二,人在宇宙大生命流程中的位置。在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生命流程中,人和天、地并称为“三”,是万物中有灵性、最尊贵的存在。《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与道、天、地并称“四大”,可见人在宇宙大生命流程中的位置之重要。人是万物中最具灵性的。《周易》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立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以立天之道,日阴日阳;立地之道,日柔日刚:立人之道,日仁日义。兼三才而两之……”可见,人不仅是与天地并立的,而且能以其灵性认知和揭示天地的奥秘。人是宇宙大生命流程中的一部分,是万物中的一物,这就规定了人不仅有生存的权利,也有生存的义务;所谓“立人之道”就是说,作为宇宙大生命中的一分子,人不是消极被动的存在,而是自觉的主体。不过,这个“主体”不是西方哲学中与自然、客体对立,甚至规范自然、客体之存在的无限膨胀的“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人,来自自然,归于自然,“是宇宙大生命中平等的一员”②,它有灵性,因而也有责任。所以,人要好好认识自己在宇宙大生命流程中的位置,知道应该以怎样的“智慧”对待自身和万物。
第三,人应该如何对待自身和万物?在这个问题上,老庄和儒家的观点差别较大。简单地说就是老庄主张顺应自然,本真地生存;儒家主张效法自然,自觉地生存。《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老子认为人的生命是自然万物之一,人应该服从这一自然法则,自然地、本真地生存,这便是他的“法自然”的生命观。他认为体道的人,就是顺应自然的、身心自由的人。在《老子》中,“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一句,即充分说明了他的这一观点。人,既不能以主观意志强加给万物而改造万物,也不能以主观意志强加给他人而改造他人,“一切顺其自然就是最大的生存智慧”③。特别是,人不能过于追求声、色、货、利、功名、权势,而伤身损性、破坏自然之道,因为人的自然生命是最可贵的。《老子》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即充分证实了他的这一观点。可见,老子追求的生命境界,就是不为情欲、物欲伤身损性,一切顺应自然;本真地生存就是智慧地生存、诗性地生存、审美地生存。老子为人们追求旷达的生命境界奠定了哲学基础。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所建立的大生命宇宙哲学的人生观。他对人的生命有着最为透彻的感悟——“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日天放”,这无非是在说。人的生命本身,有其自然之性,衣食住行不过是生命的本能,浑同自然万物而无偏私,因任自然就是自由自在;人的一切活动都不能违背这一自然常性。既然这样,我们又何必为物欲、情欲所扰,不将个体生命顺应自然,从而获得身心的愉悦,以达到生命自由自在、和谐快乐的境界呢?
至于先秦儒家,在生命观方面作出系统论述的是孟子。他把人的生命划分为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两个层面。自然本性是指人的肉体及其自然的生理需求,如《孟子·尽心下》所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社会本性是指“天”赋予人的“善”的本性,如《孟子·告子上》所说的:“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不过,在儒家看来,人的生命的两个层面不是并立的,而是有“大”有“小”、有“本”有“末”的。孟子认为,人的肉体本性为“小体”,人的社会本性为“大体”,人要获得个体生命的完满,必须养其大者,节制小者,逐步把自己潜在的天赋善性变成自己现实的优秀品格,并落实在行动上,乃至对社会人生、家、国、天下作出重大贡献。也就是《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告子上》有云:“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均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日: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得夺也。”可见,在孟子看来,人先天具备的潜能只有经过后天的不断努力,锲而不舍,才能达到现实的自觉,否则就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本性受到了限制,而不是任其自然。《孟子·告子上》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可见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性,要想把它们化为现实的人性,就必须不断加强自我修养。正像《周易》所指出的那样,人要效法天,以“自强不息”;效法地,以“厚德载物”,将自然变成自觉,才能实现人的本性。这当然不是自然地生存,而是自觉地生存。
那么,当人的社会本性无法实现的时候,他们是以怎样的生存智慧面对人生的呢?——“不得志,独行其道”,“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可见,儒士们在不得志的时候,依然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那就是修养身心,从而完成自己的天赋善性,获得内心的完满、自由,“主动选择能让自己快乐、充实的人生之路”④。“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进则进,当退则退,既不固执,也不消极。不是要超越现实人生的一切限制而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而是直面现实人生,按照现实条件去争取个体人格的完满、心灵的自由。其实,这也是一种“旷达”。如果说,老庄学派的生命观、自由观、人生观及其所追求旷达之美的生命境界富于浪漫的理想色彩,那么,儒家的生命观、自由观、人生观及其追求的旷达之美的生命境界,则具有现实的可实践性。
二、体现旷达之美的四种生命境界
从我国古代士大夫文人的生命观、人生观中可以看出,儒、道二家都追求生存得合“道”、生存得和谐、生存得快乐而有益,这种生命的美好境界,就是旷达的美学义蕴。“何如尊酒。日往烟萝。花覆茅檐,疏雨相过。倒酒既尽,杖藜行歌”,这六句描绘的自然、自由的生存境况昭示了旷达之美的生命境界。但这只是旷达之美的一种形态,确切地说是身处唐末乱世的司空图在现实人生的无奈中选择的、可以实现的旷达之美的生命境界。如果全面地加以概括,旷达之美的生命境界,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游戏人生。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随着“人”自身的不断发展,“人”的内涵的不断丰富,人对“人”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也就是“人”历史地、逐步地走向自觉的过程。从殷、周之际到春秋、战国,人逐步走出了“神道”迷雾的笼罩而发现了“社会性总体人”(儒家)和“自然性总体人”(老、庄),也就是把每一个人都看作一切人的社会性或自然性的共同本性的体现。而发展到了汉末魏晋时期,人又逐步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换言之,就是人把“人”的“类本真”越来越明确地看作一个个鲜活的肉体生命。于是,中国古人从“总体人”的发现,逐步跃升到了个体人肉体生命的自觉。人们对此产生的第一反应就是开始着意追求肉体生命的快乐,追求肉体感官的享受。这当然是在最浅层次的意义上,对人的肉体生命的自觉。但它毕竟初步丰富、发展乃至改变了先秦以来“总体人”的观念的历史内涵,标志着“个体人生命意识觉醒时代”的到来。这种新的文化思潮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最典型的要属《古诗十九首》了。
《古诗十九首》这组诗歌所体现出来的“游戏人生”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看透了肉体生命的短暂,认为不能虚度人生,于是把享受肉体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及时行乐就成了人们的普遍追求。《驱车上东门》:“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今日良宴会》:“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青青陵上柏》:“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还有《生年不满百》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人生既然如此短暂,管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要务就是吃好、喝好、穿好、玩好,还要掌握权势,以为保障。于是,放纵生命、及时行乐,成为人们共同追求的生命境界。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内容不同、意义不同的“人”的解放运动,但几乎每一次都是从情欲、物欲的解放入手,这大概是个铁定的规律。此类作品所展示的自由、旷达的生命境界,虽然带有一定的消极色彩,但从人性发展的历程着眼,仍具有不容忽视的革新意义和审美价值。
另一方面则是对人的自然、合理的情欲有了正面肯定,男女之情被纳入审美领域。细细玩味,有的作品在表达上甚至是赤裸裸地、毫无拘束地直陈对情欲、肉体、感官满足的渴望。《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青青河畔草》写道:“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冉冉孤生竹》说:“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涉江采芙蓉》:“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客从远方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南朝徐陵编《玉台新咏》专收“艳歌”,开卷所选就是《古诗十九首》。可见,所谓专以男女之情为审美对象的“六朝艳歌”,《古诗十九首》首开其端。它不仅影响了整个的六朝诗风,而且为此后的历代“艳体”诗歌提供了范本,并把原属本能性的情欲,提升为旷达之美生命境界的有机部分。马克思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人历史地向着“人”的生成的过程。人性自身的丰富内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展开的。在审美层面上将情欲、肉体的价值铺展开来,把它作为“旷达”之美的一层意蕴,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不过,这种“游戏人生”的旷达之境,毕竟是对生命意义表层的理解。随着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士大夫文人对生命意义认识的不断深入,生命中“旷达之美”的境界也在向着更高的境界提升。
第二,回归自然。回归自然即是向人的本真回归,使人的个体生命与自然亲和,回归田园,退守林泉。从而超越官场、超越苦恼,做个真正自由的我,以保持内心的宁静和适意,获得生命的美感。我国中古时期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就是回归自然的典型代表。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之际。这一时期,个体人对短暂生命的超越已成了十分自觉的行为。再加上陶渊明汲取了道家因任自然、旷达自适的思想,就铸成了他淡薄、高雅的自由人格。他不与世同浊,坚持真我,宁愿过得清贫些,也不愿为了“五斗米”而委身于污浊的官场,于是弃官不做,飘然归隐,以获得身与心的双重解脱。正如《归去来兮辞》中所说的:“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一开头还像是在自我宽解,但接着“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就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回归自然亦即重获自由的欢欣。
回归后的陶渊明开始了躬耕的生活,虽然田间劳作是辛苦的,但农村的自然风光,与农民之间质朴的人际关系,给了他“欣然有托”、回归“真我”的淳朴的欢畅。《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些诗句所展示的生活,表面上看显得劳苦、孤寂,可细细咀嚼,一个“沾”,一个“悠然”,确是发自心底的欢畅,是活泼泼的。回归田园后的陶渊明,与自然、与农民有着淳朴、和谐的人际关系,完全进入了与“天和”,与“人和”的生命境界。《归园田居》其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五:“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濯我足。漉我新熟酒,双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五柳先生传》:“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这不就是回归人的本真吗?这种本真、自由的生命之境不就是一种“旷达之美”吗?
第三,自我超越。自我超越即是在人生境遇难以改变或无须改变的情况下,自觉地从精神层面跳出现实的苦难和挫折,而获得身心的解脱。所谓“大隐隐于朝”,想开了,无所谓身在何处。苏轼就是自我超越的典型代表。
苏轼的后半生基本上是在迁谪中度过的。可他却有着旷达自适的情怀,无论身处何境,都能找到生命的乐趣,都能实现自我生命的价值。被贬至琼州(今海南)后,他并没有颓废自放,反而积极调整心态,为琼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直面现实,在现实的苦难中安顿生命,以求自适。他自觉地与自然环境相融,与当地百姓相融,不仅“九死南荒吾不恨”,还享受了“兹游奇绝冠平生”的奇乐、大乐:“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疯。”“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在《谪居三适三首》中。诗人由“旦起理发”,到“午窗坐睡”,至“夜卧濯足”,谪居生活中难以想象的困苦不仅了无痕迹。还在字里行间洋溢着超迈的情致。读来令人忍俊不禁。请看《旦起理发》:“解放不可期,枯柳岂易逢。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翁。”《午窗坐睡》:“身心两不见,息息安且久。睡蛇本亦无,何用钩与手。神凝疑夜禅,体适剧卯酒。我生有定数,禄尽空余寿。”《夜卧濯足》:“土无重腿药,独以薪水瘳。谁能更包裹,冠履装沐猴。”这逸趣横生的诗句,决非含泪的微笑可比,而是自由生命的生动写照!
作于黄州的《定风波》一词,也尽显苏轼自我超越的旷达情怀:“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风雨袭来,处变不惊;风雨过后,笑看人生。“道是无情还有情”,在苏轼看来,这就是生活的本真!
第四,超越自我。“超越自我”和“自我超越”虽然同属于“旷达之美”的范畴。但却是两种不同的生命境界。如果说“回归自然”、“自我超越”是个体人“感性生命”自觉后向老庄式“自然性总体人”的提升,那么,“超越自我”则是个体人生命意识自觉后向儒家“社会性总体人”的突进。其共同点则是:参透生死,达观人生。而其差别则可以说:前者是老庄式的“旷达”;后者则带有儒家的色彩,而在对待有限生命的问题上,超越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接近于对“治国、平天下”的执著。其特点是:以积极的态度、奋进的方式对待自我短暂的生命,争取人生价值的最大化。这是一向被人忽略的另一种“旷达”。当然,单纯的奋发有为、济世安民、建丰功伟业,这不属于“旷达”的范畴。但敢于正视生命短暂,通达天人之理,不以人生苦短而颓然自放,顺天而与天争,则是“旷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物为数不多,曹操大概是最典型的一个。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杰出诗人的曹操,他奋发有为不是出于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纲领,而是出于对短暂个体生命的感悟。在他的诗作中处处流荡着鲜明强烈的生命意识。他对生命的必然既有无奈,又不甘心;既要顺应,又要抗争,总在必然性与可能性之间,争取人生的最大空间。旷者,放也;达者,通也。不以必然自限,不以修短挂怀,放飞生命,自由翱翔,还不算“旷达”么?他的一曲《短歌行》真是另类的生命咏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是对生命的无奈!“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看似消极之思,实为诗情转折。“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呼唤贤士归来,追求建功立业,超越自然的有限生命,争取最大的生命价值;超越一己小我,营造无限大我,这还不算旷达的生命之歌吗?《龟虽寿》则竟是直面生命与天抗争了:“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媵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观沧海》写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小沧海,大宇宙,树木百草,秋风洪波,日月星汉,好一组大生命的灵动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