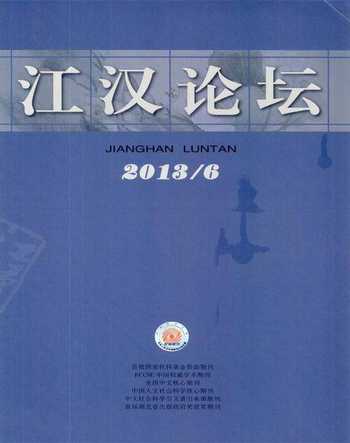自由主义权利与儒家的德性
[韩]李承焕
一、德性或权利?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迷恋权利的时代。不但在企业组织和工会中,而且在我们的学校与邻里之间,我们都会听到:“我的权利,不是我的责任”,“我的权利,不是我的义务”,以及“我的权利,不是我行为的后果”——我的权利,而当我的自私的生活方式崩溃的时候,你会承担起责任么,你会理会我的义务么,你会克服我的行为的后果么?
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会对这种态度感到惊诧。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它正在成为一种公认的日常生活的观点。在哲学领域,我们听到这样一种主张:撇开权利,我们就无法做道德哲学——“一种不以权利为基础的而又为人所普遍接受的道德理论是不可能存在的”。观察一下当代社会伦理学各种典型的模式。我们就会感受到人们狂热地热衷于权利和诉讼的热度。道德问题之被提出、争论及解决,所依靠的单单只是权利这一准法律术语。在当代,权利是这样一种占支配地位的道德价值,以致于不但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问题,而且连人类与非人类主体之间的问题也要按照权利的观点来看待。正如理查德·摩根(Richard Morgan)新著的标题所示,我们正生活在一种“权利产业”的支配之下。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我有意轻视权利在我们的道德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本文中,我所想要提出的问题在于权利运用不当之危险,易言之,在某些不合适的情形之下,个体顽固地坚持权利或许会有导向“作错事的权利”,或者“严重麻木不仁的权利”的危险。
与基于权利的自由主义道德形成对照的是,儒家提供了另一种根本不同的道德图景。作为一种基于德性的道德,儒家所重视的不是权利上的要求或自作主张,而是关怀与仁爱之德性。儒家道德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不在于一个人要作为独立自主的存在者而存在,而在于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君子)。与权利优先于善的自由主义不同,儒家则认为成为一个好人优先于做一个权利的主张者。
儒家认为自作主张不利于维护社会和谐。在儒家伦理框架中,被认为具有第一位重要性的不是程序正义或者个体权利,而在于成为一个仁者。儒家所要构建的社会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的集合体,而是一个由道德的个体所组成的集合体,这些道德的个体处于与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之间的和谐的关系之中。因此,儒家强调德性相对于权利的优先性、实质正义相对于程序正义的优先性,以及共善相对于合理利己主义的优先性。总之,儒家关注的不是一种自主的道德,而是一种和谐相处的道德:不是个人主义,而是一种有机的整体论。
无论是基于权利的道德(rights based morality),还是儒家的基于德性的道德(virtue-based morality),我们都会在其中发现极端的情形。照儒家的看法,对于维持与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言,谦逊与仁慈之德性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正如乔尔·费因伯格(Joel Feinberg)所指出的,“在适当的情形之下,一个人拥有某种权利而不去要求行使这种权利就是缺乏生气或者愚蠢的”。另一方面,照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拥有权利是件好事,因为它使我们能够“以人的方式而存在”。然而,在某些不适当的情形下,坚持权利并非必然地会帮助我们“以人的方式而存在”,反而导致我们成了冷血的“权利狂”。在某些时候要求权利并不会展现要求者的自尊,相反,“它所暴露的只是他对于其所看到的一个严重麻木不仁的、对抗性的世界的放纵的恼怒”。
即使在适当的情形中也从不坚持权利的人在道德上是奴性的,而对于坚持权利太过热心的人,在某些时候,在道德上就是麻木不仁的⑨。这两种极端的道德观点能够调和起来吗?儒家基于德性的道德与个体权利之间是可以调和的吗?换句话说,儒学能够在保留德性的实质内容的同时,将个体权利纳入到其伦理学框架之中吗?反过来。一种基于权利的道德在其伦理架构内部能够接受社群主义的德性而不丧失其保护个体的自主和自由不受任意干涉之功能吗?
二、自由或共善?
基于权利的道德与儒家基于德性的道德在当代韩国的争论可以追溯到一个更深的根源——对自由和共善的不同强调,而这二者则分别是西方自由主义与韩国儒学的出发点。
自由主义是一种将自由作为其它价值之基础根源的道德与政治论点。自由主义者争辩说,所有(道德的和政治的)价值和原则都源自于最终的自由之根源。作为一种对有利于自由的假设的支持,自由主义者赞同不干涉原则。没有正当的理由,任何人都不应当干涉他人——而如果一个人没有妨碍他人,那么他就可以做任何事情。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刑事)法律的目的仅仅在于防止个体之间相互伤害。道德的目的仅仅在于通过最大限度的不干涉,来确保行为与选择上更多的选择权,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目的。
自由主义者将所有相互竞争的生活图景都看作同样的好。一个人只要不伤害他人,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那么他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可以其喜欢的任何方式来过自己的生活。宽容是自由主义的第一美德。自由主义者不愿接受那种将一种生活图景凌驾于另一种生活图景之上的公共政策。作为道德原则,他们仅仅在乎的就是不干涉或者不伤害。在自由主义中,所缺乏的是一种好的生活的图景(a vision of a good life)。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在我们这个纷繁的世界中,自由因其给我们以较多的选择与较少的干涉而无庸置疑地是一种重要的善。然而,较多的选择与较少的干扰就会承诺带来一种真正意义的自由吗?儒家会提出,较多的选择与较少的干扰并不必然等同于真正的自由。按照儒家的观点,即使存在着开放的选择权,一个人如果不能克服自己内在的限制(较低层次的欲望或者第一序的欲望),就还是不能达到自由。按照儒家的观点,在获得真正的自由的过程中,首要的是克己(serf-overcoming)、修己(self-cultivation)与成己(self-realization)。儒家忠告我们应当将目光转向我们自己而不是外部的环境。比如射箭,如果我们未能射中靶心,那么,儒家会忠告我们既不要抱怨风,也不要抱怨箭,而要责备我们自己。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礼记·中庸》)
儒家主张,真正的自由并不能通过确保更多的选择权来获得,而是通过自然地(又是有意地)将共同体规范内在化以克服较低层次的欲望来获得的。简而言之,对于儒家来说,在一种对(行为主体认为值得遵守的)共同体规范的有道德地、自发地遵守之中,可以发现真正意义的自由。与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体权利形成对照的是,儒家的社群主义将德性一品质概念(the concept of virtues-quali-ties)置于中心地位,一个人要成功地增进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共善,德性一品质就是必不可少的。在儒家学者的心目中,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是一种贫乏的自由观,因为它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消极自由,而缺失一种对好的生活的向往。孔子,如果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将会赞同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关于自由主义自由观是“单薄的”和“缺乏内在的意义”的说法。孔子也会赞同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lntyre)关于自由主义的自我是从“叙事性历史”中抽离出来的、缺乏“品格”和“社会同一性”的说法。
儒家道德观是一种充满抱负的道德观。它所交付给我们的是一种我们应该努力成就的品格,一种我们应该尽力达到的人格,一种我们应该设法建设的共同体。然而,自由主义者则会对儒家自由观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对“极权主义的威胁”(totalitarian menace)产生怀疑。自由主义者所担心的正是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称之为“可怕的扮演”(monstrous impersonation)的东西,它往往存在于以代表诸如政府、民族、阶级或历史规律等超个人的、集体性的真实自我的名义,而对人们真实的愿望实施压制的行动之中。按照伯林的说法,自我实现的政治教条是一种忽视人或社会的真实愿望的立场,而且它还以代表他们的真实自我的名义来威吓、压迫,甚至折磨他们。在一种可靠的知识中,无论人类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它都必须与人类的自由——人类真实的自我(尽管是隐没不彰的、不假言辞的)的自由选择——是同一的。
与儒家自我实现的自由观相反。自由主义者主张,自我实现对于发展令人钦佩的品质和达到理想的人格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当其间存在压抑和折磨的时候,自我实现——如果并非不可能的话——则将更为困难。拥有一种好的生活的图景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类之善,而如果没有选择和机会,这种好的生活的图景将是有限的、狭隘的。植根于代代沿袭的传统和公认的价值之中对于一个共同体的团结是有效的,然而,失去了批判性的审视和有效的选择,它就将是盲目的。
另一方面,与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体权利相反,儒家则忠告我们,即使权利是保护我们自身免受不公正的干涉和随意压制的一种有效方法,但在某些情境之下(例如,当我们面对深爱的家人或共同体中穷困潦倒的成员的时候),这种保护屏障就会被置于一旁。认识到我们所拥有的权利是一回事。然而更为重要的,认识到我们何时应该使用这些权利,以及为了反抗什么而使用这些权利则是另外一回事。儒家会主张,作为权利实践的前提,自由主义者需要优秀的品格与一种好的生活图景。
德性需要保护与批判性的审查,而权利则需要适度和自我节制。儒家社群主义能否将个人的权利包含在其伦理构架之中而不失之于自相矛盾呢?反过来,自由主义能够在其伦理学架构内部容许社群主义德性的存在吗?
三、超越消极自由
消极自由与这样一个问题有关,即“应当为个体留有多大的道德空间使其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受他人(或政府)的干涉”?根据这种对自由的理解,自由就意味着一个人在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中不受干涉。自由主义寻求通过不妨碍他人合法利益的方式来扩展个人选择的范围。根据自由主义的观点,只要没有损害他人或者侵犯他人的权利。一个人就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任何事情。然而,消极自由论者的自由概念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由。消极自由论不能唤起我们对一种好的生活的向往,也没有给予德性、品格和共同体以足够的重视。它没有为帮助极端的贫困者提供一个道德上的理由。此外,在某些不适当的情形中,它承认个体有做错事的权利。如果不干涉是自由的唯一条件,那么,一个慢性的酒鬼与瘾君子或许都可以说是自由的——只要没有人,干涉他们的利益和权利。然而,从儒家的观点来看,他们因其意志的软弱、内在的限制以及相互冲突的欲望而是不自由的。
儒家的自由概念存在于自我克制(克己)与自我实现(成己)之中。它源自人类能自作决定之愿望。作为积极自由的倡导者,儒家希望他们的生活和所作的决定有赖于较高的自我,而不是较低的自我。根据儒家自我实现的自由观,仅仅没有外在的强制还不能算是自由的充分条件。即使公开的选择权是给定的,但是,一个处于欲望的强烈冲突之中的个体还是不自由的。因此,对于儒家来说,要想达到真正的自由,重要的是克服内心欲望的冲突,也就是说,克己、自制以及欲望的价值排序。孟子曰:
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
孟子坚持认为,阻挠一个人获得自由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外在的障碍,而是内在的障碍。按照儒家的观点,消极自由(比如通过不干涉来确保选择权的有效性)的增加,并不能够终止各种相互冲突的愿望之间的斗争。需要的是意义的观念——目标、动机和欲望的排序——一种在价值论上对高和低、高贵和卑贱、好和坏、整体和部分的了解。在价值论上对相互冲突愿望(第二序的)的排序中,可以找到自我实现的可能性条件。各种愿望的等级排序有助于愿望自身的实现,一个人是以其最重要的愿望来建立自我的同一性的。如果自我重大的愿望得到了实现,那么自我也就得以挺立起来。
对于德性的显现而言,克己或自制是一个前提。如果一个人克服了自私的愿望而表现出惠及他人的更高愿望,那么他所展现的就是仁慈:如果一个人克服了自身安全的恐惧而表现出应该表现的,那么他所展现的是勇敢。这样,德性就是一种与增进特殊的人类之善的自由(缺乏内在束缚时)行动相关的优秀品质。因而,对于儒家来说。对相互冲突的欲望的自我克服与品格的修养会自然而然地引导一个人达到自由。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即表达了他在克己、自制意义上所达到的自由境界。
自由主义者强调限制自由的外在的因素,而儒家则强调内在的因素。对于发展一种令人钦佩的品格及达到理想的人格而言,克己或自制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当其间存在压制和折磨的时候,塑造令人钦佩的品格与达到理想人格——如果并非不可能的话——反而将变得更加困难。反之,对于维持一种舒适的生活与保护个人安全来说,开放的选择权和较少的干涉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如果对于相互冲突的欲望没有进行价值论上的排序,那么一个人就会变成欲望的奴隶。缺乏自制的选择权是盲目的,缺乏有效的选择权的自制则是空洞的。
通过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和传统儒家的自由概念之间的相互批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在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的简单选择,而是这两个意义的观念之间存在的一种补充的或者相互支持的关系。完全的自由既包括选择权的最大化,又包括自我实现的最大化。一个自由主义者需要克己与品格之修养,一位儒家主义者则需要有效的选择权以及对这种选择权的保护。
四、超越底线道德
自由主义可以理解为政治上的或道德上的关于权利的修辞学。权利保护个体拥有一个自主和基本利益的领域,因而,拥有权利是件好事。拥有权利,使我们能够“以人的方式而存在”,并鼓励权利侵犯之受害者(或受动者)去愤怒、抗议及采取强硬立场⑩。权利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修改和创造制度的可能性”。
权利的功能在于保护人们的自主与未来的利益领域不受侵犯。然而,在某些不适当的情形中,权利则会使我们对道德敏感性视而不见。在某些情境下,谈论权利并不会使一个人“以人的方式而存在”。反而会“暴露一个人在这个严重麻木不仁的、对抗性的世界中的放纵的粗野”。在某些情境中,对权利过于热心的人们会显得是“执拗的、敏感的、任性的、暴躁的,并且完全还有可能是骄横的”。J.L.马奇(J.L.Mackie)说:“为了责任自身着想的责任是荒谬的,但是,为了权利自身着想的权利却并不荒谬。”如果为了权利自身着想的权利不是荒谬的,那么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维护或要求权利。马奇观点的不足在于它仅仅关心道德的最低要求,而忽视了在某些情形之下为了其它道德上的理由,权利可以被放弃、让渡或牺牲的可能性(或必要性)。
与儒家道德观相对照,基于权利的道德是底线主义(最低限要求主义)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底线主义者,将道德讨论的领域界定在人类经验的一个狭窄的部分。也正是这个意义上的底线主义者。对行为者的道德品格只做最低的要求,对行为者的儒家道德观提出的要求甚少,或者全无要求。基于权利的道德所认为的道德仅仅与斯蒂芬·哈德森(Stephen Hudson)称之为“道德的要求”的事物——权利、义务和责任——相关。道德的底线要求分享着一整套的特征,也就是说,无论这些要求是权利还是义务,它们都是必需的、被要求的、被迫的或硬性要求的。在此意义上,基于权利的道德是将道德解释为一种缺乏个人意义深度的纯粹的约束系统的“外在的道德”。
当通过道义论(deontic morals)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时候,有关权利及其义务的语言包含三种行为:(1)出于责任的行为,或出于义务的行为,或被要求必须做的行为;(2)在既非义务又不被禁止从而是被允许做的意义上的行为;(3)被禁止的行为。权利语言的道德维度(亦即,在道德上是义不容辞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在道德上是被禁止的)是最低限度的,因为它不能将诸如超出职责之外的行为与令人钦佩的行为等这些同样是人类体验中的重要的部分也考虑在内。例如,权利无法要求仁慈(仁);权利不能以其强迫一个人履行(依靠相应的权利来说明的)责任的方式来为仁慈行为提供一个道德理由。安乐哲(Roger Ames)声称:
将人类的权利当作实现人类尊严的一种手段来庆祝当然是夸张的,除非依靠人类尊严,我们就只是赤裸的、或然的存在。用人类权利作为一种衡量共同体内部的可能的生活品质的尺度,就如同将最低的健康标准作为餐馆质量的普遍指标。
按照儒家的观点,道德问题的领域是如此的宽广和多样,以致于按照权利的语言所挑选出来的狭窄的子领域无法包括重要的人类体验的全部范围。儒家基于德性的道德,与自由主义基于权利的道德相对照,是最高要求主义的。这里,最高要求主义的意义在于:人类体验中的一切都具有道德意义,每一个人一生的全部生活都是作为道德境遇而存在的。基于权利的道德所覆盖的仅仅是道德行为中最小的范围(亦即,对的、可允许的、错的),而儒家道德则覆盖人类行为的最大范围。以之作为自我修养的领域。
儒家道德所提倡和忠告的在于。我们的确不限于这些最低的要求。对儒家学者来说,存在许多既不是义务也不是责任,但是在道德上应该得到称赞和肯定的行为。如果有人希望他们自己及其共同体繁荣兴旺,这些行为对他们来说就是值得去做的。这一种类的行为——用哈德逊(Hudson)的话来说——可以称之为“道德智慧的忠告”。对儒家来说,全部人类行为范围中的一切事物都不乏道德意义。儒家认为,道德的整个领域要比其最低的要求更为宽广。作为一种德性道德(a morality of virtue),儒家强调克己、自我修养与自我实现的重要性。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如果今天孔子还活在我们这个迷恋权利的时代,他将会说:“如果人们为权利所导引,他们将毫无羞耻之心。”羞耻是一种因丧失自尊而经验到的情感。有尊严的权利实践需要优秀的道德品格作为其前提。埃利奥特·道奇(Eliot Deutsch)断言,较之履行一种最低的对或错之基准所要求的,圆满的道德行为所包含的内容更多。他是这样说的:
正如艺术作品一样,一些行为的内容要比另一些行为的内容更为丰富……当我看到其他人们的时候,我不只是看到了特定的外形和尺寸、颜色和形态,我也富有意义地看到了各种不同的具体化的人格成就。当我看到一个发生中的行为的时候,我所看到的不只是我以纯粹叙述性的、物理主义的语词所描述的残忍行为的一个片段。相反,这个行为既是行为者的美学向度,也是行为者的伦理学向度之表现、体现及展示,而我之看到这个行为,也正是将其作为此二者之的表现、体现及展示而看到的。
即使道德要求与“道德智慧的忠告”之间存在着区别,我们所要做的也不是在两种不同的道德行为之间做简单的选择。在重建儒学中,道德的这两个向度应被理解为是相互支持和相互补充的,而不是不调和或者排斥的。权利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能够保护基本的人类利益和道德空间,在此空间中。一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和行为。权利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是人类繁荣的最低条件。权利的觉悟对于超出职责的德性(supererogatory virtues)是必要的,因为,若不是与责任、权利及赏罚相对照,超出职责的德性甚至就毫无意义。
然而,对于创造好的生活或者成就理想的人格而言。权利却是不充分的。“认识到一个人拥有权利……并不足以使其拥有令人钦佩的品格,因为这个人仍然有可能是一个从不愿慷慨、宽恕或自我牺牲的卑鄙伪君子。”在道德的最低要求之上,需要增加的是优秀品格、德性的重要性以及意义——各种善在价值论上的排序。
五、以权利与德性的调和为取向
极端的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权利道德与极端社群主义者所理解的德性道德源于太过单一的二分法,并且,这种二分法也绝少考虑到人类利益、愿望、动机和目的的复杂性。一个在某些对抗性的情形中强烈要求权利的人,在另外一些情形中则可能是一个富有爱心、慷慨的人。反过来,在某些关系中,根据权利来谈论事物可能是不适当的。然而,另外一些竞争性或者对抗性的情形中,根据权利来谈论事物则可能会是一个人表达尊严和自尊的一种有效方式。
例如。在一种恩爱的夫妻关系中,如果说“我有和你睡觉的权利”或者“你有与我做爱的义务”。就是不适当的,大煞风景的。反过来,如果我们要求那些被大金融集团剥削的韩国劳工去爱对他们敲骨吸髓的雇主,那么,这种要求所提出的期望则又太多了。
与不承认权利与义务之外的道德理由的极端自由主义者(或者消极的自由主义者)和仅仅强调义务和德性的极端社群主义者不同,坚持理性地重建的“后儒学”(post-Confucianism)对权利与德性、要求与让步、自主与仁慈诸德性的重要性,均给予承认。按照他们的道德理想,一个缺乏仁慈、友谊和感激的社会将是一个令人厌恶的或者不适合居住的社会;而一个不尊重和保护自主、自制与自新之道德空间的社会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和无法忍受的社会。
透过自由主义与儒家关于权利与德性关系的相互批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要么权利要么德性的简单选择,而是权利(作为道德的基本要求)与德性(作为道德智慧的忠告)二者和谐的调和。最低要求论者与对德性抱有热望的最高要求论者,当其结合成为一个道德范式的时候,就将导向一种对于人类发展更为丰富和更为全面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