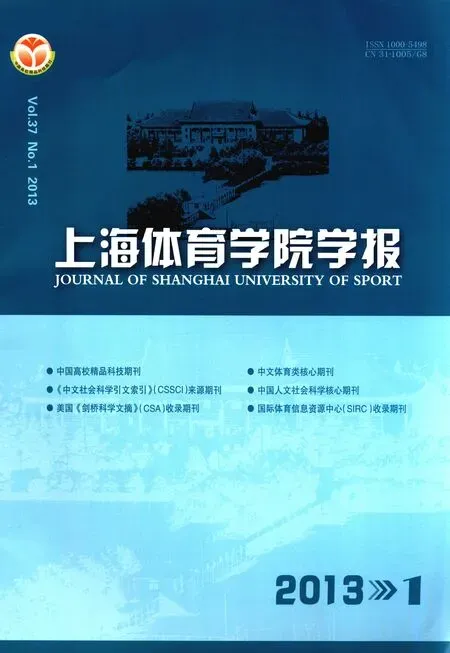民国武侠小说与武术发展的互动研究
刘 靖, 虞定海
(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上海200438)
在当今的文化研究中,有较注重对精英文化研究的趋向,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民间文化现象的梳理、研究。从清末武举制的废除,到民国武术地位的不断提升(尤其是中央国术馆的成立),在这样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中,武侠小说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它是否仅仅是对武术书面语言的故事化表达?它与武术的发展存在何种内在隐性关联?本文拟从这些历史文化发展及其交互影响的过程中,寻得一些线索进行考察和探索,以期对上述现象有所了解。这对于探究民间文化内在的交流和互动,深度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之路,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 民国武侠小说之概说
“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1]。如果说中国上层精英知识分子的躯体中都隐藏着儒的影子,那么中国民间百姓的意识深处则显现着侠的影子[2]。武侠文化中深藏着民间社会对生命的渴望与憧憬,并激发着他们在困苦中生活下去的勇气。对于武侠文化的主体表达形式——武侠小说来说,“揭示近现代武侠小说中所积淀着的文化内涵,为研究民间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中国大众文化特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2]。武侠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是我们探究民间文化“基座”的根柢,对我们了解民间社会的隐性力量有着独特的价值。
虽然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早就在传统的通俗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其文化价值的高度提升,可谓是一现代的现象”[3]。直至清代,从《三侠五义》出现开始,武侠小说的发展开始繁盛起来,到了民国,更是达到了高潮。有学者谓: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武侠小说百花齐放的年代[4]。
民国武侠小说显著的特征为作家阵容庞大、作品数量多,并借助于当时已较发达的报刊媒体,以连载的形式谱写了武侠小说的高潮。“专门以写武侠小说闻名的作家多达几十人,而武侠小说著作有200多部”[4],并且已经逐渐形成了独自的风格和流派。“至20世纪40年代,南北武侠小说家多达170余人”[4],较出名的有向恺然、赵焕亭、顾明道、李寿民、郑证因、宫白羽、还珠楼主等,其中具有“南向北赵”之称的向恺然和赵焕亭最负盛名,其作品影响也最广泛、最深远。
2 民国武侠小说与武术发展互动之背景
2.1 小说成为倡“新民”之方式 鸦片战争后,列强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西方思想逐渐传播开来。仁人志士们认识到要救中国于衰亡之中,必须唤起民众的存亡意识,并进行国民思想的革新。革命启蒙家梁启超[5]主张:“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认为,小说除了“文之浅而易解”外,更重要的是“以赏心乐事为目的者固多”,能够“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这其中有“熏”“浸”“刺”“提”4种力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使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之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此四力而用之於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於恶,则可以毒万千载”。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5]。
梁启超极力宣扬小说的“新民”作用,其最终目的为“改良群治”,振衰起弊于颓废国势。当时报刊、杂志等近代传媒从西方传入中国,使得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有了更为广泛传播的可能,并能够直接与大众对话,为大众的“思想革新”创造了条件。梁启超极力提倡创办报馆,他利用报纸等媒体,改变了以往的文学形式,创造出“报章体”,对当时的小说创作影响巨大。小说在文学界的地位开始逐日上升,以往被轻视的传统观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6],被认为是具有革新社会、启迪民智的重要文化媒介。
与之同样忧国忧民的我国文坛巨匠鲁迅,在学医救人的路上,意识到了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可怕,以至于决意“弃医从文”,立志以小说等文学形式的创作来唤醒国人,一改国人萎靡之精神状态,达到“新民”之效。从新视角对小说的解读,赋予了它更多的内涵和使命,为小说的繁荣营造出极佳的思想文化氛围。
2.2 武侠小说成为尚武之理想路径 清末,被用来指称包括中国在内腐朽体制的“sick man”一词,被志士们作为唤醒大众的“口号和工具”,来形容中国人身体“不堪一击”的病态现象。一时之间,中国人“病夫”的形象广为流传,并逐渐激起国人“集体的羞耻”,进而“一雪前耻”[3]。
此间,严复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引入中国,其主要观点为“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7]。“强种强国”的观点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那么对于国人“病夫”的身体和颓废的国势,何以强国强种、去孱除弱呢?
借鉴日本的武士道,宣扬尚武精神是许多仁人志士的主要观点。“彼日本崛起于数十年之间,今且战争世界一强国之俄罗斯,为全球所注目。而欧洲人考其所以强盛之原因,咸曰由于其乡所固有之武士道。而日本亦自解释其性质刚强之元素,曰武士道。于是其国之人咸以武士道为国粹……吾中国者特有之而不知尊重以至于消灭而已”[8]。在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中,列举了数十位足以体现中国“尚武精神”的武士道者,这其中也包含了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朱家、剧孟等人。他认为中国自古就有尚武之风,就有侠客的存在,而近日中国衰败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在封建专政统治下遗失了“尚武之风”。
这些思想在当时社会引起了极大共鸣,为武侠小说同武术的互动创造了条件。“武侠却是可爱的,他懂社会,他有神情,他能作出人家想到而作不到的事”[9]。“侠文化在本质上是人们回归原始之梦的一种实现方式”,它“以替代满足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回到原始状态的途径”[10]。在“国势垂危,人民不武”之际,武侠小说能“唤醒国魂,表扬武士道之精神,以期发扬蹈厉,一湔此东方病夫之耻云尔”[11]。可以说,武侠小说不仅是人们闲暇时的消遣方式,更成为人们“扬眉吐气”“呼唤尚武”的“理想路径”。
3 民国武侠小说与武术发展之互动实践
3.1 武术与武侠小说的双向融汇 自清末以来,受武举制的废除以及庚子拳乱的影响,武术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从武术之主体人的层面上来说,那些“耍枪弄棒”以江湖卖艺为生的武术大师,都属于社会下层。他们顶多成为文学作品中侠客主角的素材,也鲜有能以文字论说,为自己立传为武术正名[3]。善于写作的儒者对侠的崇拜仅仅为一种“暂时性的,从现实中求解脱的文人侠客梦”[12],他们很少或者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武术。以至于武术在民间的观念仍旧是“杂耍”或义和团中玄之又玄的“神拳”,或鲁迅口中“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13]。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来诠释武术并提升其话语权就显得非常迫切了。
相反,具备一定的武术知识也被认为是写“真正”武侠小说的基本要求。笔名杨六郎于《立言画刊》谈武侠,他认为在武侠小说众多分类中,如果不懂文字上的“武术”,忘了打,仅仅以“刀快血多”来描写情景场面,“这样不像回事呢,便只好以一个女的作中心,弄成英雄儿女,算是凑和着说是侠情小说,因为若刨去‘刀快血多’,便直与言情小说无异”[9]。要想写出武侠著作,那就须满足“武+侠+小说”的要素,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武侠小说。
民国许多武侠作家通过习练而体悟武术,在作品中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宣扬了武术,同时也满足了写作武侠小说的要素,使得对人物的刻画更入木三分,此概其作品为后世所推崇的原因之一。两者在这样交互影响的情境中,形成了双向融汇的关系。“在民初能文能武的习武者中,能够非常成功地宣扬技击之术的代表首推向恺然”[3],他因红极一时的武侠小说《近代英雄侠义传》而为人所知,其作品中闪现着对武术的真知灼见,为人们在赏读之余普及了武术知识。他在早年留学日本时,即向武术家王润生学习拳术,1915年回国,加入中华革命军,并致力于武术发展。他的武术理论功底深厚,著有《拳术见闻录》《拳术传薪录》《拳经讲义》等。1932年,他在湖南创办国术训练所和国术俱乐部[4]。可以说他在武术的传播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作品仍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1923年,收有大量武术知识,对武术的价值及其理论进行阐述的《国技大观》出版,本书的主编就是当时知名的武侠小说家姜侠魂。同梁启超对于侠的观点相似,姜侠魂认为“吾国民众普通体育(武术),源于黄帝征蚩尤之先”“强种保国唯我独尊之技术”等[14]。时下,武术能够强国强种、洗刷病夫之耻的观点开始流行,这也成为国术爱好者宣扬的主要论调。
3.2 武术与武侠小说书写国族英雄谱系 民国武术发展迅猛,流派林立,许多具有民族气节的武术名家成为武侠小说中的原型。如杨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孙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等。同时民间出现了如霍元甲、王子平、蔡龙云这样勇于同洋人挑战比武的武术家,“他们振兴国威,强国强种,唤起民众的爱国精神,也为文学作品中产生众多侠客形象起了促进作用”[4]。
受时代的影响,民国武侠小说在思想内容、武侠元素及艺术观念等方面凸显了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在连接当代武侠发展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他们在意识形态上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结构思路上突破了以清官统领一切豪俊的创作思路,将武侠小说从古代‘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通过大量的奇闻轶事构成了一个“英雄世界”[15],进而参与了国族英雄谱系的书写。
国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发明”“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16]。S.Anthony[17]也指出:在族群团体迈向国族建构的蜕变过程中,为了强化群体的凝聚力量,一方面要提供群体成员自我认知的地图,另一方面更要从族群的历史记忆中发掘过往的英雄人物与光荣事迹,作为国族成员仿效师法的道德典范。在国族主义史观的鼓动下,从晚清开始出现大量民族英雄,着手建构中国“国族英雄谱系”。其中民国武侠小说在“唤起国魂”“振兴民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叙事象征作用,成为建构之一环。
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武术名家之所以能成为武侠小说的原型,并参与国族英雄谱系的书写,其根本为他们通过其高超精湛的武艺,为读者呈现了浓郁的“黄帝贻我子孙”而“现今澌灭殆尽”了的“尚武遗风”,其匡扶正义、除暴安良的武侠形象成为民族的守护神,并激荡了国人求生存、求富强的信心。
在寻源、创作、刊出等一系列动作中,武术名家们作为“国族代言人”,通过武侠小说这一载体,在其文化消费和口碑相传中不断流传、延续,直至深入人心。“民族英雄”来自于有史可查的真人事迹,无形之中增加了“国族英雄谱系”书写的可信度,以便不断凝聚国人为民族奋斗的信念和决心。如霍元甲、王子平等这些“国族英雄”符号一直延续至今,仍激发着后世子孙们敬仰效法。
3.3 从读武侠小说到练武术的效仿与转化
3.3.1 武侠迷的产生 发表在民国报刊上有关武侠小说的片段完全可以反映当时人们痴迷武侠的程度。这既是对梁启超所称的“熏”之力“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之为摇颺,而神经为之营注”的最好注解,同时也造就了大量的武侠迷。著名作家张恨水[18]回忆自己写连载小说《啼笑因缘》时称:“报社方面根据一贯的作风,怕我这里面没有豪侠人物,会对读者减少吸引力,再三地请我写两位侠客……我只是勉强地将关寿峰、关秀姑两人,写了一些近乎传说的武侠行动。”
在国势颓废的形势下,人们期盼“英雄侠客”的出现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英雄们侠肝义胆的光辉形象便烙印在读者的心中而挥之不去。民国的武侠小说恰如梁启超所言,确实有如此的“熏”之境界,能够摄人心魂,“操纵众生”。民国后,“武侠小说风起云涌,几乎占了小说出版数量的大部分”[19]。
3.3.2 武术迷的产生“提”之力,较“熏”之力则更进一层次,它“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读《野叟曝言》者,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言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其“文字移人,至此而极”,“度世之不二法门,岂有过此?”[5]小说的“提”力,功效深厚,能使读者化身小说主人公,产生“移人”“度世”效应。依据武侠小说的特点,其“提”之力则更易显现。
在受到武侠小说“熏”力后,读者(尤其青少年)在武侠小说“提”之力的影响下,为了获得主人公“技艺超群”的绝世武功,成为救世的大侠,继而行动起来模仿主人公去“峨眉学道”,行为痴狂,成为武术迷。这足见民国武侠小说已经开始深入读者脑髓,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犹如当今许许多多的习武者,深受武侠影视剧的影响而赴少林寺学道修炼。这是他们内心“渴望回归”“获取自由”“与自然同一”的真实写照。
在“熏”“提”力的影响下,完成了由纸上到现实的效仿与转化,唤起了相当部分受众(青少年)习练的兴趣。对武术的追捧,又反过来催化了“武侠观念”的流行,因此而要为之负“有力诱因”的责任[20]。在这样的循环作用之下,对他们加之有效引导,振兴消失殆尽的“尚武之风”,何尝不能恢复中华、强国强种呢?
3.4 武侠小说神化武术之误导 当武侠小说引起读者行为效仿的同时,对其批判的声音也不绝如缕。“现在人人爱看武侠小说,报章、杂志没有武侠小说,当然不受人欢迎”,但武侠小说不能离开“人情”,“如果都写成剑仙下凡,举手就一道白光,便可取敌人的性命……,但是千人一面都写成这个样子,大概要使读者都有了神经病的可能”[21]。这些评论者对武侠小说光怪陆离的武技渲染效果不满,其本质是小说描写过于虚夸而脱离了武术技击这个根本,脱离了人身体能力(即人情)这个基本限度。
化君在《时时周报》中就以《国术与武侠观念》为题,抨击“武侠观念”促使人们奔赴“深山学道”这样的“把戏”,是一种“自慰式的梦想”。他认为武侠观念“看来是积极的,是颇适合于目前委靡国人的良药,但仔细研究一下,却是中国民族的毒剂,至少是麻醉剂,不安于现状的人们,并不在实际中找出路”,读者“以为不久就会有取人首于百步之外,能撒豆成兵的英雄出现以及帝国主义的压迫终必消逝,而中国也就随意地杀死民族的仇敌了”,而呼吁当局禁止武侠观念[20]。这一方面表明民国时期武侠小说对国人生活影响之深,另一方面,武术则被武侠小说过于虚幻的、超乎寻常的叙述手法神化,遮掩了其真面目。诸多青少年们由“武侠迷”转化为“武术迷”而往峨嵋学道,大概也是中了想象中武术之“刀光剑影”“飞檐走壁”的“毒”。纵然,他们能够抵达“峨嵋”,到达“武当”,但在现实世界里他们又如何才能够练成“撒豆成兵”的奇幻武功呢?
毫不掩盖,武侠小说在重振尚武精神的作用显而易见。诚然,武艺被描写得再高明、再神奇,难道真的如《续剑侠传》编者郑官应所说的那样,要靠这种“剑仙”去逐“异端”、克“强敌”、救中华民族于不坠吗?在化君的论说中,虽揭露了当时武侠小说中存在的“脱离‘武’实际”而过于怪诞的普遍现象,但整体来看仅仅“浮”于人们深受所谓“毒剂”之害的影响,而未从有效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以至于要直接取缔“武侠”。
3.5 武术对武侠小说误导之回应
3.5.1 武术的科学化传播 国术(武术)不仅为“我先哲所创”的固有传统文化遗产,重要的是它可以“强健身体”,使国家“转弱为强”,更能消除大众亡国灭种的恐惧感。志坚在其《武侠小说的影响》的评论里分析到:“一部分的年轻人所以会相信武侠小说(中剑仙等绝世的武功),甚至于离家出(逃)亡,主要是他们缺少(武术的)科学的知识”“对于一般青少年,应当多多灌输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知识,使其认识社会,了解自然现象”“以严格的精神训练及体格训练,养成一种坚毅、勇敢、奋斗的性格”。他最后呼吁道:“我们固然知道武侠小说的毒害,但是最要紧的,我们要根究这种毒害的社会原因。”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不但要找出其社会的根本原因,更要紧的是能因“武侠熏提”之势而利“国民学武”之导。
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也清楚地认识到,无论如何发挥武侠小说的社会效应,如何提倡“尚武”的必要性,都无法将“四万万病夫”转化成为身强力壮、能征善战的正常人。“这不仅仅是思想文化价值的改变,更需要长远且具体的社会教育等多方面改革”[3]。面对社会的现实需求,及社会思潮运动的不断涌现,对武侠小说所造之“流毒”进行疏导,即武术的科学化研究和传播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了。
3.5.2 “集体复制”之组织化传播 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俄国大力士履行了霍元甲提出的离开天津并不在中国内部卖艺的要求后,霍元甲叹道:“这算是什么!我虽则一时负气把他逼走了,然他在演台上说的话(中国是东方病夫国),也确是说中了中国的大毛病。我真想出来竭力提倡中国的武术。我一个人强有什么用处?”[22]在这样的民族主义意识考量下,霍元甲清楚地认识到:要洗刷“四万万同胞”的“病夫”耻辱,必须提倡强身技击之术——武术,但仅凭“一己之力”万难做到,若要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意识且投入这项民族主义身体运动中,具有“集体复制”效果的武术社团之成立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样的强烈呼声中,在民间拳师“城市”流动的趋势下,武术家们开始尝试打破门户的约束,来到都市(报刊等也只有在此才能流行)组织武术社团,倡导用西方科学思想研究和推广武术,从而开始了武术的现代组织化传播之路。
要论及武术的组织化传播,则必须提及官方武术社团——中央国术馆。最高管理机构中央国术馆“顺民众之意,应民众之需”“应时势之要求”于1928年成立[23]。它以“研究中国武术、教授中国武术、编著关于国术及其他武术之图书、管理全国国术事宜”为主要任务[24],力图全民国术化、国术科学化,并消除宗派畛域,“冀以涤除东亚病夫之恶谥,振起民族固有之精神”[25]。
在中央国术馆的带领下全国形成了上下贯通的国术馆系统。“至1933年的统计,当时已有25个省、市建起了国术馆,县及县以下国术馆(社、支社)数量尤多”[26]。它的目的不是“造就许多出类拔萃的武术名家”,而是“希望人人要国术化,有尚武的精神”,使中国“成为最健全的国家”,并把国术“发扬光大”[23]。它面向社会招生,开设研究班、教授班、练习班及女子练习班等[24],出版了大量的国术书籍,并创办《中央国术旬刊》(后改名为《国术周刊》)。各地方国术馆也纷纷创刊,向民众宣扬国术。囿于国术师资的奇缺现状,1933年又在中央国术馆内附设“体育传习所”,随后又改称“中央国术馆国术体育专科学校”,专门培养“国术”和“体育”师资,在学校及军队等多重渠道进行推广。
中央国术馆以消除门户之见为己任,凭借国家力量,其组织体系延伸到社会组成的最小单位——村(里),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全民国术化”。这也一改武侠小说中的“门派争斗、武技神秘化”的隐乱状况,成为疏导青少年因缺乏基本的国术知识、“学道无门”,而造成的“武侠毒害”的实践路径。它积极提倡国术的科学化研究、两次举行国术国考等,这些举措极大地提高了国术的地位,加快了国术现代化进程。
4 结束语
任何相关文化的互动不可能是均衡的,必会有其主动和被动的重心偏向,且总处于动态辐射状的发展趋向中。民国“武侠小说”之武侠观念在社会中的流行已引起极大关注,借助其显著的“熏”“提”之力,予以积极、有效引导,在持续“四万万病夫之国”的身份强化之下,应成为促进国民身体强健的更大动力。有关国家身体控制与民间文化的互动研究,是需要进一步深思的课题,理应引起当下民国研究者的关注。
[1]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9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412
[2] 陈山.中国武侠史:引子[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2:2-3
[3] 杨瑞松.身体、国家、侠[J].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3,10(3):25-103
[4] 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86-94
[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M].上海:中华书局,1989:13
[6] 丁善贤.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叙述艺术[D].苏州:苏州大学中文系,2003:1
[7] 严复.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5
[8]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四:中国之武士道[M].上海:中华书局,1936:2
[9] 杨六郎.谈武侠[J].立言画报,1943,25(9):15
[10] 赵言领.从侠文化到类型小说:武侠小说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5
[11] 周超然.武侠奇闻[J].社会之花,1925,18(2):1
[12]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5:281-282
[13] 鲁迅.拳术与拳匪[J].新青年,1918,6(2):566 -567
[14] 国技学会.民国书业第四编:国技大观[M].上海:上海书店,1990:17
[15] 宋琦,周俊.论武侠小说结构模式的变迁[J].当代文坛,2010(2):75-76
[16] Eley G,Sunny R G.Introduction:From the Moment of Social History to the Work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7
[17] Anthony S.National Identity[M].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1:65
[18] 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45
[19] 范烟桥.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民国旧派小说史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312
[20] 化君.国术与武侠观念[J].时时周报,1931,2(16):247
[21] 清风客.谈武侠小说[J].立言画刊,1943,26(6):11
[22] 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4:60
[23] 谭组庵.国府训话[G].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2008:387-388
[24] 中央国术馆.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G].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2008:405-411
[25] 蒋中正.中央国术馆汇刊序[G].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2008:383-384
[26]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338
——以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为中心